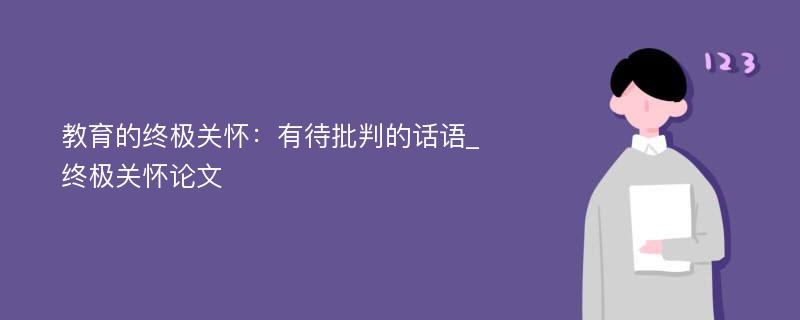
教育终极关怀:一个需待批判的话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lOOO.-2359(2004)ol-0165-03
教育以开发人的精神为旨归,引导人去过幸福生活。教育就是对人的终极关怀。谈教育终极关怀似乎是一个“假问题”。事实并非如此,现代教育充满了工具化、功利化、规训化、异化等因素和气息。终极关怀失落了。教育终极关怀确实在中国是一个真问题。然而,呐喊了近二十年的教育终极关怀遇到了尴尬:终极关怀总“怀才不遇”,实践总“有眼不识泰山”。看来,教育终极关怀在批评当代社会和当代教育的“缺陷”的同时,对自身的反思尤为重要。
一、教育终极关怀的局限性分析
(一)教育终极关怀“完美性”的局限
教育的终极关怀,是对人的最大的尊重,它排除了教育异化。但是,教育是“矢量”,引导人成人,这就决定了教育对人做出“不人道”行为——对人的发展和自我建构造成一定的“限制”。专门化、制度化教育将这种“不人道行为”推向顶峰。教育异化出现了,但这是教育的“定数”。“物物而物于物”。我们要求教育使人自由发展,但教育总限制人的自由发展。这使我们从主体自身出发去思考问题的终极关怀的习惯很不适应,自然就产生了所谓的教育异化。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去创造物时,我们同时也被物所创造,我们就不会觉得异化或者其他类似的失望是个问题。异化是人发展的条件,无异化的发展和无发展的异化是不理性的。依此,无异化亦无发展。放弃了异化,就放弃了发展,也就放弃了教育,更不用说终极关怀。我们能做的是尽可能地减少异化而非克服异化。
教育终极关怀关怀活的人,活的教育。但是,活的东西是有限的。这是活的教育和活的人存在的真正的客观基础。因此,活的人和活的教育也就总是有缺陷的。死的东西和死的人是无限的,可以达到完美,可以进入“极乐世界”享受“恩泽”。如是,终极关怀性教育恰是死的教育,关注的是死的人。活的人永远是生活中的有各种各样“缺陷”的人,扮演着各种各样社会角色,是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军人等。他们总是终极关怀驳斥的那样“目光短浅”、“看重实惠”。所以,关注活的人的活的教育要“目光短浅”、“看重实惠”(为社会培养目前急需的各种各样的才、“器”)。教育似乎无法与所谓的“和谐自由发展的本真存在的人”达成协议”,更不用说“默契”。
教育终极关怀以其“睿智”洞察出了教育现代化的“毛病”。但是,以之来克服与根治这些“毛病”确是不智之举。教育终极关怀“完美性”要求教育要批判的继承,集众所之长,“熊掌和鱼兼得”。可是,这种“完美性”建立于分裂性思维之上,即它通过破坏作为整体有机的教育来实现一种非有机体的总和。虽然,它一直一再强调“有机的整合”,但真正的有机的整合是创造出新的有机体。在新有机体中,新的精华会出现,原来的“熊掌”、“鱼”可能会“非其所是”,精华可能会是糟粕。对精华的“革命改造”与对精华“局限”的分析才能称之为有机的整合。要优点不要缺点的由被分裂的文化碎片所组成的教育终极关怀肯定弱于完美。由于缺乏一个可以依赖的有机的“根”、“家”,它肯定“四处漂泊”。最终,我们没有建立起适合中国特色的有机的教育。教育理论还在借自己的“嘴”说”别人的“话”。一方面呐喊教育要现代化,另一方面又驳斥教育现代化中的“毛病”。这正是教育终极关怀“完美性”的二律背反。教育终极关怀让我们不能知道中国教育如何现代化,中国教育如何走向。
(二)教育终极关怀浪漫化的局限
教育终极关怀要求以对人的生命、情感的终极关怀“拯救”教育的“生存危机”。审视时下教育,流落出浓浓的浪漫情感和情怀的体现终极关怀的教育话语随处可见。但是,它“导致了我国目前教育改革的理想化色彩浓重,是一种情绪化的反映”[1](P33)。情感大于理性给教育改革和研究带来了普遍浮躁倾向。充满热情、渴望、激情的教育终极关怀最容易使人激动不已,一呼百应。教育的不理性行为就更多:教育理论“诸侯割据”,草率出新,“贵族化”倾向布满。情感大于理性的教育终极关怀放弃了对教育的理性思考,一厢情愿,难怪“教育学迷惘了,教育迷惘了”。教育终极关怀反对功利化的趋向,然而,情感大于理性,教育终极关怀下的教育创新和思考恰恰成为肤浅、投机取巧的“遮羞布”,正是为“稻粱谋”的呐喊。这种尴尬情形恐怕是教育终极关怀始料不及的。它导致了时下教育的混乱不堪:理论的“繁荣”和思想的贫乏,实践的难为与不为。情感大于理性教育终极关怀自身就没有了自己的思想支撑点,成为“浮萍”。这种现象使人联想起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其未对中国文明文化进行彻底反思,反而套用西方“强大先进”的理论,造成了传统的文明文化彻底粉碎而新文明文化未能建立起来的一片混乱,各种理论也没有在中国“着床”。
教育终极关怀浪漫性总是希望现实教育“如此这般”。现实教育从来就“不好听话”。教育史上的各种教育都是那么的“差强人意”。教育终极关怀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当代的问题令其更加“头痛”。现实教育的“危机”与终极关怀间的矛盾对立使得教育终极关怀“分娩”了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哥白尼式”的教育家卢梭,也成就了雅典城邦的“牛虻”的苏格拉底。但现实教育依然“我行我素”,“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举世皆浊吾独清”。拯救教育“生存危机”变成离开现实教育。
(三)教育终极关怀人道化危机
教育终极关怀要追问教育如何成就人的最高人生价值和意义,要关涉人的美好生活,它是人道的。教育终极关怀要求教育去培养过幸福生活的人,但它极易成为“只有在终极关怀的指引下人才能实现自我,成为本真的人,获得最大自由、幸福与尊重”。教育终极关怀中潜隐着人道化的危机。“教育终极目的是衡量各种具体目的的最终尺度”,“代表着人类自身发展和完善的最高境界”。然而,终极目的、最高境界从何而来?它是受教育者个人的最终目的和最高境界吗?“它乃是某些人(理论家、教师、家长、决策者等)基于自己的欲望、理论、自我投射(ego projection)或者说宗教情感而想象出的世界状态。”[2](P85)这样,生活中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被按这样去培养而非自己,特殊人都要向大写人去靠近。“大写的真善美是先于人、独立于人而存在的,人生的极致只能是通过不同的方式静观这些实在。”[3](P75)理论上的人道化却归于反人道化。
“终极”是建立在“根顶式思维”之上的,它虽不等于终极真理,但在“唯一性”、“终极性”、“本源性”意义上,两者是相通的。教育终极关怀已显示出了它的“霸权野心”,它对与之相左的教育倾向采取“镇压”。教育终极关怀的话语已经演变成当今教育中的唯一话语。它限制了教育的多元发展和健康发展,“万马齐喑”,“百家争鸣”不“在”。若说存在“百家争鸣”,那也是“家族内部”争吵,是“家务事”。它将追求现实教育的价值超越转化为追求一种“教育终极(绝对)价值”。它使我们对教育发展缺乏历史性考察、发展性思维,导致教育的僵化,阻碍教育的改革。
教育终极关怀关怀终极意义的价值、目的。在此意义上,它体现了一定的“彼岸性”。“彼岸性”的危机是很容易遗忘生活和人。教育终极关怀是我们向往的“完美”的状态,要批判现实教育。翻阅教育书刊杂志,“谴责”和“抱怨”之声不绝于耳,否定多于建构,大有“不破不立”之势。然而,由于其是“世界之外的退想”,教育现实和现实的人在一片“怨声载道”之中被“搁浅”。“与彼岸世界至福的闽苑仙境相比,此岸世界只是泪槽”[4](P42)。
二、教育终极关怀的重新定位
问题的关键是,教育终极关怀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什么样的警觉是有意义的,什么样的对教育的“缺陷”的警觉是无意义的。
“人是在在世之中的存在。”对人的任何关怀都不能脱离人的处境,否则,无异于“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教育终极关怀对当下的教育超越应扎根于具体的历史的教育之中,是现实教育孕育出的力量。立足于现实教育,思索教育对人生的意义,教育人去追求自己的健康非“完美”生活,那么,教育终极关怀看似抽象、脱离当下,实际上切入的正是现实教育。教育终极关怀总是和教育的理想以及人的理想联系在一起,“真实的理想并非应该是现实的,而乃是现实的,并且是唯一现实的东西”[5](P247)。“现实中也有比理想更好的一面。”[6](P231)现实教育中蕴含着大量的“理想因素”,现实总是不满足于自身,总想使自己“现存世界革命化”。只有充分挖掘现实教育的“理想因素”,才能成为有根的终极关怀。这样的教育终极关怀“从本源的意义上来理解,乃属于此在的基本状况”[7](P112)。这样,教育终极关怀就是现实教育中孕育的对教育的现实的关怀。它产生于现实教育,并服务现实教育。它“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现实教育中的人总是讲“功利的”,追求效益的,希望尽快将自己变成某种适合自己和社会的“才”,教育应该“功利”地去关注人,使其迅速成为人才以满足人的“功利”需要。这是活的人和东西的最大要求,因为,活的总要成为“死的”。但是,教育现实的“理想因素”又不允许自身为功利所役。作为人,他首先要活着,他必须是讲功利的,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更使人应讲功利。但人之为人,又有超功利的人生意义的追求,在功利化极强的生存中,人更应该追求超功利。人不仅是功利的,还是超功利的,而且,功利越强,超功利越强。关怀完整的人,就应关怀人的功利性,引导人去追求功利;同时,又要防止人陷溺于功利。所以,教育终极关怀以功利为前提,内含着功利追求。不含功利追求和克服功利化的教育终极关怀却不是对人的完整性的关怀,不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就教育终极关怀教人更好的、最优化的追求功利而言,教育终极关怀就是教育的功利追求。
既然教育终极关怀与教育功利追求为伍,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缺陷”就不必“大惊小怪”,应视之为正常。教育要有所为。问题在于敢于正视和面对教育现代化中的问题。现实教育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是教育终极关怀的切入点。“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8](P289-290)靠传统教育来解决,显然不行;用西方教育来审视和观照中国的教育现代化的问题不是办法;靠中西结合,理论融通,更是不行;因为这些都是建立在破坏有机体的基础上。教育现代化的问题最终通过教育现代化自身“革命化”来求解。中国的教育问题要通过自身文明文化的转型来解决。我们的任务就是寻求中国教育自身创造性转型的力量、因素和途径。这才是教育的“终极关怀”和最大关怀。在这个意义上,为了教育更好、更健康的发展,目前我们倒是应该“偏爱”现实教育的功利化、工具化,以确保两者均衡发展、相互共存。
标签:终极关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