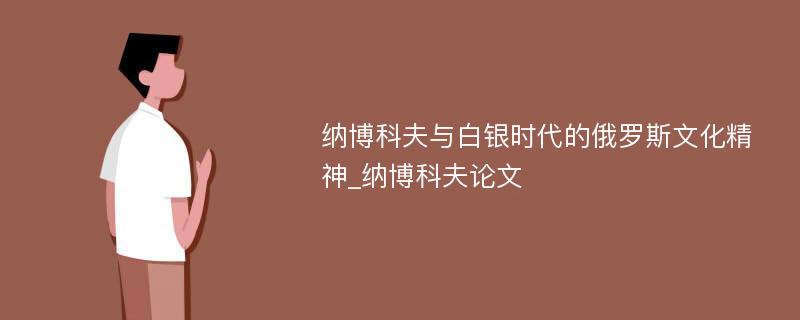
纳博科夫与白银时代俄国文化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精神论文,时代论文,博科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个俄裔作家,俄国文化精神尤其是白银时代俄国文化精神在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身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对于理解纳博科夫及其作品来说,白银时代俄国文化精神是一把必不可少的钥匙。作为一个作家,纳博科夫个人特有的感知方式是在白银时代这一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而这种素质和心理范式始终贯穿于他的全部创作中,成为构成其创作独特性的根本因素。此后的创作,不过是一个胚胎的生长过程罢了。白银时代俄国文化精神对纳博科夫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作家的选题、立意、审美表现方式和世界观类型上。
此文中,笔者主要根据作家纳博科夫与之呼应的几位俄国作家及其所代表的俄罗斯文化精神为经,探讨白银时代文化精神对作家纳博科夫在世界观、美学精神、艺术理念和诗学特征方面的影响,并以此建构解读纳博科夫的阐释路径。
一、纳博科夫与俄国传统现实主义
纳博科夫作为一个青年诗人在俄国文坛崭露头角时,白银时代已接近尾声。此后,持续整个20年代的文化(文学)大论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无产阶级文化与非无产阶级文化等)轰轰烈烈进行时,纳博科夫却是在英国和德国度过的。自1919年出国后,纳博科夫和俄国已经不再有任何外在的联系。但俄国文化精神已经在他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这烙印如胎记一般是个人意愿所不能去掉的。正如纳博科夫所说:俄国浪漫主义诗歌……“曾是我童年的祭坛和激动”(纳博科夫,《说吧,记忆》78)。又说:“我现在自认为是曾当过俄国作家的美国作家”(纳博科夫,《说吧,记忆》68)。纳博科夫在国外从事的俄语创作,对于理解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作家自己就说过,如果不研究他的俄语著作,那么,要理解其英文著作(《洛丽塔》等)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诚如作家本人在早年的一首诗作“俄罗斯”中所说的那样:“你曾是并仍将是……一个由荣耀和云烟组成的神秘国度。而当星空在我头顶闪烁,我能听见你不息的诉说!俄罗斯,你就在我心中!你是目的和山脚,你在血液的奔涌中,在理想的飞升中!在这个多歧的世纪我竟会迷路吗?不,只有你依旧在为我照明”(纳博科夫,《弗·弗·纳博科夫作品选集》6)。他还说:“作为一个盲人,我擦抹双手,通过你——我的祖国——触摸整个地上的造物。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幸福”(纳博科夫,《弗·弗·纳博科夫作品选集》7)。
那么,俄国文化中究竟是什么思想、什么人,怎样一种精神范式,文化理念,对纳博科夫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呢?纳博科夫在其创作的早期(柏林时期)以俄国传统现实主义作家特别是布宁为楷模,这是作家的学徒期。此期他写了大量短篇小说,后结集为《乔尔巴归来》等小说集。其短篇小说中“委屈”一篇是题献给伊·布宁的。这篇短篇小说和布宁以俄罗斯乡村为背景讲述少年精神体验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具有互文关系。这些短篇有:“初恋”(1890)、“杜鹃”(1898)、“别墅”(1895)、“遥远”(1903)以及“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中的某些细节。
纳博科夫小说“委屈”的主人公是一位少年,叫普嘉·希什科夫。小说是对这位孤独少年心理的研究和分析。这篇小说带有强烈的抒情性。小说只写了主人公普嘉·希什科夫一天的生活,全篇洋溢着浓烈的抒情气息,详尽描写了小主人公的印象、思绪、情感、回忆。小说遵循传统叙述方式,情节发展层次井然有序,事件展开以因果关系为轴。情感发展构成小说的情节主线。这篇小说写了小主人公所感受到的委屈从开始、发展、成熟、突变到释然的全过程。小说以一种精细入微的印象主义笔法描写了主人公情感发展的经历。标题犹如一个定音叉,暗示了作品的体裁特征和抒情性质。全篇都从小主人公的感受出发落笔。情感成为小说的真正“主人公”,而情节反倒只具有辅助作用。主人公普嘉一天中的每一刻,都具有独立价值。这些细节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们是用来表现人物的,而且还因为主人公的情感和印象与之密不可分。其独立存在的意义端在于此。
在此,布宁小说是纳博科夫取法的典范。布宁小说中特有的抒情心理小说法则,落实到细节的情节展开技巧,从日常生活和审美中性事物中发现诗意的能力以及穷尽一切方面的全面描写的追求等,都对作家纳博科夫有很大影响。因此,小说“委屈”是大师与学生的一场对话。在大师布宁笔下,生活中没有什么是丑陋和不体面的,就连门的吱扭声、公鸡打鸣、粪堆的臭味也富于生活气息。同样,在纳博科夫笔下,从小主人公眼中看到的世界,也是那么充满诗意、那么生机盎然。小说一开始,描写小主人公坐着马车前去参加一个命名日。他被迫和车夫坐在车辕一侧,随着马车的行进和颠簸,一个个日常生活、自然风景的画面依次如电影中的镜头一般展现在他眼前。小主人公平和的心境渐次被打破,预示着委屈的即将出场。伴随着小主人公的感受的,还有“象征的地平线”,小说的主题渐次清晰:即一个少年如何进入和接受社会:在“我”和“他者”之间建构理解和信任的桥梁是多么艰难啊。一个少年穿上社会服装学会行为礼仪和游戏规则居然会这么难。可是,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要使自己获得社会的承认,同时又不至于失去自我,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小说贯穿了儿童与成人、内心和外部世界的双重对立。前者童真且接近自然,后者成熟却不乏造作。普嘉前去的是一个于他而言十分陌生的社会。普嘉心地坦诚、胸无城府,而那里呢,却有一种游戏法则在统治着一切,它规定了每个人应当如何说和如何做。在这个充满戏剧规定情境意味的环境里,普嘉在他人眼中是一个还没有学会自己角色的小家伙。所以,穿过森林的路走完后,普嘉心境的平和也就不复存在了。一种生怕自己不被接受的担心涌上心头。在他心里横亘着一道无形的屏障。这样一来,他与别人外在的不同、他与共同游戏的格格不入、落落寡欢的神情、他那种一声不吭、只会睁大眼睛看来看去的样子,引起孩子们的厌恶。当他与正在打秋千的三个小姑娘搭讪遭到拒绝时,世界在普嘉眼中变得冷酷、充满了不公正。“为什么?我做错什么了?”
在最戏剧化的关头,当孤独和委屈达到绝望地步时,作者向人物显现了一个如诗如画、五彩斑斓的自然存在的一个断片:“天牛那画着方格的穹形外壳”由于诗意的投射而煞像“颤栗的阳光的斑点”。自然的真实存在使孤独的戏剧和谐化了,创造出了一种深度和前景感,从中你能感觉得到世界的不完善性、易变性和“温柔性”,原来,那里的一切绝不像小主人公所以为的那样单调、充满悲剧性。少年心中的悲剧被照亮了:周围的世界原来并非那么冷漠,而普嘉在外人心目中,也并非他自以为的那样。
所以,献给伊·布宁的小说“委屈”可以当作是一个学生向大师的敬礼,也是对其学徒期的一个总结之作。小说风格和题材尽管近似布宁,但人物却是纳博科夫笔下独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委屈”是早期纳博科夫学习传统现实主义笔法的总结性作品。
二、纳博科夫与象征派的彼岸理念
在俄国美学思想史上,对美的崇拜、对真善美三位一体的逻辑预设,是其一以贯之的主题。正是在这一基石之上,建构了俄国文艺美学从费特、丘特切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迄弗·索洛维约夫等人的美学哲学思想体系。他们继承了康德“本体界”和现象界、费特等人的“彼岸”与“此岸”的分野,把可见现实与高度的精神现实截然分开,形成一种特有的形而上学二元论世界观。
和象征派一样,纳博科夫相信艺术具有改造世界之伟力,艺术对他来说乃是一种宗教信仰,甚至是超于宗教信仰的自然本身。众所周知,白银时代受象征派艺术理念影响的大批作家都深信世界正走向末日,随着新千年的开始,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到来。所以,他们一方面认为一个非人文化反人性的时代正在到来;另一方面,又认为艺术(和艺术家)有责任引导世人走向人性和神性统一的彼岸,在现实人间创造一个超现实的人间天国。象征派认为艺术是创造生活的思想家,是宇宙、宇宙精神、社会变革的预言家。他们认为继承自然之伟业的人是哲学家、艺术家和诗人,他们是沟通上帝之天国和人间之神喻的传达者,是窥视彼岸的桥梁和媒介。诗人或艺术家的使命不是在虚幻的尘世生活中寻找真理,而是要超拔于尘世生活之上,鄙视真实的卑俗的生活本身,创造和建设新的生活。在俄国文艺美学思想中,安·别雷是继弗·索洛维约夫之后倡导创造生活说的一位主要的思想家,他提出不仅要在艺术中,而且也要在生活中复苏人的个性,以杰出个性为榜样来引导全社会走向人性和神性统一的尘世天国。
象征派对纳博科夫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其作品的意境或整体氛围中。和象征派一样,在理念与现实的二元对立中,象征派和纳博科夫都蔑视现实,认为现实本身是不完善的,它不足以构成艺术的成分。“现实既不是真正艺术的主体,也不是真正艺术的客体;真正的艺术创造着自身的现实”(纳博科夫,《说吧,记忆》12)。总之,有多少人,就可能有多少种潜在可能的现实。在他看来,一般意义上的现实是不存在的,现实在不同的主体眼中具有不同的形象。艺术即起源于一个人运用记忆和想象来调整组建的印象。所以,在真正的艺术家笔下出现的,不是原生态的现实本身,而是一种仿现实原生态的语言幻象。艺术现实永远都是一种幻觉,但这不是艺术的弱点,反而是艺术的强项。艺术之所以有力量,全在于它的这种亦真亦幻,能够超然于粗陋的现实之上,从而为人们揭示来自彼岸的信息的特性。纳博科夫并未整体接受象征派创造生活的实践理念,反对把艺术与生活混为一谈。他认为生活从整体上说不可能成为一种审美建构,艺术的法则不可以平行地移用于性质与之截然不同的现实世界。但他是认同个性反对无个性的造反的。在这一点上,纳博科夫的《死刑邀请》和扎米亚金的《我们》等反乌托邦小说构成了深层次的呼应。
除整体美学诗学观上的影响外,对纳博科夫影响较大的,还有青年象征派另一位主将亚·勃洛克。勃洛克(1880-1921)是纳博科夫景仰的年轻一代象征派中的代表作家之一。纳博科夫曾经称勃洛克为自己的“导师”。他还说:勃洛克“是本世纪(指20世纪)最初20年中最伟大的俄国诗人”(纳博科夫,《说吧,记忆》258)。他称自己年轻时是个“勃洛克时代”的诗人。纳博科夫对勃洛克的景仰即使从其为自己选用的笔名——西林(西林“Сирин”,意为“天堂鸟”。1910年,一些文学书籍应“象征主义运动”之景出版,取总名为“西林”)——也可以看出。
纳博科夫认为:“诗代表通过理性文字构想的非理性的神秘”(纳博科夫,《固执己见》48)。熟悉俄国象征派语汇的人当能知道,所谓“神秘”,在许多具体语境下,实际上指的就是形而上的意蕴,即“仿佛若有所知的寂静”。而这类意蕴,无论作为作家的纳博科夫如何试图否认,它那“……彼岸的新鲜气息渗入了我们的生命”。正如其笔下人物所说:“……可我的幸福,亲爱的朋友,我的幸福却留了下来——它在路灯潮湿的反光中,在伸向运河黑水里的石头台阶小心翼翼的转弯中,在正在跳舞的一对人的微笑中,在上帝为人的孤独而慷慨环护着的一切之中”(纳博科夫,《弗·纳博科夫作品选》308)。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对“失去的天堂”的回忆,构成纳博科夫作品中一大重要主题。和他笔下那些俄国侨民的身世浮沉感相应,纳博科夫笔下充满了命运的扣门声,到处可以意会到那只见无可见,却又无处不在的“命运的手”。《私生的标志》(1947)仿佛在和莱蒙托夫《宿命论者》的主题遥相呼应:世事繁复如转轮,所谓命者,无非偶然罢了。真乃“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
纳博科夫的每部作品,无论体裁大小形态怎样纷繁多样,都具有彼此紧密的关联,既是独立成篇、结构完整的整体,又是彼此关联、互相阐释、互相说明,具有深刻互文关系的统一的整体。这是一种“超结构的特性”,它们把纳博科夫所有作品纳入一个统一的系统之中。
三、纳博科夫与阿克梅派
白银时代俄国文坛上的阿克梅派,是发轫于俄国象征派,以象征派的艺术理念为出发点,同时又以反对象征派基本理念为号召的一个美学文艺学流派。如果说象征派的眼光是彼岸的,以向往彼岸为基点的话,那么,阿克梅派却以此世和现世为出发点,以关怀人生和现世为根本宗旨的美学流派。阿克梅派代表人物尼·古米廖夫(1886-1921)倡导一种以现世关怀为本质特征的入世的美学精神,而摒弃俄国象征派对彼岸的向往。如果说象征派是自上而下的美学的话,那么,阿克梅派则是以自下而上的美学为特征,是世界范围内“语言转向”在俄国语境下的具体体现。在象征派看来,诗和诗人是“美”的理念手中的工具和手段,诗人是“代神立言”——是世界精神和宇宙理念借诗人之手书写神言;而阿克梅派却认为诗和诗人没有那么崇高,诗不过是一种语言操作,诗是一种技巧,可以经过艰苦的学习而掌握,诗的根本宗旨是表现现实生活,反映真实。阿克梅派为自己所取名称——“诗人行会”——就标志着这一特征。他们认为诗人经过刻苦历练,就可以而且也应该能够冲击顶峰,达到艺术和诗的极境(“阿克梅”源于希腊文,意为“顶峰”、“极致”)。阿克梅派认为学习诗歌创作不仅可以塑造诗人,而且还可以创造理想的读者——即懂得诗热爱诗的人。毫无疑问,后者恰正是诗歌存在的土壤和根据。
而纳博科夫所取自阿克梅派的,是注意感性细节和知觉的敏锐。在俄国文学史上,人们一般把以上这两派截然分开,以为他们之间的对立如水火不容,但纳博科夫“却是调和这两个文学潮流固有特征的绝无仅有的范例”(亚历山大罗夫257)。
和阿克梅派一样,纳博科夫尽管并未去认同“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但也反对让赤裸裸的社会定货决定艺术。纳博科夫更倾向于认可艺术是制作,是带有优雅谜底的谜语。他更喜欢把创作比作一个“美丽的谜”。显然,在艺术观上,纳博科夫更多地带有现代以及后现代的色彩。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说、未来派对语言革新的崇拜,以及整个俄国现代主义把艺术当作与社会无关的自主领域的见解,都对纳博科夫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纳博科夫看来,艺术是一种语言的幻象,它并不祈求在真实性上与本然之真竞争,而是指向更高的真实——艺术的哲理之真。纳博科夫的艺术创新主要表现在他革新了读者与作者的传统关系,向读者的知解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他的每部作品都期待理想读者的解读,并不祈求在整体上对时代问题提出现实的回答,而是要人们关注作品的每个细节细部。他说:“……象棋棋题中的比赛不是在白子和黑子之间进行的,而是在棋题的编撰者和想象中的破解者之间发生的(如同在写作艺术中,真正的斗争不是发生在小说的主人公们之间,而是在小说家和读者之间一样)……”(转引自阿格诺索夫376)。在此,我们不拟深入细致地探讨纳博科夫诗学特征与阿克梅等派别的继承性联系,而是着重谈一谈阿克梅派主要代表人物古米廖夫作为一个英雄诗人,其伟岸人格对作家纳博科夫的影响。
在白银时代诗人中,古米廖夫是一个更多地以其个性对纳博科夫发生了重大影响的诗人。以其行为而非主要以笔来书写文学的古米廖夫,在这个意义上仍不脱象征派特征。早在1923年,弗·纳博科夫就在“纪念古米廖夫”这首颂诗中写道:“你像缪斯教导的那样,清醒而又骄傲地死去了。/此刻,在寂静无声的叶尼塞河上,你正和普希金一起,/谈论着飞翔在天上的青铜的彼得大帝/和非洲的旷野上的风。”
在纳博科夫的意识中,始终萦绕不去的,是诗人古米廖夫那种超拔于人世的英雄主义个性和他那悲剧性的死亡。70年代中,纳博科夫又在一首诗中,重提古米廖夫之死:“古米廖夫诗歌,我是多么喜爱!”众所周知,古米廖夫生前曾经不止一次在诗文中叙及并预言了自己的死——什么“一颗子弹”、“荒野上的一座坟坑”(与他被处死的情形绝相吻合)。古米廖夫认为人的死比生更能说明一个人的本质。他一生既向往英雄主义的生活,更向往英雄式的壮烈的死。古米廖夫之所以使纳博科夫如此喜爱,和他诗中的存在主义意蕴有着很大关系。纳博科夫在距其有关古米廖夫的第一首诗的50年后,在他一篇题为“文学艺术与常识”的美国讲座中,塑造了他心目中古米廖夫的形象:他是一个在道德方面无可比拟地高于其刽子手的英雄;是一个富于“崇高的彼岸性”的艺术家;是一个在被押解到刑场的路上,始终都在微笑的强者。古米廖夫临终前的笑表明他的意识境界(或灵感,按纳博科夫的说法,即共时态性)高于他的刽子手们,因为他的灵感是得到彼岸性祝福的,是不朽的象征(亚历山大罗夫267)。纳博科夫在其作品《天才》中人物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身上,展现了古米廖夫式的“临终微笑”。书中人物费多尔在描写其父被处死的情景时,写到被处死的人临终前“脸上挂着鄙夷不屑的笑意”。在生命攸关之机仍不忘关注“在黑暗中牛蒡身上伫立着的一只淡白色夜蛾”。古米廖夫的英雄主义精神在长篇小说《功勋》中也得到了呈现。我们看到,这里的描写和古米廖夫临终前的情景何其相似!
纳博科夫的艺术世界是俄罗斯文化精神和现代、后现代文化精神的绝妙融合。走近它我们既需要深入把握现代及后现代文化的内蕴,更不可缺少俄罗斯文化精神这一独特的视角。纳博科夫还是向西方介绍俄国经典作家居功至伟的一位大家。正是经由他多年孜孜不倦的努力,西方读者才得以了解俄罗斯经典作家,如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丘特切夫、霍达谢维奇的英法文译本,写作了《尼古拉·果戈理》、《叶甫盖尼·奥涅金翻译与注释》等煌煌巨著。他认为普希金是俄国最伟大的诗人。
凡此种种,都说明要研究纳博科夫,忽略乃至不正视他的俄国文化底蕴,是无缘得窥其艺术的堂奥的。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弗·叶·亚历山大罗夫:《纳博科夫与彼岸性:形而上、伦理、美学》。圣彼得堡:阿莱捷亚出版社,1999年。
[Alexandrov,V.E.V.Nabokov and The Faramita:Metaphysic,Metaphysic and Aesthetics.St.Petersburg:Altai Press,1999.]
符·维·阿格诺索夫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Argenosov,V.V.,ed.Russian Literature in 20th Century.Beijing:China Remin UP,2001.]
纳博科夫:《弗·弗·纳博科夫作品选集》。莫斯科: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1989年。
[Nabokov,V.Collected Works of V.Nabokov.Moscow:Soviet Muscovite Press,1989.]
——:《弗·纳博科夫作品选》,第一卷。莫斯科:真理报出版社,1990年。
[---.Selected Works of V.Nabokov.Vol.1.Moscow:Truth Press,1990.]
——:《固执己见》。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
[---.Interview.Changchun:Epoch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1998.]
——:《说吧,记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
[---.The Other Shore.Changchun:Epoch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