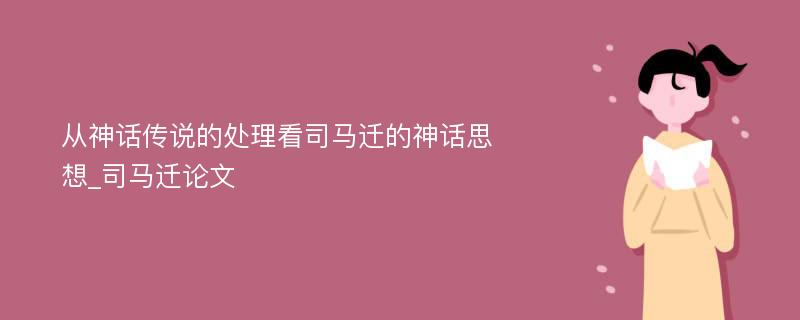
从对神话传说的处理看司马迁的神话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神话传说论文,司马迁论文,神话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神话学和历史学都已证明,人类(无论是哪个民族)早期的历史与神话不可分地纠结在一起,要明确区分哪是人哪是神,哪是神话的延续哪是历史的开端,是十分困难的。神话与历史之间的这种缠夹关系在中国古代尤其突出,这与中国古代部族内部的社会结构有直接关系。原来,我国古代各部族都是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团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氏族领袖与祖先叠合为一,氏族种姓观念根深蒂固。这种情况及其影响,从原始时代到奴隶制时代一直存在。所以,每个部族,无论是夏、商部族还是周、秦部族都经历了部族起源的历史阶段,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始祖诞生的神话,始祖与神合一,历史与神话合一因而也就成为非常普遍的事实。对于神话研究来说,这无疑是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但却给追溯民族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历史撰述带来很大麻烦。
在司马迁之前,我国的史书不是王朝史就是国别史,都是某一阶段的历史,而没有贯通古今的通史(注:参阅白寿彝《史记新论》第一个问题“史记写作的历史背景”,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因而也就不可能触及到民族起源以及相关的区分历史与神话的问题。但是,司马迁写作《史记》则不同,他要写的是一部“通古今之变”的通史,从五帝一直到他所处的时代,因此,必然要涉及这些问题。就是说,在我国古代诸多历史学家中,第一次遇到这个难题的不是别人,而是以完成通史为己任的司马迁。因此,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具体操作也就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并深刻地反映着他的学术观点,特别是对神话的观点。
作为史学家,司马迁在神话思想方面的建树主要集中在神话与历史关系的问题上。具体说来,表现在两个方面:他既看到了神话与历史的区别,又看到了神话与历史的联系。前者即神话与历史的区别,体现了他对神话某些本质的初步理解,他以是否符合经验和理性来区分神话与历史,说明他对神话的非经验和非理性特征有一定的认识;后者即神话与历史的联系,体现了他对神话价值的初步理解,他以神异性的人把神话与历史联系起来,并用以追溯民族起源和早期的发展,突出地表现了他对神话的史学价值的肯定。
二
先说第一个方面即从神话与历史的区别中来看司马迁对神话某些本质特征的初步认识。
历史所“探究的问题并不是神事,而是人事……不是万物之初、时间无考的过去的事件,它们是若干年之前、时间可确定的过去的事件”(注: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页。)。对司马迁来说,这最早的“过去的事件”就是追溯几个部族的起源。但是,文明的源头总是神秘渺茫的神的世界,民族的历史总是从神话王国中走来,因此,关于民族起源和早期历史只有在神话中才有所反映——神话是这个阶段人类历史的唯一记录。那么,面对“人神杂糅”,历史与神话合一的情况,司马迁的首要任务不仅是对材料进行鉴别,而且要从神话材料中挖掘史料,寻找历史线索。可以想象,这个任务非常繁重而困难,司马迁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一点,并清醒而自觉地对待它。
司马迁鉴别和区分历史与神话的标准是人间通行的常理,符合这个常理的,也就是符合经验和理性的,便是曾经发生过的往事,属于历史的范畴而予以保留,否则则是子虚乌有的故事,属于神话的范畴而予以剔除。通过考察,司马迁认为,在流传下来的材料中,不符合这个标准的很多很多,它们都具有“不雅驯”的特征。他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注:《史记·五帝本纪》。)以前对“雅驯”的解释多有不确,例如《史记正义》认为“雅驯”就是“典雅之驯”,今人有的解为“温文不俗”等等。这些解释既不确切也不透彻。此处“雅”即正、正宗,引申为正确、得其要领。“驯”同训,意为解说、说法。雅驯意即正确的说法。这样看来,“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的意思就是:诸子百家纷纷谈论黄帝,而多不得其正确的说法,以致后代文士对此莫辨真伪而难言之。通观《五帝本纪》和《太史公自序》的有关部分可以知道,司马迁这里所说的“雅驯”即正确的说法,正是以是否有事实根据为标准。司马迁认为黄帝作为人(神异性之人,详后)其言行和作为实有其事,符合人间常理,则属“雅驯”,是正确的;而那些没有事实根据的神话传说,皆属“不雅驯”,都是不正确的。
在鉴别和区分的基础上,司马迁对材料又做了筛选,他说:“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于本纪书首。”(注:《史记·五帝本纪》。)即把“不雅驯”的神话传说一一剔除,而把“雅驯”的史实资料保留下来写入历史。例如,《山海经》、《庄子》、《吕氏春秋》等文献中关于黄帝、颛顼、帝喾的神话由于“不雅驯”而没有采纳,而对《五帝德》、《帝系传》等文献中的“言尤雅者”则予以吸收。今天,我们所见的《史记·五帝本纪》内容多与《五帝德》、《帝系传》相同,而与《山海经》等文献不同,其原因正在于此。
在《五帝德》、《帝系传》中,有关黄帝、颛顼、帝喾的神话早已历史化了,就是说,有关他们的史实是神话历史化的结果。神话历史化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思潮,即把神话还原或解释为历史,把非经验、非理性的神话变成以体现某种神圣原则和历史因果关系的往事,把超自然的神变成具有某种社会性的人(注:详见拙作《论神话历史化思潮》,《南开学报》1994年2第期。)。 例如《五帝德》:“宰我问于孔子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民赖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黄帝三百年。’”这里把“黄帝三百年”的神话作了历史化解释,使之变成理性可以悟解的人事,从而彻底改变了神话的性质。
作为一个考信求实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当然不会相信虚妄无稽的神话传说,而更着意于追求实有其事的历史。所以,《五帝德》、《帝系传》中大量的被历史化的材料,自然引起他强烈的兴趣和关注。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些材料的真伪,他又到民间进行实地考察和搜集材料。他说:“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余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注:《史记·五帝本纪》。)由于司马迁对现成的文献资料进行了严格鉴别和考察,剔除了诬罔不实的成分,同时又到民间广泛搜集旧闻逸事,从而使他的著作远远超过了前人著作。例如,对五帝与夏、商、周诸部族的姓氏、国号及其与黄帝的关系,《史记·五帝本纪》作出了全面而系统的说明: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
就这样,有关五帝的神话被历史化的事实,经孔子肯定之后(注:详见拙作《孔子发现和肯定神话历史化的重大意义》,《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又一次被司马迁肯定, 并被正式写入历史著作中,从而使它们进一步取得“历史事实”的性质。这一点不仅对中国历史学,而且对中国神话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司马迁之所以能对他所掌握的材料进行鉴别和区分,把神话传说从史料中剔除出去,正是以对神话特点的认识为前提。在司马迁看来,神话传说荒诞离奇,根本不可能发生,这与有事实根据,符合因果关系的古史是完全不同的。实际上,这已经触及到神话的一些特征:神话实际并不存在,纯属想象,因而可以不顾客观实际,随意违背经验和理性。尽管司马迁对此没有从理论上加以阐明,但他对材料的实际操作中已经蕴含着这种认识却是没有疑问的。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把对神话的这种潜在认识用“不雅驯”来加以概括更是难能可贵。
历史与神话是不同范畴的两个事物,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特征,现代人对它们的认识一般不会相混,但是在古代神意史观的支配下,却往往将它们混为一谈,认为历史的发展暗中受着神的操纵,是神的意志和体现。相应地反映历史与神话的历史思想和神话思想也就相融为一。在这种情况下,要真正区分历史思想和神话思想是极其困难甚至根本不可能的。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将二者清楚分开是很晚的事情。在古希腊直到伟大的史学家修昔底德才做到这一点。他的著作正是由于这一重要成就而受到广泛的称赞。在神话与历史缠夹,神话思想与历史思想难分的文化背景下,司马迁不但对它们做了初步的区分,而且朦胧地认识到神话的一些特征,这在人类认识神话的历史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三
再说司马迁对神话与历史的联系及对神话价值的认识。这主要反映在他对商、周、秦部族起源材料的处理上。
周部族的起源和部族业绩的奠基主要反映在其始祖诞生的神话中。《诗经·大雅·生民》记载了这则神话,《史记·周本纪》记载了这段历史,将二者加以对比,可以看出司马迁如何处理材料以及他对神话的观点。
《史记》所记与《生民》的不同至少有以下几点:
在《生民》中,后稷是其母姜嫄履帝迹怀孕而生,他“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史记》虽也写了这一点,但更强调其父,明确指出“姜嫄为帝喾元妃”。司马迁笔下的后稷既知其母,又知其父,他是姜嫄和帝喾的共同的儿子。其次,《生民》中的后稷是其母祭祀求神而生,是神对周部族的恩赐,体现了神的意志。《史记》根本没有写这样的内容,只是说姜嫄怀孕之后,“居期而生子”。还有,《生民》写后稷出生直接惊动了上帝,使“上帝不宁”,反映出后稷与上帝相通,具有神的威力;《史记》则不同,写后稷出生根本不涉及上帝,与上帝没有关系。
可以看出,司马迁笔下的后稷与神话中的后稷相比,无论是父母、世系,还是出生过程、与上帝的关系,彼此都是不同的。前者身上神的因素在减弱,人的因素在增多。特别是有了明确的父亲和世系,更赋予他一定的社会性特征,而与超自然的神拉开了距离。司马迁正是把他作为人看待,才把他归于历史范畴,放在周部族历史的开头加以叙述。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司马迁看来,后稷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却不是一般的人,而具有明显的神异性特征:他虽有父母,但在怀孕之前却有一段神奇的经历:“姜嫄出野,见巨人迹……践之而身动如有孕者”,尚未出生,即被笼罩于神秘的光环中。另外,出生之后也有“三弃三收”的不平凡经历,说明他生而不凡,以致其母姜嫄也以为“神”。
除了周部族的祖先后稷之外,司马迁笔下的殷部族始祖契和秦部族始祖大业等,也都是具有一定神异性的人。像后稷一样,他们也都有明确的父母和世系,如契的父亲是帝喾,大业的父亲为颛顼。他们神奇不凡,具有超人的本领,创下了辉煌的业绩,如征顽凶、和万国、举贤臣、同律度、修礼乐以及治理山河,教民稼穑等等。作为部族基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们都是后代子孙心目中的英雄,具有超人的神异性。
所谓人的神异性,是说人虽不是神,但在某些方面却具有神的特征和本领,因而也是经验和理性所不能理解的。在司马迁看来,神异性具有二重特征,既适用于神又适用于个人,既表现于神话又表现于历史。神话中的神具有超自然的特征,是神异的;而从事历史活动的人也有超常的,因而也是神异的。神异的神是神话中的普遍现象,神异的人虽非普遍,但却也是存在的——司马迁确实相信存在着神异性的人(注:详见另文《关于司马迁的世界观》。)。正是因为如此,在司马迁心目中神异性也就成了某些历史人物与神之间的共通的东西,因而也是神话与历史之间的契合点和中介。正是通过这个契合点和中介,才能从神身上寻找人的影子,从神话故事中寻找历史事件的影子,从而使神话(始祖诞生的神话)成为追溯民族起源和早期历史的最可贵的材料。司马迁的这种做法体现着他对神话的史学价值的肯定。这里,如果摒除了司马迁所宣扬的人的神异性的历史唯心主义错误之外,而单就他对神话的史学价值的肯定来看,应当说,司马迁的认识和实际操作是有根据的。
神话是蒙昧时代历史事件的虚幻反映,它的产生以历史为基础。因为不论神话的想象和幻想多么离奇荒诞,总是有其事实基础,而不是凭空产生。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以神话的形式反映历史,也就是人对自己历史的神化是人类意识发展的必经历史阶段。在宗教神意史观的支配下,人所意识到的世界只能是由神统治并且是神在活动的世界。所以,“当他不再被封闭在直接欲望和需要的狭窄圈子内而开始追问事物的起源时,他所能发现的还仅仅是一种神话式的起源,而非历史的起源。为了理解世界——物理的世界和社会的世界——他不得不把它反映在神话时代的往事上”(注:恩·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19页。)。这就是说, 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上,人们要描绘自己的历史,除了使用神话形式,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所以,神话中神的活动不过是人的活动的影子,“神明人物是人类社会的超人统治者”(注:恩·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19页。)。在祖先崇拜盛行的原始氏族社会, 这个神明人物则是氏族部落或部族的祖先。正是因为如此,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那些带有野蛮气息的神话,特别是始祖诞生的神话和祖先神话,往往包含着民族起源和早期历史的重要信息和线索,只要剖开其外壳,将神话还原,就会有新的发现。而这种发现是任何其他文献都不能给予的。神话作为当时社会生活和历史的最早的记录,在填补人类历史空白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十分重要的意义。司马迁通过神话追溯民族起源和早期历史,不但反映了他对神话与历史关系的深刻理解,而且反映了他对神话价值的明确认识。
揭示族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在这方面,司马迁可谓功勋卓著。他根据神话材料和其他有关文献所揭示的商、周、秦诸部族的起源过程,他们的族系、姓氏、地域、功业以及与中华民族人文初祖黄帝之间的关系等等,都属于最基本的情况,是认识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条件。司马迁所提供的这些情况,虽不能说准确无误,没有任何差错和失真,但它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接近历史真相的“原始”记录。凭借着它的引渡,后代学者才有可能涉入浩瀚渊深的古史海洋,去做新的探索和发现。否则,如果没有司马迁所提供的历史资料和线索,那么,有关的古史研究也许更难走出沉沉的历史黑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