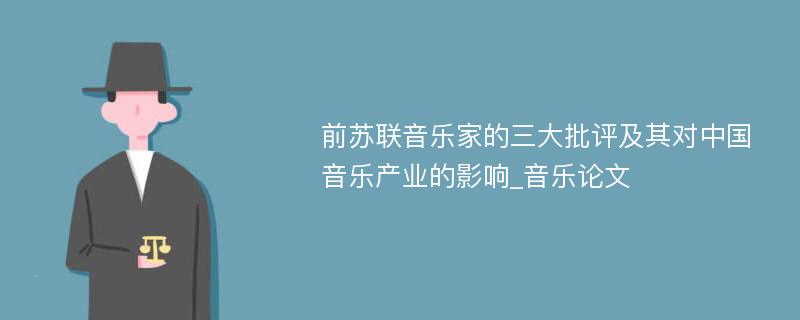
前苏联三次对音乐家的批判及对我国音乐界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音乐界论文,前苏联论文,音乐家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8年,苏共中央做出《关于纠正对歌剧[伟大的友谊]、[波格丹、赫美尔尼次基]和[全心全意]的评价中的错误》(以下简称《58决议》)(注:苏共中央1958年5月28日的决议,见《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2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3月版。)中说:《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以下简称《48决议》)(注:联共(布)中央1948年2月10日的决议,苏共中央1958年5月28日的决议,见《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1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3月版。)“总的来说在发展苏联音乐艺术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同时,《真理报》编辑部文章《苏联音乐的道路是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道路》(以下简称《道路》)(注:《真理报》编辑部1958年6月8日文章,见《音乐译文》1958年第5期第2页,音乐出版社,1958年10月版。)却肯定1936年和1948年三次批判的主要精神,所以笔者就把《58决议》、《道路》同《日丹诺夫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苏联音乐工作者会议上的开幕词》(以下简称《日一》(注:苏共中央1958年5月28日的决议,见《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3月版。)、《日丹诺夫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苏联音乐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以下简称《日二》)(注:苏共中央1958年5月28日的决议,见《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3月版。)以及《混乱代替音乐》(以下简称《混乱》)(注:《真理报》1936年1月28日专论,见《苏联歌剧创作问题》论文集,音乐出版社,1956年5月出版,第2~4页。)这些文件联系起来探讨。下面分六个问题对上述文件进行探讨和反思:
一、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和“党性原则”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据说是一种“创作方法”,在1934年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并规定为苏联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事实上,它已经超越创作方法的范畴,而成为包括作家的世界观、认识论、政治倾向和创作目的的一种创作准则。以后又在美术、戏剧、电影、音乐等艺术领域里生硬地推行这一准则。“创作方法”在音乐创作中如何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音乐创作中又如何运用?这都是至今还解决不了的复杂问题。虽然阿萨菲耶夫、苏斯洛夫为解释音乐中的现实主义和反映论,创立了“音调论”的学说,但在国际音乐学界上对它还有争议。在很多场合中,音乐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作曲家创作中的一种桎梏,或者是打击作曲家的一根棍子。对于音乐创作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较为简捷、通俗的解释倒是斯大林说过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和民族的形式”。这一解释把音乐的内容规定为必须是政治的——社会主义的,把音乐题材规定得很狭窄,无视音乐艺术的特点,也不符合苏联音乐界直到1958年的现实。即使社会主义国家的音乐作品也不可能每一首都有社会主义的政治内容。作为领导着一个国家的政党,在文艺政策中规定艺术家统一地采用一种“创作方法”是不利于艺术发展的,因此是不明智的。列宁就没有要求过苏联的作家、艺术家采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也没有规定文艺家采用统一的创作方法,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注:见《毛泽东论文学和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2月出版,第71页。)他这里说的是中国共产党内的文艺家在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上主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不强求抗日统一战线中党外的文艺家也遵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但在50年代由于盲目学习苏联的结果,我国文艺界曾普遍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并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得紧张,1957年,甚至作为划分“右派”的理论依据。1958年夏季,毛泽东曾根据其个人的爱好,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并被我国文艺界奉为准则,大家竞相从理论上或实践上探索这种不易捉摸的创作方法。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曾有“二为”、“二百”、“二革”的提法。“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党中央在1979年对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废除了“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同时也不再规定或提倡任何创作方法。从50年代到60年代,关于创作方法的规定和提倡对于音乐家的束缚、打击,至少是引起音乐家的困惑,这是历史事实,值得我国音乐界反思。
《道路》同以前的文件一样,还要求“艺术创作的党性……原则”(注:《真理报》编辑部1958年6月8日文章,见《音乐译文》1958年第5期第4页,音乐出版社,1958年10月版。)。对非共产党员的作曲家要求同党员作曲家一样遵循“党性原则”,岂不是笑话?就拿肖斯塔克维奇来说,1960年才入党。即使党员作曲家也只能在创作过程中由于世界观的指导,潜移默化地体现出共产主义思想的特点,而不能在创作过程中每时每刻都坚持着“党性”,作品中充满着党气。党员作曲家也必须象列宁所说的“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有思想和幻想”(注: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2月北京第1版,第68页。),否则他只能是一个党员,而不可能成为作曲家。
毛泽东也没有要求过非党的文艺家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他只要共产党员站在上述立场。(注: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2月北京第1版,第52页。)
《道路》中说:(苏共)“党……指出思想工作的……主要任务在于积极宣传……苏维埃国家政策。”(注:《真理报》编辑部1958年6月8日文章,见《音乐译文》1958年第5期第3~4页,音乐出版社,1958年10月版。)要求作为思想工作一部分的艺术(尤其是音乐创作)工作“宣传……政策”,这是错误的、对艺术极其有害的要求。艺术的根本任务是反映人的生活,反映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要求艺术“为政治服务”,跟在政治斗争的后面跑。已经是不适当的了。如果更进一步要求艺术“宣传政策”,作政策的图解或传声筒,势必毁掉了艺术。因为艺术是形象思维的产物,政策是逻辑思维的产物,如果要求艺术“宣传政策”,势必使艺术失去形象思维的特点,成为政策的图解、传声筒,就没有艺术的魅力了。而且政策必然是变化的,有时发现政策制定错了或现实有变化,就必须调整,改变为更正确、更适当的政策。如果要求艺术“宣传政策”,势必产生出一些在政策改变后立即作废的“艺术品”,使艺术创作者进行了无数的“无效劳动”。从30年代到80年代,我们看到苏联有不少由于政策的改变而“作废”了的艺术品,相反的,倒是有许多没有“宣传政策”的艺术品至今仍为人们所欣赏和称道。
我国建国前后,也有文艺界的人士把“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发展成“为政治服务”,“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5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过几次极左的政策,其间也有过几次必要的调整。“为政治服务”和“宣传政策”的口号伤害过不少艺术家及其艺术作品。音乐方面也是一样。回想一下,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以后,音乐家写了许多“跃进”歌,后来全部“作废”了。“文化大革命”中对音乐家的迫害,以及少数音乐家为了“紧跟形势”写的“语录歌”和赶浪头的“战歌”,更是众所周知了。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以来,党中央撤消了“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不再提“宣传政策”作为音乐创作的任务,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
二、关于“艺术同人民的生活保持联系”
《道路》批评“某些作曲家……在战后初期脱离了……那些重大而激动人心的题材”,号召作曲家“创作充满乐观主义……的音乐”(注:《真理报》编辑部1958年6月8日文章,见《音乐译文》1958年第5期第6、18页,音乐出版社,1958年10月版。)。
艺术都是从人民的生活中产生出来的,即使有的艺术家标榜或企图写出脱离人民生活的作品,他的作品还是以他的世界观或从他的角度观察人民生活的结果。有正确的反映和歪曲的反映;有全面的反映和片面的反映;有的反映人民生活的主流,有的只反映人民生活的支流或浪花。公众和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应该欢迎艺术家从各种角度、各种层面来反映人民的生活,用文艺评论的方法帮助艺术家尽量做正确的反映。不论艺术家反映重大的题材或平凡的题材,也不论艺术家反映作为社会主流的生活思想感情,或者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实际存在的非主流的生活思想感情,都应该允许。只有在作品的政治立场违背本国的宪法和法律时才禁止其公开传播。
在战争时期,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为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战争的胜利,曾提出过“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描写工农兵,表现工农兵,必须暴露“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歌颂“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要“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要刻画“资产阶级黑暗”。在中国人民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经济上的优势时,这样提法本是无可非议的。但后来文艺界有人主张“文艺工作者应当而且只能写与工农兵群众的斗争有关的主题”,这就显得过于偏颇和狭窄了。1955年胡风提出“到处都有生活”,竟受到反击和批判,造成延续20多年的冤案,给文艺创作思想加上了无形的束缚。
建国初期,在音乐领域里片面地提倡进行曲和颂歌体裁的群众歌曲,几次贬斥抒情歌曲,冷落多种多样的题材,一度出现“写十三年”的口号,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只剩下“高、快、硬、响”的“战歌”和“语录歌”,不能不说是把音乐作品的题材限制得过于狭窄的结果。1979年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以后,党中央提出“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及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182、185页。)现在,对于音乐创作的题材的禁锢已经取消,出现了各种各样题材的声乐和器乐作品。
三、关于音乐创作同古典音乐作品和民间音乐传统的联系
《58决议》说:《48决议》“强调了艺术……同古典音乐和民间创作的优良民主传统保持联系的意义”(注:《真理报》编辑部1958年6月8日文章,见《音乐译文》1958年第5期第2页,音乐出版社,1958年10月版。)。但《48决议》和《日一》、《日二》中提倡的是:作曲家“摹仿”俄罗斯古典音乐作品,并在作品中引用民间音乐的主题和曲调。这就是要求苏联作曲家在创作时墨守革命前的音乐作品的风格,并且多采用固有的民歌、民间音乐的主题或曲调,不必自己创作音乐的主题和曲调。这主要的原因是斯大林、日丹诺夫等政治家听惯了并偏爱革命前的音乐,不易接受苏联作曲家的新作,并企图阻挡苏联音乐创作沿着它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
我国建国前后,音乐界提倡继承民族民间的传统,继承聂耳、冼星海的革命群众歌曲的传统,继承刘天华、华彦钧的民族音乐的传统。继承这些传统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但有的时候把继承传统理解得过于狭窄。一种是把过去的音乐作品当作一种模式。音乐创作不许离开这些模式;另一种是把继承传统狭隘地理解为利用民族民间音乐固有的音调、节奏来创作音乐作品,以致有些歌曲作品只是某一首民歌的整理改编,有些器乐作品只是某些群众歌曲和民歌的发展变化,降低了创作的意义。
1979年第四次文代大会以来,党中央号召文艺工作者“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184、182页。),从总的方面扭转了狭隘地理解音乐创作继承民族、民间音乐和革命群众歌曲传统的问题。
四、关于“革新”与“形式主义”、“现代主义”的问题
《日二》中谴责“在虚伪的革新旗帜之下摈弃古典遗产、摈弃音乐的人民性、摈弃为人民服务而去满足一小撮第一流的唯美主义者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情绪”的倾向。说“古典音乐的特点是……把最高级的技巧跟朴素性和平易性结合起来。”“如果在某些苏联作曲家中间盛行着这种理论;我们是会在50年~100年之后被了解的,假如现代人不能了解我们,后世是会了解我们的,——那就简直可怕了。”《58决议》中也跟着说:《48决议》“谴责”了“音乐中的形式主义倾向,那种……虚假的所谓革新”、“党还坚决地谴责了同苏维埃人格格不入的个人主义的理论,这些理论的创造者企图为莫名其妙的、形式主义的作品进行辩护,说什么人民还没有达到能够了解这些作品的水平,再过数百年,人民就会理解它们。”(注:《真理报》编辑部1958年6月8日文章,见《音乐译文》1958年第5期第2页,音乐出版社,1958年10月版。)实际上,随着音乐表现内容的发展和变化,音乐创作的技巧在千百年来一直在发展和变化。每一次、每一点发展和变化都会遭到听不懂的人反对,有些发展和变化随着历史的进程而消声匿迹了,而更多的发展和变化却保留下来,并且更加向前发展和变化。这是历史的必然。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们听不惯新的音乐创作技法,贬斥它们为“形式主义”、“主观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反民主”、“极端个人主义的”、“迷醉于……现代资产阶级西方音乐、颓废派音乐”,“徒劳无益的……试验”,“修正主义观点”等等,但20世纪的音乐创作技法还是在全世界(包括前苏联)流传,由作曲家们根据自己表现内容的需要而成功地或失败地采用着。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或领导人不应该以个人的意志来提倡某一种艺术创作技法或压制另一种艺术创作技法,正如他不能禁止外国的文化在他的国度里或明或暗地传播一样。
我国建国后,由于宣传过《混乱》和《48决议》等文件,也是一贯反对现代作曲技法的。1979年第四次文代大会以后,党中央提出“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文艺……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183页。),我国一批青年作曲家吸收了现代音乐创作技法,结合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传统,创作了一批有价值的新作品,得到国内外音乐界和听众的承认和称赞。虽然在音乐界内部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如1987年冬和1995年冬至今的有关“新潮音乐问题”的讨论,但从行政上压制一种新的艺术创作技法的现象基本上消失了。
五、关于音乐作品的理解和接受、标题音乐以及“学院派”问题
音乐作品是必须要听众理解和接受的。但听众是多层次的,一部音乐作品有时因艰深而不能立即为广大听众所理解、所接受,但不一定是“脱离人民”的作品。有些通俗音乐作品是一出现就被广大听众理解和接受,但不一定是有生命力的作品。把这个问题夸大成“脱离人民”,“成为少数审美专家所专有”,作为一条政治罪状是不妥当的。
毛泽东在战争时期强调“普及”是正确的,但那时他也提过“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和“干部所需要的提高”(注:苏共中央1958年5月28日的决议,见《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102~10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3月版。)。建国以后,我国的文化水平比战争时期的农村环境有所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有了较大的差距,正应该发展高低不同各种层次的音乐艺术,并努力普及音乐知识,提高各层次音乐听众的欣赏水平。但建国初期的国内外环境致使我国的文艺政策受着前苏共中央历次文件的影响,或与之暗合,过分强调普及与通俗。混淆了“大众化”和“通俗”的界限,只鼓励群众歌曲的创作,冷淡或限制高层次或较高层次的音乐作品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成批判“大、洋、古”、“名、洋、古”,不许群众接触古今中外的音乐名作,凡写过音乐作品的作曲家都受到批判,只有个别因写了“语录歌”或“战歌”的作曲家才得以从宽处理。
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以来,党中央号召“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商品经济体制日益浸润到音乐事业中来,国家和政府没有及时制订经济政策并调集财力来支持音乐家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创作,致使民族音乐、戏曲曲艺音乐,合唱音乐、歌剧舞剧音乐、交响乐、室内乐等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濒临绝境,只有通俗歌曲、通俗音乐由于在商品经济体制中能独立经营,甚至由于国家税收政策的不完备竟得到片面而畸形的发展,致使党中央提出的“当前,要……从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注:《真理报》编辑部1958年6月8日文章,见《音乐译文》1958年第5期第6页,音乐出版社,1958年10月版。)这句话还不能实现。
《日一》中提出过标题音乐的问题。日丹诺夫说:“如果要谈到形式主义倾向之背弃古典遗产原则,那就不能不说到标题音乐作用的缩小。……忘记标题音乐,也就是背弃进步传统。大家知道,俄国古典音乐照例总是标题音乐。”(注:见《毛泽东论文学和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2月出版,第67页。)这明显地是一种错误的理论,而《58决议》和《道路》却没有加以澄清。标题音乐和没有标题的音乐(纯音乐)本来是器乐作品中的两个种类,作曲家有选择两种音乐体裁之一的自由。虽然俄国近代音乐(从格林卡起)标题音乐较多一些,但不能说标题音乐就是进步的,就是俄罗斯音乐的传统,应该抵制纯音乐。政治家听不懂纯音乐,因而不喜欢纯音乐,这是他们急功近利的表现,音乐家不必奉为“指示”。
我国有“文人音乐”的传统,许多器乐曲被文人冠以富有诗意的标题,有时又改为另一个标题。例如:从《夕阳箫鼓》到《浔阳夜月》,又到《春江花月夜》。音乐家借标题以发挥音乐的内容,听众借标题以理解音乐的内容。没有标题的音乐不容易被人接受。有时听众、音乐评论家和领导者竟要求音乐作品象文学、戏剧一样地表现具体的形象和情节,以致很难普及正确的音乐欣赏方法。也有时对纯音乐作品表示冷淡或抵触。这些同苏联音乐界出现的现象如出一辙,可见深受其影响。
至于“文化大革命”当中,江青出于阴险目的,大肆批判“无标题音乐”及“资产阶级所标榜的什么纯音乐”。其对纯音乐的理解与日丹诺夫比较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以后,党中央“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185页。),作曲家有了任意选择标题音乐或纯音乐形式的自由,没有标题的纯音乐作品也出现了。
《日二》中滥用谢洛夫和斯塔索夫对旧俄“学院派”的批评以攻击苏联的音乐学院为“学院派”。这种言论削弱了苏联的专业音乐教育,并造成苏联音乐界的内部矛盾。
我国从30年代革命音乐界的宗派主义、孤立主义起,就有忽视专业水平较高的音乐家的倾向,没有把他们当作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中的盟友,而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为艺术而艺术”的“学院派”。建国后,居于音乐界领导地位的个别人仍时常表现出宗派主义的情绪,对受过专业音乐教育的(甚至是共产党员的)音乐家还常常指责为“学院派”,联系到1948年苏联音乐界首次公开出现“学院派”的称谓(注:苏共中央1958年5月28日的决议,见《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107~10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3月版。),是受了日丹诺夫的影响。
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以来,党中央多次号召文艺队伍内部加强团结。希望音乐界内部也能捐弃前嫌,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大原则之下,团结起来。
六、关于民族音乐同外国音乐关系的问题
《日二》中斥责“形式主义倾向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迷醉于、甚至有些偏向于现代资产阶级西方音乐、颓废派音乐”,进而论述了苏联音乐和外国音乐的关系,提倡一种闭关自守的政策,威吓说否则就将成为“忘本的世界主义者”。而《58决议》和《道路》并没有对这个问题加以澄清。事实上从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以来,各国、各民族的艺术都不可能在不受别国(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文化的主流)艺术影响的条件发展起来。格林卡也是到意大利、维也纳、柏林、巴黎等地学习了西欧音乐的经验和技巧,立志创作俄罗斯的民族音乐,而不是模仿西欧音乐的。日丹诺夫说:“至于处在衰颓和堕落状态中的现代资产阶级音乐,那是没有什么可利用的。”(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182页。)事实证明,现代资产阶级音乐也并不完全处在衰颓和堕落状态。即使在衰颓和堕落状态的音乐中也还是可以批判地利用其某些技术或技巧的。发展一个民族的音乐艺术(包括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艺术),在当今的世界上,是不可能与世隔绝的,也不可能是只输出而不输入的。
我国建国后也曾受过苏联的这种影响。50年代我国对西方音乐是闭关自守的。1950年11月起,曾对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放西洋音乐节目进行讨论,当时就引用过《48决议》和日丹诺夫的言论。后来我们对外国音乐的态度基本上也是以苏联音乐界的态度为转移的,60~70年代,我国音乐界更封闭了。音乐界长期满足于我国音乐的悠久历史传统,有的领导人提倡“土要土到家”(注:吕骥《十五年来的新音乐》,1948年7月20日,齐齐哈尔。),想用传统音乐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文化大革命”当中“四人帮”批判一切“封、资、修”、“大、洋、古”,对《天鹅湖》、《巴黎圣母院》、《圣母颂》,贝多芬的《暴风雨》、《欢乐颂》,以及舒伯特、舒曼、肖邦等等,对他们道听途说得来的一切音乐家人名和曲名,他们都要批判。当时只有一个外国音乐作品可以演奏,就是毛泽东多次提倡的《国际歌》。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音乐界才惊奇地发现,我们同世界各国的音乐隔绝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19世纪末期的德彪西等印象派音乐对我们都是新鲜的。改革、开放使我们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变化的过程中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弊病是不足为奇的,也是可以纠正的。
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党中央号召我们“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注:苏共中央1958年5月28日的决议,见《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106~1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3月版。)音乐界广泛地接触了外国的音乐家和音乐作品,也创作出许多表现我国各族人民生活、思想、感情的,有民族风格和高度艺术技巧的音乐作品,其中有许多得到国际音乐界的承认和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