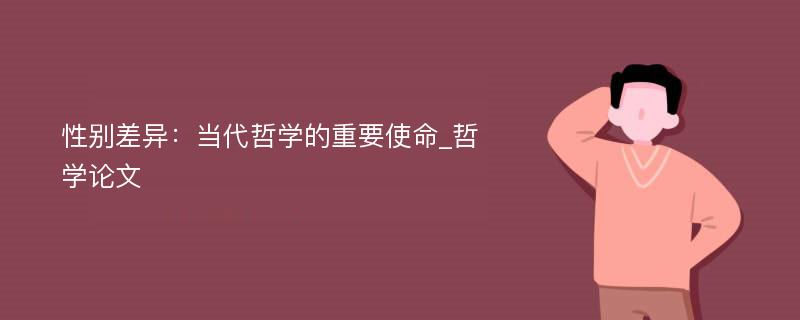
性别差异:当代哲学的重要使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使命论文,当代论文,差异论文,性别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探讨性别差异是当代哲学的重要使命,这并不仅仅是由于“性别差异问题即便不构成一个时代问题,也是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之一。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每一时代都有一个需要透彻思考的问题,而且仅此一个。如果我们进行透彻地思考,性别差异或许就是当今时代的那个能使我们获得‘拯救’的问题。”[1]也因为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已经在当代哲学思维领域掀起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性、性别与性别认同的范畴,主体与话语、主体与社会、文化与历史,以及主体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得到重新的解释,哲学也正在通过这些解释追逐着性别与人类拯救的曙光。
性别差异:形而上学探讨的历史反思
或许由于性别与种族繁衍之间的关联,自古希腊以来,哲学史上就不乏对于“性别差异”的探讨。大体说来,这些探讨可以分为三类:生物学意义、语言学和符号学意义,以及历史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意义的探讨,有时这三者也交叉在一起。
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探讨关系到一种“性别本质论”,即认为男女两性都具有由生物学因素决定的、不可改变的本质属性,例如相信女性的本质属性是肉体的、非理性的、温柔的、母性的、感性的、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关怀的和有教养的,而男性的本质属性是精神的、理性的、勇猛的、攻击性的或者自私的,这些本质属性对于男女双方来说都是不变的、具有普遍性的限定。在整个哲学史上,人们似乎总能发现这样的论述,例如“阳具中心主义”是弗洛伊德的第一原则,他认为潜意识的恋母情结结构是性别差异的基础,强调每一性别的身份和地位都与其自身的形态相关,女孩不同于男孩之处在于身体上缺少某种器官——阳具,因而她们将永远生活在“妒嫉”和“自卑”之中,“解剖便是命运”。
在后现代哲学家中,许多学者则对于“性别差异”采取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探讨,例如拉康相信,“语言结构是潜意识内在结构的外化”,或者说“潜意识是被内在结构化的一种语言”,他也试图从性、潜意识出发解释性别差异,以菲勒斯来置换弗洛伊德的阳具概念,认为语言符号系统作为社会的先在结构,试图表明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恋母情结”仅仅具有符号意义,而不是现实关系中的生理欲望。尽管拉康的这种理论突出了语言和社会文化在主体和性别生成中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但由于拉康依旧坚持菲勒斯中心主义和“阉割情结”等观点,因而他对于性别差异的解说仍未摆脱父权制的传统。
在哲学史上,许多学者对于性别差异也进行了历史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探讨,例如福柯认为,从纯粹陈述的意义上说,性别并不存在,因为它总是被置于历史文化之中,后者也总是以各种方式对性别进行构造,而且这些方式总是与不同的家庭模式联系在一起。因而,哲学的任务是揭示这些历史文化形式,说明人们为什么以及如何把性别建构成某种令人欲望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从社会意识形态意义上探讨性别差异,更为关注阶级和种族问题,把女性解放纳入到社会和人类解放之中。毋庸置疑,这些探讨都为女性主义哲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
同其他学科相比,哲学作为男性堡垒的历史更长,对于社会思想观念的影响也更为深远,因而,当今时代需要打破男性在哲学世界中的话语霸权,以女性主义为方法论探讨性别差异,在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上发出时代的巨响。
性别差异:女性主义哲学新视角
女性主义哲学认为,哲学话语并不是中性的,哲学描述并不提供普遍的视角,而是特权人的某种体验和信仰。这些体验和信仰深入到所有的哲学理论中,不论是美学、认识论还是道德和形而上学。传统哲学对于性别差异的探讨大都是以“人类”哲学的面目出现的男性体验和话语的反映,因而,女性主义哲学应当批评哲学中的男性霸权,并以消除所有霸权、追求哲学领域的平等和公正为重要使命。
女性主义哲学需要记录特定历史时代和条件下人们不同的性别体验和话语及其对于它们的哲学反思,并把这些差异的体验和话语看成是某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产物,相信它们在每一时代都构成独一无二的哲学形态。毫无疑问,这些体验和话语是由性别决定的,因为倘若没有性别差异,便不可能存在不同的性别体验和据此形成的话语。但从根本上说,这些体验和话语的差异是由社会和文化因素决定的,因为作为它们根基的“性别”不是生物学性别(Sex),而是社会性别(Gender)。
具体说来,女性主义进入哲学的使命在于:(1)分析批评“父权制”哲学知识论体系,重新思考和建构哲学知识,因为这些体系中存在着消除、压迫、排挤和漠视女性,以及社会边缘人体验和利益的危险;(2)把所有哲学概念框架和体系置于社会历史的背景下分析,要求哲学思考包括多元和差异的体验,哲学观念和知识本身必须是公正的、多层面的,必须通过过程、历史和关系来呈现;(3)打破哲学领域的性别霸权,把女性和边缘人的利益、体验和话语引入哲学;(4)在哲学领域掀起一场观念上的革命,开辟平等和公正的思维空间,追求一个更为理想的人类社会。
可以想象,当代女性主义进入哲学领域探讨性别差异时,势必在重重的围追阻截之中陷入种种的理论与实践困境。例如,人们或许会不停地追问什么是女性?谁代表女性?女性主义如何来说“我们”?哲学如何表现女性等无穷无尽的问题。的确,这些是女性主义哲学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而且恰好是由于这些作为前提性探讨的问题的存在,女性主义哲学研究才具有如此引人瞩目的魅力。这正如当代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所言,女性主义并不是先有一系列共同的前提,然后从这些前提出发,以逻辑时尚来建构一个方案。相反却是通过对于这些前提不断地进行批评思考来取得进步的过程,要努力使这些前提的含义更为清楚,在各种冲突的解释之间,在各种民主的、不和谐的声音之间进行谈判,这是因为:“性别差异并不是一种给予,不是一个前提,不是可供建立女性主义的基础,不是那种我们已经相遇并逐步理解的东西,而是鼓励女性主义者探讨的一个问题,是某种不能被充分强调的东西,因为它总在陈述的语法上遇到麻烦,它或多或少地保留作为一个永恒的追问。”[2]又如,当女性主义哲学试图颠覆传统哲学中的“父权制”知识和话语体系,在哲学领域引入女性和边缘人的体验和话语时,也立即遭遇另一个理论质疑:如何保证在这一引入过程中不陷入“性别本质论”的泥潭?作为对于这一质疑的回应,人们也应当意识到,性别的体验和话语并不是统一的,它们如同社会和文化,以及人性本身一样地丰富、差异和多元。从这一意义上说,无论是设想女性主义哲学试图基于女性生物意义上的独特体验,还是根据女性统一的体验来建构哲学理论,都是对女性主义哲学的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解。此外,在以往的“父权制”哲学背景下,很少有人探讨哲学的性别属性,因为它被相信是人类的神圣真理。因而,即便女性主义哲学已经问世,还有人仍旧不断地提出“女性主义哲学是否可能”,以及“我们是否有必要和根据什么来对哲学进行性别区分”的问题。这些疑问也反映出一些人对于女性主义哲学的另一种误解。女性主义哲学的最终使命既不是要建立“女性哲学”,也不是要建构“女性主义哲学”。换句话说,把女性和边缘人的体验和话语引入哲学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建构“女性(边缘人)哲学”和“女性主义哲学”,不如说是为了建构真正的人类哲学,弥补以往哲学在“人类”哲学外表之下的女性和边缘人的缺席。既然如此,为什么女性主义哲学还要打出“性别”的旗号?因为如果不强调性别,人们就难以意识到,并进而改变女性和边缘人在哲学中长期缺席,以及哲学领域男性和特权人称霸的局面。因而,女性主义哲学强调性别既是一种革命策略,又为时代和历史所需。当哲学真正地成为人类的哲学,每一个人——不论何种性别都能平等地以自己的话语来描述自己的体验,从而哲学变成一个平等和谐世界的时候,女性主义哲学便会自行地退出历史舞台。为了这一天的尽快到来,当代哲学需要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哲学也必须以自身的视角研究性别差异。尽管这是一个不断需要解构和建构的充满困惑和荆棘的旅程,但哲学和性别的解放,人类社会的拯救和进步值得人们为此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性别差异:当代女学者的使命
当代哲学需要研究性别差异,女性主义哲学肩负重要使命,这一使命也对当代女学者提出时代的要求。
首先,这一使命要求当代女学者具有为了信仰和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因为女性今天的解放程度,女性主义哲学的诞生本身就是无数先驱者以生命为代价奋斗的结果。公元415年,在亚历山大城,古希腊女数学家、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学派领袖希帕提亚(Hypatia)被一群狂热的基督徒残忍地杀害。据说当时这群暴民用锋利的牡蛎壳一片一片地刮下她身上的肉,然后把她的身体砍成段抛入烈火中,这位自称“已经与哲学结婚了”的把美丽与智慧集于一身的伟大女性就这样勇敢地为哲学、科学和信仰献出了生命。而今,哲学领域的一本著名女性主义哲学杂志便以她的名字来命名,希帕提亚也自然地成为当代女学者的榜样。
其次,这一使命也要求当代女学者具有一种忍辱负重,不畏人言,敢于抗争和挑战“权威”,并在困境中发展成长的勇气。在女性主义哲学方兴未艾之时,一些人会对这一领域,以及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女性充满怀疑和误解。长期以来,父权制压迫已经形成一种隐性的内在逻辑:把某些为父权制所期待的“女性气质”作为固有标准强加到所有女性身上,并让人相信这些是女性与生俱来的、纯天然的气质,而那些不愿意就范的女性便被贴上“非女人”或者“缺乏女性气质”的标签。即便在当今社会,一些受这种思维惯性影响的哲学家也会认为女性主义哲学不是哲学,从事女性主义哲学研究的女学者也不再是女人,因为她们已经失去女性的魅力。面对这种局面,当代女学者必须以非凡的勇气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学术和生活之路,“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因为女性在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是前辈不屈不挠奋斗的结果,当代女学者只不过是这场历史拉力赛中的一代火炬手。
再次,这一使命还要求当代女学者具有智慧的方法论。在父权制之下,无论是在哲学还是文学中,女性总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女性文本和写作永远裹挟着某种焦虑和不安。桑德拉·吉尔伯特在《阁楼里疯女人》中曾描述出父权制下女作家的境遇:父权制的介入使她陷于一种关于自身“作家身份”的困惑之中,因为她在自己的作品中,总会听到嘈杂含混的“他”的声音,她总是需要摆脱焦虑和寻找平衡。借助吉尔伯特的这种描述,我们可以对于父权制下的女性之“疯”作出如下分析:它既是对于男性和特权人话语霸权之下女性受压迫状况的反映,也是女性对于这种霸权的反叛,同时还是一种重要的文学计策。也就是说女作家正是凭借着“疯”来改变父权制对于女性的界定,以一种对自己来说近乎精神暴力的行为来逃离男性的文本和住所,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怒火。而今时代,女性主义哲学不必再如同以往的女性文学一样把“疯”作为一种计策,但它仍旧需要以某种计策来突破、修正、解构和重构哲学,这种计策亦可被称之为“智慧的方法论”。可以说,女性主义哲学的丰富也意味着这种方法论的完善,每一种女性主义哲学都可以为这种方法论做出独特的贡献,或许如同性别差异一样,这种方法论本身就构成女性主义哲学的一个与生俱来的、恒久性的追问。就当代而言,女性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策略或许是充分利用传统哲学中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肥沃土壤来生长,例如它并不需要彻底捣毁传统哲学中的“理性”范畴,而是要剔除这一范畴中的男性和特权人霸权的成分。又如,它应当立足于当代哲学在各个学科中发展,因为在女性主义观念中,哲学与人类思维本身都是无屏障的和无疆界的。
“心灵是通向世界的唯一窗口”,当代女学者需要用心灵来从事女性主义哲学和性别差异研究,有心灵的地方便有窗口的存在,当代女学者也正是要通过这方窗口走向世界,使哲学真正地成为人类的哲学,使世界真正地成为全人类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