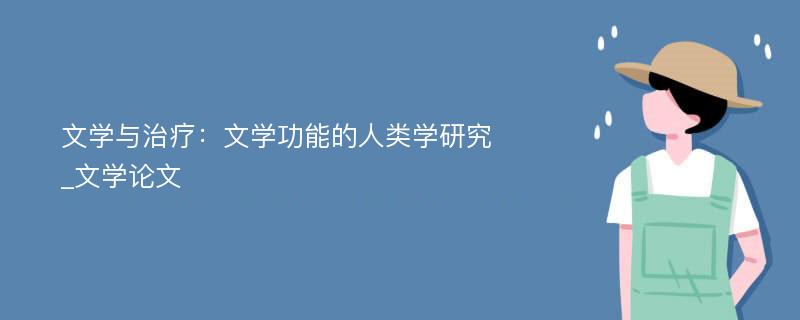
文学与治疗——关于文学功能的人类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文学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有的文艺理论教科书大同小异地把文学功能归纳为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其合理性已获普遍认可,但毕竟未能完满地解答“人学”的所以然。文学是人类独有的符号创造的世界,它作为文化动物——人的精神生存的特殊家园,对于调节情感、意志和理性之间的冲突和张力,消解内心生活的障碍,维持身与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健康均衡关系,培育和滋养健全完满的人性,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基于对文学的文化意义的上述理解,本文拟就这一被忽视的方面做初步的研究,借鉴现代人类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的角度和成果,在比较文化的大视野中探索文学艺术对个人生命的治疗功能及对社会群体的文化生态作用,以期为构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人类学理论提供若干基石。
从史论结合的意义上看,文学与治疗这个题目可以分别在“作为治疗的文学史”(个案研究)和“文学幻想的治疗原理”两个方面有所开拓。本文仅对后一方面作一些探讨,着重解答以下两个层次的问题:
一、文学治疗功能的发生学透视
中国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一个小丑进城,顶得上三车药物。”话中透露出关于喜剧性演出特有的医疗功能的思想。无独有偶,西方中世纪有个谚语用相反的方式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不论在何处有三位医生,那就至少有了两位不信神的人。”常人精神方面的困忧要诉诸神意来寻求解脱,而医生则另有一套开心释神的技术,巫医的歌舞表演便是此种专业技术之本来面目的见证。
不论何种性质的表演,都是人为构建的一种符号情境,其虚幻的性质毋须论证,而其对人类精神生存的生态功用则大有深究的必要性。扩大来说,语言虚构的文本也有同类生态功能。
在古希腊神话中,大地女神得墨忒耳因失去女儿佩尔塞福涅而悲伤不已;四处流浪去寻找女儿,精神沉重得几乎失常。一位名叫包玻(Ba-ubo)的保姆在她面前跳起猥亵的舞蹈,终于使女神破泣为笑。日本神话中记述着一个惊人相似的场景:天照大御神受到大闹天宫的弟弟速须佐之男命惊吓,躲进天石屋里,关上石门,高天原一片漆黑。众神齐集,让一位泼辣的女神跳起狂放猥亵的舞蹈,样子如同神魂附体,敞胸露乳,腰带拖到阴部。众神大声哄笑,受惊吓的天照大御神解除忧虑,重新被诱出天石屋,世界重现光明。(注:安万侣:《古事记》邹有恒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1页。)弗莱认为神话中的这类场景足以说明喜剧性表演同样具有某种“宣泄”(Catharsis)功能,而这却是亚里士多德未能讨论到的。如果我们考察早期喜剧作家如阿里斯托芬的作品,就会发现其猥亵的程度是何等惊人。也许人们会奇怪,当时那种脱胎于神圣仪式的戏剧表演岂能容忍如此放肆的内容。弗莱认为,显而易见的是,猥亵作为一种精神释放的形式是必要的。正是此种释放有助于形成喜剧的节庆气氛,当时的喜剧演出同一年之中的某些节庆时期密切相关。(注:弗莱(N.Frye):《作为治疗的文学》(Literaiure as Therapy),邓南(R.D.Denham)编《永恒的创造活动》(The Eternal Act of Creation),印地安纳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0页。)在这里,文学艺术活动作为特定文化系统中周期性的节庆礼俗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何发挥着对该文化成员精神生活的张弛有序、庄谐有度的自主调节作用,似可得到有效的说明。人类学方面关于节庆礼俗的功能研究、文学理论家巴赫金关于文学狂欢化的论点,使我们看到二者之间的某种内在的实质性对应关系。仪式行为也好,文学创作也好,作为人类符号活动的两大领域,在制造虚拟情境宣泄释放内在心理能量,以便保持精神健康方面,确实具有类似的功效。
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借助于人体象征性动作的仪式行为发生在先,借助于语言符号的文学发生在后。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把文学象征的世界当作仪式象征世界之延伸或置换。从历时关系着眼,史前社会中仪式表演(萨满、巫医等法术)乃是文学滋生的温床和土壤。到了文明社会之中,仪式表演转化为戏剧艺术,仪式的叙述模拟转化为神话程式,仪式歌辞转化为诗赋,巫者特有的治疗功能也自然遗传给了后世的文学艺术家。在枚乘作《七发》为楚太子治好病的著名情节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历史转换完成之际,文学家得自巫医的虚构致幻技术如何发挥着强有力的精神医学作用。
吉西·韦斯顿在《从仪式到传奇》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中指出,是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开辟了从巫术礼仪出发探索文学起源的新途径。仪式活动的中心主题是死亡与复活,表演和观看神的死亡与复活对于维系人的精神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原始的仪式到基督教的礼仪体系,再到欧洲中世纪的英雄传奇,同样的主题以不同的形式发展延续下来,在诸如渔王传奇、寻找圣杯的传奇等文学样式中获得整个民间社会的认同。(注:韦斯顿(Jessie L.Weston):《从仪式到传奇》(From Ritual to Romance),麦克米兰公司,纽约1941年,第1-8页。)这一现象背后的信仰和精神生态氛围的再发掘,或许可以有助于我们体认某些生命力持久的文学主题对于社会的精神生存的特殊性与必要性,进而对文学之所以存在和不衰的本体原因有所领悟。
仪式行为作为象征性的动作演示,是人类特有的符号能力之显现。文学作为象征性的语言表现,当然可以视为仪式表演的语言延伸物,因而也体现着虚构和演示的特征。著名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在《表演人类学》中指出,如果说人类是一种智慧动物,一种制造工具的动物,一种自为的动物,一种使用符号的动物,那么同样可以说,人类是一种表演动物(a performing animal)。诚然,马戏团的动物也是表演动物,不过,人的表演是自我表演,其演示将反归自身(reflexive),“他在表演中向自己揭示自己”。(注:特纳(Victor Tumer):《表演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Performance),PAJ publications,纽约1988年,第81页。)人类特有的这种反归自身的表演对于文化整体究竟有何功能呢?诚如人类学家理查德·谢克纳所概括:以毕生之时间钻研仪式的特纳最终确认,仪式表演是社会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人们解决危机的重要方式。
特纳很快意识到,社会过程就是表演性的。于是他展开了对仪式与剧场之间复杂微妙关系的详细探究。他先提出关于社会剧(Social dra-ma)的理论(1974),然后在《从仪式到剧场》(From Ritual to Theatre)中集中思索表演的本质。(注: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维克多·特纳最后的探险》(Victor Turmr's Last Adventure),见特纳《表演人类学》一书代序,第7页。)
表演行为的实质在于帮助个人和社会解决物质和精神诸方面所遇到的危机,这种寻根追源性的认识对于各种文学理论或艺术原理教科书中所强调的文艺的审美娱乐功能说,自然是一种严肃的修正或补充。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在现实功利目的的仪式性表演伴随着社会发展、理性的进化而逐渐消亡的过程中,非功利的,纯粹娱乐和观赏性的戏剧表演才得以作为替代物而发生。同样,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最初绝不是为了阅读欣赏而存在的,它的发生同旨在解决危机的仪式表演活动密不可分。神话学家对于神话与仪式关联已有充分的论证。(注:参看多蒂(W.G.Doty)《神话编纂学:神话与仪式研究》(Mythography:The Study of Myths and Rituals),阿拉巴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特别参看第163-166页“神话与仪式的心理学功能”。)而诗歌与祝咒和祈祷的因缘也得到人类学者和文学研究者的双重关注。(注:参看雷曼(A.C.Lehmann)编《法术、巫医与宗教》(Magic,Witchcraft,and Religion),梅菲尔德公司1985年;拙作《诗经的文化阐释》第二章“诗言侃”,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仪式活动本身如何在初民社会中充当了治疗手段,尚可以从现存的印第安巫医活动中获得直观的证明。日本人类学家吉田祯吾记录了墨西哥南部城镇的西班牙人天主教教堂中发生的一幕:被视为巫医的印第安人,在这座教堂的圣彼得的圣像前摆着蜡烛,用火点燃后,在巫医患者夫妇的右侧用佐齐尔语高声诵读咒文。这种在天主教堂内举行的印第安巫术性治疗礼仪,给人类学者留下奇特的印象。(注:吉田祯吾:《宗教人类学》王子今等译,陕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5页。)类似的治疗仪式活动在我国诸多少数民族中十分普遍,下面一段描述提供了戏剧和文学发生的活化石:
在珞巴族中间,那些使人生病的恶鬼均是巫师驱赶的对象,驱赶时先将它们的替身在病人身边转几下,再边念咒边把它们带到远方;博嘎尔部落的“纽布”跳鬼治病时,披红毯,执大刀,在一晒箩中跳来跳去并念念有词;有的把羊头扔进火里,取出后装进竹筒里,戴在病人头上病即治愈;……苗族认为人生病是“法翁”鬼作祟所致,届时巫师在患者家门前唱巫词并请它领受供品,鬼即请到,然后巫师把祭物陈于村边祛鬼处,请其吃喝,求其使病人痊愈,巫师念唱文后作法送鬼,并把草船和鸭子放入溪水,然后与祭鬼者一起吃肉喝酒。(注:于乃昌、夏敏:《初民的宗教与审美迷狂》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8-239页。)
当我们把注意力从巫术治疗仪式转向巫词咒语本身时,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与表演活动的起源紧密联系的神圣诗歌之形式特点。英国汉学家霍克斯敏锐地指出,《楚辞》和《山海经》中依次列举各地地名的惯用套式来源于巫术文学的功能需要:“《招魂》和《大招》两首诗列举宇宙各方威胁游魂的诸般危险时便有这样的例子。《山海经》中依次列举各座山岳,有仪式化的宗教的含义,采用的全是上述依次列举的方式。《山海经》和《招魂》、《大招》都是那种受巫术的、仪式化的思想模式制约的文学作品。”霍克斯还认为,作为一种文学表现的原型,这种按照空间顺序依次列举的格式并不仅限于汉民族的古典文学,它经常以多种不同形式出现,“各种各样的祭文、符咒,包括基督教祷文结尾处三位一体中的圣父、圣子、圣灵三者的符咒,都是例子。”(注:霍克斯:《求宓妃之所在》丁正则译,《楚辞资料海外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8-179页。)如果把依次列举的叙述法看成巫医致幻的一种技术手段,那么中国文学史上特有的体裁——汉赋的发生便同此种技术脱不开关系。不论是具有“发蒙”之效的性幻想之作《高唐赋》,(注:参看拙作《发蒙:性梦的精神启悟功能》,《淮阴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还是以“解惑”为治疗手段的《七发》,都可以作为催眠——致幻技术成功运用的范例来看。
《七发》写吴客用七种虚拟情境来疏导楚太子的心理障碍,从攻心入手来治疗其身,收到了针灸药石所不及的奇效。七件事的铺叙由小到大,从音乐、饮食、车马、宫宛、田猎写到观涛,最后要为太子荐方术之士,太子随着叙述的展开而驰骋其被压抑的幻想力,精神的荡涤带来生理的变化,出了一身透汗之后,病症全然消失。赋中吴客的“要言妙道”以及所荐之方士均让人联想到远古的巫医治疗传统。
二、文学与精神医学
说到文学的治疗功能,人们会习惯地认为这是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移植到文艺学中的结果。从溯本求源意义上看,这里存在一种历史的误会:20世纪以来精神分析学确实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学的提出也曾受到19世纪以前文学艺术史的潜在影响。弗洛伊德和荣格都不只是临床医师,而且也是文学素养深厚、对艺术文化史有着独到领悟的学者和思想家。并不是他们的个人天才把某种治疗功能赋予了文学艺术,而是他们慧眼独具地把握住文学本有的这一方面功能,并通过精神分析学的建构而使之系统化和理论化了。精神分析曾被简称为“谈话治疗”(talking cu-re);哲学家保罗·利科又称之为“进入到对仅有的那一部分可以言说的经验之研究领域”。(注:利科(P.Ricoeur):《弗洛伊德写作中的证明问题》(The Question of Proof in Freud's Wruing),《精神分析年刊》1971年第25卷4期,第838页。)这些说法都揭示出精神分析作为某种语言技术的实质,这同作为语言艺术形式的文学本来就是完全相通的。
精神分析的治疗效果通过医生与患者之间的语言交流而实现;文学的治疗效果则是通过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语言虚构世界而实现。精神分析的疗效原理建立在人的意识与潜意识的相互作用之上;文学虚构的世界其实也同样离不开意识与潜意识、理性与非理性、智慧与幻想的互动关系。上述类比可以说明,早在以1900年问世的《释梦》为标志的精神分析学诞生之前,是文学充当着“谈话治疗”的精神医学角色。从这一意义上可以引申说,文学艺术家作为人类灵魂的铸塑者,其实也是一批不挂牌的精神医护者(当然这些医护者之中有不少也兼为患者)。从文学起源上看,最早的文学样式神话与诗歌都曾在那种政教合一、巫医不分的部落社会的精神生活中扮演着法术和信仰工具的重要作用。
许慎《说文解字》释“巫”字云:
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褎舞形,与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凡巫之属皆从巫。
刘师培作《舞法起于祀神考》,发挥《说文》的观点说:“案:舞从无声,巫无叠韵。古重声训,疑巫字从舞得形即从舞得义,故巫字并象舞形。盖古代之舞以乐舞为最先,《吕氏春秋》言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入阕,又言阴康氏作为乐舞以宣导其民,此其证也。而古代乐官大抵以巫官兼摄,……盖周官瞽朦司巫二职。古代合为一官,乐舞之用虽曰宣导其民,实仍以降神为主也。”(注:刘师培:《舞法起于祀神考》,《国粹学报》1907年,第27期。)其实“降神”与“宣导其民”并不矛盾,因为在神权至上的时代,与超自然力相沟通的巫者才有资格作民众的精神导师。(注:参看周策纵《古巫医与六诗考》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原始文艺的医疗原理,正是在精神支配肉体的意义上方可透彻理解。研究彝巫的学者王光荣写道:
驱鬼祭祀,本是一种巫法活动,然而它对于病患者来说,往往是一种心理治疗,情绪治疗或叫精神治疗。那些信神信鬼的病患者,通过接受腊摩的巫法处理,解除精神上的压力和负担,情绪豁然开朗,这就为病情的好转,提供了精神支柱。特别是有的仪式,腊摩不仅念经诵词和作些象征性的动作,而且还正面接触患者的身体。(注:王光荣:《通天人之际的彝巫“腊摩”》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2页。)
精神支配肉体这一原理不能简单地视为巫医时代的迷信,80年代兴盛起来的“整体医学”正是基于这个原理之上:人的精神状态可以通过增强中枢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功能的方式,来达到改变身体状况的目的。美国整体医学会主席西格尔博士写道:只有无法医治的人,而没有医治不好的疾病。(注:西格尔(B.S.Siegel):《爱·治疗·奇迹》李松梅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151页。)治疗的巨大潜能就隐埋在病人的无意识之中。关键在于如何开发和利用这种能量。
后代的作家、诗人们是远古巫医精神治疗传统的真正继承者,他(她)们充分利用了萨满巫师等的致幻能力,发展出替代性的文学幻想,把针对他人的谈话治疗演变为既可应用于他人,又可适用于自己心理障碍的语言虚构疗法,其基本的治疗原理仍然在于充分发挥意念的能动作用。试看唐代诗人杜甫《寄韩谏议》一诗:
今我不乐思岳阳,身欲奋飞病在床。
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
鸿飞冥冥日月白,青枫叶赤天雨霜。
……
杜甫一向被推崇为写实诗人,其幻想难量被低估。身体的“病”从生理上限制了诗人的活动空间,只能暂时以“在床”的方式养息;可是疾病却未能限制诗人的想象空间,使他卧病在床的时刻反能够幻想到现实中没有的景象。那洞庭湖畔濯足的美人,有如但丁《神曲》引导诗人灵魂遨游的天使,带领病人做超越时空的自由翱翔,在壮观的自然景象中将自我与宇宙融为一体。这种诗歌幻想中的意念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作诗者往往对意念的超现实力量有自觉意识。正如《古文苑》所收汉人伪托“苏李诗”之一云:
浮云日千里,安知我心悲?
思得琼树枝,以解长渴饥。
文学不仅为诗人、作者们提供了自我治疗的途径,而且也为人类的精神医学提供宝贵的案例。法国学者克洛德·芬兰在《鲁迅〈狂人日记〉与弗洛伊德》一文中别具慧眼地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部杰出作品对于跨文化精神病学所具的意义,他写道:
不论是真实事件还是文学塑造,《狂人日记》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使我们对发生于中国的“迫害妄想症”病例有了新的认识。这并非临床观察,而是一份文学资料,表明世界各国的“迫害妄想症”的构造形式各不相同,单纯地都归之为“妄想症”不太合适。……鲁迅写《狂人日记》的宗旨是启发他的同代人思考隐蔽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的这种“迫害狂”背后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篇小说也可以成为现代科学的研究对象。(注:克洛德·芬兰:《鲁迅〈狂人日记〉与弗洛伊德》施婉丽译,《中国比较文学》1988年,第2期。)
美国批评家特里林的《艺术与精神病》一文中写道:
当弗洛伊德在他78岁的诞辰庆祝会上被誉为“无意识的发现者”时,他放弃了这个权利,认为无论自己对系统理解无意识作过怎样的贡献,荣誉都应归功于那些文学大师们。(注: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艺术与精神病》(Art and Neurosis),亚当斯编《柏拉图以来的批评理论》加州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959页。)
这并非弗洛伊德自谦托词,它明确地告诉世人:文学对无意识心理的发现如何为精神分析学的诞生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如果我们承认文学大师的创作离不开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学传统,文人的文学(高雅文学)是以俗民的文学(大众文学或通俗文学)为基础或土壤的,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地附和弗洛伊德的说法把无意识发现者的桂冠戴在个别文学大师头上,而应当进一步沿波讨源,从文化生态系统的总体中追溯文学得以发生和存在的主体心理根源。这就意味着要透过作家创作的表象去追问更具有自发性的民间文学之所以传承不衰的内在动力之源。
20世纪后期的跨学科研究获得长足进展,在文艺学和人类心理学之间的森严壁垒已被打破。某些具有超学科意识和知识结构的学者先行一步,对上述问题做了初步探索。列奥·施奈德曼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神话、民间故事和宗教的心理学》一书中,解析了埃及的奥西里斯神话、古希腊的吉生(Jacon)与美狄亚(Medea)传说,古印度的罗摩与悉多故事,以及其它的神圣戏剧,得出如下结论:“神话与仪式表演旨在满足人类个体和群体的精神及物质需求。”他指出,从心理动因方面看,神话以奇异的故事传达着人类无意识中的希望与恐惧。神话本身并不直接表明其潜存的内在动因。作为替代形式,我们所面对的总是象征性的伪装和精制的外观,就像在梦的运作中常常出现的那样。这种改装的目的在于解除希望与恐惧的情感冲击力。不然的话,那些足以诱发罪恶的强烈希望,或那些具有潜在伤害力的恐惧,就会在经验中危及个人的安全或集团的存活。相形之下,神话一定会象征性地满足持续不断的情感需要,而无需让其公开露脸。(注:施奈德曼(Leo Schneiderman):《神话·民间故事和宗教的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Myth,Folklore,and Religion),芝加哥1981年,第187页。)在施奈德曼看来,古老的神话所发挥的心理调节功能随时代演进而变换表现形式,但从来未曾中断,这正是因为人类心灵需要的内在动力永不衰竭。神话思维时代结束以后,是民间故事、传奇之类叙事作品继承着神话的幻想作用。现代以来又有了科学幻想小说继续发挥着神话般的职能。科幻作者们同神话讲述者一样,只能构想一种充满矛盾和悲伤的世界。在那里,和平与合谐只是瞬息即逝的偶然。那些怪异的外星生物无非是人类灵魂的镜像而已,正如古人所构想出的神灵不过是人的变相投影,外星生物和古代神祇对于人类想象力来说,都是要确认超人的可能性,其内在动因都在于超验的渴望。(注:同上,第197页。)按照这种逻辑,人类似乎不能仅仅存活于现实经验之中。作为具有想象力的动物,人需要在经验与超验之间、理性与幻觉之间取得自身精神生态的平衡。如此视点的解说,有助于真正理解文学存在的理由为何,人类为什么自古及今离不开文学,在茹毛饮血的洪荒时代需要它,在电子时代的地球村中依然需要它。
即使是理性和哲学的存在,原来也离不开神话、想象和隐喻的土壤。弗莱为此把文学称作“作为纯粹理性批判的文学”,旨在凸显其对于人性完整的调节使用。他引用罗素和怀特海的见解,提出如下比喻:想象的背景是裸体,哲学是罩在这裸体外面的语词的衣裳。并进一步阐述说:“我一生试图研究的正是这种隐没在(哲学衣裳)后的裸体,我称之为隐喻的或神话结构。在我看来,如同罗素和怀特海所说:许多哲学都是在隐藏这种内在结构的种种尝试中形成的,而文学却更直接地把握它,一代又一代地再创造它。文学批评的主要功能就在于帮助我们更加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种‘神秘的想象的背景’,因为它过去在发挥作用,现在仍然在发挥作用。”(注:弗莱:《作为“纯粹理性批判”的文学》(Lite-rature as a Critique of Pure Reason),《神话与隐喻》(Myth and Metaphor),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69页。)
作为意识形态形式的哲学与文艺之间的这种潜在依存关系,归根结底是人性本身内在张力的体现。失去了感性制约的纯粹理性单向发展有可能导致人性的异化,正像失去理性控制的非理性放纵会导致疯狂一样。只有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同存在主义的“我舞故我生”统合协调起来,健全完整的人性方能得以维系。文学对于人性的生态平衡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在《一千零一夜》的框架故事中已清楚地看到,若没有智慧少女山鲁佐德用讲故事的方式给国王施行“谈话治疗”,那位丧心病狂的人君是怎样陷入精神失常而不能自拔,又会有多少无辜者将沦为杀人报复狂的牺牲品?
综上所述,文学的发生同以治疗为目的的巫医致幻术有潜在的关联,文学在人类文化史上长存不衰,正因为它发挥着巨大的精神生态作用,使人性的发展在意识与无意识、理性与幻想、逻辑抽象与直觉体验之间保持平衡。现代精神医学的建立曾充分汲取文学家的治疗经验(包括自我治疗和文学病例),它的未来发展也有待于对文学艺术治疗功能更进一步开发和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