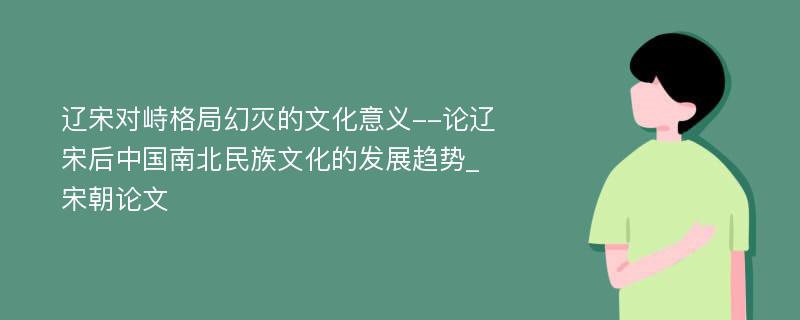
辽宋对峙格局破灭的文化意义——简论辽宋和盟后所奠定的中国南北民族文化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文化论文,发展趋势论文,中国论文,格局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宋初年,率部属降齐的大将郦琼,入金后曾与人分析时局说:“每见元帅国王(指宗弼——笔者注)亲临阵督战,矢石交集,而王免胄,指麾三军,意气自若……江南诸帅,才能不及中人,每当出兵,必身居数百里外,谓之持重。或督召军旅,易置将校,仅以一介之士持虚文谕之,谓之调发。制敌决胜,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体,愚者丧师。”“颇闻秦桧当国用事。桧,老儒,所谓亡国之大夫,兢兢自守,惟颠覆是惧。”“不即覆亡,已为天幸,何能振起耶?”[①]
郦琼之论,从当时中国南、北对立双方官僚的士气、心理状态入手,揭示了民族性格上的差异,阐发了南、北方之间优劣的比较,颇为中的之论。他大约也道出了当时许多降金将领、臣僚的共同心声,也基本道出了当时南、北方两种文化体制之间,在“形”与“质”上的迥然有异的差别。
那么,当时呈现的中国南北方之间颇有差别的文化,各自具有怎样的发展内涵,是怎样形成的,易言之,其发展趋势如何?本文试图依据当时的史事与实际情况,从宏观上把握当时南北方文化发展的时代脉膊,并祈方家不吝赐教。
一
公元12世纪初,当女真族建立的金政权在1125年、1127年先后灭亡辽和北宋后,标志着中国历史上自10世纪初以来,由辽宋双方苦心经营、共同维持了百余年的南北对峙分立的政治格局,在金朝政权的强大武力打击下,彻底瓦解了。因此,当时无论是辽国的遗族,还是宋朝的亡臣,都力图根据自己切身的政治体验,来判明格局变换后的发展前景,以便为自身利益及处身于其中的政治集团利益寻求一个可靠的寄托,谋求政治上的保障和继续发展的前景。
就辽朝的亡族而言,萧海里、耶律余睹等人,最初以不满意辽天祚朝的政治现状而投入女真之中,并积极指引女真军队攻掠辽朝的州县和人口;及辽朝被灭亡以后,余睹发觉自己想借女真力量来拥立晋王的设想难以实现时,便积极策划起兵反金以恢复辽朝的故土和宗室的权力[②];直到金海陵王时,犹有萧裕、耶律朗等亡族,策划拥立天祚之孙,来恢复大辽帝国的统治[③];但,这些均未能成功。于是发生了金海陵王末年时的大规模的契丹撒八之乱,目的也是想恢复辽朝的统治,当起义受挫后,撒八遂决意率契丹遗众脱离金国,西投大石[④]。契丹亡族,在入金之后,复国的企图始终未能泯灭,直至金亡,仍此起彼伏。
同时,当辽天祚帝被俘之后,大漠以北又同时出现了两个亡辽遗族建立的政权,一以天祚之子梁王雅里为首,活动于“沙岭”之地,建元神历,大约维持了10余年的统治,及雅里死后,其政权遂不知所终,大约是受到金人的压力,而被迫远徙,融入了当地的游牧部落集团之中。这个政权存在的时期,基本上沿用和承袭了辽朝的文化体制,史称雅里“每取唐《贞观政要》及林牙资忠所作《治国诗》,令侍从读之”[⑤]。而其所统治的人口,大都是接受中原影响较少的乌古、迭烈诸游牧部族,所以建国伊始,便丧失了统治的基础。而另一以耶律大石为首建立的西辽政权,则是大石在与天祚分背之后,转入漠北草原地区,追述祖制,获得了诸部的支持,并逐渐转徙抵达中亚草原建立了稳固的统治,现知其国家机构中仍沿用了南北面官体制和“属国属部制”等“祖制”,并将中原文化输入中亚地区,最终又与当地的各族人口融为一体,并将辽朝的文化体制远被中亚各国。
而1125年当金兵直抵汴京城下之际,徽宗禅位于钦宗,在群臣朝议强烈要求制裁造祸主谋的呼声中,钦宗遂对王黼、童贯、赵良嗣等及前朝诸执政大臣进行了严厉制裁,同时,也严格约束宗泽等主战派力量。于是,将北宋朝廷的政治态度,首先自徽宗时“不顾盟好”的立场转变到卑躬屈膝、忍辱求和的方面,并再变到拾起“存亡继绝策”的态度上来,这是一种求和不成被迫开战的消极态度。自北宋从金人手中赎回燕山后,便屡遣间使北上,欲与金约和;钦宗即位后,更因间使欲与入金的辽之旧臣、遗族相约,共图金人,以恢复辽宋故局,由于行事不谨,而屡次激怒金人,结果“宋少帝(即钦宗)诱萧仲恭贻书余睹,以兴复辽社稷以动之”,萧仲恭献书于宗翰,这样又给金人败盟的口实,“宗翰、宗望复伐宋,执二帝以归”[⑥]。
北宋灭亡后,金人尚无力直接统治中原地区,遂于天会五年(宋靖康二年,1127年)三月,别择宋臣张邦昌为傀儡皇帝,国号大楚,以统治宋之故土人民。而张邦昌在中原亦不敢以帝号自居,遂上书劝进康王赵构于归德;赵构即位,首诛邦昌。其后,“遣王师正举表,密以书招诱契丹、汉人”,结果又被宗翰截获,于是金太宗“下诏伐康王”[⑦]。1129年,赵构遂南逃扬州,中原之地遂为金有。金天会八年(宋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金人又立宋降臣刘豫为大齐皇帝,总治中原事。此时,也正是康王赵构建立的偏安政权与金人“解仇仪和”的开始阶段。当时南宋宰臣秦桧建言于赵构曰:“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⑧],即倡言以黄河为界,其北归金,其南归宋。从此,南宋政权遂积极致力于打击控制河南的刘豫集团,为实现金宋和盟创造条件。终于宋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1137年),金朝废齐国,以河南、陕西地归宋。但不久,金兵统帅宗弼又统兵南下,尽复河南陕西之地,从此金宋双方又开战端。至金熙宗皇统二年(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金宋之间始成盟约,“约以画淮水为界”[⑨]。
至是,自辽宋末年以来,南北之间变换不定的政治局势,才重又稳定下来,形成金与南宋之间以淮水为界的南北对峙的新格局。这样,自金太祖1113年起兵抗辽,至1141年金宋定盟,中国南北大地先后经历了30年的铁血相争的过程,最终打破了一种旧的政治格局,而建立了一种更为广阔的北南对峙的新局面。
应当说,当辽宋之际的政治格局一旦破灭之后,曾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以及人类的社会生活领域,都产生了极大的触动。首先,一种新的政治统治秩序——金朝,毫无保留地囊括了契丹辽朝的旧有版图,同时又攘取了北宋统治的中心地区——黄河流域,以后又过渡为金朝的统治重心。其次,作为辽朝政权和北宋政权的文化体制的延续,其残余势力都纷纷呈现了大规模的退缩趋势。作为辽朝的延续,雅里的后辽与大石的西辽政权,在保有辽朝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前提下,已分别后撤至远离辽朝统治中心的漠北草原和中亚草原地带;而作为北宋政权的延续,南宋政权在保留了各项祖宗旧制的前提下,已退出中原而偏安江南。在这种形势下,生活于辽、宋故地的大部分人口和脱离辽宋故地的一小部分人口,都程度不同的经历了一次漫长的血与火的“洗礼”,同时,也经历着异族文化侵入和同异族文化相融的痛苦的历程,像契丹故族被编成“猛安谋克制”,汉族被施以“剃发令”,这些严格的强制同化措施,客观上无不激起彼此双方在社会观念方面的巨大变革。这一切,无不猛烈地撞击着当时辽宋故国所有区域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刺激着辽宋故国内那些持有不同政见的地主阶级士人,面对金朝和辽、宋的孑遗,进行重新的分化组合。这种组合过程完毕之时,就是南北方政治局面的重归稳定之日。所以,金朝政权能够叱咤一时,或多或少的也是借助了辽宋集团内部分化的政治风云,经历了30余年的过渡阶段,才奠定了大金帝国的历史地位。但是,在这过渡时期的前后,客观上却最终演变为自发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的效果,伴随着历史步伐的前进,有金一代历史文化发展的最直接的结果,是继承了辽朝多源汇聚的社会文化内蕴,并继续将之推向成熟一体的发展过程。
但也应当看到,辽宋曾经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区系的民族政权的灭亡,必然要保留一些相应的文化孑遗。事实上应该承认,北宋时期社会文化的发展,在中晚期以后已渐入颓废、偏隘、毫无进取的境地,所谓“心性”之学,成为其思想文化中的主流;而辽朝虽然也借鉴了以儒治国的经验。但主要借鉴的还是儒学富于活力的“经世治用”的思想,实用原则是当时北方文化发展的主旨所在;这完全代表了二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二种性质迥异的文化模式,但二者间有联系也有对立。像南宋、西辽与后辽政权的延续,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这二种文化形态孑遗的存在。虽然,就某种程度而言,强大的政治力量也可以对相异的文化区域实行某种程度的占领,但最终必将随着文化相一性的出现,而形成对该占领区域的真正统一的过程。辽、金文化,同属于起源于中国北方地区的中华文化发展中的奇葩,其文化基础具有极大的相近性,这是北方民族文化的特点决定的。但是,就12世纪初辽、宋、金三方区域间所处的文化发展阶段而言,相互间既有很大的差异,也有很大的联系,如辽宋与辽金之间文化的联系,固然是有很大成份的;而宋金之间的文化比较,则具有明显的差别。所以,当金灭亡了辽、北宋政权后,却不能灭亡辽与北宋各自的文化机制;当一种新的或者说相对落后的文化体制侵入辽、宋文化区系后,势必会产生巨大的撞击力,而形成新的政治抗衡集团。由于区域文化发展所决定的人们在意识观念系统上的差异,促使其演化为政治斗争的方式而表现出来。这就是南宋、后辽与西辽政权之所以能延续下来的重要原因。当然也还有其他的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归根结底,人类社会内的一切政治上的抗衡,都是一种文化上的抗衡手段。
二
关于辽、宋亡国的原因,北宋遗臣众口一辞的责难宋徽宗,弃辽宋百年盟好不守,是造成宋辽先后亡国的主要原因。靖康二年(1127年),当徽、钦二帝被拘金营时,留守汴京的北宋群臣也自言:“顷缘奸臣败盟,结怨邻国,谋臣失计,误主丧师,遂致生灵被祸,京都失守。”[⑩]而南宋初人庄绰则更以悲天悯人的态度,将亡国之痛,归咎于徽宗“渝盟”之举[(11)]。
其实,这种看法的产生是和北宋中期以来形成的毫无生机的思想意识形态息息相关。改革失败后的政治现状,已是一派“荐绅崇尚虚名,以宽厚沉默为德”的无所事事局面,正如欧阳修所云:“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敬重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颓堕宽驰,习成风俗,不以为非。”[(12)]甚至当出现思有为而兴利去害之贤者时,则“众皆指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随而挤陷”[(13)]。故赵滋主持雄州边事时,“会契丹民数违约,乘小舟渔界河中,吏惮生事,累岁莫敢禁”,而滋至一切禁止之。于是,“知瀛州彭思永、河北转运使唐介、燕度,皆以滋生事,请罢之”[(14)]。宋之群臣,习性即是如此,务以安默无过为持重,而以忠于职事、进取图强为生非。更有甚者,英宗朝时,大臣胡宿仍不遗余力的攻击赵滋为惹事生非、破坏盟好之徒,并献言曰:“今缙绅中有耻燕蓟外属者,天时人事未至,而妄意难成之福。愿守两朝法度,以惠养元元,天下幸甚。”[(15)]这种无意进取、以维持盟好为主旨的政治态度,便成为北宋晚期群臣的普遍心态,并在朝臣中渐以多数而占优势地位。所以,当徽宗起用童贯、赵良嗣等以规复燕云故土时,几乎多数的朝臣皆起而抨击。因为他们已习惯了辽宋对峙格局这样的一种政治环境,只愿意固守成规,不希望再见到兵火交融的险恶场面,只想维持既定的“安定与和平”条件下的富贵生活;他们已腐朽到了极点,像刘正夫、郑居中、安尧臣、沈积中、程振、朱胜非、范致虚、宇文虚中、王庶、胡松年等一大批朝臣,皆以“边隙不可轻开”为由,反对规复燕云。这些崇尚精神虚无的“理学”之士,或直斥规复燕云为“辄造事端”[(16)],或以败盟干常相诮责,斥为“万死不足谢责”[(17)],甚至直接威胁参与复燕之议的人员“当思异时覆族之祸”[(18)]等。他们的论调都同归于一种说法,即待时而动,“取之当以渐”[(19)],这也正是南宋时形成体系的程朱理学,在宋金对峙中所坚持的主要论调。其实,徽宗朝收复燕云的举措陷于失败,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的在于金宋双方所具有的内在因素的差异上,而仅仅将其丧国失地的罪责归之于北宋君臣的毁盟背辽,是过于牵强的。由此而言,它无疑反映了北宋末颓废堕落的士风和偏隘落后的政治取向。
易言之,当徽宗规复燕云的目的暂时实现后,那些本来奋力抨击“图燕之计”的人,又群起致贺以干取爵赏,已无复大臣之体。而一旦因张觉事件而又使全燕之地尽失于金时,这些人便又乘时而起,坚决打击、排陷主张伐燕的人员,若和诜、赵良嗣辈,此时或流或杀,结果反而纵容、帮助了金人的贪鄙,导致战祸横行,使徽宗退位。徽宗退位,拥立钦宗,并未从根本上扭转北宋末颓废的政治局面,反而使朝臣中和、战两派间的斗争愈演愈烈,致使钦宗在位的短短的一年中,便表现出了极不稳定的举足失措的政治局面:一方面与金人议和,不惜割地赔款以换取“相安”的并存局面;一方面又联络辽朝的遗族、故臣,以图借辽人以牵制金人的南下之势。而朝廷中也不间断的重复着起用和排陷主战人士的作法。
综上所述可以归纳为,当辽宋对峙格局形成之后,中原地区思想文化之发展已渐入一种消沉、狭隘的轨道,这种思绪发展的直接结果,就使承其余绪的南宋时期确立了体系完备的程朱理学,这是以北宋时期特定的历史、政治局面为温床孕育而成的。由于它整整毒化了有宋一代几辈人的思想,所以众口一词,视规复燕云为惹事生非,指斥徽宗“败辽宋百年盟好”为亡国的祸根,使这位著名的浪子皇帝又肩上一份洗不清的历史责任。这情景便与南宋时期韩胄伐金的遭遇有些相似。韩氏以准备不足而使北伐失利、殒身丢命;徽宗以料事不足而失地退位。其结局都是十分残酷的,直至后世史家,也因其影响,不能脱其窠臼[(20)]。
三
至于辽朝灭亡的原因,只有辽末入金的降臣,将亡国之痛归恨于宋朝毁盟,必欲报之而后快。史载,及“燕山之议”起,辽降臣左企弓便献诗于金太祖曰:“君王莫信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21)];及张觉事件发生后,辽之遗族遂共诿责于宋,时“刘彦宗,时立爱为金国相,二人皆燕人也,以坟垅、田园、亲戚之故,愈劝金人南侵”,“兼契丹旧臣降金人者,已得用事”,“各阴间可入,内外劝之南侵,阴报宋朝助兵攻辽之隙”[(22)]。
其实,关于辽朝匆匆而亡的原因,《辽史》中已写的非常明白。辽朝自道宗已来,国势已是江河日下,及天祚在位,又无丝毫振兴迹象,主上猜忌日重,而朝臣大族离心离德现象愈益明显。计天祚在位,前后不过26年,而统治集团内部便出现5次大规模的叛亡事件,除乾统二年(1102年)萧海里自乾州叛投女真原因不明外,其他4次皆有记载,这些都是发生在契丹族内部的勋贵阶层(其他各族群众的反抗斗争更是风起云涌)。而且每一次内部叛乱事件的发生,都对辽朝触动极大,加速了辽朝灭亡的过程。天庆五年(1115年),耶律章奴反,“至祖州,率僚属告太祖庙云:‘……今天下土崩,窃见兴宗皇帝孙魏国王淳道德隆厚,能理世安民,臣等欲立以主社稷。……迩来天祚惟耽乐是从,不恤万机;强敌肆侮,师徒败绩。加以盗贼蜂起,邦国危于累卵。臣等忝预族属,也蒙恩渥,上欲安九庙之灵,下欲救万民之命,乃有此举。”参与此事的“贵族二百余人”[(23)]。又如,保大元年(1121年),耶律余睹又以谋立晋王敖卢斡事泄,“即引兵千余,并骨肉军帐叛归女直”,此次从乱者多贵戚子弟[(24)]。而保大二年,耶律大石、萧斡、李处温等,遂于燕京拥立魏国王淳为帝,“以燕、云、平、上京、中京、辽西六路,淳主之;沙漠以北、南北路两都招讨府、诸蕃部族等,仍隶天祚。自此辽国分矣”[(25)]。而当保大四年金人平燕后,耶律大石遂再与天祚分裂,率所部西去,辗转漠北,抵达西域,建立西辽。
耶律大石在分析天祚政权败亡时说:“自金人初陷长春、辽阳,则车驾不幸广平淀,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则都燕山;及陷中京,则幸云中;自云中而播迁夹山。向以全师不谋战备,使举国汉地皆为金有。”[(26)]辽朝败亡在于天祚帝一意退守、不谋战备之过。然而,内政不稳,叛乱迭起,可能是天祚一意退守的真正原因。所以,当燕京魏国王淳的势力被金兵消灭掉,耶律大石又掉头西去之后,天祚余部却一度振兴于碛北,可能也正是此时内政和军令统一的效果。金人倾全力,方得包抄剿灭。由是言之,辽之灭亡,其故不在北宋,而在于内政混乱,变难迭起,人心不一,这样的政权又怎能不亡?大石将之归罪于天祚;惟有燕京魏国王淳建立的短命政权中的遗臣,燕京地区的望族,若左企弓、时立爱之流,才将亡国之痛归恨于北宋,因为北宋军队帮助金兵剿灭了魏国王淳刚刚建立的北辽政权。
辽朝中期以后,君臣唯以“国家大敌,惟在南方,今虽连和,难保他日”为警诫[(27)]。道宗时,以“今同家人,礼当瞻拜”为由,邀求宋帝画像,务使和盟之局“契同一家”。这一点使宋人也明显地感觉出来。宋人苏辙使辽后报告所见云:“北朝皇帝(指道宗)年颜见今六十以来,然举止轻健,饮啖不衰,在位既久,颇知利害,与朝廷和好年深,蕃汉人户,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加以其孙燕王幼弱,顷年契丹大臣诛杀其父,常有求报之心,故欲依倚汉人,托附本朝,为自固之计。”而辽接伴使臣等“言及和好,皆咨嗟叹息,以为自古所未有,又称道北朝皇帝所以馆伴南使之意极厚”[(28)]。强大的契丹辽王朝,在其向下坡路滑落的时候,开始出现了某些“疲惫”的症候,那就是一改以往对待宋人的凌厉气势而转用好语慰抚,以图与虚弱的北宋王朝永保盟好、传祚万年。
但是,辽人也同样清楚地感觉到了北宋王朝虚弱的国力状况。因此,当女真攻辽,宋人欲图复燕之际,辽人非但以背盟诮责于宋人,还遣使于军前,坦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恶也。今射一时之利,弃百年之好,结豺狼之邻,基他日之祸,谓为得计可乎?救灾恤邻,古今通义,惟大国图之。”[(29)]也同样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维持现状的态度,北宋群臣在激烈地反对收复燕云的决策时,有人提出了一条“存亡继绝策”,其主要内容是:虽然规复燕云地区的师旅已出,但尚未开战,“今契丹之势,其亡昭然,取之当以渐,师出不可无名。宜别立耶律氏之宗,使散为君长,则我有存亡继绝之义,彼有瓜分辐裂之弱,与邻崛起之金国,势相万也”[(30)]。其实,这也是一种力图维持辽宋和盟状况的态度,是在宋徽宗采取独断措施、出师图燕之后,那些反对图燕之议的人士所采取的折衷办法。它完全符合了当时北宋朝野士大夫阶层的思想状况,能予人以心理的慰籍,所以也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赞誉和支持。
如上所述,在辽宋末年群臣的意识中,面对强劲的金朝政权除了恐慌和毫无抵御之术外,都基本上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错觉:只要辽宋和盟局面不变,疲惫的辽朝与虚弱的宋朝便能延续下去。其实,这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在刚刚兴起的、如日中天的强大女真政权武力打击下,试想辽、宋这样的两个衰弊政权,又怎能长久地延续?!所以,历史的和现实的条件,共同注定了维持百年“和局”的辽宋政权,最终同归于灭的结局。
四
由于辽宋时期南北对峙政治格局的形成,决定着双方间随着政治对立及相互联系的发展过程,也呈现愈来愈多的不同文化区系之间的直接碰撞、交流与融合的发展机遇。于此,我们可以将眼光向后看一下,直到金元时期为止,结果会发现,辽宋之际的对峙,事实上,已开始将中国南北方文化的发展,置入一个等同发展的氛围之中,双方间既对立又互渐,既有明确的政治分野,又有明显的文化相互浸润区域;此后经金、元两代的努力,将南北文化逐步融会、交流、归一。因此,我们对辽宋时期的历史活动及存在形态的研究,便不能分割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体现象,而要视为文化同构过程中所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调整,以及文化的重新组合,当然也要包括文化的载体——人类群体的重新组合,这些构成了同一整体的内容。也就是说,应当去探究其共同构成这一整体格局的历史动因,及其整体发展的共同效果,才是我们认识辽宋对峙格局的根本点。
辽宋对峙格局的形成,是南北民族求同意识发展的直接结果。由于当时对峙双方的文化体制与政治体制呈垂直交叉的多重关系,以及双方间平行交叉的边际关系等,不但引发了各自社会组织结构的错位变动,如北方草原地区修筑了大批城池,从而沟通了南北的交流,也常常引起政权间边际关系的错位变动,契丹族继承北方民族不断南进的传统,将政治分界线推进到燕云地区以南。这不但改变着农耕人口和游牧人口的生活信念,也直接影响着当时中原地区经济重心向东南沿海地区的倾斜转移,这些无疑都给当时南北双方的社会观念形态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纵横交错状况的影响,才使得金灭辽、宋政权后,辽、宋的亡臣便在“择主而仕”的问题上,既呈现了极大的自觉性(或忠贞性),也呈现了与故国极大的游离性,如大石西走、赵构南迁、雅里北去、余睹降金、刘豫建齐、岳飞抗金等等,造成了当时政治形势的纷纭繁复的局面。可以说,这也是南北两种文化在同构过程中,发生相互渗透后而引起的连锁反应。
辽宋对峙的历史格局,也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客观发展规律;辽宋对峙,也仅是中华历史有起有落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由于客观存在的两大敌对的政治集团的抗衡,结果使双方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背道而驰的现象,腐朽没落的程朱理学的形成,便呈现了与当时北方崇重实用的儒学体系格格不入的现象。但是,在这一深刻的历史发展阶段中,社会文化的主题,是植基于当时南北方人口观念变革基础上的文化同构。北方文化以其勃勃的生机,主动地摧残着中原文化被动的思想防线,从而将中华文化推向了一个更新、更广阔的发展阶段,并整整包容了辽、金、元三代的历史发展过程,将文化的重任从南方移到了北人的肩上。金末时人刘祁曾说:“金朝名士大夫多出北方……不可胜数。余在南州时,尝与交游谈及此,余戏曰:‘自古名人出东、西、南三方。今日合到北方也’。”[(31)]北人也自豪地肩起了这份重任。
还有一条史料,是关于金朝统治者任贤与能方面的。完颜守贞,以其祖希尹之故,家富书史,博达典籍,为当时金国著名学者,而金章宗却评论曰:“守贞固有才力,至其读书,方之真儒则未也。”[(32)]我们知道,金初北人指斥南宋士大夫阶层为“老儒”,以为百废而无一用,海陵王时即直以“老儒”为废物。可见当时北方的文人学者,已在继承辽代文化的基础上,在学习儒家文化的同时,对儒学的内容和儒学的载体(儒士)在理解和取舍的方面都有清楚的态度,说明辽代倡行的以实用为原则的儒学思想体系的发展,至金初仍沿用不坠;北方文化的延续性发展,便与南方崇尚虚无的没落儒家“心性”之学(即理学)呈现了越来越清晰的文化分野。
因此,辽宋对峙格局破灭的文化意义,就在于占领了中原地区的金朝政权,继承和发展了辽朝时期的北方文化的基本形态,将那种本来优于中原地区现状的文化形态,又进一步的推进于中原,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也使南北文化进一步的融会贯通,使得燕云地区从古史中的边鄙地位上升为文化的重心所在,进一步奠定了北方优胜于南方的地位,为元代大统一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注释:
① ③ 《金史》卷79《郦琼传》,卷129《萧裕传》。
② 《金史》卷133《耶律余睹传》。
④ 《金史》卷133《移刺窝斡传附撒八事记》。
⑤ 《辽史》卷30《天祚纪附雅里事记》。
⑥ ⑦ 《金史》卷74《宗翰传》。
⑧⑩ 《宋史》卷473《秦桧传》。
⑨ (21) 《金史》卷77《宗弼传》;卷75《左企弓传》。
(11) 参见庄绰《鸡肋编》卷中,中华书局,1982年。
(12) 《诸臣奏议》卷14。
(1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条。
(14) (15) 《宋史》卷324《赵滋传》;卷318《胡宿传》。
(16) (17) 《宋史》卷351《郑居中传》;卷350《赵隆传》。
(18) 《宋史》卷354《沈积中传》载程振语。
(19) (30) 《宋史》卷356《任谅传》,卷371《宇文虚中传》。
(20)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4,赵良嗣不应入奸臣条。
(22) 《大金国志》卷3,天会三年;中华书局校证本,1986年。
(23) (24) 《辽史》卷100《耶律章奴传》;卷102《耶律余睹传》。
(25) 《辽史》卷30《天祚纪附耶律淳事记》。
(26) 《辽史》卷29《天祚纪》载大石语。
(27) 《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
(28) 厉鄂:《辽史拾遗》卷10引苏辙《栾城集》。
(29) 《宋史》卷335《种世衡传附师道传》载辽使军前语。
(31) 刘祁:《归潜志》卷10,中华书局,1983年。
(32) 《金史》卷73《完颜希尹传附守贞传》。
标签:宋朝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南宋论文; 金史论文; 金朝论文; 宋史论文; 辽史论文; 契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