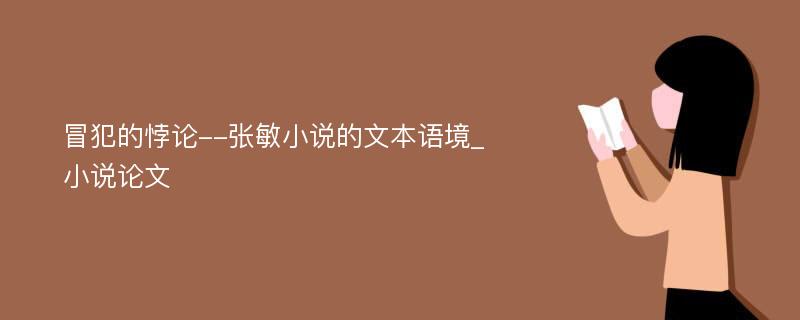
冒犯的悖论——张旻小说的文本脉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脉络论文,文本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说张旻的小说都是冒犯之书,也许并不为过。90年代,被称之为新生代的某些作家曾有过“断裂”的雅号,其实“断裂”就是一种冒犯的姿态。张旻小说的冒犯之处并不在于人们经常说的,他的书写一如既往地源于校园生活,“插队”于嘉定之一隅。相反,它们是张旻小说的禁锢之地,也是张旻美学的伊甸园。在小说《寻常的日子》中,周钧在经历三年半的家庭婚姻后,温暖如春的生活黯然失色,显得猥琐无聊,而心中“仍是多么怀念那一段的学校生活,多么怀念那时的自由、孤寂和耽于冥想”,说穿了,这里的自由无非是远离热闹中心,无家庭婚姻生活之累的自由;孤寂和耽于冥想也无非就是一段师生之间的暗恋及自恋。被许多阅读者指责为离经叛道的书写,情欲的幻想如何经书写演绎为现实、渴望认同而又无法认同的经验,“我更关心的是日常生活状态下两性之间的基本关系……生命进入常态中的成长与延续,是男女关系中不稳定的、潜在的、变幻的、自我矛盾的方面”;“与表达爱情的或道德的主题相比,我更感兴趣这个极端的故事显示了人的情爱潜能和丰富的表达方式,这几乎是不可穷尽的”①。这些自白自有依据。即便是从张旻的文本实践来看也是真实的。但是,要进一步理解冒犯两字的含义,恐怕还要返回到更早的时代背景,那是清教主义引领我们道德生活的年代。
要进一步理解冒犯两字的含义,恐怕还要返回到更早的时代背景,那是清教主义引领我们道德生活的年代
一
情色故事使人变得恐惧,就像童话故事将恐惧人性化一样。张旻的故事既简化又繁复,它的简化使被驱逐的世界的复杂性只能像影子一样跟在后面。人不是影子,不管你的感觉如何虚无飘渺,不管你对生活的把握多么闪烁不定,你得进入真正的影子的世界才能发现这一点。人无法摆脱影子,我们怎样才能跳出自己的影子来观察影子的存在?经验是在自我与世界之间斡旋并且与两方面都扯不清道不明的、模糊而又混杂的领域。张旻不愿意在这个领域纠缠不清,“对我来说,通常一篇小说的题材一小部分来源于我本人或我关注的生活事件,大部分则来源于内心体验和想象”;“在题材的选择和价值取向上更注重个人偏爱和一己体验”;“我就像个白日梦者,没有语言,终日枯坐,在内心和想象中过着另一种生活”②。另一种生活和第三种状态是表达张旻写作主张的一种说法,作者想区别和摆脱人们业已习惯的那种创作生活。我以为,第三种状态的说法其实还是一种姿态,是对以往陈规陋习的抵御。说到底,对每一个追求创新的写作来说,都是第三种状态的书写。
假如越界和冒犯是真实,它所轻视的戒律也一定是,这意味着越界和冒犯无法不肯定它违背的清规戒律那无所不在的权力
但如果将来讲今晚的故事,有可能会很丰富、生动,如他们今晚讲过去的故事那样。③
此话不是我从小说中的摘录,而是作者自己的摘录并用来放在小说前面作为题示。故事的存放都是时过境迁,叙事的现在进行时严格地说也是一种过去时,但是否因此会变得丰富和生动,难说。虽然这里多少包含着理论的武断,但仍然可以从中看出作者乐此不疲的愉悦,一种沉冥于往事的自我慰藉。《往事》是典型一说,“想起我魂系梦回的那个故乡”,“它已经存在于我的目力之外,隐身于我所熟识的那些物体中,使它们变成另一种存在”。一封情书、一次性的爱慕、初次萌发的暗恋像瘟疫般古怪地孤立于公众之外,四处是毛骨悚然的反应。叙事者内心敏感地捕捉着每一微小的信息,劳心伤神地想象那噩梦般的往事。变态的环境和教育使性的常态变形放大,恐惧和震颤的力量才得以进入叙事的谱系。舆论一律的力量、社会环境的权力、意识形态的制约是渗透性、弥漫性的,即便是个人主观中最私有的部分都因此而转变成某种感伤、怅惘、孤寂、怀旧和琐碎;即便是张旻自许的“私人日记”式的小说也将难逃这一噩运。暗影无处不在,尤其是当我们回首那充满禁忌的年代和往事的时候。
律法并不是欲望的对立面,而是催生欲望的禁忌。张旻90年代叙事的背景,从讲述昨天故事的时间算,我们可以追溯到80年代甚至更远。清教时代既是禁忌的时代,同时也是律法贫困的时代。我们最持久的欲望之一便是对戒律本身的欲望,对自我苦恼的一种激情。假如越界和冒犯是真实,它所轻视的戒律也一定是,这意味着越界和冒犯无法不肯定它违背的清规戒律那无所不在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小说名字出现类似“情幻”、“情戒”、“犯戒”等就不难理解了。自然的情欲既是一种欲望,又经常表现为禁忌的破坏。自相矛盾的是,只有通过戒律我们才能认识它所禁止的欲望,因而禁止乃是我们对欲望的最初了解。
仿佛是和简化的背景作对似的,张旻的情欲叙述都是繁复的。迷醉于感官,津津乐道于情色分析,为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私密性寻求话语的出路,以及不厌其烦的身体诉求,捕捉两性间梦幻般种种情绪,这些东西在张旻所有的作品中回响,絮絮叨叨地缠绕不去,既充满着诱惑又令人心生厌烦。张旻反对爱情的理想化与婚姻的道德化,强调两性关系的世俗面和日常生存之状。甚至在“爱情”和“情爱”含义并无多大差别的字词中,他都宁愿选择后者。在一些“司空见惯的鄙俗内容”中,掩饰着“最意味深长的,令人想象和体味其中触目惊心的,蕴藉丰富的人性内容”。这些话意在表示作者的艺术追求,但听起来却多少有点自我退缩的味道。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学纲要》中有着类似玄奥但却简洁得多的说法,他认为本能是“肉体对精神的需要”。据说,王朔曾经认为,张旻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剖析到了荡气回肠的地步。④ 此话值得怀疑,首先我们并不清楚王朔在什么情况下、针对什么具体作品说这番话的,其次,严格意义上说,张旻的故事并不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剖析,而都是有关“自我”的故事:“我”的情、“我”的欲和“我”的恋。而其他都是“我”的影子延伸和变形。当然,这里说的张旻作品指的还是90年代的书写。还是李劼在论述张旻小说中所讲的:“作者始终在朝着一个方向叙述”,“始终在讲述同一个故事、在寻找同一个意象”⑤。朝着一个方向叙述,这个说法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单调、没什么变化,坚持个性,有独特的追求等等,似乎都可以。问题在于,这同一个方向、同一个故事和同一个意象是否就抓住了张旻这二十年小说创作的文本脉络,说清了张旻文本的没有变化与变化。
二
张旻描述两性世界如此执著、痴迷,以致绵延长达近二十年,以至于在这如同钻进死胡同般的探索掘进中,事实与意义、形式和内容互相毒化、腐蚀、伤残、羞辱对方。一方面小说诉诸世俗琐碎的情爱,另一方面叙述者又坚持一种逻辑推理的方式,丝丝入扣乃至神神叨叨;一方面爱是具体的,从皮肤接触开始,光是摸异性的手在小说中就经常出现,占据了不少的篇幅,另一方面爱又是一种奇妙的隐喻,爱的记忆牵涉到一种超乎寻常的兴奋。当爱的自我把一个理想化了的对象作为一面自我观察、自我欣赏的镜子,它就会不由自主地突出自己、美化自己,不然,就好像自己会被肢解、被淹没似的。但这种爱又从未杜绝对现实的理解。从错觉到叙述幻觉,其中不乏苦恼、忧郁、悲痛、欺骗以至扼杀。《情幻》、《爱情与堕落》、《了结三章》等都是前者的典型;《生存的意味》、《顾梅的故事》等则是后者的例证。一方面是鄙俗内容的舞台,一方面又是唯美意象的登台表演,想象在象征和真实之间拉拉扯扯。无论是《生存的意味》中两代人的宿命,《寻常日子》中的逃避和自辩,还是《告别崇高的职业》中爱的障碍;无论是《了结三章》中的感伤、《不要太感动》中无法忘却的记忆,还是《往事》像噩梦般的往事等等。张旻笔下的男人似乎都是徒劳地接近各种女性,然后又是莫名的逃避。叙述者像是个好事之徒,在两性的接近之间享受愉悦,在逃避之中沉醉于梦幻的牵肠挂肚。在旅游的途中、在舞会、在餐桌、在课堂、在宿舍,幽会总是因禁忌而显得神秘和恐惧,继而在事后的藕断丝连中沉湎于沾沾自喜的孤独的牢笼。对张旻来说,叙事的艺术不是扩展,而是不断的重复与不断向内收缩,艺术就是对独处的留恋。
激情不仅意味着一种不顾一切的投入和执迷不悟,而且也意味着对审慎原则的拒斥。张旻的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者是禁忌时代的情欲记忆和书写,这是一个好像惧怕可恶的罪行或者致命的传染病似的害怕欲望的时代。两性间的种种关系在秩序的核心表现为某种不适当的东西,一种受压抑的欲望。这是关于阴影的两性书写。“人在社会过程中社会性被不断强化,戴上面具,本性则受到了压抑,以至于麻木。这或许是人存在的悲哀。”作者甚至感叹道:“对我来说,写作好像是更真实的。”⑥ 沉醉于想象的真实,相信书写符号的可信与可靠,即是对外在真实世界的怀疑,也是对虚幻世界的过度依赖。在雅克·拉康看来,身体用符号表达自己,结果却发现符号背叛了自己。过度信任文本的物质性到头来是一场身体学和符号学的交易。我们既被故事的世界所支撑,又同时被它压垮。两性之间的种种情爱并不只是一个真实的对象,更是一种对真实的渴望,渴望知道两性之间的生活被我们碰巧弄得琐碎和混沌之后可能是或者应该是什么样子。
对张旻来说,叙事的艺术不是扩展,而是不断的重复与不断向内收缩,艺术就是对独处的留恋
《顾梅的故事》发表于1996年,小说虽不起眼,但就张旻两性叙事的转变来说,却是不可忽略的。顾梅的故事是那么的通俗,现实且充满着暴力。什么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了,商品成了主宰,那无处不在,神奇而法定的交换原则进入了现实生活。货币是强力的中介,穿梭于世俗和想象之中。一切都可以交换,顾梅为了得到童车厂的处理废料,用身体与佥厂长作为交换,“这可是一笔大买卖,赚头是很大的,你想都想不到”。不是想的问题,而是如何付诸实践的问题,他们甚至用互写保证书的形式作为交易的契约。交易的原则用身体的砝码贯穿全篇,往前移,顾梅十八岁进入盛家也是交易,“我的这个想法一点也不算过分,就算我把自己卖给他,也该有个身价”;往后那为平息伤风败俗引来的非议,连互睡对方老婆的游戏也粉墨登场了。我们终于看到了性的需求和欲望现在成了商品,和别的商品成为共同体,相互串通彼此兑换。
《顾梅的故事》是一道分水岭。以前那沉醉于自我,注重叙事向内转,强调个人生活经验,留意日常世俗的情欲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顾梅的故事》是一道分水岭。以前那沉醉于自我,注重叙事向内转,强调个人生活经验,留意日常世俗的情欲悄悄地发生了变化。禁忌的解除,两性间神秘的面纱已经揭开,性欲在获得人性自由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落入商品的交换原则。在关于情欲的话语中,我们的内心生活从以前的吵吵嚷嚷转为空空荡荡,相反,我们生活的外在形式则从空空荡荡转向了吵吵嚷嚷。性欲的暗流变为物欲的横流,摹仿性书写不得不经历一次背景与舞台变化了的考验。我们终于发现,叙述者称呼的世界,不啻是叙述者为着“自由”进行伪装的一种形式,它所有的关系都维系在自我陶醉与幻想之间,小说的主体是一种几近疯狂的造物,它在挪用对象的自然时也挪用了自己的客观性。在《黄玉萍的婚后生活》中我们窥见了生活中的物质力量,优裕从容的生活成了幕后的黑手,性欲开始被符号化,而物欲则被生活化了。真相只能埋在心中无法被叙述。而在《破绽》中两性关系成了传闻,成了匿名信的材料,成了人与人之间为了争权夺利的舆论工具,情欲本身则演绎成了杀手。
三
张旻小说的前期是这样一种版图,其中阴影和冒犯被认为是审美的颠覆性,而柔情和肯定则是不露声色的造反和扭曲。自我反讽的自恋者要么完全鄙视外部世界,要么就把外部世界仅仅当作他奇思怪想的可塑性材料对待。自我在这里是个战场,戒律和欲望在这个战场上展开可怕的战斗,却又时常结成欺诈成性、不稳当的、充满矛盾的同盟。两性书写被阴影和禁忌所支撑,冒犯有着存在的理由,到了张旻小说的后期又是另一种版图,其中财富仿佛是一种权力强大的叙事,我们只有嘲弄地接受它所说的一切,才能保护自己不受它的支配。《谁在西亭说了算》是作者最近的一部长篇小说,一位在西亭飞扬跋扈的老板被人大白天勒死在自己办公室,现场留下的一张画上,写着死者家喻户晓的名言,“谁在西亭说了算”。围绕着凶杀案,两性间的情感纠葛再次浮出水面。《谁在西亭说了算》无疑是《顾梅的故事》的放大,情欲和凶杀继续着叙事时空的支撑,所不同的是前者有些嘲讽,后者则试图演绎真情在两性间的扑朔迷离、在物欲世界中的风雨飘摇。在经历过无数风波曲折之后,文昕和“我”的结婚终于走向叙事的尾声。文昕却在句号后面抛出了问号:
不瞒你说,我很想问你,你有罪恶感吗?你现在这样对我,是出于什么动力?爱情、情欲、怜悯、赎罪心理?
这几年我感觉自己仿佛一再被一双不可抗拒的手抛起来,生命失去重心,不知道我是怎么走过来的。现在你告诉我,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我理解这话你说可以,但是请原谅我想都不敢想。
张旻的两性书写近二十年了,很少有从女性立场提出关于性、情、爱的质疑,由于其小说大多是男性角度的叙事,很多故事都重在一个男性和几个女性间的关系,而此次写的却是一个女性和三个男性间的关系。虽然此次第一人称的叙事依然是男性;虽然迷惑、越界、彼此误解产生相反结果的叙事策略依旧,但让女性作为叙事主轴,从女性角度对两性关系提出问题,这在张旻尚属少见。
张旻的叙事变化也从侧面给予我们启示,物的权力日益兴盛,作为压抑的外在因素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即昔日道德规范的秩序正在持续衰弱。现在身体是空虚的,世俗正在变异,一种局外的冷漠,与世无争的心态,仿佛都在讲述着无关痛痒的故事。物欲窒息了无数个美丽的故事,被投入妄想症的境遇也难以使其再生。当清教主义逐渐淡出舞台时,冒犯的书写自然地失去了其对象和动力。激进主义丧失了激情和行为能力,超我演变为放纵主义和伪叛逆的诱惑,媒介、网络、广告和娱乐业已成了潜移默化的导师,成为新兴道德观念的护卫者。两性世界的神秘和恐惧感在文本书写中已失去了原有的魅力。张旻的两性世界仿佛是经历了两个时代的书写,这既是时代的转型,也是写作的转型。对张旻来说,面对转型,那种好钻牛角尖的写作似乎是走到了尽头,写作的转型既是一种痛苦,也是一种对原先冒犯书写的冒犯。长篇小说《对你始终如一》就是面对两个世界的尝试。“林越和万志萍之间有过一段上世纪80年代的恋爱,这也许是我们这代人都非常怀念的纯粹、浪漫的爱情。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当他们之间出现了一个微妙的‘第三者’陈中之后,三人间的关系在各方面都处于一种‘边界’状态,也就是‘可接受的极限状态’。在最后的变化到来之前,这一‘边界’似乎在他们脚下无限地扩张,这一状态充满复杂性。”⑦ 这是作者对小说的自我阐释。反对将小说变成道德谴责的意图很明确,似乎也是其一贯的主张。追求人际关系中微妙复杂的局面,“边界”也罢,“可接受的极限状态”也罢,无非是此一追求的换一种说辞。创作中事与愿违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叙事者努力追求复杂的局面,结果却是走了一条简单的线路。说感情上“对你始终如一”,令人难以置信(事实上是否始终如一并不重要)。一方面是始终如一,一方面又是扑朔迷离、真假难辨。一种左右为难的叙述始终是此部小说的顽症。我们终于发现,日愈贫困的利益驱使正在逐渐抬头并开始规划着两性间的情感曲线;苦修的虔诚作家和世俗的爱情诗人在使用激情这个词时,意义是如此不同。在这个意义上说,身体是错误的话题,它甚至算不上话题,或者也许几乎是所有的话题。张旻后期小说的一个症候就是,或许你解决了一种困窘,但走出困窘的叙事仍然令人难忘地更加贫穷。
当清教主义逐渐淡出舞台时,冒犯的书写自然地失去了其对象和动力
四
张旻属于那种虔诚相信自我的人,他在冒犯那些不人性的禁忌时,努力地寻找自我,探寻两性世界作为人性的基本含义和外在的丰富性,一心恢复自我的本能,和两性间基本的欲望。但就是寻找自我的努力也很容易地造成叙事的龟缩,两性世界的无限放大的同时也是对真实他者社会的缩小。过度信任内心的自我,丢弃的很可能是自我缺乏的我,是那不能在自我中停留的我,一个缺乏他者目光的我。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旻文本对第一人称视角的过度依赖既是特色,又是局限。自称为第三种状态写作的人,结果却经常地沉湎于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叙事面不能自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自我冒犯的悖论。
自称为第三种状态写作的人,结果却经常地沉湎于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叙事面不能自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自我冒犯的悲哀
张旻的叙事是抵御性的,他的两性世界反抗宏大的社会意义,试图剔除爱情故事的浪漫成分,回避道德判断决定叙事的命运,逃离道德主义的诱惑。但是叙事意图是一回事,阅读伦理又是一回事。张旻小说引起批评家的阐释少,而同时记者的访谈又很多,这一奇怪的现象至少说明了叙事和阅读间的隔膜,即记者的提问又无例外地都抓住道德问题不放。我注意到张旻创作全盛期中的小说《情幻》经常被转载、选载,其意图全在引起争鸣的可能性和市场份额,而非一厢情愿的文学性肯定。张旻的小说审美价值在那“身体写作”的年代既被兜售又随即被吞没。
在情欲的叙事上,应该明白的是,没有东西比冷峻更煽情,风格上的麻木超越了内容粗劣的煽情主义。对张旻这样一个天生敏感、好讲逻辑、喜欢有条不紊的人来说,用冷色调来处理情欲无疑是拿手好戏。凡别人喜欢热闹的地方,他都喜欢删去,而别人不经意的地方,容易忽略的空白和盲点他总是大书特写,甚至没完没了。整部《情戒》都是这样,应该发展的故事从不发展,阅读期待所渴望的东西总不现身于话语中。整个一部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长篇叙事,难怪李劼长长的序言从不提及故事的内容,说的只是意象。主人公章勇自视清高、外表冷淡、内心则燃烧着性欲萌动的引诱幻想,幻想是欲望的表演,其中主体虽然一起在场,而我们却永远无法确定其身在何处。幽灵般的章勇唯有对象出现时才现身,身陷此岸而不能自拔,彼岸是否存在并不重要,故事的内容及其发展并不重要,唯有奇幻的意象行走自如。幻想本质上又是虚构的,能否通过再一次虚构让其成为事实,这是《情戒》的叙事难题。而小说的行文则平静如水,一意孤行,似乎没有注意到任何不对劲的事情。《情戒》的叙事犹如单行道,从不考虑回来的路径。
张旻的两性书写,既有冒犯的一面,又有着循规蹈矩的另一面。他在时间顺序上基本上是“顺民”,人与人的交往接触总是顺序道来,开始怎样,几天、几个月、几年后怎么怎么的,即便是描绘心理活动也是依序而行。但在结构布局上他又是“刁民”,经常因为一个看似多余的引子,意外的结尾都有着意料之外的余韵和耐人寻味的施舍。《情幻》发表于1994年,就是今天看来,它在张旻创作历程中依然占据着不可忽略的重要地位。当代文学的探索浪潮在这一年几近尾声,《情幻》既是张旻小说探索走得最远的一部作品,也是这一文学浪潮的余音和回响。《情幻》是一部欲望之书,小说中无论是刘忠的故事,还是余宏正在书写的故事;无论是余宏和前妻小岚记忆中的故事,还是小说中记录下的同样事件截然相反的陈述:无论是虚构的真实事件,还是事发过程的幻觉和无法证实的谎言。一会儿在文学的诗意中寻找生活,一会儿在生活中寻找文学的诗意;一会儿在真实中寻找虚构,一会儿在虚构中寻找真实:神秘的“那个”一再出现,我们却又始终无法知道他是谁。凶手是谁?叙事者也许假装不知道,也许真的不知道,我们在等待着明白,结果却是不明白在折磨着我们。一切都充满着欲望的悖论,欲望既拥有美好的瞬间,又是易变和无法捕捉的流动。无法辨认真伪。欲望是叙事的制造者,张旻小说中出现最多的字词是“匪夷所思”,其实他故事中的情节未必匪夷所思,唯有欲望一旦作祟的“奇谈怪论”才是匪夷所思的。欲望又是叙事的捣乱者,当我们需要一个结局,渴望一个解释和一种胜利,它总是“限制我们得到完全的满足”(弗洛伊德语)。欲望是这样的国度,那里拥有一种非个人秩序的无名,释放出一种难以驾驭、无法无天的力量,造访这个国度有一种恐惧的愉悦,令人着迷,又给人带来淫秽意义的愉悦。欲望是危险的,就像爵士乐一样,但它的危险正是它的迷人之处。《情幻》基本上是一部完美之作,除了有些段落有着自然主义摹仿的笨拙之外,其他都是无可挑剔的。
总的来说,张旻近二十年的小说,后期的作品不如前期,这里指的不是创作的退步,而是这种“不如”和当代创作总体退化是息息相关的。就个人而言,一种冒犯的书写,一种背负“阴影”的写作,一旦冒犯的对象销声匿迹,冒犯也就无从说起,这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共同难题。许多与张旻同时期或不同时期的作家都远离了小说创作,除了生活中有更大的选择和更多诱惑之外,恐怕也是和无法跨越两个时代的写作有关联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旻的坚守是值得尊重的。反映现实和超越现实都是文学的理想,问题是当我们超越现实时,千万别自认为了解时代,结果却是根本不知今夕是何夕;当我们反映现实时,却根本忘了文学为何物。这使我想起齐泽克在其书中提到过一个颇具意味的故事,“讲的是芝加哥警察局里的两名侦探。其中一个是幼稚的现实主义者,全然相信再现的理论范本。另一个是世故的非现实主义者,相信再现的相对性和随意性。两位侦探似乎都要被警察局解雇。理由是,如果已经有了嫌疑犯照片,现实主义者就看不到任何逮捕嫌疑犯的必要;而非现实主义者一旦有了嫌疑犯的照片,就开始逮捕见到的每一个人”。这个故事并不是简单地提醒我们现在到处充斥的幼稚的现实主义和世故的非现实主义这一事实。幼稚与否,世故与否,并不存在着泾渭分明、清晰可辨的界线。它们经常潜伏于我们意识之中,蛰伏在我们的内心中,时隐时现于作品的某个角落。就张旻的小说而言,也不例外。我的意思是,对经历二十年创作生涯、目睹两个时代的巨变、身陷两性关系的密室而又努力追随当下生活的张旻来说,这既是财富,也是难以丢掉的包袱。两性世界中恪守男性为主的主观视角既是一种特色也是一种局限,弄得不好更是一个陷阱,张旻的两性世界如果换个角度,那些坚持女性主义观点的人们该不知如何评说。冒犯的艺术真谛在于对事物一成不变的拒斥,是对压抑和禁忌人性丰富性的抵御和反抗,它所授予的当然不是“现实”,而是认识“现实”的概念如何强加于我们的方法。一旦冒犯失去了对象,对自身的冒犯便会提到议事日程,而这个问题可能会伴随张旻未来更长的时间。
文中所提张旻小说目录
小说集
《情幻》,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
《犯戒》,北京华侨出版社1996年版
《爱情与堕落》,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我想说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良家妇女》,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
长篇小说
《情戒》,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对你始终如一》,北京十月出版社2006年版
《谁在西亭说了算》,《收获》增刊2008年秋冬卷
注释:
① 张旻小说集《爱情与堕落》代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张旻小说集《爱情与堕落》代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③ 张旻小说集《我想说爱》。
④ 《答张英》,载《作家》2001年第2期。
⑤ 《情戒》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⑥ 《生命的摆渡——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
⑦ “答文学报记者问”,载《文学报》2006年7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