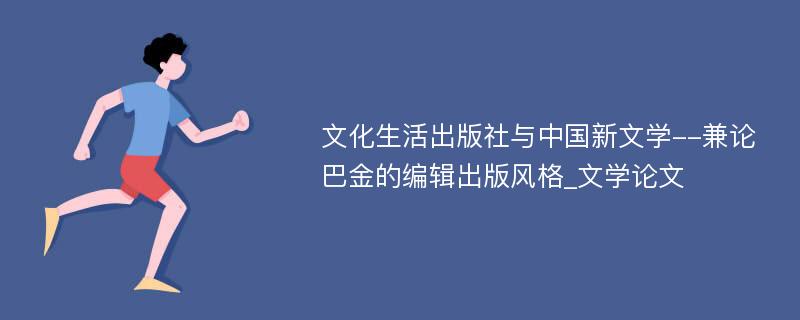
文化生活出版社与中国新文学——兼论巴金的编辑出版风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文化生活论文,中国论文,巴金论文,编辑出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12(2001)02-0060-06
五四新文学作为深刻影响中国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文化革命运动,它的发生和发展也必然依赖于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借助社会性的传播手段,特别是出版机构的物质保证,才能得以实现。作为文化组织形式之一,出版机构利用一定的资金、技术及发行网络,将新的思想观念物化、实化,推向社会,造成一种事实,从而在客观上对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培育、扶持和推进的作用;同时,出版业自身也获得了发展机遇。在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出版与新文学发展的这种互动关系,是很少涉及的论题。近几年,随着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人们开始愈来愈重视从文化机制的视角,对中国新文学的特点进行新的观察和思考,这无疑将开启新文学与新文化研究的新的空间。
本文讨论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创建于1935年5月。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严重殃及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工商业萧条,文化产业衰落。由于杂志刊物比单行本图书容易销售,出版界与书商一般都不愿意出版单行本的文艺作品。鲁迅于1934年12月4日给孟十还的信中就曾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他很久就想出版一些果戈理的作品,“我想中国其实也应该有一部选集……不过现在即使有了不等饭吃的译者,却未必有肯出版的书坊。现在是虽是一个平常的小梦,也很难实现。”[1](P673)鲁迅当时的境遇尚且如此,普通作家、译者,特别是有志于文学创作和翻译的年轻人所面临的困境,也就可想而知了。文生社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为弥补这一缺憾而创办的。
文生社的创办者吴朗西、伍禅、郭安仁(丽尼)等都是当时深受五四思想影响的进步知识青年。吴朗西和伍禅曾留学日本,“九一八”事变后,出于爱国热忱,他们弃学回国。出版自己翻译的外国文艺作品的强烈愿望,促使他们产生了创建文生社的最初构想。在为该社出版的第一套丛书“文化生活丛刊”所作的广告中,他们指出:“艺术哲学,只有少数人可以窥它的门径,一般书贾所看重的自然只是他们个人的赢利,而公立图书馆也以搜集古董自豪,都不肯替贫寒青年作丝毫的打算。多数青年的需要就这样被人忽略了,然而求知的欲望却是无法消灭的。青年们在困苦的环境中苦苦挣扎,为知识而奋斗的精神,可以使每个有良心的人流下感激之泪。我们是怀着这种心情来从事我们的工作的,我们的能力异常薄弱,我们的野心却并不小。我们刊行这部丛刊,是想以长期的努力,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文库,把学问从特权阶级那里拿过来送到万人的面前,使每个人只出最低廉的代价,便可以享受它的利益。”(《申报》1935年9月21日)这一文艺出版的主张,在三四十年代处于动荡和战乱中的中国文化界,很有几分标新立异的味道。历史证明,文生社对其宗旨的大胆实践,为五四新文学在三四十年代特别是抗战期间的不断成长,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发展空间。
文生社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创办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这是该社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期间,巴金、伍禅、陆圣泉、杨挹清、俞福祚等先后参加了文生社的编务工作,由巴金任总编,带领文生社同仁满怀激情地投入了以中外文学名著为主要对象的出版工作中,共编辑、出版了八种丛书,近一百多本文艺和科学书籍。丛书包括:“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译文丛书”、“现代日本文学丛刊”、“新艺术丛刊”、“新时代小说丛刊”、“战时经济丛刊”、“综合史地丛刊”等。其中,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和“译文丛书”几乎独立支撑了30年代中国新文学的创作和翻译,对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在这过程中,文生社自身的出书速度也不断加快,有一段时间大约两天即可出版一本书。抗日战争的爆发,使文生社的出版工作陷入困境,进入缓慢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吴朗西、巴金等人辗转大西南,先后创建了四川、广州和桂林分社,文生社同仁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坚持出版工作。这一时期出版的书刊,除“文学丛刊”之外,还有“现代长篇小说丛书”、“文季丛刊”和“文学小丛书”等,都由巴金主编。其中,“现代长篇小说丛书”对40年代新文学的发展影响最大,收入该丛书的作品,有不少都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杰作,如老舍的《骆驼祥子》,沙汀的《淘金记》、《还乡记》,巴金的《憩园》等。1954年文生社公私合营并入新文艺出版社,先后共经营了19年,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无论从现代文学史的角度,还是从现代出版史的角度来看,文生社都有它独特的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存储了新文学创作成果,为五四新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积累了宝贵财富。文生社不仅出版了许多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而且也出版了一些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家的全部或大部分作品。如抗战后文生社出版了一套戏剧家的全集,其中包括《曹禺戏剧集》(八种),《李健吾戏剧集》(八种),《袁俊(张骏祥)戏剧集》(五种),《林珂(陈西禾)戏剧集》(二种),《丁西林戏剧集》(二种)等。另外,还出版了靳以的长篇小说《秋花》、《前夕》等近十部作品,师陀的《谷》、《里门拾记》等近十部作品,以及萧乾、陆蠡、丽尼、罗淑、周文等人的大部分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文生社大量出版大型文学系列丛书的这种胆识与气魄,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还没有哪一家出版社能与之相比。第二,文生社对五四新文学在三四十年代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推进作用。文生社推崇进步文艺的指导思想,团结了以鲁迅为核心的左翼和进步青年作家群,出版的作品中,有不少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揭露、控诉侵略者的罪恶行径,客观上配合了中国人民的对敌斗争。第三,文生社同仁将社会上无序的文学创作归入不同的类属,再有计划、成系列地整理出版,奉献给读者的是有结构的图书体系。在这一过程中,编辑代替作家和读者,将他们的出版理念贯彻在对文化的整理之中,为社会建构着新的文化环境。这是一项非同一般的文化工程,它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发展及社会发展的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
在文生社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巴金一直是灵魂式的人物,他长期担任主编并主持了文生社大部分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巴金的编辑思想、编辑风格、编辑业绩即标志着文生社的整体编辑追求与成就。巴金在晚年写的一些回忆性文章中,曾特别指出:“我一直被认为是作家,但我也搞过较长时期的编辑工作。”[2]“上海朋友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担任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我编了几种丛书,连续二十年中间我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书的编辑和翻译方面。”[3](P351)与巴金相知甚深的作家萧乾也回忆说:“谈巴金而不谈他惨淡经营的文学出版事业,那是极不完整的。如果编巴金的‘言行录’,那十四卷以及他以后写的作品,是他的‘言’,他主持的文学出版工作则是他主要的‘行’。因为巴金是这样一位作家:他不仅自己写、自己译,也要促使别人写和译,而且为了给旁人创造写、译的机会和便利,他可以少写,甚至不写。”[4]实际上,文学创作和编辑出版工作共同构成了巴金一生事业中的两项重要内容,如果仅就两项工作所积累的成果来看,巴金的“行”是远远大于“言”的。
在步入文坛之前,巴金便开始了编辑活动。五四时期他即开始接触到一些宣传新思想的刊物,如《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他参加了当地《半月》杂志团体,做了月刊的同仁,也做了编辑。当时他还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自此以后,他和朋友们编过不少这类刊物,如《警群》、《平民之声》、《民众》等。1927年,他在巴黎遥控编辑了一家在旧金山出版的刊物《平等月刊》,发表了大量对当时国内局势的看法。1934年参与郑振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正式开始了他的文学编辑工作。但巴金编辑出版事业的真正开端,还是1935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成立。他担任该社总编,主编了“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译文丛书”以及后来的“现代长篇小说丛书”,在发现培育青年作家,支持新文学的发展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在继续主编文生社丛书的同时,还担任了《史学》、《中流》、《文季》、《译文》和战时联合刊物《呐喊》周刊的发行人。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文联主办的《文艺新地》、《文艺月报》、《上海文学》等刊物,他都兼任过主编。1957年,巴金又与老友靳以合作,编辑出版了全国性的大型刊物《收获》,该刊至今仍在中国文坛产生着重要影响。可以说,编辑出版工作贯穿了巴金的一生。
从巴金所编辑的大量书籍刊物考察他一生的编辑出版活动,我们发现,巴金对书稿的筛选有着独特的眼光和追求,他的编辑出版工作形成了自己个性化的风格。
一、求异。这里所说的“异”,是指在出版工作上积极寻求一种突破和创新,尤其在发现新人新作,推进新文学向纵深发展等方面,显示了其特有的胆识和气魄。比如曹禺的处女作《雷雨》,1934年由巴金推荐在《文学季刊》上发表,当即轰动了整个文坛。1935年巴金在“文学丛刊”第一集中出版了《雷雨》单行本,接着又在第三集中出版了《日出》单行本,这两部话剧,一举奠定了曹禺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地位。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当中,经过胡适、欧阳予倩、田汉、洪深、丁西林、熊佛西等人的探索耕耘,话剧创作及其理论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话剧与新文学其他文体的发展状况相比,总是显得较为薄弱,这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现代话剧缺乏在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形式上真正融合中西风格的力作,因而一直难以使中国读者和观众信服。巴金对曹禺《雷雨》、《日出》的格外注重,不仅仅是看重曹禺个人的卓越才华,这其中还特别包含着巴金对整个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总体思考。正是曹禺《雷雨》《日出》的问世,才真正奠定了中国现代话剧的坚实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巴金“发现”了曹禺,甚至可以说是巴金促成了中国现代话剧的实质性进展。巴金及文生社的这种做法,对当时的文化界而言,无疑有着前瞻性、开拓性和导向性的意义。巴金始终认为:“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2]这一编辑风格的形成,据巴金自己的解释,主要是受了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也是编辑家叶圣陶先生的影响。巴金曾在文章中多次表达过对“好的编辑”叶圣陶先生的感激之情。“倘使叶老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我甚至觉得他不单是我的第一本小说的责任编辑,他是我一生的责任编辑”;“作为编辑,他发表了不少新作者的处女作,鼓励新人怀着勇气和信心进入文坛”;“他以身作则,给我指出为文为人的道路”。[2]
“文学丛刊”是文生社出版的最重要的一种丛书。第一集编于1935年,最后一集编于1949年,一共出了十集,每集16本,整套书囊括了86位现代作家的作品,体裁包括长、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电影文学,杂文,评论,书信等。可以说,它是现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丛书。而整套丛书中,新作家的处女集子就达36部,占了总量的四分之一。除前文提及的曹禺的《雷雨》、《日出》以外,刘白羽最初的小说集《草原上》,荒煤早期短篇小说集《忧郁的歌》、《长江上》,师陀最早的三篇小说《谷》、《里门拾记》、《野鸟集》等都是在这套丛书中发行的。此外,何其芳、卡之琳、李健吾、吴组缃、陆蠡、丽尼、罗淑等许多人都是通过这套丛书开始登上文坛并享有文名的。
文生社虽然将出版重点放在培育新人方面,但同时也采用了以老带新的促销手段。如“文学丛刊”一集中,除收入曹禺的《雷雨》、沈从文的《八骏图》、李健吾的《以身作则》、卞之琳的《鱼目集》等,也收入了鲁迅的《故事新编》、茅盾的《路》、巴金的《神·鬼·人》等。“文学丛刊”的每一集都以有成就的前辈作家打头,带进冒尖的新作者,慢慢地再由这些杰出的新人带动更新的后起之秀,一批接一批,队伍不断壮大。在文生社周围团结了大批进步青年作家,如胡风、萧军、沙汀、张天翼、靳以、李广田、师陀、荒煤、方敬、穆旦、林蒲、李白风等,形成了庞大的作者群。这些作家大多是30年代的文坛新秀,是文生社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空间,成就了他们的文学生命。如果没有巴金,中国现代文坛能否出现这么一大批优秀作家,还真很难说。巴金一贯坚持的“求异”的编辑出版风格,也在过去文化的堆积层上添盖了新的文化积累,为五四新文学、新文化的向前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求精。出版精品图书在当今的出版业已经成为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树立形象、提高声誉、获得效益的重要营销手段。半个世纪以前的文生社,虽然在性质上还不能算作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实体,股东都是挂名的,社员义务工作,不领取报酬,但追求精品的意识在当时即已深入文生社同仁之心。巴金更是把书籍的艺术质量、文化品位作为自身极其重要的出版准则加以强调。在“文学丛刊”第一集后面所附的一篇发刊词性质的广告中,巴金就明确指出:“我们这部小小的丛书虽然也包括文学的各部门,但是作者并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辑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不过我们可以给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丛刊里面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
巴金对“精”的追求,并不是被动地适应市场的举措,而是主动地对文生社图书艺术含量的定位。可贵的是,巴金在编辑出版工作中,不仅超越了自身,不用自己的文学主张和文学理论来框架图书出版,同时也超越了社会上相当一些“作家编辑”利用编辑出版工作传播自身理想、排斥异己的普遍做法。巴金将自己的创作与编辑视为不同的工作区别对待。他回忆说:“过去几十年中间,我多次向编辑投稿,也多次向作家拉稿。我常有这样的情况:做编辑工作的时候,我总是从编辑的观点看问题,投稿的时候,我又站在作家的立场对编辑提出过多的要求。”[2]这就使得巴金既有强烈的个人追求,又能做到海纳百川,有着博大的胸怀。抗战时期,巴金曾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等地,冒着侵略者的炮火,为收集作家的作品而奔忙。由于战争,许多作家流离失所,他们的作品散见于各种杂志,巴金就主动代他们收集出版。如屈曲夫,当时已和巴金有几年不曾见面,巴金收集了他的小说,编成一集,以《三月天》为名在“文学丛刊”第六集中出版。还有其他一些不知名作家,如牺牲在浦东塘口战役中的宋樾,早逝于磨难中的郑定文等,巴金也帮助整理他们的遗稿出版,为这些夭折于成长中的年轻作家留下了宝贵的艺术生命的痕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巴金虽想方设法收集遭遇不幸的青年的遗稿,却始终没有放松对作品艺术质量的把关。如文学青年郑定文溺水死后,他的友人王元化、丁景唐、魏绍昌等人为出版他的遗稿而奔走,巴金接受了遗稿,但还是作了认真的阅读和筛选。在郑定文的作品集《大姊》的后记里,他坦言说明,“其中两篇类似文艺杂论而又写得不好的东西,我没有采用”[5](P202)。巴金不轻信名家,力主推荐新人,但对名家和新人的稿件,他又都要严格把关、精益求精,为文生社树立了“求精”的出版原则,同时,也在客观上提高了三四十年代新文学创作和接受的整体水平。
三、求广。文生社成立的30年代,中国文坛自由纷杂,作家们分成许多派系,除南京提倡“以民族意识为中心”的文学运动以外,主要还有北京以周作人为代表鼓吹闲适、幽默的小品文创作一派;上海以鲁迅为中心的批判现实社会的左翼文学一派;以《现代杂志》为主要阵地的现代主义小说创作一派;以《新月》为旗号的现代诗歌运动一派;等等。与新文学关系比较密切的大部分出版社,也都有自己明确的文学圈子,如生活书店出版《文学》、《译文》等都不脱离文学研究会的老牌作家圈子;开明书店的作家也是以文学研究会和“白马湖作家群”为主,并兼有编教科书(《国语文范本》)的工作;北新书局更是以五四老一代的老作家为主。至于当时规模最大的商务印书馆,也是从自身地位出发来考虑,对处于不稳定探索阶段的新锐作家的处女作很少出版,将文艺书的出版重心放在现代学术著作和古籍整理书籍上。文生社则截然不同,它兼收并蓄,出版各派系作家的作品,形成了广泛、丰富、多样化的风格。作家卞之琳在《星水微茫忆“水星”》一文中概述文坛30年代的派系鼎立状况时说:“当时北平与上海,学院与文坛,两者之间,有一道无形的鸿沟……地域的交通,仅仅是表面的,却也说明了内在或潜在的趋向。”[6](P38)文生社虽然是上海的出版机构,却在各套丛书中大量地收入了京派作家的作品,使京派创作在上海集体登场,也使京沪两地的文学青年获得了直接的沟通,从而形成了更益于文学发展的新的文化阵营。难怪海外学者司马长风介绍“文学丛刊”时,特别指出:“破除门户之见,编辑的作品包括各派的作家:其中包括批判巴金小说的刘西渭的作品,尤见巴金的气量与风度。”[7](P12)
巴金“求广”的编辑风格还体现在对中西文化的并举中。翻译出版外国文艺作品是文生社的又一项重要工作。文生社同仁通过“译文丛书”,在中国开辟了一个翻译和介绍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阵地。“译文丛书”前后共出书近五十种,第一批书出版于1935年11月,起先由黄源主编,抗战爆发后,黄源到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丛书由巴金接着主编。解放后,吴朗西也继续编过一些,一直出到1953年5月。它是文生社延续时间最长的丛书之一。
将世界文化大潮引入中国,是五四文化先驱对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及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三四十年代,这一译介工作虽然并未间断,但已转移到专注普罗文学的路子上去了,巴金主编“译文丛书”时,又将眼光重新拓展到整个世界。“译文丛书”不仅包括俄国和一些弱小民族的进步文学,如俄国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果戈理、普希金等作家的大部分作品,荷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秘鲁、朝鲜等国家和地区作家的作品;也包括了一批英、法、德、美等西方国家的优秀文学作品,世界名著《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法国·福楼拜),《两兄弟》(法国·莫泊桑),《双城记》(英国·狄更斯),《罗密欧与朱丽叶》(英国·莎士比亚),《简爱》(英国·勃朗特)等都是在这里与中国广大读者见面的。可见,巴金翻译出版外国文艺作品的出版策略,是出于系统地引入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学的志向,有着勃勃的雄心。在巴金的带领下,文生社一方面倡扬五四新文学,批判地继承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又面向世界,积极地从人类文化宝库中吸收营养。应该说,这种工作思路才真正地把握了五四新文化的思想精髓,在最广博的基础上组织和发展社会文化,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二三十年代翻译出版工作中的某些偏激倾向。
前文提及文生社为“文化生活丛刊”所作的广告词,从文生社同仁要“把学问从特权阶级那里拿过来送到万人面前,使每个人只出最低廉的代价,便可以享受它的利益”的理想,很自然地会理解出一种面向平民的出版宗旨。确实,文生社的编辑出版活动立足于民众,但又或多或少,甚至远远地超越了普通民众的欣赏品位和审美层次。文生社出版的绝大部分文学和科学书籍,不仅装帧设计精良,而且内容丰富充实,普通民众对它并非可望而不可及;更高层次的知识青年对它则会喜爱有加,因为他们从中不仅能感受到时代的脉搏,汲取先进的方法,更能寻找到对人生的启迪。这在培养能够欣赏高品位文艺作品的读者的同时,也刺激了社会对高品位文学创作、文艺出版物的需求,从而在客观上带动了整个社会文化大环境的优化、改新和重组。而巴金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充满热情和激情而著称的作家,以其对生活的极大热忱和对艺术的独到眼光,用自己燃烧着的生命之火,引导着文生社的航向,使文生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因而,从巴金在文生社的编辑出版活动来反观其文学创作的独特价值,探讨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无疑会对巴金文学创作研究提供新的更深入的视角和思路,不过那应该是另一篇专论的任务了。
收稿日期:2000-07-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