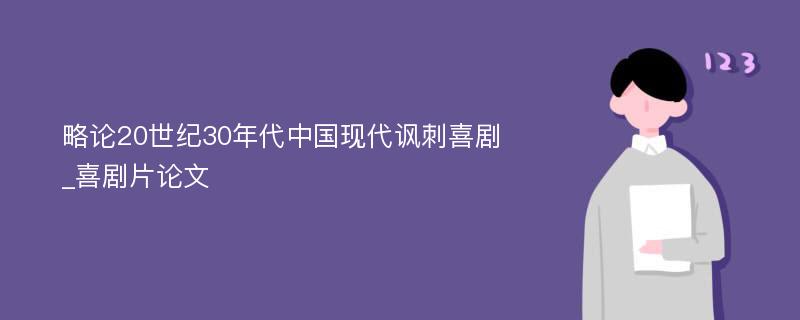
30年代中国现代讽刺喜剧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喜剧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1999)03—0353—04
无论是在实际影响上还是在艺术成就上,30年代的讽刺喜剧创作都无法与正剧或悲剧创作相比。但是,在现代戏剧的大家庭中,讽刺喜剧毕竟有着自己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功能。因此,在30年代充满战斗交响和慷慨悲歌的戏剧合唱中,人们仍然清晰地听到了讽刺喜剧特有的声音[1]。
讽刺喜剧在30年代的代表作家是熊佛西、欧阳予倩和陈白尘。他们的主要作品分别体现出30年代中国现代讽刺喜剧的三种不尽相同的取向。
一
作为中国现代剧坛上的一位著名的拓荒者,熊佛西在现代戏剧艺术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曾留下其垦殖过的痕迹。他的剧作除喜剧外,还有正剧和悲剧,但讽刺喜剧无疑是他取得重要成绩的园地。熊佛西的讽刺喜剧具有一种寓言化的明显特征。对此,我们不妨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熊氏之作具有一种单纯之美。这一点实际上是作家的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20年代末30年代初,熊佛西曾提出过以“情节精粹、背景简略、人物单纯”为具体内容的“单纯主义”的戏剧主张[2]。 这种理论的核心是要强调创作主体对于生活素材的创造性作用。当时,中国现代话剧,正处于由独幕剧向多幕剧的过渡阶段,因此提倡“单纯主义”有利于克服剧本过“实”、拉杂拖沓、结构散漫的普遍现象。这种可贵的艺术追求使熊佛西的《一对近视眼》成了一个寓言式的小品。剧本通过一对近视眼夜间将萤火虫当成鬼魂的简短故事,温和地讽刺了广义的“近视眼”,提醒人们跳出眼前的短视和烦扰,以长远的眼光去看取生活。在《裸体》当中,作家又用极为经济的笔调描绘了发生在娘娘庙内裸女雕像下面的另一场小小风波。通过道貌岸然的乡绅政大爷亲吻裸女雕像的丑行被人揭露,鞭挞了社会人生的虚伪,撕下了假道学道德风化的面纱。这些短小而有趣的作品充分显示出熊佛西喜剧的特有的简约风采。
其次,熊氏之作具有一种怪诞之美。熊佛西的喜剧大多带有浓重的怪诞色彩,为此,它们时常受到人们的白眼和小视。然而,在作家比较优秀的这类作品中,却往往包含了深沉的意蕴,反映出作者认识和表现生活的独特方式。《艺术家》中的林可梅,是“当今”“第一流”的画家,极富天才,又颇为勤勉。尽管他创作不止,然而却始终不能摆脱穷困的滋扰。最后,在贪心的妻子和兄弟的扭持逼迫之下,画家只好躺倒在地“装死一年”,为林家获得十数万元的巨款。其情节的怪诞是显然的。桑塔耶纳谈到“怪诞”时曾经提出过两个概念:“自然的可能性”和“内在的可能性”。他认为“怪诞”实际上是对生活外部形态的打破,其背离的只是前者而非后者[3]。而从后者的角度而言, 《艺术家》中的怪诞表现出来的实际上是现实生活里的某些“异化”现象。画,本是画家所为,是人的创造物,但是在这里,人和他自己的创造物却难以共存,画的价值的肯定恰恰要以画者价值的否定为前提。这样,作为那个不要艺术、扼杀艺术的时代人类异化的外化,剧中的怪诞也就具有了充分的艺术合理性和较为深沉的涵义。对于熊佛西其它作品中的怪诞,事实上也可以作如是观。
最后,熊氏之作具有一种象征之美。《喇叭》中以“喇叭”象征吹牛者和清谈家;《蟀蟋》里,用“蟀蟋”象征着同类相残的人,用周氏三兄弟象征“仁”、“义”、“礼”,用幽古公主象征人类的良知。作家在这些地方打破了形神之间的正常联系,将一种重新组合的创造性的可能与乐趣留在了生活本相和生活表象之间。和象征主义不同,熊佛西喜剧中的象征主要表现的不是人心的隐秘、通感与意象的飘忽,而是一种用粗线条写在怪诞外壳之下的人生哲理、一种对于外界乖谬悖理的审美评价。这样,无论就剧本所要表现的理性意蕴来说,还是就这一理性意蕴的具象化过程而言,它们都具有较大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使熊佛西的喜剧失去了诗意的蕴藉,但作为补偿,它却给熊氏的作品带来了某种通俗性。
对于20年代上半期讽刺喜剧的作者来说,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赋予讽刺以一种喜剧的形体,至于这种形体本身的质量似乎一时还难于真正摆进议事日程的中心。而就在这个时候,丁西林的幽默喜剧却在艺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对于讽刺喜剧,这既是启示,也是压力。因此,摆在20年代下半期讽刺喜剧创作者面前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如何提高这类作品的艺术和美学品位问题。熊佛西寓言型喜剧的出现代表了讽刺喜剧作家在这一方面取得的可喜成果。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喜剧的新品种,寓言型的讽刺喜剧虽然在30年代初以后悄然离开了中国现代喜剧的中心舞台,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寓言精神在现代讽刺喜剧艺术中的湮灭,经历了历史不断扬弃之后的那种借此喻彼、借近喻远、借浅喻深、借实喻虚的原则、方法和技巧,事实上已经流布到中国整个的现代戏剧创作中,并将化作一种艺术的基因而与之长存。
二
自20年代末开始,多重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的交织与激化,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态势向中国的剧作家们施加了巨大的社会的、政治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压力,要人们面对现实的诘问和挑战做出尽可能明确的回答。越来越多的追求进步的作家开始抛却了那种或明或暗、若即若离的生活态度,作品中的客观性的社会性因素也随之愈来愈加明朗。在时代要求的推动下,随着人们对于写实主义理解的不断深入,写实型的社会讽刺喜剧从1930年前后开始日趋活跃,并且很快走上了中国现代讽刺喜剧的中心舞台。
这一类型的作品往往是以种种社会问题为透视点,用写实或大体写实的表现方法,去表达作家对于社会现实执著的生活态度和对于社会丑恶的否定的创作激情。同寓言型讽刺喜剧相比,它们通常有着更为生活化的形式、更加明确的现实感和批判的直接性与广泛性。30年代的写实型社会讽刺喜剧以揭露虚假为中轴,对社会的堕落、人心的卑琐、金钱的毒化、特别是在爱情与家庭关系方面反映出来的种种病态与畸形作出了讽刺性的审美观照。上述因素的交叉配置和错落融合使得这一类型的作品在取材范围和立意角度上都明显地呈现一种散射状多元化的发展趋向,从而体现出写实型社会讽刺喜剧在表现社会生活方面的虎虎生气。
30年AI写作实型社会讽刺喜剧创作中艺术品位最高的是欧阳予倩的作品。作为中国现代喜剧的一位重要的奠基者,他早在1913年已经开始了讽刺剧的尝试,在其后的30年间,他的讽刺喜剧之作不断出现,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欧阳予倩是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剧作家,但他从不曾为着思想倾向的重要性而忽视艺术追求的必要性。在他看来,用艺术宣传主义固然应该,但一定要以“必先有艺术”为前提[4]。 这种可贵的艺术自觉使他的喜剧不仅具有积极的思想价值,而且也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从1929年起,他的讽刺喜剧沿着社会写实的径路日趋成熟,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富于代表性的风格。
欧阳予倩的讽刺喜剧最显著的特征是它的写实性。作家不仅将写实主义同“为人生”的精神联系起来,而且也充分意识到这一创作原则对于题材、人物及其表现艺术的特殊要求,即对于客观的、真实的、具体的社会生活本身的关注。作为一位四海为家的戏剧工作者,欧阳予倩与社会各阶层人士有着广泛的交往,这使他有着极为丰富的人生阅历。其作品中的不少题材和人物的原型都在这种亲身的阅历中撷取的。他的《屏风后》创作于广东戏研所时代,剧中所写的那位满嘴仁义道德的老绅士就“确有其人”,而且在当时的广州也确实存在着“道德维持会”一类的社会组织[5]。当然,就欧阳予倩喜剧的题材来源而言, 未必都是来自己有的真人真事,他的喜剧《白姑娘》的主要题材就脱胎于法国的一篇小说。但即使如此,作家也要求他们必须符合“会有的实情”。正如鲁迅所指出的,这种“会有的实情”同样可以符合写实性讽刺的本质要求[6]。在《白姑娘》中,两位丑角演员为了独占白姑娘的芳心, 决定以表演比赛来一决雌雄,看看谁的扮演更逼真。乍看上去,这未必是已有的“实事”,但作家却抓住了“刽子手”与当时“白色恐怖”之间隐喻性联系,利用一系列细节的描写和情境的假定为这个情节营造出一种真实的氛围。
这种对于写实性的自觉追求,对于中国现代讽刺喜剧的发展与成熟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它提高了作家观察、识辨生活的能力,拓展了作品对外部世界的表现视野,从而为讽刺喜剧乃至整个喜剧在现代中国的发展打开了广阔的通路。特别是当作家有意识地抓取那部分本身具有着多重意义的社会生活来作为自己艺术处理的对象的时候,其作品的讽刺性意蕴就可能呈现出一种层次性和丰富性的特征,而只有在具备了这一特征情况下,中国的讽刺喜剧才能最终实现自身的社会性升华。在这方面,《买卖》是一个成功的例证。
《买卖》是欧阳予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二个“十年”中的重要作品,无论在认识现实的深度上,还是在艺术表现的功力上,它都达到了这一时期喜剧创作的较高水平。作品描写买办陶近朱和梅希俞为了洋人大老板的利益和丰厚的回扣急于要在军火生意上同军方代表宋四维签定一份重要的合同;由于担心同业竞争而设下美人计,最后终于以梅希俞之妹梅可卿为诱饵达到了目的,洋人、买办和军阀三者在这场交易中分别得到各自想要的东西。正如剧中主要人物陶近朱在剧尾所说:“这才是买卖里头套买卖”,剧本所要讽刺的绝非一种单纯意义上的人肉交易,这就决定了《买卖》在客观意蕴上的多层性和丰富性。“买卖”在这里既是个人间的买卖,也是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间的买卖;既是人肉的交易,又是经济、军事和政治上的交易。从这一系列复杂交错的买卖交易中,除了可以看出国民党政权及其社会基础荒淫无耻和卑鄙丑恶之外,还可以看到封建阶级、买办阶级、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经济和政治上的交易与勾结,以及南京政府治下帝国主义势力急剧扩张、中国社会进一步买办化、殖民化的历史过程。
尽管讽刺本身并不总是引人发笑,但讽刺喜剧却无疑是一种笑的艺术,而笑的艺术是社会性的艺术。就其本质的规定性而言,作为整体的讽刺喜剧应当而且必须去反映尽可能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社会性尺度应该成为我们判定讽刺喜剧,尤其是现代讽刺喜剧艺术品位和成就的主要标准之一。虽然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现代讽刺喜剧已经对愈来愈广泛的社会问题投以了关注的目光,但就多数寓言型作品和部分写实性作品的实际情况来看,它们对丑恶与虚假的抨击主要仍是“伦理的”而非“社会的”。某些写实作品未能达到社会性高度这一事实只能说明讽刺的写实性并不等于社会性。但欧阳予倩作品在社会性方面的成功却无疑在昭示人们:对写实性认识的深化和自觉追求,显然是促成现代讽刺喜剧社会化的有效途径。当作家的讽刺锋芒不仅指向虚假伦理观念本身,而且同时也揭示出造成这种虚假伦理价值观念的社会条件的真实的时候,讽刺喜剧必然会迸射出独特的光彩。
《屏风后》常被人单纯理解为对于假道学和伪君子的揭露,但作品的实际意蕴却绝非仅仅如此。大革命过后,随着政治反动到来的必然是思想文化各个方面的反动,旧文化旧道德不仅沉渣泛起而且肆虐一时。剧中的道德维持会正是适应这样一种反动时代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官方机构。因此,作家抓住作假这个关节之点对于道德维持会的揭露,实际同时必然也是对于新军阀政权在思想文化界倒行逆施的无耻伪善的揭露。康扶持本系北洋政府的要员,而今却又摇身一变成了新军阀治下维持地方风化的官员,这说明:新旧军阀的统治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它们都是靠康扶持那样的败类“扶持”的。《国粹》是围绕妇女问题展开的一出六景剧。全剧以官办的“女子解放运动”为背景,前两景以“妾”为重心,后两景以“婢”为重点,中间两景凸出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从而组成了一个富于跳跃感的艺术结构体。作品通过言行表里、现象本质之间的多重比照,不仅表达了自己对纳妾蓄婢问题的独立见解,而且指出了正是那种贫富对立的社会现实才是产生和维系这些恶俗陋习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作品还暗示出国民党政权在其成立初期的历史特征和社会实质。从上述两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欧阳予倩30年代的喜剧已经在总体上跳出了单纯伦理批判的窠臼,完成了伦理性批判与社会性批判的艺术统一。
从中国现代喜剧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欧阳予倩30年代喜剧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们代表了一种极具生命潜力的艺术风格,而且还在于它们也是由社会讽刺喜剧向政治讽刺喜剧演进的一种过渡的形态。由于作家对于现实生活的高度敏感和对于写实艺术的不懈追求,在其作品的社会内容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政治因素的积累和扩张。当这种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作品势必会产生质的飞跃。30年代,是一个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集中以政治的形式爆发出来的时代,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政治都表现出一种压倒一切的气势和力量。这就为中国现代讽刺喜剧的政治化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客观依据。尽管在“九·一八”之后,欧阳予倩成了一位富于政治色彩的作家,但最终完成政治与讽刺艺术结合的却不是他,而是以陈白尘等人为首的一批文学新人。
三
1928年,在革命文学论争的声浪里,一位刚刚回国不久的青年文学工作者创作了我国新喜剧史上第一篇成形的政治讽刺喜剧——《县长》。他就是后来很快成为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中坚人物之一的冯乃超。《县长》在艺术表现上或许算不上完美和深刻,并且带有模仿《钦差大臣》的明显痕迹,但它对现代喜剧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928年到1935年前后的六七年间,我国新兴的政治讽刺喜剧一直在一种尴尬的情势中踯躅前行。冯乃超自《县长》之后再没有写过喜剧。杨村人1929年发表了《租妻官司》,通过青天白日旗下一场奇异的官司讽刺了国民党的法律,同时也嘲讽了南京政权统治之下社会的普遍凋敝。叶沉1930年发表的《蜂起》和白薇稍后写成的《一视同仁》以罢工为前景嘲弄了政府当局、黄色工会和资产阶级。魏金枝的《宣誓就职》则暴露了新官僚的丑恶。整个创作情况,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讲都没有明显的提高。大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时代的新三民主义迅速蜕变为国民党当权派的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南京政府的鬼蜮伎俩和倒行逆施为中国现代史册掀开了极富讽刺意味的一页,这就在客观上为讽刺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某种相应的土壤。然而讽刺性文学并没有像人们意料的那样迅速地发展起来,究其原因,和当时左翼文艺运动指导思想上的片面性不无关联。不少左翼人士对喜剧形式怀有程度不同的成见。[7] “论语派”力倡“幽默”则在另一方面加深了他们对喜剧的警觉和疑虑。
随着后来整个左翼文艺队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水平的提高和文艺观念的拓展,随着统一战线思想的广泛传播和不断明确,随着革命戏剧运动向剧场艺术阶段的发展,一部分左翼文艺人士陆续开始举起了讽刺喜剧的投枪。自1935年前后,喜剧创作逐渐出现了日臻活跃的局面。而中国新兴的政治讽刺喜剧正是在这个喜剧的跃动中取得了重要的发展,出现了宋之的《平步登天》、左兵的《猫》和陈白尘的《恭喜发财》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陈白尘的《恭喜发财》是战前中国政治讽刺喜剧创作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大型剧作,同时也是整个30年代的喜剧创作中的重要收获。从冯乃超的《县长》到陈白尘的《恭喜发财》,清楚地表明了中国政治讽刺喜剧在困境中奋然前行的轨迹,沿着这条史的线索,不难发现《恭喜发财》的艺术价值所在。
首先,剧本沿着《县长》开拓的方向,继续深化了那种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主题。粗看上去,作品反映的只是普通教育界的情况,但是由于作家的写作是以“一二·九”运动为背景的,同时又将教育界的现实同国民党政府“航空救国”的丑剧联系在一起,这样就使全剧的主题达到了政治性的高度。在现实生活中,政治并不是孤立的,相反,它的重要性正好表现在其对于包括人们日常生活在内的社会各个领域的制约和渗透上。因此优秀的政治讽刺喜剧并非意味着一定要单就“政治”去讽刺时政,它应当深入开掘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因素,然后在艺术概括的基础上使人认清社会政治的本质。《恭喜发财》基本做到了这一点。围绕“航空救国”的骗局,作品广泛描写了国民党基层政权和地方教育界中大小官僚们多方面的丑行恶德,这样,在直面关系民族存亡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同时,也将丰富的生活内容囊括到了自己的喜剧构架之中。
其次,《县长》在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的缺欠在于它的直露,而《恭喜发财》则在这方面有了明显改进。还在陈白尘的《征婚》中,人们就已经发现了作家组织喜剧冲突的特殊才能,他善于为自己的讽刺喜剧找到一种独特的审美角度和艺术形式,而不是满足于将生活中的事件平铺直叙。作家在《恭喜发财》中巧妙地运用了一种暗示的方法,顺着这种暗示的指引,让人们认识到全剧只是更广阔的社会的一部分,而这个更广阔的社会要比剧中作为外在层次的事件和人物具有更大、更重要的意义。在一座小学校里,校长假借抗日的名义侵吞着学生的捐款;在整个国家,当局打着救国的幌子攫取了民众的捐款。作家抓住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似之处,明写前者,暗示后者,最终达到了以独特的审美视角表现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生活、揭露反动当局的腐败和假抗日行径的目的。
最后,在人物塑造和心理刻画上,《恭喜发财》也达到较高的水平。如果说,《县长》的作者只是表现了自己在这些方面的追求,那么《恭喜发财》的作者在这些方面则已取得了实际的成就。随着全剧情节线索的展开,作家为我们透视出主人公心理变化的线索。由见到传单后的恐慌,到上峰派员检查时的隐忍;由中彩后的狂喜到潜逃未遂时的沮丧;由顺水推舟时的权变到受到嘉奖时的傲慢;随着这条人物心理波动的曲线,作家让刘少云尽情地表演,表现出自己灵魂的各个侧面,让人们在笑声中鞭挞着这个畸形而丑陋的灵魂。除此之外,剧本对为人正直、真心爱国的鲁效平,处世圆滑、善于逢迎的张乐平,胸有城府、官气十足的朱督学等人物的性格塑造也都给人留下了生动的印象。
中国新兴的政治喜剧在进入国防运动时期之后,面临着一种重要的转折。陈白尘等人正是实现这个转折的勇敢的实践者。他们继承了“五四”以来新文学敢于直面社会人生的光荣传统,发扬了革命文学爱憎分明的战斗精神,在俄罗斯富有讽刺特色的喜剧艺术的启迪下,以《恭喜发财》、《猫》、《平步登天》这样具有艺术价值的战斗作品,为40年代中国政治讽刺喜剧的大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收稿日期]1999—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