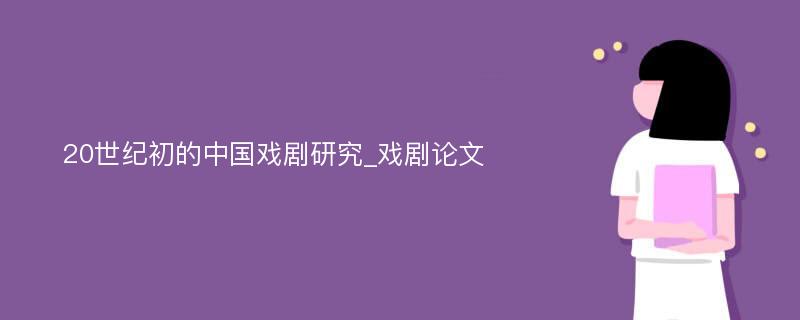
试论20世纪前期的中国戏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中国戏剧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的前半叶,中国戏剧的研究从无到有、由点及面不断走向成熟,从而最终确立了中国戏剧研究的基本格局,各方面的研究均达到相当的学术高度,在某些领域甚至取得后世难以企及的成就。所以对整个20世纪中国戏剧研究而言,前期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借助相关的历史资料,客观地呈现20世纪前期中国戏剧研究不断走向成熟的历史过程,描述其一时繁荣的历史表象及表象后的历史动因。
一、研究风气的渐成
在上个世纪初的前二三十年,中国戏剧研究风气的逐渐形成有赖于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促成。在王国维《戏曲考原》、《宋元戏曲史》等著作问世之前,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可以说是很少的,甚至可以说近乎空白。1913年,王国维自序其《宋元戏曲史》云: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硕儒,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数百年,愚甚惑焉。[1] (P1)
王国维此处主要是就元曲的境遇而言,因其“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后世硕儒,皆鄙弃不复道……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数百年”。元曲尚有“一代之文学”之誉,而元曲之前的南戏、元曲之后的传奇、乱弹,自然更遭鄙弃。在尊“经”崇“史”的文化格局中,标榜敦厚之旨的诗、文尚属雕虫小技,“致远恐泥”,词曲、小说不得尊重,乃属情理之必然。近代戏曲、小说等能作为一门学科,成为“学问之事”,必有西方文化观念的输入、刺激才有可能。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等著作正是王氏“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陈寅恪语)的结果。
当王国维1908年开始其中国戏剧的研究时,可谓是孤军奋战,偌大的中国几乎找不到可真正引为同道者。《宋元戏曲史》发表前后,同时的吴梅(1884-1939)、王季烈(1873-1952)、姚华(1878-1930)等“(昆)曲家”虽亦有文著问世,但他们的研究大多不脱传统曲学研究的格局,以“实用”为最高目的,很难以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标准来衡量。这种情况直到1917年陈独秀、胡适之等人发起新文化运动时仍未有显著改观。
新文化运动的嚆矢在建设新文化,同时促成旧文化的崩溃。这一“新”、一“旧”其属义略同于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在新文化运动的初始阶段,包括“旧戏”在内的中国传统的东西不可能得到相应的同情、尊重,甚至遭遇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中国戏剧(当时称为“旧戏”)研究自然难以展开。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发生分化,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已过,知识界民族主义精神兴起,民族的和传统的渐受尊重。1923年胡适等人喊出“整理国故”的口号,胡适本人大谈其“考据癖”,以他的学生顾颉刚为领导核心的“古史辨”派学者全心投入上古史的研究。在胡适倡议下,商务印书馆在20年代中后期陆续出版了《国学基本丛书》280多种(550册),《国学基本丛书简编》50种(120册),此外又有《学生国学丛书》93种、《国学小丛书》203种。与此同时,国学杂志风起云涌,如《国学季刊》(北京大学)、《清华学报》(清华大学)、《燕京学报》(燕京大学)、《辅仁学志》(辅仁大学)、《女师大学术季刊》(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文哲季刊》(武汉大学)、《史学专刊》(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央研究院)、《金陵学报》(金陵大学)、《中大季刊》(中央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北平图书馆)、《史学年报》(燕京大学)等等[2]。1923年后,“国(故)学”研究的风气日渐浓厚。这一方面反映了20年代知识界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时也不能不归功于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因为此时的“国学研究”已不同于此前的“国粹”派学者的研究,而是带着新文化运动的胜利成果进入到“国故”研究的。以文学研究而言,以诗文为正宗的传统的文学观念已被打破,代之以“新”的文学观——“托体稍卑”的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亦成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国学”研究的风气相应,20年代中后期,知识界对中国传统戏剧的评价也发生方向性转折,当年曾在《新青年》等杂志上猛烈攻击“旧戏”的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欧阳予倩等“新文化人”已转身向“旧戏”表现出好感和敬意。本由余上沅、赵太侔等新剧家发明的“国剧”一词不到两年即为“旧戏”所俘获,成为“旧戏”的荣誉头衔。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发表十余年后,其示范导路之功日渐显著。1925年,赵万里在《清华学报》上发表《旧刻元明杂剧二十七种序录》,这是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之后的有关元明杂剧的翔实的文献学研究。1927年,《小说月报》第十七卷号外上发表了欧阳予倩的《谈二黄戏》、许地山的《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的点点滴滴》,前者是乱弹戏研究方面最早最重要的论文之一,后者则最早在中国戏剧起源问题上提出“外来说”。钱南扬自1924年即留意南戏研究,1929年首次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他的南戏研究成果《宋元南戏考》,其学术水准已明显超过《宋元戏曲史》中的相关论述。以上论著分别涉及戏剧起源以及南戏、元杂剧、乱弹等戏剧类别,其研究方法和具体的研究均表现出对《宋元戏曲史》程度不一的超越。20年代中后期,中国戏剧研究方面发表的文著当然决不仅限于上述数篇,所有的现象都在说明中国传统戏剧研究的风气已开始形成。1923年9月,胡适为徐嘉瑞《中古文学概论》做序说:
从前的人把词看作“诗余”,已瞧不上眼了,小曲和杂剧更不足道了。至于“小说”,更受轻视了。近三十年中,不知不觉的起了一种反动。临桂王氏和湖州朱氏提倡翻刻宋元的词集,贵池刘氏和武进董氏翻刻了许多杂剧、传奇,江阴缪氏、上虞罗氏翻印了好几种宋人的小说。市上词集和戏剧的价钱渐渐高起来了,近来更昂贵了。近人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对于小说渐渐尊重赏识了。这种风气的转移竟给文学史家增添了无数难得的史料[3]。
胡适之先生的这段话真实地反映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出版界、收藏界的新风尚。1917年,武进董康编辑的《诵芬室读曲丛刊》(七种)开始印行。同年,贵池刘世珩编辑《暖红室汇刻传剧》亦开始编刊[1]。191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元曲选》。1920年,上海中国书店影印了明人沈泰编辑的《盛明杂剧二集》。1921年,陈乃乾编辑的《曲苑》由古书流通处印行[2]。1924年,上海中国书店影印日本覆刻本《元刻古今杂剧》(即《元刊杂剧三十种》)。1928年,吴梅先生编辑的《奢摩他室曲丛》(第一、二集)也开始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上述文献的刻印和流通,为一般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促成了后来戏曲研究的繁荣。
二、30年代的一时繁荣
对20世纪的中国戏剧研究而言,30年代是最值得追忆的一段时间。名家辈出,名作迭现。从各方面的情况看,中国戏剧研究在30年代呈现出极为繁盛的景象。这种繁盛局面的出现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最直接的原因则是因梅兰芳访美的刺激。
1930年1月18日,梅兰芳率领“承华社”剧团踏上访美的航班。梅剧团在美国先后访问了西雅图、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洛杉矶、圣地亚哥、旧金山和檀香山等八个城市,历时半年,受到美国朝野各界的热烈欢迎。美国波摩拿学院、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分别授予梅兰芳文学荣誉博士学位。梅兰芳博士的载誉归国,令国人兴奋异常。梅的荣誉既是他个人的,也同时是全中国人的。中国人近百年来饱尝国耻,如今从西方世界,而且是从最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赢得赞誉,所以有足够的理由感到自豪。
梅兰芳访美之后,国内民族戏剧研究的风气日盛,这首先表现在各种官方以及民间研究学会和团体的大量涌现。1932年,傅芸子在日本京都帝大支那学会发表了题为《中国戏曲研究之新趋势》的演讲,内中说:
余素喜研究中国文学,少年时代,居邻剧场,以此环境之关系,故比较的对戏剧为有兴趣——尤其是南北曲。近年以来,国人研究戏曲已成一种新风尚,余有几位最爱好戏曲之友人,复时与戏界人往还,渐养成一种癖嗜——研究戏曲——近年余在北平,又曾主编三四个戏剧刊物,平日之生活,几有“戏剧化”之倾向了[4]。
傅芸子这节话为我们透露了当时的很多社会信息。1930年,国民党元老李石曾用庚子赔款创办中华戏曲音乐院,院内设北平戏曲音乐分院、南京戏曲音乐分院。北平戏曲音乐分院由梅兰芳任院长,齐如山任副院长。南京分院由程砚秋任院长,金仲荪任副院长。北平戏曲音乐分院虽在北平,实徒具空名。南京分院实际仍在北平院内,附设中华戏曲音乐学校,焦菊隐任校长。但程砚秋在李石曾强有力的经济支持下,在徐凌霄、陈墨香、邵茗生、翁偶虹、杜颖陶等人拥护下,创办了大型戏剧专刊《剧学月刊》,颇有声势。程本是梅的弟子,此时乃大有凌驾其师而上之势。梅的好友多为不平,乃挽梅兰芳、余叔岩合作,在周作民、王孟钟等银行家的支持下,在1931年12月发起组织北平国剧学会,襄助梅兰芳国剧研究会的文人主要有齐如山、傅芸子、傅惜华、胡伯平、段子君、黄秋岳等人,他们编辑出版了《戏剧丛刊》、《国剧画报》、《戏曲大辞典》等,以此回应来自程砚秋的挑战[3]。傅芸子正是北平国剧学会中的活跃分子之一,他演讲中提到的“几位最爱好戏曲之友”正是指齐如山、胡伯平诸人。
以梅兰芳、程砚秋这两位著名京戏艺人为中心的北平国剧学会、南京戏曲音乐分院,一得民间实业家的赞助,一得政府资本的支持,其时大有抗争之势。傅芸子在文中还提到30年代初其他的一些研究学会和团体,如王泊生主持的国剧传习所,溥侗主持的中国剧学会,傅惜华、刘澹云主持的昆曲研究会等。
值得说明的是,参与南京戏曲音乐研究院和北平国剧学会的文人多是剧评家,如齐如山、徐凌霄、陈墨香等,他们多是“戏迷”出身,与演员往来密切,熟于梨园掌故,自己也懂戏(主要是京戏),有的还是剧作家或票友。他们这些人之所以心甘情愿地拥戴梅、程,因为梅、程皆以“戏”而成为社会名流(梅兰芳甚至拥有博士头衔),很有社会号召力,可以为他们提供很多研究之便(如梅、程皆收藏大量的戏曲钞本、脸谱等文物)。成就研究风气之盛的除了这样一批剧评家外,还有王国维一类的“学问家”、吴梅一类的“曲学家”,这些人其身份大多为大学教授或者有在大学任教的经历。1935年,张次溪为张笑侠《国剧韵典》做序说:
近20年来,我国文学界因受西洋自由解放思想之影响,亦起重大变化。于是向来为人漠视之戏曲小说,已一跃而升为文学。其提倡之者,初有王静安先生,继则为吴瞿安、许守白、王君九、刘凤叔诸先生。俱有深刻之研究,并刊行有价值之作品问世[5]。
张次溪此处主要提到两类人:一类为王国维式的纯粹的“学问家”。20年代中后期,王氏在国内学术界声望日隆,特别是1927年辞世后,《宋元戏曲史》的影响也愈加深广。《宋元戏曲史》历史考据的方法,在孙楷第(1898-1989)、钱南扬(1899-1987)、冯沅君(1900-1974)、赵景深(1902-1985)等后起的一辈“学问家”那里得到发扬和光大。张次溪提及的另一类人,如吴梅、许之衡、王季烈、刘富梁等,皆为闻名当时的“曲家”,社会声望甚高,皆以度(昆)曲为风雅之事。其中的吴梅、许之衡则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南京东南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4],他们在大学教授戏曲,对传统的社会观念冲击力甚大,在抬高了戏曲的社会地位的同时,也为后来的研究培养了一大批研究人员。
1936年9月,赵景深在为其《读曲随笔》所做的《序》中曾经提到他30年代因曲学研究结识的许多同道:
有一点使我高兴的,就是我一面读曲,一面认识了许多读曲的朋友,如王玉章、吴梅、沃圃、杜颖陶、青木正儿、长泽规矩也、陈乃乾、张次溪、贺昌群、郑振铎、钱南扬、卢冀野、顾名、顾随诸兄,或面晤,或神交,或通信讨论,或相与纵谈,其乐无穷。那么,这本书就算是我与诸君子作个小卒来摇旗呐喊一下吧。[6]
由赵景深先生开列的这份名单,我们不难想见当时曲学研究阵容之齐整。与整齐的研究阵容相应,林立的研究刊物也为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阵地。除《燕京学报》、《东方杂志》、《图书季刊》、《小说月报》、《说文月刊》等大型学术杂志经常刊登戏剧研究方面论文外,《北平晨报》、《大公报》(天津)、《天津益世报》、《申报》等报纸也经常在副刊上刊登戏剧研究方面文章。同时,一些戏剧类专门期刊也先后出现,除前文提及的《戏剧丛刊》、《国剧画报》、《剧学月刊》外,又有《戏剧月刊》、《戏剧旬刊》、《戏剧》、《十日戏剧》、《戏剧岗位》等。
在这一时期,名家名著亦先后问世,与此同时,大批戏曲文献亦得到刻印和整理出版。如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印行《永乐大典戏文三种》(1931)、陈乃乾编《增订曲苑》(上海:六艺书局,1932)、郑振铎编《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傅斯年图书馆,长乐郑氏影印富春堂刻本,1934)、卢前编《饮虹簃所刻曲》(30种,金陵卢氏饮虹簃刻本,1935)、卢前编《元人杂剧全集》(八册,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35、1936)、郑振铎编《清人杂剧初集》(长乐郑氏影印清刊、清抄本,1931)、周明泰编《几里居戏曲丛书》(几里居刻本,1932年至1940年)、张次溪编《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北京:邃雅书店,1934年)、郑振铎编《清人杂剧二集》(长乐郑氏影印清刊、清抄本,1934)、叶圣陶、徐调孚校订《六十种曲》(上海:开明书店,1935)、任讷编《散曲丛刊》(上海:中华书局,1936)、张次溪编《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北京:松筠阁书店,1937)、卢前编《朝野新声太平乐府》(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任二北编《新曲苑》(上海:中华书局,1940)等。上述文献的重新刻印或整理出版,使得过去不易觅得的戏曲史料、论著成为研究者们的易得之物。
从以上诸端看,30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七八年,中国戏剧的研究无疑处于一种极为繁盛的局面。可惜因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这种繁盛局面很快走向衰微。30年代末以及40年代,也有一些较为重要的论著问世,如卢前《读曲小识》(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孙楷第《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图书季刊》,1940)、王季烈《孤本元明杂剧提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41)、冯沅君《古优解》(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冯沅君《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盐谷温《元曲概说》(隋树森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冯沅君《古剧说汇》(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严敦易《元剧斟疑》(《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上、中、下,1948)、吉川幸次郎《元杂剧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48)、董每戡《中国戏剧简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等。但从总体来看,繁盛的局面已一去不复返了。
三、中国戏剧学科的建构
自20年代中后期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除王国维、吴梅、许之衡等先行者之外,20世纪中国戏剧研究中卓有建树的研究大家们已纷纷陆续登场。研究大家们的学术禀赋及出身背景各不相同,他们进入中国戏剧的研究时自然表现出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立场的选择,同时也从不同方面提供其研究方法与路径,从而使得20世纪前期中国戏剧学科的建构初具规模。
首先,从研究对象和范围来看,表现出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王国维对中国戏剧的研究限止于宋元,更具体的说是元曲。吴梅、王季烈等曲家的研究虽然以明清为主,但主要对象实际上是昆曲。这是20世纪前20多年的情况,自2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种限于元曲、昆曲的局面渐被打破。1927年,欧阳予倩发表《谈二黄戏》,这标志着近代花部戏剧开始赢得研究者的真正关注。30年代以梅兰芳、程砚秋为核心的剧评家,其研究对象大多以当时流行的京戏为主,其代表可推齐如山先生。刘守鹤《祁阳剧》(《剧学月刊》三卷二期、三期,1934年2月、3月)、马彦祥《秦腔考》(《燕京学报》第十一期,1932年6月)佟晶心《八百年来地方剧的鸟瞰》(《剧学月刊》第三卷第九期,1934年9月)、杨铎《汉剧丛谈》(北平国剧学会,1935年版)、雪侬《三十五年前粤剧班底组织》(《剧学月刊》第四卷第五期,1935年5月)、麦啸霞《广东戏曲史略》(《广东文物》,1940年10月)、赵景深《说弋腔》(《学术》第四期,1940年)、傅芸子《释滚调:明代南戏腔调新考》(日本《东方学报》第十二卷第四期,1941年)等。上述论文的发表,标志着花部戏剧(地方戏)的研究已成为戏剧研究的一大宗。
1927年,钱南扬发表《目连戏考》(《国学月刊》第一卷第六号,1927),这说明与民间宗教祭祀密切相关的仪式戏剧也开始得到研究者的注意。此后,李家瑞《中国傀儡戏考略》(《大公报·戏剧》,1929)、姜亮夫《傩考》(《民族》第二卷第十期,1934)、佟晶心《中国影戏考》(《剧学月刊》第三卷第十一期,1934)、邵茗生《汉魏六朝之散乐百戏》(《剧学月刊》第二卷第九、十期,1933)等论文对傀儡戏、傩戏、百戏、舞蹈等方面的关注,都说明这些研究者正尝试从不同方面理解中国戏剧的艺术构成。
从学术立场的选择看,20年代中后期的研究与前二十年相比也有显著的进步。戏剧本是“舞台艺术”,但不论是王静安先生,还是吴瞿安先生,他们对中国戏剧作为“舞台艺术”的特征均有所忽略,王国维先生是不看戏的,吴梅先生则热心于度曲、谱曲和订曲,所以王吴两位的戏剧研究都过于偏重案头的“曲”本或“剧”本,对作为舞台艺术的“戏”都未予足够的注意。但“戏剧”研究毕竟不同于“词曲”的文辞赏鉴或思想内涵的阐发,中国戏剧毕竟不只是案头赏读的“韵文学”,而是登诸场上的“戏剧艺术”。自30年代,这种以王国维、吴梅为代表的偏重“文学”或专重曲文格律研究的状况才渐被打破。北平国剧学会的齐如山、傅芸子、傅惜华等核心成员和南京戏曲音乐研究院的徐凌霄、陈墨香、邵茗生、翁偶虹、杜颖陶等《剧学月刊》的同仁,其学术研究的着眼点已明显与王国维、吴梅有异,戏剧角色、脸谱、身段谱、唱腔、戏班、剧场等“舞台艺术”构成的要素开始成为研究者们考察的对象。以国剧学会主办的《戏剧丛刊》、《剧学月刊》刊出的文章为例。30年代初,《戏剧丛刊》、《剧学月刊》曾相继刊出齐如山《戏剧脚色名词考》(《戏剧丛刊》第一期,1932)、齐如山《脸谱研究》(《戏剧丛刊》第一期,1932)、齐如山《国剧身段谱》(《戏剧丛刊》第三期,1932)、陈墨香《说旦》(《剧学月刊》一卷四期,1932年4月)、杜颖陶《玉霜簃藏身段谱草目》(《剧学月刊》第二卷第四期,1933年4月)、王芥兴《戏剧角色得名之研究》(《剧学月刊》三卷六期,1934年6月)、翁偶虹《脸谱的产生》(《剧学月刊》四卷五期,1935年5月)、翁偶虹《脸谱的产生》(《剧学月刊》第四卷第五期,1935年5月)等论文。上述论文,其研究旨趣与立场显与王国维、吴梅不同。
假如说齐如山、徐凌霄、陈墨香等“戏迷”出身的剧评家,其戏剧研究偏重场上,是出诸自然,那么郑振铎、周贻白、董每戡等人则出于自觉的认识和选择。1934年12月,郑振铎为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做序说:
近二十年来,中国戏曲的研究,有了空前的进步。王国维先生的《曲录》和《宋元戏曲史》奠定了研究的基础。而最近三五年来,被视为已轶的剧本和研究的资料,发现尤多。中国戏曲史的写作,几有全易面目之概。较之从前仅能有《元曲选》、《六十种曲》寥寥数书作为研究之资者,诚不能不说我辈是幸福不浅。惟一般的研究者,往往只知着眼于剧本和剧作家的探讨,而完全忽略了舞台史或演剧史的一面。不知舞台上的技术的演变和剧本的写作是有极密切的关系的。如果要充分明了或欣赏某一作家的剧本,非对于那个时代的一般舞台情形先有了些了解不可[7]。
周贻白先生的戏剧研究,案头、场上兼重,他在30年代曾分别完成《中国戏剧史略》、《中国剧场史》二书,假如说前者偏重“案头”,后者则偏重“场上”,试图以弥补前者的缺失。在周贻白撰写《中国戏剧史略》、《中国剧场史》前后,徐慕云发表的《中国戏剧史》(世界书局,1938)、治夔离《宋元杂剧演出考》(《舞台艺术》,1935)、钱南扬《宋金元杂剧搬演考》(《燕京学报》二十期,1936)等文著皆体现着将案头文献与场上艺术相结合的研究思路。
从具体的研究方法看,学术出身不同、学术趣味有异的研究大家的涌现,使得民族戏剧的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样性和互补性。20世纪前二三十年,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等论著中惯用的历史考据的方法、吴梅《顾曲麈谈》等论著对戏曲格律的专注,对后来都有直接的影响。在30年代崛起的年轻一辈学者,如孙楷第、冯沅君、赵景深、任二北、钱南扬、卢前、王玉章等人,从研究方法看虽各有所侧重(如孙楷第可能偏重“考据”、卢前可能偏重“格律”),但一般是兼而有之,最典型者为任二北、钱南扬。而且他们在“考据”、“格律”二法之外,一般同时操有其他法宝。
傅芸子在《中国戏曲研究之新趋势》的演讲中,曾经将当时的研究者分为“整理派”和“校勘派”两派。其所谓“整理派”主要是指以齐如山为代表的偏重戏曲文献、图样搜集、整理的学者;其所谓的“校勘派”即以马隅卿、郑振铎、朱逖先、傅惜华等“治戏曲版本目录学及校勘工作之学”的藏曲家。此二派实际上都是将胡适等人提倡的“整理国故”的方法施之于戏曲。其“文献”整理的范围除王国维、吴梅曾经瞩目的元曲杂剧、明清传奇等以“文人”为主体的戏曲文献外(其存在形式多是刊本),也包括艺人手钞本、曲谱、身段谱、脸谱、戏衣等与戏曲“艺人”关系更为密切的民间文献(其存在形式多为钞本)。其“文献”整理的方法除了传统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之外,亦“深合于现代之科学方法”。傅芸子指出,“此二派之研究方法虽略有不同(治校勘者亦有兼为整理之工作者),然其共同之目标,胥皆注重保存关于戏曲之文献与图样”。所以,傅芸子所谓“整理派”和“校勘派”可以统称为“文献整理派”。
但值得指出的另一类研究是赵景深、孙楷第、傅惜华、钱南扬、谭正璧等先生为代表的“通俗文艺”的观念和研究方法。上述学者皆经历过“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他们是带着“新文学”的观念进入到戏曲研究的,戏曲之外的小说、弹词、子弟书、宝卷、俗曲等“通俗文艺”皆同时是他们的研究对象,并且对这些俗文艺皆有精深的研究。如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最具代表性,其他如傅惜华的《三国故事与元明清三代之杂剧》(《中国文艺》创刊号、第一卷第二期,1939)、赵景深的《小说戏曲丛考》(世界书局,1939)、孙楷第的《近代戏曲原出宋傀儡戏影戏考》(《辅仁学志》第十一卷第一、二期,1942)等,都是在戏曲与其他通俗文艺的比较、联系中才能产生的,在戏曲文本故事源流的考证或故事主旨的解读方面也较一般单纯的戏曲研究更为通达、切理。这种思维观念和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吴梅一辈的学者较少留意和使用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浓厚的研究风气的形成,使得一大批诚实、认真的学者专心致力于中国传统戏剧的研究。研究者们以其各不相同的学术选择和研究方法,共同促成了20世纪前期中国戏剧学的合理建构。虽然20世纪后半叶的研究较之前50年仍有较大变化,在某些研究领域也有较大的提高,但若没有前期众多学者的苦心经营作为根基,后半叶研究成果的取得将是无法想象的。直到今日,在有些研究领域,30年代和40年代的研究成果仍然代表了最高的研究水准,后来者的研究仍需在充分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才能“接着说”。
标签:戏剧论文; 梅兰芳论文; 王国维论文; 中国戏剧论文; 燕京学报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论文; 新文化运动论文; 宋元戏曲史论文; 齐如山论文; 商务印书馆论文; 元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