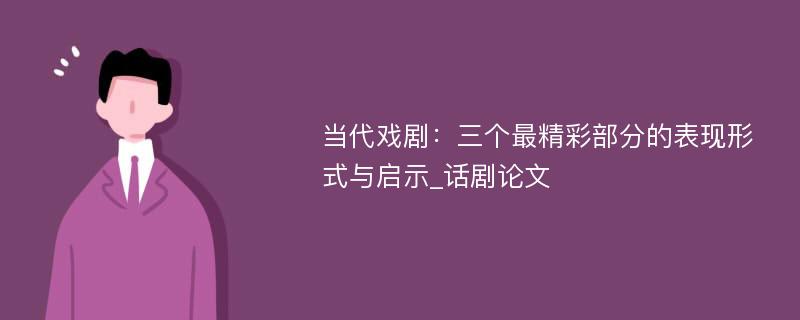
当代话剧:三次高潮的表现形态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剧论文,形态论文,启示论文,高潮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当代话剧虽然历尽风雨,也曾面临困境,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在不断发展的,其成就不容低估。特别是在它的自身发展的历程中,还迎来了令人难忘的三次高潮,这是中国当代话剧工作者的光荣,它不仅为新中国的文学艺术赢得了声誉,而且还为下个世纪的话剧发展提供了亟待总结的宝贵经验。分析当代话剧高潮的特点,研究形成高潮的内、外部原因,深入比较几次高潮表现形态的异同,将对总结半个世纪以来话剧创作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发现影响、制约当代话剧繁荣的客观规律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当代话剧的第一次高潮指的是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我国剧坛上出现的一股勇于突破、锐意创新的创作热潮。建国初期,我们国家虽然也曾有过一些过火的批判运动,但总的来说,政治生活还比较正常、艺术民主也能得到尊重,因而话剧创作也获得健康的发展。不仅老作家,象老舍、曹禺、夏衍等人创作了好剧本,而且还有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满腔的热情为建国初期的剧坛奉献自己的佳作,使得建国初期的话剧一开始就呈现出清新、刚健、蓬勃向上的态势。特别是到了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方针,鼓励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科学研究中的自由竞赛,鼓励文艺创作和个人的才能和特长,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双百”方针的提出,是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的新贡献。它不仅从理论上为社会主义文艺和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还给当代文艺创作带来蓬勃发展的景象。广大剧作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他们在继续讴歌美好光明的同时,还把目光投向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写出了直面现实、干预生活,真实、深刻地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作品。象海默的《洞箫横吹》、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段承滨的《被遗忘了的事情》等等。这些剧本从不同侧面揭露、鞭挞了阻碍社会前进的消极现象,触及到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阴暗的东西,尤其是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恶习进行了讽刺与批判,因而在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晌。此外,也还出现了一批注重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细致描绘人物丰富感情,反映家庭生活、爱情题材的剧本,如岳野的《同甘共苦》、鲁彦周的《归来》、赵寻的《还乡记》、《人约黄昏后》等。这些剧本同以往概念化的作品不同,它们突出强调的是写人,“有意识地注意了我们时代的人的多方面的生活”,不仅尽可能地保存人物生动的原貌,从人物对生活的总体态度中显示他们性格的优缺点,而且还力图掘进人物情感和灵魂的深处,在描写人物心理感情的复杂性、多面性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和探索,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再有,老舍的代表作《茶馆》也出现在这次高潮中,这部剧本“时代气息浓,生活气息浓,民族色彩浓”,不仅是作家最成功的作品,而且也是建国以来具有国际影响的优秀剧作之一。此外,这时期的戏剧创作除了现实主义精神得到进一步发展,作品的真实性与深刻性有了明显的加强,作品的题材范围更加丰富、扩大之外,戏剧的风格和样式也开始受到了重视,过去很少有人问津的讽刺剧、轻喜剧等也有了发展。最后,还应提到:一是全国规模的话剧观摩演出大会1956年3月第一次在北京举行。41个剧团,演出了49 个剧目,其中25个多幕剧和12个独幕剧获得了中央文化部的奖励。这一被称为“我国话剧运动空前盛举”的演出活动,不仅是对建国初期话剧成就的总检阅,而且还是当代话剧蓬勃发展,迎来高潮的重要标志。二是这时期围绕“第四种剧本”(指《同甘共苦》、《布谷鸟又叫了》、《洞箫横吹》等剧作)所展开的争鸣与讨论,客观上也推动了话剧事业的繁荣。它不仅引导剧作家、理论家对戏剧内部与外部规律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且还唤起了广大读者与观众的参与意识,培养了他们的文艺鉴赏水平,提高了他们对话剧艺术的爱好与兴趣。
中国当代话剧创作的第二次高潮是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与第一次高潮相比,这一次高潮形成的背景比较复杂。一方面,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越来越严重的“左”的偏差,这就导致戏剧创作中粗制滥造、粉饰生活、违背艺术规律的现象开始泛滥;另一方面,“双百”方针在贯彻中虽然屡受阻挠,但它毕竟深得人心。六十年代初,党中央发现文艺界存在“左”的错误,并及时地提出了全面调整的重要措施,象周总理“新侨会议讲话”、“文艺八条”的制定,以及“广州会议”,“大连会议”的召开……都对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起了促进与保障的作用。因而这一时期的话剧虽然也受到挫折、走过弯路,但还是迎来了当代话剧的第二次高潮。其主要标志:一是古代历史题材和民主革命斗争题材的剧作大面积丰收;二是反映阶级斗争的剧作大量涌现。
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以及从这时候起对一批作家、作品错误的批判,都给话剧创作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致使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传统受到严重损害,而歪曲现实、脱离人民的创作倾向因受到支持、鼓励而抬头。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不少作家或由于自己对戏剧艺术的迷恋与执着;或为了避开对当时现实问题的直接回答,于是纷纷转向古代和现代历史去寻找戏剧创作的素材,一时间竟出现了历史题材和民主革命斗争题材剧作大面积丰收的局面。象田汉的《关汉卿》、《文成公主》,郭沫若的《蔡文姬》、《武则天》,老舍的《义和团》,丁西林的《孟丽君》,曹禺等人的《胆剑篇》,朱祖贻等的《甲午海战》以及《红色风暴》、《东进序曲》、《杜鹃山》、《七月流火》、《豹子湾的战斗》……都堪称当代话剧的精品,至今乃葆有旺盛的艺术生命力。这些作品,有的生动地再现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有的热情地颂扬了古人勤劳、勇敢、正直、清廉、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的高尚品质,有的则记录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与国内外反动派浴血奋战的动人业绩,有的则赞美共产党人为创建新中国所作出的巨大的牺牲,不仅在国内深受欢迎,而且在国外也享有盛誉。
当代话剧第二次高潮的再一个标志,则是反映阶级斗争题材的剧作的大量涌现。从1957年“反右”开始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整个中国掀起了一场狠抓阶级斗争的政治风暴。这场风暴冲击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自上而下地强调文艺要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致使在文艺作品里反映阶级斗争成了作家普遍追求的目标与检验世界观是否得以改造的标志。至于读者与观众方面,由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强大的宣传攻势影响下,不知不觉的对这些阶级斗争的理论客观上采取了认同的态度,甚至还以此作为衡量日常是非、评判作品优劣的标准。再加上这时期的作家总结了五十年代戏剧创作的经验和教训,在艺术提炼上有了明显的长进,都促成了这些反映阶级斗争剧作的大量问世,并受到欢迎。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刘川的《第二个春天》、沈西蒙执笔的《霓虹灯下的哨兵》、赵寰的《南海长城》、丛深的《千万不要忘记》、陈耘的《年青的一代》,此外象《丰收之后》、《青松岭》、《龙江颂》、《小足球队》等等也都产生热烈的反响。这些剧作的发表与演出在当年都曾轰动一时。可以这样说,当代话剧第二次高潮的形成多少也与这些剧作的推动分不开。如今,以科学的态度来评判这些当年倍受称道的剧本显然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在复杂的背景下产生的特殊现象,当然更需要一分为二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些反映阶级斗争的剧作,当年数量多、影响大,但大部分由于先天的不足与自身的局限,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已经被人淡忘;不过其中也有一部分,象以上列举的几位作家的作品,虽然也能从中挑出毛病,但它们或是确从现实生活出发、或是在艺术上有着独到的地方,属于瑕不掩瑜,至今仍有不可否认的价值。就以《霓虹灯下的哨兵》为例,剧中所反映的广阔的生活场景,所采用的新颖的艺术构思、所塑造的鲜明的人物形象、所体现的独特的艺术风格,至今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特别是连长鲁大成、班长赵大大以及温柔贤良、朴实大方的春妮……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过平心而论,这一特殊戏剧现象的价值主要不在于作品的自身,而在于客观上所起的特殊作用。它们对唤起广大群众对话剧事业的热情,吸引更多观众步入剧院,形成六十年代初的“话剧热”,多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功绩不可抹杀。
当代话剧的第三次高潮是出现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新时期,更确切地说是出现在1979年前后。1976年10 月, 中国人民终于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政治动乱,迎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正如有的同志指出的那样:“新时期的帷幕刚刚掀开,话剧创作就以感应生活的敏捷和反映社会的深邃而引人瞩目。它同诗歌、短篇小说一起,构成了文学复兴最初阶段的‘三足鼎立’之势。”的确,粉碎“四人帮”后短短几年,话剧创作就出现蓬勃发展的繁荣局面,不论是作品的数量、质量,还是思想性、艺术性都达到崭新的高度。老一代剧作家象曹禺、陈白尘、吴祖光、杜宣等焕发青春,重又提笔;广大中年作者象崔德志、丁一三、赵寰、所云平、白桦、王正、漠雁等以更多优秀的剧本装点新时期的戏剧舞台;更可喜的是一大批崭露头角的剧坛新秀,象苏叔阳、沙叶新、李龙云、宗福先、马中骏、贾鸿源以及赵梓雄、中杰英、邵冲飞、赵国庆、邢益勋、梁秉堃……带着时代的锐气登上剧坛,为中国话剧增添了光彩。可以说以《枫叶红了的时候》为开端,以《丹心谱》与《西安事变》为标志,新时期的话剧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不仅恢复了被“四人帮”破坏了的现实主义的传统,恢复了它们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和声誉,而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的1979年,中国剧坛更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令人鼓舞的蓬勃发展势头。话剧创作不论在主题、题材的开拓,人物形象的创新或是艺术手法的探索等方面,都较过去有了明显的飞跃。
这时期的话剧创作,除了象《丹心谱》(苏叔阳)、《于无声处》(宗福先)、《有这样一个小院》(李龙云)、《报童》(邵冲飞等)、《西安事变》(程士荣等)、《陈毅出山》(丁一三)、《秋收霹雳》(赵寰)、《陈毅市长》(沙叶新)等一批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以及《王昭君》(曹禺)、《大风歌》(陈白尘)等反映历史题材的剧作倍受称赞外,“社会问题剧”的大量涌现则构成了当代话剧第三次高潮的重要特点。这些剧作如《报春花》(崔德志)、《未来在召唤》(赵梓雄)、《权与法》(邢益勋)、《救救她》(赵国庆)以及《灰色王国的黎明》、《谁是强者》,《炮兵司令的儿子》、《论烟草之有用》等等,有的批判反动的“血统论”对人的禁锢和摧残;有的告诫人们要完成新时期工作重点的转移,必须彻底解放思想,反对因循守旧;有的敢于把笔触伸延到民主与法制这样敏感的领域,歌颂了执法如山的好干部;有的则无情地鞭挞了某些领导者,利用职权、损公肥私的恶劣行径。它们的共同特点则是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提出人们热切关注的重大问题,有的放矢、感情真挚、针砭有力、促人深思。这些“社会问题剧”产生了轰动效应,不仅促进了社会主义戏剧的繁荣,而且还向人们昭示这样一个朴素的真理,那就是直面现实、忠于人民是艺术获得生命的根本保证。
此外,这时期的剧作在人物塑造上也有了新的突破。广大剧作者挣脱了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束缚,冲破了样板化、模式化的僵死套数,尊重生活、尊重艺术规律。正面人物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灵”,反面角色也不再是脸谱化、漫画化的“魔鬼”。作家塑造人物时既写出了他们特有的气质和禀性,同时又不抹煞他们作为生活在人世间普通一员的丰富、复杂的性格特征。特别要提到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在这时期话剧创造作中成功的塑造,即摆脱、摒弃了过去“神化”的作法,而将他们置身于重大的历史冲突和时代矛盾之中,既写出他们伟人的气魄,也表现他们普通人的素质;既展示了他们咤叱风云的业绩,也透露出他们平凡生活的悲欢,给人以真实感与亲切感,这对填补话剧创作的空白、丰富当代文学形象画廊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至于在艺术探索方面,这时期不少剧作家也付出了心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们有的向传统学习,有的向西方借鉴。如苏叔阳、李龙云等作家显然在师承老舍先生的现实主义戏剧创作方面作了努力并取得成效。他们“写北京人、写北京事,写那些生活在北京大小胡同、四合院内平平常常的普通人的思想感情、生活命运……剧本自然流畅、朴实无华但却深刻动人”。此外,象《屋外有热流》、《我为什么死了》、《哦,大森林》、《陈毅市长》等作品,有的构思新颖,有的结构别致,有的表现形式独特,有的则力图推倒“第四堵墙”,追求舞台上下,演员观众情绪的交流与融汇。总之,这一切共同营造了1979年前后中国剧坛多姿多彩的景观,无怪乎戏剧界的朋友至今仍然深切地怀念——“难忘的1979”。
回顾中国当代话剧三次高潮的盛况,我们发现它们之间虽然存在着差异,如第一次高潮的重要特色是题材的“丰富性”与“多样式”;第二次高潮则表现为背景与成果的“复杂性”;第三次高潮是出现在长期禁锢之后,因而具有“爆发性”的特点……但是,它们的共同点仍然不少。我认为其中最突出的,一是创作成就卓著。这是它们之所以被视为“高潮”的根本原因。的确,在中国当代话剧发展史上那些富于艺术魅力的佳作,象《茶馆》、《关汉卿》、《甲午海战》、《红色风暴》、《霓虹灯下的哨兵》、《丹心谱》、《西安事变》、《陈毅出山》、《陈毅市长》等等大多产生于这些时候。二是演出深受欢迎。这些时期优秀剧作的上演往往盛况空前,造成轰动效应,不仅演出前剧场门庭若市,而且演出后剧中不少成功的典型还成为人们日常议论的热门话题。三是持续的时间都不长。考察三次高潮的起落,我们不无遗憾地发觉它们蓬勃发展的时间不过是一两年而已。为什么兴盛的日子竟会如此之短暂?这是应该引起我们关注并深入探讨的问题。因为其间很可能蕴含着至今还没被我们完全认识的繁荣中国话剧的客观规律。
首先,我们要考察促成三次高潮形成的主要原因。在这方面不少理论工作者都曾明确地指出:关键在于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正确,特别是“百花齐放、百家争呜”方针的贯彻执行。的确,深入探究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以及1979年前后中国话剧的三次繁荣就会发觉,这一切首先应归功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引导。象鼓励不同题材、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作品的自由竞争,摒弃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无限上纲上线的极左做法,营造和谐、宽松的创作氛围等等。象1956年作家大胆突破“禁区”,深入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干预生活”,敢于触及现实生活的阴暗面,多侧面地刻划人物内心丰富、复杂的世界;以及1979年前后,反思历史、总结教训,探究“四人帮”赖以生存的气候与土壤,并及时地揭露阻碍“四化”进程的痼疾与陋习……因而收到了震聋发聩的强烈效果。这一切都和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的鼓舞分不开。即便是背景复杂、特殊的第二次高潮,也应该看到还是与“双百”方针的深入人心以及六十年代初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特别是“广州会议”的召开等密不可分。正如人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社会主义救中国,‘双百’方针救文艺”。这是新中国文艺工作者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并从切身的感受中总结出来的一条至理名言。此外,剧作家、演员与读者、观众对话剧艺术的关心与热爱,并为此付出努力也是当代话剧走向繁荣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一般人认为,所谓戏剧则是“由演员扮演角色在舞台上当众表演故事情节的一种艺术”。这个简单的定义不仅回答戏剧是什么,而且还道出了构成戏剧的几个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那就是作家(或称剧本)、演员、观众及剧场。
考察当代话剧的三次高潮,我们深感它与作家、演员的敬业精神、创造性劳动,以及读者、观众对话剧艺术的热心具有密切关系。作家的一度创作、演员的二度创作当然是迎来话剧高潮的基础。实践证明,读者、观众对话剧事业的热爱与支持更是新中国话剧事业繁荣的根本保证。广大群众对话剧演出的迷恋,剧场观众爆满,连演数十场而盛况不衰;剧场内叹息声、笑声以及热情的掌声此起彼伏,话剧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切不仅极大地鼓舞了作家与演员创作的欲望,而且应该说还是社会文明、时代进步、文学艺术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除了以上原因之外,我还感觉到,当代话剧高潮的形成恐怕多少也还与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有关。早在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就曾指出:“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回顾历史,我们不仅看到了三次高潮到来之时,不论是1956年,六十年代初,或是粉碎“四人帮”后的1979年前后,我国的经济建设都获得较为健康、迅速的发展,而且还看到了它们都是处在新中国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转折关口。象1956年,我国在绝大部分地区已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此,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主要任务是“尽快地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也就是说,国家工作的重点将从开展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转移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上来;象六十年代初,党中央及时发现和开始纠正我们经济工作,特别是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扭转了“左”的错误倾向;象粉碎“四人帮”后的1979年前后,更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时期。全国人民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并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很显然,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思想活跃而敏锐,因而对文化艺术的需求也愈发强烈。应该说这也是促成当代话剧繁荣发展、形成高潮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次,我们再进一步探究当代话剧三次高潮转瞬即逝的具体原因。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前两次高潮的跌落是与极左政治及其派生的错误的文艺政策分不开的。1957年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极左思潮的恶性膨胀以及从此开始的对作家、作品无休止的过火批判,都直接导致在“双百”方针鼓舞下开创的戏剧繁荣局面以及在周恩来同志直接关心、指导下党的文艺政策调整所带来的复苏景象遭受极大的打击……这一切都是我们必须牢记的教训。
那么1979年前后第三次高潮跌落,乃至急速地陷入低谷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是很令戏剧界朋友感到困惑的问题。粉碎“四人帮”后,广大文艺工作者总结了当代文学几十年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从思想上、理论上分清了是非、提高了认识。大家充分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开始出现,并逐渐发展起来的“左”的错误对文艺工作曾经造成无法估量的危害,认识到“双百”方针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保证,认识到必须禁止采用政治斗争与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替代文艺问题的争议与讨论,因而新时期剧坛很快便出现了思想活跃、创作繁荣的局面。不少同志由衷地赞叹,这是建国几十年来“双百”方针得到贯彻执行、艺术民主得到尊重、个人才智得到发挥的最佳时期。那么,为什么在这样的时期,在刚刚迎来第三次高潮不久,人们还陶醉在兴奋与遐想中的时刻,当代剧坛竟骤然出现了以读者、观众对话剧冷谈为特征的话剧困境呢?这是一个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问题。
我认为,当代话剧第三次高潮的跌落,即进入八十年代之后,话剧倍受冷落,步入低谷、陷入困境,或称之曰,出现“危机”,其主要原因不在于外部政治环境的干扰,而是在于戏剧界自身(剧作家、剧团、演员及有关领导部门)存在着问题。这问题不是说他们不努力、不勤奋、缺少敬业精神,或艺术功力滑坡……而是指他们对进入八十年代,发生急剧变化的艺术环境、客观世界,缺乏冷静的分析、准确的认识和有效的应对。也就是说戏剧界对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出现的“时代发展,影视冲击,业余生活的丰富以及观众思想的解放,兴趣、爱好的多样,个人艺术选择自主权的失而复得”以及由此产生的话剧观众的大量流失的现象感到疑惑不解与茫然失措。虽然仍有不少执着的探索者苦心孤诣地寻求走出低谷、摆脱困境的出路,他们创作并演出了不少富有创新意义令人耳目一新且评说不一的新潮话剧,但是,大多由于无法做到对症下药,因而收效甚微。其实,戏剧既是高雅的艺术,也是通俗的艺术。如果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恐怕它更应该纳入通俗艺术之列。它的产生、发展、兴旺,乃至萧条、没落都与平民百姓的喜好与支持密切相关,古代希腊、罗马戏剧的兴盛是这样,现代欧洲、北美戏剧的繁荣是这样,中国的古典戏剧、近代的地方戏曲,乃至于现当代话剧的盛衰也是这样。从戏剧的本质特征来说,或从戏剧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我们都可以这样大胆地断言:没有人民大众的支持与参与就没有戏剧生存的土壤。一旦脱离了人民大众,不是考虑他们的爱好、需要与习惯,仅仅凭个人良好的愿望,那么戏剧之花就会枯萎、戏剧之河就会干涸。这可以说是进入八十年代,中国话剧高潮急速跌落的根本原因。
纵观当代话剧三次潮起潮落,我们意识到,要繁荣中国的话剧事业需要的是上下同心、群策群力;既要创造民主的风气、详和的氛围,又要提倡敬业的精神和竞争的意识;既要尊重艺术规律,努力提高创作与演出的品位,又要自始至终不忘群众的爱憎、群众的需要、群众的喜好。如果能够做到这些,那么中国当代话剧的第四次高潮就有望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