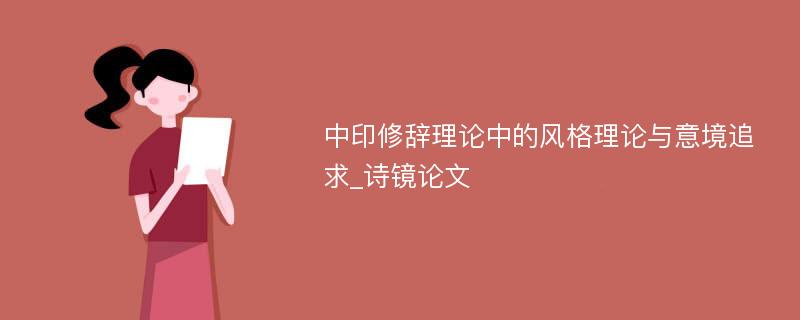
中印修辞论中的风格论和意境追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论文,意境论文,中印论文,风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4;H0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0X(2000)02—0064—07
中国和印度都是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文明古国,都很早出现了有关修辞的理论。在印度诗学史上,庄严(Alankāra, 即修辞)论是以探讨文学语言艺术奥秘为主要内容、首先得到全面发展的诗学理论。 以7世纪的婆摩诃为首,及其后相继出现的檀丁、优婆吒、楼陀罗吒等诗学家,以专著形式着重探讨庄严在诗中的地位,认为庄严是诗美的主要因素,形成了自成体系的诗学派别。中国古代的修辞理论是随着整个古代文艺理论的发展建立起来的,有关修辞的论述大多分散夹杂在众多的经解、文论、史论、诗话、词话、曲话、笔记、随笔之中,以个人经验分析为主,系统总结、阐述不多。古典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因其较全面地论及修辞的理论,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修辞理论的力作;宋代陈骙对古人的修辞经验作了总结,写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修辞学专著《文则》。由于中印两国的文化发展的背景和特点都存在较大差异,其修辞理论也形成了各自的特色。本文对双方涉及的有关风格的理论、对审美意境的追求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较早形成并不断发展的中国古代风格论
有关风格的理论一直是中国古代修辞理论所探讨的重要内容之一。自曹丕写下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开始,就提出了作家语言风格的问题。曹丕在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创作原则,“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章,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认为作家的才能气质先天决定,作家的创作反映个人的气质。在此曹丕突出修辞的个性化特色,他以王粲等“建安七子”的创作为例,分析他们的创作特点,认为各人不同的气质、才能决定了各自擅长的不同文体,决定了各自文章的不同风格,他还概括了不同文体的风格特征:“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在此基础上,西晋陆机在《文赋》中把文体归纳为10类,详细指出它们的风格特点:“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烨而谲诳。”
南朝刘勰在前人启迪下,较系统地提出了作家艺术风格的理论。在《文心雕龙·体性》中,他首先指出一个作家艺术风格的形成,是由长期的才、气、学、习所凝结而成的,“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刘勰认为作品的风格是“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不同作者有不同的风格,他把作品风格归纳为8类: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 新奇、轻靡,并一一对应,分成4组:“雅与奇反,奥与显殊, 繁与约舛,壮与轻乖。”刘勰的风格论的核心在于,他认为作家的风格是由其个性决定的,“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性情。”他对贾谊、司马相如、扬雄、刘向、班固、张衡等十几位作家的风格进行分析,阐述了作家气质个性决定文章言辞,作品风格体现作家性情的观点。刘勰比前人进步之处在于他肯定才气对风格的决定作用,同时也注意到后天学习的重要,他主张少年学习写作要从雅正的作品开始,通过后天的刻苦学习,对8 种风格融会贯通。
刘勰的风格论对后人的影响极大。唐代王昌龄、皎然等对诗的风格都作过分析、概括。皎然《诗式》提出“辨体有一十九字”的说法,把诗的风格概括为:高、逸、贞、忠、节、志、气、情、思、德、诫、闲、达、悲、怨、意、力、静、远等19种。到晚唐,司空图著《二十四诗品》一书,专论诗的风格,把风格的分类增至24种之多,比前人的分类更详细。司空图论诗重在“味”,讲求韵味,提倡“韵外之旨”、“味外之旨”,他从诗的意境、形象、表现方法等方面,把诗的风格分为:雄浑、冲淡、纤秾、沉著、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等24种,其中,他尤其推崇冲淡、自然的风格。但为追求“韵外之致”的最高意境,他认为24种风格都可以达到,所以他对这多种风格都加以赞美,赞成诗歌风格的多样化。在探讨风格与诗人的联系这一问题时,他继承前人的观点,肯定诗人自身的气质才能,同时也强调后天要加强思想、艺术方面的修养。
二、在庄严论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印度风格论
在古代印度诗学史上,对风格问题的探讨存在着一定的意见分歧,对风格的认识也存在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婆罗多早在《舞论》中就谈到戏剧的风格问题,他用梵语”vrtti”一词来阐述, 其本义是活动或活动方式。该词从广义上可理解为人类活动及其活动方式,从狭义上可理解为戏剧表演特色或风格。婆罗多将戏剧风格分为4 种:雄辩、崇高、艳美和刚烈。他认为雄辩风格“以语言为主,由男角而不由女角运用,使用梵语”。他把雄辩风格分为4支:赞誉、序幕、 街道剧和笑剧。他认为崇高风格“具有真性、正理和事件,充满喜悦,抑止悲伤的感情。”他将崇高风格分为挑战、转变、交谈和破裂4支。 他把艳美风格定义为“打扮优美,特别迷人,与妇女有关、含有许多歌舞,各种行动导致爱的享受。”欢情、欢情的迸发、欢情的展露、欢情的隐藏是艳美风格的4个分支。 他给刚烈风格下的定义是:“主要具有刚烈的性质,含有许多欺诈、虚伪和不实之辞,含有跌倒、跳起、跨越、幻术、咒术和各种格斗。”紧凑、失落、发生和冲突是刚烈风格的4 个分支。婆罗多除了给4种风格下定义、分类以外,还对风格与味(rasa )的关系作了规定,他认为“艳美风格用于艳情味和滑稽味,崇高风格用于英勇味、暴戾味和奇异味,刚烈风格用于恐惧味、厌恶味和暴戾味,雄辩风格用于悲悯味和奇异味。”[1](P148)可以说, 婆罗多在这里谈到的戏剧风格是以戏剧表演的语言、妆饰、形体、感情等因素为基础概括而来的。在《舞论》十四章中,婆罗多还提到地方风格(pravrtti),即“不同的地区特有的服装、语言、习俗和职业。”他认为地区很多,但可根据某些突出的共同特征,将地方风格归纳为:南方、阿槃底(西印度)、奥达罗摩揭陀(东印度)、般遮罗(北印度)4种。 比如,南方风格运用艳美风格,具有丰富的舞蹈、歌曲和乐器、表演机灵、甜蜜、妩媚。般遮罗风格主要运用崇高风格和刚烈风格,缺少歌曲,具有武戏的动作和步姿等。婆罗多之后的不少学者,谈到风格,大多以地域为基础,认为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语言谈吐、服饰装束、行为风俗、文化宗教决定着不同的风格,比如,南方Vidarabha 地域的诗风,被称为“维达巴”风格;东方Gauda地域的诗风, 被称为“高德”风格。庄严论者以庄严为诗美的最高因素,仅从语言角度上评论风格。婆摩诃不同意有些智者所认为的“维达巴风格优于高德风格”,他认为区分风格和评判它们的高下是无意义的,“不使用粗俗的语言,有庄严、有意义、正确、连贯,即使是高德风格,也是好诗。否则即使是维达巴风格也不行。”[2](P100)可见, 在婆摩诃的庄严论中几乎没有风格的地位。在《诗庄严论》中婆摩诃也论及诗德(guna),但他仅提到甜蜜、清晰、壮丽3种诗德。 他并没有像后来风格论者那样把诗德看成风格的基础,而只从语言构词方面谈到它们,仅把诗德视为诗庄严的手段之一。
根据现有的资料,最早将诗德视为风格的基础的诗学家是檀丁,一般认为,他既是庄严论的发展者,又是风格论的开创者。在庄严和诗病的观点上,他与婆摩诃是一致的。他也是首先从诗的语言艺术着手进行探索的诗学家,在《诗镜》中,他详细地对庄严进行分类,阐述诗病的一般表现及其特定情况下的转变。但与婆摩诃不同的是,在论说庄严的过程中,他着意区分维达巴和高德两种风格,认为它们有“明显差别”。檀丁用作“风格”一词的梵语原文是māgra,本义是道路,有时又用vartman,本义是方式。他论述了10种诗德:紧密、清晰、同一、 甜蜜、柔和、易解、高尚、壮丽、美好和三味。这里诗德一词主要指诗的语言特色或风格因素。他认为这10种诗德“是维达巴风格的生命,而高德风格中通常显示出与这些诗德相反(或不同)的情况”。[1](P303 )从他给10种诗德下的定义中可以看出,紧密、同一和柔和3 种诗德属于词音范畴。比如,他认为“紧密是不松弛”,而松弛是指诗句中大量使用不送气音;“同一”是指“词音组合前后一贯”(梵语词音分柔音、刚音、中音3类);“柔和”是指“大量使用柔音”。 “甜蜜”指“语言和内容有味”,这一诗德兼有词音和词义要求。其他6 种诗德属于词义范畴。可见,檀丁提出的风格是诗的语言风格,由音和义两方面特征构成。檀丁在《诗镜》中重点讲述庄严,在教导学诗者如何使用庄严的过程中提出诗德,而有时也将诗德纳入庄严范畴。所以,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风格论是在庄严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到了8世纪下半叶,诗学家伐摩那继承檀丁的观点, 在《诗庄严经》中完成了风格论体系。他认为:“诗是经过诗德和庄严修饰的音和义。”他在肯定庄严的同时,把诗德与庄严区分开来。继而他提出“风格是诗的灵魂”。他的“风格”用的是梵语“rīti”一词, 本义指方式或式样,此后,“rīti”成为梵语诗学中指称“风格”的通用词。 伐摩那把“风格”定义为“词的特殊组合。这种特殊性是诗德的灵魂。”他把风格分为:维达巴、高德和般遮罗。他认为:“维达巴风格具有甜蜜和柔和两种诗德。”他强调:“诗立足于这3种风格, 正如画立足于线条。”他与檀丁一样,提出10种诗德。为更明显体现音和义两方面特征,他又将每种诗德分成音德和义德,合共20种诗德。他明确指出“诗德构成诗美的成分,庄严是加强诗美的因素”,“前者是永恒的”。虽然伐摩那在《诗庄严经》中肯定庄严,论述庄严分类,也论诗病问题,但已明确地将风格论从庄严论范畴中分离出来,建立了完整的风格论体系。他甚至以风格作为标准品评诗的优劣,认为3种风格中, 以维达巴风格最优秀。尽管其后的诗学家并不完全赞同他的观点,有的仍坚持庄严论,有的持味论、韵论、曲语论等观点,但都开始承认风格这个批评范畴,并对其风格论进行改造,以纳入自己的诗学体系。后来的学者,有的不同意按地区命名风格。比如10世纪的曲语论者恭多迦将风格分为自然、雕琢和适中3 种,并将它们与诗人的才能、素养和实践相联系。但大部分学者仍采用按地区命名风格的传统,随着方言文学的发展变迁,风格的种类也有所增加。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中印风格论的发展及其内容都有所不同。古印度的风格论是在庄严论的基础上发展成独立的诗学体系;而中国古代的风格论一直是修辞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风格论主要关注作家个性化创作问题,认为不同的风格取决于不同作家的气质、才华、后天的学习、熏陶;对地域引起的风格差异关注较少。而古印度风格论更注重地方的风俗习惯、语言特色等因素对风格的影响。
三、中国古代修辞论追求自然含蓄的审美意境
中国古代修辞理论的总原则是“辞以意为主”,[3] 即适应题旨情境是修辞的第一要义。古代诗学家普遍赞同创作过程中,语言只是第二位的。它以传情达意为目的。尽管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传统诗学观点主张文质并重,但文、质的地位并非是等量齐观的,“质”始终是第一位的,所以古人有“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等有关文学本质的论述。“诗言志”在先秦是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尚书·尧典》已提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古人评论《诗经》认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4]到魏晋六朝,玄学兴起, 文学创作重视表现作家个性,抒发内心悲欢离合之情。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主张,“缘情说”一度替代“言志说”而占统治地位。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努力将“缘情”与“言志”理论统一起来,指出:“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认为文学表现感情,亦表现思想。所以他认为“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即写文章要先确定内容,然后才能产生通畅的文辞。既然以情志为主,当然对文饰的追求就是自然朴素,而非华丽了。孔子主张“辞达”、“辞巧”,注重语言通达,藻饰应恰如其分,言辞巧妙贴切。而提倡语言文辞的自然本色,做到发如自然,也是中国传统道家学派的观点。老子说“希言自然”,庄子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5]道家追求天道自然、 素朴至美的美学思想对古代修辞理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古代诗文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普遍认同以自然含蓄的语言追求深长悠远的意境的审美观。
两汉时期,《淮南子》主张质文兼备,以质为主,所谓“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质有余也”,提出言辞应该朴素,不尚虚饰,即有“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矣”。王充主张文章的内容与形式要统一,“疾虚妄”,“反艺增”。他在《语增》、《儒增》、《艺增》3 篇论文中,对夸张采取不赞成的态度,强调文学作品的真实性。魏晋时期出现“言意之辨”、“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说都对后来诗歌创作、修辞理论中发展起来的追求言外之意、诗外之味的审美倾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无论论史的修辞还是论诗的修辞都主张朴素自然。刘知几在《史通》中认为史书的写作应崇尚典实质朴,反对华丽浮靡。他提出“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他反对在史书中运用俪辞、夸张。王昌龄论诗,主张词语要自然清新,提出“不难”、“不辛苦”的观点,反对词语刻意雕琢,提倡创作中绝无“斤斧之痕”,要有自然之美,天然浑成。他在《诗格》中还提出“三境”:“物境”、“情境”、“意境”。他认为“物境”写山水,“得其形似”;“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他要求诗人以真情实感,自然地表达情、景,才能得到读者共鸣。李白提倡“清真”诗风,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主张清新自然的诗歌风格。白居易和元稹共同提倡新乐府运动,白居易提出“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指出语言要“质而径”、“直而切”,[6](P52)即要求语言质朴真实、通俗易懂。皎然论诗的修辞,提出“至丽而自然”之说,在讲求自然美的同时,与工丽文采相结合。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非常推崇冲淡、自然的风格,提倡“韵外之旨”,追求超然物外,“近而不浮、远而不尽”,意在言外的境界。所以他论述“含蓄”风格之时,提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准则,要求语言文字含而不露,曲折委婉,言尽意未尽,在字里行间蕴藏作家丰富的思想感情,使读者通过联想,去捕捉领会其中的深意和韵味。
宋代,欧阳修等诗文大家继承、发扬唐代诗文家的观点,注重语言的意蕴深长。欧阳修赞扬杜甫锤炼文字的高超艺术,认为创作应反复推敲,提出写景抒情要“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7]的观点。在散文方面,他继承韩愈的平易风格, 提倡“平淡典要”,反对华而不实。陈骙在《文则》中赞扬“古人之文,发于自然,其协也亦自然”,指出文章要辞意相协,“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文章就可以做到贴切、自然、和谐了。另外,金元时期的文学家,如王若虚、陈绎曾都强调语言文字表达要浑然天成,自然,得当,反对有意雕琢、追求生怪。
明清时期,是文学流派、思潮争论的时期,也是古代修辞理论的总结时期,大多数学者仍然秉承古人追求自然的修辞传统。比如,李贽强调“以自然之为美”;谢榛主张“反朴复拙”,赞扬“盛唐人突然而起,以韵为主,意到辞工,不假雕饰;或命意得句,以韵发端,浑成无迹”。[8]顾炎武继承孔子所倡导的“辞达”原则, 认为文章要出乎自然,“自然”就是“达”。
四、印度庄严论注重惊奇的审美效应
与中国古代修辞论所追求自然含蓄的审美意境不同,古印度庄严论者从“庄严是诗美的主要因素”的核心思想出发,认为经过装饰的词音和词义的结合即是诗。在古印度早期的诗学家心目中,语言的地位是崇高的。有无庄严是区分一般语言和诗的语言的根本所在。庄严论者认为,庄严具有产生诗美的永恒的本质,庄严即是美。
婆摩诃在《诗庄严论》中指出“理想的语言庄严是音和义的曲折表达”。古印度诗学家普遍承认庄严是言语所具有的惊奇。庄严论者认为言语的惊奇是诗的必然因素,每一个言语的惊奇都是诗。庄严不仅是外在的,而且是内在的。惊奇具有奇特性,能唤起人们的好奇心理,感化、震撼人们的心灵。尽管味论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单纯的言语惊奇不是诗,庄严只是言语外在形式的惊奇,与情、味相结合的才是诗,但庄严论者坚持凡具有惊奇效应的作品即具有审美效应,言语的惊奇本身即存有奇异味,惊奇即是美。惊奇即是庄严论者所追求的审美境界。
檀丁在《诗镜》中认为夸张是“其他一切庄严的根基”。婆摩诃给夸张下的定义是“超越日常经验”,檀丁认为夸张是“超越日常限度”。显然,夸张这种庄严表现出言语惊奇的本质,即非凡性,超越世俗的可能。在宗教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古印度,以抒发宗教感情为主的古印度诗人在创作中,运用夸张等手法表现对未知、神秘力量的崇拜,对神明的歌颂,体现神的非凡能力,引起读者的惊奇,得到共鸣。古印度诗人甚至把对神的虔信和男女爱情合为一谈,许多情诗是由歌颂大神毗湿奴的化身牧童黑天和牧女的爱情故事衍生出来的。古典梵语诗歌,还有不少早期民间流行的俗语情诗,都“追求形式,又着重‘艳情’,而以宗教感情作解释。”[9]除了庄严论者认为夸张辞格十分重要之外, 其他诗学家也有相似的观点。欢增在《韵光》中说:“唯独仰仗诗人的天才而具备夸张性的庄严,才富有魅力。”“夸张寓于一切庄严之中,与一切庄严同一,成为一切庄严的表征。”新护在《韵光注》中说:“夸张是一切庄严的共性。”夸张辞格是典型的曲折表达方式,婆摩诃更强调:“诗人应该努力通过这种、那种乃至一切曲语显示意义,没有曲语,哪有庄严?”[2](P112 )他们都认为与日常语言不同的艺术表达方式是一切修辞的本质和魅力所在。
后来韵论得到创建和发展,诗学家们注意到语言的暗示功能,把能展示暗含义的词音和词义称作韵,并认为“韵是诗的灵魂”。欢增重视味的暗示性,并从暗示的角度分析庄严和风格,确认它们是韵和味的辅助因素。此后,追求词义的暗示性,追求词音的暗示性,追求整个诗篇的暗示性,即追求韵,成为许多诗人创作所追求的审美境界。
从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到:中印古代修辞论所追求的审美意境是有很大差别的。在“辞以意为主”的修辞总原则之下,中国古代修辞讲求表达含蓄委婉,选词造句自然天成,意蕴深长而又不刻意雕饰,抒发真挚朴实的情感,令读者在字里行间领会“诗外之味”,产生共鸣。而古印度的庄严论却认为庄严是诗的魅力所在,庄严的运用使语言产生惊奇,读者体会到惊奇带来的奇特性和非凡性,从中得到审美快感。庄严论者不厌其烦地对庄严进行详细的分类和论述,努力使学诗者掌握这些技巧,以便成为诗人,这本身就表明古印度庄严论对语言装饰产生的艺术美的追求。从对夸张辞格的态度,也可见两种修辞论审美观差异之一斑。
收稿日期:1999—11—22
标签:诗镜论文; 语言风格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论文; 反复修辞论文; 意境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古印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