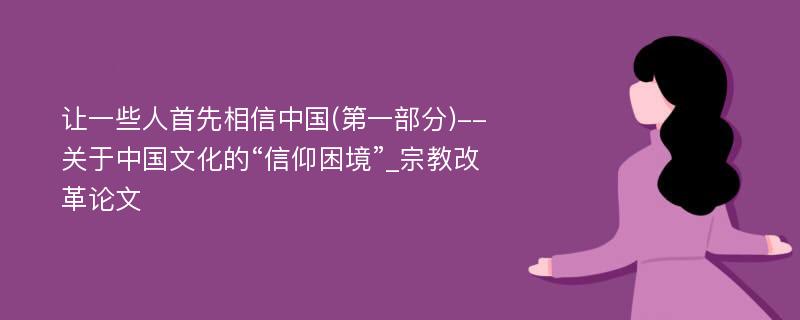
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上篇)——关于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局论文,中国文化论文,中国论文,上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看到昨天,我知道明天 ——埃及卢克索神庙法老像上的铭文 在中国,长期以来,一个曾经极为响亮的口号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作为一种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也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在社会转折的大幕即将拉开之际,“让一部分人”先“什么”起来,无疑永远是一个最为根本也极为重大的战略选择。而且,选择“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确实把我们国家与民族在30多年中所孜孜以求的核心价值和盘托出。没有人会否认,“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战略选择,曾经凝聚了所有国人的目光与期待,何况,在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这一战略选择也确实曾经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但是,在30多年后的今天,也已经没有人会否认,伴随着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深入拓展,作为一种战略选择,“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已经不足以成为能够使国人再次集结起来并且再次出发的价值选择与动力选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在中国,应该让一部分人先“什么”起来?又一次成为一个横亘在国人面前而且亟待回答的严峻问题。 就笔者而言,从世纪之初开始,就一直在呼吁“信仰启蒙”,也一直在呼吁应该“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随着思考的逐步深入,笔者日益坚信:中国人离信仰有多远,离现代化就有多远,离现代世界也就有多远。因此,“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应该成为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当今中国的不二选择。 下面,就来谈谈自己的具体思考与想法。 一、“先基督教起来”与西方现代社会的崛起 让一部分人先“什么”起来,涉及的是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 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古人还说,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要回答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问题,最为简洁同时也最为有效的,无异于直接去看一看我们所面对的当今世界的“前世今生”。 在这方面,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思考给我们以重大启迪,他说,研究历史,最好的方法是分成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长时段”,在思考所面对的全部世界的“前世今生”的时候,显然应该是我们透过世事与国情的是是非非,去洞察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前世与今生的重要参照。例如,以300年为一个周期、以500年为一个周期,由此,我们立即就会发现,有些国家的命运其实在300年前、500年前的“前世”中就已经注定了终将衰败,而有些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已经注定了终将崛起。 几百年来的全部世界,动荡和变局非常频繁。大清帝国的GDP一度领先于全世界,可是,后来却一蹶不振;俄罗斯帝国曾经不可一世,最终难逃覆灭命运;横空出世的前苏联,曾经昙花一现,现在却灰飞烟灭;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帝国,曾经雄霸欧亚非,可是,现在却踪迹全无;英国更加神奇,曾经在几个世纪中跃居世界之巅,成为日不落帝国,但现在已经气息奄奄;至于美国,后排末座的身份,也并未影响它在百年中后来居上,至今仍旧是全世界的带头大哥;德国与日本也令人困惑,曾经崛起,但是后来却悍然发动战争,挑衅全世界的人性底线(在战败之后,竟然仍旧能够转而变身成为经济大国,更是一大奇观);当然,最令人痛心的当属亚非的那些前殖民地国家,它们左冲右突,但是,到现在还大多没有走出贫困的泥沼。 那么,在一幕幕兴衰沉浮的背后,一定存在着什么规律?冥冥之中,应该存在着一只有条不紊地把神秘“天意”分配给各个国家与民族的“看不见的手”?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曾经把这兴衰沉浮都泛泛归因于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民主政治”或者“市场经济”,然而,现在回头来看,显然并非如此。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崛起与衰落无疑与“民主政治”或者“市场经济”有关,但是,仅仅归因于“民主政治”或者“市场经济”却又远远不够。无疑,在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或者“市场经济”的背后,一定还存在着一个首先要先“什么”起来的东西,而且,也正是这个先“什么”起来的东西,才导致了一个国家的终将崛起或者终将衰落。 具体来说,在历史学界,一般都将公元1500年作为一个极为值得关注的世界节点。西方最著名的历史教科书——《全球通史》分为上篇和下篇,上篇是“公元1500年以前”,下篇则是“公元1500年以后”。还有一本书,是美国人写的《大国的兴衰》,也是如此划分:“公元1500年前”和“公元1500年以后”。看来,公元1500年,应该是一个最佳的长时段,一个洞察我们所面对的全部世界的“前世今生”的时间节点。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就以公元1500年为一个参照的“长时段”,来回顾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所走过的历程。 首先,公元1500年以后,到1900年为止,几百年的时间,世界上公认,一共出现了15个发达国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15个发达国家完全都是欧洲人口。当然,其中有2个国家,它们的地理位置并不在欧洲,这就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但是,它们却同样都是欧洲人口。因此,必须承认,在最近的500年里,现代化的奇迹主要都是欧洲国家创造的——也都暂时基本与亚非国家无关。 其次,公元1500年以后,西方国家开始全面赶超中国。我们看到,到1830年,欧洲的GDP全面赶超中国,1865年,英国一国的GDP也赶超了中国,到了1900年,美国不仅仅赶超了中国,而且赶超了英国。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倘若因此而将现代化与欧洲等同起来,将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与欧洲等同起来,那无疑会铸下大错,并且会混淆我们即将讨论的问题的实质。事实上,在公元1500年以后,西方世界的崛起并不能仅仅大而化之地界定为全部欧洲。回顾西方的现代化历程,不难发现,从公元1500年以后,整个的欧洲不仅仅是开始了大步奔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自身也还在大步奔跑中不断加以筛选、淘汰。我们看到,欧洲在奔跑中很快就首先甩掉了信奉东正教的国家,然后又甩掉了天主教的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都相继后继乏力,不得不从“发达国家”的行列中被淘汰出局。因此,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最终真正跑进现代化第一阵容的,恰恰全都是“先基督教起来”的国家,都是基督教(新教,下同)国家。以我们所熟知的第一批现代化8国为例,除了法国、比利时两国属于天主教与新教混淆外,其余6国,就全都是基督教国家。 再如英国,在它刚刚崛起的时候,只有1000万人口,可是,它所带来的正能量,却实在不容小觑。本来,葡萄牙、西班牙都跑在英国前面,英国要晚100多年。然而,伴随着英国的宗教改革(安立甘宗、圣公会;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英国“在宗教上,是清教徒主义”)。伴随着新教在英国的日益崛起,它很快就大步追赶了上去(历史学家说:是加尔文宗信徒创造了英格兰)。公元1500年的时候,三个国家的人均GDP还相差不多,可是到了1870年的时候,英国的人均GDP却已经是西班牙的2.3倍,是葡萄牙的3.2倍,到了今天,葡萄牙和西班牙更已经不值一提。那么,原因何在呢?答案无可置疑,也无可挑剔:英国是“好风凭借力”,借助宗教改革和新教的拓展,是“先基督教起来”的国家,而葡萄牙、西班牙却是天主教国家,是没有“先基督教起来”的国家,因此,前者才从殿后变为领先,直至彼此不可同日而语;后者却从领先变为殿后,直至掉队落后。 再如北美。同在美洲,但是北美与南美却截然不同。它们都是欧洲背景,现在北美已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可南美却仍旧停滞于落后的境遇,仍旧还是发展中国家。原因何在?为什么南美和北美会差那么大?为什么南美、北美都是殖民地,但结果完全不同?南美为什么始终萎靡不振?而北美为什么一直高歌猛进?原来,长期治理南美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天主教国家,而长期统治北美的英国却是基督教国家。是否“先基督教起来”,在发展中是否曾经被基督教的手触摸过,于是就成为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异之所在。① 由此我们看到,在西方社会的崛起的背后应该确乎存在着规律,在冥冥之中也还确乎存在一只有条不紊地把天意分配给各个国家与民族的“看不见的手”,这就是:基督教。② 换言之,西方社会崛起的共同特征就在于:这些国家与民族往往都是“先基督教起来”的国家与民族。 遗憾的是,至今为止,我们在谈及西方的现代化的时候,往往仍旧笼而统之地以欧洲来代替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而没有考虑到是否已经“先基督教起来”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结果,本来是应该向真正的西方——欧洲的英国乃至它的第二代——北美的美国学习,可是却无端遗憾地变成了转而去向并非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的欧洲学习,例如向法国或者俄罗斯学习。然而,这“西方”并非那“西方”,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并非地理意义上的西方,也并非地理学意义上的欧洲。我们的学习屡屡以“付学费”而宣告结束,屡屡以水土不服而告终,应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事实上,我们所说的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只是地域上很小的三个国家,荷兰(革新教、自由新教和路德教等新教派别)、英国、美国。荷兰、英国是第一代的西方,第二代的西方实际上就是在英国影响之下的美国。而在它们背后支撑着的,都是基督教。至于其他的欧洲国家则不同了,例如法国,例如意大利,甚至俄罗斯。在它们背后支撑着的,都不是基督教(法国稍微复杂一些),因此也就都没有进入现代化的第一阵容。③显然,并不是任何欧洲国家都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先驱,而仅仅是与基督教直接相关的国家才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先驱。换言之,并不是欧洲的任何宗教都成为现代化的绝大推动力量。不论基督教,还是天主教,抑或东正教,无疑都是与人生与人类有益的,但是,能够强力推进现代化的,却往往是也首先是基督教。 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所谓的西方,其实就是客观化、世俗化了的基督教地域。所谓“西方”,在本质上也就是基督教的西方。④ 遗憾的是,因为在很长时间内都不甚了解世界历史的真正奥秘,中国人往往言必称希腊、罗马,但是却绝少提及希伯来;言必称雅典,但是却绝少提及耶路撒冷。同样,也喜欢言必称欧洲南部的文艺复兴,但是却绝少提及欧洲北部的宗教改革。然而,真实的情况却往往令我们大跌眼镜!例如,希腊、罗马对于“人是谁”的追问根本无法与希伯来对于“我是谁”的追问相提并论。再如,实际上欧洲南部的文艺复兴(拉丁文化)在历史上的作用远不能与北部的宗教改革(日耳曼文化)相提并论。真正引领全世界的改革的,也是北欧的宗教改革——新教改革,而不是南部欧洲的文艺复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欧洲的“北富南贫”,恰恰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同样,历史的铁律就是这样无情!“先基督教起来”的英国的鼎盛时期,号称“日不落帝国”,在西方影响了美国,⑤在东方影响了日本。后来的所谓“亚洲四小龙”,也或者是接受英美的影响,或者是接受日本的辐射,总之,都是跟“先基督教起来”有关。⑥可见,真正影响了世界的,也是“先基督教起来”的国家。 因此,只有“先基督教起来”的西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至于欧陆其他国家,则因为普遍没有“先基督教起来”,而只是先“个人主义”起来,所以也就至今为止都一直没有能够领先于历史的潮头。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神本主义现代化、法国人的人本主义现代化与斯拉夫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例如,法国面积是英国的两倍,还曾经诞生过血腥的“法国大革命”,但是法国在历史上的影响力从来就没有超过英国,⑦原因何在?无疑就与法国走的是无神论加个人主义的道路,而不是有神论加个人主义的道路,因此也就与没有能够“先基督教起来”密切相关。⑧ 二、为什么一定是基督教? 当然,认识到西方社会的崛起都与“先基督教起来”直接相关,还仅仅只是思考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的开始。 事实上,不仅仅是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还有伊斯兰教、佛教、儒教,在漫长的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也都与人类社会的进步成正相关,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那么,在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上,为什么一定是基督教?显然,在揭示了历史发生之“所然”之后,还必须揭示其逻辑发生之“所以然”,前者是事实判断,后者却是价值判断。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再从西方社会的崛起说起。 关于西方社会的崛起,学术界的研究很多,但看法不一。例如,区别于“军事性社会”的“产业社会”(斯宾塞);区别于“机械性联结的社会”的“有机性联结的社会”(涂尔干);区别于“共同体社会”的“利益性社会”(威尼斯);区别于“巫昧之园”的“合理化进程中的社会”(韦伯)等。当然,在这当中,被普遍赞同的,是韦伯的看法。而且,“合理化”,诸如“价值合理化”、“目的合理化”、“形式合理化”、“实质合理化”之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现代化、法国的现代化、德国的现代化、俄罗斯的现代化、意大利和波兰的现代化、日本和韩国的现代化、印度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与英美的现代化之间,也都存在着程度多寡与高低的不同。英美的现代化,更是以其“合理化”程度的最为彻底、最为全面、最为深刻而独占鳌头。 更多的学者则认定西方社会崛起的关键在于自由。在众多因素之中,若为自由故,则一切皆可抛。自由,是西方社会崛起的根本价值、第一推手。这正如马克思所概括的:“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也正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所概括的:“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⑨而严复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的概括也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一个国家的兴衰关键在“自由不自由”。⑩ 当然,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西方社会的崛起是根源于民主、人权、私有制、议院、个人主义等。 在笔者看来,西方社会的崛起是源于一个充分保证每个人都能够自由自在生活与发展的社会共同体的诞生。 这共同体,主要体现为“一点”和“两面”。 “一点”,当然就是作为核心价值的自由。卢梭曾经概括说:人类自古以来所追求的,就是两大价值目标:自由与平等。(11)“平等”,无疑是古已有之,例如中国,例如法国,它早已成为核心价值,但是,自由尽管早就被关注,但是却直到英国的崛起,才首次成为核心价值。当然,在西方社会的崛起中,“这种自由之感曾经是一个推动的力量”,正如黑格尔所描述的:“产生了最伟大的革命运动。”(12) “两面”,则是指其中的两个必不可缺的层面。一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二是“在契约面前人人平等”。用我们所熟悉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把上帝的还给上帝,把凯撒的还给凯撒。”换言之,就是:在灵魂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这方面,无疑与韦伯所指出的“合理化”有较多近似之处)。这是借助“自由”这一西方现代社会崛起的核心价值而展开的两个层面。具体来说:“在精神世界,一切都是按部就班,有条不紊,预先得知和预先决定的;而在政治世界,一切都是经常变动,互有争执,显得不安定的。”托克维尔这样来揭示西方社会崛起的秘密:“这两种看来互不相容的趋势,却不彼此加害,而是携手前进,表示愿意互相支持。”(13) 当然,作为一个充分保证每个人都能够自由自在生活与发展的社会共同体,在“一点”和“两面”之间,还会有层层递进的若干方面,例如,还有包括私有制、议院制、市场经济等在内的制度层面,还有包括民主、人权、个人主义等在内的观念层面等。不过,限于篇幅,本节不去详论。 至于这“一点”和“两面”的来源,则显然与在西方社会崛起过程中出现的两大运动直接相关。一是文艺复兴,二是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运动出现在南欧,发源地是意大利,欧洲的法国等国也都是受惠者,当然,天主教在其中也影响甚巨。这是拉丁文化圈的一次启蒙运动,导致的是法国人的无神论加个人主义的人本主义现代化与斯拉夫人的无神论加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换言之,导致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然,并不彻底)”;宗教改革出现在北欧,发源地是德国(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英国(宗教改革)和瑞士(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基督教(狭义)在其中起推动作用。英国、荷兰等国则是直接受惠者,它是日耳曼文化圈的一次启蒙运动,导致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神本主义现代化。换言之,导致的是自由的出场以及“灵魂面前人人平等”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出场。 由此,那个众所周知的韦伯问题:为什么在英国之外,其他国家的“古老民族的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14)也可以得到明确的回答。 例如,在中国,为什么“古老民族的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洗礼。儒教本身始终未能出现类似西方的宗教改革那样的改革,因而有如韦伯的剖析,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而且,即便是在五四时期,即便是聪慧如鲁迅,也仅仅意识到了“自由的个人”,也就是仅仅意识到了人本主义,但是却没有顾及更为重要的神本主义。 再如,在欧洲,为什么在英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古老民族的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同样也是因为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洗礼。无论是法国人的无神论加个人主义的人本主义现代化,还是斯拉夫人的无神论加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都是以理性为神、以人为神,也都是从人性中寻找世界的至善,对于人性的罪性与人性的神性都没有充分的自觉。因此,所谓的“法国大革命”,其实恰恰是对于充分保证每个人都能够自由自在生活与发展的社会共同体的破坏。尽管它承受的是文艺复兴的影响,也高扬了个人,但是,文艺复兴却实在未能令人满意,因为,它其实仅仅是希腊精神的归来,而且,归来的只是有限的人性,而不是无限的神性。其中,《蒙娜丽莎》作为非宗教的第一个圣母,她的微笑(所有的圣母都不微笑)就已经透露了文艺复兴的这一秘密。彼特拉克被学者称为“第一个近代人”。在他对劳拉的赞美中却可以看出与但丁对于贝德丽采的赞美的不同,但丁的赞美完全是精神的,可是,它的赞美却是精神、肉体兼容并蓄的。劳拉因此也已经不再是圣母,而是美女。难怪彼特拉克要借用奥维德的话表达自己的心迹:我同时爱她的肉体和灵魂。也因此,“应该成为的人”,在法国也就变成了“本能自然的人”。既然不承认上帝的伟大,人的渺小无疑也就无从谈起。联想到法国革命时把巴黎圣母院改为理性之殿,以及巴黎公社社员高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联想到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费尔巴哈、狄德罗的把罪恶归因于社会,以及以人间天堂僭代上帝之城、以英雄僭代圣人,以人神僭代神人、以艺术僭代信仰、以审美僭代宗教,联想到神本主义在法国的杳无音讯,从文艺复兴出发的法国虽左冲右突费尽周折却未能进入西方的崛起社会行列,其中原因,应该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三、基督教:“作为宗教的宗教” 还必须详加阐释的,是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为什么就能够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黑格尔的观点说起。 黑格尔曾经把全世界的信仰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自然宗教。也就是原始社会时期崇拜熊、崇拜老虎、崇拜雷神、山神、火神的那种宗教,这类宗教没有什么信仰内涵,也与人类的终极价值无关;第二类是实用宗教。这类宗教把信仰当成一种恐吓别人和安慰自己的手段,所谓“神道设教”,同样没有什么信仰内涵,同样与人类的终极价值无关;第三类是自由宗教,黑格尔称之为“启示宗教”。在黑格尔看来,人类的宗教虽然多种多样,但是,只有这类宗教才可以被称为宗教。我们所熟悉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就无疑都属于启示宗教。不过,又必须看到,它们彼此又有程度的不同。其中,唯独以基督教最为成熟。无疑,这也正是马克斯·韦伯称基督教为“理性的宗教”,马克思更称基督教为“作为宗教的宗教”的原因之所在。 至于其中的原因,则应该说,首先与基督教的一神教特征直接相关。 一神教当然并不自基督教始。例如,犹太教的精髓就在一神崇拜。唯一神,是它的核心。这当然与它要竭尽所能将散布各地的犹太人在精神上凝聚起来密切相关。基督教的起步也由此开始,不过,却又在此基础上作出根本转换。以“选民”为例,犹太教的“选民”让犹太人的未来有了保障,可是基督教却变成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就使得自己的追随者从犹太民族扩展到了所有人,遥遥开启了现代“自由、平等、博爱”的源头。再以“原罪”为例,犹太教也关注“原罪”,但是却更看重亚伯拉罕与上帝之间的签约,因为这可以让历经不幸的犹太人能够对自己有个交代。可是,一旦认定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也就没有人会再去热衷于灵魂的问题了,因为认定只要恪守那份签约就一定会得救。基督教却不同,它关心“原罪”的清洗,关心赎罪,由此,也就必然会关注灵魂。这样,重要的就不是意在强调罪人这样一个事实,而是要昭示这样一个希望:每个人都有可能重新做人,都有可能“成神”。(15) 再看基督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区别。 基督教(广义的)是耶稣基督亲自创立的教会。人所共知,它经历了两次大分裂,一次是1054年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分裂,另一次就是马丁·路德创立的新教(基督教)与天主教的分裂。就后者来看,简单而言,天主教强调教会、神职人员、圣事等中介的重要作用,但是基督教却强调“因信称义”,也就是在“蒙恩”之外,还可以“因信”。而且,《圣经》具有最高的权威,信徒可以藉此直接与上帝相遇,因此,也就越过了天主教坚持的教会释经权。显然,这不仅解放了人类整体,而且解放了人类个体,更解放了人类个体的灵魂(不再被教会掌控)。 这样,尽管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说,多神教与一神教都无可指摘,但是,如果就宗教之为宗教的成熟程度而言,那就必须要说,多神教的根本缺憾是明显的。多神,意味着在思想的层面还没有能够形成一种统摄一切的终极价值,因而往往会形成多种现实价值。而这又必然使得宗教自身趋于功利,使得人与神之间成为一场交易。需要的时候,祭祀之,不需要了,则不祭祀之,或者转而祭祀他神。如此的灵活,对于终极价值的关注,就无疑会被置之脑后。而且,多神还必然导致诸神的权能都十分有限,导致神与神之间的争斗。可是,倘若诸神连自身都难保,又怎么能够给人类以鼓舞?又怎么能够给人类以一个更加合乎人性的终极未来? 于是,大凡多神教往往都是自力宗教。沉沦是因为自己的过错,成功也是因为自己的行善,而且,误以为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而获救。因此,关注的也就不是“成神”,而是“成人”。生命仍旧是自然的、有限的,仍旧是由人开始而不是由神开始,仍旧是因理性而生而不是因神而生,就犹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个大主教,津津乐道的全然是面包、奇迹与权威,更处处以他人的“救星”自居,无疑,在这样的宗教背景下,“灵魂面前人人平等”与“契约面前人人平等”的出场,都绝无可能,自由的出场更绝无可能。 而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教却截然不同。它意味着一种统摄一切的终极价值的出现。在这里,上帝成为绝对的、无限的,而不再是相对的、有限的。或者说,上帝成为唯一。一切都只有它才能够做到,而且,一切也只有期待它去做到;倘若它不出手,那也只有继续期待。于是,宗教不再是一种现实关怀,一个更加合乎人性的终极关怀,开始引领着人生并且成为人生的全部。 更为重要的是,在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教看来,人类是根本无法依靠自性力量得救的。人之为人,所有的真善美都在上帝那边,所有的假恶丑都在自己这边。因此,自身也就干脆被劈为两半,一半是肉,一半是灵,然后,再以后者去直接独自面对绝对而唯一的上帝,以便去赋予它一种神圣的价值。无疑,这样一种做法在犹太教中是没有的,在希腊的宗教中也是没有的。例如,基托就指出:“这种看法对希腊人来说还是陌生的。在希腊人眼里,绝对只有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人。”(16)由此,人性中的神性被剥离出来、独立出来,种种与现实价值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功名利禄之类,也就已经完全不再必要。生命不再是自然的、有限的,而是灵魂的、无限的。“成神”而不是“成人”,由神开始而不是由人开始,因神而生而不是因理性而生,成为一种全新的抉择。“很久以前,基督教曾完成一场伟大的精神革命,它从精神上把人从曾经在古代甚至扩散到宗教生活上的社会和国家的无限权力下解放出来。它在人身上发现了不依赖于世界、不依赖于自然界和社会而依赖于上帝的精神性因素。”(17)应该说,别尔嘉耶夫的这段话所道出的,正是个中的奥秘。 这样,就正如尼布尔所指出的:“正是基督教信仰把个人从政治集团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并使个人有一种信念:借此个人便能公然蔑视强权的命令,使国家企图将他纯粹当做工具的企图落空。”(18)也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单个人独立的本身无限的人格这一原则,即主观自由的原则,以内在的形式在基督教中出现”,“主观性的权利连同自为存在的无限性,主要是在基督教中出现的”。(19)于是,“灵魂面前人人平等”与“契约面前人人平等”的出场,因此而成为可能,自由的出场,也因此而成为可能。 四、从“信仰的自由”到“自由的信仰” 进而,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最为重要的,还是源于它对于内在自由的强调。 平心而论,大凡宗教,无疑都是以对于自由的追求为归宿,也都可以说是为此而努力而又努力。但是,也必须看到,这些努力最终却又偏偏大多站到了自由的对立面。当然,导致如此结果,倒也并不是因为它对于自由没有敬意。事实上,它不但爱自由,而且甚至是疯狂地爱着自由。但是,又不能不说,或许正是由于对自由的热爱,才导致了它对自由的令人触目惊心的背叛。 在这里,存在着一个黑格尔所谓的“理性的狡计”:对自由的追求却导致了对自由的背叛。 究其实质,其实这也就是所谓“自由与平等的悖论”。二者的区别在于,自由是人之为人的终极价值,而平等则是人之为人在自由的前提之下所导致的一种生活状态。而且,本来的状态是:亟待保证的是自由,也就是如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说的那样一种随心所欲地塑造个人生活以及尽可能丰富多样地发展天性的权利;至于平等,则应该在自由的基础上去创造。因此,没有自由就不会有平等,平等是自由的必然结果,但是,自由却一定不是平等的必然结果,倘若先有了平等,则绝对不会再有自由。然而,很多的宗教选择,却是表面上高举自由的旗帜,暗自却以平等取代自由。它许诺的是自由,但是实际上却是在越俎代庖地允诺平等。 在它看来,自己有权代行所有人的自由,也有权强迫所有人交出自己的自由,因为,自己是完全有能力给予所有人以平等的。于是,只要是它在谈论自由的时候,其实却都是在谈论平等。可是,自由又怎么可能与强迫联系在一起?能够与强迫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平等。于是,自由终于站到了它之原意的对立面。本来应当是交付人们自己创造的自由,现在却统统被他者加以规划,并被强制性地给予,无疑,这已经完全与自由无干,而已经是对于自由的强暴与剥夺,甚至,已经是奴役,甚至是独裁。熟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人都知道,这正是其中那位著名的为了所谓“那条可以使人们得到幸福的唯一的道路”(20)而不惜放弃“上帝的自由事业”从事“魔鬼的奴役事业”(21)的“宗教大法官”的所作所为。所以,别尔嘉耶夫才会说:“哪里宁要幸福不要自由,哪里短暂的东西高于永恒的东西,哪里爱人类与爱上帝相对立,哪里就有大法官。”(22) 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恰恰就在于,它能够走出这个怪圈。 在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当然是“信仰的自由”。 “信仰的自由”最早可以追溯到马丁·路德的名著《基督徒的自由》(1520年)。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著名的口号:“因信称义。”借助《罗马书》中“义人必因信得生”的启发,他指出:真正的宗教必须是一个内心自由的人所自由接受的宗教,这必须是信仰的绝对前提。这口号当然首先是针对天主教的。因为天主教要求首先从接受种种外在规定开始,所谓“因行称义”,天主教会的绝对权威、精神垄断以及天主教会的权威和赎罪券于是就反而成为了决定性的东西。这就是马丁·路德所谓的“外在的人”。而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以及加尔文的“信仰得救”,他也因此而被称为“新的世界之主”)却不同,它否定了教会和教皇的作用,也否认了善功、圣礼和神职人员的作用,要求的是完全出自个人的自由选择,每个人都是“极其自由的王”,而不能是被蛊惑的结果、盲从的结果、强迫的结果。这就是马丁·路德所谓的“内在的人”。 由此,也就不难看出黑格尔、卡莱尔之所以赞誉马丁·路德,说他一个人就把欧洲带出了黑暗,英国宗教学家林赛之所以赞誉马丁·路德,说他重新发现了宗教,是颇有道理的。真正的自由,就是指选择的自由,指的是主体自己可以去自由选择,而不是“被迫”地去选择“唯一的选择”。在“信仰的自由”中,人与人的关系被人与神的关系所取代,人之为人,从各种功利角色、功利关系中退出来,从关系世界抽身而出,不再受任何他者的限制,不再是关系中的自己,而是自由的自己、无关系的自己。结果,错位已久的自由重新回到了优先的、领先的位置,也使人真正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灵魂得救的自主权。基督教本身也因而从对于“平等”的关注回到对于“自由”的关注、从“幸福承诺”转而成为“自由”温床。 不过,“信仰的自由”当然并非基督教的“走出”“怪圈”的全部,更为根本的,还是”自由的信仰”的出场。 “自由的信仰”的实质,其实就是以“自由”为信仰。当然,这一切都还只是作为新思考、新维度隐含在基督教的启示求索之中,还只是内在精神世界的自由,而远非自由之全部,也还有待哲学的(例如康德)与艺术的(例如歌德)等非启示求索方式的提炼、转化与回应(详细内容,在拙文的中篇中将详加讨论),但是,它却无疑正是因为深刻触及了这一焦点而傲然挺立于时代的前沿与前端。 “自由的信仰”就是对于自由的固守与呵护。既然关注的不是人与理性的关系,而是人与信仰的关系,既然人已经不是理性的人,而是信仰的人,因此,人也就如同上帝,不再以自然本性而是以超越本性为天命,不再以有限而是以无限为天命,不再以过去而是以未来为天命,人因此而成为永远高出于自己的存在,永远是自己所不是而不是自己之所是的存在。一方面,人间也就沦为赎罪的炼狱、灵魂净化所、未来灵性生活的预修学堂乃至寓所、客栈、涤罪所,沦为天国的一个叛逆的省份,置身其中,只有再次叛逆,才能重返天国,人之为人,或者匍匐为虫,或者疯狂为兽,要“自然而然”或者“顺其自然”地生长为超越本性,则已经绝无可能。另一方面,因为人首先直接对应的是神(至于与他人的对应则必须要以与神的对应为前提),首先以展现上帝的荣耀为荣耀(而不是以展现自己的荣耀为荣耀),而人与神之间的直接对应恰恰正是自由者与自由者之间的直接对应,这样,人之为人也就如同上帝,被先天地赋予了绝对自由的尊严与权利。而且,还由于这自由被认为是上帝的赋予,因此也就绝对不会让渡,正如西方学者乌尔比尔认定的:人有可以放弃的自由,因此有自愿的奴隶,但是基督徒不行,因为人是上帝的造物,自由属于上帝,人当然无权放弃。而且,既然是上帝所恩赐的一切,当然也就必须无条件地恪守。(23)于是,作为完整的自由的一个至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内在的自由,也就在基督教中被特别地予以关注、予以开掘、予以凸显。正如黑格尔所说:“只有在基督教的教义里,个人的人格和精神才第一次被认作有无限的绝对的价值。”(24) 推而广之,作为绝对尊严与绝对权力,基督神的这个内在的自由一旦形成,就必然再也无法容忍外在的种种权利的种种专横跋扈。“上帝的存在是人的自由的特许状。”别尔嘉耶夫这样说道。(25)于是,冲决一切罗网,对于政治与法律层面上的自由的追求,乃至对于终极意义的自由的追求,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正如阿克顿所指出的:“宗教自由是世俗自由的源泉”,也是“所有自由之母”。(26)最终,“市民社会比教堂更加基督教了”(27)的局面在西方社会也就一朝呈现。 五、“新信仰的力量” 再进而,由基督教对于内在自由的强调,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的根本奥秘,也就脱颖而出了,这就是:信仰。 在这里,首先亟待说明的是,西方现代社会的崛起是一个必须予以综合说明的重大社会现象。其中,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也必须给予认真关注。简单地把西方现代社会的崛起归结为某种“理念”、“观念”的推动,是不尽合理的。但是,某种“理念”、“观念”的推动却又是必须给予认真关注的。这是因为,西方现代社会的崛起当然是政治经济行为,但是,同时却也是文明现象。“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马克斯·韦伯提示:“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就像铁路上的转辙员,往往决定着轨道的方向。”(28) 其次,对于基督教与现代社会崛起之间的关系,也亟待辩证考察。事实上,基督教本身也有其重要缺憾,也并非完美无缺。对此,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都早已有所说明。当然,因此而去简单否定基督教对于现代社会崛起的积极作用,无疑是不妥的,不过,转而去简单肯定基督教对于现代社会崛起的积极作用,同样也是不妥的。 这是因为,对于现代社会崛起的重大推动作用,从表面看,是基督教,从深层看,却是在基督教背后所蕴含着的信仰。 换言之,所谓基督教,其实只是现代社会崛起的温床,在其中酝酿而出的,恰恰是信仰。一方面,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只有基督教,才最为广泛、最为深刻地触及了信仰维度;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崛起,又没有信仰万万不能,因此,现代社会崛起才选择了基督教作为第一小提琴手,基督教也才得以冲出教堂,成为了现代社会崛起的第一主角。 也因此,要深刻理解对于现代社会崛起的重大推动作用,就必须从将宗教与宗教精神严格加以区别开始。 涂尔干指出:“宗教是一种与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与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之内。”(29)显然,在他看来,宗教应该区分为信仰、仪式、信徒三个因素。其中,“仪式、信徒”二者,可以被称为“宗教组织”;“信仰”,则可以被称为“宗教精神”。前者是看得见的教会,后者是看不见的教会。前者,以宗教载体以及宗教风俗为主,后者,以基督教的思想文化体系为主;前者,意味着基督教文明,后者,意味着基督教文化。 对于“宗教组织”与“宗教精神”的区别无疑异常重要。简单否定基督教对于西方现代社会的崛起的重大推动的人因为忽视了这一点,因此也就往往忽视了历史上对于基督教的批判主要是集中在“宗教组织”而并非“宗教精神”。例如,对于文艺复兴,马克思其实就已经提示过,它主要是“对教会的攻击”。(30)简单肯定基督教对于西方现代社会崛起的重大推动的人因为忽视了这一点,因此则往往在肯定基督教精神的时候却又一并连基督教也肯定了下来。因此,也就反而忽视了其中的“表达了神圣事物本质的表象”(31)的信仰、“直接由心到心,由灵魂到灵魂,直接发生在人与上帝之间”的信仰。(32) 同时,信仰也并不唯独属于宗教。 人类是意义的动物,信仰,则是对于人类借以安身立命的终极意义的孜孜以求。卡西尔指出:人类“被一个共同的纽带结合在一起”,这个“共同纽带”就是终极意义,也就是“信仰”。(33)它是人类的本体论诉求、形而上学本性,也是人类的终极性存在,借用蒂利希的看法: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层”、“人类精神生活所有机能的基础”。(34)至于人类的哲学、艺术与宗教等,则“都被看做是同一主旋律的众多变奏”。可惜我们过去既误解了哲学、艺术,也误解了宗教,或者误以为信仰只隶属于宗教,(35)或者误以为信仰只隶属于哲学、艺术,其实,尽管在形式上存在理论的、感性的抑或天启的区别,但是,这三者的深层底蕴却都应该是信仰。 具体来看,宗教当然不是哲学,也当然不是艺术,但是,它却同样具备着人类的本体论诉求与形而上学本性。正如西方哲人保罗·蒂利希曾郑重提示的:宗教是文化的一个维度,而不仅是一个方面。这里的“宗教”,其实就是指宗教背后的“信仰”。这是因为,不是宗教缔造了人,而是人缔造了宗教。宗教的本质无疑也就是人的本质。因而人的超越本性应该也就是宗教的超越本性。而宗教对于人性中的神性的强调,则恰恰是对于人自身中超出自然的部分亦即超越本性的部分的强调。这个部分,当然也就是人类的本体论诉求与形而上学本性。无疑,正是这个“本体论诉求与形而上学本性”,使得宗教不但应该蕴含“仪式、信徒”,而且还应该遥遥指向“信仰”。遗憾的是,对此,众多研究者却往往习焉不察。 因此,从表面看,宗教似乎只是对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孜孜以求,但是,真正的宗教,却必须是对超自然力量背后的人类借以安身立命的终极价值的孜孜以求。这就是宗教的“本体论诉求与形而上学本性”,宗教也因此而与人类的信仰息息相通。所以,黑格尔才会时时提示着宗教中的所谓“庙里的神”,(36)可惜,自古到今,诸多的宗教偏偏都是有“庙”无“神”,尽管也追求某种超自然力量,但是,在超自然力量的背后的人类借以安身立命的终极价值却相对淡漠甚至空空如也;当然,有的宗教却不然,不但有“庙”,而且有“神”。在所追求的超自然力量的背后,还隐现着对于人类借以安身立命的终极价值的追求。它起源于对人的“有限性”之克服和超越的“领悟无限的主观才能”,“它使人感到有无限者的存在”,(37)这也就是麦克斯·缪勒所揭示的宗教所蕴含的信仰内涵——“领悟无限”,或者斯特伦所揭示的“终极实体”:“在宗教意义中,终极实体意味一个人所能认识到的、最富有理解性的源泉和必然性。它是人们所能认识到的最高价值,并构成人们赖以生活的支柱和动力。”(38)由此,人类的“何以来、何以在、何以归”,人类的心有所安、命有所系、灵有所宁、魂有所归,都因此而得以解决。 由此,不难想到,基督教恰恰是一种不但有“庙”而且有“神”的宗教,一种能够透过对超自然力量背后的人类借以安身立命的终极意义的孜孜以求去实现人类的“本体论诉求与形而上学本性”的宗教。而基督教的对于社会崛起的重大推动作用,也恰恰就在于其中“起拯救作用的,并不是宗教本身,而是宗教信仰所提倡推行的仁爱与正义”。(39)这就犹如西方人类学家瓦茨剖析的:“要衡量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几乎没有比这更可靠的信号和标准的了——那就是看这个民族是否达到了这一程度,纯粹的道德命令是否得到了宗教的支持,并与它的宗教生活交织在一起。”(50)西方社会的崛起,无疑因为它“得到了宗教的支持,并与它的宗教生活交织在一起”,而基督教所带来的,也恰恰是“新信仰的力量”。(41)至此,有必要提及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在谈及西方世界现代化的基本经验之时的一个发现。在他看来,其中的路径,并非人所共知的从自由的个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而是:从自由的信仰—自由的个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无疑,从前面我们的讨论来看,“自由的信仰”为我们理解基督教与现代化之间的直接相关提示了一个正确方向。(42)原来,在西方社会的崛起与“先基督教起来”直接相关这一历史事实面前,亟待引起我们关注的,其实不仅仅是基督教,还更应该是在基督教中所蕴含的“自由的信仰”。西方社会崛起中的所谓“先基督教起来”,其实也无非是因为要借此而“先信仰起来”。而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后发者而言,只要能够“先信仰起来”,却又可以不必先“先基督教起来”,显然,对于奔进在现代化征程中的全世界的非基督教国家与民族(例如中国),这,实在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启示。 注释: ①例如,1512年,西班牙人的一个武装小分队登陆了南美的厄瓜多尔,158年以后,1670年,一个英国人才赤手空拳登陆了北美的南卡罗来那,可是,我们今天谁都知道,被天主教的西班牙和基督教的英国染指之后,南美和北美的差距何等之大。 ②杜兰的《世界文明史》就把基督教与新文明之间的关系比喻为母子关系,见杜兰:《世界文明史》,幼狮文化公司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62页。 ③法国曾经进入早期的现代化8国,但是,现在已经退出了现代化的第一阵营。 ④因为王岐山的推荐,国人现在对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都很熟悉,在这本书里,所谓“旧制度”,其实就是指的除了英国、荷兰之外的整个欧洲。在历史学家的眼中,英国、荷兰以及它的第二代的传人——美国。就代表着全部的西方奇迹,它们当时的人口仅占世界的2%,但是影响力却遍及其余的98%的人口。 ⑤95%的美国人信仰上帝,其中86%为基督徒。基督徒中,60%为新教徒。美国货币上就印有“我们坚信上帝”。美国的主导人群始终是“WASP”,即白种盎格鲁—撒克逊血统(White Anglo-saxon)与新教教徒(Protestant)。美国总统绝大多数也都是新教徒。 ⑥当然,当今英国已经跌出了一线阵营,不过这一切恰恰不是因为基督教,而是因为后来的英国走向了宗教世俗化的道路,也就是说,走上了弱化基督教的道路。 ⑦甚至,英国人用500人就可以管理好5亿人口的印度,可是,法国用200人却管理不好150万人口的柬埔寨。 ⑧而且,在法国(还有德国),也是北富(新教)南贫(天主教)。 ⑨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0页。 ⑩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页。 (11)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9页。 (1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1-52页。 (13)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48页。 (14)于晓:《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译本前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 (15)还有从犹太教的“千禧年”转向“救赎说”、从犹太教的祭祀和律法转向内在的信仰(基督:我喜爱怜悯,不喜欢祭祀)、从犹太教的效果论转向动机论、从犹太教的直观性转向形而上学等。所以,基督教“比《旧约全书》的信仰更为强烈”(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杨照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92页)。 (16)基托:《希腊人》,徐卫翔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3页。 (17)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安启念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4页。 (18)转引自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238页。 (1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00、201页。 (20)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耿济之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76页。 (21)同上,第384页。 (22)别尔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耿海英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5页。 (23)参见丛日云:《在上帝与凯撒之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68页。 (2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1-52页。 (25)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与凯撒王国》,第21页。 (26)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76、399页。 (27)库比特:《西方的意义》,王志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页。 (28)马克斯·韦伯:《经济·社会·宗教:马克斯·韦伯文选》,郑乐平编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77页。 (29)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4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83页。 (31)普理查德:《原始宗教理论》,孙尚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7页。 (32)詹姆士:《宗教经验种种》,尚新建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33)参见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78页。 (34)蒂利希:《文化神学》,陈新权等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第9页。 (35)哲学、艺术部是在宗教的基础上起步的。因此与信仰并非水火不容。歌德说:如果人不信仰哲学,那就信仰宗教吧。其实也是在提示我们去关注哲学、艺术背后的信仰。 (36)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页。 (37)麦克斯·缪勒:《宗教学导论》,陈观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页。 (38)斯特伦:《人与神:宗教生活的理解》,金泽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Z年,第3页。 (39)博泰罗等:《上帝是谁》,万祖秋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161页。 (40)瓦茨语,转引自包尔生:《伦理学体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55页。 (41)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曹未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0页。 (42)在这方面,西方一些著名学者的研究值得注意:“自我的优先,植根于基督教信仰。”(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第15页)“专制制度可以不要宗教信仰而进行统治,而自由的国家却不能如此。”(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国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41页)标签:宗教改革论文; 基督教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中国法国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法国文化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天主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