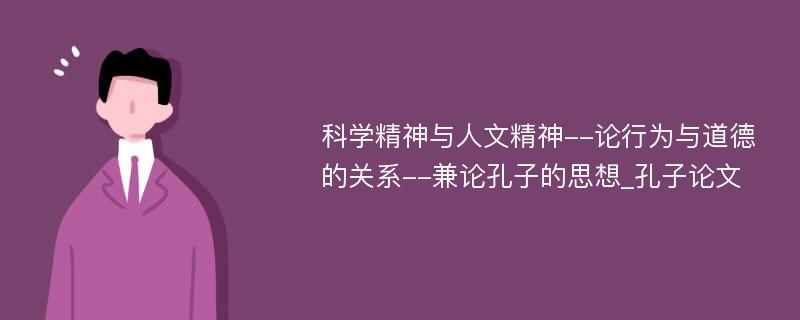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谈行动与道德的关系——兼论孔子的见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见地论文,人文精神论文,道德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笛卡儿的困境
提出心物二元论的人不算少,但以笛卡儿最著名。他推崇的认知方法着眼于对象的分割、形状和运动,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倚重自明的观念;不过,笛卡儿很快就知道,有些对象没有可割性、形状和运动可言;于是提出心物二元论,指出对象如果有分割、形状和运动可言,便统称为“物”,否则便统称为“心”;两者都可知,所用的方法和概念却不相同。虽然如此,笛卡儿毕竟没有切断心物之间的联系,他清楚地表明了人由心物两种实体合并而成,承认心通过意念引发行动;如果是这样,行动便有别与笛卡儿所指的物,也有别于他所指的心;那么,行为究竟是物还是心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让笛卡儿陷入困境。
二、康德的代价
摆脱困境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非认知主义者所采用的方法,康德是这个方面的代表,他构思了两种秩序,一种是自然秩序,另一种是道德的秩序;在他看来,自然秩序关乎现象界,所以是可知的;至于道德秩序则关乎本体界,由于人没有认识本体界的知性,所以道德秩序被视为认知对象以外的东西。采用这个立场的好处在于不用再费神去解答人怎样认识行动所负载着的道德含义,省却麻烦,坏处则在于承认两种秩序分置于现象和本体两界而带来了严峻的问题:“人处于现象界,受制于自然秩序,他要怎样才可以摆脱制约而依据自己的自由意志作出道德上的抉择呢?”这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笛卡儿心物二分的问题。
按照康德的想法,这是协调自然和道德两种秩序的问题;说明两者可协调就要让人在道德上所做的工夫适当地反映到他所得到的福祉上,最高的善就在道德和福祉有了最完美的协调时体现出来;康德认为要知道完美的协调在哪一段个人或群体历史中出现就要靠一种有别于认识自然秩序的知性,这种知性所涉及的是追求完美协调的无尽历程,康德不相信人作为有限的存在物能够有这种知性,所以他把这种知性归于上帝,名为智的直觉,保持了非认知主义的立场;不过,他为此付出了代价。
在康德的体系里,设想上帝的作用就在于说明道德与福祉有可能得到完美的协调,人在道德上下了工夫之后,还得要上帝的眷顾,(注:《纯粹理性的批判》表述了这个想法。)才得以实现道德与福祉的完美协调;也就是说,道德与神的力量并举,最高的善才得以实现;得出这个看法实在是他所始料不及的;他在开始的时候,就一反传统的神学思想,从人的自由意志出发谈论道德,而今却要回到上帝那里寻找道德的根据,使自由意志失色;这就是代价,也说明他还没有真正放弃神学的道德观点;康德要减少神学的影响还得要进一步修正他的想法;办法是以新的观点来看待自己所构思的两种秩序,这个做法让他倒向认知主义,承认人既可以从自然秩序的观点看自己的行动,也可以从道德秩序的观点看自己的行动;(注:《道德形而上学的基本原理》表述了这个想法。)从前面的观点出发,所有的行动都服从自然的秩序,与笛卡儿所指的物同受自然秩序的制约;从后面的观点出发,这些行动却有不同的道德理由决定它的取舍,与笛卡儿所指的心一样,取舍与自然秩序无干;换句话说,人的行动尽管受制于自然的秩序,它仍然有道德的含义;有了新的观点,原来的严峻问题得到了缓和,我们开始明白,尽管自然秩序不依照道德理由而定其是非;不过,自然秩序中总有一些行动具备了道德的含义,这些行动当依照道德理由而定其取舍。然而,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康德的追随者不得不问:“我们怎样掌握这些行动的道德含义?”他最终也回避不了认知主义的立场。
摆脱困境的第二个方法是坚守认知主义,怀特海有这种想法,他主张“心意引发行动”为可知之事;在他看来,笛卡儿的理论仅仅阐述了心物两种本体靠自身而存在的道理,却没有说明心物共存的理据,这种安排妨碍了“心如何通过意念引发行动”的说明。按照怀特海的想法,补救办法在于提出更为优胜的理论,让它告诉我们,“事件”才是最基本的存在,笛卡儿所说的心与物仅是观念,用于说明“事件”的两个方面,以如此的理论说明“心如何通过意念引发行动”会容易得多;他相信坚持这样的理论除了有助于弥补心物两种观念之间的裂痕之外,还有助于消除永恒与偶然两个观念之间的矛盾;中国哲学有“天人合一”之说,“天”代表了永恒,“人”是偶然的表现,提倡两者合一正是怀特海所向往的哲学,因此他相信中国人会接受他的想法,与他一道主张任何称得上是“事件”的东西,既有心之性,也有物之性,同时面对两种制约;说明两种制约并行不悖,也就消解了永恒和偶然的矛盾,让人们明白事件必可从其心之性去了解它,不会受到物之性所影响;那么,行动如为一事,人们便可以放心以此事的心之性去说明行动如何为意念所引发,从而消解笛卡儿的烦恼。(Whitehead 1957,pp.5-21)不过,儒家讲“天人合一”,却另有一番景象。首先,儒者注意到仁者出仕未必发挥道德的作用;其次,儒者注意到大道行之于世的时机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仁者出仕就难于发挥道德的作用;再其次,他们也注意到甚么时候是时机成熟之时,人们难有明确的认识。就凭着这三个基本的观点,人们当可进一步构想出一个较具规模的理论,藉以说明孔子如何说明行动的道德含义,这个理论包括了以下六点:第一,出仕是否为道德的行动不取决于它的“道德效用”,因为“仁者之出仕在没有发挥道德效用的时候便会丧失其道德性”的讲法难有自圆之说,这一点下一节讨论“仁者不必有功”时会详细讨论;第二,时机是否成熟,取决于众多的因素,当中有些因素受制于自然的秩序,也可能有一些因素受制于道德的秩序;那么,说“出仕在时机成熟时才发挥道德的作用”,其实是承认了这样的讲法:“行动不必摆脱自然秩序的制约才发挥作用。第三,仁者“志于道”,不必要求自己先知道何时时机成熟,才考虑出仕的问题;因为时机是否成熟难有定说。以上两点在第四节有详细的讨论。第四,“时机成熟与否”的问题,仁者是否有确切的答案,不能作为评论仁者是否有道德的标准,理由很简单,仁者当重视行动的道德性,其次才是道德的效用。第五,仁者无时无刻不考虑匡扶道德,毫不松懈,于机遇一旦来临之时,便有十足的准备让自己的行动发挥较大的道德效用;有些不仁者也相当接近仁者,两者的差别仅在于是否有松懈的时候;另外,还有些不仁者,根本不在乎于道德,这些人的行动,在偶然的情况底下,或会无意地发挥了道德的作用;虽然如此,这样的行动不会变成为行动负责者的道德行动。由此可知,衡量行动的道德性,关键不在于行动的道德作用,也不在于行动的负责人是否掌握了适当的时机,而在于行动的负责人是否锲而不舍地致力于道德。
上述五点帮助我们认识这样的道理:“说明行动有道德含义,不在于说明行动因着甚么而得到心之性,也不在于说明行动因着甚么而受制于道德的秩序;说明行动有道德含义,要先说明有些行动因为它的负责人的确锲而不舍地致力于道德,因而成为有道德的行动。”明白这个道理,就不用再担心我们是否有办法找到合适的本体论,说明行动作为自然秩序之一员,也能够有心之性,而成为道德秩序中的一员,受其制约;也不用再担心我们是否具备了合适的知性,如实地揭示行动的道德含义;综上所说,我们当意识到儒者所关注的,既不是怀特海所憧憬的本体论,也不是康德所回避不了的认知主义。儒者所要认真对待的,就在于说明仁者促成天道得行于世要怎么样做才不失时机的问题;人们一旦明白不失时机,在乎锲而不舍,就没有理由继续相信行动与道德之间存在着消除不了的鸿沟,《论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值得探讨。
三、子贡的疑惑
《论语》记载了孔子给弟子们讲述仁、义、礼、智、信等五个方面的道德修养。让弟子们从几个方面来认识成德之教;可是,弟子们并没有因此而消除了为学的疑难。子贡就曾经向孔子提出了“仁”的问题,他问道:“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雍也篇)孔子在回答中提出了“标准”的问题,他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同上)在他看来,子贡的提法把“仁”的标准定得太高了。就连古代圣王也难于满足;不过,除了“标准”的问题之外,这里还有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要考虑;情况是这样的,孔子心仪古代圣王的政绩;因此,对自己也有期望,他曾经说过:“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而有成。”(子路篇)这是事功方面的要求;然而,孔子并没有执着这方面的要求,他所执着的是道德方面的要求,其执着的程度已经达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里仁篇)的地步了。在事功与道德面前,孔子的两个执着有明显的差异,这并非意味着道德要求难于达到,所以要特别执着;在他看来,成就道德不难,“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篇)根本就没有任何外在的因素足以左右我们的道德;如果我们在这个方面出现了什么缺陷,完全在于我们离道德而去,并不是道德背弃了我们;谁失掉了道德,谁就难辞其咎,没有托词;因此,孔子劝告弟子们要在任何时候都要执着于道德;如此强调“无终食之间违仁”,无非是要凸显这样的要求:“一个人在博施济众”之时要执着于道德,在不能够“博施济众”的时候也要执着于道德。所以说:事功上的成败影响不了个人的道德成就;这一点子贡没有把握好,以为“博施济众”是个善举,一方面以为谁做到了,谁就接近了道德;另一方面又以为谁履行不了这个善举,谁就要加把劲,结果让道德的成就寄托在事功的成就上,违背了孔子的主张。造成子贡的误解,关键在于没有注意事功和道德在成败上受着不同的制约。前者的成败取决于众多的外在因素,后者的成败则取决于个人自身的内在因素。明白这个差异,谈论道德的成败时就不会把眼光集中到事功上来,这个解释固然有助于免除子贡的疑惑;可是,让事功和道德分成两截,由不同制约的条件来左右其成败,却带来了难于解决的问题,借助康德的讲法,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性质和难度:“人的行为是现象界里的事,所体现的当然是自然秩序;而人的自由意志却在本体界中呈现出来,由此而作出的抉择也就体现了道德的秩序。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又怎样能够要求现象界中的行为去配合本体界里的自由意志,让自由意志的抉择通过行动去体现道德的秩序呢?难道人的行动能够摆脱自然秩序的制约,为自由意志效力吗?”子路似乎有类似疑惑,回顾一下孔子怎样为子路释疑,便知道他怎样消解这个难题。
四、子路的疑惑
孔子开释弟子的方法在于言传身教,鲁大夫季氏的家臣阳货请孔子襄助他,遭到拒绝,于是讥笑孔子“怀其宝而迷其邦”(阳货篇),算不上是个仁者,孔子听到后处之泰然;子路明白孔子不为阳货效力的原因在于他谋取鲁国的政权;不替这样的人做事,无损于“仁”;再者,子路没有子贡的疑惑,完全明白未能“博施济众”,也能够成就道德的道理,并且据此认定仁者不必有功。不过“仁者不必有功”的论点不好掌握,《论语》就有记载,指出隐者不明白孔子为什么不洁身自爱,明知“人心不古”,却偏偏要到处游说邦国之君接受他的主张,这样做哪有“仁者不必有功”的想法?提出这种疑问说明隐者没有把握好“仁者不必有功”的道理。孔于着实希望他们明白过来,所以借子路代为解释,指出仁者不能够但求洁身自爱,就拒绝和一切的邦国之君打交道,眼巴巴让伦常纲纪不停地毁坏下去。在孔子看来,不消除消极的归隐态度,于机遇来临时也改善不了恶劣的情况,是仁者所难于忍受的,所以他让子路给隐者回话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卫子篇)在“道之不行”的年代里还寻找出仕的机会,并非忘掉了“仁者不必有功”的想法,而是要捕捉每一个“道之将行于天下”的机遇,这个用心隐者不理解,而子路却是明白的,当机遇来临,孔子出仕,一定会得到子路的支持,因为这个时候出仕,能行其义。
不过,在明知机遇还没有来临的时候还想试探是否可以出仕,子路就不理解。《论语》的《阳货篇》便记载了子路的这个思想状况。当时有一位破坏了纲纪的封邑主管,叫做佛肸,他把孔子叫来见个面,孔子竟然没有直截了当地拒绝他,还盘算着是否接受这个佛肸的邀请;子路知道了,不以为然,并且意图劝阻,这大概是由于他相信出仕是否配合得上个人的自由抉择而成就道德,完全取决于天,人的主观意愿起不了作用;天意让大道不行,出仕不但没有配合个人的自由抉择而成就道德,而且更会沦为败德之举,所以子路设想不了为什么孔子竟然不顾天意,妄想出仕可以脱离现实的制约,为个人的道德抉择效力,更何况孔子相信仁者不必有功,又何苦执意要在大道不行的年代里求有功于世呢?在子路看来,孔子实在是难以理喻,竟然要求现实的行动摆脱社会以至自然秩序的制约,为个人的道德抉择效力。看来,孔子的想法还没有得到子路充分的理解。
在孔子看来,支配大道之兴衰有各种因素,这些因素在甚么时候起着甚么的作用,难以预知,更难以控制;承认这些因素难知难控,就不必要求自己在实践道德之前预知大道是否将行于世;仁者实践道德,最重要的是随时作好准备,在大道将行之时能够马上承担起补弊起救的责任,让自己在履行责任的过程中成就道德。佛肸有意召见,孔子予以慎重的考虑,无非是一种作好准备的举动,以免辜负了天意,成为一个道德意识薄弱的人;在这个情况底下,如果孔子没有识破佛肸的诡计,为他效力,当然要付出道德上的代价;不过,这并不足以证明孔子妄想过出仕能够摆脱现实的制约而为他的道德抉择而效力。要证明他有这个非分之想,首先要确定他的确相信恢复天道的机遇还没有来临,另外又要确定他在相信机遇还没有来临之余,执意要出仕以实现他的道德理想。不过,孔子已经指出了大道之兴废有人事以外的因素,难以预测;甚么时候大道重临他没有明确的认识,子路又怎能认定他明知恢复天道的机遇还没有来临?又怎能认定他坚持出仕要为道德的使命而摆脱自然的秩序?其实,孔子那有如此极端的想法?在他的心目中,一个人目睹道德沦亡,愿意尽其所能匡扶道德,就是个仁者;不过仁者未必有功,这也许是由于个人未尽全力,也许全力已尽却不得其法,也许已得其法而天意却未许大道行之于世;关乎个人的用力或方法,仁者可以过问,并且要求自己不断进步,至于天意如何,就不得而知;仁者在不断要求自己进步之时如果还看不到道德的前景,他也许要承认这是天意;不过,大道是否将行于世他没有明确的认识,所以他没有理由肯定大道不行一定是天意,自己用力不足可能是真正的原因;在这种不知底蕴的情况底下,如果他还是个有志者,便会义无反悔地在自己的用力和方法上继续多做工夫;仁者能够做到这一点,他的行动便充分地彰显了道德的意义。
五、结语
如此阐述行动的道德意义,比较接近孔子的想法,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上述的讲法没有设想过行动要摆脱自然秩序的制约才可成就道德,没有笛卡儿的苦恼;第二,行动者如果义无反悔地在自己的用力和方法上继续多做工夫,他比其它人更有机会让自己的行动发挥最大的道德作用;就凭这一点,当可认定他最懂得掌握行动的道德意义;这样说,掌握道德意义的关键不在于明白天意何时让大道行之于世;谁明白“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子罕篇)所依托的道理,就会明白天从来就没有遗弃过道德;人如果活得没有道德意义,完全是因为自己离弃了道德,不应该怪责上天,也不应该怪责别人。这正好说明离弃道德与否是个人的抉择;一个人如果不让自己的决择受到干扰,实在难以在他的行动与道德之间划出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按照这个讲法,人只要明白道德不会离弃我们,便有十足的依据说明人的行动为道德秩序中的一员;看来,康德没有透彻地说明这一点,以为行动与道德之间有一道鸿沟要逾越,于是设法说明这个困难如何克服,让人的行动体现自由意志所向往的道德;在儒者看来,这是个误解。能够掌握以上两点,便会明白孔子为甚么不担心行动受制于现实的自然秩序,永远体现不了个人抉择所指向的道德意义窒碍了行动,因为我们从他那里知道了天不会遗弃道德,我们不必设想行动要摆脱自然秩序的制约,才实现道德;另外,我们也会明白孔子为甚么不担心行动与道德之间有难以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从他那里知道了道德不会离弃我们。总之,阐述行动与道德的关系,依靠怀特海和康德的心思,解决不了子路的疑惑。
标签:孔子论文; 康德论文; 道德论文; 人文精神论文; 国学论文; 笛卡儿论文; 自由意志论文; 哲学家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