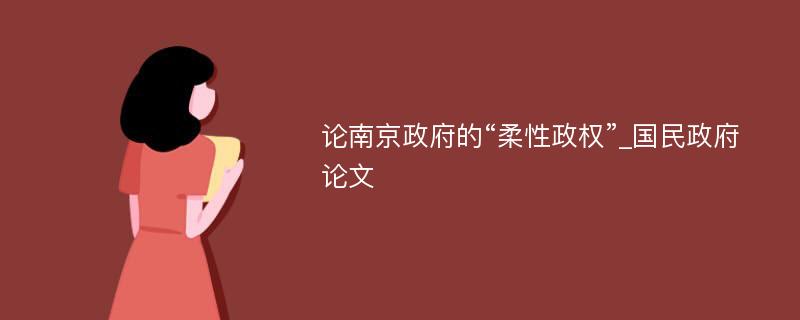
论南京政府的“弹性政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体论文,南京论文,弹性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南京政府存在的22年间,其政府体制在常规制衡下各组成部分职能的不断变动,导致了实际政体的弹性变动。本文简要的勾画和分析了其变动的轨迹及其制动因素。
关键词 南京政府;政体;弹性政体
中图分类号 D693
从1927年建立到1949年在大陆的崩溃,南京政府22年间政府体制在常规制衡下各组成部分职能的不断变动,导致了实际政体的变动不定。本文拟简要的勾画和分析一下这种“弹性政体”变动的轨迹及其制动因素。
一
从主体上看,南京政府是代表资产阶级中上层及其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权,就其性质而论当属地主资产阶级专政,而在世界范围内,共和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大多采用的政体形式主要有总统制、内阁制以及委员制亦称合议制。那么南京政府在组织形式上应属于哪一种呢?
要分析这一问题,有两点必须注意:其一是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其二是国民党与政府的关系。南京政府的主要建立者蒋介石一直声称尊奉和实行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而且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将其付诸实施了。但是孙中山并没有明确指出按“五权宪法”建立的政府是什么形式的政府。在《五权宪法》一文中,按照孙中山的解释即把“全国的宪法,分作立法、司法、行政、监察、考试五个权,每个权都是独立的”。[①]所以所谓“五权宪法”,就是实行五权分立制度的宪法原则。与此同时他又提出了“权能分治”的主张,即把国家的政治权力分作两部分:一个是“权”或称“政权”,一个是“能”即“治权”。“政权”也就是民权,归人民所有。包括选举、创制、复决、罢免四个方面的权力。“治权”就是管理权,它归政府。包括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个方面。按照孙中山的设想,这种“权能分治”可以使人民不必有处理政务的能力而可以享有政治实权,同时又能创造一个和谐的、有能力的、有工作效率的“万能政府”。但是这个政府究竟采用什么形式即用什么样的政体才能把权能分治、五权分立完整的统一起来,孙中山既没有明确说明又没有垂范。虽然1912年的南京临时政府以及后来的护法军政府多取总统制或类似总统制的集权制,但这些政府都不是按“五权分立”原则建立的,因而都不足以说明南京政府的政体。蒋介石说按照“五权宪法”建立的政府应该是总统制,但是反蒋派则说应该是内阁制,特别是在“行宪”以前成为导致政体弹性可塑的重要原因。
考察南京政府的政体,国民党与南京政府的关系又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这是几乎所有的共和制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孙中山自革命伊始,就注重组织革命党,通过党来领导革命。而且从孙中山的革命生涯看,其自始至终对欧美式政党政治亦即议会多数、政党内阁并不推崇,而一直主张和推行一党建国即依靠他所领导的革命党来完成革命和建国的任务。由于这种历史渊源关系,最终形成了“党在国上”、“以党御政”的格局。孙中山逝世后,这一格局一直延续下来。那么国民党与南京政府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对此《训政纲领》第1、2条明确规定:“训政时期开始,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②]。关于治权,《训政纲领》规定:“治权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付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③]。但要由国民党指导和监督。为此,国民党成立了训政最高指导机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简称中政会)。中政会“在决定训政大计指导政府上,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政府在实施训政计划与方案上,对中政会负责”[④]。而且从国民政府的主席、委员到五院的各部会首长都由中政会选任。所以在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之间剪不断、理还乱,国民政府政体的每一次变化和细微的颤动无不是国民党决策层的操纵和得到它的认同。同时从法理上看,训政时期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委员会又实际上成为政府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依据南京政府公布的众多“政府组织法”看,南京政府的政体大致可依“行宪”后总统府的成立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从1927年4月到1948年4月是第一个时期;从1948年4月到逃离大陆为第二个时期。
1927年4月南京政府建立时,既没修正以前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也没有发布任何法律性的文件来说明南京政府是什么形式的政府,而且也不承认南京政府与广州时的国民政府有本质上的区别,仅以广州的国民政府迁都南京自为,并电促在武汉的原广州国民政府委员速到南京就职。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广州、南京两政府性质的不同,仅着重政府形式问题。既然是广州国民政府迁都南京,那么其政府组织当依广州国民政府所颁布的“政府组织法”。在这个共十条的组织法中,明确规定国民政府采用委员合议制,国民政府以委员若干人组织,并于委员中推定主席一人,常委5人处理日常政务。这是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组织政府颁布的第一个政府组织法,其合议制政体的采用在客观上也是国民党内还无人能取代其领袖地位的结果。广州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曾对这个组织法进行了修正,取消了国民政府主席,由国民政府委员会处理政务,常务委员执行日常政务。合议制的色彩更浓了。对这个组织法南京政府实际上是将其作为政府组织的依据,保持着合议制的政体不变,同时也受到武汉国民政府的影响,没有设主席一职。以此为开端,合议制的政体形式在南京政府中开始固定下来,虽然后来的政府组织法屡加修正,但是合议制的政体形式上始终保持不变,直到蒋介石1948年4月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为止。
应该说这一时期政体的规定是明确的,但同时也是抽象的,甚至是空洞的,而实际中又是如何运作的呢?
(一)从主席集权到个人独裁——合议制体制的第一种走形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恢复设立国民政府主席一职,由国民党中执会于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中推定。这是南京政府中主席一职的开始设立。从这时期的规定看,主席没有超越其他常委的特权;连署公布法令的规定显示了主席仅是常委中的一员。到了同年10月,五院制国民政府组织法颁布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根据该组织法,国民政府设主席1人,并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在中国由于军权历来是最重要的,国民政府主席一兼任三军总司令,立刻使主席的实际权力大大提高,同其他常委的平等地位开始发生倾斜。但这仅仅是主席权势加重的第一个表现。该组织法在原则上还没有脱离合议制精神,仍由国民政府委员组成国务会议处理国务。然而合议制的精神在不断减少和消失。1930年11月,修正的“国民政府组织法”重新规定,公布法律由主席署名,立法院长副署,发布命令由主席署名,主管院长副署,无须五院长共同负责。可以说分权与集权、民主与专制在概念的涵盖上是相去甚远的,然而在实际运作中有时仅仅是一步之遥,南京政府由合议制向个人集权到独裁的过渡正是这样。1931年6月《训政时期约法》颁布,据此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对政府组织法又作了重要修改:国民政府主席对内外代表国民政府,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为国民政府会议主席。五院正、副院长,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及直隶于国民政府的各部会首长,以主席提请国民政府任免。国民政府发布法律及发布命令,不须国民政府会议议决,只须国民政府主席署名,关系院长副署。至此,国民政府主席从军权开始,进而将人事任免权、公布法律权、公布命令权等等,统统集于一身。因而使南京政府在合议制名义下,合议制的原则和精神荡然无存,而形成主席个人集权的局面。
这一过程表现的很清楚,合议制的被破坏、合议制体制的被扭曲和嬗变是以非常规的措施实现的。也就是说不是通过变动政府机构,从根本上重新划定和组成行政、立法、司法等相互关系而实现政体的转轨。南京政府实际运作中的合议制政体被破坏后,名义上的合议制形式还保留着,国民政府仍由主席及委员们组成,政府的主要机构依然是五院,它们的相互关系保持不变,而仅仅通过修改政府组织法,加重政府中某一部分比如政府主席的职权,从而使整个政府的权能平衡被打破,因而在实际上改变了政府的体制形式。这种手法所达到的政体变动往往被人所忽视,而且其被扭曲、改变的程度也因人因时而异,时大时小,时多时少,弹性可塑的特点异常突出,导致了南京政府的政体总是在不断扭曲中摇摆不定。
第一次主席集权进而独裁后,在国民党各方的围杀下,不久即告结束。国民政府主席被限定不负实际政治责任,不得兼任他职,似乎是要维持合议制体制的权能平衡不再因主席的个人集权而打破。但是1943年8月,“恬静守法”不负实际政治责任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后,情况再次发生变化。9月,民国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政府修正案”:取消国民政府主席不得兼职的限制,得兼任陆海空军大元帅;国民政府主席由不负实际政治责任改为对国民党中执会负责;五院的正副院长由国民政府主席于国民政府委员中提请国民党中执会选任;将五院独立行使五种治权改为分别行使。如此种种加之在实际中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同时兼任着国民党的总裁和最高国防委员会的委员长,集党、政、军权于一身,因而事实上形成了国民政府主席的再次集权和独裁。
应该说,从广州国民政府到南京政府,采取合议制的原因不外两点:避免个人的权力独占和没有一个各方公认的领袖,而且后者恐怕更具实质性。从表面上看,没有一个公认的领袖似乎有利于合议制,但是实际上各方的对峙并不等于是各方势力完全相等,而且在对峙中力量是不断消长变化的,从而也就产生了改变合议制的潜在力量。当这种力量成熟的时候,靠势力相峙所维持的合议制在实际中就会被别的政体形式所取代,如果取得优势的一方不能保持其优势,各方在联合、对抗后重归对峙的话,那么合议制就会回归和反弹。
(二)隐约的内阁制——合议制的另一种走形
第一次主席集权从实际上看是蒋介石一派势力膨胀的结果。这时的蒋虽取得了明显的优势,但还没达到彻底摧毁各派的地步。1931年2月蒋介石把坚决反对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的胡汉民扣押幽禁于南京汤山,使胡派愤起反抗,于是反蒋各派以此为契机纷起响应,进行联合大反蒋,坚决要求蒋介石下野。在一拳难敌四手的情况下,蒋被迫辞去了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等本兼各职。接着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突出地削弱和限制国民政府主席的权力: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内外代表国民政府,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不得兼任他职。这一规定在法律上从而也在实际上使国民政府主席成为真正的虚位元首。力图将政府体制从个人专权再拉回到合议制的轨道上来。在其他方面还规定,国府委员、五院正副院长均由国民党中执会选任,废除由政府主席提请任免的做法;国民政府的所有命令处分及军事动员令由主席署名,但须经关系院长、部长副署始得生效。并特别规定,在宪法颁布之前,五院独立行使五种治权,各自对国民党中执会负责。可见,这一次无论各派的动机目的如何,其结果在政府体制上都可算是对合议制的重塑。而且由于对个人集权的恐惧心理,在这次重塑的合议制中同时包含了更多的内容,以至向内阁制的方向倾斜。在国民政府的五院中,无论怎样规定五院的地位平等,而事实上行政院总是政务活动的主体,国家机器运转的枢纽。当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而且五院的正副院长及各部会长不得兼任国府委员时,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唯一的“解决院与院间不能解决事项”的职权便成为一句空话。从而使本来是在五院之上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名存实亡。很自然五院便各自向国民党中执会负责,独立行使五种治权。然而我们纵观整个南京政府,它的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四种治权究竟发挥了多少作用,恐怕在多数情况下象征意义更浓,五种治权中唯一没有萎缩的只有行政权了。也就是说,南京政府所有的国务活动都是在撇开合议制的国民政府(委员会),而由行政院长负责,这与责任内阁制又有多少区别呢?
(三)内阁制下的总统制——内阁制的走形
第二个时期亦即宪政时期的政体,按照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其中央制度虽然并非完全合于内阁制,但是在正常体制的运作下则基本符合内阁制的原则和精神:行政院是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长虽由总统提名,但须立法院同意任命;总统在行使缔约、宣战、媾和、大赦、宣布戒严、发布紧急命令等重要职权时,要由行政院会议议决,其命令要行政院长副署。行政院不是向总统而是向立法院负责。但是如果仅仅据此断定南京政府这一时期实际运作的政体是责任内阁制显然是错误的。《中华民国宪法》在确立内阁制的同时又赋予总统两项特殊权力:一是总统对于院与院之争执,得召集有关各院长会商解决。二是立法院不赞成行政院的重要政策而作决议,或行政院对于立法院决议的预算案、法律案等认为窒碍难行,经总统“核可”,行政院可将决议案退还立法院复议。第一项特权使总统可以解决院与院的争执为手段,影响和最终操纵五院。而第二项特权使总统对行政院的控制大大加强。也就是说,总统可以“核可”,也可以不“核可”行政院的复议要求,什么样的“核可”,什么样的不“核可”,法无限制而权在总统。如果行政院处处违背总统的意志,那么它得到总统“核可”的优遇从常理上说是不存在的。因此宪法所规定的行政院向立法院报告的施政方针,必须首先向总统报告并得到总统的同意才有可能报告立法院。从而使宪法规定的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变为实际上向总统负责。
如果按照惯例,内阁制下的总统只是国家的元首,不兼任行政首脑。但是当国家遇有紧急变故时,一般都为总统留下了紧急处分的权力亦即所谓“良性独裁”权,使总统能够及时予以处置,确保国家与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当然该项权力也要受到立法的约束。对此《中华民国宪法》第39和43条分别作了类似的规定:“总统依法宣布戒严,但须经立法院之通过或追认,立法院认为必要时得决议移请总统解严”;“国家遇有天然灾害、病疫或财政经济上有重大变故须为紧急处理时……,总统依紧急命令法,为必要之处置,但须于发布命令后一个月内提交立法院追认。如立法院不同意时,该紧急命令立即失效”[⑤]。不可否认,这些条文基本符合“良性独裁”的惯例,成为区别实际独裁的一个标志之一,从而也成为检验南京政府实际体制与否的试金石。正因为如此,所以1948年4月的“行宪国大”在宪法尚未施行就急欲去此障碍。最终《动员戡乱临时条款》解除了这种束缚:“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39条或43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⑥]。这样,总统就完全抛弃了立法的制约而为所欲为,从而彻底暴露了真正独裁之实。而内阁制又仅仅是条文而已。但令人疑惑的是,同是这些条文,当李宗仁代总统时,形势顿时大变,指挥不灵,调动不动,又俨然责任内阁的架式。
通观南京政府的两个时期,无论是在“训政”的“特殊时期”,抑或在进入“宪法轨道”后,其政体总是在表面不变的假象下,实际上是以法定政体为中线左右扭曲后的变形体制,因而留下的是一条弯曲不规则的轨迹。
三
本文前面已经说明,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宪法与权能分治仅仅是原则,至于政府的权能结构,孙中山并没有明确的规画,所以南京政府的政制政体与孙中山及其学说并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特别是政体的非常规变动尤其如此,可以说完全是南京政府的建立者和主导者自己意志的产物。蒋介石曾总结过:“我在去年(1949年——引者注)下野之后,经过半年的检讨认定我这次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建立制度。”[⑦]这话无不是对南京政府政制的否定,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从总体上看南京政府的体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在政府组织中一方面规定五院分别是最高的行政、立法、司法等机关,另一方面又在五院之上加个委员合议制的国民政府,使五院成为具体的执行机构,而不是最高权力机构。如果要使之成为名符其实的权力机构必须撤去由一名主席和若干委员组成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对此,南京政府的组织者无论如何是应该清楚的。可是明知如此,而实际非行,那么就只有一种解释了:为了某种需要。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南京政府的政体弹性可塑是必然的。因为从它建立时起,就留下了要在日后何时需要何时改变它的余地。即便是“神圣”的宪法颁布之后,这种余地依然存在。蒋介石一再认为:“一种良好的制度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民族的传统精神,二是时代的科学精神。”[⑧]就政治制度而言,中国几千年传统精神除了积淀日久的专制和独裁外还有什么更重要和突出的呢?从蒋的思想中不难理解,南京政府的政制中民族的传统精神与时代的科学精神都是不可缺少的。正是对时代科学精神的追求,所以有了诸如合议制、内阁制的条文。然而无论如何,“民族的传统精神”是第一位的,不管是实行合议制还是内阁制,它都顽强地表现了出来。
严格地说,单纯的分析南京政府的政体是不存在的。在国民党“以党御政”下,究竟是政府的体制在变,还是国民党的政策、人事在变,很难有明显的界限。五院加上国民政府(委员会)组成南京政府,即便是这种组织形式与政府的组织法相矛盾,但它也已经构成了完整的政府体系。然而它却如一个软骨巨人,离开了国民党的指导便寸步难行。而且全国性的政府要对一党的代表大会负责,那么冠以“国民”二字的南京政府是政府体系还是国民党的具体执行机构?既然如此,政府的体制已经失去了它实际的意义:党权决定着政府体制的常与变。当然完全否认国民党从军政、训政到宪政的过渡也存在着某种制度建设的因素,显然也是不尽符合事实的,但是在主观上看南京政府政体的变动则与此无关。
在南京政府公布的诸多法律及由此造成的政府组成部分关系和职能的变动中,有很多是令人困惑不解的东西。《训政时期约法》中,国民政府主席是实际上的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约法》可谓是国民党训政时期的根本大法,且第84条明文规定其他法律与约法相抵者自属失效。可是《约法》墨迹未干,修正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就将国民政府主席剥夺得一干二净,成为真正的虚位元首,而且这一规定一直生效了12年。12年后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要兼任国民政府主席,这一规定便立即失效。1930年11月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随即修正的政府组织法,将执行国务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改为国民政府会议,只负责议决院与院之间不能解决的事项,而将行政院长任主席的行政院会议改为国务会议处理国务。如此等等,统观这些事例,结合政体弹变的情况,诸如此类的似乎令人困惑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很简单也很清楚的原因,南京政府政体的变动主要的不是在进行制度上的探索和建设,而是军权、党权在握势力膨胀者贪图一人一时方便的结果和彼此争斗、妥协的产物,是常还是变都决定于当权者的需要,决定于需要者实力的大小。
注释:
①《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第2版,第494页。
② ③ ④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页。
⑤ ⑥《国民政府公报》1947年1月1日,1948年5月10日。
⑦ ⑧《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合编,“中华民国”五十七年,第3版,第1793页、1738页。
标签:国民政府论文; 孙中山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国民党主席论文; 历史论文; 国民党论文; 台湾立法院论文; 南京国民政府论文; 中华民国宪法论文; 组织法论文; 内阁制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