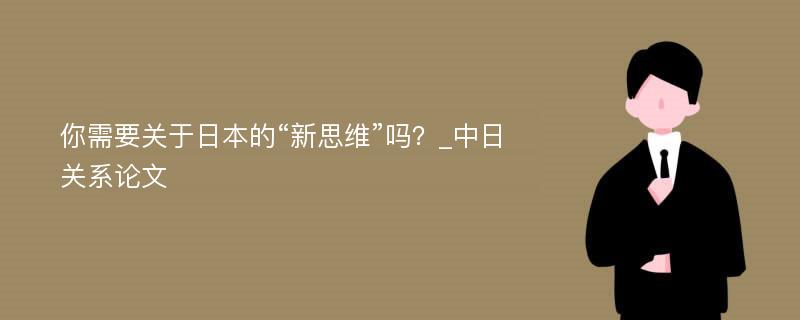
对日需不需要“新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思维论文,不需要论文,对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是一次特殊的会晤:5月31日,中日两国领导人在离双方国家数万里之遥的圣彼得堡,实现了今年第一次,也是中国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的首次中日高层对话。
这次会面的特殊意义在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自去年10月参拜靖国神社以来,中日关系陷入冷淡状态。新当选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先后会见了日本在野党社民党党首土井多贺子、民主党代表菅直人,以及自民党山崎拓、公明党冬柴铁三与保守新党二阶俊博三位执政党干事长,双方进行了深入交谈;而小泉访问北京的计划却搁浅。外电因此评价说,中日关系因“政权外交”出现僵局,而另辟“政党外交”渠道。
SARS、磁悬浮列车建设、新世纪中日关系、历史问题等等,胡锦涛和小泉进行的45分钟对话里,涉及内容相当广泛,然而,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协议达成。小泉在结束谈话时,再次提出希望推动首脑层次的交流,对此,胡锦涛以“相互努力”作答。
尽管如此,国内不少学者仍然认为,这次会面表明了中国新一届政府对日态度仍是趋于积极的。小泉不顾中国人民感情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内容,多次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本应“为此付出代价”,但中国国家领导人以大局为重而进行会谈,表现出中方的善意和务实精神。
日本舆论对双方领导人的会晤也给予高度关注。《东京新闻》在第二天的评论文章中称,这是“新型日中关系的开端”。
200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前一年,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
“新思维”与“外交革命”
中国和日本舆论界不约而同地对两国领导人会晤表示关注和热切希望,可见两国关系对双方仍是举足轻重。
但是,一衣带水的地理位置,纠葛多年的历史心结,越来越紧密的经贸关系,恩恩怨怨,浮浮沉沉,即便是从事美国问题研究的专家,也不得不承认,中日关系比中美关系更复杂,更容易拨动国民的神经。敏感多变的中日关系,会否给中国未来发展造成阻碍,更是引起不少专家学者的担忧和思考。
人民日报资深评论员马立诚,发表在《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上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使他成为众矢之的。他以游记见闻和史料回顾的方式,重新审视中日关系,提出把历史问题放在次要位置的“对日新思维”,引起学界乃至舆论界一片哗然。
事情还没有结束。
今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同样在《战略与管理》上,发表主旨类似于马文的《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一文,对“新思维”进行了更为系统的阐述。
文章开篇就指出,“中日关系中相当经久、广泛和深刻的紧张”,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中特别令人担忧和催人思索的问题。
鉴于此,时殷弘提出,中国首先要优化自己的有关战略和态势,为中国自己至关紧要的利益促进大幅度改善中日关系,大力尝试中日接近。
搁置历史问题,平衡日本经济需求,不公开担忧日本的“军事化大国”问题,加强与日本在东亚的政治经济合作,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5条,是时殷弘提出“尽可能避免或缓解中日之间‘安全两难’问题”的解决之道。他把这种可能超出日本政府和公众“预期”的政策改变,称为一次“外交革命”。
以给政府外交思路进行建言姿态出现的时文,很快引起了社会各界反响。尤其在日本,震动前所未有,媒体铺天盖地进行转载,舆论充斥猜测之声,认为中国政府对日思维将因此发生新的转变。时殷弘也因此受日本外务省力邀,于5月到日本进行短期访问。
“新思维”:如何争取利益最大化
事态的发展,也许是时殷弘始料未及的。
人民网日本版主编唐晖告诉记者,他主持的中日关系论坛,网友们就时殷弘一文反应颇为激烈;另一方面,他原想请一些日本研究方面的学者来就此进行探讨,但找了不少学者,都不愿意出面讨论此事。有学者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时文不值一驳,因而不想就此卷入争端中。
从日本归来,时殷弘感到了压力。各界的质疑之声,新闻媒体的不断追踪,包括一些海外媒体的造势……时殷弘选择了沉默,拒绝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6月8日,日本参议院通过“有事法案”的第三天,非常关注日本问题的时殷弘,首次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尽管日本人对历史问题的看法,仍然不能使中国人感到满意,尽管日本政治有右倾化的倾向,但是我们要考虑,我们是不是永远都无法接受一个现实,就是日本的政治作用在增大。”时殷弘不无忧虑地表示,40年来没能获得通过的“有事法案”日前以高票通过,是日本国内民众和民族的心态、政治右倾化、东亚乃至世界局势变化等多方原因造成的,而中国无法阻止,只能在适当情况下提高警觉,放眼未来,做好自己的战略应对。
他指出,中国政府表达对此的态度时,“是非常有分寸的”,与过去的激烈程度不能相比。时殷弘表示,与其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还不如在有分寸的战略警惕下,把精力放在加强自身建设上,同时以一个冷静的态度,来看待东亚战略局势变化。
现实主义是时殷弘认为自己写作《中日接近》一文的立论根基。
他认为,他与马立诚文章的区别,在于马是以一名记者充满感情的眼光和笔触,来探讨对日关系问题,不免掺杂主观情绪;而他那篇文章,前提是不用确定日本是好还是坏,归根结底一个问题:如何在两国关系中,争取中国利益最大化。
“正是因为日本出现了变化,我们自己出现了变化,中日关系的中心点,才必须由过去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历史问题,转到以战略为中心上来。”时殷弘解释,所谓“战略为中心”有两方面内容:第一,要防止中日两民族形成持久对抗,以致为中国的未来安全造成严重的隐患;第二,在中国国力上升、日本希望追求成为正常国家的情况下,中日要在很多战略问题上对话。
关于与日接近是否为了应对美国的疑问,时殷弘坦承,与日接近首先是为了争取中日关系正常化,而不是为了增加对美的外交或战略的筹码。
“就是没有美国,我们也需要调整对日政策。当然,如果你调整了,从长远来看,我们一定可以加强应对美国的地位。”时殷弘表示,今后50年,中国外交的主要问题就是美国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所以,为了中国更大的利益,应该学习正视现实,搁置一些问题。
日本问题专家:冷眼看“新思维”
“这是一厢情愿,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的表现。”对目前掀起的“对日新思维”思潮,绝大部分接受采访的日本问题专家,都做出如是评述。
北京大学历史系从事日本问题研究的王新生教授认为,在对外关系上,不仅要知道自己有多大实力,还得清楚对方在想什么。“不是说我们做出让步,日本就会答应的。一厢情愿反而容易造成被动,达不到目的。”
在他看来,中日两国虽是近邻,文化和一些习俗都相近,但两国仍存在诸多不同,不能用一个逻辑模式,把两国关系限定到一个框架里去。
王新生认为,中日两国国民有100多年的恩恩怨怨,由于近10年来经济发展上的反差,使双方国民心理都更加微妙,因而两国间出现摩擦和“政冷经热”的局面,是很正常的表现。“有了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这才是一个良性循环。所以不要把目前的现象看得过于悲观。任何操之过急的做法,试图来解决这种状况,是不现实的。”
远在日本讲学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金熙德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思维”最大的缺陷,就是脱离了当前日本的现实以及中日关系的实际,而试图采取矫枉过正的做法。
“如果政府加以采纳的话,其政策效果将是过犹不及。”金熙德解释说,“‘新思维’在主张搁置矛盾、实现中日和解这一动机上无可厚非,但‘新思维’大大低估了日美同盟的牢固性,低估了美国控制日本的能力和日本追随美国的意志,低估了日本对华防范心理,低估了日本鹰派势力的能量,低估了历史问题的复杂性。”金熙德分析,如果基于这些低估之上而放弃一切原有对日政策,无条件迎合日本的一切要求而不必要求日本的回报,其结果只会造成战略被动,最终能否出现“中日接近”局面,十分令人怀疑。
另外一方面,“新思维”也完全忽视了中国对日政策不能脱离中国国民感情这一重大前提。“好像日本的国民感情应当尊重,中国的国民感情就可以靠政府强行压住似的。”金熙德说,实际上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克制态度,是包括日本有识之士在内的世人有目共睹的,而中国民众中存在着强烈的情绪,这种情绪,不是某个人或某届政府可以说了算的。
许多专家还指出,事实上,中国在1998年推动签署“中日联合宣言”时,已初步定位未来中日关系,即与日本建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此后,中国身体力行,对日本友善而克制,并没在历史问题上过多纠缠。
“有关历史事件的真相问题,是日本政府在刻意推动,中国方面只是被动回应。这种情况下,再提搁置历史争端来促进双方关系,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王新生说。
国际关系学者庞中英日前撰文指出,加强中日关系是大家的共识,但是历史问题总是中日之间的最大干扰因素。中国确实需要长期巩固的、友好的中日关系,但是一厢情愿、简单化、急功近利,甚至缘木求鱼之所谓“战略”要不得。
中国:需要务实的思维
新加坡学者卓南生,长期在日本龙谷大学致力于中日关系方面的研究。他告诉记者,自马立诚、时殷弘发表了有关“对日新思维”方面的文章后,日本方面如获至宝,认为这种思维战略和他们的历史观相吻合,是发展符合日本人利益的新机会,于是利用舆论,极力引述两篇文章的言论,宣扬“新思维”。另一方面,日本却又没有对表示善意的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回应相应的善举,而是高票通过了“有事法案”,加快向军事大国迈进的步伐。
“日本和美国结成同盟以来,一直利用美国壮大其军事力量,达到其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目的。中国是日美的一个潜在对手,而‘新思维’轻易赞成日本的军事诉求,支持其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会,正好掉进了日本的战略陷阱。”卓南生委婉地表示,在研究一个问题时,既要看历史,更要看未来,不能闭门造车。
“新思维”可谓大大激起了日本舆论的兴趣。一些偏右媒体甚至鼓吹,这是新一届中国政府“投石问路”之举。在未来,中日关系“将发生巨大转变”。
6月5日,日本《读卖新闻》借采访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之机,打出“北京将改变对日本政策”的旗号。该报还特意指明,由于社科院是中国政府的直属研究机构,蒋立峰的见解“反映中国政府的意向”,“强烈暗示中国将接受小泉首相访华”。
蒋立峰所长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对《读卖新闻》的解读一笑了之,表示自己并没有那么多言外之意。“1972年的《联合公报》,1978年的《和平友好条约》和1998年的《共同声明》3个文件,已经把中日间的主要问题都讲清楚了,而历史问题只是其中之一,没有必要单独提出来说,做一个过分的强调。”
十六大报告曾提出中国今后的外交方针,归结为“与邻为善,与邻为伴”,这次胡锦涛访问俄罗斯,也曾向不少国家领导阐述这个观点。蒋立峰由此推测,这表明中国今后会在与周边邻国关系上付出更多努力,那么不排除对日本采取一些更为积极的做法,以使中日关系能够突破一些僵局,能够有更好更快的发展。
“但那也不能说,中国对日本政策就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外交政策是有连续性的,不可能有180度的大转弯,也许会作一些策略性的调整。”蒋立峰说。
“事实上,在冷战后,中日调整相互政策的过程中,中国的对日政策调整走在了先,而日本的对华政策调整则尚未跟上。”金熙德赞同中国应继续保持主动姿态,积极推动中日间相对薄弱的政治领域的战略对话和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以此相互逐步消除戒心,增进信任。“这将是一个长期的相互作用过程,而不会在短期内就实现决定性突破,也不会是单方面作出重大退让就可以得到良好效果。”
金熙德还建议,中国的对日政策,要坚持和强化1999年以来的对日重视路线,积极主动地推动双边关系和在地区与全球事务中的中日合作。
“每当发生‘历史问题’,不宜使这一问题影响中日之间其他领域的合作进展,采取‘政经分离’、‘分别解决具体问题’、‘不使一种政治摩擦点燃另一种政治摩擦’等做法,使两国在充分认清相互分歧的基础上,不断推动相互利益部分,使分歧部分在整个中日关系全局中所占的分量日益减小。”金熙德认为,在目前,启动和推动中日战略对话和军事交流,创造良好的政治、安全关系氛围,对21世纪中日实现战略和解和合作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对日政策的继续积极改进,当为中日关系不断发展下的顺理成章之事,而不是因为换了领导集体才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