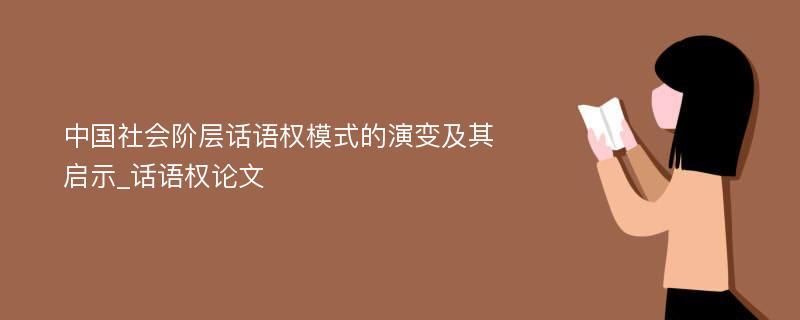
中国社会阶层话语权模式的嬗变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话语权论文,启示论文,社会阶层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129(2011)02-0011-05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考察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话语权状况、构建均衡阶层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回溯中国社会阶层话语权的发展史,不断总结经验得失,才能够真正实现资治通鉴。自秦汉以降,按照社会性质可以把中国社会发展史分为三个时期:封建社会时期、“中华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与此相应,中国社会阶层话语权的发展也经历三个阶段,呈现为三种典型的阶层话语权模式:中国封建社会阶层话语权模式、“中华民国”社会阶层话语权模式与二元社会阶层话语权模式。
一、中国封建社会阶层话语权模式
中国封建社会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其存在的基础,与此相应,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也呈现为鲜明的金字塔型:居于塔尖的是占总人口极少数的由君主、高级官吏以及大地主构成的统治者阶层,居于中部的是由中小地主、中下官吏、商人以及手工作坊主等构成的被统治者中的中间阶层,居于塔底的是佃农、手工业者、雇工等被统治者中的弱势阶层。赋予这种社会阶层结构合法性的宗法礼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宗法制度的作用下,国家政权与社会融合为一体——家国天下。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乡村自治的特点,但这也不能说明相对独立的、自治性社会领域的存在,原因只是由于当时统治技术的限制。并且这种自治也区别于现代民主意义上的“对抗性”的自治,而是国家在基层社会“大一统的延续”。在这种宗法礼治话语叙事的背景下,中国封建社会的话语权只能是统治阶层的话语霸权。
与宗法礼治话语叙事相呼应,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话语体系也论证了上述阶层话语权状况的合理性。儒、法、道的政治思想话语体系无不是在不同侧面为统治阶层提供统治策略、统治技术。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占据独尊地位,“他把先秦儒家的‘五伦四德’改造为‘三纲五常’……董仲舒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名教纲常精神实质上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正统”。[1]通过历代统治者不断地对儒家思想所做的一元化、政治化的符合自己统治的解释,统治阶层的话语权合法性也就具有了不证自明的合理性。当然儒家经典中也有很多“民本”思想,如孟子极为重民,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2]250。主张行仁政,他说:“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2]56荀子则把君民关系比作舟水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3]但这些思想的出发点不是为保障被统治阶层的权利,而是从维护统治阶层的统治出发来强调重视被统治阶层的意义。
除了上述的宗法礼治话语叙事与儒家话语独霸的文化体系的原因外,被统治阶层的阶层意识无法形成还与封建社会的户籍制度密切相关。从秦汉以来的户籍制度,无论是乡里制、乡保制还是保甲制,都是农耕文明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的强制制度,农民被分割在缺乏联系的一个个孤立的单元地域中,没有迁徙的自由,团结在一起是不可能实现的,更遑论形成共同的阶层意识,他们集体的话语沉默也就顺理成章了。但这并不说明被统治阶层的利益是被完全忽略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封建社会实行中央专制集权的君主的“超阶级”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世袭制的皇帝为了维护一家一姓的统治,皇帝及其统治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能够体察民意、照顾民生的。二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精神特质。秉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士大夫阶层,经世济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一种高贵的士大夫精神,区别于封建官僚的奴性与一般知识分子的狭隘。在一定程度上,士大夫阶层也起到了为民鼓与呼,维护江山社稷,沟通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作用,缓和了社会矛盾。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一个社会的生命力就在于内部各阶层的流动性。通过制度化的机制把下层精英流动到统治阶层,是几乎所有阶级社会的共性,中国的封建社会也不例外。与普通的被统治阶层成员的话语沉默不同,下层精英的话语表达与改变自身现状的愿望要强烈得多,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统治秩序是很难维持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人事制度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难题,除了世袭制、恩荫制等被用来保障统治阶层的利益外,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荐举制、隋唐至明清的科举制,为社会各阶层精英开辟了进入统治阶层的制度化渠道,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最为典型,是中国封建制度中后期最重要的人事任用制度。这种用封建正统话语叙事洗脑的社会各阶层精英,被整合进统治阶层,成为统治阶层话语霸权新的维护力量。科举制度的神话叙事也使得被统治阶层深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完全遮蔽了阶级剥削的真相,麻痹了下层人民。
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的主要特点是皇帝大权独揽、乾纲独断,虽然君权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相权的制约,但总体来看,君主中央集权的趋势是越来越强,这使得君权滥用难以避免。纵观中国历史,暴君的暴政数不胜数,非但被统治阶级的利益被摧残殆尽,甚至统治阶层的利益也难以保全。一旦最基本的生存都无法维持,基于生存本能的农民起义势必连绵不断,质疑统治阶级话语权合理性的异议就出现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由于当时农民的阶级局限性,这种异议仍是凤毛麟角,难以得到大规模回应。农民起义也往往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封建社会的阶层结构没有改变,统治阶层话语独霸的局面也没有丝毫变化。
在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末清初,也出现了部分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家。黄宗羲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君与民:谁为主人,谁为客人?他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4]2一切罪恶都源于君反客为主,“秦汉以来的君,无论是明君还是昏君,都‘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5]692-693“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4]5顾炎武批判了“家天下”观,“易姓改国号,仁义充塞,而至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6]他还主张通过“清议”和放权等措施来改变君主专制。龚自珍则从重人才的角度批判了君主专制,在《病梅馆记》中他批评了君主专制对人才的摧残;他还批判了误才、害才,而不能得到真才的科举制度。“在《与人笺四》中言道:‘今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间刻本如山海。《四书》文录士五百年矣,士录于《四书》文数万辈矣’。”[5]738这些批判不可谓不深刻,但是这些批判都集中在君主专制上,而不是对以君主为首的整个统治阶层的批判,还没有质疑赋予统治阶层话语权合法性的封建话语叙事;由于当时中国仍然是小农经济社会,没有市场经济的发展,他们批判的立足点也不是人权话语意义上的,还不能够揭示统治阶层剥削的实质。
中国封建社会阶层话语权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统治阶层话语霸权,封建的宗法制度、户籍保甲制度赋予这种差序阶层话语权模式以合法性的同时,也从意识与制度层面剔除了民众的话语表达、结社的危险。它给我们以重要启示:没有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没有封建等级制度的破除,没有权力的制约,没有基本的人权,没有旧文化的批判、新文化的产生,合理的阶层话语权是不可能形成的。
二、“中华民国”社会阶层话语权模式
“中华民国”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1927年)与南京国民政府专制时期(1927—1949年)。民国时期的社会阶级结构比较简单,主要有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地主阶级以及农民阶级。民国时期是大变革的时代,中国社会加速向现代化迈进,在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下,政治制度与人民大众的观念渐渐地发生着变化,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独特性质,民国时期的政治格局与社会阶级结构也处于剧烈嬗变中。因此,当时社会各阶级的话语权呈现出“新旧杂陈”、多样流变的状况。
民国时期的农村主要存在两大阶级:地主阶级与农民,由于政治格局的破碎,农村成为民国政府统治的薄弱环节,这一点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无大改观。这并不是说农村处于无政府状态,传统上沿袭的缙绅乡村自治有效地填补了这块空白,但这两个时期的乡村自治是有明显差别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乡村自治是封建的、自发的乡村自治,而南京国民政府专制时期的乡村自治是政府干预下的乡村自治,体现了民主思想。1928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专门召开民政会议,检讨了乡村自治的意义和运作方式,审议通过了《限期实行乡村自治案》,指出:“地方自治,为训政实施之基础……苏皖闽浙赣五省处交通便利之区,接近畿辅,尤宜树之风声,模范全国,事关训政基本工作,认为无可缓行。”[7]总体说来,这一时期的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基本无权利可言,乡村的话语权往往处于缙绅话语独霸中,但通常这也受习俗的约束。然而,在南京国民政府专制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与边区,农民的话语权状况却得到极大改善。民国时期乡村话语权的表达主要集中在缙绅身上,他们既是自身利益的代表,同时也是整个乡村利益的代表,在政治决策上特别是关于乡村的决策上起着主导地位。
民国时期的资产阶级大致可以分为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民国的不同时期,他们的社会阶层排序是有所变化的,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消长。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由于军阀官僚政府尚不能有效控制政局和经济,国民收入的分配是以市场化分配为主,工商业者相对独立,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高。当政府很弱而不能解决一些公共事务时,上层工商业者常挺身而出发表意见,甚至在战乱或经济动荡之时领导工商组织代行维持地方经济和社会稳定的职责。这一时期,政府法令奖励实业发展,且消除了封建专制的阻碍,又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列强无暇东顾,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短暂的春天,民族资产阶级的话语权是有很大力量的。在南京国民政府专制时期,由于官僚政府基本有效地控制了社会和经济,而官僚阶层的行为却没有受到应有的约束,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呈现出一种非市场化的倾向;又由于缺乏公平的二次分配,分配的不公趋于极端,官僚特权阶层通过种种手段攫取国民财富,特别是对民族工商业进行排挤、控制,民族资产阶级陷入窘境。[8]如中国近代著名企业家荣宗敬1932年一年从茂、福、申新系统的收入达到236.4万元,等于14070个纱厂工人的收入总和。[9]但至南京国民政府专制后期,中国最大的民营纺织企业申新纱厂连维持生产的流动资金都无法凑集,向国有银行申请购棉贷款手续繁杂,不仅缓不济急,而且要得到贷款很困难。[10]荣氏企业的生产节节下降,而1948年8月政府的限价政策更使其损失率达到一半以上。[11]这一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话语权受到官僚特权阶级的压制,他们由民族资本的大老板变成了官僚资本的伙计。
近代中国工人在经济、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为了争取自身的利益,罢工是一种必要的表达手段,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工人阶级处于自发形成阶段,工人通常是缺乏阶级觉悟与行动自觉性的。根据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资料统计,从1840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工人共发动经济性质的罢工533次,其中与机器大工业有联系的产业工人的斗争共285次,占经济罢工总次数的53.5%;城市手工业者和苦力工人等的斗争共247次,占总次数的46.5%。[12]1919年以前的工人罢工多是经济性质的,他们还没有自觉地去争取本阶级的话语权,因此罢工失败者,多成功者少。五四运动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转折点,标志着工人阶级实现了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此后中国工人运动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政治性,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人阶级结合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的话语权的影响力大增,成为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民国时期社会各阶层的话语权是严重失衡的,工人阶级、农民基本处于无权地位,小资产阶级的话语权也极其有限。虽然民族资产阶级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话语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彰显,但很快在民国后期沦为官僚资产阶级强势话语权的附庸。虽然民初的政治制度设计带有很强的民主政治形式,但是仅仅在上层政治领域搭建一个西方政治制度架构,这并不是民主政治。议会斗争在民国初期显得分外热闹,但是这种议会斗争所呈现的政党斗争仅仅是寡头斗争与政治分赃的折射,而不是民权、民意的代议,这些政治势力既不能代表广泛民意,也无意对民众进行组织动员,他们所争取的民众支持局限于城市中的上层市民、大商人以及学生知识分子,政党组织本身也很不完善,它们不是以长期的政治目标为政纲,而是以某一权势人物为核心,充其量只能算是政治俱乐部。剥开民国初期政治运作的热闹表象,看到的不是民主,而是军阀、官僚、大资产阶级之间利益争夺。因此,即使有一套民主制度设计,如果不能起到实质作用,也只能是骗人的噱头,不能真正实现社会各阶层话语权的均衡,民主政治更谈不上。至于民国后期,国民党一党专制、话语权独霸也就无法避免了。
“中华民国”社会模式给我们重要启示:其一,民主、均衡阶层话语权的形成,不在于搭建一个民主政治制度的空壳,而在于合理制度性安排——实质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民主程序与手段。其二,实践证明市场分配更有利于阶层话语权的均衡,因此,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更要防止官僚资本的滋生。其三,话语权的获得不是恩赐的,要通过本阶层成员自觉地、不断地斗争来取得,代表本阶层利益的政党或社团是阶层话语权实现的现代政治组织形态。
三、二元社会阶层话语权模式
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提出来的,他认为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普遍呈现出城乡有别的二元结构。经济结构的二元性本来是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过渡的必然现象,在世界各国,城乡有别也只涉及行政建制与辖区划分,市民或农民的身份只是一种职业或居住地的标识,并不存在一种行政上的身份管制或迁徙壁垒。但在我国却由于歧视性政策制度的安排,形成了特有的城乡隔离二元社会结构,这一概念最早由农业部原政策研究中心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课题组于1988年提出并详细论述的。所谓二元社会结构,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通过一系列分割城乡、歧视农民的制度安排而人为构建的城乡隔离的社会结构与制度体系。
二元社会模式的实质与核心在于强制性的居民身份制度,不同的身份享受截然不同的社会待遇,它是由一系列具体制度建起来的,即户籍制度、粮食供给制度、生产资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等,由此中国被切割成泾渭分明的两大块。政府人为地将全体公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形成农民和市民之社会地位完全不平等的制度体系,这在当今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构成发展中国家特有的中国式社会状态。这种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表现在权利保障和经济发展上天壤之别的城乡差距:一方面城市和市民享有各种特定权利和利益,另一方面农村和农民则丧失了一系列基本的平等权利和利益。
具体来说:其一,经济权利包括劳动权、休息权、社会保障权、同工同酬权等。在我国特有的二元社会模式下,农民的经济权利受到严重侵犯。剪刀差是二元社会中以农养工的代名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照搬苏联模式实行以农养工政策,人为实行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以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村源源不断地吸取巨额资金支持工业和城市的发展,这使得农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据测算,1954—1978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手中获取了5100亿元的巨额资金,1978—1991年,剪刀差累计已高达12329.5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生产总值的22%,也就是说农民将自己创造的1/5的财富无偿交给了国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剪刀差还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以上”[13]。剪刀差的存在与不断扩大意味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由20世纪80年代的1.8:1扩大到2002年的3.11:1……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之比为1.5:1,超过2:1的极为少见”[13]。近年来,虽然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增加农民的收入,但与因高昂的学费、医疗费、价格飞涨的农资等导致的开支剧增相比,农民经济平等权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经济权利的不平等对农民话语权的伤害是异常显著的,没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农民话语权也就没有了坚实的支撑。
其二,政治权利通常包括平等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自由权、出版自由权、集会自由权、结社自由权、游行自由权、迁徙自由权、人身自由权、批评建议权、申诉控告和检举权等。但我国农民的政治权利却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就迁徙自由来说,自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出台建立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来,农民的自由迁徙权事实上就被取消了,1975年《宪法》干脆取消了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权的规定,此后历次宪法修改都没有恢复此项规定;二元分离的户籍制度是农民“二等公民”地位的制度渊源,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户籍制度才有所放松。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来说,1953年的《选举法》对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同规定,即自治州、县为4∶1;省、自治区为5∶1;全国为8∶1。这个比例一直延续到1995年,新的《选举法》才统一把各级人民代表选举中的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数改为4∶1。从历届全国人大的构成来看,第一届有农民代表63人,占5.14%;第二届67人,占5.46%;第三届209人,占6.87%;第四届662人,占22.9%;第五届720人,占20.59%;第六届348人,占11.7%;第七届与工人代表合占23%;第八届280人,占9.4%;第九届240人,占8%。[14]这显然与农民占总人口80%的比例不相称。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农民也缺乏统一的群众性社团,如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私营企业主也都有个体协会,这些群众性社团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本阶层成员的利益。但是对于农民来说,由于政治参与渠道的缺乏,人口众多以及经营的分散性,使得各种坑农、伤农、卡农的事件不断发生,各种摊派、集资名目繁多,虽经中央三令五申,农民负担问题却难以得到有效解决。显然,没有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农民话语权在政治层面上的影响力就无从谈起。
其三,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社会权利主要有获得物质帮助权、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等,然而在二元社会模式中,中国农民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却是普遍的。就社会保障权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1世纪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只属于城市户口的居民,农民既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也没有工伤事故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就受教育权来说,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差别巨大,长期以来,“城市中小学教育基本是国家投资;农村中小学教育基本是以摊派的方式由农民自己投资。一部分大中专院校录取分数线,农村考生竟被要求程度不同地高于城市考生”。[15]这实质上是对农民平等受教育权的剥夺。以就业权来说,政府统计层面上的就业指的只是城市居民的就业与失业,人口众多的农村剩余劳力根本不在政府统计的就业率或失业率的范围内。此外,在自由迁徙权、健康权、社会安全权等方面对农民的不平等也普遍存在。
正是二元社会的制度性障碍造成了中国农民的弱势,这也是农民话语权虚弱的根源。在当今世界上,反歧视或不平等对待已经成为文明社会的共识,因此在消除对农民的歧视和实现农民平等权利的进程中,每一个农民是否与全体国民一样享有宪法规定的平等权利,每一个农民是否得到政府的平等关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也是检验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管理水平提高与否的重要标志。
综上分析,中国阶层话语权模式嬗变的重要启示在于: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均衡阶层话语权萌生的前提,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是均衡阶层话语权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民主制度下合理阶层话语权博弈制度的搭建是均衡阶层话语权健康成长的制度性保证,旧文化的批判、新型政治参与文化的塑造是均衡阶层话语权发展完善的文化环境,橄榄型阶层结构的形成则是均衡阶层话语权形成的关键条件。因此,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民文化,精心培育和保护社会中产阶层,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程,构建现代化服务型政府,唯有如此,均衡阶层话语权才能够得以实现。
标签:话语权论文; 二元经济结构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官僚资本论文; 二元结构论文; 封建社会论文; 南京国民政府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