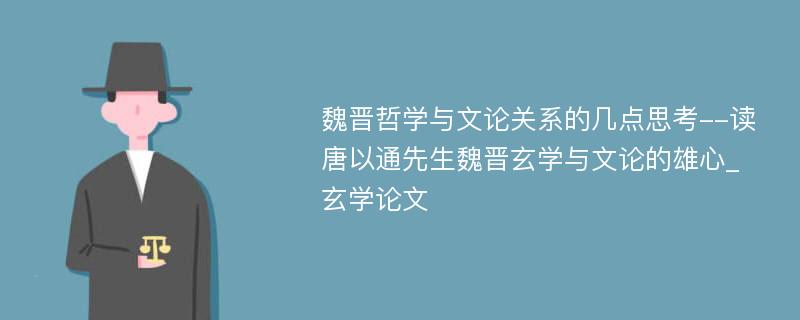
关于魏晋哲学与文论关系的一些思考——读汤用彤先生《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志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魏晋论文,文学理论论文,文论论文,玄学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当然应该结合其哲学思想背景,以求得深一层的了解。魏晋时思想界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崭新的面貌,无论文学思想还是哲学思想都是如此,因此学者们对于这一时期二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感兴趣,努力加以探讨。然而笔者在学习诸家论述的过程中,感到存在一些疑惑,颇觉有所质疑问难,以求贤达之教诲。
汤用彤先生有《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①,发表既早,影响亦大。汤先生是中国古代哲学史、宗教史研究的大师,其学术成就具有奠基的性质,实乃难以企及之高峰,我辈深受其沾溉。先生知识之广博、见解之深湛,真是令人高山仰止。但读先生该文之后,也觉得有难解之处。乃不揣谫陋,以之为例,略志所疑如下。
(一)
汤先生此文,首先声明其所欲论者,并不在于文学的内容方面,不在于诗赋内容、情思所受玄学的影响,而在于“论文”之作,在于时人对文学之基本看法与玄学的关系。“魏晋玄学之影响于文学者自可在于其文之内容充满老庄之辞意,而实则行文即不用老庄,然其所据之原理固亦可出于玄谈。”②笔者也正是对于魏晋文论之原理“出于玄谈”这一方面感到有所疑惑,至于玄学影响于文人心态、文学创作,那并无异议,也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汤先生认为,魏晋玄学的根本性论题乃是本末有无之辨,而其治学的新眼光、新方法则是言意之辨。魏晋贵无之学以“无”为宇宙万物之本,它是抽象而不可言说、只能以意体悟之本体。欲把握此本体,既不能不透过言,又不能拘于言,必须领悟言外之意。汤先生又认为,凡思想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其各种文化活动无不受其新理论、新方法之陶铸而各表现出新的特质,魏晋时期的文学理论也是如此。汤先生说,魏晋文学原理“出于玄谈”,“魏晋南朝文论之所以繁荣,则亦因其在对于当时哲学问题有所解答也”。③汤先生据此而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论有两方面重要内容:其一,探讨文之本质。“宇宙之本体为一切事物之宗极,文亦自为道(明按:即指本、无)之表现。”④其二,探讨如何方能找到适当的方法,以表现此宇宙本体(或云“通于天地之性”、“感受生命和宇宙之价值”等⑤);其方法即在于求“言外之意”。
汤先生引用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和《隐秀》等对上述观点加以论证。而笔者对其引用、论证存在一些疑问。
关于《典论·论文》。曹丕云:“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汤先生从两个方面阐释这段话:第一,从文章体裁说,“所谓‘本’者即‘文之所为文’,‘末’者为四科。”第二,“就为文之才能说则有‘通才’,有‘偏至’,‘通才能备其体’,而‘偏至’则孔(融)、王(粲)、徐(幹)、陈(琳)、阮(瑀)、应(玚)、刘(桢),此七子以气禀不同而至殊,因才气不同而分驰。……因有‘偏至’,故‘文人相轻’,此非和平中正之道也。惟圣人中正和平,发为文章可通天地之性,则尽善尽美也。”⑥
对此阐释,窃有疑焉:关于第一点,汤先生说“本”就是“文之所以为文”。⑦那么,“文之所以为文”是什么意思呢?通读《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可知汤先生所谓“文之所以为文”,就是说文乃道(本体)的表现,文之功用、性质,就是表现道。好的文章,能够体道,能够表现天地之自然,表现“对生命和宇宙之价值的感受”。⑧这就是文章之“本”,它表现于各种体裁的文章之中,正如道体现于万事万物之中。“本”是唯一的,各种体裁的文章之中的“本”都是同一的,故曰“本同”,正如道是唯一的,万物中的道都是那个作为宇宙本体的道。汤先生认为,魏晋文论受哲学影响,此即一例。但我们想,曹丕的原意真是这样吗?依笔者之见,曹丕说本同末异,大约是说:凡是文章,都起于连缀文字以达意,但发展到后来,乃形成各种不同的体裁。如此而已。曹丕这个观点,来自对文章发展历程的总结,未必是受玄学本末体用之说的启发。所谓本同末异,原为汉人常用语。如王符《潜夫论·志氏姓》:“或复分为古氏、成氏、堂氏、开氏、公氏、冶氏、漆氏、周氏。此数氏者,皆本同末异。凡姓之离合变分,固多此类。”谓同一姓氏,后来衍化成若干不同的姓氏。又,《隶释》卷五《汉成阳令唐扶碑》云:“赫赫唐君,帝尧之苗。氏族不一,各任所安。本同末异,盖谓斯焉。”是说尧之氏族分化迁移。又,荀悦《汉纪·元帝纪论》曰:“杨朱哭多歧,墨翟悲素丝,伤其本同而末殊。”一条路分歧为数条,一种白色染成不同的颜色,故曰本同末殊。又,《三国志·魏志·臧洪传》载臧洪答陈琳书:“悲哉!本同而末离。努力努力,夫复何言!”臧、陈二人皆广陵郡人,原有“婚姻之义”、“平生之好”,后来趋舍不同,遂相离绝,故曰本同末离。凡此诸例,就时代言,均在魏晋玄学有无本末之辨以前;就内容言,均未见有何哲学意味。曹丕所言,也就是论文章体裁而已,从其上下文语言环境看,都很具体,丝毫未曾论及文之本原为道、文是道的表现之类,为何一定要用哲学上的本末体用关系加以解释呢?关于第二点,曹丕的意思本也很明白。“通才”就是指各体文章都很擅长的人,与“圣人”不是一回事。而汤先生将“通才”与“偏至”的对立关系,转化为“中正和平”与“文人相轻”的关系,中正和平者乃是圣人,然后进一步说唯圣人“发为文章可通天地之性”,于是似乎曹丕之说又体现了本末有无的原理:圣人体道,“通天地之性”,是本;“偏至”者“非和平中正”,是末。这样转换的依据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要将曹丕之说与哲学思想背景相联系,那么联系到东汉以来的人物品藻风气及其理论,那是恰当的、自然的;一定要联系到本末有无,就觉得费解。
《典论·论文》又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汤先生对此解释道:“年寿有限,荣乐难常;而文章为不朽之盛事,或可成千载之功。如欲于有限时间之中完成千载之功业,此亦与用有限之语言表现无限之自然同样困难。然若能把握生命,通于天地之性,不以有限为有限,而于有限之生命中亦当可成就‘不朽之盛事’也。”⑨这还是说,好的、理想的文章能以有限之语言表现无限之道,其作者也就是能“把握生命,通于天地之性”的人,这样的文章、这样的作者,方能不朽。汤先生的这一解释,与他所说“文之所以为文”是一致的。但是曹丕的话里似乎看不出有这样的意思。“把握生命,通于天地之性,不以有限为有限”,陈义甚高,但如果结合文章写作、文学创作的实际看,林林总总、内容极其丰富、用途极为广泛的作品(包括奏议、铭诔等实用性文章),似不可能都做到“通于天地之性”云云,也不需要都做到“通于天地之性”吧。似也不能说凡没有这样做到的就都不是好文章,不能传世不朽吧。而且,究竟怎样的文章算是“把握生命,通于天地之性,不以有限为有限”呢?我们希望能举出实例来加以说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几句,受到闻一多先生激赏,称之为“更夐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⑩也许这可以说是通于天地之性的体道之作吧?闻先生举出了实例,所以容易明白。但这固然是佳作,却未必所有作品都得如此才称得上佳作吧?如果那样,文苑翰林岂不太单调了。事实上也不可能那样。闻先生也不曾将此作为衡量一切作品的标准。
下面再看陆机《文赋》。
汤先生说:“万物万形皆有本源(本体),而本源不可言,文乃此本源之表现,而文且各有所偏。文人如何用语言表现其本源?陆机《文赋》谓当‘伫中区以玄览’。盖文非易事,须把握生命、自然、造化而与之接,‘笼天地(形外)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文当能‘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以求音’。盖文并为虚无、寂寞(宇宙本体)之表现,而人善为文(善用此媒介),则方可成就笼天地之至文。至文不能限于‘有’(万有),不可囿于音,即‘有’而超出‘有’,于‘音’而超出‘音’,方可得‘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文之最上乘,乃‘虚无之有’、‘寂寞之声’,非能此则无以为至文。”(11)
汤先生这里仍然强调文乃本体(道、无)之表现;此外,提出为表现此本体,作者“须把握生命、自然、造化而与之接”,于是其文乃有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先生认为《文赋》体现了这样的文学思想。笔者亦窃有疑焉。
汤先生于《文赋》“伫中区以玄览”之“玄览”,似解释为“把握生命、自然、造化而与之接”,亦即体道、悟道之意。陆机有此意否?学者们是有不同见解的。笔者之见,以为陆机并无此深意。“玄览”一语,首见于《老子》十章“涤除玄览,能无疵乎”,可以认为是有体道、悟道意味,但汉晋文献,并不都这样运用。张衡《东京赋》:“睿哲玄览,都兹洛宫。”曹植《卞太后诔》:“玄览万机。”玄览都只是深远地观察、了解、思考之意。当然,也有含有悟道之意的例子,如《易·系辞上》“阴阳不测之谓神”韩康伯注:“不思而玄览,则以神为名。”东晋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乃悟幽人之玄览,达恒物之大情,其为神趣,岂山水而已哉?”总之,“玄览”一语,仍须就上下文语言环境决定其含义,不可因其出于《老子》,便一概以为悟道之意。《文赋》此句,下启“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数句,显然是说深远观照自然景物,引起伤春悲秋、感叹时光流逝种种情绪,并未显言触发生命、宇宙之感慨。伤春悲秋乃文人常态,也常常是文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契机,但它可能进而引起某种宇宙意识,也可能并不引起。陆机此处只是举出作为经常引起创作冲动的契机之一(另一契机为“颐情志于典坟”即阅读典籍文章),我们看不出其中含有作者应该体悟作为宇宙本体的“道”、必须悟“道”、必须“把握生命、自然、造化而与之接”之类意思。不但此处,整篇《文赋》都看不出此类意思。《文赋》谈文章利病,谈得很具体,没有形而上的意味。其所论来自鉴赏、创作的体会,而不是来自玄学清谈。钱锺书先生认为陆机“只借《老子》之词”,而反对“牵率魏晋玄学,寻虚逐微”。笔者赞成此种意见。(12)
“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两句,“虚无”、“寂寞”确是道家、玄学用语,但这里也只是借用而已。“伊兹事之可乐,固圣贤之所钦。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联系上下文,这两句是说文学创作乃一“无中生有”的过程。本来无所见、无所闻,然而通过微妙的构思,乃形诸文辞,闻诸吟咏,竟成为可见可诵之文章。此两句连下两句,都是叹美写作之神奇,叹美作家之创造力,那也就是“兹事之可乐”的可乐之处;其中也看不出表现宇宙本体之意。至于“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两句,也不过是形容运思作文时,天地万物均可由我播弄,笼于文内,也并无笼取“形外”之本体置于“形内”之意。
汤先生又说以“有”表现了“无”,即超越具体之“有”表现无限之“本体”的作品,便有“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这样定义“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有其特殊内涵,与人们一般论文章、论文学时所指实不相同。此点留待下文再谈。
最后看刘勰的《文心雕龙》。《文心雕龙·原道》谓文源于道,文是道的体现。此“道”乃宇宙本体,而并非如后世“文以载道”那样,专指儒家经世之道,然而也包括儒道,因为儒道当然也是宇宙本体的表现。将道家、儒家打成一片,正是玄学的特点。若要举出古代文论中论述文之表现宇宙本体的例子,《原道》确是最恰当不过。不过汤先生因《原道》有“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之语,《明诗》有“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之语,便认为《原道》所持为“文以寄兴”的观点,认为刘勰“以‘文’为感受生命和宇宙之价值,鉴赏和享受自然”(13),这却又令人费解。“自然之道”和“莫非自然”之“自然”,都是“自然而然”、“必然如此”、“本来如此”之意,不是表示道、表示宇宙本体的那个“自然”。事实上刘勰并不认为文章都是“寄兴”的,都是“感受生命和宇宙之价值,鉴赏和享受自然”的。对于文章宣扬儒道的政治教化作用,刘勰也充分肯定。《宗经》称经书是“恒久之至道,不刋之鸿教”,《序志》称“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都清清楚楚地表明刘勰重视文章的政教功能。还有,汤先生说“文以寄兴”的观点“为美学的”,“是情趣的,它是从文艺活动本身引出之自满自足,而非为达到某种目的之手段”,与“文以载道”的实用的观点相对立。对此我们表示同意,但说寄兴之文便是“以‘文’为感受生命和宇宙之价值,鉴赏和享受自然”,也就是说寄兴之文便是表现宇宙本体的“至文”,也还是费解。因为“寄兴的”、“情趣的”、“美学的”作品也是多种多样的。同是嵇康的《赠秀才入军》组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固然可说是“感受生命和宇宙之价值”,但“仰慕同趣,其馨若兰。佳人不存,能不永叹”那样的怀人之思、“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那样的人物形象描绘,也是“美学的”、“情趣的”吧,却恐怕不能用“感受生命和宇宙之价值”来概括。汤先生将文学观点区分为“实用的”、“美学的”两大类,很对,但说“美学的”就是“以‘文’为感受生命和宇宙之价值,鉴赏和享受自然”,是否不够全面?事实上刘勰等六朝文论家也并未做过这样的概括。大约先生之意,认定六朝论者持“文”为宇宙本体之体现的观点;而如何才算是体现宇宙本体?毕竟太抽象了,于是具体化为“感受生命和宇宙之价值,鉴赏和享受自然”之类吧。但林林总总的文章著述、文学作品,似乎很难笼统地全都概括到“感受生命和宇宙”、“享受自然”里面去。
《文心雕龙·隐秀》也是汤先生十分重视的篇章。《隐秀》云:“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隐以复意为工。……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汤先生对“隐”的解释是:“虽言浅而意深,言有限而意无穷”,“‘得意’于言外”,“所寻觅之充足的媒介必当能通过文言(明按:即文辞)以达天道,而非执著文言以为天道”。(14)言浅意深、言有限意无穷容易理解,“达天道”则又觉费解。为何能表达言外之意就是“达天道”呢?那些未说出来的意可能多种多样,似不能用“天道”来加以概括。依笔者的理解,刘勰所谓“隐”类似于汉儒阐释《诗经》时所说的“兴”,即所谓“托事于物”。(15)例如东汉郦炎《见志诗》之二的开头:“灵芝生河洲,动摇因洪波。兰荣一何晚,严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泰山阿。”其言外之意是慨叹文士托身非所、生不逢时。又如颜延之《秋胡诗》首章开头:“椅梧倾高凤,寒谷待鸣律。”言外之意是说男女婚嫁前充满相思、期盼。如此之类,所寄托的意思是多种多样的,不能统言之曰“天道”吧。刘勰实未曾这样概括过。汤先生对刘勰言“隐”是十分重视的。他说“意在言外”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所讨论的核心问题,而《文心雕龙·隐秀》为此问题作一总结。但如果我们承认所谓“隐”,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多样性,那么就会觉得汤先生关于“隐”就是“通过文言以达天道”的结论是令人费解的。
现在再回过头来,探寻汤先生关于魏晋南朝文论的总的思路,似乎是这样的:这个时期的文学理论受玄学的深刻影响,相对应地有两方面的重要内容:其一,探讨文的本质。文与任何具体的事物一样,是道的表现,道与文是本末、有无、体用的关系。本与末、有与无、体与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融合无间的,因此文之体道,就是表现人与道亦即与天地宇宙本体的融合,表现“神思”与“天地自然接”。这样的文为“至文”,它是审美的而不是实用的、功利的,是“寄兴”的、“情趣”的而不是“载道”的。其二,道、本体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因此要写作表达道、表现与天地宇宙本体相融合的“至文”,就必须运用语言而不拘限于语言,要追求“隐”、“意在言外”的表达效果。而笔者的疑问,主要在于:魏晋南朝文论是否具备上述内容?上文已就汤先生所引到的曹丕、陆机、刘勰的一些话语,表示了不同的理解,下面再综合地表述一下自己的想法。
(二)
第一个问题:关于文的本原问题。
魏晋南朝文论认为道是文的本原,文是道的表现,此点毫无问题。这确实是魏晋玄学熏陶的结果。但是,魏晋南朝文论有没有由此而认为文章必须“传达天地自然”(16),表现与道相融合方为“至文”呢?没有。《文心雕龙·原道》大谈其道,并不是为了强调文必须表现人与“天地自然接”,必须表现人与道的融合。在刘勰看来,一切文章著述,包括儒家经典、实用性文章,当然也包括“感受生命和宇宙之价值,鉴赏和享受自然”的寄兴的、情趣的诗文,统统都是“道”的体现。刘勰的目的其实不过是:1.借谈论“道”以抬高文的地位,说明文之存在的必然性(文章是宇宙本体“道”的产物,地位岂能不高尚);2.借此说明文章应该注重文采(天地万物都具有美丽的文采,乃“道之文”,文章必也如此);3.借此提出文章应该在写作方面向儒家经典学习(“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儒经是体现道的最高典范)。《文心雕龙》以《原道》为首,虽然在哲学上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但就文论而言,是第一次谈得如此完整、系统,构思巧妙,辞采美丽,因此深得人们欣赏,现代研治古代文论、古代美学的学者也心折于它的美学意味。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帽子、引子,所述原理并无贯彻全书、指导写作的意义。汤先生因篇中有“自然”字样,遂云“文章当表现人与自然合为一体”,其实刘勰并无此意;又因刘勰倡原道、征圣、宗经,遂云“圣人中庸之极,无所不能;经亦平淡中正,无所不容”(17),盖以道家、玄学所说的“本体”的性质形容儒家圣人与经典,但刘勰也从无类似的表述。
《原道》只是一个引子,或者说拉起的一面旗帜,在刘勰的文学思想中,并不占多么重要的地位。这里想引用钱锺书先生的一段话:“简文帝《答张缵谢示集书》:‘日月参辰,火龙黼黻,尚且著于玄象,章于人事,而况文词可止,咏歌可辍乎?’按卷一二(指《全梁文》)简文帝《昭明太子集序》:‘窃以文之为义,大矣远哉’一节亦此意,均与《文心雕龙·原道》敷陈‘文之为德也大矣’,词旨相同,《北齐书·文苑传》、《隋书·文学传》等亦以之发策。盖出于《易·贲》之‘天文’、‘人文’,望‘文’生义,截搭诗文之‘文’,门面语、窠臼语也。刘勰谈艺圣解,正不在斯,或者认作微言妙谛,大是渠依被眼谩耳。”(18)确实,魏晋文论内容非常丰富,其受玄学影响而以道为文原的观点,并不占重要的地位。笔者十分赞同钱先生的意见。
第二个问题:言与意的关系问题。
《周易》、《庄子》中已经谈到这一问题,而言意之辨、言能否尽意在魏晋清谈里尤为人们所感兴趣。玄学家王弼、郭象在阐释经典时,为了突破旧说的限制,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思想,提出了“得意而忘象”(19)、“忘言以寻其所况”(20)的原则,从而使寻求言外之意这一命题深入人心。王弼、郭象所说的“意”还是实在的、可以言传的,只不过为了解此意便不能拘限于眼前之言,必须探寻言外之意而已。至于荀粲提出的“象外之意,……固蕴而不出”(21),所说的“意”其实是指道家之“道”(宇宙本体)而言,那当然是玄虚的、只能体悟而不可言传的。
魏晋文论中谈到言、文与意的关系,谈到言外之意时,有哪些情况呢?《文心雕龙·隐秀》所谓“隐”、《文心雕龙·比兴》和钟嵘《诗品》所谓“兴”(也就是汉儒解释《诗经》时所举六义之一的“兴”),都是要求看出字面以外的意思,但那“文外之意”还是质实的,是可以说明白的,只是作家没有直说罢了。上文已经举过例子。此外还有一种情况:作者并未在作品里寄托什么别的意思,但读者读了之后,总觉得余音袅袅,似乎被笼罩在一种境界、气氛、情味里,觉得有余味,却又说不明白。《文心雕龙·定势》载刘桢语:“使词已尽而势有余。”《晋书·文苑传》载张华称赞左思《三都赋》云:“读之者尽而有余。”《世说新语·文学》载阮孚摘句嗟赏郭璞诗句“林无静树,川无停流”曰:“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颜氏家训·文章》载萧纲、萧绎称赞王籍诗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为“文外断绝”,又载南朝人士欣赏萧悫诗句“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称其“萧散”。李善注曹植《七哀》“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引前人语:“文外傍情。”这些例子,表明魏晋南朝读者已体会到那种虚灵的“言外之意”。那与刘勰所说的“隐”是不一样的。这两种情况、两种“言外之意”,似都不能概括为体现“道”,体现宇宙本体。
上述魏晋南朝文论中的这两种情况,都是在阐释、鉴赏时寻味言外之意,那是不是受玄学言意关系讨论的影响呢?笔者认为,即使受到一些影响,但主要还是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逐步发展的结果。类似于《诗》六义之“兴”的那种写法,即刘勰所谓“隐”的写法,主要是受汉儒解释《诗经》和《楚辞》的影响。至于人们之所以能体会到那种虚灵的“文外”之意趣,与作品描写风景、场景能够做到逼真、宛然在目,能够引人入胜,大有关系。那种审美趣味来自审美的实践,绝非能由某一哲学命题推衍而得。玄学家强调“忘言”,诗文欣赏恰恰不能忘言。必须仔细品味作家运用语言文辞所描画的情景,深入其中,才能体会到那种“言外”的韵味。而且,这种体会作品的虚灵的“文外”意趣的表述,在魏晋南北朝为数甚少,因此只能说是那种文学趣味的萌芽而已,更不曾提升到某种理论的、原则性的高度,与汤先生所说“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实以‘得意忘言’为基础”,恐怕相去尚远。
有没有显然受玄学讨论言意关系影响的例子呢?有的,多见之于谈论写作、言及如何用言辞进行表达的场合。如陆机《文赋》:“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又:“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盖所能言者,具于此云。”又陶渊明《饮酒》之五:“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又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当其冲豫自得,信有味焉,而未易言也。”又康僧渊《代答张君祖诗序》:“省赠法頵诗,经通妙远,亹亹清绮。虽云言不尽意,殆亦几矣。”又谢灵运《山居赋序》:“意实言表,而书不尽。遗迹索意,托之有赏。”其赋中自注也说:“此皆湖中之美,但患言不尽意,万不写一耳。”又《文心雕龙·神思》:“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疎则千里。”“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凡此之类,几乎都是慨叹以语言文字达“意”之困难。至于所欲表达的“意”,则多种多样,绝不是仅指那种对于宇宙本体“道”的体悟。庐山诸道人的诗序里有“乃悟幽人之玄览,达恒物之大情,其为神趣,岂山水而已哉”的话,那么可说其所谓“意”里既有山水审美之乐,又有悟道之趣。陶渊明的两句诗也可作如是观,但陆机、刘勰则是泛说,谢灵运主要是说山水之美。从这些资料看,玄学言意关系之论对于文论的影响实在是很有限的。魏晋南朝的文论只是慨叹尽意之难,并没有解决如何以有限的语言文辞传达无尽之意的问题。作家们并不曾如汤先生所说的那样,因为玄学里的有无本末之辨,亦即有限与无限之辨(有、末是有限,无、本是无限),而想到用有限之“言”,表达无限之“意”。拿谢灵运来说,他的山水诗总是详细描述游历的过程,而且在描画之后,还要将自己的想法、体会直接写出来,唯恐读者不知,以至于作品往往显得冗长。这正是他“但患言不尽意,万不写一”的缘故,他还不懂得以少胜多。我们将六朝诗与唐诗比较,就会感到就含蓄有余味这一点而言,六朝诗实瞠乎其后(当然是就其总体而言)。即使是说理,王维《酬张少府》的“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杜甫《缚鸡行》的“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苏轼《百步洪》的“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回船上马各归去,多言哓哓师所呵”,何等耐人寻味、富于理趣!汤先生说:“魏晋文学争尚隽永”,(22)窃以为不然。魏晋清谈论辩或可谓“争尚隽永”;至于诗文写作,实还未达到自觉追求隽永的地步。先生又说:“依言意之辨,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王弼首唱得意忘言,虽以解《易》,然实则无论天道人事之任何方面,悉以之为权衡,故能建树有系统之玄学。”(23)但在笔者看来,在文学理论方面,似看不出玄学“得意忘言”、自觉追求言外之意的明显的影响。
(三)
从以上所述,笔者想到,研究古代哲学对于文论的影响时,似应思考如下几点:
首先,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想,对于其他文化、学术领域,包括文学创作和批评、理论,确实很可能产生影响。但此种影响表现在哪些问题上,影响的范围、程度如何,还是要实事求是地加以估量。哲学中的热点,未必就是文学理论中的热点;哲学思想的核心问题,未必就成为文学理论中的重要问题。同时,哲学思想对不同文化领域的影响,可能是不平衡的。
其次,考察、研究此种影响,应从文学本身出发,尽可能完整地搜集资料,尽可能准确地理解这些资料,然后看它们与哲学思想的关系如何。亦即应该从文学到哲学,不应从哲学到文学,不应先入为主地认定哲学必然发生重要影响,然后去寻找一些哲学观点在文论中有何表现。应充分尊重文学的独立性,注意文学自身的特点、特殊的规律。研究文学与哲学的关系,首先还是要对文学本身有尽可能详尽深切的了解。文学理论归根到底是文学鉴赏、创作实践活动的总结。文学实践尚未达到某种水平,文学理论也不可能提出相应的概念、命题。
还有,尽可能准确地解释文论话语十分重要。许多时候文论中出现一些哲学的概念、用语,只不过是借用而已。借用当然也是影响的表现,但不应夸大。为了准确地理解文论话语,应该尽量结合文学创作、结合具体的文学作品加以研究,从理论到理论往往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业师王运熙先生反复强调,研习古代文论必须要多读古代文学作品,必须把批评史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结合起来。(24)笔者深切感到,先生的教导来自其亲身的体会,来自其长期的研究工作的实践,实在是非常重要。讨论文论与哲学思想的关系,也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
最后,应该说明:笔者认为在上文所说的一些具体问题上,看不出魏晋哲学对文论具有多大的影响,但并不是否认哲学与文论的关系。哲学是人们对于人生、宇宙的根本性看法。魏晋时期形成的新的哲学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士人的人生观、生活态度。上流社会相当一部分士人重本轻末、尚玄远轻实际的心态,有利于审美意识的发展。魏晋南朝文论与汉代主流意识——儒家的文论不同,它不再屈从、附属于政教目的,其功利性大为减弱,而审美方面、探讨文学内部规律的内容大为发展。这是魏晋南朝文论与汉代文论的重大区别,是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重要标志。就这一点而言,魏晋南朝文论的发达与哲学思潮可能有相当的关系——哲学通过士人心态而影响及于文学和文论。
注释:
①该文系由汤一介先生根据汤用彤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大的讲演提纲和在美国加州大学授课的讲义(英文)整理而成,最初发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1980年第1期,后附入《魏晋玄学论稿》。参见汤一介:《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附记》,《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245页。又参见汤一介、孙尚扬:《〈魏晋玄学论稿〉导读》,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导读”第36页。
②汤用彤:《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魏晋玄学论稿》,第195页。
③④⑤⑥《魏晋玄学论稿》,第195、197,197,204、206,203—204页。
⑦原文“文之所为文”,当是“文之所以为文”之意,大约误脱一“以”字。兹举两证:其一,汤先生《魏晋文学与思想》(讲演提纲)有如下表述:“本同而末异:本同——文之所为文;末异——四科不同——各有所偏。”又:“但文之所以为文,即表现在此四者之中。”(见《魏晋玄学论稿》,第126页)其二,《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有云:“刘勰之《文心雕龙》首篇为《原道》,论文之为文者更详,曰:……”(同上书,第205页)而汤一介、孙尚扬《〈魏晋玄学论稿〉导读》则云:“刘勰的《文心雕龙》对文之所以为文者有更详细、深入之探讨,首篇《原道》曰……”(同上书,“导读”第41页)相互对照,可见“文之所为文”、“文之为文”皆“文之所以为文”之意。
⑧汤一介、孙尚扬:《〈魏晋玄学论稿〉导读》,《魏晋玄学论稿》,“导读”第42页。
⑨(11)《魏晋玄学论稿》,第204、204页。
⑩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唐诗杂论》,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页。
(12)钱锺书:《管锥编》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181页。但钱先生关于《文赋》此处文脉的意见,笔者并不赞成,此不赘。
(13)《魏晋玄学论稿》,第206页。
(14)(16)《魏晋玄学论稿》,第208、208页。
(15)参见杨明:《刘勰论“隐秀”和钟嵘释“兴”》,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编:《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后收入杨明:《汉唐文学辨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17)《魏晋玄学论稿》,第206、207页。
(18)钱锺书:《管锥编》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392页。
(19)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09页。
(20)郭象:《庄子·逍遥游注》,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4页。
(21)《三国志·魏志·荀彧传》注引《晋阳秋》,《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20页。
(22)(23)汤用彤:《言意之辨》,《魏晋玄学论稿》,第36、24页。
(24)王先生在许多文章里都曾谈到这方面的问题,可参见其《谈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与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标签:玄学论文; 文学论文; 典论·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魏晋论文; 汤用彤论文; 文心雕龙论文; 读书论文; 原道论文; 刘勰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 魏晋时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