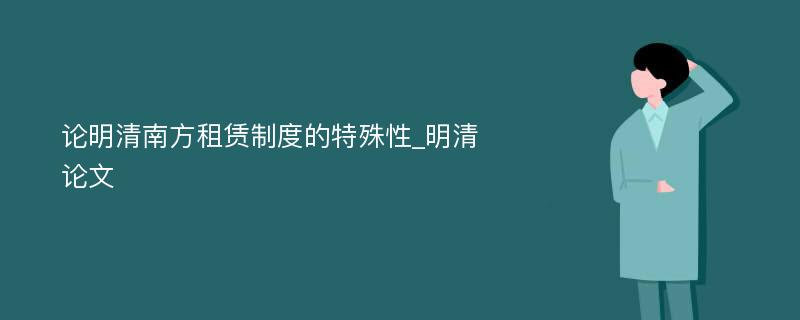
论明清南方租佃制的特殊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殊性论文,明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清时期,我国南方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并由此而引起其生产关系的某些变更:首先,在契约制的基础上较为普遍地产生了定额地租制。其次,以额租制为起点,较为广泛地实行了永佃制。永佃制是一种佃农意志的体现;是江南耕作经济持续向前的一条杠杆。广大佃农往往利用额租制和永佃制(包括一田二主和一田三主制)抵御田主的额外剥削,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并利用永佃制,努力改良农田,继续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不断地提高土地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增加其经济效益。
我国历代封建社会实行土地私有制,地主不仅以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任意加租,而且可以随时夺地别佃,使其无田可耕、危及生业。由于佃农没有长期的巩固的土地使用权,故民间同称:百姓生计操于富人之手。明清时期,土地集中,兼并严重,佃农队伍也在增大,主佃矛盾不断发展,冲突越来越严重。租地农民为求得生存而跟地主进行长期的斗争,特别是南方农民在斗争中往往获得和巩固了永佃权,并逐渐在一些地方形成了“一田三主制”的租佃关系。
一、南方永佃制与额租制的关系
所谓永佃,是指佃户长久承租一主之田。田主不得增租夺佃之意。此制开始于北宋年间,到明清时代,普遍盛行于南方各省,在中国租佃史上,曾产生过一定的经济影响和作用。《宋史·食货志》讲,北宋淳化五年(994),政府令:“凡州县旷土(荒田),许民请佃为永业,蠲三岁租,三岁外,输三分之一”。即人民开垦荒芜的官田,费了很多工本,以工本代为价换取了永佃权,据魏泰的《东轩笔录》记载:在宋时,曾有河南杞县人孙诚欲买近处李诚庄的一片腴土,因资力不足,无奈,只得向此田上的原佃农借钱,并许给佃户永佃权,使其“常为佃户,不失所业”。此处,佃户以借出之款免息为代价而取得永佃权。这都是个别的零星出现,属于永佃制的雏形。到了明清时代,永佃制盛行起来,并完全演变为一种单纯的价值关系(它与定额租制合而为一。而在宋代时并没有脱离分成租制,还有田租“输三分之一”的事例。)
以前学者曾对永佃制的产生原因提出过各式各样的结论:有的说是农民开垦地主的荒芜土地而付出了工本,佃农以工本为理由而取得了永佃权;有的说是由于农民向地主交了押租,农民以此为条件而获得了永佃权;或者认为是在前两种情况之外,用货币购买是永佃权产生的原因之一。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其实,定额租的出现和盛行是永佃制产生的根本原因,上述人们提出的几条是永佃制的形成过程中的各种表现形式或直接的导火索,即定额地租制应该是永佃制产生的大前提和小前提,各处的永佃制之产生情况都因地而异,何止十种百种,但一般都是以额租制为基本条件的。
自宋朝后,由于中原人口大量南迁,国民经济的重心从北方移到了南方,江南大地逐渐被劳动人民开拓并改良成腴田沃土,田肥产丰。随着产量的增长而地租也在增加,有的佃户为了防止地主增租而与田主相约采取契约的形式,将租额写在佃约上,固定下来,不容变更。此种形式到明代有了很大发展,较为广泛地实行起来,对以后的租佃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傅衣凌先生讲:“契约制的租佃关系,早见于宋、元时代,……然其(大)量的施行,则不能不说是到了明代中叶以后才逐渐发达起来的。据日本仁井田氏搜集明代通行的百科全书类的图书二十多种,差不多都记载有租佃契约的格式,则可见知其流行之广①。”此契约大多有限定租额的内容。到有清代则以契约限租更为普遍。在傅衣凌先生收集的福建省永安县的13种租约中,就有12种是限定租额的。在江苏、浙江、广东、江西等地也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限定地租之情况。尽管在不少地方往往有一些地主背信毁约增租,破坏佃契,但一般地说,佃农利用契约总算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地主的剥削。于是佃农大量地投资于租田,改良土壤,不断提高产量。这增产的部分就是佃农新创造(增加)的土地价值和使用价值,将其理所当然地归为已有,这样,产量与地租在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就各自成为两个独立的范畴了,地租成了一个不可变的常量。此时在额租制下,地主没有随时侵犯和剥夺佃民耕作权(佃种权)──变换佃户的必要了。无论佃田归谁使用(让谁租种),他们的收入都不可能有所增减,因而地主也就没有择佃的兴趣了。佃农就由此而有了较为长久的稳固的佃种权,有的还取得了永佃权。如江西的瑞金、宁都等地,自明朝以来一直实行定额地租──每亩交租1石,历久不变。田主只管收租,不问其它。在很多租田上,从明朝前期到清朝初年这200多年来皆未曾撤佃夺耕,仍由原佃之家世代守耕。故顺治三年(1646)魏礼述称:“(宁都)下乡闽佃先代相仍,久者耕一主之田,至子孙十余世,近者五、六世,三、四世②”。此县佃农努力经营土地,使其产量不断增加,地主欲增租不能,欲撤佃又没有必要(即使换了佃户也不能加租),只得让其长久守耕,世代佃种。此种事例,到了清代就更为普遍了。据乾隆刑科题本所记,福建仙游县佃户林正佃种地主陈王里之土地,“议定每年租谷二石二斗,交各房轮收办祭,并在(契)约内载明:如无欠租,不得另付他人耕种,相安已久③。”意即只要交足额租,就可以永佃。同样,刑科题本,乾隆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刑部尚书尹继善题奏:据说,广西武宣县壮民,佃人土地者常向田主交纳额租,故“历来只换田主,不换佃户,就算世业一般”。不少地方在铁板租制下,地主将土地的支配权或使用权(耕作权)完全交出──让佃户全面自由管理,永不过问(以交额租为前提),即使是佃户象处理自己的财产一样典当顶卖田皮转租土地,田主也不管。如湖南省茶陵县,交纳定额租的耕户之租佃权受人尊重,不容侵犯。故该地“俗例,凡是佃户无力耕种,可把佃种田亩顶给别人,收得钱文,去还田主租谷④”。显然,在定额的铁板租制下,田租与土地出现了相对分离的趋势。在每块土地的租子收入经主佃双方订死后,就再也不能为地主增加利润了,佃户也就不容易被驱赶出土地之外了。
上面所述皆为佃户通过定额地租制而直接取得永佃权的事例,同时广大的佃农群众还借助土地贸易这一环节,在额租制下间接地获得永佃权利。
首先,由于大多数地区租额固定不变,所以人们在土地交易的过程中,往往使用代换概念或代换名词的手法,即用以若干两银购买若干石租来代替以若干两银买取若干亩土地的计算。地主卖若干亩田,就等于卖若干石租,因为每亩租田的地租都是固定不变的。在土地买卖契约上,常常要写上:××石租田,价××两银。如广西横县地方,据民国《横县志》第5编,“自明(朝)以来,相沿有一田两卖者;业户用价银买受粮田,……上则租田每石(租)价值或十两、八两;中则、下则每石或五两、六两,……而佃户则用价银买受粪脚田。……”同样,在广东的香山、顺德等县,在土地买卖中,也是“论租不论田⑤”,即论斗论石不论亩。也就是说,在定额的铁板租制下,卖土地和卖租成了同一意义;从租田中割出一块出卖就等于从额租中抽出一部分来出卖,二者是同一概念。于是往往有的田主在地产贸易中,不直接卖土地,而只是从地租中随便抽出几石或几斗来出卖于人,使买者成了不完全的名义上的田主或部分意义上的土地所有者,而去纳税服役,而实际上对方买走的不是全部的地租或全部土地价值,因而也没有权利来支配和掌握土地。田与租就进一步分离了。如在明朝时,福建的漳州府地区,“邑民受田者(田主),往往惮输赋税,而潜割本户米(税米)配租若干石,减其值以售,其买者亦利其贱而得之。当大造之年,一切粮差皆其出办,曰大租主。有田者不与焉,曰小税主(小租主),而租与田遂分为二⑥。”所谓“租与田遂分为二”,就是说,在以后的土地买卖中,小租主可以卖地,大租主只可以卖租,不得干沙土地之事:“得其租无田曰大税主(大租主),“民间卖田契约,大率计田若干亩,岁带某户大租谷而已⑦”。小税主就是土地的田皮或田根的所有者。这种土地贸易中的地租分割,构成了永佃权的基本内容──当小税主将此田卖给直接耕种土地的自耕农时,买者就成了向大租主交租的拥有永远佃种权利的佃户了,此处永佃权使──用权中又包含有所有权的内容。同样,在广东“惠阳的定额获租制中,也有包租或包收田租的人们,俗称为租客,这是与租额也很有关系的。惠阳和海丰的租客就是从明至清有威权而能抗税的官僚巨商,一般小地主曾将所有的田地活卖给他们(仅卖地租的一部分),所求得他们的保护,结果成了地主可卖田,而租客可卖租。租客纳粮轻而取租重。惠阳……每斗种子(约一亩),佃客(即佃户)纳田利(即地租)一石六斗给业主(即地主),业主再纳二斗谷给租客,租客只须纳粮半升给政府⑧。”此处租客只购买了地主八分之一的土地价值(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当然无权支配整个土地,在出售所谓的土地所有权时,只能出售所得的2斗租谷。地主将此田(就象田皮一样)卖给自耕农民时──“地主可卖田,租客可卖租”,买者同样是成为向租客交租的拥有田皮的永佃农民。
至于人们说的佃户开垦或改良田主的荒瘠之地而付出工本,以工本为理由而取得永佃权之举,也是通过额租制来实现的。因为实行定租额后,佃农在土地上付出过多的工本才能得到补偿,使佃户能够长期占有增产的劳动果实,即在契约的保证下,地主不得通过随意换佃而抢占应归佃农的这部分增产的东西之故。否则,任听地主增租或按丰歉分成收租,那部分增产的东西就给剥削去了,所费工本就得不到补偿。永佃权也就没有意义了。如北方人民也有为地主垦荒或改良土地的,但因实行分成租制而没有得到永佃权,常被夺耕撤地。
定额地租又分软租和硬租两种,前者可变动,后者不可变动,而前者较为普遍。永佃制是硬租或铁板租的产物,与软租的关系不大。换句话说,并不是所有的定额租都可以产生永佃权,而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永佃制才没有在全国全面出现(南方较多,北方只是零星半点地存在),从明至清,随着铁板租的增多,永佃制在不断地产生。这就决定了永佃制的产生和发展极不平衡,它的地域性很强,有的地方在明代就有很大发展,有的地方,到清代才开始出现。
二、永佃权的巩固及其价值问题
定额地租虽然是永佃制得以产生的根源,但把永佃制固定和普遍发展起来,还是借助于人民的反抗斗争的。由于广大佃农群众为获取和保卫永佃权而进行斗争,致使一些地主难以完全破坏永佃制,取消永佃权。
我国的南方与北方相反,人稠地窄,栽禾之田甚少,不足以百姓使用。并且南方土地集中程度高,又兼并严重,人们得到土地是很不容易的,因而自耕己地者不多,大部分农民是佃种地主的土地。故大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卷10中指出:明末清初,苏州府、松江府等地,农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由于南疆人均占地面积小和佃农数量大,决定了佃户承种租田的面积小。在此情况下,佃农的生机就全埋藏在这小面积的租田里,要求得生存,要想多得到粮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只有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欲达到此预期的收成(丰产)之目的,只有较多地投资于土地的基本建设,在水肥上多下本钱,南方广大佃农群众就是这样,从种到收,用于土地的灌溉、粪壅等项费用要占去全年田间收入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⑨,有时还会更多。由于佃户在赁耕的土地中投入了很多的工本,付出的代价很高,一旦遇到田主撤佃夺耕,所遭受到的经济上的损失要比北方佃户重,因而,他们要求维持原佃的愿望比较强烈,要求保持永远佃种的权利。遇时由于南方佃户不断改良土地,提高产量,获利渐厚。对此,地主往往因妨忌而增租夺佃,主佃双方因此而经常发生冲突。
就一般而言,由于佃户的强硬坚持和地方的习惯影响,地主难以增加或不便增加正租。在此情况下,他们往往转而进行一些附加的额外剥削,用种种手段破坏额租制。如自明末以来,他们向佃户索取额外的附加财物:在松江,地主历年要佃户在额租外另行交纳瓜干;皖南的佃户年终须向田主交送信鸡。在福建,地主要佃户送交“冬牲”的地区和事例甚为普遍。此外,地主又以诡诈手段用大斗大称浮收,百姓谓之为富不仁。种种行径都是在蓄意破坏额租制。我们知道,额租制是南方地主与佃户利益分配的准绳,是永佃制的坚实基础和重要内涵。破坏额租制,对于永佃制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变相否定,严重地威胁到佃民的耕作权利和生计。佃民作为一个群体,出于自卫,起而反抗:正统十三年(1448),福建邓茂七起义,倡革附加地租──取消冬牲,巩固了租额和佃权。日本学者讲:“邓茂七起义之后,设定了佃权(永佃),而得买卖之⑩”。后来,嘉靖七年在光明、万历至天启年间在泉州、清顺治二年在江西新城、康熙十三年和二十三年在福建宁化以及上杭、宁泰等地的广大佃农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较斗”、“平斛”、“减租”的反抗田主之斗争运动。较为有力地打击了江南地主的恶劣行为,沉重地制裁了田主从斗头、秤头浮收和额外城索实物之作法。
自明代邓茂七起义之后,清代南方的佃农群众除了进行以上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外,也同样举行了武装暴动,以此最为猛烈的进攻形式对付垄断田产的地主,去更有效地保卫额租制,扩大永佃权。文献记载,清初顺治二年(1645)九月,在江西省石城县,“石马下吴万乾倡永佃,赴田兵(11)”。这次武装斗争,是明末江南农民革命的继续,声势大,范围广,波及附近各府州县。当时官方言称:“明季谢、闫二贼交炽,凡闽广侨居者思应之,皂隶何志源、应捕张胜、库吏徐矶、广东亡命徐自成、潘宗赐、本境(江西瑞金)惯盗范文贞等,交宁化、石城,故倡立田兵,旗帜皆书,八乡均田。均云诸,欲三分田主之田,而以一分为佃人耕田之本。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无易人,永为世业
(12)。”意即那时发生在闽、赣的佃农革命,其主要斗争内容是:佃农耕种地主的租田,付出了很多的工本,他们以工本为理由,要求维持永佃权,也就是要以工本为代价而换取三分之一的土地价值,将此三分之一的租田价值作为佃产或佃价──长期的耕作使用权。继之,又在石城县,“吴八十与陈长生、孔昌等于康熙九年(1670)庚戌,穴左坑起田兵,借永佃为名,抬碑直竖县门,知县不能捕治,以致蔓延(13)。”这清楚地反映了在广大佃民的斗争之下,永佃制在发展──“蔓延”。随之江西兴国佃农也纷纷起来以无情的对抗手段成功地稳定了地租原额和维护了自己的佃权。影响不断扩大,遍及各地。
佃农通过一系列的斗争,巩固了额租制,巩固了永佃权之后,就算真正限定了地主的剥削,使后来地产价值的增加成了单纯的佃产的增加,即成了属于佃户的田皮价值的增加,使南方的租佃关系出现了相对的正常化,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平衡状态。
由此可知,永佃制既是一种物质运动的产物,也是一种社会运动的结果,它是广大佃耕者通过改造自然、开发地力而创造的生产方式。它的存在是江南佃农意志的反映和标志。赁地耕种的佃民利用最起码的价值规律、等价交换之法,光明正大地在田主面前划定了租田的原有价值和后增价值两部分,并把后增价值确定为佃户自己付出的工本,以坚决的斗争手段迫使地主承认。如此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佃农应有的权利和地位,它以乡规民约的形式维持下来,具有民间自然法的性质,并含有原始的初级的民间自治之因素。
前面说过,永佃权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土地使用权,而且它是具有实在价值的,那么,可以确认,永佃权本身就是一种财富,是一种实体。它与所有的其它财富一样是应有转让和交换的可能性和客观性的。正因为如此,明清时期,南方各地都曾有永佃权或田皮的交易市场,买卖盛行。如在福建,清代陈盛韶的《问俗录·仙游县》讲:当地“田分根面,根(田皮)系耕田纳租,极贵:面系取租完粮,极贱”。分明是说,在这一带的田产贸易中,永佃权的价格超过了地主的所有权的价格。有的地方称田皮(永佃权)是“田面”,名词虽有不同,但所指实为一物。又有江西的同治《雩都县志·风俗》记载:在雩都的土地租佃关系中,民间赁耕之“田有田骨、田皮,田皮属佃人,价时或高于田骨(田骨属田主)”。在福建等处也有类似的现象。一般地讲,上面田皮之价贵于田骨之价,即佃价贵于产价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田皮本身的价值在起作用,也就是说,是田皮之价值经过佃农的努力,大幅度提高,往往超过了地主的田产(同一块土地)──田骨之价值的缘故,绝不是象学界一些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单纯地因为有些地区人稠地窄,耕田供不应求,出现劳动力过剩,从而使得永佃权(田皮)价格贵于租田田骨(所有权)之价格,如《政治经济学辞典》等有关书刊。其实,这些价格高于田骨(产价)的田皮,大都是纳租少而收获多的肥田沃壤,有较高较显著的实惠。如史料记到:这种永佃田,江苏之“昆山(县)稍多,南通次之,……且以行之于上等田地者较为多(14)”。在赣南的于都等各县,有肥皮(田皮)瘦骨的说法。同治《雩都县志》卷5《风俗》称道:“不知(田皮)价之高者,因出息(利)广,厚利皆归佃人,而田主仅得些须之租,官或不知,……”。乾隆《政和县志·田赋》讲:“民间主佃交易,又有顶手田皮诸弊。……为贪余利而购田皮,……”。这几种材料都一致说明了吴(苏)、闽、赣各地之田皮(即永佃权)的价值是很高的,是有利可图的,农民购买■而来,并非是在简单地争取劳动机会。
当然,田皮价格也是有高有低,它是由田皮本身的肥瘠程度或价值的高下决定的,也并不是说所有的田皮价格都高于田骨,但无论情形怎样,田皮价格的高低主要是由其本身的价值所造成的,并不是由于劳动力过剩的程度轻重决定的。农村劳动力的过剩程度诚然对田皮的价格有影响,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但它产生的影响较小,根本不起什么决定作用。常有一些瘠田的田主招佃种田,都没有人承耕,必须事先许给永佃权才有人租种,更何况要让佃户出钱买耕呢?即使是土地(租田)稍好,但不太肥沃,田皮价值不太高,没有厚利可获,此时,又有谁会象前面资料讲的那样,愿以高价买耕(买田皮),甘愿为地主纳租,而不愿意低价买田成为田主呢?如前面所说,如果不是某些地区田皮的实际价值超过田骨价值,又有谁会高价购买田皮而辛苦耕种终年,而不愿贱价买田骨而坐收其租利呢?特别是在同一时间内的同一地区,常常出现各种田皮的价格贵贱悬殊之事,用劳动力过剩程度这个概念是无法解释这种价格的大差大异现象的。我们必须用田皮的价值观念来对待此问题,对之进行具体分析。如乾隆十九年(1754),广东揭阳县人买质田(永佃的田皮),面积2亩半,售价5两银,平均每亩田皮价为2两银。在同年同地有人买田皮8亩,出了价银55两,每亩田皮售价近7两银(15)。在如此同时同地的田皮贸易中,各劳动力与田皮市场之间的供求关系就该是一致的,即劳动力的过剩程度对市场交换的影响无疑是相同的,而后者价格之所以贵到前者的3倍半,不可能是供求关系在起那么大的作用,只能是因为两种田皮的质量或价值悬殊之故。同样,雍正四年(1726)的十一月,在广东揭阳县,10亩田皮(佃业)卖得13.5两银子,每亩平均为1.35两银。过了几个月在同地,有佃户将13亩佃产(田皮)售价87两银(16)。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后者之价格之所以贵于前者5倍多,其原因当然也是与上例相同的。综上所述,归于一点,当时的田皮交易或佃产买卖,实质上是价值的交换,即以田皮价值为交换的尺度。
三、“一田三主制”下的租佃关系
有些人从田主手中取得了永佃权后,不仅自种或出卖,而且有时甚至又把属于自己的田皮转佃给别人,收取第二地租,形成了“一田三主”之现象。道光《龙岩州志》卷7《世俗》记载,清中期在福建龙岩地区各乡,“若各族祖遗祭产(租田)、授耕多年,佃(户)直据为世业,其间辗转流顶,有更数姓,不闻业主。小租加倍原租者,尤为积重之势。”同样,据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11《风俗志》,在江西宁都地方,也有转租佃田皮之例。如清朝雍正年间,当地一些“佃人,承赁田主之田不自耕种,借与他人耕种者,谓之借耕,借耕之人,既交田主骨租,又交佃人皮租。”此两段引文所反映的二次出租或两个层次的同时出租现象,是南方“一田三主制”的一种典型事例,本文称之为第一类型。显然,在通过永佃制而产生的这种“一田三主制”下,佃产或田皮也具有了产生封建地租的职能,它逐渐演变成与地主的田骨无多大差别的一种生利性地产。这一来,就扩大了田皮的利用范围,使得企图掌握购买田皮的人进一步多了起来,不仅是一般的劳动人民购买田皮,而且连一些官绅富户也把永佃权或田皮作为一种重要的特殊的财产而争相购买,充当佃主。据民国《福建省例》卷15《田宅》,福建布政使于乾隆三十年(1765)讲:建阳等县,“绅监土豪,贪嗜无粮(税)无差,置买皮田,剥佃收租”。在福建、江苏、江西等省,这种情况出现不少。陈益祥:《采芝堂文集·风俗》记到,闽省地方有竞买田根(田皮之异名)之风,常有“奸滑富厚者,多蓄田根”,“根主得栗(第二地租)与业主同,而实无苗粮之苦(无赋粮役银之征)”。在以上形式的一田三主制中,这些购买田皮(田根)而又转手出租的人,无论是绅士也好,土豪富户也好,都是具有双重身份──一身而二任。他们对于田主来说自己是交租的佃户;对于真接耕种租田的佃户来说,自己又是收租(皮租)的佃主──二田主。如此情状,仍属于永佃制的范畴。
一田三主制的另一种情况,则是封建地主诡脱赋税徭役造成的。因为在明代时因赋派定徭,因地编差,征调簿上,赋粮多者要当重差,当大差,土地多者,税粮就多。那些租多税多的富户必须去充粮长、解户、养买军马、支应递驿马匹等特大的自然形态的徭役,充户往往赔累不堪。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稿第八册称:“一条鞭法未行之时,有力差一事,往往破人之家,人皆以田为大累,故富室不肯买田”。同样,叶梦珠:《阅世编·田产》也曾记到,前明时,民间赋粮多者,所当徭役随之也重,乡村多田之人(包括住城地主),“相率以有田为戒矣”。在此背景下,富人既欲多购置地产扩大封建地租剥削,而又怕承担重役,致使他们处在痛苦的彷徨之中。后来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悟出一个窍门,即开始采用了一田三主的形式,继续发展封建地主经济。就是象前面所讲的那样,田主把自己的土地活卖给别人,即贱卖给别人──将土地价值的一部分卖给对方(卖一部分租),保留大部分价值(大部分地租)作为永久使用或享用此土地的条件,使买者成了大租主,自己成了小租主(小税主)。这样,小税主成了一方面向大租主交租的拥有永远使用或永远租佃权利的佃户;一方面又是向佃户继续收租的田主──佃主。除了大租主、小租主之外,真正佃种土地的佃户又取得了永佃权,成了田皮的所有者,可私自将田皮顶卖给别人,获得田皮顶价“粪土银”。故南方有“久佃成业”之谣。这是真正的一田三主制,而前面所讲的“第一类一田三主制只是一种假称的一田三主,因为其佃户并不是田皮之主。如此一田三主制同为永佃制的范畴。在这第二类一田三主制中,若真正耕种土地的拥有永佃权的佃户将田皮转租于人,收得另外一份地租(第三次地租)时,此一田三主制就成了假称的一田四主制了,福建漳州等地区就有这种一田四主的现象。有的地方,除了大租主、小租主外,佃户并不是田皮之主,没有取得永佃权,此时就不是真正的一田三主,而是成了假称的一田三主制了。第二类一田三主制的实行的结果是成全了原田主(小租主)的想法。此时小税主的土地再多也不会有赋役重担之虑了,将其赋役登册过户,转由大租主全部承担了。据嘉靖《龙溪县志》卷4《田赋》讲,此小税主获取之租,在龙溪县称之为“粪土税子,谓之无米租;……大租谓之纳米(税米)租,无米租皆富家巨室蟠据,纳米租则有力者攘取。”在购置地产时,他们往往大量地买取这种无税田作为发展地主经济的出路。明中期时这第二类一田三主制纷纷出现,争购无税田已成其风。一条鞭法实行时,因力差被取消,此风亦随之稍止。可不久,加派盛行,三饷“扰民甚为严重,第二类一田三主制又复得以发展,无税田又复以增多,富有者又以增置小租田(无税田)为积累资财的重要手段了。
小税主利用一田三主制的办法,不但可继续维持对佃户的剥削,而且还能产生更多的超过大租主的利润。万历《漳州府志》卷5《赋役志》记载,在福建的漳浦、长泰、南靖平和等各州县,“一田而有三主之名。一曰大租,一曰小租,一曰佃户,如每田十亩,带米(税米)九斗六升三合,值银八十两,年收租谷五十石,大租者只用银二十两买得年课租谷一十石,虽出银少而办纳粮差皆其人也。小租者则用银五、六十两买得年科租谷二十石,虽出银多而一应粮差不预也。至于佃户则是代为出力耕收,年分稻二十石。“这当中,大租主要拿出全年土地收入的一半来支付田税和差徭,虽收10石租谷,而实得者才5石粮而已。因为大租主通常“岁纳本折色、机兵、驿传米、八丁银等项,该银一两二钱有零。若以十石租论之,约值银二两五钱(17)”。而且常常难免有赋役加派加征。那么,大租主所付地价银必须用16年的纯收入才能收回来,而小租主只用12年就可以收回地价本钱来了。可见,小税主(小租主)是剥削佃户最厉害,获利最大者。
看起来,南方一田三主制是一个由多种经济因素和多种社会关系互相作用的综合体,它是封建社会末期江南地方农业经济活动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租佃关系之枢纽形态。农业生产力和生产环境决定了农民的生产活动形式,特定的生产活动形式决定了农业生产关系包括租佃关系。由于江南地少人多,地产兼并严重、佃农生产力大为提高的内部运动,受到明朝封建国家以田定赋以赋定徭之财税政策的外部影响;受到了田产市场内容变化的冲击,使得苏、浙、闽、粤、桂、湘等各地出现了高度利用土地资源的一田三主制。这是在永佃制的基础上,农村民间各阶层人们互相协调、互相组合的一种特殊的农业经济结构,这是一种分割田产权和使用权的多层次管理的经济结构。如此经济结构──一田三主制是以高效益的农业生产为必要条件的:它象是在一块能盖几间平房的地皮上筑起了高层楼房一样,极大地提高了发挥了单位面积的土地效益,故而能在一种租田上养育田主、佃主、佃户3种人,从而造成了由这3种人组成的独特的江南租细关系──双重地租、多重主人、结构层叠、内容繁杂。
人们一般认为,一田三主制下的直接生产者或租种者──佃户,因受大租主、小租主或者是田主、佃主的双重剥削,故比一般的佃户苦累。并由此而推断出永佃制发展到转租或出租田皮收取第二地租的阶段,就由进步转向倒退,成了封建剥削的物质基础。其实并非如此。首先,在价值关系的作用下,他们是不可能偏苦偏累的。请看,在赣南的宁都州,清中期时普遍存在着一田三主制,“如五十亩之田,岁可获二百石,……则以五十石为骨租,以七十石为皮租,借耕之人自得八十石(18)在福建南部之漳州地区,10亩租田上,大租主和小租主取租谷30石,佃户得20石(19)。在这些一田三主的永佃田上,尽管剥削较重,但永佃田一般都是最好的土地,佃户仍然可以在每亩土地上获得1.6石到2石稻谷的收入。因为不少永佃的三主田是原来永佃农民不断努力,成倍地增加地力和租田价值的,特别是到了清代,尤其是如此。在一田三主制下,一方面有田主、佃主的双重剥削;一方又有很高的产量,使土地耕种者(佃)的田间收入一般不会低于非永佃制或非一田三主制下的佃户所得,甚至还有超出的时候。清初在苏南,非永佃农民的收入之逊是显而易见的,如“金陵,上田十亩,一夫率家众力耕,丰年获稻不过三十余石,主人得半,……”(20)。此上等田在丰收之年佃户亩收稻谷才不过1石5斗多,一年全家收入不过15石多。这还是在江南稍称沃土之乡的事例,若是在其它一般的地区就更低了。如章谦存在《备荒通论》中讲到宝山(上海地区)等县情形是:“上农耕田二十亩,则口食之外,耗于田者二十千(投入土地的工本为20千文钱)。以中年约之,一亩得米两石,还田主租息一石,是以存仅二十石(21)。”在江南的一些旱田上,佃农的年收入更低,在皖南、赣中的一些旱田上常有佃户输租外亩得几斗者。可见,一般佃户的收入稍逊于一田三主制下的佃农收入。
本来南方人稠地窄,地价很高(也因肥沃),又因永佃农民不断增进地力,创造和增加了田皮价值,有时成倍地超过了原地产的价值。于是在土地交易中,田皮就成了比一般土地包括田骨更好的更昂贵的地产了,一般的贫穷佃户就买不起了,使得田皮或田根大量地落到了富人之手。如闽史称道:“贫佃揭债莫偿,指田禾岁岁输纳,名田根(田皮)。根主得栗(佃主得第二地租)与业主同(与田主所得的正租相等),而实无苗粮之苦(不纳赋粮役银),此风闽省最盛。故奸猾富厚者,多蓄田根,根价遂倍于面(产价,即田骨之价),而佃农之苦,也倍于他郡(22)”此处,佃农创造了很大利润──第二地租(佃租)竟达到了业主所得正租的程度,等于佃农在原地产的基础上又创造出一块地产。此处的“佃农之苦”是指买不起地产之苦(买田根),而不是其衣食之苦。佃户买不起地产(田根)之苦,并不是真正的生活之苦,若能够买地产(田根)也就非原来之佃户了,就成为新的财主了。买不起佃产之佃户往往“借耕”,即充当一田三主制下田主与佃主共同的佃户,即使这样,他们的收入也不比一田一主制下的佃户收入少(如前所述)。
在明清封建社会,佃农虽然在南方的一些地区取得了永佃权,增加了以劳动致富的能力,但无论如何,也不能与那些封建的势家富户之经济力量抗衡,在抢购佃产的风潮中,佃价猛涨,经济不支的首先是佃户,并且,一般佃户是不能依靠第二地租生活的,他们大都进行直接的田间劳动。大量的出租佃产,收取第二地租,进行封建剥削的是那些较富裕的“赔主”,不是一般的佃主。换句话说,第二地租或佃租的较多出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富人的行为,而不在于一般持有佃权的佃主(收取佃租的佃户出身的剥削者属极个别),也就是说,在某些地方改变永佃制性质的──将其由劳动致富的可能性变为进行封建剥削之可能性的是封建阶级之富户,而不是一般的佃户。
永佃制刺激了佃农巨大的生产劳动积极性,佃户利用永佃制创造了很多的社会物质财富──粮食,这是毫无疑义的,显然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很强的适应性和推动性。至于永佃制被何人如何利用,又如何产生第二地租,那就不是永佃制本身的问题了,我们知道,永佃制并不是必然要发展为一田三主制,或必然出现第二地租。如广西永淳、横县等地从明代到清末的永佃制一直是一主一佃,佃户虽获厚利但并不二次出租(23)。二次出租田皮,是当时特定地域和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当时出租田皮的一田三主制主要出现在人口高度集中而土地甚少的地区,一般的地产不足以富户搜刮,于是便购买田皮(佃产)二次出租,形成一田三主。这又是与赋役制度有很大关系的,如前所述,它并不全是永佃制自然的结果,或本身内部的原因,即使是没有上面两个原因,也应该看到“出租田皮,获取第二地租是与永佃制本身责任无关的。谁都知道,在封建社会的农村,只要有土地私有制存在,只要有地主阶级存在,就会有地租剥削的存在,这是总根源。田皮之所以从佃户手中转到富人之手被出租,就是因为贫佃受不了各种灾害和生活困难所迫而出卖田皮的。由于生活的困难,有土地的自耕农可出卖土地(因为土地私有,可自由买卖);有田皮(永佃权)的佃户可出卖田皮,若地主富户买取了这些土地、田皮时,都可以将其出租。我们没有理由埋怨自耕农有土地,没有理由埋怨这种自耕田变为剥削人民的出租地,因为土地是无罪的,自耕农也是没有错误的。既然如此,我们同样也没有理由说永佃制之田皮一旦成了富人出租之物就是倒退。就是说,田皮(永佃权)变为出租之物,并非永佃权本身的问题,因为永佃制是没有错误的。永佃农民利用永佃制更好地创造了增加了社会财富,至于这个财富最后被谁夺取,就不应由永佃制承担责任了。比如说,社会化的大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这些财富又大都被资本家占夺了,人们不能因此而否定社会化的大生产之进步性和合理性。永佃制在明清时代的进步性和合理性之不容否定也是同属一个道理的。
注释:
①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71页,三联书店,1961年。
②魏礼:《魏季子文集》卷8《与李邑侯书》。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清代地租剥削形态》第596页,中华书局,1982年。
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清代地租剥削形态》第702页,中华书局,1982年。
⑤民国刊本:《顺德县水藤堡沙边乡厚本堂何氏事略》。
⑥乾隆《龙溪县志)卷5《官民田赋始末考》。
⑦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4。
⑧冯和法等:《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17章,4节,上海黎明书局,1935年。
⑨沈镜贤:《东草堂笔记》。
⑩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51页,三联书店,1961年。
(11)乾隆《石城县志》卷7《兵寇》。
(12)乾隆《瑞金县志》卷7《艺文》。
(13)乾隆《石城县志》卷7《兵寇》。
(14)冯和法等:《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章,4节,上海黎明书局,1993年。
(15)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清史论丛》,第2辑,第78页,中华书局,1980年。
(16)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清史论丛》,第2辑,第78页,中华书局,1980年。
(17)万历《漳州府志》卷5《赋役志》。
(18)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11《风俗志》。
(19)万历《漳州府志》卷5《赋役志·土田》。
(20)万历《漳州府志》卷5《赋役志·土田》。
(21)贺长龄、魏源等:《皇朝经世文编》卷39《仓储上》。
(22)陈益祥:《采芝堂文集》卷13《风俗》。
(23)黎斐然等:《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下册第319页,中华书局,1978年。
标签:明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