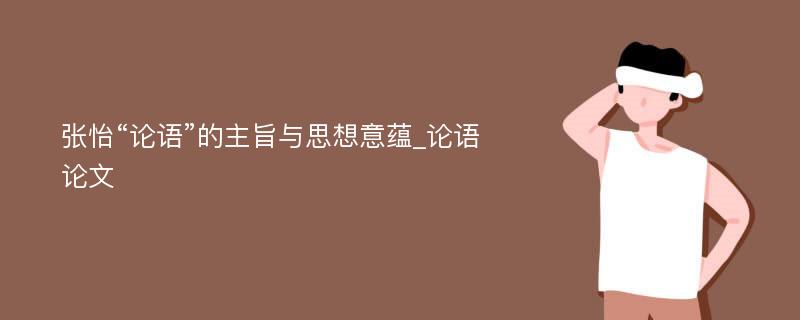
张栻《论语解》的学风旨趣与思想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旨趣论文,意蕴论文,学风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1)05—0024—09
张栻(1133-1180),字敬夫,一字钦夫,号南轩,学者称南轩先生。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湖湘学派代表人物,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张栻一生著述甚丰,编撰的经学著作有《诗说》《书说》《四家礼范》《南轩易说》《论语解》《孟子说》《中庸解》等,大部分已经散佚不存。《论语解》自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前后开始撰作,反复推究、删改,至乾道九年始成。是年岁在癸巳,故名为《癸巳论语解》。该著为张栻倾注心力之作,在《论语》学史上有很大影响。
在《论语解序》中,张栻谈到,“《论语》之书,孔子之言行莫详焉,所当终身尽心者,宜莫先乎此也。”① 河南二程先生有关《论语》的论断“以穷理居敬之方开示学者,使之于致知力行有所循守,以入于尧舜之道”,因此其《论语解》就是“因河南余论,推以己见”。② 本文依据张栻所述,对《论语解》的学风旨趣与思想意蕴加以探讨。
一 解经原则:宗奉二程之学
二程非常推崇《论语》,在北宋中期的儒学复兴运动中,将《论语》《孟子》抬高到为学根本与尺度标准的地位。二程认为:“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③“《论》《孟》如权衡尺度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④ 在对《论语》的解说方面,二程也留下许多精辟见解,开辟了《论语》解说的新方向。可以说,二程是最早从理学视角对《论语》进行阐释发挥的代表性人物,其《论语》解说在理学学派《论语》学中具有奠基性的作用。
张栻为二程的三传弟子,与二程学脉相通。后来又以杨时《河南程氏粹言》重订而成《二程粹言》,对二程思想学说有很深的了解。他推尊二程,认为“道之不明久矣,自河南二程先生始得其传于千有余载之下”。⑤ 在与友人的书信中,张栻多次颂扬二程之学:“近来读诸先生说话,惟觉二程先生完全精粹,愈看愈无穷,不可不详味也。”⑥“二程先生之言真格言也”。⑦“解经义处,惟伊川先生之言看得似平易,而研究其味无斁”。⑧ 在《论语解》中,宗奉二程之学的特点表现得十分明显。
《论语解》大量引述二程之言,在此基础之上进行进一步的引申、发挥。如解《学而》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张栻解说道:“学贵于时习。程子曰:‘时复紬绎,浃洽于中也。’言学者之于义理,当时紬绎其端绪而涵泳之也。浃洽于中故说。说者,油然内慊也”。⑨ 在这里,张栻在简明扼要地点明主旨之后,即引用二程之说对此句内涵进行解说,进而通过发挥二程之意说明“学而时习之”的含义以及由此产生内心愉悦的原因。整个解说均以二程之学为依归。
又如《为政》篇“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一句,汉唐以来古注多解为温故知新可以为人之师,何晏注及皇侃疏均将“可以为师”解为“可以为人师”。⑩ 宋代学者也往往如此立论。如朱熹解云:“言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其应不穷,故可以为人师。”(11) 但张栻的解说与此不同:“可以为师者,言其温故知新为可师也。”(12) 这种解说,本于二程。张栻直接引用了二程之言作为其解说的依据:“程子曰:‘如此处极要理会。若只认温故知新可以为人师,则气象窄狭矣’”。(13)
《论语解》极少专门对字、词进行训释,但在少数对文字进行训释之处,也多引述二程之说。如《学而》篇中“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一句,张栻直接引二程之说进行解释:“程子曰:‘温,和厚也。良,易直也。恭,庄敬也。俭,节制也。让,谦逊也。’”(14) 在解《公冶长》篇“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时,张栻援引二程“材”与“裁”通用之说,将此句解释为“夫圣人之勇,不可过也。而过焉,是未知所裁度也。”(15)
《论语解》的许多解说,虽然并不直接引述二程之说,但从中不难见到对二程之学的汲取。如《子罕》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段,张栻解云:“此无息之体也。自天地日月以至于一草木之微,其生道何莫不然?体无乎而不具也。君子之自强不息,所以体之也。圣人之心,纯亦不已,则与之非二体矣。”(16) 这一解说,从精神旨趣到具体内容,都与二程的解说颇为一致。二程说:“此道体也。天运不已,日来则月往,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纯亦不已焉。”(17) 二程从“道体”的高度对文本进行解说,发掘出“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纯亦不已”的内涵。张栻的解说与此有很明显的渊源关系。
又如《宪问》篇“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一章,张栻解云:“学以成己也;所谓成物者,特成己之推而已。故古之学者为己而已,己立而为人之道固亦在其中矣。若存为人之心,则是徇于外而遗其本矣。本既不立,无以成身,而又将何以及人乎?”(18) 这一解说,把“为人”解释为“成物”,则为己与为人的关系就被阐释为成己与成物的关系。成己成物之说出于《礼记·中庸》:“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意指自身德性充盈,而后事天济众,成就他人。张栻在解说中所强调的是学者应该以追求自我完善为根本,专注于修身养性,外在的事业只是其内在德性的自然推衍与外在显现而已,不能舍本逐末,离开己立、己达而追求立人、达人。
这一解说,迥异于汉唐诸儒之说。孔安国将为己、为人解释为:“为己,履而行之;为人,徒能言之。”范晔则解为:“为人者凭誉以显物,为己者因心以会道也。”(19) 两种解释均排斥“为人”之学。在历代众多的儒者看来,为己、为人二者是互相对立的,为人之学是应当鄙弃的,为儒者所深戒的。朱熹也指责张栻此说为“错解”,认为“此‘为人’,非成物之谓。伊川以‘求知于人’解之,意可见矣。”(20) 朱熹试图援引程颐之解说服张栻,但实际上张栻此解恰恰本于二程。二程说:“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余无他为。二者,为己、为人之道也”。(21)《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中还载有二程与弟子的一段问答:“问:‘古之学者为己。不知初设心时,是要为己,是要为人?’曰:‘须先为己,方能及人。初学只是为己。郑宏中云:‘学者先须要仁。’仁所以爱人,正是颠倒说却。’”(22) 从上引二程之语可以看出,二程在这里把为己、为人理解为为己以及人、育德以振民。按照这一理解,则为己、为人只有本末、先后之别,并无价值取向上的褒贬与相互对立。张栻的解说,所体现的正是这一精神。
《雍也》篇中“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一章,张栻解云:“德合于中庸,则至当而无以加矣。中者,言其理之无过不及也;庸者,言其可常而不易也。世衰道微,民汩于私意,以沦胥其常性,鲜有是德久矣。”(23) 这一解说实际上是基于二程之说而作出的。二程说:“中庸,天下之正理。德合中庸,可谓至矣。自世教衰,民不兴于行,鲜有中庸之德也。”(24)“中者,无过不及之谓也。”(25)“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26) 从文字到义理,张栻的解说均源于二程。
从总体上看,张栻《论语解》全书直接引述二程之说共32处,约占全书所引述的前人注解训释的40%,从中不难看出对二程之学的崇重。全书直接引述的其他训解,也基本上来自张载及二程的门人弟子,其中引述张载9处,杨氏10处,尹氏8处,谢氏、范氏、吕氏兄弟、侯氏各3处。他们与二程之学精神旨趣接近,二程诸弟子的《论语》解说更是受到二程的强烈影响。《论语解》引述其解说,同样体现了对二程之学的尊崇。至于在义理发挥中对二程及其弟子门人之说加以阐发或汲取二程一派观点的情形,在全书中更是比比皆是。宗奉二程之学的倾向十分明显。
南宋中期,二程之学在学界已经产生很大影响,出现了“二程先生之说天下知诵之”(27) 的情形。因此,在《论语》诠释中推尊二程之说,自然成为当时众多理学学者的共同倾向。朱熹在隆兴元年(1163年)编成《论语要义》时曾经谈到,其《论语要义》是在早年所编的有关《论语》的集解之作基础上修订而成:“隆兴改元,屏居无事,与同志一二人从事于此,慨然发愤,尽删余说及其门人朋友数家之说,补缉订正,以为一书。”(28) 后来朱熹作《语孟精义》,其编次原则也是将二程之说“搜辑条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学之有同于先生者,若横渠张公、范氏、二吕氏、谢氏、游氏、杨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说,以附益之”。(29) 据邱汉生先生的统计,朱熹《论语集注》前三篇90处引述中,二程之说多达30处,程门弟子共31处。(30) 可见,在朱熹那里,对二程一派之学的尊崇同样表现得很明显。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在推尊二程之学的同时,也对二程之学有不少批评。他曾经指出程颐解经的弊病,认为“伊川解经,是据他一时所见道理恁地说,未必便是圣经本旨”,(31) 因而往往对二程的解经之说加以辨析驳正。钱穆先生说:“《语类》载朱子于二程遗说诤议驳正,就其事题,约略计之,当近两百之多。若论条数,有一事而言之异时,记者异人,重复至二三条七八条者,则总数至少当在三四百条以上。”(32) 这些诤议驳正的内容,有不少与二程的《论语》学成果有关。钱穆先生曾论及朱熹对二程之学的态度说:“朱子治论语,其先乃从程门以上窥二程,奉二程以上窥论语。稍后乃摆脱程门,专主二程。更后则一本论语本书,多纠二程之失。”(33)
与上述情形不同的是,在张栻留下的文字中,未见对二程之学的任何批评与非议,而只有称颂与尊崇。在与友人的信中,张栻多次要求他们反复研读玩味二程之学。事实上,张栻虽然为人平易宽厚,但在学术上并不缺乏批判精神。张栻对程门的几位弟子都有过批评,如认为“上蔡《语解》偏处甚多,大有害事处”,(34)“吕与叔游伊川、横渠之门,所得非不深,而至论中处,终未契先生之意”,(35)“侯师圣之说多可疑”。(36) 甚至对张载也颇有微词:“近来读《系辞》,益觉向者用意过当,失却圣人意脉。如横渠亦时未免有此耳”。(37)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栻对于其师胡宏的《知言》也曾有所质疑:“《知言》之说,究极精微,固是要发明向上事,第恐未免有弊,不若程子之言为完全的确也。”(38) 朱熹曾经作《知言疑义》对胡宏的某些观点加以辩驳,张栻在很多问题上赞同朱熹而并不株守师说。他评论胡宏之父胡安国的《春秋传》说:“栻近因读《春秋胡氏传》,觉其间多有合商量处。”(39) 可见,张栻并未落入为尊者、亲者讳的窠臼,在学术问题上有其独立的思考。张栻在这一问题上甚至还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自觉,在书信中向友人坦言其惟学术之真是求的心志:“前辈未容轻看。然吾人讲学,则不可一毫有隐尔。”(40)“后生何足以窥先辈,但讲论间又不可含糊耳。”(41)
以张栻如此认识及如此理性的态度,他对二程之学的种种推尊、崇重恐怕只能理解为一种基于自身理解领悟的服膺与由衷钦敬。因此,宗奉二程之学也就成为《论语解》必然的立场选择。
二 解经风格:玩索经义、阐发己见
在宗奉二程之学,大量吸取二程一派《论语》学成果的同时,张栻也对《论语》文本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与独具特色的发挥。在其阐释发挥的过程中,张栻不重名物制度的考订与字词的训释,其关注点乃在于对文本的义理阐发,所追求的是义理的连贯和意义的圆通。往往不下一字训诂,而直接阐发义理,发挥己意。如《里仁》篇“朝闻道,夕死可矣”一章,张栻解云:“人为万物之灵,其虚灵知觉之心,可以通夫天地之理,故惟人可以闻道。人而闻道,则是不虚为人也,故曰‘夕死可矣’。然而所谓闻道者,实然之理,自得于心也,非涵养体察之功精深切至,则焉能然?盖异乎异端惊怪恍惚之论矣。”(42) 整段文字议论风发,不拘一格,直抒胸臆,在新的学术视域中对原文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将其道德认识论、修养功夫论表达得淋漓尽致。
又如《雍也》“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一章,仅仅寥寥数字,汉唐注疏对此较少措意。但张栻则由此生发出大段议论:“觚而失所以为觚之制,其得谓之觚乎?故有是物必有是则,苟失其则,实已非矣,其得谓是名哉?故凡言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皆以失其则故也。至于人生于天地之中,其所以名为人者,以天之降衷,善无不备也。失其所以为人之道,则虽名为人也,而实何如哉?圣人重叹于觚,意盖深远矣。”(43) 在这里,张栻对其人性论与道德观进行了阐述。在他看来,这才是孔子重叹于觚的深远之意。但是平心而论,张栻的这种诠释发挥似乎已经超出了文本内容,成为其自身思想的阐发。甚至可以说,《论语》文本仅仅是触发其议论的话头,他的解说与文本并无内在的关联,这些解说即使脱离文本,仍然不失其意义的独立性与完整性。
朱熹曾经对张栻的解经风格提出批评,认为张栻“天资明敏,从初不历阶级而得之。故今日语人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学子从之游者,遂一例学为虚谈,其流弊亦将有害。”(44) 朱熹所言的“矫激过高”的学风,在《论语解》中有明显体现。在《论语解》成书过程中,张栻曾多次将书稿寄给朱熹,“望便中疏其谬见示”,(45) 希望收探讨切磋之益。朱熹在《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中提出讨论驳正,(46) 从几个方面直陈其《论语》解说之蔽。
朱熹批评张栻立言太高,以致凌虚蹈空而无实:“其立言造意,又似欲高出于圣言之上者。解中此类甚多恐非小病也。”“今为此说,是又欲求高于圣人,而不知其言之过,心之病也。”
批评最多的还是张栻之解好发明言外之意,失却圣人本旨:“今以心无不溥形容,所包虽广,然恐非本旨,殊觉意味之浮浅也。”“此等既无考据,而论又未端的,且初非经之本意,未言亦无害也。”“大率此解多务发明言外之意,而不知其反戾于本文之指,为病亦不细也。”“窃谓高明更当留意,必如横渠先生所谓‘濯去旧见,以来新意’者庶有以利圣贤之本心耳。”“理固如此,但此处未应遽如此说,夺却本文正意耳。”在朱熹的批评中,“本旨”、“本意”、“本心”被反复提及,他认为张栻解经不能去除成见,所说的是自己的道理而非经文之义。因此他建议张栻应当将自己的发挥与经文本意区分开来,避免以己意乱圣人之意:“不应遽说以乱夫子之意。向后别以己意推言则可耳。”“经文未有此意……若欲发明,当别立论而推以及之,不可只如此说,无来历也。”
朱熹的批评,主要针对《论语解》立言造意过高,自信过重,对文本原有的语境与义理脉络缺乏尊重,直伸己见,却往往失之穿凿,以致以己意强加于圣人,偏离乃至违戾了经文本意。在他看来,此书虽为依托《论语》的解经之作,但由于发挥己意太过,其意义已经溢出了经文,实际上几乎成为一部与《论语》平行的著作:“今读此书,虽名为说论语者,然考其实,则几欲与论语竞矣。”(47)
这种批评相当严厉,未尝假以辞色。虽然朱熹之言并非定评,四库馆臣更以“讲学之家,于一字一句之异同,务必极言辨难,断不肯附和依违,中间笔舌相攻,或不免于激而求胜”视之,认为“不必执文集旧稿,以朱子之说相难”(48)。但是,研读《论语解》,我们可以发现,张栻解经的确不重字词训释,而重在阐发义理,发挥己意。我们不必以朱熹之说为依据非难张栻,却不能忽视朱熹的批评中所透露的信息。
这种解经风格的形成,与时代学术风尚有密切关系。北宋中期义理之学的兴起,使学者摆脱了汉唐繁琐学风的影响,不再拘囿于经传注疏而注重对经义的自我体认与自由发挥。在他们看来,解经不必一味受到经书文字束缚,只要义理通达,即使文义解错也无妨。二程说:“善学者,要不为文字所梏。故文义虽解错,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49) 以这种观念看,解经是否得当,主要在于能否使道理通达。而在他们看来,解经者的主观体认才是衡量义理通达的标准。张载说:“心解则求义自明,不必字字相较。”(50) 二程说:“思索经义,不能于简策之外脱然有独见,资之何由深?居之何由安?非特误己,亦且误人也。”(51) 这种学风,促进了新的儒学体系的建立,有其历史意义,但是,这种学风也存在着矫枉过正之弊,其流风所及,致使后来很多学者解经,往往忽视对经文本义的探究,着重发挥己见,自立其说。在南宋时期,这种现象已经蔚然成风。朱熹谈到当时学风说:“近世说经者,多不虚心以求经之本意,而务极意以求之本文之外,幸而渺茫疑似之间略有缝罅如可钧索,略有形影如可执搏,则遂极笔模写,以附于经,而谓经之为说本如是也。”(52) 这种时代风气,很容易对个人治学风格产生影响。
张栻《论语解》解经风格的形成,也与他对《论语》的认识有关。在《论语解序》中,张栻说:“《论语》之书,孔子之言行莫详焉……圣人之道至矣,而其所以教人者,大略则亦可睹焉。盖自始学,则教之以为弟为子之职,其品章条贯不过于声气容色之间,洒扫应对进退之事。此虽为人事之始,然所谓天道之至赜者,初亦不外乎是,圣人无隐乎尔也。故究其始则有致知力行之地,而极其终则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亦贵于行著习察,尽其道而已矣。”(53) 在张栻看来,《论语》中“声气容色之间,洒扫应对进退之事”,虽为人事之始,但实际上其中蕴含了高深幽邃的天道。日用常行之事是致知力行的本原,不断致知力行,努力察识,“极其终”就能把握“非思勉之所能及”的天道。这种对人事与天道关系的认识,使张栻非常关注从具体而微的人事之中发掘、体会抽象深奥的天道,由此也决定了张栻《论语解》注重阐发事中之理、重视从性与天道层面立论的旨趣。
在《论语解》解经风格的背后,有其方法论的支撑。张栻强调对于《论语》应当沉潜其中,熟读精思,反复玩味:“《论语》不可一日不玩味”。(54)“且当熟读《论语》,玩味圣人所以教人与孔门弟子学乎圣人者,则自可见。”(55) 这里所谓玩味,是指涵泳于文本之中,反复体察、思索,领会把握其精神实质。这种玩味、体察所强调的是通过心思专一、精神集中的“持敬”工夫,进入经典的义理世界,达到与圣人在精神意蕴中的契合。因此,张栻反对仅从语言文字入手解经,认为仅通过语言的辨析、文字的训解,不可能达到对经文的真正理解:“大抵读经书须平心易气,涵泳其间……要切处乃在持敬。若专一,工夫积累多,自然体察有力。只靠言语上苦思,未是也。”(56) 在与友人讨论读《二程先生遗书》时,张栻说:“若只靠言语上求解,则未是。须玩味其旨,于吾动静之中体之,久久自别也。”(57)
显然,张栻关注的重心不在言语训释,而在于对经义的玩索。玩索经义,重在对经义的深入体会,通过对文本精神实质的把握实现与圣人的精神沟通。如果局限执着于语言,则会堵塞与圣人心心相契的通道。然而,玩索经义达到与圣人之心相通的标准为何?恐怕就只能是类似张载“心解”之类的自我体认与证悟了。这一思路体现在解经过程中,解经者的主体地位无疑会被大大突显。就这一点而言,朱熹批评张栻《论语解》“尽黜其言而直伸已见”,“自信太重,视圣贤太轻,立说太高”,(58) 批评的立场可以商榷,但的确已经触及了问题的实质。
不难看出,在解经方法论上,张栻与朱熹是存在差异的,而差异的关键在于对经文字词的态度。朱熹曾在给张栻的信中自称“熹则浅暗迟钝,一生在文义上作窠窟”。此语含有明显的反讽意味,针对的乃是张栻“见理太明,故于文意琐细之间不无阔略之处”。(59) 在朱熹看来,训释、理解文字是求得经文义理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学者之于经,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60) 因而张栻对语言文字的轻视,在朱熹看来就不免疏阔。这种解经方法论的差异,是导致张栻与朱熹解经风格不同的根本原因。朱熹对张栻之学的批评,根源也可以追溯到方法论的不同。
在对《论语》玩索体察过程中,张栻在很多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不乏精辟之论,为历代的《论语》解说者所重视关注。与张栻就《论语》解说反复诘辩的朱熹在其自认为“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的《论语集注》中也多次称引张栻之说。王若虚(1174-1243年)是金元之间著名学者,被吴澄称为“博学卓识,见之所到,不苟同于众”。(61) 王若虚对宋儒解经从总体上多有批评,但其《论语辨惑》则对张栻《论语解》不乏揄扬肯定之处。如他谈到,《学而》篇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段,二程解为:“弟子之职,力有余则学文,不修其职而先文,非为己之学也”。张栻则解为:“非谓俟行此数事有余力而后学文也,言当以是数者为本,以其余力学文也。”相较而言,张栻之解更为通达,“说甚佳”。(62) 宋末撰有《四书集编》的著名理学家真德秀则认为张栻与朱熹“二先生之书旁贯群言,博综世务,犹高山巨海,瑰材秘宝,随取随足”,张栻《论语解》《孟子说》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或问》一样“于学者为尤切,譬之菽粟布帛,不容以一日去者也。”(63) 从这些学者的评价中,我们或许可以略窥《论语解》的地位和影响。
三 《论语解》的理学意蕴
玩索经义、发挥己见的解经方式,使张栻得以依托《论语》文本而大量阐发其思想观点。在解说过程中,张栻将其理学观念熔铸于《论语》文本之中,赋予《论语》以理学的精神面貌。
“理”“天理”是理学中集宇宙本体与价值本体为一的核心范畴,张栻以“理”“天理”对《论语》中“天”“中”“礼”等范畴的内涵进行了阐发。
如“天”,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范畴,《论语》中多次提及。自二程体贴出“天理”二字,以“天者,理也”(64) 沟通了“天”与“理”的内涵之后,理学学者多沿袭这一思路,以理释天。《论语·宪问》中“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一段,张栻解云:“所谓天者,理而已。圣人纯乎天道,故其发言自然如此。”(65) 在这里,张栻按照二程等理学家的思路,直接将“天”等同于“理”,使二者实现了内涵上的相互置换,完成了对“天”范畴的理学化改造。
又如,“礼”是古代社会政治、伦理生活的基本原则与秩序规范。从周敦颐、二程开始,理学学者就以理释礼,将人伦社会之“礼”提升为贯通宇宙万物、社会人生的最高本体原则。周敦颐说:“礼,理也”,(66) 二程说:“视听言动,非理不为,即是理,礼即是理也。”(67)《论语解》也按照这一思路,以“理”对“礼”的内涵进行了阐释。《八佾》中“林放问礼之本”一章,张栻解云:“礼者理也,理必有其实而后有其文。文者,所以文其实也。若文之过,则反浮其实而害于理矣。”(68)《为政》“孟懿子问孝”一章,“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一段,张栻解云:“礼者,理之所存也。”(69)
基于对“礼”与“理”内涵的沟通,张栻进一步把“得其理”“失其理”作为判断是否合乎礼的标准。《先进》中“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一章,张栻解云:“葬以礼者,谓得其理也。颜子箪食瓢饮,居于陋巷,及其死,门人乃欲厚葬之,则失其理矣。”(70) 对于礼在社会伦理政治生活中的应用,张栻也从“理”的高度予以解释。《八佾》中“或问禘之说”一章,张栻解云:“夫礼者,天之秩也。禘之为礼,惟天子得用之,而诸侯不得用之者,盖天理之所当然也。天下万事皆有所当然者,天之所为也。苟知禘之说,则于治天下之道如指诸掌之易明,亦曰循其理而已矣。”(71) 在这里,张栻以“天理之所当然”说明了“礼”所强调的等级秩序的神圣性、合理性,突出了其不可逾越的特点。由此他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循理而行,则无往不利。张栻还以“循其理”对礼的因革损益的必然性进行了说明。《为政》中“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之说,张栻解云:“三王之礼各因前世而损益之,盖曰随时循理而已。以殷、周已验之迹而推之,则夫百王继承损益之常道盖可得而知矣。”(72) 礼须因时而变,这是“理”的内在要求,而礼的因革损益只不过是遵循理的法则而已。
《论语》中有“中”的范畴,在宋代理学话语系统中,“中”的重要性被大大突显。二程等理学家都对“中”进行了大量理学化的阐释。如二程说:“圣人与理为一,故无过无不及,中而已矣。”(73) 张栻在《论语解》中,进一步对“中”进行更为明确的理学化的诠释。《雍也》中“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一段,张栻解云:“中者,言其理之无过不及也。”(74)《尧曰》中“允执其中”一段,张栻解云:“允执其中,事事物物皆有中,天理之所存也,惟其心无所倚,则能执其中而不失,此所谓时中也。”(75)《子罕》中“可与立,未可与权”一段,张栻解云:“事事物物,莫不有中。中者,天理之当然,不可过而不可不及者也。”(76) 在上述解说中,张栻以“理”诠释“中”,进一步突出了“中”范畴的理学内涵,使“中”范畴完全理学化,成为其理学范畴系统中的重要内容。
对于《论语》中的其他思想资料,张栻多从“理”的高度进行了多角度的阐发,使其在理学的视域中呈现出新的意义。《论语》中多次以君子、小人二者对举,讨论二者之别。在《论语解》中,张栻从其天理人欲观出发,以天理人欲的理论框架对君子、小人进行了界定。《子路》中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一章,张栻解云:“和者,和于理也;同者,同其私也。和于理则不为苟同,同其私则不能和义,天理、人欲不两立也。”(77)《里仁》中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张栻解云:“盖君子心存乎天下之公理,小人则求以自便其私而已。”(78)《宪问》中“君子上达,小人下达”一章,张栻解云:“达者,达尽其事理也。上达者反本,天理也;下达者趋末,人欲也。”(79)《为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一章,张栻解云:“君子小人之分,公私之间而已。周则不比,比则不周,天理人欲不并立也。”(80) 在张栻的理论框架中,心存天理抑或心怀私欲,成为判定君子小人的标准,理欲之辨成为君子小人之别的真正内涵。通过张栻的诠释,君子、小人这两个概念具有了新的内涵,在其理学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除了对《论语》中的范畴及其他思想资料进行理学化的阐释,张栻还在《论语》解说过程中,依托经文对理学中的性与天道、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性情关系等主题进行阐述。
理学的一个重要思路是为人性寻求天道的依据,因此性与天道成为理学的重要主题。但是在《论语》中却并无太多直接探讨性与天道的内容,甚至子贡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之叹。在宋代以前,注疏之家仅以“夫子之道深微难知”(81) 进行解说,并未肯定天道性命乃圣人之学的重要内容。为了突出性与天道的主题,肯定圣人对性与天道的重视,为理学重视探求天人性命之奥的致思方向寻求理论依据,二程、张载等理学家对子贡之语进行了种种解说与发挥。张栻把子贡之语解释成为耳之闻不是真正的闻,凭耳目之官不可能真正深入领悟、体会圣人所谈的性与天道:“不以苟知为得,不以了悟为闻。”(82) 二程则肯定性与天道“可自得之,而不可以言传。”(83) 张栻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加以发挥:“文章谓著于言辞者。夫子之文章,人人可得而闻也;至于性与天道,则非闻见之所可及,其惟潜泳积习之久而有以自得之。自得之,则性与天道亦岂外乎文章哉?”在张栻看来,性与天道非常深邃,无法以闻见达到对性与天道的把握。但性与天道虽然具有超越性,却不外乎文章之中,只有反复涵泳、长期积累,才有可能深造自得,达到对性与天道的体认、领悟。通过张栻的解说,子贡之言被赋予了丰富的理学意蕴:“曰性,又曰天道者,兼天人性命之蕴而言之也。”(84)
二程、张载等理学学者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人性理论。他们将人性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由此建构起一套颇为完整的人性理论。在解说《论语》的过程中,张栻按照理学人性论将人性区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基本义理间架,对其人性理论进行了阐发。《述而》“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一句,张栻解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之生斯人,无不具德于其性也,人则自息之耳,惟圣人为能全夫天之所命。曰‘天生德于予’,而所为与天理无间者,亦自可见矣。”(85) 这是对人的天命之性本然至善的说明。张栻认为,人皆受天命而成性,天命之性,纯粹至善,人人皆具,但只有圣人能够保全其天命之性。《阳货》中“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句,张栻解云:“原性之理,无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论性之存乎气质,则人禀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与禽兽草木异。然就人之中不无清浊厚薄之不同,而实亦未尝不相近也。不相近则不得为人之类矣,而人贤不肖之相去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者,则因其清浊厚薄之不同,习于不善而日远耳。习者,积习而致也。善学者克其气质之偏,以复其天性之本,而其近者亦可得而一矣”。(86) 在这里,张栻指出,从性之理看,人、物之性皆善,但从气质之性的角度看,人禀受天地之精,五行之秀,而人与人的气禀虽有清浊、厚薄之不同,但同为人类,仍相去不远。最终贤者与不肖之人之所以在现实表现中有天壤之别,则是由于在气质清浊、厚薄不同的基础上习染不同而导致的。善学者,就应当克去其气质偏弊,恢复本然至善的天性。张栻通过诠释经文,对其人性理论进行了颇为详细的阐发,而“天生德于予”“性相近,习相远”等文本在理学的视域中又呈现出了崭新的意义。
性情关系是宋代理学家集中讨论的问题。张栻在《论语》解说中,也非常重视从性情角度予以发挥。《子罕》中“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张栻解云:“好德,因人之秉彝;而目之于色,亦出于性也。然此则溺其流而不止,彼则汩其情而不察,是何欤?则以夫物其性故耳。故君子性其性,而众人物其性。性其性者,天则之所存也;物其性者,人欲之所乱也。若好德如好色,则天则存而人欲遏,性情得其正矣。”(87) 在张栻看来,人具有至善的德行,同时也具有耳目口腹之欲,这是气质之性的表现,如果拘于形气,诱于物欲,则会汩乱其情,使感性情欲占据支配地位,从而失去其本性之正。君子就能够使情感欲望符合天理的要求,而众人则往往放纵感性情欲而乱其性。所谓“好德如好色”,在张栻的阐述中,就是天理存而人欲遏,性情得其正。
在对《论语》中孔子论《诗》的诸多言论进行解说时,张栻也多从性情关系角度加以阐发。《八佾》中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张栻解云:“哀乐,情之为也,而其理具于性。乐而至于淫,哀而至于伤,则是情之流而性之汩矣。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不逾,则性情之正也。”(88)《泰伯》中有“兴于《诗》”一语,张栻解云:“学《诗》,则有以兴起其性情之正,学之所先也。”(89)《为政》中有“《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一章,张栻解云:“学者学夫《诗》,则有以识夫性情之正矣。”(90) 按照张栻的解说,孔子论《诗》,之所以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思无邪”“兴于《诗》”之类的评价,是因为《诗》能得“性情之正”,或者能借以识“性情之正”,或者能够兴起其“性情之正”。很显然,性情关系已经成为张栻解说《论语》中孔子《诗》论的立论基点与切入点。
总体而言,张栻立足其理学立场对《论语》进行了具有浓厚理学色彩的阐释。张栻对《论语》的思想资料阐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赋予这些思想资料以理学意蕴,将《论语》纳入理学轨道的过程。可以说,《论语解》是张栻的解经之作,也是阐述其自身思想的理学著作。
[收稿日期]2010-11-16
注释:
① 张栻《论语解》,《南轩先生论语解序》,《张栻集》第3页,岳麓书社2010年版。
② 《论语解》,《南轩先生论语解序》,《张栻集》第4页。
③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322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④ 《二程集》第205页。
⑤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六,《答陈平甫》,《张栻集》第733页。
⑥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五,《寄吕伯恭》,《张栻集》第718页。
⑦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二,《答朱元晦》,《张栻集》第695页。
⑧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六,《与吴晦叔》,《张栻集》第761页。
⑨ 《论语解》卷一,《学而》,《张栻集》第5页。
⑩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二,《为政》,《十三经注疏》第2462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1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一,《为政》,第5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12) 《论语解》卷一,《为政》,《张栻集》第14页。
(13) 《论语解》卷一,《为政》,《张栻集》第14页。
(14) 《论语解》卷一,《学而》,《张栻集》第8页。
(15) 《论语解》卷三,《公冶长》,《张栻集》第35页。
(16) 《论语解》卷五,《子罕》,《张栻集》第74页。
(17) 《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五,《子罕》,第113页。
(18) 《论语解》卷七,《宪问》,《张栻集》第121页。
(19) 《论语注疏》卷十四,《宪问》,《十三经注疏》第2512页。
(20)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一,《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朱子全书》第13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1) 《二程集》,第140页。
(22) 《二程集》,第247页。
(23) 《论语解》卷三,《雍也》,《张栻集》第50页。
(24) 《二程集》,第1143页。
(25) 《二程集》,第608页。
(26) 《二程集》,第100页。
(27)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七,《答宋教授》,《张栻集》第747页。
(28)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论语要义目录序》,《朱子全书》第3614页。
(29)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语孟集义序》,《朱子全书》第3630页。
(30) 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第31-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31)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五,第2625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32) 钱穆《朱子新学案》下册,第1437页,巴蜀书社1986年版。
(33) 《朱子新学案》下册,第1581页。
(34)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四,《答朱元晦》,《张栻集》第713-714页。
(35)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六,《答刘宰》,《张栻集》第736页。
(36)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答朱元晦秘书》,《张栻集》第681页。
(37)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一,《答陈平甫》,《张栻集》第688页。
(38)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五,《答胡伯逢》,《张栻集》第724页。
(39)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四,《答朱元晦》,《张栻集》第708页。
(40)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七,《答胡广仲》,《张栻集》第744页。
(41)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七,《答乔德瞻》,《张栻集》第748页。
(42) 《论语解》卷二,《里仁》,《张栻集》第29页。
(43) 《论语解》卷三,《雍也》,《张栻集》第49页。
(44)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二,《答石子重》,《朱子全书》第1922-1923页。
(45)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三,《答朱元晦》,《张栻集》第704页。
(46)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一,《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朱子全书》第1357-1384页。
(47)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一,《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朱子全书》第1370页。
(48)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五,《癸巳论语解》,第464页,中华书局1997年整理本。
(49) 《二程集》第378页。
(50) 张载《张载集》第276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
(51) 《二程集》第1186页。
(52)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一,《答万正淳》,《朱子全书》第2415页。
(53) 《论语解》,《南轩先生论语解序》,《张栻集》第3页。
(54)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七,《答潘端叔》,《张栻集》第750页。
(55)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六,《答周允升》,《张栻集》第704页。
(56) 《南轩先生文集》卷十九,《答潘端叔》,《张栻集》第667页。
(57)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三,《答胡季随》,《张栻集》第726页。
(58)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一,《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朱子全书》第1375页。
(59)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与张敬夫论程集改字》,《朱子全书》第1324页。
(60)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八十一,《书中庸后》,《朱子全书》第3831页。
(61)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六,《滹南遗老集》,第2200页。
(62) 王若虚《滹南集》卷四,《论语辨惑》,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0册,第2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3)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四十,《劝学文》,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4册,第617-618页。
(64) 《二程集》第125页。
(65) 《论语解》卷七,《宪问》,《张栻集》第124页。
(66) 周敦颐《周敦颐集》卷二,《通书·礼乐》,第25页,中华书局2009年版。
(67) 《二程集》第144页。
(68) 《论语解》卷二,《八佾》,《张栻集》第20页。
(69) 《论语解》卷一,《学而》,《张栻集》第12页。
(70) 《论语解》卷六,《先进》,《张栻集》第90页。
(71) 《论语解》卷一,《八佾》,《张栻集》第22页。
(72) 《论语解》卷一,《为政》,《张栻集》第18页。
(73) 《二程集》第307页。
(74) 《论语解》卷三,《雍也》,《张栻集》第50页。
(75) 《论语解》卷十,《尧曰》,《张栻集》第165页。
(76) 《论语解》卷五,《子罕》,《张栻集》第77页。
(77) 《论语解》卷七,《子路》,《张栻集》第112页。
(78) 《论语解》卷二,《里仁》,《张栻集》第32页。
(79) 《论语解》卷七,《宪问》,《张栻集》第120页。
(80) 《论语解》卷一,《为政》,《张栻集》第15页。
(81) 《论语注疏》卷五,《公冶长》,《十三经注疏》第2474页。
(82) 《张载集》第307页。
(83) 《二程集》第1253页。
(84) 《论语解》卷三,《公冶长》,《张栻集》第37页。
(85) 《论语解》卷四,《述而》,《张栻集》第57页。
(86) 《论语解》卷九,《阳货》,《张栻集》第145页。
(87) 《论语解》卷五,《子罕》,《张栻集》第74页。
(88) 《论语解》卷二,《八佾》,《张栻集》第24-25页。
(89) 《论语解》卷四,《泰伯》,《张栻集》第64页。
(90) 《论语解》卷一,《为政》,《张栻集》第11页。
标签:论语论文; 朱熹论文; 儒家论文; 读书论文; 学而论文; 理学论文; 国学论文; 为政论文; 孔子论文; 二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