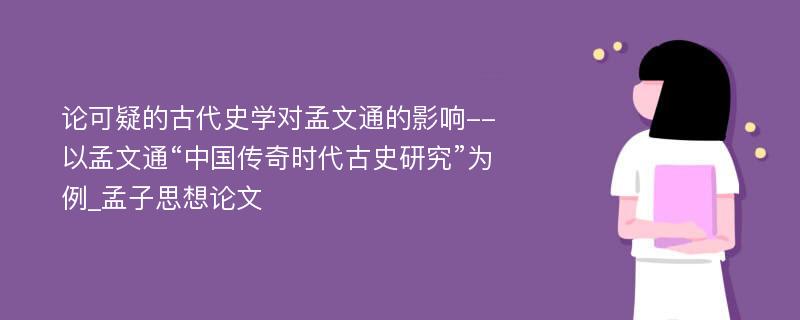
试论疑古史学对蒙文通的影响——以蒙文通的中国传说时代古史研究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为例论文,中国论文,试论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22X(2010)03-0034-08
蒙文通是疑古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著名古史专家。他的治学既与“疑古派”学分两途,同时二者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剖析蒙氏之学,可以透视出20世纪前半叶不同史学流派间矛盾、交流和交融的跌宕起伏,对于今天正确认识并评价“古史辨派”及疑古运动也具有一定的表征意义。
一、早期疑古运动中的古史传说研究
清理中国传说中的古史,这是现代疑古运动一上手就面临的一个课题。“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中国人头脑中的这一层根深蒂固的意识,成为横亘在以破除封建迷信为职志的疑古健将面前的一大障碍。所以,早在提出著名的“层累说”以前的“民国十一年(1922)”,顾颉刚先生已在“《努力周刊》副刊的《读书杂志》里对于三王的第一代(禹)和五帝的末二代(尧舜)”下了“一番破坏”,“把关于他们的传说作了一番系统的建设”;同年,顾因祖母病重回故乡,经胡适介绍,商务印书馆特邀请顾编写一部《中学历史教科书》[1](第七册中,P45),顾“想了许多法子,要把这部教科书做成一部活的历史,使得读书的人确能认识全部历史的整个的活动,得到真实的历史观念和研究兴味”。对于“上古史”中三皇五帝的传说,顾在编写前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三皇五帝的系统,当然是推翻的了。”[2](P51)为此,顾拟仿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视三皇五帝为“传疑时期”的做法,专“列了一章‘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正是在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过程中,顾在理论上有了重大创获。他“忽然发现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的问题”!思考的结果是“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2](P52)。这说明,“层累说”的胎育与“三皇五帝”的辨正有着直接的因缘关系,并且早在1922年顾先生已经有了初步的想法。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一事,后虽因主管当局以“否定三皇五帝动摇了民族的自信力”为由加以阻挠最终未果[1](第七册中,P45),但它在“层累说”的构思、酝酿及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却是不应忽视的。
1923年,顾提出了“层累说”,此说仍然紧紧咬住传说中古史的一些问题,以此作为理论阐述的突破口。“层累说”发表后,刘掞藜、胡堇人提出了批评,1923年顾撰《答刘胡两先生书》,提出了理解中国古史的四条原则,四条中的两条比较具体地谈到了对传说中古史内容的甄别:(一)打破民族一元的观念。顾先生认为,自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扩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亦渐渐归到了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从而造成了“在现在公认的古史上,一统的世系已经笼罩了百代帝王,民族一元论可谓建设得十分巩固了”的现象。但是,根据史书的记载,周出于姜嫄,任、宿、须句出于太昊,郯出于少吴,陈出于颛顼……他们原是各有各的始祖。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民族的分合为分合,寻出他们的系统的异同状况。”(二)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指出:古人对于神和人原没有界限,所谓历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话,人与神混,人与兽混,举不胜举。“他们所说的史固决不是信史,但他们有如是的想象,有如是的祭祀,却不能不说为有信史的可能。自春秋末期以后,诸子奋兴,人性发达,于是把神话中的古神古人都‘人化’了。人化固是好事,但在历史上又多了一层的作伪”;“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那时人的想象的史为史,考出一部那时的宗教史,而不要希望考出那时以前的政治史,因为宗教是本有的事实,政治是后出的附会,是假的”[2](P100-101)。显然,顾先生的所论已经明确指向了对传说中古史的清理,其中涉及到了许多民族始祖的神话传说。顾先生这里使用了神话的“人化”这个概念。虽然顾先生承认有关古史的神话传说中“有信史的可能”,但同时又认为“他们所说的史决不是信史”,这样,顾先生就自相矛盾地否定并轻易放弃了他论断中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思想胚芽,即:“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那时人的想象的史为史,考出一部那时的宗教史。”而顾的这一卓识却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蒙文通《古史甄微》的核心论点(见后文)。自然,1923年顾先生所谈传说中的古史,无论从内容的广度还是从论证的深度来看,都还是浅近的,因而是初步的。但自觉地将传说中的古史置于现代文化认知的背景下加以批判地考察,顾先生终是最先的觉悟者。
“层累说”发表后影响巨大,“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3](P17),顾说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是自然的。就在“层累说”发表四年后的1927年,中国古史研究领域诞生了第一部从地缘因素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古代民族和文化差异的代表性专著——蒙文通的《古史甄微》。
从“疑古”的角度看,《古史甄微》的面世是值得重视的一件事。蒙文通治学的基本立场自然不是“疑古”而更加接近于“考古”、“释古”一派;他撰写《古史甄微》,旨意也不在疑古上。如《古史甄微》“七”为“上古文化”,“八”为“虞夏禅让”,“九”为“夏之兴替”,基本上是将从上古到夏代作为一部信史来勾勒的。而我们看顾颉刚、童书业的《夏史三论》,却认为整个夏代的历史是由神话传说演变而来①。此可见蒙文通与疑古派的不同。以此,蒙默《蒙文通先生小传》指出:“时疑古之风方兴,或颇引为同道,谓‘在他之前,没有像他那样把三皇五帝彻底研究过’。并以此即先生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然先生之破三(皇)五(帝)说也,止以其体系不足据而已,并非娲燧牺农两喾祝公诸传说而摒弃之,故与疑古者流迥异其趣。”[4](P324)虽然如此,蒙默之说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蒙默谓蒙文通“与疑古者流迥异其趣”,这大体上固然不错。但值得注意的是蒙默点出了“当时人”对蒙文通“此即先生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定位。这个定位虽与蒙默谓蒙文通“与疑古者流迥异其趣”的立场相径庭,因此“大体上”可以视为当时学界的一部分人对于蒙文通的“误解”甚至是“曲解”。但此种“误解”乃至于“曲解”仍然有意义,它至少表明客观上当时人有将蒙氏视为疑古派的意思。在时过境迁80年后的今天,此说提醒我们,在当时人的眼中,“疑古”与“释古”、“考古”派之间的界限并不像今天的“考古派”之评价“疑古派”那样视同水火。其次,之所以说学界有人将蒙文通视为疑古派只是“大体上”的一种误解或曲解,是因为从蒙文通治学的具体内容来看,存在着他对于疑古派关键性学术成果的借鉴和利用。因此只能说:蒙仅仅大体上“与疑古者流迥异其趣”而已。换言之,蒙文通与“疑古派”的治学,二者并非泾渭分明。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在20世纪20-40年代疑古之风炽烈,这个大背景对蒙氏之撰写《古史甄微》的影响不容否认。事实上,作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学术派别,疑古派的一些学术精华——尤其是疑古派的方法论——对于考古、释古两派都有影响。这点从蒙文通的治学中体现得很明显。
二、蒙文通的学术渊源及《古史甄微》
蒙文通与“前古史辨派”的疑古代表性学人在学术上有着渊源互接的关系。这不仅因为蒙文通是廖平的弟子,而且因为他的代表作《古史甄微》就是为了完成廖平的嘱托而撰述。正如《古史甄微》蒙氏《自序》所言:
乙卯(1915)春间,蒙尝以所述《孔子古文说》质之本师井研廖先,廖先不以为谬。因命曰:“古言五帝疆域,四至各殊;祖孙父子之间,数十百年之内,日辟日蹙,不应悬殊若是。盖纬说帝各为代,各传十数世,各数百千年。五行之运,以子承母,土则生金,故少昊为黄帝之子。详考论之,可破旧说一系相承之谬,以见华夏立国开化之远,迥非东西各民族所能及。凡我国人,皆足以自荣而自勉也。”蒙唯诺受命。[5](P335)
按:廖平要破除古帝王世系的“一系相承之谬,以见华夏立国开化之远,迥非东西各民族所能及”,此说系针对20世纪初章太炎、刘师培等提出的华夏民族西来说而发,其中虽不乏与章、刘之间今古文经之争的经师门户意味,但基本的旨趣是立在培养国人的中华民族自豪感上的。而顾颉刚“层累说”要破除“一统的世系”和“民族一元论”,虽然顾说是为了铲除国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迷信,与廖平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但二说目标一致,这一点颇值得注意。蒙氏《古史甄微》提出了“太古民族显有三系之分”的卓越论断[5](P337),将我国上古居住民划分为分别活动于江汉、河洛、海岱三大地区内。蒙氏整个学术框架的逻辑起点即在于破除或者说否认中华民族起源之一系说。考虑到廖平与蒙文通的师承关系和蒙文通实际受到过疑古派重要影响的事实,蒙氏的整个论断既可以视为承袭并发展廖平而来,也可以说与“层累说”有关,至少不相枘凿。
蒙文通的治学系从治经入手,他的治经则从辩证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切入。
对于今文一派的一些核心观点蒙氏均感不满,指出:“刘(逢禄)、宋(翔凤)、魏(源)、崔(适)、康(有为)之流,肆为险怪之辨,不探师法之源,徒讥讪康成,诋讦子骏……即以是为今文,斯谓之能讪郑则可,谓之今文则不可。……鱼目混珠,朱夺于紫,其敝也久矣。”[5](P336)“《左》书多符六经,安得日不祖孔子?”[5](P338)按,蒙氏师廖平之学曾有数变,在撰《今古学考》时他尚能对今古两家不分轩轾②。但到了蒙文通撰写《古史甄微》的1927年,廖平之学早已数变而根底移易,以大诋郑玄,尤以讥诃刘歆造伪为能事了。现蒙氏对常州一派的非康成、刘歆深致不平,又谓《左传》“祖孔子”也就是认为《左传》“传”《春秋》,此皆大不同于刘逢禄下至于康有为视《左传》为经刘歆改窜之伪学的论断,亦与廖平数变之学根本不同。然溯其渊源,蒙氏之论却仍然系植根于廖《今古学考》而扬弃者。蒙默所言“先生以秦以前无经学,经学乃始于汉,既为先秦诸子之总结,故其精义在传记不在六经,在礼制不在义理,在行事不在空言”[4](P324),这个观点也与廖平针锋相对,然亦益发可见蒙氏之学脱胎于廖平之迹③。
蒙氏对于今文经学不满,对于古文经学,蒙氏同样提出了批评。在蒙氏看来,古文之弊在于“徒诋谶纬,矜苍、雅,人自以为能宗郑,而实鲜究其条贯”[5](P336)。何谓“条贯”?“条贯”者,“义理”之谓也。蒙氏意谓若只重苍、雅考订,没有“条贯”义理,此于康成颇类买椟还珠,徒然袭得郑玄之皮毛而已,却并未明其精华之所在。这种议论,很容易使人想起章实斋批评乾嘉考据学的饾饤而缺乏“别识心裁”。自乾隆年间庄存与复兴濒临死绝的今文经学以来,上自清代中期的刘逢禄、宋翔凤,下迄中国近代的龚、魏、廖、康,重视六经中的“微言大义”始终是今文家坚守的治学方向,今文家并且以此为据批评古文家的繁琐考据而不得要领。蒙氏学出廖平,在重条贯义理方面容或继承了今文经学的某些治学精神。古文家均信奉“六经皆史”,尤其章太炎、刘师培等,“六经皆史”更是他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但在蒙氏看来,史以真为先,六经中的历史人物如商汤、周武王的“记法”均与《汲冢书》、《山海经》所言相异,则究竟各说何者为真?在这个问题未辨明以前,“六经皆史之谈显非谛说”[5](P338)。蒙氏师从廖平,廖平与章太炎、刘师培辈势同冰炭。在《古史甄微》的写作时代,今古文经之争仍然激烈,“数十年来,两相诋諆嘲嚷,若冰炭之不可同刑”[5](P336)。蒙氏指摘“六经皆史”论的瑕疵,恐多少受到了其师攻击章太炎、刘师培等古文经学的影响。但蒙氏毕竟已非一介经师,而是一位学养深厚的现代学者,他批评“六经皆史”,并不是站在传统今文家派立场上的狭隘陋见,而能够跳出今、古两家的门户,站在现代学术立场对于今、古文经作出评骘。以史之求真为旨归是蒙氏的基本立场。从治史求真出发,蒙氏既探究今文经学内部鲁学与齐学之异同,于上古因地缘之差异而导致的神化传说的各不相同,蒙氏亦无不穷源而竟委之。蒙文通之于廖平虽有上述如许矛盾,但在文化研究的地缘性方面,蒙氏却受到了廖平的深刻影响。
廖平提出了以地缘划分今文内部的鲁学、齐学和古文经学的主张,指出:“鲁、齐、古三学分途,以乡土而异”;“邹与鲁近……荀子赵人,而游学于齐,为齐学。《韩诗》燕人,传今学而兼用古义,大约游学于齐所传也。《儒林传》谓其说颇异,而其归同。盖同乡皆讲古学,一齐众楚,不能自坚,时有改异,此韩之所以变齐也。而齐之所以变鲁,正亦如此。予谓学派由乡土风气而变者,盖谓此也”[6](P41)。乡土异则学术文化受其影响肯定存在差异,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廖平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是他的卓识。廖一生固守“鲁、齐、古三学分途,以乡土而异”的理念,这个认识成了蒙文通理论框架的基石。如其自谓:“余作《经学抉原》,深信齐鲁学外,而古文为三晋之学,则经术亦以地域而分。”[5](《自序》,P348)从辨镜学术源流出发,蒙氏再由今文而上,探其异同之故,指出:“古文学既南北异趣,今文学亦齐、鲁殊致,适海适岱,言各有宗。”[5](P337)他分析地缘文化的差异性,认为:“盖鲁人宿敦礼义,故说汤武俱为圣智;晋人宿崇功利,故说舜禹皆同篡窃;楚人宿好鬼神,故称虞夏极其灵怪。三方所称述之史说不同,盖即原于其思想之异。《古史甄微》备言太古民族显有三系之分,其分布之地域不同,其生活与文化亦异。六经、《汲冢书》、《山海经》,三者称道古事各判,其即本于三系民族传说之史固各不同耶!”④ 按,六经、《汲冢书》、《山海经》之评价商汤和周武王的伐夏、商的确存在明显的矛盾。在学术史上过去从未有人探讨形成此种矛盾的原因,更没有人从鲁、晋、楚因地缘差异而产生出的不同文化背景来加以说明。因此,蒙文通之说具有开创性意义。
又如,《孟子》中多载史事并且“尽人所信”。但蒙文通注意到,如果“以《孟子》书证《孟子》书”即采用校勘学上的“内证法”,可以发现,除了孟子的说法以外,“显有异家之史存于其间”。两相比较的结果,“孟子所称述者若可疑,而孟子所斥责者翻若可信”。如关于伊尹辅佐商汤一事,《孟子》中提到了万章的说法。孟子不同意万章,但万章之说却有《韩非》之说为之佐证,蒙文通认为,《孟子》中的矛盾之处足见“万章之疑非诬”,反证孟子之说可疑。以此,“六经皆史论”如何站得住脚?蒙氏又指出,关于伊尹的相关说法,孟子与《韩非》、《天问》不同而“惟墨翟与合”,原因何在?蒙氏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岂以邹鲁所传自相同,而与晋、楚之说各异耶?”[5](P339)
从地缘角度考察经学内部的分化以及今、古二学之所以异趣,是廖平已经初步建立的学术路径。蒙文通则进一步拓展了廖平,他的考察也从经学扩大到了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范围从六经扩大到了《汲冢书》、子书、《山海经》和三皇五帝,这些都是廖平所未曾涉及的领域。但蒙文通的学术基点却仍然不能不说是由廖平奠定的。
三、“三皇五帝”的考订与蒙氏对“层累说”的袭用
救亡图存保国保种,这是自甲午战败后萦绕在国人脑际挥之不去的一个“结”。以此,探讨中华民族的起源,便成为20世纪初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下至于疑古运动勃兴,因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与神话传说杂糅一处难解难分,于是世纪初叶已然兴起的民族研究热到了二三十年代仍然持续不减。蒙氏的研究重点之一即是考察上古时代中华民族的起源与构成,厘清有关三皇五帝的传说便成为蒙氏绕不过去的第一道“坎”。对于三皇五帝的传说,蒙氏认为起于晚周,《汉书·郊祀志》中有“梁巫、晋巫、秦巫、荆巫、晋巫祀五帝”之说,可见“五帝”原先只是“神祇”,并没有确指的人名。不仅如此,而且在天神中贵者为“泰一”,五帝只是泰一之“佐”,也就是说,在最初的传说中五帝的地位比起泰一来还要次一等,并不像后世抬得那样高。到了汉武帝时有人上书说:“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祀三一:天一、地一、泰一。”结合秦始皇时博士所奏言“古者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贵”,蒙氏指出:“三皇之说,本于三一,五帝固神祇,三皇亦本神祇,初为神,不谓人也。”按,三皇五帝“本神祇,初为神,不谓人”,也就是承认了三皇五帝之成为“人”,系由“神”变化而来。这个论断中显然有着“层累说”中提出的“自春秋末期以后,诸子奋兴,人性发达,于是把神话中的古神古人都‘人化’了”的影子。1936年顾颉刚撰《三皇考》,其中即专列有“‘皇’的由神化人”一节,认为“三皇”“是介于神与人之间的人物”[1](第七册中,P51)。而顾《三皇考》的基本方法仍然是“层累说”。从考察三皇五帝传说的历史性着眼,自1923年顾的“层累说”,到1927年蒙的《古史甄微》,再到1936年顾撰《三皇考》,“疑古”与“释古”或“考古”,两家的结论基本一致,这表明了“疑古派”和“释古派”或“考古派”在学术上互依互存相通的一面。
再看蒙氏论“三王”、“五帝”和“三皇”的发生次序,蒙氏谓:“撮周秦书之不涉疑伪者而论之,孟子而上,皆惟言三王,自荀卿以来,始言五帝,《庄子》、《吕氏春秋》乃言三皇。……战国之初惟说三王,及于中叶乃言五帝,及于秦世乃言三皇。”按,孟在荀前,毫无疑义。而依照蒙氏时代的一般认识,《庄子》、《吕览》成书更在荀子以后,那末,蒙氏之论中有关“三王”、“五帝”和“三皇”发生次序的考订,其与“层累说”时愈后则说愈详,“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的精神内核如出一辙。所以蒙文通认为:“帝之与皇,固无关人事也。方皇、帝说之起初,皇则一而帝五,及郑(玄)注《中候》,又列少昊于五帝,则又皇三而帝六,弥附会而弥离本也。”[5](P349)看蒙氏的这个揭示,其基本方法与“层累说”同样灵犀相通,即追踪初始史实在历史上的“放大”或变更是顾、蒙两家的共同取径。
当然,蒙氏与顾颉刚也存在明显的不同,即按照地缘性差异来探讨神话传说之不同,并考察上古民族的形成以及学术文化的差别,这是蒙氏从廖平那里承袭而来并加以发展的独家之学,却是顾颉刚未曾措意或重视不够的所在。在考察“五帝”说的缘起过程中,蒙氏即具体运用了文化的地缘性差异的理念和方法,指出,《孙子·行军》:“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蒋子万机论》:“黄帝初立,不好战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称号,交共谋之。”这是最早的五帝说。其说将黄帝与四帝并称为“五帝”,“与齐、秦之说各不同,别为吴楚之说。五帝说始见《孙子》,三皇说始见《庄子》,岂三五皆南方之说,邹子取之而为之释,乃渐遍于东方、北方耶?”[5](P351)这里,蒙文通以地域为据论五帝说的起源并推测其流布的路向,带有鲜明的地缘性文化研究的特点。由此出发,蒙文通将上古时期我国先民文化的发展,明确划分为三大块,即“江汉民族”、“河洛民族”和“海岱民族”,“其部落、姓氏、活动地域皆不同,其经济、文化亦各具特点”[4](P324)。值得注意的是,蒙文通并没有将传说中的人物机械、僵硬地理解为某一个人,而是能够将其视为某一族群的代表。例如蒙氏在谈到共工与姜姓的关系时指出:“共工固世为诸侯之强,自伏羲以来,下至伯夷,常为中国患。而共工固姜姓炎帝之裔也。”[5](P375)《史记·五帝本纪》言:“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迁徙往来无常处。”蒙氏据此认为西北的黄帝部族为“游猎民族”,“为行国”;“九黎”,群书或作“犁”,“犁”从“牛”;“三苗”者,亦“盖意均谓农稼”,“则西南民族为农稼民族”,“为居国”。蒙文通“江汉”、“河洛”、“海岱”三大部族的重要构想,对于徐旭生1943年撰《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提出我国古代“部族”的三集团说,即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具有重要的启迪性。蒙文通及徐旭生的这一前瞻性构想现在已经被大量考古实践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四、余论
重新评价疑古派是现今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关于这个话题,与疑古派同时代学者的意见对于今天全面、正确评价疑古派或许更具参考价值,因为这些亲切而直接的评论本身即富含历史的因素和意味。而本文之所以选录郭沫若、钱穆、徐旭生的相关论断,是因为他们都不属于疑古派,因此他们对疑古派的评价应当更加客观、公允并具有参考价值。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山郭沫若的成名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有自序,该自序另题《评古史辨》,收在《古史辨》第七册下。文中郭首先肯定了疑古派先他而发的一系列结论,如钱玄同“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时代底东西”;丁文江“《禹贡》晚出”等。胡适的见解得到了郭的首肯,认为胡适“较一般的旧人大体上是有些科学观念”,“就《古史辨》看来,他于古代的边际却算是摩着了一些”。对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郭沫若承认原本存在着隔阂,说:“从前因为嗜好的不同,并多少夹以感情的作用,凡在《努力周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读过。”这可以理解为郭与疑古派“政治立场”的不同,也可以说二者存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但在认真思考了“层累说”后,郭摒弃了“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承认顾说“确是个卓识”,认为顾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并未充足以前,他的论辩自然并未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的”。至于具体的古史考辨,郭也部分借鉴了疑古派的成果。例如郭考黄帝的来历,引《山海经》并下按语谓:“黄帝即是皇帝、上帝。”此说顾颉刚、杨向奎《三皇考》已先郭而发且考订极细密。郭沫若的重要甲骨文研究专著《甲骨文释》中有《释干支》一篇,郭提出轩辕“又为星名,即西方之狮子座”,“亦称王星”,“与黄帝号有熊,鲧化黄熊等传说,均有关系”[1](第七册下,P361-365)。而黄帝号有熊、鲧化黄熊等传说正是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已经注意到并运用现代神话学加以研究了的课题[1](第七册上《杨序》,P2)。
在顾颉刚同时代的学者中,钱穆的意见值得注意。如所周知,钱穆的治学立场与疑古派存在诸多抵牾矛盾,但钱穆并没有因此而全面否定疑古派。《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是顾颉刚有代表性的疑古论著,顾穆撰成此文后拿给钱先生看并请钱先生批评。钱穆撰《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对于顾文有关“五帝的传说”以及“刘歆伪造《左传》”、“五德终始说”中“五行相生”和“五行相克”等问题钱先生都提出了商榷,从中可见钱先生与疑古派的矛盾。但对于顾颉刚和《古史辨》特别是顾颉刚的“层累说”,钱先生的整体性评价却仍然很高。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出了有清一代的学术是“以复古求解放”,“最后到今文家上复西汉之古解放东汉郑许之学。譬如高山下石,不达不止”。钱穆虽指出梁说仍残存着今文家的门户遗绪,但基本还是同意此种文化诠释的进路,并指出“自今以后,正该复先秦七国之古来解放西周,复虞夏之古来解放殷商,溯源寻根,把中国从来的文化学术思想从头整理一过,给予一种较为新鲜而近真的认识,对于将来新文化思想的发展上定有极大的帮助”[7](P618),而钱将疑古派及《古史辨》放在“以复古求解放”的背景下予以透视后恰恰认为,“顾先生的《古史辨》,不用说是一个应着上述的趋势和需要而产生的可宝贵的新芽”。对于“层累说”,胡适从方法论的层面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钱穆对胡适的评价以及“层累说”的方法“也抱着相当的赞同”,认为“《古史辨》也是一种以复古为解放的运动”[7](P619)。时人有将顾颉刚和今文家混为一谈者①,钱穆则注意将顾颉刚与晚清今文家如康有为作了严格的区分,指出:“《古史辨》所处的时代已和晚清的今文家不同”。钱穆非常深刻地揭示了顾颉刚方法的可取之处是“重在传说的经历和演进”,“而康有为一辈人所主张的今文学,却说是孔子托古改制,六经为儒家伪造,此后又经刘歆王莽一番伪造,而成所谓新学伪经”[7](P620)。分析传说的演进和造伪之不同,钱穆提出了几点区分的标准,都很重要:
伪造与传说,其间究是两样。传说是演进生长的,而伪造却可以一气呵成,一手创立;传说是社会上共同的有意无意——而无意为多——的一种演进生长,而伪造却专是一人或一派人的特意制造;传说是自然的,而伪造是人为的;传说是连续的,而伪造是改换的;传说渐变,而伪造突异。[7](P620)
虽然钱穆对于疑古派的诸多学术观点均不赞成,但他在方法论层面却充分肯定了“层累说”,指出顾的不足正在于未能坚守住“层累说”,未能用顾自己倡导的“演进的方法”看待古帝王的传说以及今古文经问题,而是过分强调了刘歆、王莽个人的造伪。钱穆的这种褒贬互见的分析鞭辟入里合情合分,并不像现在学界的某些人那样将疑古派一棍子打倒。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一章在谈到“疑古学派”的学术贡献时说:
西欧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评判史料的风气才大为展开,而且进步很快,在历史界中成为压倒一切的形式。自辛亥革命以后,这个潮流才逐渐扩大到中国。我国历史界受了西方的影响,地域古史才逐渐有所谓疑古学派出现(按,虽然受了西方影响,但主要自有中国学术背景)。这一次参加的人数很多,工作的成绩也很丰富,一大部分由顾颉刚先生及他的朋友们搜集到《古史辨》里面。……由于疑古学派(广义的)历史工作人员及考古工作人员双方的努力,才能把传说时代和狭义历史时代分开。[8]
众所周知,将“传说时代和狭义历史时代分开”,这在史学史上是衡量历史学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一条重要标准。例如,克罗齐在谈希罗多德的历史意义时即认为:“在那个时候,思想放弃了神话性的历史及其较为粗糙的形式,即神异的或奇迹的历史,变成了尘世的或人类的历史。也就是说,变成了我们今天所仍怀抱的一般概念。”[9](P144)柯林武德也据此将希罗多德作为开创“科学历史学”的鼻祖[10](P49)。徐旭生充分肯定了在历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疑古派”的历史功绩。徐将“历史工作人员及考古工作人员”全都囊括在“疑古学派”(广义的)中,不管他的这种划分在今天看来是正确还是错误,它却是当时很具代表性的一种意见,表明了疑古派在当时学界的影响之大以及“疑古派”与“考古派”或“释古派”边际的模糊性。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主导性史学以前,“疑古学派”是我国史学界影响最大的学术流派。由于疑古运动的吸引⑤、砥砺和磨练,我国学界的一大批栋梁之材在疑古运动中脱颖而出。仅据《古史辨》收录的参与过“疑古”问题讨论的学者,就涉及到历史学、考古学、古典文学、哲学等多个学科,且参与者多为当时的一流学者⑥。饮水思源,疑古运动对于我国学术界人才培养的高功伟绩也是后世学界应当永远铭记的。
从史实考订的“操作性”层面看,“层累说”中如下一段人们耳熟能详的论述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并为今人提供了可对之进行“现代性”诠释的丰富学术内涵。顾先生说:“我们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2](P60)这段话是“层累说”的精髓,实际上包含“疑”和“信”两个层面的内容:“东周史”和“夏商史”往往并非“东周”和“夏商”人所作,而是“后人”的作品,史家考订并揭露这个“历史事实”是理所当然的。这是顾先生的“疑”。但顾说中还涵有“信”的一层要素,这一点,却因为人们将顾先生定位为“疑古派”而被长期遮蔽掉了。顾先生的“我们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和“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本质上是一种“信”。顾先生之所以以“史”冠以“东周”和“夏商”的名下,这是指示我们应当明了:“战国”和“东周”史家笔下的历史仍然值得期待和信赖,因为它们本质上仍然是“史”。就是说,史家必须尊重史实这一原则,使得史著至少可以为后人提供值得信赖的历史讯息。换言之,顾先生的考辨,是建立在相信经过了传说的演变业已“凝固”、“定型”以后的古史的。传说的原貌究竟如何,这是顾先生要“打破沙锅问到底”的⑦。细细体会顾说,他是要从“至少能知道”往“上”、往“前”,往那个能够得知“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推进的。这也就是钱穆先生指出的顾先生及《古史辨》“以复古求解放”的本质。就“古史的传说”来看,顾对于辛亥以后到处张贴的“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的布告认为不可信,因此怀疑。但顾要知道的是“这些相信四千或五千年的年数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⑧,亦即要求厘清此种说法的源头以及何时“定型”,这是“层累说”的根本目的所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疑中考信”。顾先生的辨伪固然存在“疑过头”的倾向,每每使得“至少能知道”某一史事变成了“只能知道”某一史事,此即张荫麟深刻批评过的“默证法”。但我们却不能因为顾先生在具体辨伪中的某些操作失当便全盘否认顾说中具有方法论重要意义的“信”的一面的存在。例如,顾在谈到他考察戏剧、歌谣的“分化”时指出:戏园中有“尧舜生,汤武净,五霸七雄丑末耳”的说法,顾认为戏曲中这种对历史人物的“定性”很可以用来观察史书上对“圣贤”与“恶魔”的理解,倘若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便可以明白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作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是颂誉和诋毁的积累的层次”[2](P41)。这个揭露,其方法论上的意义在于:它提示我们注意史家撰史时存在着按照“好人”、“坏人”的模式简单化地对历史人物进行“归类”的倾向。再如,关于纣,在从《尚书》到《史记》的不同典籍中的确有各种不同的“记法”,这是一个事实。揭露此类事实,是顾说的重要构成和顾先生的疑古取得过的重要成就,这一点不容否认。而此类“疑”的目的均在于探究某种传说的源头及其演变,即目的都在于“信”。若以认识论为视角,则我们必须承认:后人对业已存在的前人思想的任何诠释都不能不带有诠释者的时代性和诠释者个人的烙印,因此总有不尽符合诠释对象的本真之处,亦即总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这一原理是现代诠释学普遍认定并且被当今历史学有效引进的一条准则。克罗齐认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顾先生的“我们至少能知道传说中的历史真相”的说法,用了顾自己的学术用语,表达了与克罗齐、柯林伍德同样深刻的思想,即顾先生同样注意到了“人”的主观性在历史演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此,对于“后人”在诠释对象的过程中种种的“失真”,我们就可以视之为原始史实的“放大”、“缩小”或“变动”,并且可以用“层累说”的表达来加以理解和剖析。从这个意义上说,“层累说”到目前来看仍然没有“过时”,仍然具有相当的效应,至少我们现在还提不出全面否定或取代“层累说”的新方法和新理论。
收稿日期:2009-10-25
注释:
① 载《古史辨》第七册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② 参见拙著《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廖平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③ 廖平认为经学起于先秦,早在先秦即已有今古文经之争:“经在先秦已有二派:一主孔子,一主周公,如《三传》是也。”见廖平《经学抉原·序》,载《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廖平蒙文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47页。
④ 蒙文通:《古史甄微》,载《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廖平蒙文通卷》,第337页。按,后杨宽、童书业的神话地缘说,即从蒙文通的文化地缘说变化而来。杨、童如此探究神话传说,既为神话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学术进路,同时也无形中影响着民俗学研究的取径,因此是有价值的。
⑤ 钱穆提到,在《古史辨》第一、第二册中“便可以看出近时一辈学者对此问题的兴趣和肯出力讨论的情形。”载《古史辨》第五册第618页。
⑥ 读者可参阅拙著《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第五章。
⑦ 《古史辨》第一册顾序第45页:“你又要‘打破乌盆问到底’了!这是我的祖母常用来禁止我发言的一句话。”
⑧ 《古史辨》第一册顾序第45页。按,以“黄帝”为纪元,这是二十世纪初章太炎、刘师培等“革命派”为反清而鼓吹的一种“政治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