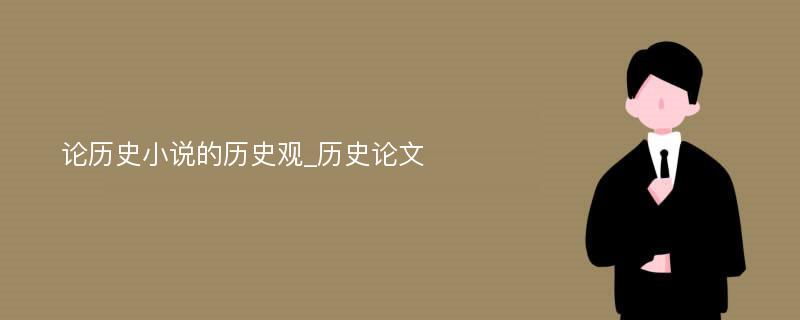
关于历史小说中的历史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观论文,历史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与历史有着极为亲近的血缘关系,甚至就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最早起源于纪录和 诉说历史的需要。正因为如此,面对历史,文学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实录传统” 。对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人们总不免要首先追问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的真实 ,实指史料的真实,并以此作为评判其真实性的重要标准。在很长时期里,谈历史小说 ,“历史”是第一位的,“小说”是第二位的,所谓创作,或是借用文学形象魅力普及 历史知识,或是用故事的吸引力“演义”历史本事,从而达到“还原”、“复活”历史 的“本来面目”的目的;而所谓“本来面目”又不过是作者的意识形态对尘封的史料的 提取、加工和阐释而已。事实上,“主观性”无所不在,只是必须以忠于历史的名义把 自己隐蔽起来。于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尤其在古代,历史题材的创作不可能真正独立 于历史,也没有走出历史的附庸的地位,更谈不上能动地重铸历史精神。由于这样的传 统观念极大地束缚了历史题材的创作,现代以来,该片领域有过许多争议,其焦点仍逃 不出能否虚构和虚构到什么程度,能否想像和想像到什么边界。郭沫若的观点较有代表 性,他提出,历史研究应该“实事求是”,史剧的创作(应含小说家)应该“失事求似” ,并认为历史家的任务是发掘历史之精神,史剧家的任务是发展历史之精神。这当然是 重要的见解,但也只是一家之言,争论并没有止息。
对“真实性”的不同理解始终左右着对具体作品的评价。其实,“真实性”不过是表 相,在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历史观,不同的历史观会突出和抑制不同的真实。历史观才 是核心。我们知道,在古典小说中,其历史观主要是“历史循环论”“宿命观”和“英 雄造时势”。最典型的便是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建国后到80年代,历史 题材的创作中的历史观,主要是努力运用阶级斗争学说,其描写对象主要是围绕着农民 起义领袖和少量公认的杰出的比较有把握的历史人物展开,后者数量并不很多。虽然也 出现了史剧《武则天》《蔡文姬》,但旨在“翻案”,也有史剧《胆剑篇》《王昭君》 ,但旨在“配合”。自抗战时期直到十七年,“借古讽今”的配合意识似是一种顽固的 观念,这表现为过于明显的政治功利主义的历史观。建国后写杰出人物的作品不多,如 林则徐、海瑞、邓世昌等,多以电影和戏剧的形式出现,皆引起过很大的风波。写农民 战争和农民领袖的,其代表性作品应属姚雪垠的《李自成》,它获得了巨大成功,并得 到毛泽东的首肯,甚至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应该承认,这部作品,尤其是它的第一部, 确实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它是它的那种历史观的圆满体现。继《李自成》之后, 在80年代,迅速出现了一个竞写农民起义领袖的热潮,如《星星草》《陈胜》《九月菊 》《风萧萧》《义和拳》《庚子风云》《神灯》《天京之变》等等。这虽不是当时历史 小说的全部,却已是最重要的部分了。这些不同的作品的历史观其实是很一致的,那就 是,它们都遵循着“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一经典表 述,要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要着力于表现“历史前进的主体”。这可说是 当时的历史小说的历史观的精髓所在。它们都强调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解释历史,强调农 民战争的根本推动作用,强调历史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它们都是通过政治视角来概括历 史。
80年代末《少年天子》的出现也许是意味深长的。它的作者选择了顺治皇帝作为主人 公,并且给予了肯定、欣赏和同情。作者完成了一种超越:超越局部的、暂时的正义和 非正义,超越文明与愚昧的简单判断,力求把握历史运行的某种内在精神。历史的内在 精神要由一个封建帝王来体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作品透露出这样一种新颖的历 史观念: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人数少而落后的满清,固然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 ,可它偏偏用武力征服了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地区,这意味着它不只是弓马娴熟,仅具 蛮力,而是它没有包袱,极易吸收新东西,本身具有一种活力,证明封建社会还没到寿 终正寝的时候。至于由“后金”而“满清”,且迎来了康乾盛世,表面看是军事征服的 胜利,实乃争取到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实现了满汉文化融合,且以归依汉文化为主 ,建立了多民族封建帝国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胜利者并非真正的胜利者,失败者也 非真正的失败者,诚如马克思所说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较高文 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规律”。不管作者凌力是否自觉,她首开了一个以“圣君贤 相”为中心的创作潮流。当时也有其它类似作品几乎同时出现。作者自言,它的小说是 个复杂的恒星系统,数层行星按不同的轨道围绕恒星运行,而恒星即是顺治这个人物。 继之,《雍正皇帝》《康熙大帝》《乾隆皇帝》《曾国藩》《白门柳》《杨度》《张之 洞》《张居正》《汴京风骚》《梦断关河》《大秦帝国》等等相继出现。这些作品里的 人物好像是80年代作品里的农民起义领袖的对立面,他们不是帝王,就是宰相,要么就 是才子佳人。主角易位了,好像翻了一个个儿。我认为中心人物的“换位”只是表面现 象,其中隐含着历史观的大变化。至今没有人真正点破。我认为,显而易见,在这些作 者看来,历史不再只是由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推动的,而是由人民群众和“圣君贤相” 共同创造的,后者的作用甚至被认为更显著。这不由让人想到“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 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 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总之,这一批历史小说,它们摆脱了比较狭隘 的阶级观点,摆脱了单一的政治视角,摆脱了简单的配合、影射、比附的功利主义历史 观,开始走向了一种更为深沉的思考。
上世纪90年代至今,历史观的大变革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如上所述,强调历史是 由人民群众和“圣君贤相”们共同创造的——对后者的作用尤其强调。第二,不少作品 由单一的政治视角转化为经济视角,文明视角,以至更为宽阔的文化眼光。第三个方面 是,众多作品的主题几乎都由原先阶级斗争史转换为政治经济的变革史,无不贯穿“敬 天法祖”还是革故鼎新的矛盾。第四方面,突出了人性内涵,更注重历史中的个人命运 和心灵变化的历史。这一切无疑给创作带来了大变化。举个例子,比如写鸦片战争,电 影《林则徐》强调的是通过林则徐折射出受压迫人民反抗列强侵略的正义性,现在《鸦 片战争》的主题则暗转为强调“落后就要挨打”。比如周大新的《第二十幕》便是反思 被长期忽视的中华工商文明传统。又如陈忠实的《白鹿原》,扬弃了较狭窄的阶级斗争 视角,代之以文化和文明的高度正面观照中华文化。唐浩明的《曾国藩》也许更为典型 ,它并不是如有人所说,在简单地为曾国藩翻案,而是客观冷静地解析曾国藩的文化性 格,突出其人格中的文化内涵及其复杂性。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在以文带史与以史带 文的问题上,固然与唐浩明的创作风格大异其趣,但总体而言它们都属“正说”之列。 雍正曾被认为是个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的刻薄寡恩之徒,是大两面派,大伪君子, 这里道德化评价的成分自然很重,而二月河却创造了另一个雍正,一个励精图治却又深 沉莫测,极具性格魅力的冷面王。哪一个更真实,只能到历史观中去寻找原因。再如孙 皓辉的《大秦帝国》是一部篇幅浩繁的作品,尚未写完,从已出版的第一部来看,作者 的主导理念是,要写出大秦帝国是中华文明的正源。作者对大秦帝国心向往之,他要向 源头寻找智慧、基因,寻找原生文明,从而探究民族精神的根因。新近受到好评的熊召 政的《张居正》,选择明代,选择张居正这个聚讼纷纭的改革家为主角,本身就体现了 一种历史眼光。因为明代在表面平静之下,是社会结构急剧变化的时代,它有可能充分 发展前资本主义的因素,但它终究未能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其中教训至为深刻,抗 战时期写了《张居正大传》的朱东润曾说,他想从历史陈迹里,看出是不是可以从国家 衰亡的边境找到一条重新振作的路,反复思考,终于想到明代的张居正,这是他写作《 张居正大传》的动机。应该说,熊召政之写作《张居正》与之是有共鸣的。它们都不是 要比附什么,而是寻求历史发展的内在精神。
凡事都有两面性,这一面强调过了头,另一面就会把矛盾和问题暴露出来。虽然与某 些影视作品相比,文学界的历史题材创作要严肃许多,但对帝王将相的描写依然存在值 得审视的问题。若对某些皇帝重臣的美化失了度,张大其辞,过于理想化,甚至搞成高大全,若在赞颂人物的过程中无形中把人治思想,专制思想抬得很高,奴才味儿十足, 那就会形成对皇权文化的膜拜,有悖于现代民主法制精神,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当然 ,一般地谈谈容易,要在对肯定性人物的具体描写上掌握好尺度和分寸,并不容易。要 改变大众审美趣味对这类作品的喝彩,也不容易。目前在历史观上的另一种变化是,对 农民起义,比如太平天国,义和团等等,史学界和创作界中不少人是存有质疑的态度和 重新评价的欲求的,将之称为游民文化。这也是很正常的,是学术上进步的表现,实际 上已经影响到历史题材的创作。比如张笑天的《太平天国》,无论在他个人的创作上, 还是在整个历史题材的创作中,都是一部比较严肃有力的作品(具体争论姑且不谈,仅 就文学性而言),但是,电视剧几乎播不下去,书的评价也大受影响,其实这与作者的 关系已很小,乃是历史观大动荡中的必然牺牲,“非战之罪也”。
事实上,当前历史题材创作已呈现多样化格局,大致划分,有以“正说为主的”现实 主义的一种,有以“解构”为主的新历史小说的一路,还有以“戏说”为主的消费历史 的一路。比如,受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影响较为明显的以解构历史为主的作品,一般 被称为新历史主义小说,我们谈得不多。这些作品,在对什么是“历史真实”,对是否 存在一个“历史规律”,甚至对什么叫“历史”的看法上,都有迥然不同的理解。在这 些作品里,决定论被扬弃,偶然性备受尊崇,过去强调的推动历史的某些重要因素被置 换为食色,人性,原始的生命强力等等因素。消费历史的一路则主要写权谋,性爱,争 宠,夺位等等,追求好玩,趣味,刺激,突出娱乐化,消遣化因素,迎合大众文化的审 美趣味。对此,简单的指责是没有用的,首先要看到它的合理性,对其消极面,只能引 导它。还应看到,目前历史学界的新见和争议,正在进一步影响文学界的创作。比如重 写晚清史的问题,就很引人注目。其中对太平天国,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慈禧的 评价问题,颇为敏感,看来有关的争论是不可避免了。
标签: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小说论文; 历史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张居正论文; 古希腊论文; 历史故事论文; 历史学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