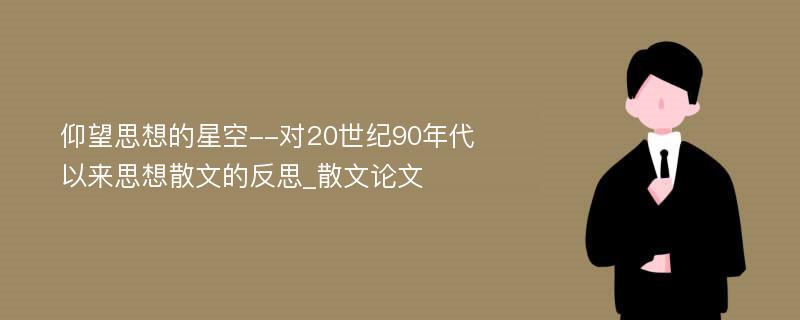
仰望思想的星空——关于90年代以来思想散文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散文论文,星空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的散文热,曾被人们称作当代文坛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之一。新时期以来小 说一直在中国文坛独领风骚,而散文却受到冷落,有人曾断言,散文已走向末路,“散 文已趋于解体”(注:王干、费振钟:《对散文命运的思考》,《文论报》1988年第1期 。)。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已近寂寥的散文园地忽然热闹了起来,许多新老作家、 学者和各阶层文化人纷纷登场,各种媒体积极为散文写作提供空间,各种散文集和选本 纷纷问世,其数量之多,作者之众,令人目不暇接,有人将这一文学现象称作“世纪末 的狂欢”。
“狂欢”只是一种现象,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内蕴。实际上,90年代以来的散文,就其 精神深度,特别是文化反思力、思想穿透力而言,真正触动人们心灵,留给人们长久回 味,具有大时代大散文的气势和品格的,是中后期以来那些富有人文精神、洋溢着现实 关怀热情、饱蘸着历史浓墨的“思想散文”。
一
90年代初,散文已呈现出兴盛的势头。这一时期,除了多年活跃于散文园地的老一代 散文作家不时有佳作推出之外,还涌现了一大批差不多与新中国同龄的散文新秀,如陈 丹、胡晓梦、筱敏、苏叶、斯妤、冯秋子、叶梦、素素、张立勤、唐敏等;更有许多小 说家、诗人批评家、学者,也纷纷涌进散文世界施展才华,一时间,散文随笔包括各种 小品文蔚为大观,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女性散文”(南方则有“小女人散文”)、“文 化散文”、“学者散文”和其它各种所谓“新潮散文”,等等,那热闹景观,几乎要与 小说平分秋色。
上述各类散文,取材多元,风格各异。“女性散文”常于寻常人家寻常生活的叙写中 表现女性独有的焦虑与烦恼,或表达她们对人生意义的感悟,或披露她们在现代物质文 明冲击下的心理感受,情真意切,流韵萦绕,像斯妤的《心灵速写》,素素的《女人书 简》,筱敏的《西陲五题》、《家》、《规矩》,张抗抗的《牡丹的拒绝》,苏叶的《 车辚辚马萧萧》等,都是当时颇有代表性的“女性散文”佳作。“文化散文”往往通过 对历史文化的考察,或抒写千古兴亡,或感受历史沧桑,抚今追昔,引人遐想,如曾产 生过强烈反响的余秋雨散文尤其《文化苦旅》,就是极有感染力的“文化散文”集。“ 学者散文”的特点是带着学者特有的个性、知识、学问、思索和独特的语言,或穿越历 史记忆的时空,或俯视现实人生,娓娓道来,余味无穷。如季羡林的《牛棚杂记》和谢 冕的《永远的校园》等。
纵观这一时期的散文,艺术上明显有别于十七年散文写作的特点是大大地强化了审美 性、娱乐性、可读性和结构模式、文体形态的多样化,不再因意识形态而牺牲艺术。这 是90年代初散文写作最大的观念突破与变革。这种突破与变革,一方面源于自新时期以 来,特别是80年代文学界对“文学回归文学”的呼唤和理论界对文学审美性质的强调; 另一方面也与文化消费对文化生产的制约、调节密切相关,因为,散文写作如无视社会 生活的急速变化和文化市场的需求就无法改变被冷落的境遇。
然而,仅仅这样理解90年代初期的散文写作未必不简单化。当人们过份强调文学的审 美性、娱乐性时,就潜伏着另一种倾向:把审美性、娱乐性当作文学的唯一价值。换言 之,为了艺术而牺牲思想。90年代初,这种倾向实际上在理论界和创作界已经存在了。 特别是在经历了精神挫伤和文学“边缘化”之后,一些散文家对现实多多少少疏离了, 对社会责任感之类也了无兴趣。90年代初发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提出的“文学危机” 和作家“精神危机”问题,多少揭示了当时文学创作包括散文创作的宿弊。当我们回过 头去审视90年代初的散文时,不能不承认,尽管如前所说,散文出现了兴盛的势头,但 思想者缺席。一些“女性散文”取材过于琐碎,思想平庸;南方的“小女人散文”太多 小市民意识,拒绝问题意识的介入;有些“学者散文”喜谈禅释道,缺乏忧患胸怀;某 些“文化散文”一味从现实逃进历史,缺乏文化反思力;有的则津津乐道于绝对的“个 人化写作”,标榜自我却无思想深度,等等。有人对此曾尖锐指出:“几乎所有的散文 作家都停留在一个静止的镜面上。”(注:林贤治:《90年代散文:世纪末的狂欢》, 《文艺争鸣》2001年第2期。)话虽夸大,但值得深思。 实事求是说,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散文,也有思想含蕴深刻的佳作,如邵燕祥、李国 文、牧惠、舒展、林放、冯英子、吴有恒等的散文随笔。拿邵燕祥来说,这位被誉为“ 80年代杂文创作的代表”的诗人(注:何西来:《当代中国的理性和良知》,《文学的 理性和良知》,第124页,人民文
学出版社,1995年版。),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就接 连发表了一系列散文随笔,其中《历史中的今天》、《说欺骗》、《英雄观》、《避席 畏闻篇》、《读布哈林遗嘱》、《读<大清洗的日子>》、《画蔷小集》、《读<我与胡 风>随记》、《1957年:中国梦魇》等,一串串沉甸甸而犀利的文字,无论直面现实, 或是触摸历史,都表达了对社会人生的深层思考,不时闪烁着洞察真理的思想辉光。虽 然邵燕祥这些文字有的明显地对思想表达的热情超过了审美情趣的追求,但是,在许多 人的思想触角近乎麻木的时候,它毕竟有如一道湍急的河流,不时激起朵朵思想浪花, 引领了新时期思想散文发展的潮头。
当然,90年代初像邵燕祥这样的思想散文尚未形成亮丽的景观。90年代初散文的思想 内蕴,总体说是贫困的。
二
在90年代初散文的思想力量普遍疲软的背后,同时也正默默地酝酿着一股蓄势待发的 思想激流。到了90年代中期后,激流终于冒出地表,汇为大河——一种有别于为艺术而 艺术的思想散文终于蔚为大观。
这一时期中,除了邵燕祥、牧惠、李国文等继续保持其以思想见胜的写作传统外,又 有大批有思想、有见识的新老散文家、学者、人文社会科学家等走上散文舞台,以各种 形式的思想散文、随笔点缀着美丽的思想星空,其中还结集出版了各种颇有影响的散文 丛书,如“九十年代思想散文精品”、“思想者文库”、“草原部落:名报名刊精品书 系”、“文化热点争鸣书系”、“《博览群书》百期精选”等。这些丛书中的文章大部 分属于思想散文的范围。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散文作者中,已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有王小波 、林贤治、筱敏、朱正、朱建国、严秀、刘烨园、李锐、徐无鬼、王充闾、徐友渔、潘 旭澜、王学泰、蓝英年、钱理群、余杰等。他们的文字,洋溢着深厚的人文精神,闪烁 着犀利的理性智慧,为散文阵地注入了蓬勃的生命活力。
这里我想特别谈谈王小波、林贤治与筱敏。
王小波英年猝死,而这一年(1997年)他的散文随笔自选集《我的精神家园》出版。从 留下的散文文本看,王小波的确是一位睿智的思想者,他的大部分作品就是很有深度的 思想散文,其中像《知识分子的不幸》、《文化之争》、《椰子树与平等》、《救世情 结与白日梦》等,都是极具思想智慧的篇章。王小波思考的问题非常广,而主要问题是 知识分子问题、专制主义问题、文化问题、信仰问题、道德问题等。
王小波非常关注知识分子的命运。在《知识分子的不幸》中,他提出一个问题:“什 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他说他自以为有一个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的答案, 这个答案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时代。”什么是不理智的时代呢?“就是 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 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知识分子的长处是讲理,而在一个不讲理的 时代,他们是注定不幸的。“文化大革命”是不讲理的年代,于是便有千千万万的知识 分子惨遭不幸。作者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引出了“信仰”问题,说,信仰 是要的,但信仰不能离开理智,否则信仰一旦被滥用,“都可以成为打人的棒子、迫害 别人的工具”。“国学”也如此,它的“制高点”是一个“国”字,“抢到这个制高点 ,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 大的诱惑力”。
在《椰子树与平等》一文中,王小波从云南没有椰子树说起,在对诸葛亮的调侃中, 对“平等”问题发了一通幽默的议论,让人忍俊不禁。四川不长椰树,那里的人要靠农 耕为生;云南长满了椰树,这里的人活得舒服。那么怎样才公平呢?要不就让四川长椰 树,但自然条件限制,办不到,只好把云南的椰树砍了,这就公平了。同理,有人四肢 健全,有人生有残疾,为公平故,只能把健全人弄成残疾;“聪明人与傻人争执,我们 总说傻人有理,久而久之,聪明人也会变傻。这种法子现在正用着呢。”
王小波的思想散文往往在平实、幽默的言说中揭示了深刻的思想见解,读来余味无穷 。当然,王小波思想散文的学理性探索仍有较大的局限性。而林贤治恰好补充了这种不 足。
林贤治作为诗人、散文家,早已负有盛名;作为学者,似始于他对鲁迅的研究(其《人 间鲁迅》深受学界赞赏)。林贤治的散文,最引人注目的是近年推出的《平民的信使》 、《胡风集团案: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五四之死》、《娜拉:出 走或归来》等思想散文集。
读林贤治的思想散文,总感到有一种鲁迅风,尤其是直面人生的勇气。与鲁迅的严峻 冷静不同的是林贤治像一个燃烧着的灵魂,阵阵热浪逼人而来;有时又感到这灵魂忽而 化为一条冰冷的长鞭,正无情地抽打着另一种灵魂——国民的劣根性。林贤治始终充满 思想激情,而他的思想激情又集中体现为一种批判激情。他说,思想的全部力量在于批 判。对外,是文化批判——奴性文化和专制文化批判;对内,是自我批判——灵魂批判 。他的批判常因其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和穿透力而令人拍案叫绝。例如,在《五四之死》 中,作者对五四的真义作了独特、严肃的阐释之后,怀着一种历史的苍茫感,对五四新 文化运动以后历史行进中的吊诡现象议论道:知识分子曾苦苦追求的,最后又自愿放弃 ,甚而在游戏中自得其乐,而对曾经搏斗受伤的战士,在“白日到来之后”,他们“便 纷纷围拢过来,嘲笑他遍身花纹般的创痕”。从历史到文人,林贤治利刃般的文字,常 常使之无可逃遁。
林贤治对奴性文化给国民带来的深重戕害的剖析和批判的确是异常深刻的。尽管林贤 治的批判不无偏执,不无片面地将一切批判泛道德化,换言之,他常常以道德批判替代 技术化的批判,因而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但无论如何,这种片面性的批判,却使其具 有某种思想的深刻性和尖锐性。
另一位值得称道的思想散文作者是筱敏。
读筱敏的散文集《成人礼》,很难不为她那深刻的思想洞见、沉稳的理性智慧和美丽 的文笔而惊叹,难怪牧歌在一篇短评中说这本书“让人爱不释手”,说“筱敏的文字和 思想在当今中国女散文家中绝对是独一无二的,简直是一个‘精神贵族’”(注:牧歌 :《“精神贵族”筱敏》,《城市牛哞》,第438页,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以前,筱敏的散文已引起人们的关注,但那时的散文如《爱默生 的弧线》、《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致死的痼疾》、《火焰成碎银》、《无家的宿 命》、《规矩》等,主要是日常生活、人性的琐碎感受,少有大时代大课题的宏大叙写 ,缺乏思想震动力。90年代中期以后,她的散文发生了质的飞跃,跳出了一般女性作家 惯于抒写生活琐事和私人感受的套路,忽而向人们展开了一个宏大的历史空间和思想空 间,着力于对历史灾难和人类命运的深沉思考。筱敏的思想散文涉及法国大革命、德国 法西斯、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斯大林肃反和中国文革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现象, 作者通过追忆、反思、诘难、剖析、评判,诉说苦难,鞭鞑罪恶、讴歌崇高,昭示正义 ,字字铿锵,新见迭出,可谓“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这是真正的大时代的思想 散文。
在《这是一场革命》、《1789年原则》、《遥想法兰西》、《被风支配的灵魂》等篇 章中,筱敏满怀激情地诉说着自己对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理解和讴歌。她写道,自由, 平等,财产,安全,反抗压迫,信仰,思想和表达的权利等,“这些著名的1789年原则 ”,“为近代世界奠立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新的普世价值铺设了基石”,而这一年《 人权宣言》的诞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以致人们在言说现代社会的时候 ,只能把1789年作为起点”(《1789年原则》)。从这个时候开始,“思想——这个‘不 可知神’登场,成为作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力量”(《天平上还有七弦琴》)。
在《群众海洋》、《语言巫术》、《情感瘟疫》、《法西斯摧毁了什么》等篇章中, 筱敏对20世纪人类遭遇的灾难作了深刻反思。反思是从“法西斯”开始的,“法西斯” 原指捆在一起的一束棍棒,中间插一柄斧头,是古罗马高官的权力标志,象征着万众团 结一致,服从一个意志,一个权力”;接着,作者以大量的史实披露了当时德国“群众 ”对希特勒发狂般的迷信之后感叹道:我们“能不为这个群体的生存性质哀泣么”(《 群众海洋》)?“群众”这种不幸,与法西斯的“语言巫术”是分不开的,“群众”正是 被那重复千遍而变成真理的谣言所改造和奴役而改变了思想的性质,改变了人的情感和 良知的,从而法西斯政权的一切反人类、反人道的行为都没有遇到来自“群众”的抵制 (《语言巫术》)。这是多么催人哀泣的历史悲剧啊!
对俄罗斯精神的讴歌,是筱敏散文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救援之手》中,作者记述了 高尔基、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涅克拉索夫、金兹伯格等俄苏作家救援蒙难濒于 死亡线的另一部分作家的可歌可泣事例,感叹道:“俄罗斯文学的长链,在洪水和风暴 中都没有断开,她是由作家们相互间救援之手连接起来的。这样的手,在她们广袤的土 地上栽种的是人道和正义,是信念,是对人类的信念。”接着作者意味深长地写道:“ 每一块土地都生长杂草,每一场风暴都制造流沙……但是,一些土地是只配杂草和流沙 的,偶有一两株乔木灌木,也很快就矮化或枯死。而另一些土地,却总有高大的树木站 立起来,于是当风暴来袭,这里除了杂草流沙琐琐碎碎战战兢兢的声音以外,还会有大 树的声音。”
读着筱敏这些文字,恍惚之间,我看到了一位苦苦呼唤着思想、感情和良知的真正知 识分子的忧郁胸怀,眼前又浮现出那痛苦地弯着腰、屈着双膝、右手托着下颏、默默蹲 在地狱之门上横楣中央、俯视着人间悲剧并沉入“绝对”冥想的“思想者”形象。在他 (也是她)深深的沉思中,我感受到了他(她)内心的苦闷与悲哀。筱敏,无愧是当代作家 中深刻的思想者。
90年代中期以来思想散文的繁荣,与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有关,但主要还是时代使然 。大变革时代,人们面临种种关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社会普遍关心的共 同问题,当时代迫切需要作出判断和回答的时候,思想散文必然应运而生。而经过新时 期十多年的思想积累和知识积累之后,思想散文发展的条件也成熟了,从而它的兴盛也 就成为必然。
三
以上的描述和对部分作品的分析,不仅说明了90年代来以散文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内容 上由思想的贫困到思想含量、力度不断增大的演变状况,同时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思想 散文的价值的理解。
这里存在着一个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这就是:如何看待思想散文的思想与 艺术的关系问题。
首先必须指出,本文所论述的思想散文指的是作为文学的思想散文,而不是一切表达 思想的文章。思想表达的方式既可以是叙述的、理性的,也可以是艺术的、诗性的。前 者可以成为社会科学论文,后者却是文学、艺术。我们所谈的是后一种。据此,在上文 的论述过程中,笔者并不把一些类似于社会科学论文、学术论文的文章列入讨论的范围 。
顾名思义,没有思想的散文不能称为思想散文。但是,思想的含义也可以是非常宽泛 的,如果把思想理解为一切对世界的主观认识成果或体现的话,那么,没有思想的散文 几乎是不存在的。然而,我们所说的思想散文,指的是对重大社会历史问题、人生问题 表达了深刻的理性认识的、而不仅仅提供一般知识或表达一般生活感悟的散文,例如仅 仅让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就不属于思想散文。
那么,如何理解思想散文的思想与艺术的关系呢?
毫无疑问,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当然不是思想,但文学不是一种不需要思想的奢侈品。 “文学要回归文学”的口号是合理的,它针对文革和文革前将文学异化为某种思想、政 策的传声筒的左倾文学观念,要求文学恢复自身本性和面貌,这是对文学的尊重,对艺 术规律的坚守,并不是说文学应该拒绝思想。对文学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的强调,同样 不是要求文学放弃思想。文学与理性、思想有对立的一面,却又是可以媾和、统一的。 我始终认为,缺乏思想的文学总是苍白无力的,文学常因思想而提高了意蕴的内含,从 而也提高了文学的整体价值。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就是艺术境界与思想境界的高度统一 。这一基本认识也完全适用于散文。而且,散文作为介乎诗与非诗之间的文学形式,一 方面自身在表达方式上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另一方面由于其对生活更加接近,更适合于 直接表达创作主体对社会人生的见解,这就必然与思想更加亲近,从而更配担负表达深 刻思想的社会重任。尤其是,今天我们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生活空前 丰富多彩同时也是人们面临种种生活与生存问题的时代,人们更需要思考与判断,也更 需要通过文学来认识自己所生存的世界,甚至还非常需要思想启蒙的时候,我们的散文 写作更应该以深刻的思想见解去启发他们,提升他们。散文,我们时代的散文,没有理 由逃避或淡化思想。
基于这一基本认识,我不赞成把文学,把散文降低为一种单纯的消遣自娱的手段而放 弃社会思考的责任。林贤治说得好,如果我们的散文作家可以绕开重大社会事件和问题 ,可以逃避良知与责任而源源不断地写作,那么,这种写作不过是机会主义写作,不过 是认同散文作为一种文类的泛滥与平庸(注:林贤治:《90年代散文:世纪末的狂欢》 ,《文艺争鸣》2001年第2期。)。筱敏也说:“我反对作家不过是一种职业的说法,因 为这种看似平民化的说法,回避了某种实质性的东西。……作家,实际上指的是一种人 的精神事实,他至少需要个体的人格尊严,独立的思想能力和感受力(注:筱敏:《生 存,加上一枝笔》,《成年礼》第212页,太白文艺出版社。)。总之,对于散文写作, 思想始终是一种深度的标志,也是作家尊严的一种标志。
另一方面,我也不赞成为了思想而牺牲艺术。作为艺术的思想散文,其思想的表达必 须诗化,而不是抽象的叙述。我以为无论是邵燕祥还是林贤治,他们也有一些思想散文 显得不够韵味。何西来在充分肯定邵燕祥的作品的同时,也不无道理地指出,他“有不 少篇什因率意挥洒,而文意失之平浅”(注:何西来:《当代中国的理性和良知》,《 文学的理性和良知》,第1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林贤治的思想散文, 也有些篇章过于抽象化,或因感情太烈反而少了些诗性。至于筱敏,我以为她的思想散 文虽不如前两位那么自由潇洒,但更加细腻婉丽,在思与诗的融合方面更加和谐圆满。
人们衷心地期盼着更多优秀的思想散文问世;期盼着产生像蒙田的《随笔集》、卢梭 的《忏悔录》、《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产生像杰斐逊的《独立宣言》、潘恩的 《常识》、林肯的《就职演说》、梭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产生像赫尔岑的《往事 与随想》、托尔斯泰的《我不能沉默》等那样感动过千千万万人的思想散文。
散文的世界宛如那广袤无际的星空,而这星空是因仰望她的眼睛而存在的,是因嵌缀 她的灵魂而存在的。人类丰富多彩的思想,也像那熠熠生辉的星空,她也是因我们的仰 望而存在的。
标签:散文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王小波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邵燕祥论文; 筱敏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