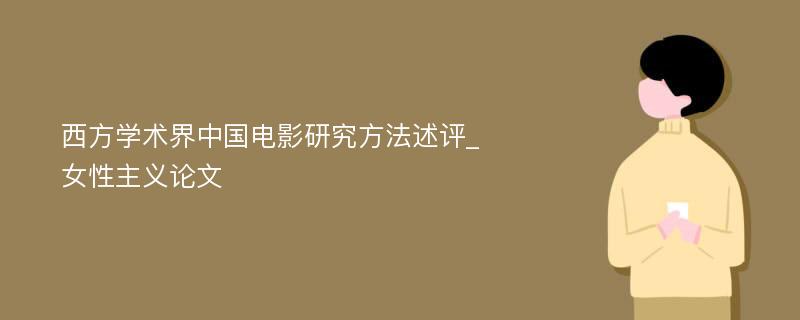
西方学界的中国电影研究方法选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界论文,中国电影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列举、分析20世纪末在西方中国电影研究(包括用英文写作的华裔学者)的一些主要方法和议题。正如裴开瑞(Berry)在其编辑的《中国电影视角》(康奈尔大学东亚书系39号,1985)论文集中早已经预见到的,迄今为止,对中国电影的研究一直是具有学科性质的。近十多年来活跃于这一新兴学科的学者中,专门受过电影博士研究训练的有(以英文姓氏的字母为序)裴开瑞、尼克·布朗(Browne)、斯堤·弗尔(Fore)、刘国华、乔治·桑赛尔(Semsel)、邱静美。来自其他学科的博士学者有中国现代史的康浩(Clark )、傅葆石、毕克伟(Pickowicz)、萧志伟,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克里斯汀·哈里斯(Harris)、蓝温蒂(Larson)、李欧梵、张真,传媒研究的维玛·迪沙那亚基(Dissanayake)、司蒂芬妮·唐纳德(Donald)、约翰·仁特(Lent),比较文学的周蕾、 鲁晓鹏及笔者本人等。此外,这一领域也大大受益于亚洲、欧洲、澳大利亚的影评家, 如张建德等。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学科训练出来的学者在研究方法上也会有显著的差别 (如刘国华与邱静美),而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又常对某些问题(如性别与性话语)有共同 的兴趣。
中国电影研究领域的重要方法和议题如下:历史研究、产业研究、类型研究、美学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性别研究、文化研究。我将引述一些论文以廓清这些方法和议题,但所引的作者和著作意在其启发性,而不在其全面性,因为本文的目的是勾勒这一领域的大体的学科地形图。为行文方便,所选介绍的论著截至2000年。
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关注社会政治事件或文化事件如何影响电影的生产、流通与接受。在中国电影研究中,主要有两种历史研究方法,一种集中关注电影政治,一种则关注电影文化。有关社会主义中国时期(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电影史,一般都属于第一类,如雷吉·柏格森(Bergson)的法文的著作《中国电影,1905—1949》(劳赞·埃贝,1977),和约格·洛瑟尔(Lsel)的德文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故事片的政治功能,1949—1965》( 慕尼黑:米聂瓦,1980),以及康浩的英文著作《中国电影:1949年后的文化与政治》(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毕克伟的两篇文章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电影政治史的作 用。他在《后毛泽东时期中国的通俗片与政治思潮:官方公告、电影、电影观众》一文 中,力图理清“官方”(official)与“通俗”(popular)之间的关系。他希望读者意识 到,“在精英文化领域,官方的与非官方的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其次,希望能以 此文来探讨精英们的非官方政治思想与非精英的大众政治思潮之间如何互动”。毕克伟 的模型比康浩的要灵活些。康浩严格划分党、艺术家、观众,但这一划分中的每一项既 可以是官方的,又可以是非官方的,因此精英(elite)和非精英的区别就很复杂,界限 也变得模糊(注:林培瑞(Link)等合编《非官方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通俗文化与 思想》,波德:西景,1989。)。毕克伟在另一文《天鹅绒监狱与中国电影制作的政治 经济》中,借用了匈牙利作家哈拉茨提(Haraszti)提出的“天鹅绒监狱”的概念,来勾 勒后社会主义中国的主要变化。他把《顽主》(1988)与《疯狂的代价》(1988)作为20世 纪80年代以后城市影片的代表,以揭示“中国电影界很多深层的、半被遮蔽的结构和心 理层面,它们阻碍着进步”。他从改革时代电影制作的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得出结论:90 年代的场景是一片矛盾,其中,半持“异见”的影人(如张艺谋、陈凯歌)专门制作东方 的东方主义作品;而张元、何一等第六代导演则在制片厂体系外拍片(注:德波拉·戴 维斯(Davis)等合编《当代中国的城市空间: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自治与群体的可能性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
早在1972年,陈利(Leyda)就以其历史研究,开始了对电影文化的研究。陈利研究了各种出版文献,如报纸、杂志文章、政府文件、影人生平与回忆录等。他的《电之影:中国电影与电影观众》(剑桥:麻州理工学院出版社,1972)有意使用一种不连贯的、松散的叙述,以对应程季华等人写的那部结构严谨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值得留意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直到90年代初期,学者们即便没有完全抛弃电影文化(电影界的一些短文表现出对电影文化的明显兴趣),却也基本忽略了这一研究方法。关于早期中国电影文化的有分量的新作,直到90年代中期才开始重新出现。萧志伟的博士论文《中国的电影审查,1927—1937》(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1994)就是一例。人们一般认为电影审查是一个政治工具,对电影工业施加着巨大控制力。但萧志伟则把电影审查作为文化史中权力的一个交结点,作为政治意识形态与各种文化力量之间的交汇点,这些力量有的保守,有的现代,有的甚至激进,但当时它们都没有明确的定义和地盘。萧志伟为此进行了大量档案、文献研究。这一研究方法对哈里斯的博士论文《无声的言语:早期中国电影中的国族想象》(哥伦比亚大学,1997)和张真的博士论文《“银幕艳史”:电影文化,城市现代性与中国的白话经验》(芝加哥大学,1998)来说,也至关重要。笔者编辑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1922—1943》(加 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也展现了中国电影的一种新的文化史的研究角度。所 辑的很多文章,如李欧梵关于城市文化的机制(电影院、流行报刊、通俗文学),迈克· 张关于早期女明星制度的兴起等论文,都勾勒了电影文化的广大空间,期待学者将来的 进一步探索。
产业研究
产业研究关注电影业的机制与运作。仁特的专著《亚洲电影工业》(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90)与桑赛尔为其所编的文集《中国电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电影艺术现状》(纽约:普拉格,1987)写的导言,都概述了中、港、台三地电影工业的结构与机制。20世纪30、40年代正是向有声片过渡的时期,左翼电影在上海兴起,粤语片在香港繁荣,而对这段关键历史时期的产业研究(而非意识形态与艺术研究),基本上没有展开。另一个被长期忽略的空白是日据时期的上海。傅葆石的文章《娱乐的模糊性:日据时期上海的中国电影,1942—1945》详述了当时中国电影业的领军人物张善琨与其日本老 板在娱乐片制作问题上进行的拉锯。傅葆石认为,日本占领时期的电影“成为多种声音 、各种彼此争吵的意义的共存之地……这是一个意义模糊的空间,英雄与小人、政治与 非政治、私人与公共的界限很不清晰,而且总是被跨越”(注:《电影研究》37卷1期, 1997,第66—84页。)。
另一方面,康浩的专著则清晰描绘了20世纪50—80年代中叶的社会主义时期,后文革时代(或新时期)也受到大量关注,比如毕克伟的上述著作,但是二者的重点都不是电影工业。此外,弗尔的《全球化时期的嘉禾公司与香港电影业》为香港电影研究做出了积 极贡献(注:《绒灯罩》34卷,1994,第40—58页。),但研究台湾电影业的英文著作仍 付之阙如。跨媒体产业研究这一新发展方向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卓伯棠在《香港新浪潮 的出现:电视与电影业之间的互动》一文中,探索了70年代末电视与电影业之间的紧密 联系,这种联系直接促成了香港新浪潮电影的出现(注:《跋》19卷1期,1999,第10— 27页。)。在《热门行业:香港媒体的文化经济》一文中,迈克尔·克尔金(Curtin)考 察了90年代的形势,把电影与电视业(包括有线电视与卫星电视)并置在一起,勾勒香港 这一大都市中的媒体景观。他认为,如果香港媒体不那么拘泥于具体媒介中,而更多地 发展跨媒介的合作关系,将受益良多(注:《跋》19卷1期,1999,第28—51页。)。
类型研究
类型研究关注某一类型的程式与惯例,及其在具体影片中的表现、变化及意识形态功能。在所有电影类型中,通俗剧(melodrama)受到了批评界的最大关注,比如布朗论政治通俗剧的书,马宁论家庭通俗剧的文章,卡普兰论通俗剧中性别问题的文章等(注:布朗与马宁的文章参见尼克·布朗等合编《中国新电影:形式,身份,政治》,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卡普兰的文章参见迪沙那亚基编辑的《通俗剧与亚洲电影》,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有关评论,参见张英进《审视中国:评五本中国电影研究的英文书籍》,《电影艺术》1997年2期,第52—57页。)。此外,在《通俗剧的表现与中国电影中的五四传统》一文中,毕克伟质疑了认为左翼力量在1932年把五四运动带进了上海的电影制片厂的说法(这是程季华等人表达的主流提法,李欧梵和一些西方历史学家不同程度上同意这一说法)。毕克伟认为,通俗剧依靠的是“极端的修辞、夸张的表现,以及强烈的道德诉求”。毕克伟细读了《小玩意》(1933)和《天堂春梦》(1947),他对《芙蓉镇》(1986)的分析进一步说明,通俗剧形式的想象是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的(注:毕克伟文章收入埃伦·维德梅尔(Widmer)、王德威合编《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小说与电影》,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
中国电影中另一个比较流行的类型是功夫片。从普通图书到香港国际电影节读物,关于这一类型有很多出版物。西方一般认为这一类型只限于香港,其实这一看法是错误的。最近一些学者研究了该类型,成果如杨明宇的博士论文《中国:<黄飞鸿>/香港:1997:当代功夫片研究》(马里兰大学,1995)、黑克特·罗德里格(Rodríquez)的《解读香港通俗电影:黄飞鸿系列片》(注:英国《银幕》38卷1期,1997,第1—24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卫·波德维尔(Bordwell),他在《行星香港:通俗影片与娱乐艺术》 (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一书中,用不少篇幅讨论功夫片。还值得一提的是张建德,他撰写的《香港电影:另外的维度》(伦敦:英国电影研究所,1997)的16章中,有4章是关于功夫片艺术家的,其中胡金铨、李小龙、成龙各占一章。跟功夫片相关的还有动作片,也常被看作香港的专有类型。但是,关于动作片的大部分研究,多集中于某一导演或影人(如成龙)身上,而较少把这一类型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
除通俗剧、功夫片外,类型研究不经常完全以类型研究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几种类型也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被涉及。首先,改编文学作品在中国大陆一度曾是占主导地位的类型,路易斯·罗宾逊(Robinson)的《<家>:类型改编研究》面对这一话题,比较了巴金的原作《家》(1934)、曹雨的舞台改编(1942),以及上海、香港的三个电影改编(1941、1953、1956)(注:《澳大利亚中国研究》12卷,1984,第35—57页。)。其次,喜剧是中国和香港都很流行的类型,也得到了研究。马宁在《<满意不满意>:60年代中国戏剧中的欲望与话语》中分析了《满意不满意》(1963),这是社会主义中国“为人民服务”这一主题的一个喜剧变奏。刘国华的文章《拳头与血之外:香港喜剧及其80年代的大师》分析了许冠文及其代表作品,尤其是《摩登保镖》(1981)(注:马宁文章见《东西电影杂志》2卷1期,1987,第32—49页;刘国华文章见《电影研究》37卷2期,1998,第18—34页。)。
第三个同样流行的“类型”是都市电影。裴开瑞的《中国都市电影:极端现实主义对 荒诞主义》,以《雅马哈鱼档》(1984)和《少年犯》(1985)代表“自然主义式的现实主 义”,而以《黑炮事件》(1985)和《错位》(1986)代表荒诞主义与表现主义。他认为, 用电影来表现城市的这两种极端方式,都有意违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那一传统 “把经典好莱坞制作与苏联的斯大林风格,以说教的方式捏合在一起”(注:《东西电影杂志》3卷1期,1988,第76—87页。)。唐小兵的《勾勒现代空间:电影对北京的表现及其政治》一文,区分了电影中对北京的两种不同的处理策略:“如果我们说《本命年》的政治,是以现代主义美学的深度表现拒绝与远离的态度,那么《北京你早》中的妥协语言,则看重文化与政治参与,反过来又支持了正在发展的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换言之,如果说在《本命年》(1989)中谢飞表现刑满出狱的李慧泉(姜文扮演)的卒死,是为了表达“后乌托邦的焦虑”,那么张暖忻在《北京你早》(1990)中则把各种空间并置在一起,创造了某种“拼贴的”城市,以力图取得妥协(注:《东西电影杂志》8卷2期,1994,第47—69页。)。
在香港方面,梁秉均研究了20世纪50—70年代的电影中城市形象的历史变迁,而洛枫则探索一种特殊的香港亚类型,即80—90年代的“怀旧电影”(注:参见傅葆石、大卫·德泽(Desser)合编的论文集《香港电影:历史,艺术,身份》,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当然,还需要做更多研究来评价城市电影的影响,尤其是在台湾。其他需要进一步关注的类型包括少数民族电影和战争片,这在笔者的专著中已有论述(注:张英进《审视中国:当代中国电影的批评介入,电影重构与跨国想象》,安纳堡:密支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2002,第151—205页。)。
美学批评
美学批评关注整体的电影美学,某一导演和影片的美学特征,以及传统美学或地方艺术形式对电影的影响。罗德里格在《中国美学问题:胡金铨作品中的电影形式与叙述空间》中提供一种全方位视角,反映中国与西方理论都关注的问题。罗德里格首先认为胡金铨表现了一种“渴望中国”的怀旧情结。胡金铨对放逐及文化漂泊感的体验,西方个人风格理论对他的影响(推重导演的个人特点,鼓励自我表现),他对中国视觉艺术与表演艺术的浓厚兴趣,以及对新道家及禅宗道德准则的关注:这些都是他“渴望中国”情结的诱因。罗德里格分析《龙门客栈》(1967)、《侠女》(1970)、《山中传奇》(1979)等影片,详细描述了胡金铨与京剧、风景画、传统哲学的关系,这些都促成了该导演典型的反理性主义、超脱、非全知全能视角(注:《电影研究》38卷1期,1998,第73—97页。)。
罗德里格的文章表现了对某一导演风格的深厚兴趣,这是西方中国电影研究中不太多见的“导演风格研究”。除胡金铨外,受到学者关注的主要导演还有陈凯歌、侯孝贤、许鞍华、王家卫、吴宇森、谢晋、张艺谋等。有时学者关注的方式是美学批评,但更多的时候则跟意识形态问题或主题问题联系在一起。
心理分析批评
心理分析批评的关注点包括欲望、狂想、凝视、窥视欲/拜物、缺席/在场、恋父情结的发展轨迹、正/反镜头、缝合(suture)、主体性等的运作方式。作为西方电影理论中 的重要一环,心理分析由裴开瑞的文章《潜文本:<大路>中的性与革命》和卡普兰的《跨文化分析存在的问题:近期中国电影中的女性问题》,而进入了中国电影研究领域(注:裴开瑞文章见《东西电影杂志》2卷2期,1988,第66—86页;卡普兰文章见《广角镜》11卷2期,1989,第40—50页。对这两篇文章的批评,参见张英进《重思跨文化研究:西方中国电影研究中的权威、权力及差异问题》,《电影艺术》1996年2期,第19—23页。)。王班1997年对50—60年代的革命电影的研究中,也使用了心理分析批评的方法。他阅读了《青春之歌》(1959)和《聂耳》(1959),对个人与政治之间的截然划分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共产主义文化之所以吸引人,正因为它包含了性的成分;革命电影“也 意识到个人性愉悦的重要性”,其方法是引诱观众“在想象中认同母亲”(祖国),然后 试图“把释放出来的心理能量”转移到“象征性的崇高秩序上”,也就是最高领袖所体现的父亲的律法上(注:王班《历史的崇高形象:20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加州: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
就香港而言,大卫·英格(Ing)的文章《最后地点之爱:关锦鹏<胭脂扣>中的等待俄狄浦斯》,研究《胭脂扣》(1987)针对传统的俄狄浦斯(Oedipus)情景提出的一个反常命题:女性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流动性。英格把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妓女如花[梅艳芳扮演],十二少的母亲及其女仆),以及不同时间段(20世纪30年代与80年代)的女性,通过她们“面对男性时的共同主体位置:处女/非处女”,而联系在一起。英格注意到,阿朱这位1987年的“职业女性……似乎被描绘为一个已解放的后女性主义的主体,她独立于俄狄浦斯(袁),而传统女性(如花)则依赖于俄狄浦斯(陈镇邦)……而阿朱最终又被写入了男性欲望、女性的话语服从这一传统俄狄浦斯情景中”。遗憾的是,英格没有解释,袁和陈这两个相隔半个世纪的迥然不同的男性角色,为什么可以同时毫无争议地代表俄狄浦斯。英格接着又批评了该片与父权体系的共谋关系:“《胭脂扣》的结尾强调了过去、现在、将来之间的连续性,人、技术、风景之间的相邻性。现代的性别模式根本上是传统与过去的再现,集体记忆、集体想象、男性特权在这样的模式中仍固若金汤”(注:《暗镜头》32卷,1993—1994,第75—101页。)。
女性主义批评
女性主义关注主流电影对女性的建构,常常批判宗法父权的意识形态,凸显女性的主体性与性别差异。裴开瑞关于中国“女性电影”的文献汇编,对中国女性影人的情况采取了宽泛的视角。他先从1986年5月《当代电影》在北京组织的一次研讨会说起,总结了一些“公认”的观点,提出主体性与女性体验之间的关系、女性主体性与失落感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典电影的叙述结构原型,都是围绕着分别与团聚的。”他推测说,“如果说西方的意识形态似乎醉心于俄狄浦斯体验,那么中国流行的意识形态,似乎同样醉心于表现和运用在获得主体性过程中体验到的失落,以及渴望回到获得主体性之前的状态。”裴开瑞在序言之后,还附上自己对张暖忻、彭小莲、胡玫的三个访谈(注:《暗镜头》18卷,1988,第5—41页。)。
前面说过,周蕾和卡普兰都对中国电影进行了女性主义色彩很强的解读。女性主义立场的其他论文,还包括吕彤林(音译)的《如何区分男孩与女孩?<疯狂的代价>中模糊的性别界限》(1993)。吕分析影片《疯狂的代价》(1988),讨论了视觉技术(照相机、望远镜、摄影设备)的破坏性,导演把罪责(片名中的“疯狂”)逐渐从强奸者身上,转移到了受害者的姐姐青青身上,她闯入了警察、高塔所代表的男性世界(那位粗暴的强奸者就藏在高塔上)。这样,导演周晓文就自觉地认同了男性权威。对以控制、知识、权力为特征的男性世界来说,歇斯底里的、偏执的青青代表了“阉割”的威胁。她的“疯狂”显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最突出症状:所有界限,包括性别界限,都将消失”(注:参见威廉·伯格温克勒(Burgwinkle)等合编《重要的他者:东西电影与小说中的性别与文化》,檀香山:夏威夷大学语文学院,1993。)。
在《性别化的视角:<菊豆>对主体性与性话语的构建与表现》一文中,崔淑琴也与吕彤林一样,批判了“仇视女性的态度”(即把男人的问题归罪在女人身上):“从父亲形象到儿子,从过去到将来,男性的全部重担、欲望、损失,都推到一个女人的肩膀上。这就是《菊豆》的深层结构和内在声音”(注:参见鲁晓鹏编《跨国的华语电影:身份 ,民族性与性别》,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7。)。崔淑琴对男性意识的批判 ,在唐纳德的文章《异化的症兆:近期中国电影中的女性身体》中也得到了回响。唐纳 德分析了《冬春的日子》(1993)和《北京杂种》(1993),认为在这两部片子中,“男性 焦虑都从男性转移到女性身上”,“‘人工流产系列’……是一种叙述技巧,掩饰了男 性意识的空洞混乱状态”。就性别表现的政治而言,唐纳德发现:“革命的类型与后革 命的独立电影或‘第六代’电影之间,存在着惊人的连续性”。因此她认为,“后社会 主义的英雄主义,起源于转译而非改变”(注:澳大利亚《延续》12卷1期,1998,第91 —103页。)。
性别研究
性别研究常被融入女性主义批评中,它关注性别差异、性别关系、权力结构的表现方式,以及女性特征、男性特征、同性恋问题。邱静美在《文化与经济的错位:80年代电影对中国女性的幻想》中,采用女性主义/心理分析的视角,探讨电影表现与当代政治现实之间的关系。她讨论了20世纪80年代电影形式的内省性,指出占主导地位的是“人道主义”而不是“女性主义”视角,电影也倾向于在文化批判中扮演“选择性的人类学家”的角色。对女性主义来说尤其有意味的,是邱静美所说的“阉割的修辞”:这种共产主义修辞否认一切男性权力,除非其遵从党的权力。这一逻辑在20世纪50年代形成,在文革中达到极端,它使“男性特点在政治上被负面地重新定义”,结果是“权力与欲望被普遍压抑,其对男性的影响要大于女性,因为在1949年以前及其以后,男性都是占据着权力地位的”。正因为这种象征意义上的阉割,拒绝政治对男性的阉割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一个关键问题。《湘女萧萧》(1985)、《红高粱》(1987)等电影都有意把普通农民(而不是党员),作为女性有吸引力的性伙伴,标志着肯定男性特点的新过程(注:《广角镜》11卷2期,1989,第6—21页。邱静美后来在博士论文《1949—1965年中国电影表现女性的话语:艺术、意识形态与社会关系》(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1990)中,继续了这一研究方向。)。
笔者的文章《30年代中国电影话语中的性别:三部无声片中的上海摩登女性》回到了更早的时期,当时男性和女性特点第一次在政治上获得重新定义。笔者考察的是,从《野草闲花》(1930)到《三个摩登女性》(1933)到《新女性》(1934),表现上海新女性的 话语策略如何发生了重大变化。笔者认为,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被“ 无性化”或男性化,而30年代的电影中已出现了其先声(注:《立场》2卷3期,1994, 第603—628页。)。王跃进的文章《<红高粱>:杂糅记忆与欲望》频繁往来于中国文化 传统与西方批评理论之间,研究了张艺谋这部电影里中国式的男性与女性特征(注:裴 开瑞编《中国电影视角》,伦敦:英国电影研究所,1991。)。
鲁晓鹏的《中国肥皂剧:视觉、性话语、男性特征的跨国政治》一文,把中国电影与电视肥皂剧放在同一个比较框架内。他认为,90年代中期的一些中国电影和电视剧,比如《狂吻俄罗斯》(1995)和《洋妞儿在北京》(1996),表现中国男性在追求白人女性时,完全胜出其外国竞争者(如俄国与美国对手),在跨国文化想象的欲望结构中,重新确认了中国男性的核心地位,取代了张艺谋式的“民俗电影”中女性化或去势了的男子角色。(注:《电影研究》40卷1期,2000,第25—47页。)
就香港电影而言,弗尔的文章《重组的女性故事:<潘金莲之前世今生>,<金瓶梅>以及香港通俗剧的政治》,探索了导演罗卓瑶如何在一个父权意识形态统治的社会中(这种意识形态融合了传统与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建构“荡妇”形象。弗尔意识到,罗卓瑶的潜在“女性主义”批判,在《潘金莲之前世今生》(1989)中“却从未浮现到文本表面”。其结果是,该片“最终没有解构荡妇形象,而是为故事选择了更为传统的通俗剧式的解决方式”,也就是“在该片几乎虚无主义地冲向全盘毁灭的过程中”,潘金莲“命中注定”要自杀(注:《电影与录像杂志》45卷4期,1993,第57—70页。)。
香港电影中的男性形象问题,常与动作片或警匪片联系在一起研究。1997年之前的动作片常被解读为“对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的隐喻式阐释”。刘国华认为这样的解读“过于简单化”:“对香港的每一部当代电影都进行这种1997式解读,容易把整个香港文化,尤其是香港电影,缩减成狭窄的政治和经济范畴。”(注:《东西电影杂志》3卷1期,1988,第21—22页。)
同性恋是中国电影研究中的一个新话题。裴开瑞在《性迷惑:同性恋权利、东亚电影、后现代的后民族主义》一文中,力图寻找一个位置,来勾勒这一新领域。他认为:“以视觉形式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同性恋,呼应了其他全球性流动、后殖民混杂,以及各地对正在兴起的后现代全球秩序的接受,而这种秩序同时又是后民族主义的”(158)。他在描述这些与众不同的性群体时,更喜欢“偏离者”(deviationists)而不是“下层者 ”(subaltern)一词。他认为,“‘出轨’(deviant)一词含有想要符合常规而不得的意 思,而‘偏离者’(deviationist)则暗含……更积极的主体性;它包含自觉的因素”(1 70)。他呼吁一种身份政治,它应该是后民族主义的,也超越各种简单的文化或地理界 限(注:唐小兵、司蒂分·斯耐德(Snyder)合编《追寻当代东亚文化》,波德:西景,1 996。)。实际上,视觉性也是裴开瑞的另一文《表现中国的同性恋生活:<东宫西宫>》 中的核心议题。他认为,张元对同性恋进行的电影研究,“所关心的并非如何以与众不 同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身份(这在巴特勒[Butler]等人关于表演性[performativity]的 讨论中,是主要的关注点),而是这种身份根本可不可以表现这一大问题”(注:《跳接 》42期,1998,第84—89页。)。
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界定的“领域”,它关注一系列广泛的问题,比如性别、性话语、阶级、种族、民族、权力、知识、现代性。阿克巴·阿巴斯(Abbas)的《香港:消失的文化与政治》(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7)与周蕾的《原始的感情:视觉性、性欲、民俗学与当代中国电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5),在不同程度上代表着中国电影的文化研究取向。二人都集中关注视觉性在现代、后现代、后殖民文化中的意义,二人也常常自由往来于电影与其他文化产品、话语行为(如建筑、文学、音乐、摄影、理论、翻译)之间。
彼得·希奇科克(Hitchcock)的文章《关于异化的美学:中国“第五代”》,以高度理论化的方式来阐述中国新电影。他游弋于马克思、阿尔都塞、布迪厄、拉康等众多西方理论家之间,如是界定自己的目标:“我不想描述‘第五代’的历史,而是想根据前面说的彼此矛盾的线索(一条线索是‘异化’,在当代电影中,从历史上而言,这是一种特殊的中国美学实践……另一条线索是‘女性的暗喻’,它既在中国文化关系中表现一种男性至上的欲望,又在国际公共领域表现了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来理论性地对待他们的作品”。在分析了《黄土地》(1984)、《红高粱》、《女人的故事》(1987)后,希奇科克得出结论说:“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些导演在美学上力图对抗集中化艺术生产的雷同倾向,但我认为,他们显然常会造成自己本要反对的那些意识形态的效果”(注:《文化研究》6卷1期,1989,第116—141页。)。
多学科研究
在结束西方中国电影研究的方法和议题的选评时,我想指出三个要点。第一,就象文化研究的情况一样,上面说的每一研究类别,都可以根据具体的方法或批评的重点而继续细分。在“历史研究”的条目下,我区分了电影政治与电影文化,但我们也可以从中分出其他三类:(1)社会学方法,其中数字表格和统计对理解电影工业研究来说至关重要;(2)实证方法,即通过访谈和个人观察来获得第一手资料;(3)档案方法,即依赖各 种出版物,从政府文件、行业报告、影迷杂志、影评,到生平资料、回忆录、日记、信 件。
其二,依据具体研究题目的不同,同一个学者也会采用不同的方法。比如,裴开瑞在阅读《大路》时采用心理分析方法,但在其《市场之力量:中国第五代导演面临底线问题》中提供最新发展的情况时,则转向产业研究(注:参见其所编新版的《中国电影视角》,1991。)。同样,邱静美在《<黄土地>:西方的分析与一个非西方的文本》中运用符号学和结构主义,而在《国际化想象与“中国新电影”》中则采用文化史的方法,把第五代导演取得的国际成功,以及新城市电影在中国的出现,置于跨国文化力量、国内社会经济与意识形态变化的背景之下(注:邱静美前文见裴开瑞的《中国电影视角》,1991,其后文见《电影与录像季刊》14卷3期1993,第95—107页。)。
第三,西方的中国电影研究这一领域是朝多学科开放的,所以至少迄今为止,上述的任何一种方法或议题都不占主导地位。当然,分析、解读某一导演或影片的文本研究远远多于描述、预估市场经济的产业研究或挖掘、整理资料的历史研究。无论20世纪的研究成果有多少局限,西方的中国电影研究毕竟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在跨学科的领域里扎根、发展,成为电影研究和中国研究领域中令人注目的后起之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