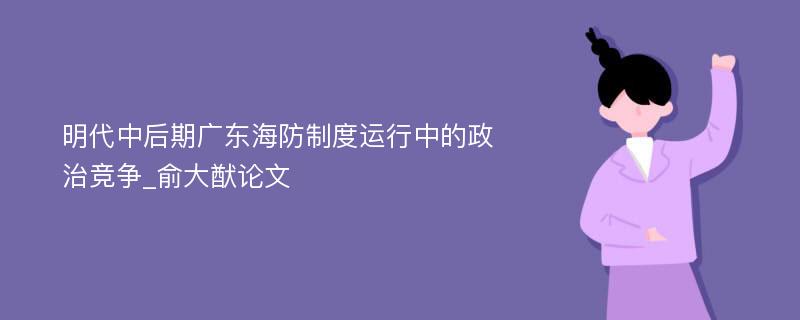
明代中后期广东海防体制运作中的政治较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防论文,广东论文,明代论文,后期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6)02-0111-08 隆庆三年(1569年)五六月间,闽广两省兵船先后在福建铜山、玄钟和广东莲澳等海域会剿曾一本及其党羽,最终铲除了这支肆虐多年的海寇势力。关于官府平寇的过程,万历十年(1582年)任潮州知府、江西泰和人郭子章(1543—1618年)在《潮中杂纪》中有如下简略回顾: 曾一本者,福建诏安人。招亡纳叛,聚党数万,出入闽广,大肆猖獗,攻城掠地,杀虏参将缪印等官兵数多,屡年不能平,致厪圣怀。廷议推兵部左侍郎刘焘总督闽广军务,以兵部员外郎王俸随军赞画。议于南北两京帑银内解发十万两以资兵食。(隆庆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入境,督催广东巡抚熊桴、福建巡抚塗泽民、总兵俞大猷、郭成、李锡、参将王诏等进战。……五月十二日一战于铜山,胜之;六月十二日再战于玄钟澳,又胜之;二十六日再战于莲澳,又胜之,生擒贼首曾一本,擒杀党伙数千,悉除。[1] 郭子章的追述重在铺陈隆庆三年(1569年)闽广两省合力“生擒贼首”的“后果”,①至于“屡年不能平”的“前因”并未过多着墨。事实上,当局清剿海寇之所以屡屡受挫,期间的政策和人事反复调整,恰有助于揭示明代中后期区域海防体制的症结和发展趋势,反映政治、军事和社会的纠葛,值得今人深究。 曾一本是明代中后期活跃在闽广交界海域的巨寇之一。在他之前,有许朝光、吴平,后续则有林道乾、诸良宝、林凤等相继为患,“鲸鲵聚啸,旋讨旋发,未有晏然享数十年之安者”。[2]既往的研究对海寇活动的影响、海寇的身份背景及相关史料的整理发掘,已有相当充分的讨论,②但鲜有专论从事件的发展深入分析当时海防体制存在的问题。拙稿试以曾一本之变为背景,通过勾连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管窥这一时期广东海防体制运作中作战策略、军备、事权、军情传递等方面面临的挑战。 一、广东的“抚贼之策”与闽广协剿海寇的矛盾 曾一本的籍贯来历众说纷纭。《明实录》多处笼统称之为“广东贼”、“广贼”、“广东盗”。[3]前引《潮中杂纪》说他是“福建诏安人”,与稍后万历三十年(1602年)刊刻的《广东通志》略同,但后者又有“一本,潮阳人”的记载,前后龃龉矛盾。[4]晚出的康熙《澄海县志》则说“海阳薛陇人”。[5]潮阳、海阳均为广东潮州府属县。一些地方文史学者则明确指出曾为海阳(今潮州市潮安县)薛陇乡人,但未明所据。[6]对曾一本身份的模糊记载,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当时海盗活动出此入彼、流动不居的特性。无论如何,曾一本作为海寇吴平的同伙,在前者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逃遁后整合其余党,“西寇高雷等府,回屯东港口,四出嫖掠,潮揭受祸最酷”,[7]很快就发展成为这片海域又一巨患。 以总兵汤克宽(?—1573年)为代表的广东当局起初试图招抚曾一本,将之安插在潮阳县,但未奏效: 先是海贼吴平既遁,而余党曾一本突入海惠来间为患。克宽倡议抚之。贼既就抚,乃从克宽乞潮阳下会地以居,仍令其党一千五百人窜籍军伍中。入则廪食于官,出则肆掠海上人。令盐艘商货报收纳税。居民苦之。[8]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八月,佯装就抚的曾一本突然进犯邻省福建的玄钟澳,但在福建兵船阻击下,“彼即遁回潮州”;由于此前咨会两广提督吴桂芳(1521—1578年)、广东总兵汤克宽发兵协剿遭拒,时任福建巡抚塗泽民不敢贸然越境剿寇: 本院咨会两广军门吴(桂芳)发兵协剿,随准回称“宁照封疆为守,贼在广则广自任之,过闽然后闽任之”等因。又准广东总兵官汤克宽手本开称“曾一本面缚军前请降,散党安插。但虑闽中兵船越潮哨捕,惊疑反侧之心,以坏招抚成功,烦行各将领知会”等因。本院以此为信,谕令官兵各照封疆自守。是以贼虽迫近邻境,亦不敢轻发一兵,越境行事,以伐其陵渐之谋。一则惟恐悖两广军门画疆之议,以取贪功之讥。一则惟恐坏汤总兵抚贼之策,以为日后借口之资。[9] 塗泽民没有指示福建兵船进入广东海域追击曾一本确有所顾忌。虽然塗泽民申明尊重广东当局的军事策略,确认了基于政区界限的事权划分,但从他“惟恐”的“贪功之讥”和“借口之资”足见两省在剿寇问题上存在嫌隙。闽广山海相连,海寇出此入彼,在海防问题上本为一体。但受制于两省之间信息沟通、权责分工和兵船装备等因素,协剿海寇却往往难以做到步调一致。塗泽民后来也承认,双方矛盾在稍早前的“吴平之役”就已埋下伏笔: 闽南地接广东,彼省海寇,东击西遁,故每议夹剿。然夹剿之事,其势实难。约会之文,往返不易。船在海上,往时镇巡司道不得亲行坐督,惟凭将领较短竞长,致生嫌隙。上年吴平之役可见。是以前任两广军门吴咨议宁照封疆为守、如贼在广则广自任之,如贼遁闽则闽自任之,以绝推诿之奸等因。[10] 由此可见,要理解广东当局对曾一本的初始态度和后续处理,有必要回顾两省共同对付海寇吴平产生的纠葛。吴平在嘉靖末年多次勾引倭寇,流劫闽广沿海,一度受抚安插在闽广交界的诏安县梅岭。③时任广东总兵、曾负责招抚吴平的俞大猷(1503—1579年)在给福建总兵戚继光(1528—1587年)的信中说,“吴平徒党颇众,向以旧倭在境,恐其合伙,故权处分”,[11]似乎表明当局的招抚乃权宜之策,但这样做并未奏效。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八月,吴平再次举兵叛乱,“驾船四百余艘出入南澳、浯屿间,谋犯福建”,朝廷诏令闽广两省协力夹剿。[12]由于刚刚发生柘林叛兵围攻广州事件,两广总督吴桂芳奏设“督理广州惠潮等处海防参将”,将分处惠州、潮州的碣石和柘林两地兵船归并到东莞南头,集中兵力拱卫省城,直接导致吴平复叛时东部海防虚空,广东方面根本无力招架。④前线指挥作战的俞大猷深知“吴平事,闽中决用兵……闽中兵兴,平必率众由船入广,则责专在广矣”,为此一面呈请吴桂芳早日调遣兵船前来,[13]一面去信时任福建巡抚汪道昆(1525—1593年),声明“潮中时下水陆俱无兵,如欲会剿,乞约会于三个月前,方可齐备”。[14]可见,广东参与协剿作战从一开始就相当被动。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四月,戚继光先行督发福建兵船袭击吴平,迫使后者率众退保广东南澳岛;紧接着,“闽兵先至,围攻之,平得间道去,以小舟奔交趾,官军竟无所得”。[15]由于吴平逃脱,俞大猷因追战不力被弹劾革职,广东惠潮军务暂时改由戚继光兼管。[16]事实上,闽广会兵有约期在先。此番合作以广东失责告终,但福建也有急于求成、贪功冒进之嫌。当吴平避退南澳时,福建巡抚汪道昆已收到“贼阳筑室而阴修船,盖将乘汛而遁,俟北风起”的谍报。在给兵部尚书杨博(1509—1574年)的信中,他表示“其势不能缓师,闽人各持二月粮,计必穷追以责成效”,因此“藉令广兵如期而至,相与犄角而一鼓歼之,此上愿也。不然,则闽人可为者不敢不自尽,其不可为者亦无如之何矣”。[17]但由于“广东兵船尚无消息”,无法判断广东当局动向,福建一方于是单独采取军事行动。[18] 两省会剿“有会之名,无会之实”,未能一举擒拿贼首,“彼此之间,不求其故,反相归咎”。[19]究其原因,以往的研究一般认为,由于畛域有别,人事不和,两省官员相互推诿,难以协调。[20]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广东仰赖雇募兵船作战的海防体制使然。对此,指挥前线作战的俞大猷指出: 二省大举夹剿之师,一备一未备,实其所遇事势之不同。闽广之官,易地则皆然。若责广,谓怠慢;指闽,谓猛于从事,皆未考易地皆然之义也。何也?闽五水寨,各有兵船,福、兴、泉、漳沿海地方不过十日之程,督府总戎檄书驰取官民船只,旬日可集。广中无水寨兵船,又道里辽远,一公文来往,非四五十日不能到。而东莞民间乌船,时出海南各处买卖,官取数十之船,非月余不能集。船集而后募兵,兵集而后修整杠具,又非三二十日不能完美。抚按诸公非不严文督限,其势自不能速耳。此在人者不可必,岂敢故自怠慢乎?又二三月风色,与八九月同。船自广来潮,俱要唱风,不可以时日计。此在天者不可必,岂敢故自怠慢乎?[21] 可见,广东沿海并无常设水寨,完全仰赖募集民船民兵,加上季风气候影响,无法短时间大规模集结兵力,与福建水寨兵船的机动能力形成鲜明对比。⑤当日率闽兵入广的戚继光甚至奏称“近该臣入潮、惠,未见彼中一兵”。[22]此说或许夸张,但也表明广东兵船不足乃不争事实。 在军饷筹措方面,广东同样捉襟见肘。早在福建单方面行动前,俞大猷“请取五千之兵于军门”未果,误以为吴桂芳“以钱粮困乏为辞”,专门去信福建巡按、广东南海人陈万言(1519—1593年),请后者“便中于自湖公处为借一言”(按:吴桂芳别号自湖)。[23]吴桂芳为此多方筹措,但收效甚微。例如,他奏请归还“两广先年协济浙中兵饷银十余万”,“以济一时燃眉之急”,但遭到浙江官员反对。虽有时任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广东南海人庞尚鹏(1524—1580年)支持,认为“吴平未灭,即两浙未有安枕之期”,但未见下文。[24]吴桂芳又以“用兵缺饷”为由,奏请归还先年解送四川布政司协济采木的35万两军饷银,但户部覆议“止准该省解还银三万两前来两广支用”。[25] 上述背景直接促使吴桂芳在吴平事件后推动广东沿海水寨建设。他认为“今广中素无水寨之兵,遇有警急,方才召募兵船,委官截捕”,“必须比照浙闽事例,大加振刷,编立水寨,选将练兵”,“要害之所无处无兵,庶奸慝无所自容,而海波始望永息”,[26]显示他已充分认识到广东海防体制的局限。 但必须指出,吴桂芳奏设的六大水寨(柘林、碣石、南头、白鸽门、乌兔、白沙)自东往西分布在潮州、惠州、广州、雷州、琼州五府沿海,兵船规模庞大,但毕竟只是规划设想,并未完全付诸实践。就在奏设水寨不久,吴桂芳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九月改任南京兵部右侍郎。[27]上述如此大规模的兵船几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配备到位。而造募兵船的巨额经费从何而来,吴桂芳也未及交代。以往一些研究者没有细究吴桂芳的去留问题,直接征引其《请设沿海水寨疏》相关内容,视之为当时已经推行的举措,并不符实。⑥事实上,直到隆庆初年俞大猷征剿曾一本仍苦于兵船不足,感慨“东广虽新设六水寨,向未设有战船。近日事急,方议打造,并搜掳民间次号船只追捕”。[28] 回过头看,正因为当时水寨蓝图筹划未果,兵船尚未齐备,当局面对前述曾一本的迅速崛起,首先倡议招抚,可能也有不得已为之的苦衷。 二、造船募兵的争议与曾一本进犯广州 对于招抚曾一本,福建巡抚塗泽民自始至终都不以为然。在给广东当局的咨文中,他认为曾一本“明系阴怀异志,假为说辞,不然既称投降,何又抢虏渔船,勒要居民报水。其顺逆之情,居然可见”。可见塗泽民对曾一本的动向密切关注,因此“闽人固不敢越境剿贼,然亦不肯甘受侵犯而竟寝伐暴之师”。[29]相比起福建的警惕,广东当局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却明显不足。 隆庆元年(1567年)七月,曾一本再次叛变,一度绑架澄海知县张璿三个月,“焚杀潮郡居民数千人”。[30]刚刚接替吴桂芳履任两广总督的张瀚(1510—1593年,隆庆元年八月调任)把矛头指向总兵汤克宽,一方面严词批评他“身膺重任,轻率寡谋”,“抚处失策,致复背叛”,认为“曾一本者,止一黠贼,逼挟良民,纵肆为盗,向使将领有司处置得宜,岂遽猖獗至是”;另一方面,因汤克宽被革职处置,新任广东总兵一时推补未至,张瀚疏请重新起用“素负威名”的俞大猷带管广东总兵官事务,会同巡抚李佑合力剿寇。⑦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初,参将魏宗瀚、王如澄等率领的广东各路官兵8482名、战船145只在雷州海域与曾一本激战。初次交战后,见在官兵4979名,战船80只,损失大半。这批兵船退回雷州府的南渡港整顿,不料“各贼尽数连至港内”,守备李茂才战死,官兵“陆续奔逃”,战船焚烧殆尽。而官兵仅打死贼人300余名,打沉贼船三只。[31]经此“南渡之败”,“广省数年预备攻战之具,坐是一空”。[32]敌我力量对比开始发生逆转。 隆庆二年(1568年)正月十七日,俞大猷向张瀚提出进剿海寇对策,主张先安抚其他尚未成气候的海寇,对曾一本则“必至于灭而后已”,认为当务之急是差人前往福建造船募兵: 为今日广东海洋之计,宜吊回参将魏宗瀚、王如澄,把总俞尚志、朱相牵连,差去福建打造福船。每一参将、一把总二十只,共四十只,每只该银三百三十两,其船用福建造船尺,宽二丈六尺,船外钉以竹板,并船上杠椇、器械完整,总在三百三十两数内。每船合用头目一名,听参将、把总自选。每船用兵七十五名,并头目七十六名,每头目合给银三两,每兵合给银一两五钱。造完,各船齐驾南下。以广之白艚船五十只,共用兵一千五百名,乌艚、横江船四十只,共用兵二千八百名,与福船合势,以总兵总统之,何患贼之不灭乎![33] 俞大猷同时估计,“以差往造船之日为始计,至收工之日决不出六个月外”,长远来看,“功成即将此船分各水寨,则地方可期永宁”,适可解决前述六大水寨的军备问题。[34]几天之后,俞大猷再次重申“海贼不患不灭,但灭贼无具,而欲求速则决不可”,请求当局照前议加紧赴闽造船募兵,限期一个月完成。[35]俞大猷提出前往福建打造的福船,是一种“蜂房垣墙”、“重底坚牢”的大型船只,与当时过洋和使琉球船式相同,[36]时人常把福船与广船并举,后者俗称“乌艚船”、“大头船”,它们经过改造均为一流的海战船。但是,福船一般以松杉木打造,广船则以铁栗(梨、力)木为船料,坚牢性更高,造价也更昂贵,“广船若坏,须用铁栗木修理,难乎其继”、“广船用铁力木,造船之费加倍”。[37]笔者曾专门讨论过明代中后期广船在海防上的应用及其海上作战优势,此不赘言。[38]此番俞大猷之所以要如此大费周章,主要有以下两点考量:一是赴闽造船花费、耗时较少,有言“福建造,每只用银三四百两,此间造要银七八百两乃造得;且取匠于福建,买木于广西,恐日月又迁延也”;[39]二是避免船只成为海寇攻击的目标,有言“若在此造,贼必入犯,咎将谁委”,[40]“贼知在此造船,入烧将如何”。[41]然而,此举并未得到广东地方官员支持,不少人认为身为福建人的俞大猷有徇私之嫌,最后“众议福船就于广省打造”,仅采纳赴福建募兵的建议,[42]造成“造船委官,日延一日,并无一只完备;雇募福兵初到,无船可驾,只在岸上安宿”的窘局。[43] 同年六月,曾一本攻打省城,“率众数千、乘船二百余艘突至广州,杀掠不可胜纪,外兵入援乃引去”。[44]事件导致“半载经营战船杠椇,复为贼烧毁占据”,[45]应验了俞大猷建议赴闽造船的“先见之明”,但他久久不能退敌,也因此成为众矢之的,招致各种责难。广东番禺人郭棐(1529—1605年)在其编撰的《广东通志》中毫不掩饰对俞大猷的不满: 隆庆二年海寇曾一本犯广州,总兵俞大猷、郭成御之,败绩。……大猷能言,著兵书画策,多可观听,而遇事失措,竟无功。欲致一本以自解。因令人招一本,许之高职,命郭成统楼船驻兵波罗,上下冀得相机擒之。一本亦欲致大猷,阳许焉。约至大鹏所降,大猷以为信。然先至以待时,所将兵少,一本驾大艚六十艘直掩,大鹏有侦事把总知之,豫以报。大猷怒把总妄语,把总以死邀之,大猷始心动,趋归。越夕而一本至大鹏矣。遂乘风直进,郭成御之。贼投火,兵船尽焚。大猷与成敛兵入城。一本乘潮上下,饮于海珠寺,题诗诮大猷。大猷丧魄,不能以一矢相加,遣其杀掠,视柘林叛兵尤憯。驻城下旬余,竟无一援兵至。及退,福兵横恣,大猷尚曰:“我当时不诛首恶二人,此曹亦叛矣”。闻者笑之。[46] 对俞大猷的作战策略、处事风格以及由他募集的福建兵,郭棐均有微词,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广东官员的态度。当时甚至有人揭发俞大猷“通贼”,“数人欲进猷所居衙门搜奸细”,俞大猷的处境可想而知。[47]至于郭棐所谓“福兵横恣”,其实与“招兵闽海,虚冒尤多”有关,⑧乃当时募兵作战的通病。反过来,俞大猷则多次抱怨“管广船参将坚不准福兵上广船”,[48]“福兵为此方人疑,用之于水,则无大船,用之于陆,便说劫掠”,[49]等等。为此,俞大猷的福建同乡、广西按察使郭应聘(1520—1586年)在得悉曾一本攻打广州后建议他把兵力分散屯驻,“不然闽兵逾万专扎省城,其不生扰而速谤者无几矣”。[50]事平之后,郭应聘也建议他不应留下闽兵,“不然他日驭失其道,又诿之闽兵,往事不足鉴乎?”[51]可见相互猜忌之深。 三、督抚职掌与闽广兵权的统一 在曾一本寇掠广州之后,两广总督张瀚面临更大的政治压力。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朝廷“切责总督张瀚,令亟率镇巡等官悉力剿贼,以安地方”,总兵俞大猷、郭成都受到停俸处罚。[52]内阁大学士张居正(1525—1582年)在给张瀚的私信中也批评他用人不善,认为“广事不意披猖至此,诸将所领兵船亦不甚少,乃见贼不一交锋,辄望风奔北,何耶?将不得人,军令不振,虽有兵食,成功亦难”,指示他“诸凡调处兵食事宜,似宜少破常格,乃克有济。公若有高见,宜亟陈本兵,当为议处也”。[53]前面说过,张瀚出任总督时就疏请起用俞大猷,后者有关赴闽造船募兵的对策也曾直接向他呈报,但实际推行阻力重重,剿寇事宜并不完全在张瀚掌控之中。其要因,是两广总督与广东巡抚之间职掌不明、相互掣肘。 成化五年(1469年)十一月,朝廷采纳广东巡按监察御史龚晟、按察司佥事陶鲁等人建言,开设两广总督府于广西梧州,选址“界在两省之中”,以韩雍(1422—1478年)总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旨在解决“两广事不协一,故盗日益炽”的军政难题。[54]开府梧州之初,两广总督重在经略粤西。[55]随着海寇活动日益猖獗,虽然广东省城广州和肇庆府城均有总督行台,以备巡行,但毕竟常驻梧州,远离沿海战争中心,文檄往来不便,军情传递不畅,难以及时指挥调度。⑨俞大猷就感叹“此间议论不一,朝夕更改。军门又远,禀请颇难。奈何?奈何?”[56]在这种背景下,由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添设广东巡抚“专驻广城以御海寇,兼防山贼”,重点经理惠州、潮州二府,两广总督止兼巡抚广西,[57]其在广东的军权无形中被巡抚架空。正因如此,身处广州指挥作战的俞大猷在给张瀚的禀贴中直言:“地方之事,惟有李巡抚同心戮力。无如人不奉行,事多阻坏,心亦苦也,恩台当知之。”[58] 在广东军务上逐渐沦为“虚位”,又不得不为战争失利担责,张瀚于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奏请“明职掌以一政体”,两广总督与广东巡抚的矛盾公开化。 张瀚指出,前年添设广东巡抚,“是东省既有巡抚而又使总督得兼制之”,“广东地方一应兵马调遣、剿抚机宜与军饷盈缩、仓库积储、各衙门大小文武官员考核贤否及考满给由,皆总督职掌所系,理得与闻;抚按官诸凡调遣举措,或提请有干军计及举劾官员等项,俱应关会”,但他“奉命前来将及半年”,“巡抚衙门往往不行关会”: 如前奏讨浙直四川原借军饷,竟不相闻,以致臣与广西巡按御史朱炳如陷于不知,亦复题请前银为西省之用。又如分巡兵备等官考满呈详,应准给由或应会本保留,俱宜计议定夺。今每径自具题或移咨吏部,并不相闻,事皆龃龉。 接着,他疏请“今后除巡抚事宜不关军计外,其地方稍重贼情、调遣官兵、处置粮饷与文武官员给由应留应考等项及事干题请,俱要关会议处施行”,兵部报可。[59] 张瀚此番奏请有多重政治意义。通过批判广东巡抚擅权妄为,暗示其剿寇指挥失误,不仅适可缓解因战争失利承受的舆论压力,更重要的是重建两广总督权威,有助于扭转内部事权不一的体制弊端,为后续闽广两省再次会兵剿寇奠定基础。 隆庆二年(1568年)十月,曾一本“突至南澳,窥福建玄钟界”,朝廷命令闽广两省协力夹剿,显然已意识到此前两省“彼此推诿,以致滋蔓”的恶果。[60]为了避免“各官兵有彼疆此界之嫌,怀分功计利之意”,张瀚鉴于前述吴平之役的教训,奏请两广军门督率福建官兵进剿,暂时节制该省镇巡将领,突出广东当局在剿寇中的主导地位,力图理顺双方事权关系。[61]此议得到朝廷认可。同年十二月兵部左侍郎刘焘(1512—1598年)接替张瀚出任两广总督,得旨兼督福建军务,[62]两省之间因政出多门产生的纠葛终于得以化解,闽广兵权得以暂时统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文开篇征引的郭子章《潮中杂纪》所述闽广兵船合力剿寇、节节胜利的历史画卷才得以展开。晚年张瀚追忆治粤往事,仍津津乐道当初奏请“福建官兵亦应听两广节制”,自诩“余方解绶而一本就擒,计诚得也”。[63] 四、结语 明代中后期广东沿海动乱持续不断,时称“遍地皆贼”。[64]地方士绅多次强烈反对安插“抚贼”。⑩嘉靖年间曾任兵部主事、潮州海阳人陈一松(1498—1582年)为家乡父老奏呈《急救生民疏》,称“群丑日招月盛,居民十死一生”,[65]足见舆论对当局动辄招安、剿寇不力相当不满。但若简单地将时局的混乱归咎为官府腐败和无能,难免失于鸟瞰泛论。 通过上述对曾一本之变中种种纠葛的分析不难看出,首先,在应对策略上,招抚海寇一贯被视为解决沿海动乱的主要手段,广东当局一开始就主张招抚曾一本而非积极剿杀,显示出官府作战决心不强。但客观上当时广东新设水寨,沿海兵船不足却是影响决策的一大制约。官府非不作为,实有难作为的苦衷。其次,在用人和事权分工上,前线将领官员之间猜忌攻讦,加上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衙门分处梧州和广州,两者在军务上职掌不明,造成政出多门,军情传递不畅,直接造成俞大猷赴闽造船募兵的对策大打折扣,终究在随后曾一本进犯省城时酿成严重政治危机。第三,在对外协同作战上,广东当局与福建在早前合剿海寇吴平时产生嫌隙,相互推诿,难以协调,以至于曾一本初叛时两省对战局的判断不一,固守疆界,各自为战,贻误战机,让海寇集团得以休养生息,最后酿成尾大不掉之势。 要言之,通过“曾一本之变”的案例,会发现当时广东海防的部署变化背后包含相当复杂的权力和利益之争,过多的政治较量及人事纠葛贯穿其中,始终是左右时局发展、影响海防战斗力的关键因素。因此,要全面认识明代中后期广东海防体制的症结及其面临的挑战,有必要进一步深究具体人事对制度和战事的动态影响,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海防设施或海防地理的静态描述。 注释: ①关于曾一本“被擒”的内情,有传言在第三次会剿的莲澳之战中,广东参将王诏与曾一本遭遇搏战,“会一本发铳,火落药中,焚毁其手足,因被擒”,官府有侥幸获胜之嫌。事见万历《广东通志》卷70《外志·倭夷·海寇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济南:齐鲁出版社,1997年,第760页。 ②相关研究详见陈春声:《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2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第73-106页;陈学霖:《张居正〈文集〉之闽广海寇史料分析》,《明代人物与史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21-361页;冷东:《明代潮州海盗论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黄挺:《明代后期闽粤之交的海洋社会:分类、地缘关系与组织原理》,《海交史研究》2006年第2期;陈春声:《16世纪闽粤交界地域海上活动人群的特质——以吴平的研究为中心》,李庆新主编:《海洋史研究》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29-152页;汤开建:《明隆万之际粤东巨盗林凤事迹详考——以刘尧诲〈督抚疏议〉中林凤史料为中心》,《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 ③参见前引陈春声:《16世纪闽粤交界地域海上活动人群的特质——以吴平的研究为中心》,第129-152页。 ④有关“柘林兵变”之后吴桂芳的海防改革,参见陈贤波:《论吴桂芳与嘉靖末年广东海防》,《军事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 ⑤谭纶(1520—1577年)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巡抚福建时为应对海寇重建沿海五大水寨,包括浯屿水寨、南日水寨、烽火门水寨、铜山水寨和小埕水寨。参见卢建一:《闽台海防研究》,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年,第71-77页。 ⑥相关研究详见蒋祖缘、方志钦主编:《广东通史(古代卷)》下册,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57页;广东海防史编写组:《广东海防史》,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8-169页。黄中青:《明代海防的水寨与游兵——浙闽粤沿海岛屿防卫的建置与解体》,宜兰:学书奖助基金,2001年,第129页。 ⑦俞大猷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革职闲住,但随后吴桂芳奏请派俞大猷镇守广西,于隆庆元年(1567年)正月十六日受命为镇守广西地方总兵官(参见何世铭:《俞大猷年谱》卷3,泉州:泉州历史研究会,1984年油印本,第24页)。因此,张瀚奏请将之再次调来广东,仅是暂时带管总兵事务。 ⑧值得指出的是,俞大猷对部下的管束可能不够。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带兵剿抚惠州山贼时,其部下扰民,深为当地士人百姓所恶。事见唐立宗:《矿冶竞利——明代矿政、矿盗与地方社会》,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11年,第519-520页。 ⑨关于两广总督府址的变化,学术界历来争议较多。有学者认为嘉靖四十三年总督府已迁驻广东肇庆,但新近研究表明,两广总督于万历八年(1580年)迁移肇庆、崇祯五年(1632年)迁移广州。在此之前仅于两地分别设立过总督(提督)行台,以备不时巡行之需。参见吴宏岐、韩虎泰:《明代两广总督府址变迁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3期。 ⑩陈春声对当时官府招抚海寇的做法和引起的反弹有详细讨论,参见前引陈春声:《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第73-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