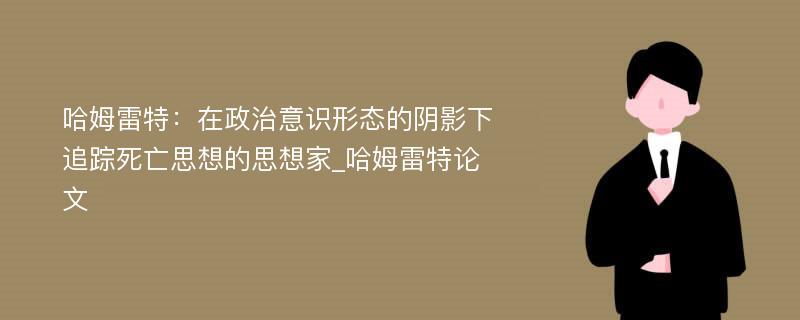
哈姆雷特:政治意识形态阴影中追踪死亡理念的思想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者论文,意识形态论文,阴影论文,理念论文,哈姆雷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莎剧的研究者们对《哈姆雷特》一剧条分缕析,层层探究。但如云的批评家们也许忽略了一个历史文本所能建构出来的基本状况,那就是:在莎士比亚时代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动荡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新旧政 治、知识和伦理意识纷然杂呈,处于互相冲突碰撞、互相选择组合的矛盾运动中。主体浸透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注:本文使用广义的概念、与阿尔图塞的泛意识形态概念近似,即,意识形态就是现实生活中任何表征系统表达的价值观念和利益关系。它不涉及明显的虚伪性和政治压制性。任何立场和观点皆存在于意识形态之中。意识形态之外,别无他物。为具体的文学文本的意识形态分析起见,泛意识形态观念可以按社会意识的不同层次具体区分为政治意识形态,智能(知识)意识形态和伦理意识形态。关于这一提法,本文作者另有拙文详细论述。)漩涡之中,在构塑自我的过程中必然呈现出无中心的零乱和无常的混乱状态。排除莎士比亚本人的意识构成和现实的艺术创作意图,我们可以说,《哈姆雷特》集中地演示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现代主体确立的这种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哈姆雷特作为自我意识极强的主体,面临着各种意识形态的召唤:克劳狄奥的政治权力包容;鬼魂的父子伦理;奥菲丽娅的性爱,还有友情与勇气,正义和忠君意识。这些纷杂不定的社会意识和价值观,期望通过这个自觉的主体显现自己的存在。然而,哈姆雷特总是拒绝俯就,他的意识总是超越社会现实层面,上升到终极存在的本体论高度。在哈姆雷特的思想世界里,政治就是阴谋,国王犹如乞丐;超自然力量的真伪之辨也是个实践问题,有情人终归还是“罪孽”的滋养者……。哈姆雷特习惯于用哲学思考和自我追问来代替现实的行动。他常通过想象来确定他与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由于强烈的身份感,他总是执著地坚守着知识和智能的意识形态阵地,不愿通过沟通和交换来获得观念的妥协和心灵的安宁,甚至不惜最终付出生命的代价。换句话说,哈姆雷特总是保持着主体的意识形态构成,拒绝其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召唤和同化,直到主体意识的彻底消亡。
本文侧重讨论哈姆雷特特有的知识和智能意识形态与克劳狄奥为代表的主导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对持续的政治意识形态召唤的拒斥过程中,哈姆雷特在充满了哲理思辩的话语中反复征用与死亡有关的意象来表达他的世界观和厌世情感。他的脑海里经常浮现出死神的形象,他寻求与死亡对话,描述尸体的腐烂过程,思考着自杀的可能性和合法性,用哲学的思辩来探求死亡的意义。哈姆雷特似乎是一个死亡哲学的朝圣者,不受人间现实价值、五情六欲的诱惑。在旅途的终点,他充分展示了独立于世、群而不党的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同时也制造出一种超乎道德判断以外的有关死亡的意识形态。在此过程中,哈姆雷特没有被克劳狄奥邪恶政治意识形态所包摄或同化,相反,他的主体内质不断地被一种形而上的意识形态所重写和强化,反复显现出一种人文的理想主义精神。本文首先围绕着哈姆雷特的知识意识问题对以往一些经典性的观点作出评析。在此基础上细读剧本,意图在哈姆雷特充满死亡意象的生命思辩中窥视到哈姆雷特智能(知识)意识形态的基本特点,从而揭示出英国早期现代主体意识构建的过程。
二
为了在上述范围内讨论哈姆雷特的智能意识问题,有必要首先简要地讨论一下有关这个问题的几个本源性的批评观点。首先,笔者认为18世纪莎评大家约翰逊博士可算是研究哈姆雷特思想心智的始作俑者。约翰逊认为,哈姆雷特复杂的心态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父亲暴亡、母亲匆匆改嫁,本已使这位多思的王子难以承受这生命之重,超自然的道德谕示又使幻灭的心灵蒙上了理性怀疑主义的阴影。哈姆雷特“欲而其反, 则恍惚无定;自知责任压人而不知所措。
”(注:参见G.R.Woudhuysen:《塞缪尔·约翰逊论莎士比亚》,伦敦,1989年(英文版),第240页。)为此,“他的心灵遭受了无以伦比的巨大创痛。 ”(注:参见G.R.Woudhuysen :《塞缪尔·约翰逊论莎士比亚》, 伦敦,1989年(英文版),第241页。 )由于哈姆雷特极端的哲人气质和对外部事件的敏感力,他不分利弊,完全忘记了他的王子身份。因此,剧中哈姆雷特的一切过失行为都不是出自他内心的驱使,而是应归咎外部事件引发的精神刺激。用哈姆雷特本人的话来说就是:祸根是“他的疯狂”,而这正是“可怜的哈姆雷特的大敌”。(5.2.237,239 )(注:本文中引用的莎士比亚戏剧原文皆出自G.Blackmore Evans编《河畔莎士比亚全集》(波士顿:1974版),并由本文作者参照朱生豪译本译出。引文后括号中的阿拉伯数字分别表示引文所在幕、场和行数。)约翰逊用启蒙理性的尺度来衡量哈姆雷特的意识和性格特点,建立了哈姆雷特主观心智特点和外部事件作用的二元对立模式。这样说来,哈姆雷特本人内心的理性是自然的存在,而一切非理性的话语和失常的行为都是外部力量的体现。正因为哈姆雷特不同寻常的哲人气质和思辩习惯,使得外部事件通过主体的想象和推理能够延展下去,而这位文人气质的王子“在剧中自始至终都是事件发展的被动工具,而不是主动的行为者”。(注:参见G.R.Woudhuysen:《塞缪尔·约翰逊论莎士比亚》, 伦敦,1989年(英文版),第244页。)与此相反,19 世纪浪漫主义诗论家柯勒律治从个人心理构成来解开哈姆雷特的心智和性格之迷。柯勒律治用他的诗人内心有机形式和心理创造想象力的美学理论来观照《哈姆雷特》,认为应该跳出剧本结构框架来理解哈姆雷特的内心世界。哈姆雷特首先是个诗人和哲学家,他富于幻想,充满智慧。他为思想而思想,忘却现实功利价值和客观的生存世界。文人学者从现实中具体的人物和事件看到人类的总体特征和生存状况,看到客观世界形而上的规律和真理。柯勒律治也曾说:“如果能如此作比的话,我自己就有点象哈姆雷特。”(注:参见R.A.Foakes:《柯勒律治论莎士比亚》,伦敦,1989年(英文版),第89页。)诗人和哲学家的内心世界是想象和知识的世界,同时也是个人与客观现实对立的源泉。由此观之,衡量哈姆雷特思想怪异、行为失范的标准并不是某种现成的理性道德规范。哈姆雷特沉湎思想、疏于行动是由他本人的思想意识构成决定的。用柯勒律治的话来说:哈姆雷特的意识构成“抽象和概括的思维习惯远远甚于实用的倾向……。现实中的每一事件都会引起他的苦思冥想。”(注:参见R. A.Foakes:《柯勒律治论莎士比亚》,伦敦,1989年(英文版),第89页。)上述两种观点在20世纪初莎评大家A.C.布拉德雷那里得到引申和延展。布拉德雷深受黑格尔悲剧冲突论的影响,同时在方法上也十分赞同利F.R.利维斯所谓文学批评要获得对文本“完全的细部的反应”以达到“完全占有文本”(注:F.R.利维斯:《文学批评与哲学》,见K.M.纽顿:《20世纪文学理论文集》,伦敦,1988年(英文版),第67页。)的主张。因此他努力全方位地来阐释悲剧“行动中的人物”的现实意义。布拉德雷主张把哈姆雷特作为现实生活中真实的社会人来加以细致的剖析。实际上,布氏综合了约翰逊的外力论和柯勒律治的内因说,通过细致分析《哈姆雷特》剧中各人物在不同场景中的心理反应,得出结论:哈姆雷特特殊的哲人心智和外部的突发事件共同作用,导致了这场悲剧。哈姆雷特能思善辩的习惯久之积成严重的忧郁症,令人震惊的事变加深了哈姆雷特的心理危机,促成了他失常的精神状态。而且,随着剧情的发展,哈姆雷特内心的失衡又因不断受到外部事变的刺激而不断加剧。尽管哈姆雷特具有“精致入微的感悟力”和“天才的思考能力”,但是由于他内向的心态和多事的现实,“他的道德感悟力和智能天才反倒成了他的大敌。”(注:A.C.布拉德雷:《莎士比亚悲剧》,纽约,1991年(英文版)第96,98,103页。)
这就是对哈姆雷特智能知识意识构成的三种经典性观点。20世纪以来其他有影响的《哈姆雷特》评论家都不同程度地回应了这三种批评基调。例如,50、60年代历史现实派的代表J.多佛·威尔逊对《哈姆雷特》的评论是柯勒律治观点的回声。威尔逊认为,哈姆雷特沉湎于探索生物终极真理的哲人精神具有超现实的意义。研究哈姆雷特就是“研究人类的天才”;这位忧郁的王子是“最令人钦佩的英才”。(注:J.D.威尔逊:《哈姆雷特引言》见新剑桥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50年,第LXIV页。)与此针锋相对,意象象征派莎评家G.W.奈特认为,哈姆雷特因外界事件的刺激变得疯狂变态。在他颇具影响的《烈火的车轮》一书中,奈特集中地讨论了哈姆雷特“极端的忧郁病态和迷狂的厌世主义”。(注:G.W.奈特:《烈火的车轮》,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30年(英文版),第24页。)奈特认为,哈姆雷特被“心理和精神死亡”(注:G.W.奈特:《烈火的车轮》,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30年(英文版),第31页。)的病魔附身;他“就象一剂毒药,在哪里出现,就在哪里威胁着丹麦王国的健康和幸福”。(注:G.W.奈特:《烈火的车轮》,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30年(英文版),第33页。)奈特把哈姆雷特与邪恶的伊阿古相提并论,因为“他们都在残暴的行为中获得魔鬼般的满足。”与在剧中表现得“心地善良,举止文雅的国王克劳狄奥”(注:G.W.奈特:《烈火的车轮》,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30年(英文版),第29页。)相比,哈姆雷特“却是丹麦王国邪恶的根源”。(注:G.W.奈特:《烈火的车轮》,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30年(英文版),第42页。)介乎二者之间的是以提倡细读文本著称的L.C.奈茨。奈茨一贯反对对莎剧的主观臆说。但在哈姆雷特内心意识和性格特征这个问题上,他也必须基于剧本例证对上述两种极端看法加以调合。奈茨通过文本分析,认为在哈姆雷特的精神世界里,邪恶的冲动和善良的愿望混杂一处,共同受制于一种“自我思想沉迷的气质”。(注:L.C.奈茨:《哈姆雷特王子》,见《探索:十七世纪文学批评集》,伦敦,1946年(英文版),第67页。)外部发生的事件可以催化这种心态,加重哈姆雷特性格和意识的两面性。奈茨认为,总体而论,尽管《哈姆雷特》问题成堆,悖论不少,但对于所有带有某些难以克服的人性弱点的人来说,这出剧“都是一种可能的亲身经历”。(注:L.C.奈茨:《哈姆雷特王子》,第76—77页。)“起码说来,我们大家都有点象哈姆雷特。”(注:H.列文:《1660—1904年的莎士比亚评论》,见S.威尔斯 编,《剑桥莎士比亚研究指南》,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第224页。)当然,除了上述三种批评主流外, 还有其他新解异说。例如E.琼斯用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对哈姆雷特心理意识的解说。哈姆雷特被说成是一个深陷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而不能自拔的狂想症患者。他与叔父克劳狄奥的关系自然就成了变态情敌的关系。这种大胆的心理推论即使不是缺乏根据的主观臆说,也是依附精神分析学说而生成的理论注解。它虽成一家之言,但难以形成气候。
新批评派的莎士比亚学者却不以为然。他们把上述莎评家称为“最危险的一类批评家”。(注:T.S.爱略特:《哈姆雷特和他的问题》,见H.艾顿 编《柏拉图以来的文学理论》,纽约,1971年(英文版),第788页。)因为他们的写作里充斥着评论者强烈的主体表现欲。用T.S.爱略特的话来说,这些批评家“用想当然的创造意识”来评论文学文本。他们“基于各自的艺术见解,在《哈姆雷特》中捕风捉影”。这些批评家“从来就不记得,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研究艺术作品本身”。(注:T.S.爱略特:《哈姆雷特和他的问题》,见H.艾顿 编《柏拉图以来的文学理论》,纽约,1971年(英文版),第505页。 )对于新批评派莎评家来说,剧本《哈姆雷特》是第一性的,而人物哈姆雷特是第二性的。莎评家的唯一任务就是研究和分析作品上的白纸黑字,因为有了它们的有机组合才构成了艺术作品本身。如果基于个人的心理学见解和道德观念对戏剧人物的言行细加评说,只能使艺术沦为现实生活中价值判断的注脚。我们要打破主观价值判断的思维习惯,把哈姆雷特看成是文本中一个活跃的因子,而不是活生生的现实人物。这样才能对这出剧文本细部的艺术结构和价值作出客观的归纳和分析。
受新批评派影响的莎评家既不对哈姆雷特的性格、意识和情感作出大包大揽的主观价值判断,也不去找寻哈姆雷特复仇延宕的最终原因。他们即使有时离不开剧本的意识和价值评判,也首先深入文本的形式结构。这样,作为人物存在的哈姆雷特王子就渐渐隐去,不同形式结构或艺术意象所形成的意识总体框架随即显现。笔者认为在此方面著名莎评家,耶鲁大学教授M.麦克在他颇有影响的《哈姆雷特的世界》中作出了很好的示范。麦克在细读《哈姆雷特》的过程中力图把握文本结构所趋示出来的宏观意识总体而不是具体的意识状态。他把这种意识总体称为“想象的环境……一种心灵的微观境界”,即一种有机结构,其中“各组成部分互为意蕴,每一组成部分的存在和意义都与其余的成分密切相关”。麦克从文本结构细部入手,发现《哈姆雷特》的语言结构所表征的是一种充满了神秘指义、质问意念和玄思迷语的智能思想世界。在这个复杂的语义网络里,现实的存在成了问题。现实与想象的关系不断地由一些反复出现的词和意象推到思想的前台。 比如, “鬼影” (apparition),“似乎”(seem),“假定”(assume),“装扮”(put on),“形状”(shape)等词反复出现,构成一种意念链。 还有疾病、衣物、脂粉、涂料、彩色饰物等意象也反复出现,构成意义的网络。在这个充满迷雾和断裂的意识世界里,个体的人物失去了主体的选择,而是“在两种选择的废墟上摸黑前行,既不能拒绝一种选择,又不能完全接受另一种选择……只能用思想的线索来安慰自己”。(注:M.麦克:《哈姆雷特的世界》,见L.F.狄恩:《现代批评文集》,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年(英文版),第243页。 )用英国文化唯物主义的话来说,主体被非中心化,在空洞的能指构成的幻觉虚像中靠无现实目的盲目行为驱动着。这里,麦克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从文本结构到思想意识世界的自下而上的阐释途径,使我们能够隐约找到文本形式特点与全剧总体意识之间的联系。可以说,麦克用新批评细读文本方法,又突破了新批评不言作品表征意义的限制,开了联系文本形式构造特点与文本指意阐释的先河。
近来有些莎评进一步注意到了文本特征对揭示《哈姆雷特》中折射出来的整体意识的有效性。构成《哈姆雷特》独特的意识和情感世界的不是外部事件的突变,不是人物的心理或性格因素,也不是二者的综合作用,而是文本形式构造特征(特别是反复出现、形成格局的文字意象)。例如,J.亨特对《哈姆雷特》中大量的肉体意象的采集和分析犹为引人注目。亨特把全剧视为一个“人体肢体解剖大作坊,堆放着不同种类的肢体、脏器、肌肉和体液”。(注:亨特对《哈姆雷特》中的肉体意象的收集和统计十分详尽。其中出现的身体器官从头到脚共42个,内脏器官14个,体液种类共6种,器官功能27种,身体肿瘤病变8种。正如有些评家所论,这些肉体意象聚会一处,可以归结哈姆雷特提出的那个问题:“人是怎样一件特殊的造物?”(What a piece of work is aman?)。这恰恰反映了莎士比亚时代人文主义和怀疑主义智能意识形态的中心议题。)人的整体形象隐退,取而代之的是破碎人的感觉。莎士比亚似乎在这出剧里把现实社会简约为支离破碎的肉体存在。亨特认为,这种对有机生命整体的肢解“引发出一种本体错位的烦躁情绪”。这些意象的反复及其分布使人感到中心的永久缺席。“《哈姆雷特》中的一切事物分崩离析,或被强行撕裂扯碎。”随着剧中鬼魂召唤哈姆雷特去砸碎新国王为首的政治肌体(body politics)的神秘呼声, “哈姆雷特就会从生理、心理、道德、伦理、政治各方面把个社会搅个天翻地覆。”(注:亨特对《哈姆雷特》中的肉体意象的收集和统计十分详尽。其中出现的身体器官从头到脚共42个,内脏器官 14个,体液种类共6种,器官功能27种,身体肿瘤病变8种。正如有些评家所论, 这些肉体意象聚会一处,可以归结哈姆雷特提出的那个问题:“人是怎样一件特殊的造物?”(What a piece of work is a man?)。这恰恰反映了莎士比亚时代人文主义和怀疑主义智能意识形态的中心议题。第31页。)亨特的分析说明了莎士比亚时代智能(知识)意识形态的两面性。一方面,人文主义借古典文化复兴冲破中世纪禁欲主义的樊篱,高扬人的主体精神,使之显出“世界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哈姆雷特》1.2.307)的光彩。另一方面,人的血肉之躯和精神状态短暂无常,不过是“一堆污浊的肉体”和“一捧精细的尘土”,它顷刻就会“融化,消散,化成一滴露水”。(1.2.129—130;2.2.308)正如F.巴尔克所说的那样,《哈姆雷特》中大量的肉体意象“不是僵化的隐喻”,而是“社会现实秩序的指示标志,因为人体在社会构成中处于不可简约的中心位置”。(注:F.巴尔克:《颤抖的个体:论主体》,伦敦和纽约,1984年(英文版)第23页。)在这类文本形式研究中,剧中人物哈姆雷特的意识构成和性格特征不再重要,批评的聚焦点是戏剧文本整体的话语构成(特别是隐喻手段)所揭示的整体意识。而这种整体意识正是通过剧中主要人物哈姆雷特的言语和行为得以传达和张扬的。
三
我们知道,主体的思想意识和性格形成是一个与现存的各种社会意识互相拒斥、互相商讨、妥协和包容的过程。文学文本的阐释中,如果以现实生活为参照,对人物的意识和性格特征作主观的价值评判当然是片面的,而专注于文本形式指义规律,并以此归纳出文本的总体意识特征也是不够的。如果我们用一种动态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哈姆雷特》中显现出来的智能(知识)意识形态,把它看作一个各种社会意识互相碰撞、互相召唤的过程,我们就不难发现,对哈姆雷特的思想意识和情感作古典主义的理性判断、浪漫派的主观想象以及新批评的形式勾玄,都更多地是对一种预设观念的描述,而不是对一种动态意识形成过程的分析。它们要么展示了批评家基于个人现实经验和伦理观念对哈姆雷特哲人般的思想和气质的阅读感受和判断,要么试图通过对文本形式细部的发掘和联系来揭示出《哈姆雷特》总体的社会意识形态构成。有鉴于此,下面本文试图解读文本,从一个侧面来描述和分析哈姆雷特智能意识在拒斥政治意识形态召唤和包容的过程中的自我塑构。我们注意到,在这个主体自我塑造的过程中,哈姆雷特抵御以克劳狄奥为代表的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招募和置换,其主要表达方式就是在“精神失常”的掩护下发出的一系列知识话语和反复出现、形成格局的主导意象。剧中大量反复出现的是与死亡有关的意象。在哈姆雷特的哲思玄想中,黑色的死亡首先是对人类生命之光灭顶的遮蔽,然后是对污浊丑恶的人类社会的逃避,死亡成了社会不平等的最佳均衡手段,成了人类一切欲望和抱负的毁灭者。这一系列的死亡意念正是哈姆雷特智能(知识)思想意识和哲人情感的重心,也是哈姆雷特拒斥政治意识形态召唤和包容的主要意识堡垒。
哈姆雷特的智能(知识)意识形态一开始就与政治危机后重建的丹麦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直面相撞。作为丹麦王储、国家未来的栋梁和骄傲,哈姆雷特具有强烈的身份感和对自己生存状况的认同感。国家政权发生变故,他即刻受到以篡位君主克劳狄奥为首的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召唤。得知父亲暴亡,母亲匆匆改嫁叔父,哈姆雷特悲愤交加,出现在宫廷中,听取新王克劳狄奥对朝廷变故的处理和对外政策的训令。克劳狄奥那富于修辞色彩又讲求实效的开场白(1.2.38)隐含着多层次的意识形态意图:对先王的伪善悼念并号召节哀;对国家现实的关心;宣布与前王后这位“伟大国家共同的统治者”(1.2.9)的及时婚姻, 以此巩固自己的地位;显示自己精明的政治和外交手腕以赢得朝野的认同和支持。克劳狄奥传布的正是典型的国家权力伪意识。它的基调是:国家的现实利益高于一切。由于暗杀国王而取得的国家政权是非法的,克劳狄奥意图用现实表象的合法冲淡伦理道德的不合法,用国家利益的伪意识掩盖死亡的沉重和人性情感的悲哀。而这一切伪意识的背后是政治权力的最终目的,即建立国家政权的权威和合法性。另一方面,年轻的哈姆雷特本是封建政治意识形态确立的正统王位继承人,此时与国家权力无缘,倒成了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召抚对象。哈姆雷特对这样的权力分配组合在潜意识中是十分抵触的。(注:哈姆雷特在剧中回答国王派来的密探时几次提到他“脑子坏了”的原因时欲言又止,却在无意识中表露了自己对失去王位的耿耿之心。(2.2.252—265;3.2.240—344)在他的意识中,在这个颠倒错乱的年代,担负起国家兴亡,重整乾坤是他当然的职责。(1.5.188))而且, 如此的政治权力组合格局一直笼罩在哈姆雷特父亲,前国王突然死亡的阴影之中,这也是哈姆雷特一直挥之不去的疑团。克劳狄奥却不然,谋杀篡位得手,对死亡之事已不在意,他一心只想在现实中确认和巩固既定的意识形态关系。此时他一开口便称呼哈姆雷特为“我的儿子”(1.2.64)。表面上,这是家庭亲情关系的表达,而实际上这却是国家权力对哈姆雷特的直接意识形态召唤。哈姆雷特对此拒绝屈从。他以讽刺意味极强的一句旁白作答:“亲情关系还算近,品性言行相去远。”(1.2.65)“亲情”(kin )和“自然同类”(kind)这两个词的对比是表象与实质的对比,它表露了哈姆雷特对以亲情为幌子的伪意识的抵制和对自然真诚的人际关系的向往。这也正象征着克劳狄奥政治意识谋略与哈姆雷特人文理想的意识形态冲突。同时,kindness这个词在此语境中双关,意指“相似”(likeness)和“家族成员”。哈姆雷特用之来识别自我主体的身份,表明他认同与克劳狄奥的叔侄关系,但拒绝认同他们的君臣关系。在哈姆雷特的意识中,克劳狄奥虽为亲族成员,但与刚刚暴亡的前国王在人格品性方面毫无相似。克劳狄奥对哈姆雷特阴郁的态度并未在意。他知道,捕捉和包容主体是一个反复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他必须首先知道哈姆雷特表面的悲哀后是否隐藏着某种逆反主导意识形态的思想活动:“为什么愁云依然笼罩在你的心头?”(1.2.66)克劳狄奥用“云”这一意象比喻遮蔽哈姆雷特真实思想活动的意识伪装。这立即在哈姆雷特的意识里引起了“太阳”这个相反的类意象:“不,陛下,我已在太阳里呆得太久。”(1.2.67)这里的“太阳”(the sun)与“儿子”(the son)同音,构成意义强烈的双关:“儿子”处于父权社会的从属地位,一直生存在象征着国家权力的“太阳”的恩泽之中。这种文字游戏实际上就是一种智能意识形态,它的弦外之音在克劳狄奥强烈的政治意识中是昭然若揭的。哈姆雷特接着用一连串使人联想起前国王的死和真情悲哀的意象和意念进一步表明他与克劳狄奥貌似理智的伪意识不相容的立场:“黑黑的外套”、“习俗规定的黝黑的丧服”、“郁闷的叹息”、“滚滚江河般的泪水”和“悲苦的脸色”。这些都是“悲哀心情的装饰和门面”。(1.2.77—84)而哈姆雷特从来“不知道什么‘好像’不‘好像’”,因为他的悲哀是“无法表现出来的”。(1.2.85)他是在追寻人对死亡所持有的根本态度。在情感爆发之后,哈姆雷特开始了他探究死亡观念的旅程。然而,克劳狄奥并不轻易放弃。他顺势接住哈姆雷特用隐喻传达出来的死亡意念,试图用“理性”的教谕来归化哈姆雷特:人皆有一死,而且不可抗拒的自然律条的“共同主题就是父亲的死亡”。 (1.2.103)用“上天”、“理性”和“人之常情”来衡量,哈姆雷特“放任不节的悲伤”、“顽冥不化的固执”和“女人气的哀恸”表现出“逆天背理的任性,经不起挫折的心胸,缺乏忍耐的意志和简单愚昧的理性。”(1.2.94—97)但是,直接的意识形态宣教往往机械而空洞,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克劳狄奥还必须“动之以情”,再次启动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和召唤功能,驱动主体的潜意识想象。他称哈姆雷特为“朝廷重臣,至亲和儿子”(1.2.117), 把主体的政治地位和亲属关系合为一体,并郑重宣布:“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是王位的直接继承者。”(1.2.108—109)可是,哈姆雷特对国家权力的承诺不屑一顾。他对克劳狄奥伪善地劝他暂缓回威登堡而留在宫中(实际上是借此控制其行动)的劝告置之不理,只因母亲的再三恳求才勉强同意。他的答语故作庄重有礼,一反适才耿耿的怨恨语气,但清楚地表明了蔑视权威的意蕴:“谨此勉力从命,母亲大人。”(1.2.120 )克劳狄奥对这当众给他下不了台的挑战自然怀恨,但是精明的政治头脑告诉他,此时小不忍则乱大谋。于是他作释然状,好像刚才紧张的意识形态对峙已经冰消瓦解,哈姆雷特已经屈从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召唤,确认了自己“朝廷重臣,至亲和儿子”的主体身份。他不失时机地宣布通宵礼炮齐鸣,狂欢庆典,“让上天应和着地上的雷鸣,发出欢乐的回声。”(1.2.126—128)政治意识形态就这样制造假象,让人们相信它已经成功地对哈姆雷特这个最容易形成对立政治势力的主体进行了包容和同化。
然而,这才刚刚开始。如果我们暂且不论这部剧的道德和复仇延宕问题,上述简短场景中显示出来的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关系即可视为贯穿全剧结构的中心线。在此场景以后直到第三幕第二场的戏中戏,克劳狄奥和哈姆雷特都似乎有意回避面对面的遭遇。表面上似乎井水不犯河水,但实际上各自却在自己的意识形态领地积蓄力量,以备终有一搏。意识形态的张力始终吃紧。国王的策略是“躲在帷幕之后”(2.2.163),在大臣波洛涅斯和朝臣罗森格兰茨和吉尔登斯吞的协助下,策划一系列旁敲侧击的话语圈套,以深入哈姆雷特的意识,“发现发疯的真正原因。”(1.2.49)另一方面,哈姆雷特求得同学和巡回伶人的帮助,进行了反调查,设计了戏中戏(即“捕鼠器”mousetrap )中一系列的戏剧意象,以便“捕捉到国王内心的隐秘。”(1.2.605)。 在此过程中,死亡意象及其关联的意念不断出现在哈姆雷特的想象中,最终被观念化,成为哈姆雷特形而上沉思的重心。
克劳狄奥对哈姆雷特意识深处的第一次窥测发生在第二幕第二场。哈姆雷特已从鬼魂口中得知这场“最为伤天害理,最为逆伦不道的谋杀”。(1.5.25)此时他神情恍惚,手捧一本旧书从侧台独自入场。国王和王后急避帷幕后侧耳细听。大臣波洛涅斯为探虚实主动凑近前搭讪,却被哈姆雷特唤作一个“卖鱼的”,即不诚实的人。哈姆雷特似乎以他特有的敏感,知道波洛涅斯为人鹰犬,人格低下。因为在他的想象世界中,在这个“乏味,平庸,腐朽荒凉的世界上”(2.2.133), “万人之中方可挑出一个诚实人。”(2.2.78)虚伪的意识掩盖了一切本真的东西。于是,哈姆雷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多用隐喻回答波洛涅斯的提问。他的话多否定人生价值,描述衰老过程,感叹人生奋斗的徒劳和不可避免的死亡。人的价值是“死狗身上的蛆虫”;(2.2.187 )爱情和生命繁衍也终将成为“太阳光亲吻下的臭肉”(2.2.182); 衰老匆匆而至:“灰白的胡须”,“布满皱纹的脸”(2.2.197—199);象征知识的书籍也不过是干巴巴的“字符,字符,字符!”(2.2.192)死亡的意象随即而至。哈姆雷特有意把波洛涅斯的建议“走进去避避风”(walk out of air)理解为“走入坟墓”, 声嘶力竭地向他吼道:“我不愿给予的东西你休想取走,但你可以要我的命!你可以要我的命!你可以要我的命!”(2.2.216—218)。哈姆雷特的这番“疯话”意在告诉躲在帷幕后的克劳狄奥:他的意识中充斥着在死亡阴影笼罩下的人类生存意义问题。这属于哲学问题,与政治毫不相干。
这一连串关于死亡的疯话不是对克劳狄奥政治意识形态的直接威胁,而是人性精神深处永久的恐惧,它与人生观和世界观有着密切联系。早些时候,哈姆雷特说他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连一棵针都不如”。(1.4.65)他成天思考着为什么上天会“制定出禁止自杀的律法”。(1.2.132)此时,经过鬼魂超自然的死亡谕示,哈姆雷特已经走出了个人肉体消亡和灵魂毁灭的思想胡同,开始研究死亡的普遍意义。在那段著名的“生存还是毁灭”的独白中,死亡的意象已经十分观念化了。哈姆雷特看到了存在的虚无、生命的困境和来世的劫难。G.威尔逊说:“死亡是这部剧的主题,因为哈姆雷特的病根就是精神的、灵魂的死亡。”(注:G.W.奈特:《烈火的车轮》,第42页。)批评的焦点如果落在哈姆雷特这个人物身上,这个观点有其合理性。但如果超越个体,以普遍社会意识为参照,那么哈姆雷特有关死亡的思辩就不是个人心理错乱失常的表征,而是一种有关死亡的知识话语,一种拒绝以现实利害关系为目的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体现。个人的忧生畏死生成现实的人际关系,而对死亡的观念的追踪显示的却是哲人探索真理的精神。
如果说波洛涅斯与哈姆雷特的问答只是克劳狄奥用一个“令人生厌的老傻瓜”(2.2.219 )对哈姆雷特的内心世界作出的一次小小的试探,那么紧接着上场的朝臣罗森格兰茨和吉尔登斯吞则代表着克劳狄奥政治意识形态对哈姆雷特的一次直接的召唤和逼迫。哈姆雷特刚见儿时的好友,叙旧中自然暂时脱去了意识形态的伪装。但不久就警觉起来:此二人在宫中的突然出现并非偶然。哈姆雷特于是重新带上面罩,使用模糊的语言以遮蔽思想:他把丹麦比作一座大监狱并解释说,“世间并无善恶,只是思想会作这样的区分。”(2.2.149—150)罗森格兰茨立即抓住话题,意图引诱哈姆雷特承认自己精神失常的原因是“丹麦太小,容不下[他]的政治野心”。(2.2.250—252)这句话代表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哈姆雷特的直接召唤。它好像在说:“喂!你就是这样的,认同这个身份吧,很多人都和你一样的。”可是哈姆雷特拒绝合作,他遵循着自己的意识形态惯力,用貌似中立的智能知识话语来抵制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定位。他利用有限时空和无限思想这一传统的二元对立关系,玩起文字游戏来:“呵!上帝,倘若不是恶梦缠身,那么即使把我关进小小的硬果壳,我也能把自己设想成拥有无限空间的君王。 ”(2.2.254—256)然而,罗森格兰茨和吉尔登斯吞目的明确,他们不会放过哈姆雷特话语中任何暴露自己内心意识的蛛丝马迹。他们指出,所谓“恶梦缠身”,正是政治野心在意识中的躁动不安,因为野心即主体意识深处无边的欲望想象。它缺少理念,离现实太远,“是空洞轻浮的虚体,不过是影子的影子。”(2.2.261—262)至此,哈姆雷特几乎被逼入穷途,他挣扎着接过话题,把它推至一个荒诞的极端:这么说只有乞丐才算是实体,因为只有他们才没有野心。这个比喻多少有点勉强,哈姆雷特于是只得宣布自己江郎才尽:“说实在的,我的头脑坏了,不能谈玄说理。” (2.2.265)面对国家权力要求非此即彼的回答的追问,哈姆雷特不能作指义明确的应答,否则就会陷入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漩涡而招致杀身之祸。于是,他退回自己的智能(知识)意识形态领域,用对宇宙人生存在和意义的肯定或怀疑来与现实政治权力保持距离,用死亡的观念来掩饰对现实国家权力的反叛。他告诉这两个御用朝臣,这个宇宙神奇壮观,在“金黄色的火球[太阳]的点缀下”,负载万物的大地是“一座美好的框架”,覆盖众生的苍穹是“一顶壮丽的帐幕”。可是归根结底,这天堂式的乐园又是一片无望的死寂:大地不过是“一片不毛的荒岬”,宇宙也就是“一大堆污浊的瘴气的集合”。(2.2.298—313)一方面,人类是世间一切生物高贵的主人:“世界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另一方面,人类又是死亡卑躬的奴隶,是“一捧精细别致的尘土”。(2.2.307—308)对于观众或读者来说,这番话是包蕴在文艺复兴时期怀疑主义氛围中的人文主义思想的曲折表达。但对于两个国王派来的宫廷密探来说,这正是哈姆雷特“巧妙地装疯卖傻”的证据,这位多思的王子正是以此“有意回避”(3.1.8 )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的检验和召唤。
精明实干的克劳狄奥却不是那么容易被蒙蔽的。哈姆雷特的政治地位以及这些谜语般的话语对国家权力表现出明显的不恭。而且,国王深知:“大人物的疯狂是不能听其自然的。”(3.1.189)因为他发现,在“这些长吁短叹之中,都含有深长的意义。我们必须设法弄懂其真正的含义”。(4.1.12)波洛涅斯被哈姆雷特刺死的消息传来,克劳狄奥终于发现用隐喻传达的意识形态召唤与同化已经无济于事。哈姆雷特不仅是一个对主动政治意识形态不予合作的“坏主体”(bad subject 阿尔图塞语),而且还是危及国家权力肌体的“毒疮恶疾”。(4.1.21)更有甚者,哈姆雷特“深受那些糊涂群众的爱戴”(4.3.4), 而且宫廷里的意识形态斗争已经“在全国上下引起窃窃私语”。(4.3.41)这些都无疑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国王此刻必须当机立断,走出意识形态帷幕,向不羁的主体施行强制行动。他派遣罗森格兰茨和吉尔登斯吞去找哈姆雷特和波洛涅斯的尸体。但是哈姆雷特仍采取不合作态度。他称国王的使者是“海绵”(意即国家权力虚设的意识形态工具),把死尸的意象与国王混为一谈,再次套用书本典故,把玩智能(知识)意识形态的游戏:
罗森格兰茨:殿下,那尸体您怎么处置了?
哈姆雷特:它本身泥土,现在又和泥土合为一体啦。
……
罗森格兰茨:殿下,您必须告诉我们那尸体在哪儿,然后跟我们见王上去。
哈姆雷特:那尸体与国王共居一处,但国王却并不与它同体。国王可是一件物体。
罗森格兰茨:一件物体?殿下!
哈姆雷特:一件空空的物体!带我去见它。
(4.22.5—6,25—30)
哈姆雷特在这里又在玩弄传统的观念与实体两分法,从中透视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鄙视,以此获得智能独立、知识占有的满足感。国王的肉体和国王的观念不可相提并论;当朝国王虚情假意,根本不配国王的名分。此外,哈姆雷特在此对死亡的观念也有了更新的玄想。死亡是社会不平等最终的均衡状态。国王也是“犹如一件空洞的物体”(《圣经》,赞美诗,144:4)的人;而人又是乞丐,“匍匐于天地之间”,(3.1.127—128)把“生活的价值和目的仅仅看作吃吃睡睡”。 (4.4.34—35)去见王上去?就是去见“一件空空的物体”而已。 在国王面前,哈姆雷特更进一步地渲染他的天均观。他把国王、乞丐、腐尸、蛆虫的意象揉和一体,把人均于死的玄思表达得淋漓尽致:
国王:好了!哈姆雷特,波洛涅斯呢?
哈姆雷特:吃饭去了。
国王:吃饭?在什么地方?
哈姆雷特:不是他吃饭的地方,是在人家吃他的地方;有一群在政治家身上养肥了的蛆虫正在他身上大吃特吃呢。蛆虫是世界上最大的饕餮家;我们喂肥各种牲畜供自己受用,再喂肥了自己去给蛆虫受用。胖胖的国王和瘦瘦的乞丐是一个餐桌上的两道菜,不过就这么回事。
国王:唉,唉。
哈姆雷特:一个人可以拿一条吃过国王的蛆虫去钓鱼,再吃那吃过那条蛆虫的鱼。
国王:你这话什么意思?
哈姆雷特:没什么意思。我只是提醒你,一个国王可以在一个乞丐的脏腑里作一番巡礼哩。
(4.3.16—31)
哈姆雷特在意识中获得了一种超越死亡的境界;人的一生有意识无意识都在避死。而死亡一旦成了天均人均的总体观念,也就失去了现实意义。
哈姆雷特对荣誉和死亡都不屑一顾了:对个人,死亡是永恒的睡眠;对社会,死亡是知识,是观念;对宇宙,死亡是天均大道。荣誉又是什么呢?哈姆雷特注视着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那些“为了争夺区区不毛的弹丸之地而视死如归地走向他们的坟墓”(4.4.53)的两万士兵,突有顿悟:荣誉是“一个狂想中空虚的名声”。(4.4.61—62 )哈姆雷特就是用这形而上的判断又一次确认自己知识哲人的意识形态身份。我们也许可以说,在这场意识形态的对抗中,政治意识形态未能成功地包容或归化哈姆雷特的智能迷想,却反倒加强了后者固存的主体意识。哈姆雷特在读者(观众)心目中越来越明显地成了一个善于通过对宇宙人生苦思冥想和追问来建构自我于现实关系的形而上学家。至此,莎士比亚本人似乎也走失在哈姆雷特智能(知识)意识形态的迷津中,无力在扬善惩恶的原则指引下把握哈姆雷特在戏剧情节发展过程中应有的言行。具体地说,戏剧家的职业理性已被哈姆雷特追踪死亡观念的精神所淹没了。
从波洛涅斯的死开始,死亡的意念充斥着各个场景。首先,哈姆雷特在回国途中目睹了为政治意识形态而战的两万挪威士兵面临的灭顶之灾。此后,罗森格兰茨和吉尔登斯吞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英王砍掉了脑袋。哈姆雷特被死亡之象占据了心胸:“从这一时刻起……,让流血的思绪充满我的脑际!”(4.4.65—66)在宫中,奥菲丽娅被父亲突然死去的消息惊呆,理智全无(4.5.85);在她催人泪下的悲歌中,她的父亲下葬和在坟墓里渐渐腐烂的悲惨意象反复出现:“未被遮盖的脸”在“灵柩架”上“苍白如纸”,引起“泪雨纷纷”(4.5.164—167);“冰冷的泥土中”,腐烂的尸体“头上长出青青草,脚前竖着石碑”。(4.5.36,31)紧接着,悲恸过度,精神失常的奥菲丽娅攀上柳树去悬挂她用“死人指头”做成的花圈,却失足掉进“鸣咽的河水里……去迎接她埋入河泥中的死”。(4.5.175—183)
在舞台横尸的结局到来之前,这些森然悲怆的死亡意象为哈姆雷特在墓地的再次出场作了极好的铺垫。第五幕始,哈姆雷特在好友霍拉旭的陪同下走入墓地。此时的哈姆雷特不再显得那么怨己尤人,躁动不安。他已经超越存在与生命,显示出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他现在可以与死亡进行平等的讨论了。在墓地里,哈姆雷特手捧一个骷髅头骨,十分轻松地对它说道:“这也许是一个政客的头颅,”他是“第一个弑兄的该隐的腭骨”。(5.1.78,76—77)对于观众,这话可能会引起对克劳狄奥的联想。但哈姆雷特已经超越了这个层次:克劳狄奥的死与任何人的死没有两样。他接着与骷髅对话,去考虑死亡观念的另一种现实表现:“这个头骨也许是一个朝臣”,他“爱管闲事,见风使舵”。(5.1.82)这里闪现着已经在墓穴中腐烂的波洛涅斯的影子,或许也是在泥土中腐烂的罗森格兰茨和吉尔登斯吞的形象。但哈姆雷特对此已毫不在意。善于思考的人的“灵魂是超脱的,对此无以挂牵”。(3.22.242)他甚至以死神自居,召唤着他的“蛆虫夫人”(5.1.88),细细琢磨着从生命的诞生,到世间的五情六欲、三教九流的兴衰,直到“这个填满了臭土”“没有下颚的”白骨骷髅。(5.1.88,108 )所有这些没遮拦的死亡意象在历史伟人的死亡意念中达到了极致的象征意义。哈姆雷特的“想象力追寻着亚历山大大帝高贵的骨灰,直到发现这些骨灰不过就是塞在酒桶上的泥土”。(5.1. 202 —203)霍拉旭认为“这样想未必太想入非非了”。(5.1.206)但哈姆雷特不会接受这样现实的坦诚。他更愿意直趋理性思维的逻辑极点,以此袒露人类事业的荒诞与生命的虚无:
亚历山大死了,亚历山大埋葬了,亚历山大化作尘土;人们把尘土作成烂泥,亚历山大所变成的烂泥,不会被人家拿来塞在酒桶上呢?
(5.1.208—212)
在死亡的逻辑与规律面前,一切都显得平等和无意义。可是克劳狄奥骨子里可不这样想。意识形态的召抚既然不成,借刀杀人的伎俩又落空,此时须采取更为实际稳妥的政治手段。国王的行动是迅速的。他利用莱昂提斯悲愤的心情和为父报仇的急切心理,设计让他用带毒的开口剑在比武会上刺杀哈姆雷特。死神迫近,哈姆雷特已经准备好了。死亡之于哈姆雷特是存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此时他几乎是不加思索地接受了比剑会的邀请。霍拉旭预感此行凶多吉少,劝哈姆雷特三思而行。但在哈姆雷特的意识中已经不存在任何现实的目的,只有对存在状态、绝对意志的玄思冥想:
一只麻雀的生死,都是冥冥中注定的。注定在今天,就不会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今天;逃过了今天,明天还是躲不了,随时准备着就是了。
(5.2.119—122)
哈姆雷特在这里坚持,人类的空间存在不可能用时间来度量。换言之,人的自由意志可以趋于无限,这本身就是存在的目的。在此悖论的前提下,死的恐惧烟消云散,生命最好的选择,用哈姆雷特的话来说就是:“随缘”(Let be.)(5.2.224)。这就是哈姆雷特在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权力的压迫下孤奋忧思,追寻死亡之论划下的句号。
四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作出结论:这是一场早期现代主体拒斥主导政治意识形态召唤和包容的斗争。它显示了觉醒中的主体拥抱理性、迈向启蒙的迫切愿望,显示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宇宙和人类本体的追寻胜过现实政治和伦理价值承诺的思想取向。在这场明争暗斗中,哈姆雷特不是输家,因为他没有被以克劳狄奥为代表的国家权力政治伪意识所软化和包容;但是他也不是赢家,因为他在现实中没有成功地扮演既定伦理道德规定的实际社会角色。 事实上, 在这场主体塑构(subjectification)的过程中,哈姆雷特沉迷于对现实的玄想和话语建构,在形而上的理念中追寻着生命的意义。用死亡的绝对理念代替人类社会的各种价值观念。用G.W.奈特的话来说,“哈姆雷特是一个超人,[他]用死亡的幻影和犬儒主义的否定精神在意识中永不待歇地劳作。”(注:G.W.奈特:《烈火的车轮》,第42页。)哈姆雷特已经被智能意识形态所吞没,被简约成为一个无主体(subjectless)的声音。 当然,这声音终会沉默。哈姆雷特终被自己的智能意识和死亡的话语所消耗殆尽。当他在比剑中被莱昂提斯的剑刺中,并知道那剑带有剧毒时,他终于意识到,“铁面的死神巡捕”已经对他的死亡话语听得不耐烦,开始行使他“严酷的职责”。(5.2.336—337)哈姆雷特的智能意识仍在活跃,临终的话语仍是静谧的玄思,那就是,随着肉体的消灭,智能意识话语的生产也终将止于尽头——“此外仅余沉默而已。”[死](5.2.358)本文至此,沉默如斯。
收稿日期:1999—09—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