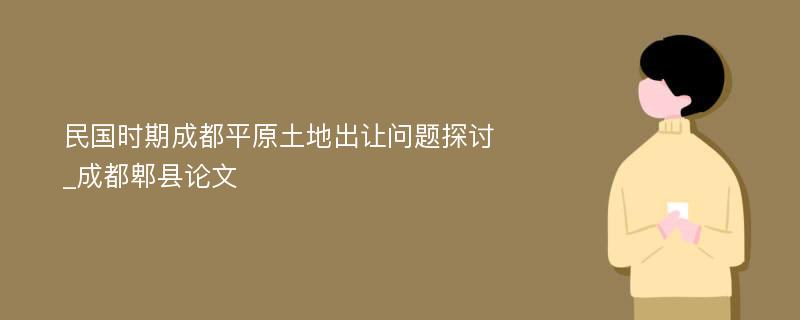
民国时期成都平原土地转租问题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都平原论文,民国时期论文,土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95.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6)03-0085-11
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的租佃制度非常发达,土地十分集中,促成了耕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进一步分离,促成了自耕农的减少和佃农数目的增加,其重要原因是旧地主的没落,新地主的兴起。新地主多数是不在地主,他们对田地的经营管理大多需要代理人来进行,或是将土地租给一些人,这些人又将土地细分后转租给其他人耕种,所以在成都平原的土地经营中,土地转租之风十分盛行,尽管民国法律明令禁止,但在广大的乡间,国家法律的约束力十分有限,“转佃”作为租佃制度中的一种习惯,仍然依照自己的规范存在。①
一、土地转租的主要形式
土地转租又称为转佃,就是将自己从田主手里租佃的土地,整体或部分转租给他人。成都平原的土地转租,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分佃,即第一承租人向田主承租土地后,再出佃一部分给其他人耕种。这种转佃形式大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原承佃人负责纳租,新佃户不与田主发生关系;另一种是新佃户必须与田主直接重定契约,将稻田耕种权顶替。②
(二)包佃,承佃的人并非佃户,而是将土地包租下来,再转租给佃户耕种,“是时承佃之人并非佃户,事实上仅为居中包揽性质。此制多用之于教育或其他团体拥有田亩甚多,而不欲自行招佃者。”③包佃制的产生,大多是因为居城大地主不愿直接经营管理土地,将其土地租与一个或少数承租者,每年收取一定租金,此后地主对其土地是否转佃,并不过问。这些承租者,并不直接经营土地,再以高额地租转租给许多佃户,从中赚取利润。在私人地主之外,各地公产(寺庙、祠堂、学校等公田)也乐于采用这种包佃制。④各县公学产租佃,往往租佃关系成立在百年以前(形同永佃),佃户传授数代,自然有分割,久而久之,分佃到无法稽考的程度。
(三)大佃制,这是成都平原特有的一种转佃形式,在中国其他地方很少见到。
所谓“大佃制”,又称“大押佃”,以高出一般押租数倍的押租租佃田地,佃户不必缴纳租谷,这实际上相当于土地的典当。“成都平原通行的押租额是每亩十四元,这可称为按押制度的常态,遏此如果押租额高至七十元,则按四扣计息,佃户已不要缴纳租谷。此时租佃关系,即所谓‘大佃’之制。”⑤这种大佃佃户若是以取谷利为目的,则所佃的田地,一定不是自己耕作,而是转佃给他人。
之所以产生“大佃”,主要是中小地主在急需用钱又无法借贷的情况下,只有出卖土地,可是祖宗留下的产业,不忍丢弃,而且加上“卖田不卖粮”的心理,⑥以为出售田产有损体面,于是在佃农身上想办法,加押或加租。习惯上,成都平原加押是地主的权利,佃户依例不得拒绝。即使押扣低于普通利率,佃农也有承受的义务。如此情形,“大佃”即成为一种变相的典当行为。所谓押租便是按市场利率计算的典当本金。所以“大佃”在实质上便相当于一种带强制性的典当行为。
“大押佃”,也是转移土地的一种方式,为兼并土地逃避租税开辟了一扇方便之门。民国时四川田地买卖典当均需纳税,官契一纸工本费收1元5角(典契5角),契税照田价每百元正附合计15、16元。有些人想要避免税负,于是以“大押佃”代替买典,这里有一道四川省府的训令,可作证明:
查民间买典不动产,投税印契原所以保障产权,承巷法益。乃一般不明厉害,往往忽视法律保障,不求有效凭证,卖典产业,或则匿不投税或则短报业价或则明典暗卖或则变更为大佃大押及抵借顶付等名称,以图避重就轻短漏税款,弊窦丛生,不一而足。⑦
用“大佃”来代替田地典卖,在这样的租佃关系中,所谓“佃户”只是徒有其名,实是按利收租,取地主而代之了。地主通过收取高出一般押租数倍的押租金,获得了自己急需的资金,而佃农通过成都平原特有的押扣制度计算⑧,使每年交付给地主的地租减少,有的佃户再将所佃田地转佃出去,成为按利收租的二地主。即使不转佃出去,通过一次性付押,来减轻每年的田租负担,尽管仍然存在风险,但从理论上讲,并非不利于佃农的生产。
例如郫县佃农陈尚有1945年向同村中农赵某的田地8亩,交了40石米作为押租,与主家协议,每年扣除8亩田的地租作为押租利息,这样佃户就不用每年向业主缴纳任何地租,但土地的所有权仍属原来的业主,业主若要收回水田,必须归还佃户的40石押租米,这就是大押佃的实例,相当于土地典押。下表反映了大押佃的一些情况。
表1 “大押佃”的几个实例
佃户成分 住址业主 成分
租佃田亩 租佃年月 押租 扣田数地租
姓名 姓名(亩)
陈尚有 中农
郫县赵元乡赵光和
中农8.00
1945 米40石 8.00
扣尽无租
方广树 贫农同上 卫主培
中农2.8
光绪年间
银元30元 2.8扣尽无租
杨长顺 贫农花园乡
杨华兴
中农1.501949 米4.30石 扣尽 无租
陈茂和 贫农 花园乡第六保
施少康
富农4.001947 米10.00 扣尽 无租
李绍清 赤贫郫县镇子 李绍良
赤贫0.80
1949.8 米2石
扣尽 无租
李绍清 赤贫郫县镇子 李绪华
赤贫0.80
1949.8米2.3石 扣尽 无租
彭雨清 贫农华阳涌泉 何利生
地主5.701945 米6石
当尽 无租
魏银山 贫农华阳涌泉 何利生
地主2.00
1949.10米6石
扣尽 无租
陈子仪 中农郫县苏坡 余敬波
地主1.00
1939.10
银元70.00元 扣尽 无租
刘洪顺 贫农郫县和盛 杜子刚
地主1.001950 米2.2石 扣尽 无租
王元华 贫农郫县寿安 杨怀成
地主7.401943 米19石 扣尽 无租
资料来源:四川省档案馆,全宗号建西003,案卷号17,《成都华阳七县农会驻蓉联合办事处》,《中共温江县委汇集的全县有关业主的出租田地租押调查登记统计表》(1950年11月)。
上表的佃户就是“大押佃”的情况,佃户交给地主的押租多,通过押扣扣除田租,不交田租。上表显示佃农通过大押佃佃取的耕地面积比较小,最多的才8亩,最少的只有0.8亩。
“大佃”也是高利贷者“吃谷利”的一种花样。举例来说,大佃户向田主佃田10亩,交押租300两,额纳租谷18石。他佃田并不是自己来耕种,而是转租给第二佃户。第二佃户交押租百两,扣押息外每年向大佃户纳租14石。大佃把6石租谷交给地主,留下的8石租谷即成为200两押银的利息,这就是所谓“吃谷利”⑨。再进一步,高利贷者索性借大佃来兼并土地,经过“吃谷利”而爬上地主的地位。他们以每亩70元的押租,向业主佃取田地,再转佃给耕者,收取的租谷作为利息。这与典当没什么区别,每亩70元的押金即为典金。“大佃”逐渐变成了高利贷和典当的一种形式。
田地大佃以后,付税还粮均由承佃者负责。假使押租不够标准数目,而田主还收一部分田租时,就在佃约中规定“主家收租之田由主家完纳,佃客扣除之田,由佃客负担。”⑩主家与佃户各自承担自己的赋税义务。
“大佃”制在成都平原颇为流行,土地典当逐渐有被其代替的趋势。典契税率高,是促成这种趋势的一个原因。地价飞涨使“大佃”的押租额跟着增加,抗战前1亩大押至高70元,1937年已涨到84元,而1938年“据说有增加到一百四十元(一百两)的可能”。(11)这对于高利贷土地兼并者固然无甚关系。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大押增加表示押扣减少,在佃农经营收益不能增加的情况下,这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大押佃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逃避契税,行政当局也知道民间存在大押佃的情况,所以加强对大押佃的控制,1934年四川陆军第二十一军就公布了《典契税暂行条例》,第一条就规定大押佃必须纳税:“凡在本军戍区典当不动产者依本条例之规定完纳典契税。民间变名大押佃,其佃户收入在原产业全部收益三分之二以上者,应依典契税规定完纳典税。”(12)巴县征收局对大押佃如何征税作了具体规定:“巴县四乡民,最近对于房产、田产典押特多,但押款轻重不等,粮款之完纳,时有不匀,巴县征收局徇人民之请求,特加重规划,凡以大押佃而享有收益者,依其所佃产业收益之全部计算,如原业主全无收益或收益不及1/10者,各该业应纳粮款及一切派垫,由佃户负担,原业主收益在1/10以上至4/10者,其粮款及一切派垫,由原主与佃户平均负担。”(13)这些规定都要求对通过大押佃而重新分配的利益进行征税,分别规定了利益与税收的比例,二十一军规定佃户收入在原产业全部收益的2/3以上的,应交纳典税,巴县规定以业主收益的1/10为限,业主全无收益或收入不及1/10的,各种粮款和摊派,由佃户完纳,若业主的收益在1/10以上到4/10的,粮款和摊派,由二者共同承担。当局希望通过这种利益与义务平分的办法,将大押佃纳入其控制之下,保证当局的税收利益。
以上三种情形无论是那一种,所转佃的人(第一佃户)其目的都是在田主和实际耕作者的中间分一些利益,即使他自己耕作一点,也仍然有取利的方法。通常有如下几种:
(一)赚押扣成数。如某甲向业主佃田,交押金若干,议定四扣取息。甲将所佃田地转佃于丙,议定押扣为二扣五,其他条件照旧。此时甲就可以赚取一扣五的押息。如原来议定每亩押14元,则甲转佃10亩可以不劳而获谷利1.5石。如华阳县仁义乡佃户刘自名,从地主廖静坤处租佃了16.8亩田,交给地主的押租为银85两,每年扣回谷利5.1石,为六扣,而刘自名又将其中的2.8亩田分佃给同村的易尹氏耕种,收押租米3石,每年扣回谷利1.5石,小佃户易尹氏只享受了五扣的押租利息,其中一扣为转佃人获得,“原系六扣,转租人剥削一扣。”(14)
(二)取得无押耕地。某甲佃田20亩,押租金100两,于是分出10亩或15亩,分佃给他人,仍然取押租金100两,结果甲自己所种的10亩或5亩田,成为没有押租的耕地了。表2中李石上就是通过分佃3亩田出去,收取22元押金,每年还收取8.36石租米,使自己从田主处佃来的田地成本降低。表中还有几家类似的例子。
(三)加押和加租。转佃也需要订立契约,内容和原来的租佃契约差不多,仅租额或押租有变更而已。
表2 成都平原部分佃农转佃情况
佃农姓名成分 住址 租佃年月租佃田亩(亩)转佃情况
鄢少青 佃富农 郫县镇子乡1928 39.00转佃与罗义威1.6亩,傅海山
2.3亩,刘井元3.6亩。
文浩贵 贫农郫县镇子乡1939 21.00转佃与文刘氏2.3亩,文杰3.9亩,
文国华0.7亩。
郭黄氏 中农 同上1932 12.70拨出1.9亩与谢登云,2.3亩与
胡邓氏。
李子超 佃富农同上1921 24.80拨出7.5亩与邓青云。
庄光裕 佃富农 郫县清平乡1917 46.22转佃11亩与何三友,另外转佃
三家共7.3亩。
李石上 贫农成都县苏坡乡 1935 10.31同年分佃出3亩,租米8.36斗,
押金22元。
陈方贫农成都县苏坡乡 1948.8
25.14同年转佃2.5亩与温绍章,押米
2石。
黄富留 中农 同上
同治7年3月16.801940年拨田5.8亩与黄绍清,取
有押银14元。
萧治云 贫农郫县清平乡 193114.30自耕10.95亩,余分与何玉廷0.8
亩,萧子影1.25亩,萧明清1.3亩。
资料来源:四川省档案馆,全宗号建西003,案卷号17,《成都华阳七县农会驻蓉联合办事处》,《中共温江县委汇集的全县有关业主的出租田地租押调查登记统计表》(1950年11月)。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些转佃者的生活境遇各不相同,根据土改时的成分划分,有佃富农、中农,也有贫农,从租佃时间看,有晚清租佃的,也有1947年才租的,但他们都是分佃出去,而非包佃,有的收取了押租,有的没有收押租。他们租佃的田地都在10亩以上,分佃出去的小佃户多为自己的同乡,正如郭汉鸣、孟光宇所总结的“大多数是附近的佃农在耕种面积上的互相调剂,依照原承租额及押租额量田划分。”(15)转佃成为佃农互助的一种方式。
同时,转佃也是佃农对付地主的一种手段,据卜凯、乔启明的调查,在江南等地,佃农对于地主最大的舞弊行为,就是转佃,而不让地主知晓。“佃户将租田转让与他佃户耕种,按理第二佃户,应赴租栈出立承揽,但有时并不如此,而仍用原佃户名义,其理如下:(甲)佃户恐租栈再要加租;(乙)佃户可省承揽费;(丙)第二佃户再可转让于第三佃户,而仍用第一佃户的名义。因此,则第二佃户,可脱离关系而得渔利”,“有时佃户因加租关系,私将原种田亩假名让与失信用之佃户,实则仍为自己耕种,以图欺瞒。有时第二佃户仍假让于第三佃户,转之再转,以致地主不得收好租。”(16)
在成都平原,由于人多地少,人地争耕,地主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往往有加租、退佃的自由,而佃农讨价还价的机会较小。所以他们想出了许多对付地主(特别是不在地主)的办法,如转佃,缴纳劣质租谷,在谷物中掺杂沙粒等等。但佃农的这些行为一旦被发现,就会酿成租佃纠纷。
二、转佃引起的租佃纠纷
尽管转佃现象在成都平原比较盛行,但转佃却是法律和租田规则中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从《金堂县志》所载道光二十九年“公议义仓谷石规条”十二则和《崇庆县志》所载的社田条规十项中可以看出当时关于租佃制的一些规定:关于租田手续方面:租田需要订立佃约,佃约载明押租、租石数目,并得有担保人。担保人的义务也规定明白,而且还禁止私田私自转佃加押等:“一议佃户承佃,必自请殷实绅粮,具保认佃,注明其佃田若干?押价铜钱若干?每年捐纳租谷若干?如有拖欠惟保人是问。倘有私佃转押,亦为保人是究。”(17)租约规定不得转佃,但当时转佃以从中取利已通行,为此义仓条规更载明可以撤佃:“一议义仓佃户不得私抽所佃田亩重取押租分佃别人,如有此等情弊,一经发觉,定取田另佃。”(18)以上尽管是义仓、社田的租佃条规,但可以看出转佃是在清代以来就是明令禁止的,民国的《土地法》第171条也明确规定:“承租人纵经出租人承诺,仍不得将耕地全部或一部转租于他人。”(19)1948年四川推行二五减租和农地减租时,颁布的《四川农地减租办法》中也明确规定:“承租人不得将耕地转租他人耕种,如有此项转租情事,应即由出租人依法予以撤佃,并以现耕作人作为承租人。”(20)一些佃约也有“不得另招小佃”,或其他限制转佃的条款。根据郭汉鸣和孟光宇的调查,成都平原租约中明令禁止转佃或另招小佃的租约占27%,川西南区为17%,川西北区为10%,川东区为4%,全川平均占所收集租约的13%。(21)尽管27%的比例与其他事项相比并不高,但与其他地区相比成都平原是最高的,可见成都平原在租约上对于转佃的要求比其他地区更严格一些。一些租约规定“田土房屋,不得私招另佃”、“不得转顶,添招小佃立即起迁。”(22)
尽管法律和规则不允许,但是民间转佃还是十分盛行。(23)因而也造成了不少租佃纠纷。政府在处理这些纠纷时,往往是以收到政府征收的赋税为目的,有时默认民间的转佃行为,有时又会严厉苛责,不予保护。笔者在双流县和崇州市档案馆查阅民国政府档案时发现不少由于租佃关系而引起的主佃冲突,其中有不少是因为转佃而造成的。以下几案且作典型:
案例一 转佃引起的欠税责任转移:地主——佃户——小佃户。
根据民国土地法,国家征收的土地税赋,都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而不是土地的耕作者。但一些地主为了省事,往往采取减租,请佃农代交的方式,让佃农直接向政府有关机构交纳地主应缴纳的赋税。
1947年,双流县升平乡四保田家桥田主刘庆和欠田赋被询,刘庆和称曾将租折赋请佃农艾雨之代纳,但艾雨之夫妇却没能按期纳粮,欠田赋和租谷共计10石(双市石)而被双流县田赋征辑处拘押,艾雨之夫妇于是状告小佃户冉吉安欠租,而引出了复杂的租佃关系。(24)
1948年3月,由于欠租赋,艾雨之被双流县田赋粮食管理处、双流县税征稽查处拘押,被保释,承诺近日完粮,未果。5月,其妻艾赵氏亦被拘,通过对艾赵氏的讯问笔录,我们知道艾雨之从刘庆和那里租来50亩田,转佃给冉吉安13亩,李那钦7亩,黄子钦3亩,其余27亩由艾雨之夫妇耕种,每年向田主交20多石租米,但1947年只交了10石,还欠10多石。原因是小佃户欠租,李那钦欠5石多米,黄子钦欠几斗,但这两家太穷了,拿不出来。自己家的生活也困难,每天只能磨炒面吃,没有米帮地主上粮。
从赵氏的回答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租佃关系层次:
刘庆和(地主)
艾雨之(大佃农)
冉吉安 李那钦 黄子钦(小佃农)
艾雨之将欠租原因归结到小佃户冉吉安身上,说小佃农冉吉安欠他租米4.9石(古量),多次催促,仍未缴纳,艾雨之说如果自己收到这几石租米,就可以帮地主上交欠粮10.9石,所以希望县府传押冉吉安,逼其缴租。双流县政府于是扣押了冉吉安,冉吉安上书县府,说自己家在民国前就在艾家佃到水田十多亩,由于生活高涨,1947年自己欠主家租米1.8石,冉吉安要求保释,承诺10日内将欠租交给主家。
艾雨之得知冉吉安被保释,立即上书双流县政府,要求县政府不要同意保释冉吉安,以免冉氏再次拖延不纳,影响完粮纳税。
双流县田赋粮食管理处、双流县税征稽查处仍将冉吉安保释,并限期完纳欠粮。但1948年8月26日,艾雨之又向县府呈报,叙述冉吉安拘不交付欠租,还扬言不但不付欠租,也不纳欠粮,还偷砍艾家的林园竹木,要求县府乘黄谷收获之际,催促冉氏纳粮纳租,害怕收获之后,冉氏再拖延,欠租欠粮无法收回。
9月7日,双流县政府饬令升平乡公所处理此事:“升平乡公所:为再令饬该所转饬该乡第四保保长迅将冉吉安欠付艾雨之租米如数扣押,并具报告。”(25)最后由该保保长扣管小佃冉吉安的稻谷,使长达半年的欠租欠税案得以解决。
此案透出以下信息:其一,在这场租佃纠纷中,作为地主、应履行纳税义务的刘庆和似乎置之事外,纠纷在转佃的双方进行;其二,艾雨之作为大佃农,已扮演二地主的角色,其与地主刘庆和和小佃农冉吉安的租佃关系已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26);其三,县政府为了追缴欠粮,不惜动用一切手段,从拘押人质到扣押谷物,所有的目的就是为政府征粮,在与农民的关系上,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者。
案例二 佃户出事,殃及田主。
由于转佃存在权利与义务的再分配,而且转佃中小佃农仅与大佃农存在租佃关系,与土地的真正主人没有契约关系,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受到威胁,所以一些田主不愿意佃农将土地转佃出去,因为一旦大佃农有什么天灾人祸,田主的利益很难保证。下面这个案例就反映出这样的问题。
田主周世清佃出14亩水田给梁子清,梁子清又分佃与他人耕种,小佃户未与田主签约,1948年,梁子清的兄弟梁正富打死了当地驻军的一个士兵后逃跑了,士兵的长官向保长要人,保长交不出,就把士兵的尸体抬到梁家门口,保长梁天籁知道梁正富逃跑在外,不可能回来抵命,于是就命人割了梁正富哥哥梁子清8亩田的稻谷,交给长官平息事端,这就影响了梁子清缴租,使田主的利益受到影响,而且梁子清分佃出去的田地又没有与田主订立租约,田主也无法向他们去收租,所以田主完粮纳税成为问题(27)。
此案由人祸引起,由于没有与小佃签约,十多亩土地颗粒无收,该地主不得不向县府申请免赋。租佃制作为一种契约制度,使租佃双方都受到约束,也承担一定的风险,佃农如此,田主亦然。
案例三 保长强行分佃不成,以公报私。
成都平原盛行的转佃现象,并非一种固定的模式,从生活水平和状况而言,并非一定是田主强于佃农,大佃农强于小佃农。有时候,还会是相反的情况。比如下面一个案例,就是村里的保长强行分租一个佃农的田产未果,而公报私仇的事情。
崇庆县元通场万寿寺附近的30亩水田,原来由保长彭泽君承佃,后来撤佃,由文焕章承佃。但彭泽君心有不甘,向文焕章提出分佃的要求,遭到文焕章拒绝,彭泽君就强行耕种了一些田地。由于彭泽君是保长,负责在乡里拉壮丁,1942年9月9日,在文焕章刚刚收获谷物的时候,拉文焕章做壮丁,文氏只有用谷物换钱,用钱抵补,免了壮丁,但谷物收而不获,无法缴纳田租和粮额。而文氏的两位兄弟已于1940年9月参军参加抗战。所以文焕章向县府呈文,希望核定彭泽君强迫分佃的田地,使田租和粮额能名副其实。(28)
因不能分佃,而拉壮丁,用手中的权利报复不愿分租的佃农,这个保长的行为与下个案例中的土豪一样,都是依仗权势,强租强佃,强行获得土地的使用权,以谋取更大的利益。
案例四 包办佃权:转佃的又一种形式。
1942年,崇庆县苟家乡白云庵附近的几户佃农,多年来一直租佃庙里的田地耕种,但1939年村里的士绅吴梓愚将山地全部承租下来,过去直接向寺庙佃地的农民,就成了吴梓愚的小佃户,吴梓愚不仅妄加租押,用大斗强行收租,还在山中开设纸厂,令佃农作无偿劳动,所以佃户们向县府申请解除吴氏的包办租佃关系,直接与县府签约承佃,否则宁愿退押退佃,另谋生计。(29)
上面这种转佃形式与前面的又不一样,前面所提的转佃行为是由大佃农先承佃下来,再招小佃户,而这个案例中,佃农原先已与田主有租佃关系,大佃农是依仗权势横插一杠,将原来的田主与佃户分割开来,自己成为二者之间的代理人,从而谋取利益,这种做法损害了原有佃户的利益,所以受到佃户的反对。
案例五 佃户劳动力弱,分佃他人,政府不保护转佃利益。
还有一种转佃行为是佃户家里劳动力弱,无法耕种过多田地,所以分佃一部分出去由别人耕种,目的是既减轻劳动负担,又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收入。
崇庆县佃户高蔡氏,祖辈佃种汉原书院的水田13亩,每年缴纳租谷15.4石,河埂坟垣杂地不缴租。(30)1935年全国财政统一,清理公产,丈量田地,坟垣基地收租6斗,这样每年共缴租16石,每年都交清,从未欠租。1940年,县经收员王耀南重新丈量土地,把河边的河埂和坟垣基地一律算在纳租的田地之内,共15.86亩,共该缴纳租谷22.05石。后来,高蔡氏的丈夫高洪炳作为义勇壮丁,出征抗战,孩子幼小,缺乏劳动力,于是由其丈夫的兄弟代理分佃2亩水田给杨忠树耕种,每年收租2.4石,由王耀南经收,但王与杨一起作弊,1941年,杨忠树欠租谷1.3石不收,王耀南向高蔡氏追讨。并且高吕氏强种了三分前坝基地,应该缴租9斗,未交给高蔡氏。1941年,高蔡氏已交清田租,但王耀南等人仍告高蔡氏欠租,将高蔡氏的夫兄高洪顺拘押在案,要求高家河埂坟垣杂地与良田一律算租,高蔡氏不服,要求将转佃的小佃户杨忠树和强行耕种的高吕氏传唤到庭,追还欠租。(31)
县财委会批示:“呈悉。授称田地混淆情形,当清丈时该你砌词种塞,应不照准。至于分租转佃早经严禁,该氏违令分租,殊有未合,所有欠租自应仍由该氏负责缴清,仰即遵照此复。”(32)县财委会的态度一是坚持清丈田地时的规定,二是绝不保护转佃利益,因为政府是明令禁止转佃的,所以一切后果由该佃户承担。
上面这个案例很复杂,它涉及的问题很多,首先,是土地丈量和认定的问题,民国后期为了增加土地税收,曾多次丈量土地,本来河埂坟地不应缴纳租税,但在该案中,这些由佃农自己开垦出来的荒地也被纳入公产收租;其次,该佃户是一个军属,孤儿寡母缺劳动力,分佃一部分给杨忠树耕种,但中间人——经收员从中舞弊,使军属利益不仅未能保证,反而生出欠租的问题。再次,县政府在处理该案时,不仅没有保护转佃行为,反而严厉斥责,责令该妇女完粮纳租。
以上几个案例,只是大量租佃纠纷的很小一部分,它们分别反映出因为转佃行为而造成的种种问题:首先,转佃使田主、大佃户、小佃户的利益都不能得到保障;其次,转佃给政府的征税带来麻烦,所以政府反对民间的转佃行为;第三,转佃还可能激化各种社会矛盾,挑战已有的社会秩序。所以政府和法律均不保护转佃行为及其利益。
三、转佃盛行的原因
是什么原因使转佃之风盛行不已?笔者根据相关资料,对此略做分析:
首先,人多地少,生态环境压力增大。成都平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之一。见下表。
表3 成都平原各县土地面积及人口密度统计表
县别市亩市方里 公方里占全省总面积之百分比
每方公里之人口数
总数 11,898,120 31,728.32
7,932.08
1.91
温江 375,810 1,002.16250.540.06
702.47
成都 368,535 982.76 245.690.06
532.77
华阳 1,436,040
3,829.44 957.360.23
400.41
灌县 2,463,435
6,569.161,642.29
0.40
179.41
新津 473,205 1,261.88315.470.08
512.88
崇庆 1,674,375
4,465.001,116.25
0.27
373.34
新都 365,310 974.16 243.540.05
615.62
郫县 410,010 1,093.36273.340.07
623.80
双流 431,475 1,150.60287.650.07
473.38
彭县 3,394,575
9,052.202,203.05
0.54
157.70
新繁 237,825 634.20 158.550.04
644.15
崇宁 267,525 713.40 178.350.04
501.80
资料来源:据《四川省各县土地面积及人口密度统计表》整理而成,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1月版。
上表中,除灌县、彭县两县人口密度在200人/每平方公里以下,其余各县均在300人/每平方公里以上,最密集的温江竟达到700人/每平方公里以上,而当时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英格兰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才262人。(33)成都平原如此高的人口密度,给该地区的土地资源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为了养活大量的人口,成都平原的土地利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租佃制度就是为适应人地关系紧张的状况而产生的,通过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单位土地的劳动成果在更大的范围内被人们所分享,以养活更多的人口。而转佃,又进一步将土地使用权分割,增加更多需要养活的人口。
如果我们这里暂时抛开经济效益和收入多少这些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暂不考虑生活水平,只是单纯从人口养活出发,设想一下,如果一个田主拥有50亩土地,他可以选择以下几种经营方式:一、自己耕种,或雇人耕种;二、自己耕种一部分,佃出一部分;三、全部佃出。第三种情况又可分为两种,一是分别租佃给几个佃户,分别向田主交租,一是统一出租给一个佃户,由这个佃户负责向田主交租。哪一种经营方式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呢?如果田主选择自己耕种(前提是有足够的劳动力,假定田主为5口之家,3个全劳动力),那么这50亩土地,除了上缴给国家的赋税外,只养活了这一家5口,若雇工人耕种,50亩土地两个工人就够了,(34)那么除主家5口外,加上2口,即7口;若选择租出,据陈太先的估计,在成都平原,“农家普通有田十亩自耕自食,或能佃耕二十亩以上的田地(指上等水田),则在生活上都可以过得去,可称为中等富力的农家。”(35)田主可留下10亩自耕,再将其余40亩分别租佃给两家佃户,这样这50亩水田就可养活3家人了,若按每家5口计算,就是15个人;若两家佃户再分别将手中的水田转佃10亩与他人,那这50亩水田就可养活5家人,仍按5口计,就是25人了。有学者统计,在成都平原,一个佃户若能佃到10亩田,就可维持起码的生计。(36)因此,这样的假设并不一定不成立。如果这一假设成立的话,成都平原的租佃制以及转佃行为盛行的原因就不难寻找,那就是用有限的土地养活更多的人口。虽然,不论是地主还是佃农,他们的选择和行为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但在客观上,租佃制度做到了这一点。过去的研究仅仅从劳动者(耕作者)应得的劳动报酬的角度来看待租佃制度,认为它是地主剥削农民的一种生产关系,而忽略了它在人地关系的矛盾中、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通过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能够养活更多人口的事实。当然,这也许是以降低一些人的生活水平为代价的。
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地适应自然,也让自然适应自己的过程中成长,任何一种制度都为适应当时当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而产生,否则它就不可能存在并发展起来。成都平原的租佃制度能在这一地区盛行一千多年,是这一地区生态环境与人地关系状况的反映。因而从生态和经济角度看,租佃制度以及转佃行为有其合理性。
其次,在转佃的问题上,国家法律与民间习惯,存在冲突,也互为补充。习惯是源自老百姓处理实际问题时的日常行为和态度,法律则是根据为国家利益和公共秩序而制定的行为规范,二者有很多矛盾与冲突。对于一些国家不愿认可的行为,官方法律几乎没有相关的条文进行规范,需要通过民间习惯来解决,它们可以为这些行为提供实用的解决办法。租佃制度中的转佃问题,就是国家不愿认可的行为之一。所以很多时候,它是按照民间的习惯来寻找解决办法。民间的调解所依循的原则,更多的不是出于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而是乡土社会日常生活的内在逻辑,是乡民们所了解、熟悉、接受乃至视为当然的知识。事实上,主要是通过宣传和普及等方式自上而下灌输给乡民的国家法律,远未内化为乡民自己的知识,而这些令乡民感觉陌生的新的知识,也未必都是他们生活和解决他们问题的有效指南。农民们之所以尊奉一些长期流行的习惯,首先是因为这些习惯具有根植于社会生活中的合理性,因为他们为社区成员所能带来的好处更多于它们的害处。(37)所以尽管民国的《土地法》不允许土地转佃,但各地民间习惯中自有一些解决转佃纠纷的规则,如简阳的转佃习惯是“佃户有时将租来的田地,转佃于人,只能转佃一部分,但必得业主之同意,方可执行。其转佃人每年应纳之租,只能缴于原佃人,不能直接缴与业主”,而由此产生的纠纷“由中间人或本地保甲解决之,绝莫有闹到官厅的。”(38)
民国时期一些希望保护佃农利益的精英人士,虽然原则上反对转佃,但也并非不能接受转佃的事实,“转佃制度原则上虽应禁止,但是例外的临时转租(如因病临时转租)及租佃团体的转租(如意大利及罗马尼亚的佃租合作社,租人土地之后皆可转租),应予承认,以解决其临时困难,或奖励团结,使自谋条件的改善。”(39)精英对转佃的容忍,也反映在当局的态度中。
各地方政府也知道民间转佃行为并未因法令不允而消失,对于民间的转佃行为,县级政府的态度多是听之任之,(40)不出问题就不过问,出了问题则是以政府的税收利益为前提,为了完粮纳税,什么办法都可以使用。从上面的案例中也可看出,政府在处理因转佃引起的租佃纠纷时,往往以能收到土地税为宗旨,所以有时会斥责转佃行为,有时又会纵容这种行为。双流县对待艾雨之的转佃行为是默认的,而崇庆县对高蔡氏的转佃行为则坚决反对,不予保护,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态度虽然不同,但结果都是一样,一定要收到政府应收的田赋。
再次,转佃也是一种租佃制的一种补充,是一种受利益驱动的经济行为,对此,张五常有非常经典的论述:“如果地主把他的土地分给几个佃农耕种从而可获得更高的地租额的话,他就不会把他所拥有的所有土地出租给一个佃农耕种”,(41)在1950年温江县土地改革的资料中,笔者看到拥有100亩以上田地的地主,很多都分别租给了几个佃户,而不是由一个佃户承租。一位姓王的地主在有280亩水田,他分别租给了14个佃户,最多的租了33.16亩,最少的只租了7.4亩,一般的在12亩与25亩之间。(42)地主通过这样的办法,可以避免大佃农通过转佃从中渔利。佃农也一样,“为使得自耕作的收益最大化,佃农会把他的投入资源分散到许多农场,以使得自农场的边际收入(或边际收益)相等,直到他的投入被耗尽。在这种情况下,佃农所获得的总收入会高于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可能得到的收入,其他佃农将加入竞争的行列。假如每一个相继进入农业的佃农也在几个农场工作,并也使他得自不同农场的边际收入相等。随着佃农人数的增加,每一佃农得自不同农场的边际收入将下降,从而使地主的地租份额上升。只要每一个佃农的总收入高于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可能得到的收入,就会有人不断加入竞争行列。给定佃农边际收益,假定地主在合约中接受任何数量的劳动,那麽佃农之间的竞争便会把在每一农场上的劳动投入推进到最高。由此造成的‘过度耕作’意味着,地租的份额并没有最大化。竞争再度盛行。假定生产要素是同质的,财富最大化意味着,地主将在提供与均衡地租一样高的佃农中选择承佃者,而地主之间的竞争意味着地租率不会比均衡地租更高。”(43)由于佃农的增加,土地竞佃十分激烈,转佃也就成为佃农对付地主、谋求利益的一种手段。通过从地主那里租佃较大规模的土地,然后转租,在土地所有者和实际耕作者之间谋取一定利益,这成为有一定经济条件的大佃农的重要经营手段之一。如温江县佃农周正全,1924年从业主牛泽文处佃到30.30水田,然后转租12.3亩出去,不仅向小佃收取押租银84两,每年还要收谷租米6.8石,另外,他还做一点小买卖,生活过得不错,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富人,所以解放初划分成分时,被划为富裕佃农。(44)
通过上述论证,笔者认为,成都平原的转佃现象是在人地关系紧张的状况下,一种土地利用的模式,通过转佃对租佃制度进行补充,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耕种田地的机会,养活了更多的人口;其次转佃也是一种追求利益的经济行为,转佃者希望通过转佃,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成都平原的转佃与广东等地的包佃现象不同,广东一带转佃的特点是,富商巨绅整块租进土地,本人不耕种或经营这些土地,他们变成了二地主或地产公司,将土地分成数份转租出去,有时直接租给耕种者,但更多的是租给一批三地主。(45)这种包佃制更像农业垦殖公司,能组织较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而成都平原的土地被切割得十分零碎,下面是成华两县耕地分配百分比表。
表4 成都、华阳两县耕地分配百分比较表
类别 亩 十亩 十亩至 二十亩至 三十亩至 四十亩至 五十亩至 六十亩
以下 十九亩 二十九亩 三十九亩 四十九亩 五十九亩 以上
农家占地各级百分比45 22
1610 322
地权自田主13 62
156 211
分配半田主19 45
164 522
百分率 佃农 69 1093 213
资料来源:康捷生:《成都华阳地籍整理之研究》,1938年,(台湾)萧铮主编《中国地政研究所丛刊》,《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12月版,第15294页。
由此表可看出,大多数农户的农场规模均在30亩以下,其中大多数佃农在10亩以下。分割太细,使农民的农业经营不合经济原则,土地愈碎割农民愈贫困,很难进行较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而转佃行为,使原本碎割的土地更加碎割,很难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同时,由于转佃造成的各种纠纷和冲突,也是农村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所以尽管盛行不衰的转佃行为,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归根结底,它还是中国“糊口农业”的一种表现形式。
结论
我们讨论了成都平原佃农土地的转租的几种形式、转佃带来的租佃纠纷和转佃之风盛行的原因,通过分析,我们知道土地的转租、转佃,由于牵涉田主、大佃农、小佃农及国家税收等多方面的利益,历来都被政府法律和民间一些契约所禁止,但在现实中法律所起的作用似乎并不大,转佃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尽管各种因转佃引起的租佃纠纷层出不穷,但转佃行为仍然有其存在的理由。首先,人口压力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是租佃制和转佃现象存在的重要原因;其次,国家法律与民间习惯存在冲突与补充,转佃是国家不愿认可的行为,但民间的习惯却为解决转佃问题提供实际的办法,由于种种自然、人文和历史的原因,民国时期国家权利对农村乡土社会的控制并不紧密,靠宣传和普及等方式自上而下灌输给农民的国家法律,并未内化为他们自己的知识,成为他们解决问题的行为指南;另外,地主和佃农双方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而选择经营模式和规模,是一种经济行为,转佃也符合某种经济需求,同时也是民间互助的一种方式。
注释:
①多年来,人们将租佃制度作为一种封建剥削制度而进行批判,土地的转租也就成为大地主和富裕农民剥削佃农的一种手段,近年来,学术界对租佃制度的研究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参见李金铮、邹晓升:《二十年来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新探索》,《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2期。
②分佃这种转租形式在其他地方也存在,在江浙一带,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押顶”,即佃户对他人负债,用耕种权作抵押,订立耕种年限押据,以耕种利益代替利息。到期满时,仍然要还清原来的欠款,然后将佃权收回。这样做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佃农耕种所得的利益,除了能补偿其劳动费用外,还存在与借款利息相当的余额。另一种叫“杜顶”,即将耕种权永远卖给他佃。浙江佃户大都有转佃他人的权利,田主不能干涉。见刘大均:《我国佃农经济状况》,上海太平洋书店1929年9月版,第99-111页。
③刘大均:《我国佃农经济状况》,第16页。
④包佃制在全国各地都存在,其中广东的包佃制比较有特色。广东的公田多,其入息动辄千万,如中山市第八区信义庙公田田租达数百万元,东莞县明伦堂田租亦达数十万元。由于这些田地租额巨大,一般农民佃户很难被信任,于是一些富商就以低租租进,再以高租转租给农民,转手间,获利巨大。例如东莞明伦堂,田产极多,所有田地均租给大规模的包佃人,其中最有名的周殿邦,就是一个大包头,他是一个买办,经营银行及其他企业,他以包租的田地,分租给小包头,小包头再转租给佃农。还有一些集资组成的公司,专门负责包租业务。瓦林·伊尧克:《广东省农业关系概说》,(日本)《东亚杂志》,第7卷11期,1942年11月,第27页。
⑤陈太先:《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1938年冬,(台湾)萧铮主编《中国地政研究所丛刊》,《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国)中文资料中心1977年12月版,第32456页。
⑥这里的“粮”,即“粮户”的意思,向政府上粮的农户,也就是土地的所有者——绅士。这是一种身份,在四川民间,一向以粮额为绅士身份的护符,所以有“绅粮”之称。“卖田不卖粮”,就是出售田地,但不出售“粮户”的身份。(参见彭雨新、陈友三、陈思德:《四川省田赋征实负担研究》,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有竹枝词曰:“拥田坐食号‘绅粮’,往岁威名镇一乡。未必人人皆土劣,不劳成获遭天殃。白日飞田主不和,‘伟粮’名号更离奇。豪家威重田无税,弱者无田亦税之”。词中的“飞田”就是有粮无田的情况,“飞粮之结果,使有田者无粮。飞田之结果,使有粮者无田。伟人例不纳粮,名曰‘伟粮’”。(见黄炎培:《蜀游百绝句》,林孔翼、沙铭璞辑《四川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2-303页。)
⑦1938年财字2098号,四川省档案馆,全宗148,案卷号1413。
⑧在成都平原,佃农交给地主的押租,可以从每年缴纳的谷租扣除一部分,作为押租利息,称为押扣,这也是成都平原租佃关系中非常独特的一项制度。关于押扣制度,笔者有详细论述,见拙文《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的押租与押扣》,《近代史研究》即将刊出。
⑨此处须说明:前面讲纳租18石,为什么只向地主交纳6石?这是成都平原特有的押扣制度。扣息的方法即按每安押租银100两,每年扣谷3石、3石多至5石,扣3石称为三扣,4石为四扣,以此类推。民国十年以前押扣通例为三扣五(3.5扣),民国十年以后,随着一般利率的上涨,增加到四扣以上。此处即是按四扣计算,安押租300两,应纳租谷18石,按四扣计算,每100两减去4石,300两共减去12石,所以此大佃户每年只向地主缴纳6石租谷即可。关于押扣的内容,亦见李德英:《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的押租与押扣》。
⑩新都县档案馆,全宗号28,案卷号8,新繁县繁江镇农地租约。
(11)陈太先:《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1938年冬,第32520页。
(12)《四川月报》,第5卷第5期,1934年11月,第58页。
(13)《四川月报》,第10卷第1期,1937年1月,第50页。
(14)四川省档案馆,全宗号,建西003,案卷号47,《成都华阳等七县农民协会驻蓉联合办事处》(1950-1951年),“邓锡侯、潘文华、熊克武业主自报出租田地押金登记表”。
(15)郭汉鸣、孟光宇:《四川租佃问题》,商务印书馆1944年8月版,第120页。
(16)卜凯、乔启明:《佃农纳租平议》,南京金陵大学《农林丛刊》,第47号,1928年12月刊印。
(17)社田条规,谢汝霖、罗元黻等修纂《民国崇庆县志》,1926年铅印本。
(18)义仓条规,(清)王树桐、徐璞玉、米绘裳等纂修《同治续金堂县志》,(清)同治六年(1867年)刻本,卷8“民赋”。《中国地方志集成 四川府县志辑》(4),巴蜀书社1992年8月版,第366页。
(19)见1930年6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土地法》第三章《农地》中关于农地耕种的相关规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一编《财政经济·农业》,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154页。
(20)四川省档案馆,全宗号156,案卷号78,《四川省农地减租推行委员会》1948年。
(21)郭汉鸣、孟光宇:《四川租佃问题》,第46-57页,第8表,《四川各县租约所载事项之一般》。
(22)郭汉鸣、孟光宇:《四川租佃问题》,第57页。
(23)见谢放教授的研究:《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经济结构的变动》,彭朝贵,王炎主编《清代四川农村社会经济史》,天地出版社,2001年3月版。
(24)双流县档案馆原卷号1249,案卷号2533,《民国双流县政府双流田赋粮食管理处、双流县税征稽查处关于欠粮办理田赋粮民清单的令、公函、呈文》。以下未注之处皆出自此卷档案。
(25)双流县档案馆原卷号1249,案卷号2533,《民国双流县政府双流田赋粮食管理处、双流县税征稽查处关于欠粮办理田赋粮民清单的令、公函、呈文》,第13页,训令。
(26)冉吉安给双流县政府的呈文,“于民前数年佃到艾雨之名下水田十亩有余”,从民前数年到1948年,已近40年,而艾雨之年龄才40岁,艾氏不可能刚出生就去租佃刘庆和的田,由此判断,艾氏与刘庆和的租佃关系以及与冉吉安的租佃关系至少形成于上一代。
(27)1948年9月4日,周世清给县政府的呈文,双流县档案馆,案卷号2535,《民国双流县政府、双流田赋粮食管理处、双流县各乡镇,关于催收欠粮办理事宜的训令、公函、呈文》,第25-26页。
(28)1941年9月10日,文焕章给崇庆县政府的呈文,崇州市档案馆,全宗号003,案卷号660,《敌伪政治档案卷 崇庆县政府经收处》,《关于公学产佃户各案卷》1941年9月,第9号。
(29)1942年2月5日,白云庵佃户给崇庆县政府的呈文,崇州市档案馆,全宗号003,案卷号660,《敌伪政治档案卷 崇庆县政府经收处》,《关于公学产佃户各案卷》,第104号。
(30)这是成都平原多年的习惯,只对水田收租,旱地或其他杂地均不收租。
(31)1942年8月,高蔡氏给崇庆县政府的呈文,崇州市档案馆,全宗号003,案卷号660,《敌伪政治档案卷 崇庆县政府经收处》,《关于公学产佃户各案卷》,第17号。
(32)崇州市档案馆,全宗号003,案卷号660,《敌伪政治档案卷 崇庆县政府经收处》,《关于公学产佃户各案卷》,第17号。
(33)据1930年《世界年鉴》,世界各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是英格兰和比利时,英格兰每平方公里人口数为262人,比利时为261人。
(34)郫县一个做保长的佃农,租佃了90亩水田,才只雇了2个工人,由此推论,50亩田,雇2个工人足够了。参见欧学芳:《四川郫县实习调查日记》,1938年,(台湾)成文出版社1977年12月版,第61873-61874页。
(35)陈太先:《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1938年冬,第32516页。
(36)郭汉鸣、孟光宇:《四川租佃问题》,商务印书馆1944年8月版。
(37)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载《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6页。
(38)《简阳租佃制度调查》,《四川月报》第8卷第1期,1936年1月,第99页。
(39)熊伯蘅:《租佃问题的对策及佃农保护法》,《中农月刊》第8卷第10期,1947年10月31日,第14页。
(40)从案例一,艾赵氏的问讯笔录中,可以看出县粮食征收局的人员对艾雨之转佃行为的默认。
(41)张五常:《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和台湾的土地改革》,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页。
(42)四川省档案馆,全宗号建西003,案卷号17,《成都华阳七县农会驻蓉联合办事处》,《中共温江县委汇集的全县有关业主的出租田地租押调查登记统计表》(1950年11月),《温江县住成都业主出租田地租押调查表》,第7页。
(43)张五常:《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和台湾的土地改革》,第77-78页。
(44)四川省档案馆,全宗号建西003,案卷号17,《成都华阳七县农会驻蓉联合办事处》,《中共温江县委汇集的全县有关业主的出租田地租押调查登记统计表》(1950年11月),《温江县住成都业主出租田地租押调查表》,第9页。
(45)陈翰笙著,冯峰译:《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8月版。
标签:成都郫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