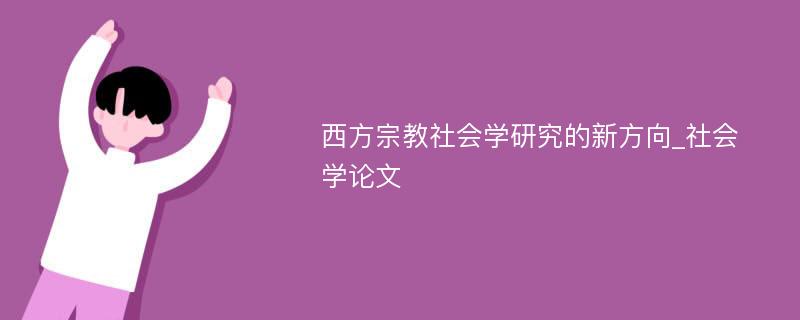
西方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新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社会学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西方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已经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转变:即从对宗教的批判到对宗教的重新定位,从世俗化到非世俗化再到多元化;从理性批判到感性取向乃至灵性证明;从社会建构论到主体建构论。这种新研究取向既是对当代宗教复兴的反映,又是现代西方社会特定发展阶段及其社会思潮所决定的。
一 对宗教功能的重新定位
西方宗教社会学理论从一开始就是肯定宗教的社会地位和功能。孔德早在《实证哲学教程》中对应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提出了宗教起源和发展的进化论,他把人类的认识分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并把宗教只限定在人类理智早期发挥作用。晚期孔德作了修正,提出社会需要一种“人类宗教”,孔德认为人不可能知道比人更高的东西,宗教知识的真实对象只能是指人类,人类本身就是神。并为此设定了礼仪、庆典等一套程序。
其后,无论是涂尔干、韦伯、齐美尔都对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重新加以肯定。齐美尔认为,家庭、种族、国家等都是社会整合性的体现,在这些整合性中都普遍存在诸如忠诚、信任等旨趣,而这些旨趣如果上升到了上帝那里,就得到了最纯粹的表达,整合性也因此达到最纯粹的表现。所以齐美尔说:“宗教整合性简直就是社会整合性的绝对形式”。①
当代著名的美国宗教社会学家贝拉提出了公民宗教的概念,他认为:“美国公民宗教的核心传统不是作为一种国家的自我崇拜的形式,而是作为这个国家对超越于它的那些道德原则的服从,对于它的评判也应该根据这些原则来进行。”②贝拉认为公民宗教是一种宗教象征和信仰主体,公民宗教不是一种救赎宗教,它不是要拯救灵魂,而是要维系一种秩序;它是美国公民生活与信仰之间起沟通作用的桥梁,而它的作用之发挥也离不开各种救赎宗教。美国的公民宗教是一种美国生活方式,一种美国精神,一种美国人的统一意识。这是对美国的宗教意识泛化成为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的考察。
西方马克思主义一部分学者追随马克思的批判传统,进行宗教批判。但是另外一些学者则不同意马克思对宗教的完全批判,认为应该重新思考并定位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这些学者包括美籍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学家威海姆·赖希、弗罗姆、布洛赫,以及晚期的哈贝马斯等。
赖希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宗教情感和心理生活的作用,而他则是用宗教的心理学来解释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社会学解释。赖希认为性冲动在人性格结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而“性高潮激动现象同从最简单的虔诚屈从到总的宗教狂热一系列宗教激动现象之间是有一种相互联系”。③这样,赖希就从人的生理需要找到了宗教的根源。在他看来,宗教就不再像马克思所说,是社会压迫的产物,是虚幻的东西了。
弗洛姆认为现代社会具有严重的病态。由于人们只注重物质享受,导致生活已经丧失意义,成为完全扭曲的人。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求诸宗教。他认为宗教是“能为个人提供取向结构和献身目标的团体共同的思想行为体系”。④弗罗姆认为个体的满足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自我保存的基本需要的满足,另一个是弗洛姆称为“利比多需要的满足”。如果说社会能够满足的是人的自然和文化本能的基本需要的话,那么,宗教所提供的则是一种“里比多需要的满足”,它们主要是在“幻想中产生的满足”。
至于宗教的心理功能,弗洛姆认为宗教有三重功能:对全人类,为由生活所迫而必需造成的贫困提供安慰;对大多数人,为他们在情感上接受其阶级状况鼓足勇气;对少数统治者,为他们消除由被他们压迫的人的苦难造成的负罪感。⑤从这里看出,弗罗姆的看法与马克思关于宗教是“鸦片”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他认为这些麻醉功能对于人类来说是必须而且重要的。在弗罗姆看来,人类需要宗教的原因在于宗教与心理分析一样,旨在“灵魂的治疗”,关注的问题都是“人的灵魂及其治疗”。⑥
布洛赫被称为是“手持圣经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为数不多的重视宗教的研究者。布洛赫认为,人是一个“指向前面的意向”,也就是说,现在的人是尚未完成的人,充分完整的人是“某种仍然必须加以发现的东西”。他说:“我们仍处于尚未形成的状态中,但我们仅仅处于形成之中”。人的这种未定状态指向未来,就有了希望的可能。这样,布洛赫就把人的希望与上帝联系起来,他认为上帝就是尚未彻底完成的未来的人。“人类在上帝的本质中表达的,不是别的,完全是盼望中的未来。”可见他认为的宗教的本质特征即是给人提供希望。
构建后现代宗教的格里芬认为,现代社会在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却将丰富多彩的世界简单化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一切事物都失去了神圣高雅的色彩,支撑现代文明的就只剩下经济动机或获利动机。现代社会永远都不能告诉人们面对世界应该怎样去做一个人,也无法满足人们对精神需求的渴望,因而整个世界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格里芬坚信:“如果要有一个健全的和可以维系的社会,则公共生活必然反映宗教价值。”⑦因此,后现代社会必然是一个宗教社会。
现代的一些西方学者还提出了宗教功能多重性的理论。哈贝马斯前期对宗教是否定的,他认为现代性就是合理性,而合理性就是世俗性,世俗性就是解构神秘性,因此现代社会是以牺牲宗教为代价的。但是在后期,从1980年发表的《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理想》开始,哈贝马斯对宗教的看法开始有了转变。⑧哈贝马斯认为:启蒙的反思文化虽然值得骄傲,但是他和宗教分道扬镳了,而且相互之间井水不犯河水。宗教的衰退导致知识和信仰的分裂,而这又是启蒙自身无法克服的。他也不再仅仅强调教会的体制和特权,而是认为教会是扎根在世俗传统中的解释共同体,相互竞争的解释共同体。基于这种转变,哈贝马斯开始重新看待宗教和他的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他从宗教语言的语义学结构找到了它们的契合点。他认为“一神论传统所驾驭的语言,具有一种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的语义学潜能”。“只要宗教语言仍然具有启示作用和必不可少的语义学内涵——而这些内涵是哲学语言(暂时)所无法表达的——并继续拒绝转化成论证话语,那么哲学,哪怕是以后形而上学形态出现,也同样无法代替宗教,也不能排挤宗教。”⑨
哈贝马斯还认为宗教对日常生活具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并且重新认识了宗教的功能。他认为“彻底世俗化的生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一点不受超常事件毁灭性和颠覆性侵入的影响”。尽管宗教建构世界观的功能还在被削弱,但它对于日常生活中和超常事物打交道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规范作用,因此后形而上学思想和宗教实践也可以平等共存。可以看到,哈贝马斯开始将宗教看做是重建人与人或者人与世界交往方式的一种努力。
对于宗教的社会功能既肯定又否定的,还有帕森斯及其学生默顿。帕森斯认为宗教可以成为创造革新的来源他认为:“一个特别的事实是,在紧张的人类生活中,在深层次的情感层面上,宗教团结意味着有可能成为应对更富有创造力的而并非传统的环境的主要领域之一。然而,基于相同的理由,这种创造力很可能是一种我们在上面所讲的逃脱不了的被嵌入的骚动和各种类型的‘非理性’反应。此外,在宗教发展最具创造力的时期也有趋向社会骚动而不是稳定和平的倾向。”⑩
默顿不赞成涂尔干对宗教整合功能的绝对肯定,他认为:“涂尔干的研究取向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无文字社会的研究。由他这种取向,这些学者倾向于只关注宗教整合的后果,而忽视宗教在某种社会结构中可能有的解体后果。”(11)他认为,至少可以相信的是,从无文字社会研究中得出的理论取向,模糊了本应清晰的宗教在多宗教社会中的功能角色的事实。也许,正是功能一体假设的转移,导致了对宗教战争、宗教法庭(破坏一个又一个社会)、宗教团体自相残杀的全部历史的抹杀。因为,这一事实依然存在,即所有这种广为人知的事实都为迎合对无文字社会宗教研究的成果而被忽视。”(12)默顿的论述引导人们去研究宗教对特定社会的冲突、失范、分离、解组功能,宗教对社会变迁和社会革命的作用等。
二 从宗教的世俗化到反世俗化和多元化的理论转向
(一)从世界的脱魅到宗教的世俗化
作为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的韦伯首先提出了现代社会的“脱魅”说。韦伯认为宗教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非理性到理性的进化过程。所谓非理性宗教是充斥着大量神秘的、巫术的、情绪的、传统的力量,总之是不可计算的,不能由人控制的因素在起作用的宗教,此外,这种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无关或影响甚少,反之摆脱了各种神秘的巫术力量,一切可通过计算,可为人控制的因素起作用的宗教被称为理性宗教。判定一个宗教理性化的程度,就是看宗教本身摆脱巫术的程度和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体系相结合的程度。(13)
韦伯在其《古代印度教》中提出过“世俗化”一词,但并没有明确地形成世俗化的概念。但是他提出的“世界观的脱魅”实际就是指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世俗化,并成为后来其他学者提出的世俗化理论的基础。
明确提出世俗化理论的是当代美国著名的宗教社会学家贝格尔。什么是世俗化呢?贝格尔的分析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世俗化指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即社会和文化的一些部分摆脱了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征的控制。其次,世俗化不止是一个社会结构的过程,它影响着全部文化生活和整个观念化过程。第三,世俗化还有主观的方面,存在着意识的世俗化过程,也就是现代社会的人看待世界和自己的生活时根本不需要宗教解释的帮助。(14)
那么世俗化的原因是什么呢?贝格尔肯定了“在西方世界中工业化采取了社会主义组织形式的那些地区,与工业生产过程的接近和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仍然是造成世俗化的主要决定因素”(15)。但贝格尔并没有停留于此,他更感兴趣的是“西方宗教传统在何种程度上可能在自身中就带有世俗化的种子。”他与韦伯一样,认为“世俗化的根子可以在古代以色列宗教最早的源泉中发现。换言之,我们可以断言,世界摆脱巫魅在旧约之中就开始了。”(16)
世俗化导致了对宗教的信任危机,“世俗化引起了传统宗教对于实在的解释之看似有理性的全面崩溃”。世俗化包括主观的世俗化和客观的世俗化。主观方面,人们在宗教问题上倾向是不确定的。客观方面,对实在有更多的解释,而不只是一种宗教解释。这样世俗化导致了宗教社会基础的多元化,而多元化反过来又加深了世俗化。在这里,多元化与世俗化是互为因果的。
(二)对世俗化理论的质疑
世俗化理论自从明确地提出之后就一直遭到争议。(17)特别是由于传统的制度型宗教和以民间宗教为特征的对意义的追求始终没有死亡,反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兴盛起来(18),更是引起了众多学者对世俗化理论的质疑。
英国学者季利在1973年出版的《宗教的持久》一书中,他承认现代化为宗教带来了一些改变,例如:宗教不再直接影响大型的社会架构;一些以前用宗教解释的现象,现在已经用科学解释;宗教本身更个人化,更倚赖自由的选择。(19)但他仔细分析美国的调查数据,认为世俗化理论并不符合这些数据,而且“当我们考虑世界其余地方的宗教实践,会发觉欧洲而不是美国,才是例外的。在第三世界,宗教并没有失去力量……从全球的角度看,基督教在一些欧洲国家表面上的失败并非标准情况,而是异常的例子。”(20)
英国学者马丁也对世俗化概念大为质疑,他甚至曾一度呼吁学者取消这概念,(21)他说:“我对这论点甚有保留——它既矛盾又复杂,概括地说,我怀疑他可否普遍的涵盖现在和未来的社会或历史发展,我也怀疑它是对宗教意识的组织框架的偏见。”英国的格雷斯·戴维也对“欧洲例外论”进行论证,认为欧洲的宗教模式并不是全球宗教信仰的一个典型范例,它只是适用于欧洲大陆。
英国宗教学者葛瑞勒研究英国林伯德的宗教发展,他的结论是一些本地的人口改革,政治发展等因素,比普世的现代化进程,能更好地解释当地的宗教改变,他将世俗化理论比喻为一把钝的工具,只会掩盖更多的社会因素。他认为一揽子将所有改变都归入所谓的世俗化进程内,很可能会阻碍我们对其建立真正历史性的了解。(22)
(三)反世俗化和多元化理论的形成
正是由于许多不利于世俗化的证据的累积,贝格尔的态度也改变了。他认为,“假设我们处于一个世俗化的世界是错误的,除了下文要谈及的一些例外,今天世界的宗教狂热已如往昔,在某些地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指由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宽松的标签为‘世俗化理论’的所有著述,在本质上都是错误的。”(23)
贝格尔指出世俗化理论的应用范围主要有两个,一是欧洲,二是跨国界的组别:受西方高等教育的人。但世界的其它部分和以前一样热衷于宗教,或许比以前更热衷。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传统宗教仍大有影响力。而更有两个很有活力的宗教运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福音派。前者的影响不单在伊朗,而是由北非延展到南菲律宾,而福音派则在东亚韩国、南太平洋次撒哈拉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快速增长,甚至在某些地区转化社会。对于宗教的未来,贝格尔明确地提出,“下一个世纪的世界不会比今日的世界缺少宗教性”。(24)贝格尔在其近期著述中更多地强调宗教的多元化,他指出:“世俗化理论越来越不重要,而关于多元化的问题逐渐成为中心问题。如果说世俗化并非现代世界的基本特征,那么,什么是现代世界的基本特征呢?我认为多元主义是现代世界的基本特征。”(25)
美国学者斯达克在《宗教的未来》中,他认为宗教世俗化是一个自我限制的过程,它导致了宗教复兴和宗教创新,是宗教经济的基本动力。在近期出版的《信仰的法则》一书中,斯达克继续基于实证资料驳斥了世俗化的观点。首先,他认为传统“世俗化理论”有三点涵义,一是“非制度化”,即指宗教制度的社会权利的衰落,对此他并无异议。二是指宗教参与(即到教堂参加宗教仪式)的人数。从文献资料看,他认为欧洲人的宗教参与并没有刻意证明的长期的下降。事实上,在欧洲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什么“信仰时代”,在西欧和北欧现代化开始之前的几个世纪,宗教参与的程度就很低。所以,所谓宗教参与的下降,是夸大了过去的宗教参与。第三,斯达克认为宗教世俗化的最重要含义应是个人虔敬度的下降。而这一点,情况却恰恰相反:150多年里,美国人的宗教性不仅没有下降,而且教会会员的比率实际上增加了一倍,欧洲比美国的宗教参与率低很多,与此同时,在信仰的主观量度上则差别很小。至于伊斯兰世界中的宗教复兴和亚洲、非洲等第三世界中的宗教热更是全面地驳斥了世俗化的判断。
总之,斯达克认为,宗教是否会在未来消失,不能肯定。但即使宗教在未来真的被赶进历史博物馆,那仍然不是现代化引起的。信仰的消失与世俗化的教条设定的过程是不同,因此“让我们再以此宣布社会科学对于世俗化理论之信仰的中介,那只是愿望的产物。”(26)
三 知识论的感性取向乃至灵性证明
众所周知,就认识论传统而言,西方社会一直是注重理性,贬低感性的。从启蒙时代以来,西欧的学者们总是用人的理性来批判教会的神性,这种情况在早期经典社会学的理论中也是十分明显的。不过,从上世纪下半叶开始情况就发生了些许变化,从西方社会思潮的宏观背景中开始有了感性论的出现,并逐渐地向这个方向靠拢。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不再一味强调理性选择的根本作用,而是进而转向了研究中经常被忽视的非理性部分,感性取向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而当我们切入要宗教生活中来看时,会发现这种由理性向感性的转向在这个部分表现得更为突出,甚至除了转向感觉论之外,进一步趋向于神秘主义和超感觉主义灵性论。
索罗金在《社会和文化的动力学》中把人类文化分为由神支配的灵性阶段、感官支配的感性阶段以及理性阶段,而且断言此三者定处循环交替中。而当今,“西方社会和文化有机体似乎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一场最深刻、意义也最深远的危机……这是一种感性文化的危机,它现在已经到了腐朽的阶段。”(27)而现象学宗教社会学家舍勒正是关注宗教的情感方面,舍勒以基督教的集体观念作为出发点,第一次提出了所谓的上帝的“社会学”论证。
他认为,基督教集体理念的第一条原理认为,个体是有精神的、有限的人格存在,个体需要与其他和自己同类的个人过着共同的生活:“一个理性人的全部存在和行动,既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责任自负的个体现实,同样也是某个集体中有意识的责任共负的成员现实,这乃是一个理性人的永恒的理念的本质。”(28)也就是说,任何个体既是有个性的独立存在,也是依赖集体的共同存在。这里的集体,并非指现实中的有组织的团体,而是指一种“对集体的精神意向”。例如爱、同情、诺言、请求、感谢、顺从、效劳、统治等。
在我们灵魂的核心,有一种超越的精神冲动,它们“只可能在一个理念中得到它可能得到的完结和完全的满足。这个理念就是与一个无限的、精神的个体缔结爱的共同体,组成精神的集体”。而这个“无限的、精神的个体”就是上帝。“只有在上帝之中,只有通过上帝,我们才真正在我们当中以精神的方式结合在一起。”(29)舍勒明确的把这种感性的爱作为认识的基础,也是作为信仰上帝的基础。舍勒认为还有一种真正的爱,那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具体情感比如欲望,贪婪,渴望等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条件。
那么这种爱是如何可能呢?在这里舍勒发现了宗教的原因。他诉诸基督教的学说来作出回答。舍勒认为,如果印度人和希腊人哪里,爱是认识的结果,那么在基督教的体验结构中,爱则是认识的第一推动力。在基督教中,一切宗教的认识过程和拯救过程都根源于作为爱的化身的上帝自身。(30)舍勒认为,对上帝存在的认识一方面有赖于上帝施爱与人“只是在上帝的爱的行为和过程之中,上帝的存在之完整图像才展示给精神的慧眼”;另一方面也有赖于人的爱心,“只有有爱心的人眼睛是睁开的,眼睛的明亮程度取决于他们的爱的程度。”(31)总之,对上帝的爱乃是认识其他一切事物的基础。因为,对上帝爱同时也意味着与上帝一起爱他所创造的一切,包括人在内。(32)上帝的爱的本质就在于,因为爱,上帝才创造了万物,才赋予了万物以价值。
美国的宗教社会学一直是以“理性选择”自诩的,如果说,在贝格尔的《神圣的帷幕》一书中,还坚持着社会学的理性实证路线,把社会学视为宗教所面临的一道“火溪”,宗教不过是一种“用神圣的方式来进行秩序化的人类活动。”(33)但是在其随后的《天使的传言》中,为了挽回人们对他前一著中消解宗教的指责,贝格尔又从基督徒的角度转而用感觉主义来论证“超自然者”的存在。他认为要从人开始,要提出一种具有高度感受性的神学,就要将其命题与能够从经验中了解到的东西联系起来。为此,贝格尔提供了关于超自然者的五项证明:
第一,从秩序出发的论证,人对意义和秩序的信念是人生和社会中普遍的支柱,但它在此世没有证据支持,因而指向了超自然;
第二,从游戏出发的论证,游戏可以使人们忘记自己面对的现实的时间,游戏中的时间是永恒的,所以它指向了超自然的永恒之存在;
第三,从希望出发的论证,人总是要凭借希望而生存,希望总要超越死亡,因而它存在的根据也不在此世;
第四,从诅咒出发的论证,诅咒在我们日常经验中经常发生,它表示对某些恶人恶事的谴责是绝对的和确定的,但在此世一切都是相对的和不确定的,因此诅咒的根据只能在超自然那里寻找;
第五,从幽默出发的论证,幽默根源于万世万物的不协调,人认识到了这种困境,并使用幽默来把它相对化,在此世的压力得不到根据但却能缓解压力的幽默,只能到超自然那里去寻找。
贝格尔的归纳完全从人类的感性生活出发,是一种直观的体验。
与贝格尔经常合作研究的德国宗教社会学家卢克曼,也从感性的经验和超验来解释宗教现象,他在《无形的宗教》一著中说:“人类生活根本上的宗教本性……把单个的人置入一种社会的和历史的超验现实之中的那种模式化,本身是一个宗教的过程。”(34)“每一个人都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经验和超越自我的经验之间做出了区分……每一个当时现在的经验都有一个被现在化的内核和一个关于现在未被经验者的视域。”(35)宗教的形成“在第一个过程中,对超验性——从微小的、日常的超验性,到巨大的、非日常的超验性——的各种类型的主体经验被以语言的—象征的方式客体化,并被告知他人(或者也告知自己)。……在叙述中,经验被转化为神话……在仪典中,经验得到了共同的记忆。”(36)
意大利的弗朗哥·费拉罗迪同样也是对于宗教中非理性情感的重要地位做过相关的阐述。在《非信仰者的神学》(A Theology for Non-Believers)一书中,他非常清楚地说明:“我们并没有像某些人草率地声称的那样,看到神圣者的完全隐退,正相反,我们看到了一种回归神圣者的趋势,他被体验为对使人失望的人类理性的一种否定,被体验为一种对非理性的回归、对作为满意之源泉的纯粹情感的回归以及对令人迷茫而同时不乏建设性的荒诞之重要性的回归……此外,所需要的是,重新创建一种后传统主义的合理性:它不再是以理性—非理性之两难为基础的二分法,相反,它能够容纳反理性和初始理性的各种冲力,这些冲力是人类体验的一部分,甚至是进入如人类体验的一些决定性因素。”(37)
格里芬也认为,在当代占统治地位的两种神学形态——保守的基要主义神学和现代自由主义神学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已不能实现应有的普及和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打破这种困境,格里芬提出后现代神学要建立起第三种神学形式,“它通过对实在所做的一种更理性化、也更经验化的描述,而向现代世界观挑战。”(38)第三种神学形式能既实现现代化又有效地避免现代的弊端。在上帝问题上坚持自然主义有神论;在认识论上以非感觉性知觉的论断为基础,重视创造性经验。格里芬说:“世界仅仅是由瞬时单元组成的,这些瞬时单元是部分地自我创造的知觉经验。”(39)“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瞬间经验或者是由瞬间经验组成的”。(40)“上帝是宇宙的灵魂,是包罗万有的经验统一体,并且是使宇宙成为一个统一体的原动力……世界对上帝的相对独立性”。(41)这里我们看到了莱布尼茨的单子,佛教的“刹那”存在,经验批判主义的“超越”了物质和意识对立的“经验”的混合物。“后现代神学是以非感性知觉的论断为基础的”。(42)
四 思维方式上的主体建构论
传统的宗教社会学的思路是一种主客体二元,社会客体单向构建宗教的思路,可以涂尔干为例。但到了20世纪后期,社会学的宗教理论已逐渐从社会构建论转向主体建构论,与人文主义、感性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是现象学的主体建构论。社会制度、社会秩序乃至宗教不再是由社会来构建,而是主体在实践中的构建,是内在的外在化。这种思想最初源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费尔巴哈认为,宗教是人的投射。一般而言的宗教代表了人与其本质的关系,上帝是人的这种本质的结果,人的本质被提到形而上学的高度,并且成为信仰的对象,神在本质上是人。自然人通过与他人接触去实现自身,或者通过平等和有回报的对话形式与上帝接触实现自身。
从主客体单向度的二元思维方法向主体性思维方式的转变这是当代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吉登斯在《社会科学方法的新规则》一书中,明确提出要抛弃传统的社会与个体的二元对立,更关注于被不断再生产的实践,即行动与结构间的双重建构。哈贝马斯认为社会学理论再也不能以实证科学的面孔出现了,而应从人际关系、生活世界、行动主体的视角来知觉社会的交往行动。(43)而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的双重辩证运动,强调“内在性的外在化”和“外在性的内在化”。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也反映到宗教社会学的领域内。
齐美尔认为宗教有两种基本的存在形式。一种是客观的宗教,无关乎主体生命,而另外一种是生存在主体生命中的宗教,不对应客观物。(44)传统的研究把眼光集中于客观的教会的研究,但齐美尔另辟蹊径,他关注的是后者。他的整个宗教理论都落脚在宗教性上。
齐美尔认为,“宗教性是从最深刻的个体创造性和自我的责任中涌出的一种灵魂生命自身,作为宗教的存在,它自身具有一种超越主体的形而上的意义和庄严。”(45)也就是说,作为灵魂生命自身的宗教,就是人在宗教行为中表现出的主观反映和主观态度:“宗教主要是构成整体关系一方的人的主观态度,或是人对该关系现实性的主观反应,它纯粹是人的感觉和信仰,是我们灵魂的一种状态或经历。”(46)
这样,齐美尔提出了宗教性和实体宗教的关系。宗教性就只是一种天生的灵魂状态,它并不必然演化为实际的建制宗教,只有宗教性寻找到合适的社会化形式,产生具体的超验系统知识和专职从事超验知识传播的人群时,实存宗教才成型。用齐美尔的话来说就是:“不是宗教创造了宗教虔诚,而是宗教虔诚创造了宗教”。(47)
齐美尔认为宗教人是以生命之在担当宗教实在。这些与教会教义,礼拜仪式等没有关系。只有那些没有或者较少宗教性的人,他们才会上教堂参加仪式。“谁内心没有上帝,就肯定要从身外去拥有它”。(48)这样齐美尔提出了主体性宗教和大众性宗教的区分。主体性宗教是宗教人的宗教;而大众的宗教则必须对应着一种客观的现实物,它必然创造出最外在化,最现实化的客观宗教神物。
贝格尔进一步构架了宗教的“建造世界”的具体过程,“每一个人类社会都在进行建造世界的活动。宗教在这种活动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49)贝格尔认为:“人生来是‘未完成的’”。(50)与其他高等动物相比,先天地具有生理构造的未完成性,贝格尔感到奇怪和不解。其实这正是人类进化史上的飞跃和提升,正是摆脱了动物简单的本能遗传,才能为个人后天的社会化提供广阔的可能性,人类儿童特别漫长的依赖期也是如此。而形成这一特点的正是千万年人类进化过程的沉淀,这是进步而不是退化。人社会化的前提是先要创造社会,而“社会最重要的功能是法则化……人生来就不得不把有意义的秩序强加于实在之上。”(51)这一建造世界的过程是一个外在化、客观化和内在化的过程。人通过自己的活动,不断把自己注入世界,这就是外在化。而作为人类活动这些产物,它们一旦产生,就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性,而反过来要制约人类,这就是客观化。而所谓内在化是指这些外在的产物重新吸收进人的意识之中,成为主体意识的不可分割部分。与人类其他的活动不同,宗教是“用神圣的方式来进行秩序化的”人类活动。“神圣意指一种神秘而又令人敬畏的力量之性质”(52),而宗教又是建造世界秩序的最强大的方式,“宗教意味着最大限度地达到人的自我外在化,最大限度地达到人向实在输入他自己的意义之目的,宗教意味着把人类秩序投射进了存在之整体。”(53)
卢克曼认为,个人要理解外部世界并对世界做出行为,必须要依赖一个意义系统。但是个体总是生活在一定的解释范式或者文化之中,而这种意义系统是由社会中历史传承的世界观所提供的。世界观是卢克曼理论的核心概念,他认为世界观提供了关于普遍秩序的范式系统,而且更深的意义上来说,它通过这种作用构造了世界秩序,也就是构造了一个有意义的世界。总之,世界观对于人来说,乃是一个客观的与历史的实在,“正是世界观是社会客观化的历史实在这一事实可以解释它为个人所具有的关键功能”。(54)
那如何理解宗教呢?卢克曼是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宗教的,他认为宗教就是能为个人和社会提供意义根据,超越指向以及道德基础的某种实在。卢克曼发现,“世界观作为一个客观的与历史的社会实在,执行着本质上是宗教的功能”,因此,“我们将它定义为宗教的基本社会形式”。(55)卢克曼又发现了宗教的人类学条件。卢克曼认为,“将人类有机体对生物特性的超验称为宗教现象,是与宗教概念的基本含义是一致的……这种现象依赖于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功能性关系。”(56)对卢克曼而言,不是具有基本社会学意义的宗教活动,而是客观化了的意义系统即象征世界将日常生活的体验与实在的超验层面联系起来。其他的意义体系并未指向日常生活世界之外。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包含一个超验的指涉领域。因此,卢克曼认为,宗教的起源要到人类有机体对生物特性的那种超越那里去寻找,这种超越基本上是一个宗教的过程。而社会化作为获得这种超越的具体过程,在本质上也是宗教的,它依赖于宗教普遍的人类学条件以及在社会过程中意识与良知的个体化,并且在历史社会秩序之下的意义结构的内化中实现自身。
综上所述,关于主体构建宗教的思想,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主体性思维方法在宗教社会学领域内的应用,它揭开了宗教起源和本质的神圣帷幕,起着一种祛魅的进步作用。但如果过分强调主体意识的能动性,否定宗教的社会历史根源,则可能会堕入另一种片面性,因此主体性思维方式仍应注重个体和宗教的双重、双向建构。
西方宗教社会学研究取向的这些转向是应对全球宗教复兴的需要,是西方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反映,也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主流范式向非理性演变的学术环境的影响。西方宗教社会学理论的这种新取向已开始影响中国学术界,但由于国情和教情的不同,西方宗教社会学的某些新取向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需要批判和扬弃。
客观地讲,作为现代化过程中的当代中国,结构—功能分析特别是新功能主义方法仍是我们在研究宗教时运用的主要范式。这是因为当代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之中,社会的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宗教本身也已面目一新,宗教和社会及社会各子系统的关系非常复杂,发挥宗教的积极功能已成为近年来教内外共同关注的热门议题,关于宗教社会学“结构—功能”范式,我已有专文另述,有兴趣的同仁可作参阅。(57)
注释:
①西美尔:《论宗教社会学》,曹卫东译,载《宗教社会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②罗伯托·希普里阿尼:《宗教社会学史》,高师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5页。
③参见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32页。
④参见弗洛姆:《精神分析与宗教》,转引自《宗教心理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80页。
⑤参见弗洛姆:《基督和教条》一文,载《弗洛姆著作精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页。
⑥参见高师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对弗罗姆关于精神分析与禅宗之间的对比有详细的论述。
⑦格里芬:《后现代宗教》,孙慕天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第24页。
⑧参见傅永军、铁省林:《哈贝马斯宗教哲学思想研究述评》,《哲学动态》2006年第11期。
⑨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上海: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50页。
⑩J.M.Yinger:《宗教社会学经典快读》,李向平、博敬民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323页。
(11)(12)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等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20、121页。
(13)参见韦伯:《韦伯作品集: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14)(15)(16)参见贝格尔:《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诸要素》,高师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8、131、132-135页。
(17)有学者认为世俗化其实只是个假设,还不足以成为一种理论。只能作为一种对来自于经验事实的综合解释。
(18)这里有很多反驳世俗化的例子,比如东亚和拉丁美洲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宗教都仍然保持着影响力,而美国更是一个宗教性非常强的国家。
(19)葛瑞勒:《宗教的持久》,转引自关启文《宗教在现代社会必然衰退吗?——世俗化理论的再思》,载王晓朝主编《信仰与社会》。
(20)A.Greeley,Religions Change in Americ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117-118.
(21)D.Martin,The Religionus ande the Secular,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9.
(22)J.Cox,The English Churches in a Secular Society:Lambeth,1870-1930,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23)(24)贝格尔:《世界的非世俗化:复兴的宗教及全球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15页。
(25)游斌 孙艳菲:《回归“大问题”意识:论现代社会与宗教》,《世界宗教文化》2006年第1期。
(26)参见斯达克·芬克:《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杨凤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0-97页。
(27)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21页。
(28)(29)(30)(31)(32)[德]舍勒著:《爱的秩序》,林克等译,刘小枫选编,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95、99、17、18、19页。
(33)[美]贝格尔:《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高师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页。
(34)(35)(36)[德]卢克曼著:《无形的宗教》,覃方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122、126页。
(37)[意]罗伯托·希普里阿尼著,劳拉·费拉罗迪英译,高师宁译,《宗教社会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至第191页。
(38)(39)(40)(41)(42)[美]大卫·雷·格里芬著:《后现代宗教》,孙慕天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5、135、136、158-159、6页。
(43)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4-440页。
(44)齐美尔说“一方面,是宗教的或教会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宗教完全放置在主体的内在生命。”参见《伦勃朗的宗教艺术》,转引自陈戎女:《西美尔与现代性》,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226页。
(45)(46)参见《伦勃朗的宗教艺术》,转引自陈戎女著《西美尔与现代性》。
(47)(48)参见齐美尔《现代人与宗教》,第94、56页。
(49)(50)(51)(52)(53)贝格尔著,高师宁译,《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的要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29、33、36页。
(54)(55)(56)卢克曼:《无形的宗教》,覃方明译,第41-42、43、37页。
(57)可参见拙文《西方宗教社会学“结构—功能”范式的演进》,《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1期。
标签:社会学论文; 宗教社会学论文; 美国宗教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社会经验论文; 齐美尔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