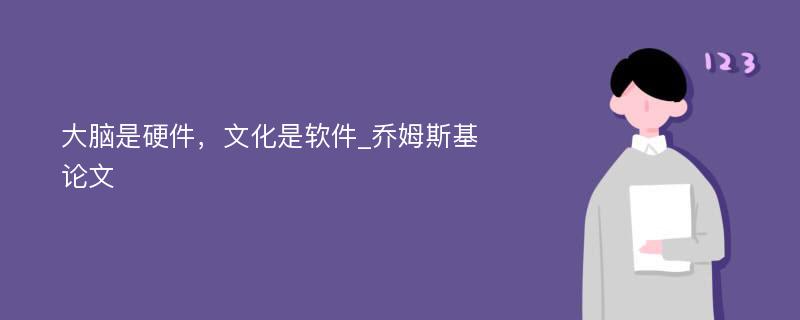
大脑是硬件,文化是软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脑论文,硬件论文,文化论文,软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新卡尔纳普学派对新维特根斯坦学派:乔姆斯基对戴维森
在刚刚过去的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卡尔纳普的“统一科学”运动的追随者和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追随者一直进行着某种斗争。现在,通过比较这两派哲学家对认知科学所持的态度,就可以非常充分地把握他们之间的各种差异。
这些卡尔纳普派学人都看到了这种已经得到公认的、行为主义还原论的不可能性——卡尔纳普曾经希望,通过揭示这种还原论为我们留下的、有关意向性在物理粒子世界之中的位置的问题,把这种不可能性充分地揭示出来。不过,这些哲学家之中的许多人认为,由于“计算机革命”,这个问题已经以某种非还原论的方式得到了最终解决。杰里·福达(Jerry Fodor)告诉我们,由于“计算机向我们表明了怎样才能把语义学与符号的因果属性联系起来”①,这种革命就成为可能了。考虑一下计算机已经帮助我们意识到,各种符号都可能具体化(incarnate)成为像各种神经状态那样的人化之物,并由此而发挥因果关系方面的效力吧。福达认为,这种革命是一次伟大的学术突破,它使我们能够深刻地洞察以往根本不可能洞察的心灵(mind)的运作过程。
虽然诸如戴维森、布兰登(Brandom)和德斯康伯斯(Descombes)这样研究心灵和语言的哲学家对这种革命持怀疑态度,但却没有受到这种意向性之物(the intentional)的无法还原性的任何困扰。根据维特根斯坦的思路,他们认为,一种词汇无法还原成另一种词汇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与一种工具不可能被另一种工具所替代的问题并无二致。而且,他们并不认为心灵是一种可以由认知(cognitive)科学家们来研究其各种运作过程的机制。他们虽然同意说大脑是这样一种机制,但并不认为把大脑等同于心灵会有什么益处。
这些新维特根斯坦派学人迫使我们放弃赖尔所谓“笛卡尔的准机械式(paramechanical)假说”,而不是通过把大脑的各种状态当作表象来处理,用物理学家的术语对它加以重新解释。这些维特根斯坦的后裔都很希望既摆脱有关内在表象的整体观念,同时也摆脱产生这些表象的各种机制。新卡尔纳普学派学人认为,心灵和语言都是一些事物,通过把它们分解开来,观察它们的组成部分相互适合的方式,观察它们与有机体的各种环境特征相适合的方式,就可以理解它们;而新维特根斯坦派学人则认为它们都是一些社会技能(social skills)。例如,戴维森指出,虽然意义理论必须描述一位解释者能够做什么,但是,认为“某种存在于解释者内心之中的机制必须与这种理论相符合”却是没有任何根据的②。
乔姆斯基对这种主张的评论是:“对于任何一位从自然科学的立场出发来探讨这些问题的人来说”,戴维森的思维方式都是“完全错误的”③。他指出,对各种潜在机制的怀疑态度很可能曾经阻碍过化学的发展。正像道尔顿和门捷列夫使我们能够看到存在于化学元素结合而形成化合物的能力背后的、原子之间的机械性相互作用那样,认知科学也将使我们能够看到存在于各种社会技能的发挥过程背后的、神经细胞之间的机械性相互作用。在乔姆斯基看来,诸如蒯因、戴维森和达米特这样的哲学家,都是一些顽固地拒绝进行变革、试图扼制由已经确立的经验结果构成的兴旺发展态势的人物。
他指出,这些结果包含着下列发现,即“语言机能的某种初始状态即体现了某些关于语言结构的一般原则,包括语音方面的原则和语义方面的原则”④。在出版其《笛卡尔语言学》(Cartesian linguistics)大约二十五年以后,乔姆斯基便清楚地表达了他对维特根斯坦派学人的反笛卡尔主义的厌恶,特别是对下列观点的厌恶,即只要把语言简单地当作某种可以教授的技能、而不是当作某种生成语法程序来考虑,我们就可以感到满足了⑤。虽然赖尔认为,所谓对他所说的“理智和性格之诸特性”的研究有可能成为对各种机制进行的研究,只不过是“笛卡尔式的神话”而已,但是,乔姆斯基却认为笛卡尔和洛克为我们指出的方向是正确的。蒯因确信存在于物理原子和心理原子之间的各种类似会使哲学误入歧途,而他却对这些类似会使哲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坚信不疑。乔姆斯基使两类哲学家之间的分歧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化——一类哲学家同意赖尔和维特根斯坦所谓“观念的观念”(the“idea idea”)已经因为过于陈旧而毫无用处的观点,而另一类则并不认为如此。
乔姆斯基对戴维森的下列主张持讥讽态度,即通过摆脱分析—综合的二分法,蒯因便“拯救了作为一个严肃主题的语言哲学”。乔姆斯基指出,“实际上,任何一位从事描述性语义学研究的人”,都会认为这种二分法是理所当然的。他写道:
如果在语句“约翰杀了比尔,所以比尔死了”和“约翰杀了比尔,所以约翰死了”之间存在着某种由语言本身决定的、性质方面的区别,那么,人们很可能根本无法找到对语言进行的、不指定各种结构并且描述杀、所以等语词的意义的研究⑥。
乔姆斯基指出,要想说明与学习语言有关的、诸如“每一个儿童都知道存在于‘约翰看到了比尔和谁在一起’和‘约翰看到了比尔和谁’之间的本质性区别”这样的现象,我们就需要这种对“语言本身决定的”东西和语言本身并未决定的东西进行的区别。因为正像他所指出的那样,“儿童们并不是……先说出‘约翰看到了比尔和谁’,然后再由他们的父母告诉他们话是不能这样说的”,唯一可以利用的解释就是语言机能所具有的内在结构⑦。
在这里,乔姆斯基的论证所依据的是下列假定,即某种行为的在场和不在场一样,实际上都是一种有待解释的语词(explanandum)。但是,这似乎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有关为什么没有一个儿童在掌握了三位数“104,108,112”之后,却不能把“2,4,6,8”这样一种序列进行下去的某种说明,或者有关为什么父母所提出的任何一种指令或者纠正,都不一定能保证儿童不出偏差的某种说明。这种乔姆斯基式的说明的意思大概是,有某种内在机制在发挥作用。对于诸如戴维森这样的哲学家来说,这是一种对于某种非事件(non-event)的“具有麻醉效果的”说明。
当乔姆斯基批评戴维森那“消除学习某种语言的过程与了解我们以这个世界为中心的一般方式的过程之间的界限”的尝试的时候,存在于他和戴维森之间的、就这些问题而言的僵持状态便最清晰地表现了出来。这种消除并不会给对语言的经验性探究提供什么立足点,因为它将使有关语言学习的理论变成乔姆斯基所谓“无所不包的理论(a theory of everything)”。他接着指出,“确切的结论”并不是我们必须抛弃可以卓有成效地加以研究的、关于语言的各种概念(诸如乔姆斯基本人那关于“某种生成语法程序的内在表象”的概念⑧),而是有关在由经验构成的现实世界之中进行成功沟通的论题极其复杂和含糊,因而不值得进行经验性探究的人们加以注意⑨。
乔姆斯基认为,戴维森所感到满足的那种关于儿童如何学习语言的常识性说明,对于各种科学研究意图来说并不能发挥什么作用,因为“对‘语言误用’的参照,对‘各种规范’的参照,对‘各种共同体’的参照等等……所要求的耐心细致都远多于实际上已经付出的。这些概念都含糊不清,人们并不清楚它们对于探讨语言和人类行为来说究竟有哪些益处”⑩。通过一系列诸如此类的论述,乔姆斯基表明,只有他自己才真正继承了卡尔纳普的衣钵。卡尔纳普也必定会发现“规范”这个概念是含糊不清的,因而并不适合于各种进行科学探究的意图。不过,对于维特根斯坦派学人来说,使一个概念变得清晰只不过是熟悉某种语言表达的用法而已。在他们看来,使用“社会规范的内化”和使用“有关某种生成性语法程序的内在表象”一样没有什么问题,甚至可能出现的问题更少。
从维特根斯坦派学人的视角出发来看,乔姆斯基和追随他的认知科学家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看起来与在路灯柱下面寻找其失落的钥匙的人的方法很相似——这样做不是因为他把钥匙丢在了附近,而是因为这里的光线更亮一些。乔姆斯基所谓“自然科学的立场”,只不过是在宏观行为的背后寻找各种微观机制的习惯而已。在这派学人看来,关于采用这种立场始终会有所收益的主张,看起来与卡尔纳普学派的独断论是非常相似的。
例如,可以考虑一下乔姆斯基的下列主张,即“对于所有各种语言来说,都始终”存在着“某种固定不变的、从生物学角度得到确定的、把可资利用的证据描绘成为既得知识的机能”(11)。人们很难认为这是一项经验研究的结果,因为他们几乎不可能想到可以用什么来证伪它。凡是能够学习语言的有机体都具有这种能力,因为它们无疑都具有不同于其他有机体的神经组织(neural layouts)。这些组织也确实是从生物学角度得到确定的。但是,一种机能从什么意义上说也可以如此得到确定呢?
所谓一种机制体现了一种机能只不过是说,人们可以根据某种可以详细说明的、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对这种机制的行为进行有益的描述。没有一个人能详细说明存在于由教授语言的成人提供的各种输入,和由学习语言的某个儿童提供的各种输出之间的任何诸如此类的关系,因为它们太复杂多变了。这可能与下列做法相似,即试图具体说明存在于一个人在学骑自行车时发生的各种事件,和那些作为熟练的自行车骑手所进行的各种行动而存在的事件之间的关系。
不过,乔姆斯基告诉我们有这样一种机能,它不是把各种输入描绘成为各种输出,而是把各种输入描绘成为某种被叫做“既得知识”的东西。那么好吧,自行车骑手也获得了某种知识。我们难道应当说,他之所以获得这种知识,是因为某种已经从生物学角度得到确定的机能,这种机能把他以前的、不断尝试和不断失败的骑车事件描绘成为一组内在表象,而拥有这组表象则是他近来获得这种能力的必要条件吗?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可以把什么看作是存在于这些学习事件和导致成功的骑车行为的行动之间、能够证明这样一种发挥中介作用的存在物(entity)确实存在的证据呢?
诸如此类的考虑不仅导致维特根斯坦把对于作为一门学科的心理学的怀疑作为其《哲学研究》的结尾,也导致赖尔以同样的怀疑作为其《心灵概念》的结尾。这两位哲学家都怀疑,假定在可以观察的行为和微观神经组织之间存在发挥中介作用的“各种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真实的状态”,就可以获得某种回报——这种能力方面的回报使我们能够预见并控制我们通过假定不可见的物理粒子而获得的东西。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认为“心理学可以像物理学论述存在于物理领域之中的过程那样,论述各种存在于心理领域的过程”的观念,是一种“使人误入歧途的类比”(12),而且,“心理学的混乱和贫瘠是不应当通过称它为一门‘年轻的科学’来加以说明的”(13)。对于当代认知科学来说,当前的维特根斯坦派学人也持有类似情绪。
说乔姆斯基派学人的语言学,以及其他一些使自己致力于成为“认知科学”之组成部分的学术专业,都是值得尊敬的学科,都是一些使非常睿智的人在其中进行精力充沛的相互辩论的论坛,这是一回事;而说这些学科都曾经对我们的知识做出过贡献则是另外一回事。许多同样值得尊敬的学科也曾经辉煌过,但在衰败之后却并没有留下这样的贡献。15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17世纪的赫尔墨斯神智学(hermeticism)以及20世纪的逻辑经验主义,都是一些广为人知的例子。
维特根斯坦派学人认为,认知科学究竟是一种成功的、能够名垂青史的、使自然科学的研究程序承担研究心理和语言之任务的尝试,还是另一种迄今为止仍然促使哲学走一条安全可靠的科学之路——和其他所有各种道路一样,这条道路也同样由于自身的负重而最终崩溃了——的尝试,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们所怀疑的是,认知科学也许永远都不可能通过化学脱离哲学的方式,通过展示它那派生出各种新技术的能力,而使自身摆脱哲学的束缚。狂热地鼓吹认知科学的学者们认为维特根斯坦派学人都是独断的行为主义者,而维特根斯坦派学人则使用与培根用来批判晚期经院哲学的术语完全相同的术语来批判乔姆斯基学派。他们用与培根考虑奥卡姆和司各脱的方式完全相同的方式来考虑乔姆斯基和福达:他们的所有各种美妙理论和精致论证,都不可能经受得住实践的检验。他们都是在建造空中楼阁。
二、构成性:福达对布兰登
福达试图通过下列论证来打破这种困境,即如果维特根斯坦派学人希望做到的并不只是提出与行为主义相似的偏见,那么。他们就必须提供某种属于他们自己的、关于语言发挥作用的方式的理论。他所怀疑的是,他们所能够提供的只不过是“语义学整体论”,只不过是认为“一种表达的意义是由它的所有各种推论关系构成的,因而是由它在语言中发挥的全部作用构成的”的学说而已(14)。
戴维森曾经潜在地提出过这种学说,而布兰登则把它明确地提了出来。由于对各种表达在语言中所发挥的作用的研究,也就是对乔姆斯基所谓的“在由经验构成的现实世界中进行的成功沟通”的研究,而且,由于整体论者们都无法轻而易举地把学习一种语言的过程与认识一个人以这个世界为中心的一般方式的过程区别开来,所以,这种研究将不可避免地变成被乔姆斯基轻蔑地称为“无所不包的理论”的东西。因此,语义学不可能是一种与化学有几分相似的学科,甚至有可能根本不是某种学科。戴维森和布兰登之所以没有为热衷于认知科学的年轻学者提供任何可供他们实施的研究纲领,乔姆斯基之所以认为这些人很像蓄意进行阻挠活动的勒德分子(obstructionist Luddites),原因就在于此。而且,布兰登之所以在坚持卡尔纳普以往区别语义学和语用学的过程中根本不得要领,原因也在于此(15)。
福达认为,可以对语义学整体论者做出某种断然的回答,从而使乔姆斯基派学人完全占领这个领域。这种回答就是语言是构成性的:“各种从句法角度来看复杂的表达所具有的意义,就是它们那与句法成分的意义共同存在的、句法结构所具有的功能。”(16) 因为“意义是构成性的,而各种推论作用却都不是构成性的,所以意义不可能是推论作用”(17)。福达对这个要点的详细说明如下:
“棕色乳牛”这个短语的意义……取决于与其句法共同存在的“棕色”和“乳牛”所具有的意义……但是现在,初看起来,棕色乳牛的推论作用不仅取决于“棕色”和“乳牛”所具有的推论作用,而且还取决于你们关于棕色乳牛而恰巧相信的东西。所以,一般说来,推论作用与意义不同,它不是构成性的(18)。
在论证过程的这个关节点上,维特根斯坦派学人可能会说,如果诸如意义这样的东西确实存在,那么语言就的确是构成性的,但是,蒯因和戴维森已经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他们认为,即使为了说明学习语言的有机体所具有的各种社会技能,也根本没有必要假定心理原子和被称为“意义”“概念”或者“表象”的语言原子之间存在着某些关系。认为存在着某种可以在对话流(conversational flux)内部检测到的、被称为“意义的同样性(sameness)”的特征,也就是坚持某种早在蒯因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对语言和事实的区分,而这种区分除了使认知科学家们忙忙碌碌之外,并不能发挥其他任何作用。
福达对这种维特根斯坦派学人的论证思路的描述是:
一面非常光滑、非常适合于移动的斜坡:只要滑到了坡底,人们就会发现自己接受了这样一些初看起来稀奇古怪的学说,诸如,从来就没有两个人分享过同一种信念,诸如翻译这样的关系根本不存在;从来就没有两个人用他们的话意指涉过同一个事物;同一个人也从未通过其两个时间片段(time slices)的表达意指过同一个事物;从来没有一个人能改变其心灵;从来都没有一个陈述或者信念会受到反驳(更不用说受到拒斥了);如此等等。怎样才能在不付出如此高昂代价的情况下得到推论角色语义学(inferential role semantics)的好处,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9)。
为了做出回应,维特根斯坦派学人提出了下列赖尔式的观点,亦即,即使无法具体说明有关同样性的各种标准,我们也可以把两个人描述成看到了同样的事物——例如,同一座建筑或者同一处景致。赖尔曾经指出,不仅某种可以使许多人看到同样的建筑、同样的景致的日常感觉(everyday sense)是存在的,而且,另一种同样有益的、使两个人不可能看到同样的建筑、同样的景致的感觉也是存在的。同样,有关“意指相同事物”和“相信相同事物”的日常感觉所发挥的效用,也不会使我们拒斥德斯康伯斯以赞赏的态度引用的萨特的下列观点:“无论我什么时候构造一个句子,其意义总是逃避我、被从我这里偷走;通过每一位说话者、在每一天,各种意义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发生了变化;我说的话的意义都被其他人改变了。”(20) 当布兰登说下面的话时,他也重复了这一点:“与你们所说的相比,我说的每个语词——‘狗’,‘愚蠢’,‘共和党人’——都具有不同的意味,因为在它可资利用的范围之内,并且由于我具有不同的附带信念,运用它所产生的各种结果对于我来说都不相同”(21)。
福达坚持认为,维特根斯坦派学人的阿基里斯之踵就是自然语言的生成特性(productivity),这是一种只能由构成性加以说明的特性。他把这种生成特性粗略界定为表达一组无限制的命题——有关潜在的无限长度的、形状优美的线索——的能力。不过,维特根斯坦派学人则会回答说,只有当我们已经把语言当作生成语法的机制来考虑时,我们才会认为它们具有某些诸如此类的能力。如果我们遵从戴维森对下列需要的否定,即对“为了挤压出随意说出的言词的意义而设立的、便捷的解释机器”的需要的否定,那么,我们就不会这样认为了。对于那些认为学习语言的过程是某种技能的人来说,福达所提到的无限的生成特性,似乎和熟练的自行车骑手能够扮演的、可能无限多的花样一样,都是无关紧要的。
福达指出:“生成特性就是当一个系统具有数目无限的、从句法和语义角度来看明确的符号时,这个系统所具有的特性。”(22) 但是,从维特根斯坦派学人的视角出发来看,这却是一个用来否认说自然语言的人所拥有的就是这样一个系统的充分理由。如果一个人从各种各样有机体进行的对话性交往中,抽象出某种抽象的、被称为“English”的存在物,那么,他就可以像福达那样说:“Ehglish包含着一个无限的非同义表达系列:‘导弹护盾’‘反导弹护盾’‘反-反导弹-护盾-护盾’……诸如此类。”但是,这又很像是说一个被称为“算术”的抽象存在物包含着这样一种无限系列。各种抽象存在物都能具有各种有机体所无法具有的特性。具体说来,它们可以包含数量无限多的各种事物。而诸如说英语或者骑自行车这样的技能则既不包含数量有限的事物,也不包含数量无限的事物。
三、确定的存在
福达用于系统表述这种发生在卡尔纳普派学人和维特根斯坦派学人之间的争论的另一种方式是,使认为“存在关于意义的各种事实,而且它们都是适合于进行科学探究的对象”的“意义实在论者”,与那些认为“意义产生于我们进行的解释性实践,所以,无论‘皮纳克尔’是什么意思,还是‘哈姆雷特’是什么意思,都必然只存在一种正确答案”的人形成对照。他指出,维特根斯坦派学人都认为:“试图得到一门关于意义的科学是愚蠢的;就像试图得到一门关于游戏的科学、或者试图得到一门关于星期二的科学一样。”(23)
福达对他所谓的“同情这种维特根斯坦-古德曼-库恩-德里达类型的描述”表示悔恨,并且祈求上帝“不要让从哈佛泄漏出来的任何毒雾漫过(原文如此)查尔斯家族而延伸到麻省理工学院”(24)。他把这种毒雾与他所谓的“语言学唯心论”(linguistic idealism)联系起来,并认为后者是由“诸如罗蒂、普特南、库恩,以及德里达”这样的哲学家创造的(25)。回顾一下赖尔所举的那些例子可见,这种类型的哲学家都认为,意义实在论和造型实在论(build realism)、景致实在论(outlook realism)一样,都是不得要领的。
蒯因之所以通过主张信念和意义根本不能符合物理主义的世界观,以哈佛为基地发动了对意义实在论的攻击,恰恰是因为,意向性归因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人们根本没有办法断定说同一句话的两个人所指的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事物,或者说根本没有办法断定他们究竟是不是持有共同的信念。从主张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存在物出发,蒯因得出了下列结论,即在任何一幅“描绘实在的真实的终极性结构”的图画之中,各种信念和意义都没有立锥之地。
福达争论说,由于各种信念和意义都需要人们赋予这样一种地位,而且,由于蒯因所谓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存在物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必须成为意义实在论者。相形之下,布兰登则既不认为有必要坚持认为“‘皮纳克尔’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有唯一正确的答案,也不认为有必要按照蒯因的做法去做,从缺乏这样一种答案推论出下列主张,即各种信念和意义在本体论上无论如何都不与电子和神经细胞等价。戴维森在《与墓志铭有关的严重精神错乱》一文中对语言能力的描述,是与布兰登的下列观点相一致的,即理解一个断言的内容,是一个确定它在某种特定的、有关询问理由和提供理由的游戏之中通常具有的位置的问题。对于这两位哲学家来说,进行明智的对话所需要的这种社会技能,并不要求运用各种有关信念或者意义的同样性的标准。
可以用下面的话来概括福达、蒯因和维特根斯坦派学人之间发生的三角辩论,即福达和蒯因都同意,唯一能够实际存在的是那些使各种不依赖于语境的标准得以存在的存在,而戴维森和布兰登则不这样认为。不过,由柯尼利乌斯·卡斯托里阿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以及最近由文森特·德斯康伯斯(Vincent Descombes)使用的专门术语,则提供了某种描述这种僵局的、更富有启发意义的方式。德斯康伯斯指出,卡斯托里阿迪斯批判了“哲学家们和所有那些(不知不觉地)受他们启发的人的棘手的偏见:所有各种实际存在的事物都是通过某种确定的形式存在的。所有各种存在的事物都是精确的、确定的和可以理解的。如果某种事物恰巧展示出不确定状态、惰性状态或者模糊状态,那么,这种事物——即使不完全是虚假的——就表明自身处于比较低级的地位”(26)。
在德斯康伯斯看来,福达、蒯因和认为存在物需要同一性的其他人所遇到的麻烦是,他们都经受不住他所谓“某种一般的形而上学的幻象”的诱惑。他指出,这样一种形而上学“将不得不研究统一性和多样性、统一和差异、个体和关系,而所有这些研究却没有对任何特定的范围加以考虑。具体说来,它将不得不表明,在把哲学探究分为包括自然本体论和心灵本体论在内的各种‘局部性本体论’之前,人们应当如何理解‘存在’和‘同一性’这些术语……(但是)如果人们不把其试图加以识别的事物类型考虑在内,那么,他们如何探究同一性的各种条件呢?”(27)
在这里,德斯康伯斯强调了一个布兰登也强调过的观点。德斯康伯斯指出:“‘事物’这个概念并不意味着被运用于计数过程之中。”布兰登指出:
确立某种同一性标准并不只是足以满足可计数性的要求;它也是必要的。未经分类的“事物”或者“对象”是不可能计数的。所谓这个房间里究竟有多少事物这样的问题根本没有答案;这里存在的是一定数量的图书、一定数量的分子、一定数量的原子、一定数量的亚原子粒子……计数只有通过参照某种分类概念才是可理解的(28)。
但是,只有经过分类才能计数这个事实,未必意味着所有分类都可以辨别不同组的可计数项。正像德斯康伯斯所指出的那样,一个人根本不知道如何回答“藉里柯的《美杜莎之筏》里有多少表象”这个问题,这个事实的存在并不是因为各种表象比其他事物更加模糊,而是因为没有经过分类的表象和没有经过分类的事物一样模糊。因此,德斯康伯斯指出,要想回答“有多少”的问题,“人们就必须能够把通过这幅绘画表现出来的事物列举出来”(29)。
他指出,同样的问题就大脑而言也存在。假如有一个相信大脑包含各种表象状态的人,希望把那些——通过与集中关注正在扑过来的食肉动物的眼睛联系起来的大脑视觉皮层表现出来的——表象列举出来。她所能够提供的数目将取决于她究竟把大脑当作表现各种色彩的机制来对待,还是当作表现各种色彩的阴影、表现各种色彩的模式、表现各种中等大小的物体、表现各种光波、表现环境的各种危险,或者表现视网膜的各种化学变化的机制来对待。说大脑是一种计算手段,并不能确定在许多输入-输出功能之中,这种手段被预定要执行的究竟是哪一种功能。有关它的环境和行为之可供选择的描述有多少,诸如此类的功能就有多少。成为一个意义实在论者,就要主张有一种这样的功能是正确的。不过,所谓经验性证据可以使人在所有这些描述中做出决定,是非常可疑的。这就像为了确定我的笔记本电脑目前究竟是在处理数据、语词,还是在处理思想,而收集各种经验性证据一样。
从德斯康伯斯和布兰登的角度出发来看,蒯因关于因为数量极多的翻译手册都会对行为方面的证据一视同仁,所以各种意义都具有次等的本体论地位的观点,与说因为数量极多的输入一输出功能都会对已经观察到的、存在于大脑视觉皮层和有机体的环境之中的各种事件的相互关系一视同仁,所以诸如视知觉这样的东西实际上并不存在,是非常相似的。只有在那些沉迷于德斯康伯斯所谓“某种一般的形而上学的幻象”的人那里,才会看到从可供选择的各种描述的存在推论出本体论的次等性的冲动。
因此,维特根斯坦派学人对蒯因关于翻译的不确定性学说所做出的回应,就是否认关于语言,或者更加一般地说,关于意向性之物,存在着某种特殊的疑难之处。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像乔姆斯基最先论证的那样,翻译的不确定性(或者意向性归因的不确定性)与理论的日常的、未被经验确定的状态,并没有令人关注的不同。这种未确定状态与人们熟悉的下列事实一样都没有什么令人困惑之处,亦即,即使你们发现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术语来描述同一部分时空很有用,你们也不可能从用一种术语系统表述的断言出发,直截了当地推论出用另一种术语系统表述的断言。因为假如这样的推论屡见不鲜,那么,这两种术语早就融合到一起了。
那些和我本人一样由于吸入了这种维特根斯坦-古德曼-库恩-德里达毒雾而获得刺激的哲学家,都声称完全知道究竟为什么用“rabbit(兔子)”翻译“Gavagai”(30)要比用“rabbit-stage(兔子的部分)”更好。我们确信这与检查两种被称为“意义”的存在物、列举其相似和不同之处无关。它与获得——受熟练运用两种语言的能力推动的——社会技能的相对容易有关。同样,我们能够理解有时候把有机体当作对通过视觉体现出来的、中等大小的物体做出反应来处理,有时候把它当作对审美价值做出反应来处理,有时候把它当作对各种光波做出反应来处理这样一些做法的用处,而根本不担心它“实际上”是对什么做出反应。在我们看来,这里的后一个问题就像关于《哈姆雷特》实际上论述的是什么、关于(作为儿童骂人的话的)“傻瓜温尼”的主题究竟是不是“真的”、关于低劣的文学作品是不是具有自毁特征,或者关于晚期资本主义会不会崩溃的问题那样,都是非常拙劣的(31)。可用来描述电脑的同一种状态的输入-输出功能的多样性,是与弗里德里克·克鲁斯(Frederick Crews)把A·A·米尔恩(Milne)的本文插入其中的各种语境的多样性非常相似的。
即使认知科学家开始同意在对这种功能进行选择时所依据的标准,这大概也是因为他们都认为,这样一种选择可以使他们那对人类和动物行为进行预测和控制的学科得到最充分的保护。不过,维特根斯坦派学人却怀疑他们究竟是不是能够达成这样的一致意见。他们之所以对采纳乔姆斯基所谓的“自然科学的标准方法”、对把各种语义特性归因于大脑状态犹豫不决,是因为他们都怀疑这样的做法对于各种预测和控制来说究竟是不是有用。争论的焦点既不是本体论方面的,也不是方法论方面的,而是实践方面的。你们都不会只通过进行实验并系统表述那些用于解释其结果的假说,就断言一门自然科学具有各种特权地位。即使炼金术士们也可能做到这一点。要想使这样一种科学得到承认,你们就必须对培根所谓的“人类生存状况的改善”做出某些更加具体的贡献。
维特根斯坦派学人所怀疑的是,假定“对于所有各种语言来说,都始终存在着某种固定不变的、从生物学角度得到确定的、把可资利用的证据描绘成为既得知识的机能”,究竟是否能够使我们更快地学习更多的语言,或者说,这种假定是否特别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有些人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另一方面,他们非常希望做出下列预测,即将来有一天,我们开发神经元的所有潜能的能力会使教学法和治疗法都得到极大的改进。因为维特根斯坦派学人和卡尔纳普派学人一样,都是出色的物理主义者(physicalists)。他们也同样确信下列观点,即只要不以某种方式、在某个地方改变一个人的大脑状态,你们就不可能改变她的心理状态。他们所怀疑的,只是在平民心理学和神经病学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有益的探究层次——亦即,对“从心理角度来看真实的”东西的发现,究竟是否能促进有益的潜能开发。
四、德斯康伯斯论心灵的定位
德斯康伯斯对目前这场争论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把它与下列事实联系了起来,即早在计算机革命出现很久以前,哲学家们就开始对心灵究竟是一种什么事物,以及更加确切地说,对心灵究竟存在于何处,众说纷纭了。德斯康伯斯指出,这些哲学家在心灵究竟“存在于内部还是外部”这个问题上分道扬镳了:
根据笛卡尔、洛克、休谟和迈内·德·布里安(Maine de Brian)的精神第一论(mentalist)后裔的观点来看,心灵存在于内部,人们还可以把现象学家和认知主义者也包含在这些人之中;而根据那些论述客观精神和公众对指号的用法的哲学家的观点,比如说,根据皮尔士和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来看,心灵则存在于外部(32)。
这种存在于作为一方面的笛卡尔、洛克、休谟,和作为另一方面的皮尔士、维特根斯坦之间的对照,突出展示了德斯康伯斯和布兰登的另一种相似之处。布兰登认为,维特根斯坦是他本人对语言和心灵进行的所谓“社会实践”的推论主义(inferentialist)探讨的先驱,并认为这种探讨是与洛克和休谟的表象主义相对立的。在有关哪些哲学家是可靠的盟友这一点上,他和德斯康伯斯也持大致相同的意见。
德斯康伯斯和布兰登的研究策略的最大不同是,德斯康伯斯通过运用其内在论-外在论区分方法,把已经过世的大哲学家们分成了好人和坏人。他指出,《心灵的储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外在论辩护——通过主张由于思想存在于头脑之中所以是心理的,而存在于外部的一本书则完全是物理的,表明内在论(也以“关于主体的经典性哲学”为人所知)是错误的。一本书就像一个民族那样,可以认为相当于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精神,它们都是有关皮尔士称为“某种指号”的东西的例子。
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使德斯康伯斯在其著作的最后一章中得出了下列结论,亦即,即使认知科学的确超越了竭力鼓吹的阶段,它也仍然“无法告诉我们关于心灵的观点,亦即无法告诉我们关于各种思想的观点”。德斯康伯斯指出,这种无能为力的原因在于,“关于心理的术语具有深刻的历史性,是指出意义具有各种历史条件的另一种方式。主体的语言和思想具有下列意义,即它们在他的世界之中必然是既定的,因而不可能从这个世界之中分离出来……这个为了理解主体所思考的东西而必须加以认识的世界并不仅仅是自然的世界……(它)是一个文化的世界,是一个包含着诸如日历、金钱、银行,以及国际象棋游戏这样一些制度的世界”(33)。
我认为,即使德斯康伯斯并不要求我们选择在这种内在论-外在论问题上究竟站在哪一边,他也是建议我们把“心灵”看作是一个既用于描述某种内在之物(无论每一个成年人所拥有的这种东西是什么,它都能够使之参与诸如玩国际象棋和在银行存款这样独具特色的人类活动),也用于描述某种外在之物,亦即用于描述这些活动的集合。人们可以非常有益地把这种集合描述成“客观精神”,或者更简单地描述成“文化”,不过在我看来,把它称为“心灵”也未必会出现悖论。
德斯康伯斯的主要观点是,对大脑的了解未必有助于我们理解有关文化的东西,反之亦然。这个论题既真实又重要。的确,卡尔纳普[以及近来的E·O·威尔森(Wilson)和其他社会学家]希望有朝一日将会出现的那种“知识统一体”,是不大可能出现的。不过,我更愿意通过下列观点来回避德斯康伯斯关于“心灵的定位之处在哪里?”的问题,即这个术语以令人困惑的方式指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其中一方是类人猿大脑的硬件(hard-wiring),另一方则是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一组社会技能。从唯我论的、笛卡尔的、内在于大脑之中的意义上说,“心灵”的确就像认知科学家们所坚持的那样是大脑。而在客观精神的意义上、在书籍和印刷品都是精神的存在物的意义上说,“心灵”则显然不是大脑。它是一个使我们得以在其中找到日历和国际象棋棋局的社会世界。
这种把心灵一分为二并给予每一半相应权利的、非常明智的策略,似乎是一种用来处理当前正在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之中流行的各种争论的、过于匆忙和卑劣的方式。不过,我希望通过表明这种存在于大脑和文化之间的区分,与存在于硬件和软件之间的区分有多么相似,把这种做法的各种优点具体表现出来。
五、大脑是硬件,文化是软件
为了具体表明这种区分所具有的关联,让我们考虑一下下列虚构场景:在24世纪,每个人都有一台按照今天的型号生产的电脑,就像这些型号都是按照巴贝奇(Bahhage)的计算机生产的那样。每个人的电脑都完全是以同一种模型为基础的,都是对两百年以前出现的原型的精确复制,这种模型已经得到了数量极大的自动复制,因而此后以极低的价格就可以买到。如果你的电脑开始出毛病,你可以扔掉它,再买一台与它完全一样的新电脑。由于制造商的垄断性贪婪,如果你试图打开你的电脑,它就会自毁;如果你试图进入机器人集成生产线,机器人就会杀掉你。虽然软件每年都会变得越来越好,硬件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没有一个置身于24世纪的人会想电脑究竟是如何工作的、会考虑这些黑匣子里面运行的是什么。
但是,人们有一天终于明白,这种自毁机制在近来生产的绝大多数电脑中都不再起作用了。所以,他们开始把电脑拆开并进行反向操作。他们发现,电脑的所有工作都是通过1和0来完成的。至关重要的诀窍是各种编码指令和数据都采取了二元数字的形式。接下来,他们对组成电脑操作系统的不同层次的编码语言进行解构。现在,他们宣布,有关这种新发明如何运作的谜已经解开了:我们已经知道了关于硬件所应当知道的一切。然而,这种知识在人们开发新软件时是否发挥某些作用,却仍然有待于观察。
我所要进行的类比是显而易见的。文化指的是软件,而大脑指的则是硬件。大脑长期以来一直是某种黑匣子,但借助于纳米技术,我们也许有一天能够以一个神经细胞轴索、又一个神经细胞轴索的方式把它拆开,然后说:“噢,这里的诀窍原来是……”这种发现很可能导致新的教学方法和治疗方法的出现。不过,人们根本不清楚它对“知识统一体”究竟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大脑通过编码就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就像在我所虚拟的场景中,电脑使用者都知道他们的电脑能做什么那样。对大脑的微观结构细节的不断发现,也许能也许不能使我们做某些与我们以前所做的事情不同的事情,就像有关硬件设计的更多信息也许能也许不能促进经过改善的软件生产那样。不过,无论能还是不能,人们都难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应当以某种新的方式开始理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
认为自然—精神(Natur-Geist)二分法仍将像以往那样具有重要意义,主要是因为意向性归因具有整体主义色彩:人们无法以这样一种与神经状态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方式使各种信念个体化。戴维森、阿瑟·柯林斯(Arthur Collins)、林·贝克尔(Lynn Baker)以及海伦·斯图尔特(Helen Steward)和其他一些人,都提供了为这个论题辩护的令人信服的论断。他们已经表明我们究竟为什么不能指望把各种信念描绘到神经状态之上,尽管这样的描绘过程可能会,比如说,有助于各种心理意象,或者有助于欲望的高涨。如果就信念的变化如何与神经病学方面的机制联系起来而言,人们根本不能发现任何有意义的东西,那么,他们就很难理解,怎样才能期望对乔姆斯基称为“大脑/心灵”的东西的研究与文化研究发生相互作用了。
这种观点可以帮助人们看到乔姆斯基所做的与化学的类比究竟出了什么问题。道尔顿和门捷列夫有助于我们理解宏观结构是如何与微观结构组合到一起的。由这些宏观-微观相互关系带来的兴高采烈,导致了卡尔纳普的“科学统一体”的萌芽。但是,硬件-软件和大脑-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宏观-微观之间的关系。它们都是有关某种工具与其各种用法之间关系的例子。
人们有的时候提出,可以把有关大脑运作方式的发现与进化论生物学联系起来,从而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大脑已经适合于做什么,并由此而更加充分地理解“人的本性”。不过,这种对生物进化和软件开发的类比表明,大脑当初已经适合于做的事情,很可能与人们目前让它做的事情毫不相干。软件的第一批突破性进展是在导弹定位、信息搜寻和纠正领域之中出现的,这个事实并没有就今天的电脑的长处是什么告诉我们任何具体的东西。同样,有关人脑进化的某些早期阶段受狩猎-采集的需要支配的事实,也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与因此而出现的产物有关的东西。
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告诉我们:“心灵是一种由自然选择过程设计、由各种计算器官组成的系统,其目的是解决我们的祖先在搜寻食物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34) 大概德斯康伯斯对此也会回答说,这一点对于大脑来说是对的,但对于心灵来说却是不对的。然而,我所要强调的却是,即使我们用“大脑”代替作为主语的“心灵”,平克的这句话也会使人误解。由于与说“我那只用于文字处理的笔记本电脑是以跟踪导弹和搜索数据库为目的而设计的会使人误解”的原因相同的原因,平克这句话也会使人误解。有关工具的最初设计者之想法的说明,与我们使用这些工具的方法并没有多少区别。
这种实用主义态度,也就是维特根斯坦派学人在面对诸如平克和威尔森的著作这样的书的时候所采取的态度——这些著作告诉我们,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和进化论生物学都图谋改变人类的自我形象。这些著作告诉我们,我们以前认为是文化的东西将会被事实证明是生物的。但是,只有当我们开始认为进化所创造的,是某种不幸无法以某种方式对其进行编码的大脑——这种大脑的建构方式使它根本无法实现某些输入-输出功能——的时候,这种主张才听起来令人信服。承认生物方面具有霸权地位,就会承认人们不应当进行某种表面看来大有希望的文化创新,因为生物学已经堵塞了这种创新的道路。
难以想象为这种堵塞进行的辩护究竟是什么样子。因为它很可能相当于说:根本不要试图以人们建议的方式对我们的社会实践加以修正,因为我们已经预先知道这种修正根本不发挥什么作用。我们知道不应当进行这样的试验,是因为它注定要失败。这可能相当于说,“不要再尝试使劣金属嬗变成黄金,因为道尔顿和门捷列夫已经表明了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出现的原因”。不过,诸如平克和威尔森这样的认知科学家能够用来维护这样一种禁令的唯一方式,大概就是基于生理学方面的理由表明,人们不能坚持某种信念或者不能拥有某种欲望。这一点之所以很难做到,既是因为我前面提到的、那些不承认有可能在大脑中为意向性状态定位的哲学论断,也是因为如果人们真的永远不可能拥有某种信念,那么,也就不会有一个人能够提议对它加以宣传了。
六、语义学整体主义、历史主义和语言学唯心论
到此为止,关于我所主张的、使大脑与文化相关就像使硬件和软件相关那样困难,已经讲得够多了。我将以评论德斯康伯斯、布兰登和“语言学唯心论”的其他一些拥护者共同具有的历史主义的重要意义作为结束——在这种哲学观看来,福达的名字处于那种非常光滑、使语义学整体主义者在上面往下滑的斜坡的底部。
德斯康伯斯的论题“关于心理的术语具有深刻的历史性,是指出意义具有各种历史条件的另一种方式”,与布兰登关于概念的内容通过历史过程才会——以黑格尔所说的方式,即以萌芽通过花朵、花朵通过果实而明确表现出来的方式——明确表现出来的观点非常相似。语义学整体主义告诉我们,各种推论关系变了,意义或者内容也会发生变化。而历史告诉我们的则是,至少就大多数令人感兴趣的概念而言,这些关系近来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布兰登认为,黑格尔把概念当作能够不断成熟的亚人格(quasi-persons)来处理的做法——亦即使用语词的方法——是正确的。
诸如福达和乔姆斯基这样的表象主义者都认为,语义学整体主义导致其拥护者失去了与实在的联系。由于这两个人都受到了德斯康伯斯所谓“某种一般的形而上学的幻象”的支配,所以,他们都认为,这个世界是固定不变的,而人们通过拥有越来越多关于真实事物的表象,通过拥有越来越少关于虚假事物的表象,就可以越来越充分地表现它。因此,当发现德斯康伯斯说“为了认识到主体所思考的并不仅仅是自然界,就必须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就忍不住了。这是因为,正像通过其用法在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多少变化的术语——诸如“棕色”“乳牛”“和”“与”“红色”以及“黄色”这样的语词——表达出来的那样,认知科学家们所研究的、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都是借助环境进行的。他们感兴趣的是我们的儿童与黑猩猩的共同点是什么,而不是这样的儿童与柏拉图的共同点是什么(35)。
从语言学唯心论的观点出发来看,如果你们想象一头黑猩猩具有信念并使之通过语词表达出来,那么,牠将要谈论的就是自然。文化则是我们一直怀疑黑猩猩会对其具有某些看法的论题的总和。用另一种同样粗略的方式来说:自然就是运用其用法在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的语词来描述的东西,而文化则是用那些其用法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语词来描述的东西——这种区别的确是程度上的,不过也是非常重要的。虽然由于为了进行隔代对话而复活的柏拉图,有可能迅速了解“和”指的是kai、“乳牛”指的是bous,但是,他很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理解为什么“原子”指的不是atomon,而且“城市”“民族”和“国家”指的都不是polis。
七、结论
我一直在论证的是,只有当一个人受德斯康伯斯所谓“某种一般的形而上学的幻象”支配时,他才会宁愿要表象主义而不要推论主义,宁愿要意义实在论而不要语言学唯心论,或者宁愿要卡尔纳普而不要维特根斯坦。因为他在这种情况下会认为,一种描述事物真实存在方式的词汇是存在的,而把真理归因于我们的信念则意味着下列主张,即展现各种心理表象的方式是与展现事物真实存在的方式同形同构的。那些被福达称为“语言学唯心论者”的人都强调,我们必须放弃对这样一种同形同构的寻求。
把“心灵”这个术语的运用范围分解为那些希望采用乔姆斯基所谓“自然科学的标准方法”的人研究的领域,和不希望采用这种方法的人研究的领域,也许会把这种争论再推进一步。因为正像大脑在一种明显的意义上是一团无法观察和不断旋转的粒子、在另一种明显的意义上并非如此那样,心灵也在一种明显的意义上是大脑,在另一种明显的意义上并非大脑。根据我已经论证过的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来看,人们所需要做的既不是还原,也不是综合,而只能是消除歧义。
如果我们把知识的统一体看作是人们为了互不干涉而使用不同词汇的能力,而不是看作以单一的共同观点看待他们的活动的能力,那么,我们就不会再受形而上学的一般幻象诱惑了。这种幻象就像观念的观念那样,都产生于追求这样一种景象的欲望。但是,如果我们采纳德斯康伯斯关于使我们自己局限于局部本体论的建议,如果我们把布兰登关于“存在物”和“同一性”都是分类概念的主张贯彻到底,那么,这种欲望就会被削弱。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用有关自然科学在文化之中的地位的问题,来代替有关意向性在粒子世界之中的地位的问题。哲学便与其说是发现各种事物如何结合起来的问题,不如说是建议各种社会实践怎样才能和平共处的问题。
霍桂桓,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与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主要从事西方哲学、文化哲学研究。
注释:
① Jerry Fodor,Psychosemantics(《心理语义学》),Cambridge,Mass.,1989,p.18.
② Donald Davidson,“A nice derangement of epitaphs”(与墓志铭有关的严重精神错乱),该文载Truth and interpretation:perspectives on the philosophy of Donald Davidson(《真理和解释:探讨唐纳德·戴维森哲学的各种视角》),ed.Ernest Lepore,Blackwell,1986,p.438.
③④⑥⑦⑧⑨⑩(11) Noam Chomsky,New horizon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mind(《语言和心理研究的新视界》,以下简称《新视界》),Cambridge,2000,p.56.p60.p47.p56.p69.p70.p72.p53.
⑤ 关于这种对比,参见《新视界》,p.50.
(12)(13) Ludwig 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哲学研究》),I.sec.571.232.
(14) Fodor,“Why meaning(probably)isn't conceptual role”(“意义为什么(或许)不是概念的作用?”),该文载Mental representations(《心理表象》),ed.,Stephen P.Stich and Ted A.Warfield,Blackwell,1994,p.153.
(15)(16)(17)(18)(19)(28)(32)(33) See 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使之明确》),p.592.p146.p147.pp147-148.p143.p438.p2.p244.
(20)(26)(27)(29) Vincent Descombes,The mind's provisions(《心灵的储备》),Princeton,2001,p.247.p240.p241.p241.
(21) Robert 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使之明确》),P.587.也可参见p.509:“……一个人所说出的一个语句,通常并不一定具有与另一个人说出的这同一个语句相同的意味,即使当存在对这种语言的足够多的共享、存在人们所希望的足够多的相互理解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正像我下面将要评论的那样,与其说布兰登和德斯康伯斯把各种概念当成了原子,还不如说当成了人,因为它们所具有的是历史而不是本性。
[22]Fodor.The compositionality papers(《构成性论集》),Oxford,2002,p.1.
(23) Fodor,“A science of Tuesdays”(一门关于星期二的科学),该文载London review of books(《伦敦书评》),20 July 2000,p.22.
(24) Fodor,“It's all in the mind”(一切尽在心灵之中),该文载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时代文学增刊》),23 June 2000.
(25) Fodor,The compositionality papers(《构成性论集》),pp.22-23.
(30) 此词系W·V·蒯因用来表示其虚拟的一个原始部落中人奔跑时发出的声音,旨在说明翻译的不确定性;参见其著作Word and Object(《语词与对象》),The MIT Press,1960.,第二章。
(31) See Frederick Crows,Postmodern Pooh(《后现代傻瓜》),New York,2001.
(34) Pinker,How the mind works(《心灵如何工作》),New York,1999,p.21.
(35) 考虑一下平克的下列观点,即“当哈姆雷特说‘人是一件什么样的作品’的时候……我们所应当注意的不是莎士比亚、莫扎特、爱因斯坦,或者卡里姆·阿卜杜勒-贾巴尔,而是一个4岁大、正在按照要求把一个玩具放到架子上的儿童。”[How the mind works(《心灵如何工作》),p.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