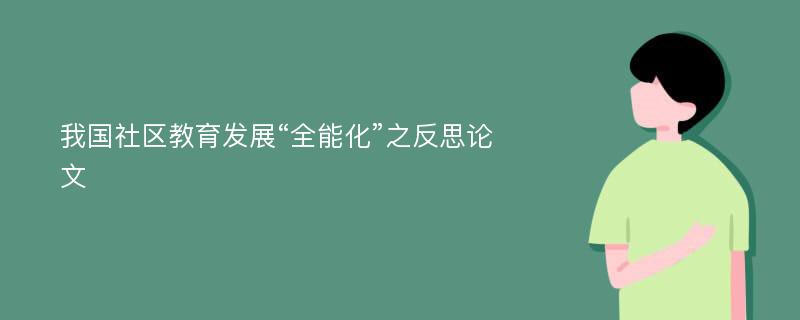
我国社区教育发展“全能化”之反思
马 莹,邢 悦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天津 300350)
【摘 要 】“全能型”社区建设思维、叠加式引入国外社区教育经验以及学校教育经费不足与利益共同体的形成直接导致了社区教育“全能化”倾向的形成。社区教育的“全能化”看似提升了社区教育在终身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实际上阻碍了社区教育本质作用的发挥。因此,需要从社区教育本质、职能以及主体三个方面进行反思,回归社区教育应有的本源。
【关键词 】社区教育;“全能化”;原因;反思
社区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来的时候,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教育形态,而是作为中小学德育教育的辅助体系。后来,随着社区教育职能、范围以及主体的扩大,其在终身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日渐重要,进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教育形态。也正是因为社区教育在终身教育体系中地位的改变,加上各级政府的政策引导,逐渐使得社区教育走向了一种“全能化”的教育模式。社区教育发展的“全能化”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其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但也模糊了社区教育应有的职能定位以及发展方向。“全能化”教育看似是一种理想状态,但实际上会影响社区教育职能的发挥,不利于其在终身教育体系中的定位。因此,应该对其“全能化”状态进行反思,探寻社区教育发展的正确路径。
一 、我国社区教育 “全能化 ”的发展历程
我国社区教育最初是作为中小学德育教育的辅助体系而提出的。可以说,社区教育在设计与构想之时并没有形成“全能化”的思想,社区教育全能化的出现是各级政府政策引导与推动的结果,是被动产生的。[1]在推进社区教育“全能化”的过程中,其动力源自于国家提出的终身教育体系构建以及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战略。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99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的《面向21世纪振兴教育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该文件指出,要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进社区教育实验以及试点工作,建设社区教育示范区,通过推进社区教育发展来完善终身教育体系,进而满足人民群众终身学习的要求。当国家政策明确了社区教育的历史定位之后,各级政府纷纷响应,进一步明确了社区教育在终身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2001年6月,北京市率先响应国家政策对社区教育的定位,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教育的意见》,该意见是我国第一个地方政府对社区教育定位的政策,明确要求北京市社区教育发展必须与城市体制建设与社区规划进行结合,充分利用北京市各级各类学校的优秀教育资源,在3—5年的时间内建立起包括学前教育、基础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技能教育以及社会文化教育在内的面向社区全体民众的社区教育体系,进而明确了社区教育的范围。客观看,北京市教委出台的这个政策,将社区教育的范围进行了充分的扩大,并将其与基础教育、学前教育进行对接,使社区教育初步具有了“全能化”的苗头。2001年9月,上海市教委、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上海市民政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本市社区教育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指出,社区教育机构除了要重视国民教育之外,还必须将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进行结合,按照市民的实际需求,强化法律政策、思想道德、科技文化、体育娱乐、家政服务、医疗健康、心理生理、老年文化等教育内容。上海市关于社区教育的政策进一步拓宽了社区教育的范畴,推动了社区教育“全能化”的发展。
2011年11月,教育部联合中央精神文明办、民政部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会议肯定了全国各地开展社区教育所取得的成就,总结了相关经验,确立了上海市宝山区、长沙市岳麓区等28个基层行政区的部分社区成为首批社区教育实验区。2017年,实验区已经发展到第六批,涵盖了全国210多个基层行政区域的680多个社区。[2]2017年12月,教育部办公厅正式印发了《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工作经验交流会会议纪要》(下称《会议纪要》),在这个文件中,正式明确了我国社区教育的两项主要职能:第一,立足于本社区居民技能、文化、精神以及生活多方面的需要,结合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来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区教育与培训活动;第二,组织社区民众建立学习型组织,完善社区教育的网络体系,扩大全国范围的社区教育经验交流。从教育部的这个文件可以看到,国家政策完全肯定了社区教育“全能化”的趋向,也凸显了国家政策对社区教育职能广泛性的认知与期待。
2004年12月,教育部在总结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关于推进社区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这一政策文件是我国社区教育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政策文件之一,对社区教育的内涵、职能进行了全面的定位,明确了社区教育的办学模式、办学原则、功能定位、目标任务、实施方式以及保障体系,对促进社区教育在全国范围的全面开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此外,《意见》还明确了我国社区教育十年内的发展目标,提出到2014年使得社区居民每年参与各类培训的比率不低于80%;并明确要求社区教育建设的师资标准,建立一支专兼职教师相结合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意见》通过对社区教育机构师资、课程等方面的具体规定,为社区教育的“学校化”、实体化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间接推动了社区教育发展的“全能化”。同时,《意见》中还明确了各级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在社区教育发展中的权力范围,要求各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定期对社区教育工作开展检查与评估。此项规定对于推动社区教育的发展具有正面作用,但同时也突出了各级政府教育部门以及社区教育领导机构在社区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区民众在社区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至此,基于各级政府政策推动的“全能化”社区教育模式完全确立。
党的十六大提出建立学习型社会以来,社区教育就被视为学习型社会构建的基础,也是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基石。2010年教育部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以及2012年发布的《关于加快继续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均将社区教育定位为学习型社会建设与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一部分,成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的基本战略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在解决了经济需求之后,人们对精神文化以及相应教育产品的需求也在逐渐加大。面对社会形势及民众教育需求的改变,社区教育的职能定位与目标任务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适时地成为推进社会大众终身学习的方式,其首要任务是满足社区民众日渐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3]
荥经黑砂的前世是陶器,经历了陶、砂陶、黑砂三个阶段,与青铜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经过几千年的沉淀,荥经黑砂在制作工艺上与陶器已经大相径庭,自成一派。但也存在量产能力低,古老技艺传承难等发展瓶颈。笔者认为荥经黑砂要以文化传播为核心,借助互联网、博览会,让黑砂文化走向世界。
(3)湿润烧伤膏商品名为美宝湿润烧伤膏,是中药制剂,为浅棕黄色至深棕黄色的软膏,具麻油香气,其主要成分是黄连、黄柏、黄芩、地龙、罂粟壳。主要作用为清热解毒、止痛、生肌,常规用于各种烧、烫、灼伤。中医认为化疗性静脉炎是指输液过程中的穿刺和留置针致局部脉络血行不畅,血瘀阻滞,不通则痛;气血不畅,津液输布受阻肿胀,瘀血内蕴,蕴久化热,则局部发热;脉络损伤,血溢肌肤或血热内蕴则局部发红,其发热机理为气滞血瘀,毒结凝滞于血脉致局部脉络、气血运行不畅,治疗应以清湿热、活血化瘀、散结止痛为主。故我科扩大湿润烧伤膏的应用范围,将其与喜辽妥软膏交替外敷,用于化疗性静脉炎的预防和治疗,取得了显著效果。
二 、我国社区教育 “全能化 ”现象的原因分析
1.全能型社区建设思维推动了社区教育的“全能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计划体制开始解体,单位体制也随之解体,原来由单位承担的社会管理、服务以及社会保障的职能开始从政府主导、单位主导体制下分离,社区开始担负起这些职能。随着社区职能的扩大,国家对社区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是因为计划体制与单位体制的解体,才为社区建设及其功能的发挥提供了条件。
1.2方法 对照组:采用颅脑损伤后常规护理措施:抬高床头,卧三马气垫床,垫软枕,翻身拍背1/2h。实验组:在其基础上采取全面护理包括加强护士对压疮知识学习,病因预防,患者及家属的宣教,弹性排班及护理模式,头部压疮危险因素评估,卧位护理,病情观察,发热护理等。
N为数字低通滤波器中截止频率的调节信号,即设计的数字低通滤波器只需调节整个算法程序中的N值即可实现不同带宽的低通滤波器。
当然,对于社区教育机构而言,其经费同样是短缺的。《若干意见》中指出,社区教育经费的筹措,必须发挥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建立政府投入为主,社会、社区、个人分担的经费筹措机制。而社区教育对象是复杂的、多元的,导致了社区教育产品也必须是多元的、多层次性的,由此进一步加剧了其经费的短缺。经费的短缺,使得社区教育机构无法聘请正规学校的教师来为学习者打造个性化课程或学习模块。正因如此,部分地区的社区教育机构开始建立学校教育体制,打造社区教育实体,如上海市从2001年就陆续在全市建立了200多个社区学校,并有自己的专职教师团队。当社区教育开始走向实体化、学校化,加上其教育需求的多样化,其走向“全能化”自然不可避免。
2.对国外社区教育经验“大而全”的引进助推了社区教育的“全能化”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社区教育概念以来,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我国极为重视借鉴国外社区教育的经验及发展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按照三级行政区划设置了三级社区教育架构。在区县一级设立社区教育学院或社区教育中心,在街道或乡镇一级设立社区教育学院分院或社区学校,在居委会、村委会一级设立社区教育教学点。其中,区县一级的社区教育学院,在办学过程中既能够为社区民众提供学历教育,还能够为其非学历培训服务。这一级的社区教育学院具备独立的办学场所与条件,在部分没有独立办学条件的情况下,与区县一级的职业学校、成人学校、职工大学、电大等在一起办学,如此一来,职业教育、远程教育、成人教育、技能培训等就成为社区教育学院的主导业务,除了这些教育服务之外,还针对具体的培训项目开展教育培训,如各类资格培训、文化培训、涉外培训等。[5]由此,在客观上推动了社区教育学院的综合化与全能化。在街道或乡镇一级的社区教育分校或分院,通常并无独立的办学场所,往往是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点承办各类学历教育项目与非学历培新项目,同时还按照街道办、乡镇政府的要求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的相关活动,该级机构起到了一定的承上启下的作用。社区教育教学点是真正立足于基层与社区的教育机构,通常设在居委会或村委会中,其开展的文化教育活动与居民生活、技能培训、文化娱乐等密切相关。综观三级办学体制,只有真正的基层教学点立足于社区且紧贴社区民众生活。
2000年11月,民政部在总结了全国26个城市社区建设实验区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该意见对社区有了明确的界定,认为社区是一定地域范围内人们组成的共同社会生活体,城市社区的范围是在单位体制改革后的居委会辖区。从这个政策文件看,社区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其管辖权归属于居委会,居委会实际上是代表社区来行使管理职能的。居委会是街道办的派出机构,而街道办同时是城市基层政府的派出机构。居委会是城市基层政府的授权组织,属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但其职能管理是属于政府行为而并不是居民自治。在我国政府全能型的管理体制下,其授权的居委会管理的社区,必然也是一种基于政府管理而形成的全能型社区。2006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强与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下称《工作的意见》)中指出,社区是代替政府行使“一站式”服务的基层组织,在社区居民就业、社保、救助救济、计划生育、卫生健康、流动人口管理、文化体育、教育服务、安全保障等方面需要发挥主导作用。2007年,教育部、民政部联合发布了《“十一五”社区服务体系发展规划》,该文件进一步扩大了社区的职能,要求社区在便民服务、老年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在研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城市精明增长与蔓延发展的关系时,不可割裂看待精明增长与城市蔓延,这两者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阶段,有相互交织、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各地城市发展都有一定的意义。
从我国社区教育三级办学体制可以看到,其在运行过程中借鉴了美国社区学院、日本公民馆等模式。但在引进国外经验的过程中,必须要认知社区教育的本质,美国社区学院、日本公民馆均只有一级模式,直接面向社区大众。我国这种三级叠加式的建设模式,是一种“大而全”模式,不仅层级多,而且教育内容庞杂,进而在客观上也加速了社区教育朝着“全能化”的方向发展。
3.教育经费的不足以及社区利益的分割也助推了社区教育的“全能化”
社区教育的“全能化”,看似提升了其在终身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实际上是扼杀了社区教育的本质,阻碍了其应有作用的发挥。因此,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与建立学习型社会的今天,必须要对社区教育的“全能化”倾向进行反思,回归到社区教育应有的本源。
社区职能是全能性的,服务于社区职能的社区教育其功能自然也是全能的。社区教育被当成是社区建设的一部分而纳入到各级政府社区建设政策及发展规划中,社区建设的政策实际上就是社区教育发展的政策。在政府政策助推下,社区教育的“全能化”现象就此产生。
三 、我国社区教育发展 “全能化 ”现象的反思
从理论上看,教育产品应该是一种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教育具有公益属性。但在市场体制下,市场经济对学校教育的影响是难免的,进而也就强化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投入-产出”意识,也就推进了学校利益共同体的产生。[6]正因如此,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职能向社区教育延伸,在一定程度上损失了学校的经济利益。这就使得各级各类学校只有在假期或空余时间才将其教学设施或场所向社区教育开放,为社区教育的学习者提供一些免费的课程或学习资源,在教师派遣方面,也只能是少量派遣,部分地区社区教育的师资只能依赖于志愿者。这一点在社区教育基层教学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为了在最短时间内提升教学效益,社区教育不能不将其需要传递的教学内容全部纳入到这一环境体系下,间接推进了社区教育发展的“全能化”。
1.社区教育本质的反思
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将学校之外的各类社区资源作为中小学德育教育的辅助体系。1999年的《行动计划》对社区教育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认为社区教育是一种面向全体社区成员,致力于提升社区民众生活质量及综合素质的社会教育实践活动。但这种内涵界定与社区教育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并不吻合。如果按照《行动计划》中对社区教育的界定,社区教育是一种社会教育,应该完全归属于教育部门管理。但如今,除了教育部门之外,精神文明建设部门、党委宣传部门、民政部门均可以参与社区教育管理,实际上将社区教育作为社区工作的一部分,甚至认为社区教育就是社区工作,社区教育发展不仅偏离了其应有的路径,更是加大了社区教育的负担。
因此,要厘清社区教育的本质,还必须从社区教育的官方定义中着手解决。客观而言,教育部当年在界定社区教育定义的过程中,还是受到了社区建设“全能化”思想的影响,将原本部分属于社区工作的职能强加在社区教育的头上。[7]即认为社区教育应该担负起提升社区民众生活质量、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职能,影响了社区教育应有的定位。更重要的是,这种内涵界定使得社区教育管理体制在设计上走向了混乱,在实践中出现了多头管理的局面。社区教育的本质是教育,是我国现行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特性是立足于社区。社区教育之所以是社区教育,是因为与其他教育形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差异:第一,社区教育必须是服务于社区发展的;第二,社区教育必须是社区动员社区全体成员参与的,社区大众也可以自发参与;第三,社区教育的对象是社区全体民众;第四,社区教育的场所必须是在社区,办学条件必须立足于社区。明确了社区教育的本质之后,社区教育作为现行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其应当由各级政府举办,由教育部门管理,列入区县一级政府预算。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计划体制的瓦解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单位体制开始瓦解,“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进而使得社区这一基层组织体承担了原来由单位承担的部分功能,社区成为一个涵盖民众经济、社会及生活的综合性的基层组织。[4]随着社区公共服务职能的范围不断扩大及社区人口结构的变化,社区建设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社区教育成为社区建设的一部分,进而也就推进了社区教育与社区建设的并行发展”。在社区体制变革的过程中,社区教育的功能定位与发展模式迎合了社区体制的变化,成为社区民众维系与社区联系的一种基本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社区教育的“全能化”发展。
2.社区教育职能的反思
按照2015年新修订《教育法》的规定,我国教育在整体上分为学校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三大类型。其中学校教育又包括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四个阶段,而社区教育并不属于该法中列举的教育类型与教育阶段。但《教育法》第11条规定将终身教育与国民教育作为并列的两大体系,第20条将促进各类学习成果的互认与衔接作为推进全民终身学习的基础。由此可见,终身教育作为一个教育体系,主要是指继续教育。社区教育作为终身教育体系的一部分,显然不是国民教育,而是属于继续教育体系。社区教育也是一种理念上的提法,并不是法定的教育类型。换言之,社区教育不是单独的教育类型,而是教育服务职能向社区的一种延伸。社区教育的功能是教育在社区服务中的拓展,是教育为社区服务的一种体现。
按照国务院2006年的《工作的意见》中的要求,社区教育的职能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充分调动社区一切资源来为青少年的成长创造良好的社区环境。实际上该职能定位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社区教育作为德育教育的辅助体系是一致的。第二,统筹各类教育资源,为社区全体居民提供学习服务支持。这项职能充分体现了社区教育在终身教育中的定位,也体现了其作为继续教育的内涵属性。由此看来,政府与社区的任务并不是要为社区构建一个全能化的教育体系,而是要通过合理的教育项目、教育计划、教育资源来促进居民的终身学习,为其终身学习提供服务支持,进而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其生活品质。因此,社区教育的职能有以下方面:按照社区民众的不同需求,引入多样化的教育项目;整合资源,保证每个教育项目的顺利实施;动员、组织社区民众参与社区教育学习;为社区民众的终身学习提供服务支持。
3.社区教育主体的反思
教育主体问题是教育的核心问题。社区教育作为教育服务在社区中的延伸,包括政府、社区、教育举办者以及社区民众各个主体,对社区教育均有不同程度的参与。从教育学理论上看,教育主体是双主体行为,作为学习者的社区民众和作为举办者的社区教育机构是社区教育的共同主体,而政府、社区是社区教育的辅助者。
目前,巷道镇蔬菜在生产、服务、加工、销售等各环节尚没有形成连贯的产业链,产销难衔接,服务不到位,产业化程度低,致使菜贱伤农现象时有发生。
办学者的主体性应该体现在需要适应社区民众的学习需求、努力提升社区教育及服务质量上。在这个过程中,社区教育的举办者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办学条件与资源,通过科学合理的设计教育项目、课程及方法,为社区大众创造更多的终身学习机会。需要明确的是,尽管社区教育带有较强的公益属性,但也不能认为社区教育是完全的公益性教育,而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公益性、非公益性的教育项目,需要向社区民众平等开放,由学习者对此自行选择。[8]同时,政府、社区还必须尊重举办者与学习者的意愿,如果一味注重社区教育的公益性,或是随意采取行政干预的方式,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优秀的非公益性的教育项目进入社区教育体系,损害社区大众的学习权利。
社区民众的主体性体现在提出学习需求,积极参与社区教育过程,维护自身的学习权益。按照我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居委会、村委会尽管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但两者在实际运作中依然被视为是政府的派出机构或授权组织,根源在于社区民众的参与意识、自治能力不强。因此,社区民众应该提升自身的主体意识,依托政府力量来积极参与社区管理,参与社区教育学习,促进社区教育能够更具针对性地为社区大众服务。
社区教育之所以呈现“全能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级政府推动的结果。政府作为社会事务的主导者与管理者,应该关心社区教育发展,但也不能过度干预,将一些不属于社区教育职能范围的事情强加在社区教育身上。政府部门应该做好社区教育服务工作,不宜占据举办者与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因此,政府在社区教育发展中的职能应该有明确的定位:第一,做好社区教育发展规划,保障社区大众的学习权利。第二,改善社区教育办学条件,为社区教育机构提供经费支持。第三,制定社区教育发展标准,受理社区教育投诉事宜,为社区教育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
[1]黄琳.中国当代社区教育研究现状述评[J].职业技术教育,2018(7):66—71.
[2]张青.社区教育: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着力点[J].人民教育,2018(2):68—70.
[3]侯怀银,尚瑞茜.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的社区教育新发展[J].江苏开放大学学报,2017(6):12—17.
[4]张秀兰,徐晓新.社区:微观组织建设与社会管理——后单位制时代的社会政策视角[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30—38.
[5]陈为化,李飞虎.终身教育背景下职业教育对社区教育发展的影响与作用[J].成人教育,2017(12):46—49.
[6]袁强,余宏亮.城乡学校共同体发展的隐性矛盾及其消解策略[J].中国教育学刊,2016(7):1—5.
[7]刘尧.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143—148.
[8]黄云龙.我国社区教育的嬗变、发展态势及其实践策略[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1):55—60.
Reflection on the “All -roun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China
MA Ying, XING Yue
(Tianjin Institute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The “all-round” community construc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community education experience, the lack of funds for school educ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a community of interests have directly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all-powerful” tendency of community education. The “all-round” of community education seems to enhance the status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the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and actually hinders the play of the essential role of community educ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flect on the essence, function and subjec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return to the origi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Key words 】community education; all-round; reason; reflection
【中图分类号 】G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794(2019)01-0044-05
doi: 10.3969/j.issn.1001-8794.2019.01.009
【收稿日期 】2018-10-29
【基金课题】 2018年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双创视域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评价研究”,项目编号为TJ18JY03,主持人:黄向荣;天津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社会关系资本对高职教育供给效率影响研究”,项目编号为VESP3044,主持人:邢悦
【作者简介 】马莹(1981—),男,天津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区教育、企业创新管理;邢悦(1981—),女,天津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创新创业。
(编辑/乔瑞雪)
标签:社区教育论文; “全能化”论文; 原因论文; 反思论文;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