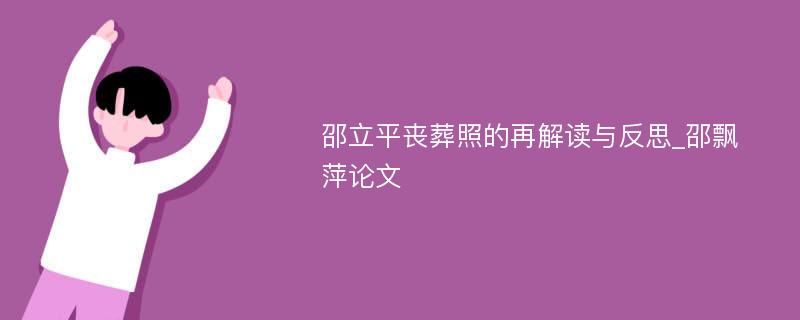
对一幅邵飘萍殓葬照片的重新解读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幅论文,照片论文,邵飘萍殓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引出:一幅殡殓照片透露出的新信息 在邵飘萍被奉系军阀枪杀后留下的一些珍贵殡殓照片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幅,是邵的遗体从永定门外二郎庙临时掩埋处挖掘出后,一些人为邵飘萍入殓的一个近距离特写场景。照片拍摄时间为1926年4月27日,但它被发现时间却是在56年后的1982年,由邵的侧室夫人祝文秀提供给前去采访她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方汉奇先生。此后,照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公诸于世,陆续被不少书籍和报刊采用,网上也能查阅到。 不过,笔者注意到一个现象,即一直以来无论是照片的刊发者还是读者,人们都将注意力集中于棺中死难者——邵飘萍先生,却无意忽视了两旁为其殓葬的那些“无名氏”活人。例如,《中国新闻事业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页)一书对照片的说明是“邵飘萍遗体”;《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以下简称《乱世飘萍》)一书,注明文字为“死难后薄葬的邵飘萍”。析其因,或在于年代太过久远,能辨识“无名氏”的知情者寥寥,对研究者来说亦属无奈,对该幅照片的意义与价值的认识也就有了局限性。另外,也有胡乱解读的情况,如《北京青年报》2011年6月6日刊发《京报报馆,飘萍胜抵十万军》一文,对这幅照片的解释是:“图为当年北京的知名文化人士到天桥悼念邵飘萍”,不仅将地点搞错,所谓“知名文化人士”,也是作者未经考证的猜测,对读者有误导性。 对此,笔者母亲吴大年(88岁,江苏省教育厅离休干部、京报社经理吴定九长女)提出了新的看法。近年来,她为写纪念其父的文章,参考阅读了一些研究《京报》的论著,尤其是《乱世飘萍》这本书。她认为,该书中插用照片“死难后薄葬的邵飘萍”中,位于左后扶棺位置,低头面向死者的戴眼镜中年人就是吴定九,其他人则是京报馆的同事。 为慎重对待这一指认,笔者特将这幅照片分别发给吴定九的儿子吴大受(86岁,国家卫生部离休干部)和次女吴大箴(84岁,上海嘉定一中退休教师),请两人过目辨认,结果得到二人完全认同的回复。至此,照片经吴定九的三个子女共同指认,吴的身份已可确定。接下来的问题,如何才能证实吴大年所言“其他人肯定都是京报馆的同事”这一推断? 经查《东阳文史资料选辑·邵飘萍史料专辑》第二辑(东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1985年10月版),书中对这幅照片有详细说明:“从临时掩埋处起出运至临时停放处待殓时的邵飘萍遗体。站在遗体头部右侧,手扶棺、面有戚容的年青人,是邵夫人祝文秀的弟弟祝寿南,其余均为京报馆的工作人员。”显然,这段说明文字来源于照片的保存者和提供者祝文秀,且完全证实了吴大年的推断,但祝并未(或不能)具体指认那些京报馆工作人员的姓名和职务。 二、寻找失落的京报馆同事 细观照片上人物,除死难者外共有9人(左后挖掘者除外),其中,身着长袍马褂、胸戴白花者8人,穿白孝服者一人。他们或站或蹲围拢在薄棺两侧,手扶棺木,神情悲戚,目光肃重,与死者的亲近关系一目了然。除去已辨认出的吴定九和祝寿南二人外,还剩下7个人。吴大年认为,那位穿白孝服者的身份无疑是亲属,当年加入到京报馆事务中有两个邵家亲戚,一为邵飘萍的堂弟邵新昌,做总务和编辑;一为邵飘萍的堂侄邵逸轩,任美术编辑,二人均以亲属和同事的双重身份参加了邵的殓葬。也就是说,穿白孝服者必为二邵之一,但从辈份和在报馆任职情况判断,邵新昌的可能性更大些。 对于余下的六位京报馆同事,笔者以为,如果能有一份当年京报馆工作人员的名单作为作为参照比对,再从中进行筛选并对号入座,应是个办法,但现有史料中却没有这样一份现成的名单。好在笔者在查阅《京报》过程中,发现《京报》于1925年12月31日和1926年1月1日连续两天,在第一版上用整版篇幅辟出邵飘萍、京报馆同人及相关人士向社会各界和读者恭贺新禧的专刊,其上参与新年贺岁的人共有36名。毫无疑问,这份36人的贺岁名单给后人留下了极有价值的参考线索。经笔者查考,这36人分两种类型,一是与《京报》有较密切联系的亲属、同行、撰稿人及社会各界人士等;二是在京报馆供职的工作人员,也即京报馆同事,如编辑、记者、会计、杂务、听差等。属于后一种类型的人有15位,他们是:邵飘萍、汤修慧、吴定九、孙伏园、邵新昌、邵逸轩、姚钧民、邢墨卿、马秉乾、许邦璋、沈江、朱凤鸣、王生暄、张汉徽、李钰。 这份15人的京报馆同事名单,对进一步辨识照片上余下的六位京报馆同事当有所助益,具体再缩小范围而言,名单后9人为照片上其中者的可能性较大。不过,若要将失落近80年的这些京报馆同事一一拎出来对号入座,恐笔者目前力有不逮,只能以后寄希望于他们的亲友或后人了。事实上,即便有朝一日具备辨识条件,最多也只能再辨认出5人,因为其中有一人(白孝服者左侧)是背对着镜头,根本无法辨识。 三、谁是负责殡殓活动的主角? 这一问题的提出,基于对照片重新认识的自然延伸性思考。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展对《京报》和邵飘萍研究以来,不少著作文章中有关殓葬邵飘萍的叙述,流传着一种说法,大意为:邵飘萍被害后,亲属和报界同人因慑于军阀淫威不敢为邵收尸入殓,而邵的生前好友、戏剧界名伶韩世昌和马连良等人却不畏邪恶,挺身而出为烈士收尸、拍照、出钱操办丧事。由于此举未招致反动当局的横加干涉,邵的亲属、朋友和同事随后才敢将邵的遗体重新入殓安葬,韩、马等人也因见义勇为而被人们誉为“义伶”。对此说法,笔者虽早有耳闻,但因知韩、马二人也是外公吴定九生前的好朋友,故一直不太在意。但当笔者对这幅照片进行重新解读并有了新认识后,则悟出上述说法既不合逻辑,也有悖事实。 关于记录邵飘萍遗体被发掘和入殓的十幅现场照片,方汉奇教授早在1983年即有概括性介评:“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到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的烈士遗体,可以看到弥漫着惨雾愁云的殡殓活动场景,也可以看到家属们在烈士灵前悲痛欲绝的镜头。看了这些照片,使人们仿佛又回到了充满着血雨腥风的那个可诅咒的时代。屠夫们的凶残,令人发指。历史是不会重演的了,但却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发现与探索——记祝文秀和她所提供的有关邵飘萍的一些材料》,《方汉奇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8页。)笔者以为,即使将这段话放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仍是客观准确和发人深省的,而从这幅照片中京报馆同事们身上,则可看出更深一层含义。 照片上的京报馆同事大都上着深色马褂,下穿浅色长袍,头戴礼帽,胸配白花,整齐一致地围拢在烈士遗体两旁。为加强拍摄效果,吴定九与另一侧的祝寿南一起,双手将棺托起成45度,使之面向镜头。笔者以为,京报同人如此刻意造型,除一般意义上的合影留念,更在于为控诉军阀暴行而立此存照,从他们的脸上读到更多的是继承遗志、坚忍不屈和勇于担当的悲壮情怀,用今天的话说,这些京报馆同事们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团结有力的战斗集体。与其他现场照片不同的是,其实这幅照片本身已经说明了谁才是殡殓活动主角,一直以来遵循“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信条的京报同人们,绝不可能因惧怕反动军阀淫威而不敢为其社长收尸,也不需要几个“名伶”去打头阵。 同样道理,吴定九是邵飘萍的挚友和主要助手,为了追求共同的新闻事业理想,他们走到一起并肩战斗。有别于邵的其他助手,吴在《京报》辅邵的时间最长,跨度最大,从1918年10月5日《京报》创刊一直到1926年4月26日邵被害,八年间吴从头到尾未离开过邵和京报馆一步,其责任心最强,付出的心血也最多。邵吴两人关系也非一般的京报同人好友,而是有着共同信仰理念、患难与共多年的亲密战友,邵被杀,吴不可能如懦夫一般,不敢挑头露面去收埋战友的尸体。 上述反思与诘问似乎来得太迟了,这主要与包括笔者在内的人们长期以来对这幅照片缺乏深度认知有关,以致让那些缺乏事实根据的说法得以流传开来。 查当年京沪两地的报纸,可大体了解邵被枪杀至收殓的基本过程。 上海《申报》1926年4月27日第4版载:“京报邵振青昨日下午被枪毙,现同业正在觅尸。(二十六日下午三时)昨报界营救……今日警察通知邵宅,谓尊主已不测,特撤去监视。(二十六日下午二时)邵振青枪毙时不屈,犹向监刑官一笑。遗骸停永定门外义地,其妻汤氏昏厥,其本家邵某与友人某氏赴永定门外收殓。(二十六日下午九时)”,28日第4版又载:“今日邵振青遗体由永定门外土中挖出,送地蒧庵。记者等顷往襄相助成殓。(二十七日下午一时)”。 北京《晨报》4月27日第6版刊登题为《邵振青昨早被枪毙》的报道,内称:“至四十三十分,……将邵提到天桥,执行枪决。……邵毙命后,尸身即抬至永定门外义地,由警厅电告其家属前往收进城收埋。闻至昨日下午三时,始由其友具状往领。闻警厅对《京报》,则于昨晚下令启封矣。” 比照上述两报内容,除《申报》错将邵被杀时间说成是26日下午外,在其他时间、地点和情节诸方面都基本吻合。另据5月3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邵被“执行后当由在场警察将邵尸体送至永定门外停放,昨日(26日)上午已通知家属前往收殓矣。……邵氏被捕时,京报馆即被查封,而邵氏之家庭,亦由军警监视,禁止出门。及邵死后,该报馆随即启封,家庭监视亦已解决。昨晨其家族自得邵氏噩耗后大哭,其妻因悲伤过度,昏厥数次。现在亲友正在商量办后事。” 根据不同报社记者实时实地的现场报道,不难理顺26日至27日两天内为邵飘萍收殓的几个步骤:1、邵于26日凌晨四时许在天桥被枪杀后,尸体被警方装进薄棺运至永定门外义地暂埋。2、当日上午警厅撤消对京报馆的监视,并电话通知家属前去办理认领尸体手续并收殓,家属和亲友商量后事。3、下午三时后,邵新昌和另一京报馆同事前往永定门义地寻认邵尸暂埋地点,为次日正式收殓做准备。4、翌日(27日),邵的遗体由永定门暂埋处挖出,运送到地藏庵入殓。以上步骤紧凑急促,一环套一环,整个过程不过一天多点时间,看不出有“不敢收尸”和“不让收尸”的问题,更不存在需通过花钱“终于在三天之内找到了飘萍的葬地”这种可能性。 至于祝自言谢绝京报馆的出资,拿出二百元大洋购置楠木棺材一事,不仅缺乏旁证,也因与叙事者本人身份、地位不符而说不通。前面提到,韩世昌言及“邵家经济能力还很好,又买了好棺材。”可见买好棺材一事不假,但作此决定的轮不到祝,因为其时当家作主说了算的是邵飘萍正室夫人,同时又是《京报》负责人之一的汤修慧。更何况,囿于那个时代正室和侧室之间地位之悬差,从汤修慧与吴定九、邵新昌等人商量办理后事直至开吊殡殓,祝自始至终都未在场参与,谢绝或购棺之说无从谈起。 从祝寿南在照片上所处位置推断,这位年青人应为吴定九的主要帮手之一,他为邵飘萍的后事奔忙出力应予肯定,但其能量和作用有限,不该夸大。在殡殓活动中,他的身份既非亲属(未穿白孝服),也非京报馆同人,而是以亲友身份出面相助,不可能如其姐所言有组织人力的能量。事实上,邵的遗体从二郎庙义地掘出重新入殓,前后只转移了两个地方,即地藏庵和天宁寺,而非“转移了三个地方”,至于“最后下葬在城外天宁寺旁荒地”,并“用水泥浇好了墓穴”,倒确有其事,但那已是1926年11月以后的事了,且是吴定九和其他京报馆同事所为,其时祝寿南已因病离世。 四、历史写真的展现与回放 据笔者外婆杨怀英回忆: 张作霖进北京,邵飘萍躲进了东交民巷。某日下午四点左右他回家探望,拿了几件换洗衣服,有点大意了。那天我也在邵家。邵飘萍夫妇、马连良和我还打了几圈麻将。定九在前面报馆里忙活,没有和我们打牌。后来报馆的听差跑进来说报馆被包围了,邵立即离家出走,但刚出门不久就被捕了。军警进来搜查,汤夫人和同事们催促定九赶快跑,于是定九跳墙而走,好多天后才返回家中。我见他神色非常疲惫,便问他离家后的情况,他长叹一口气说,这些日子他一直住在东交民巷,为着处理飘萍的后事已经多日没好好休息了,汤夫人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邵家后事再加上报馆大大小小的事务都要他亲自过问和处理。(吴大年:《杨怀英回忆吴定九》,记录稿,1984年12月。) 《解放日报》1989年8月29日刊发赵春华的《吴定九与邵飘萍》一文,其中大部分内容源自杨的回忆,不过这篇小文章后来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笔者认为,作为亲历见证者之一,杨怀英的回忆至少有三点值得重视。一是关于邵的被捕细节,很多书刊里描写那天邵是乘着夜幕坐车回家的,实情却是他回家时天还大亮着。可能邵认为次日(4月25日)是礼拜天,周末下午警方监视会有所放松,回家一趟不会有事,有些大意。二是奉军进京,凶焰冲天,邵躲进东交民巷,京报馆也有所防备,吴定九等人虽每天到报馆上班,但都作好了随时撤退的准备,事态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报馆听差李钰恪尽职守,细致机警,是吴定九的得力下属,此君于第一时间通报了报馆被包围的消息,如果邵飘萍弃车不按原路返回,而是与吴定九一样窬墙出走,历史或无此沉重一页。其三,从家属和亲友同事得知邵就义消息到为其举行殓葬,不过一天时间,然而活动全程显得忙而不乱,有条不紊,体现出吴定九和京报馆同事们齐心协力办事的极高效率。不过,要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办那么多事,不可能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和筹划。上世纪八十年代,外婆曾对母亲忆及,其实外公在避居东交民巷时,各方面消息都很灵通,也已预料到邵此次在劫难逃了,还在汤夫人和报界同人设法营救时,他已未雨绸缪,作了两手准备。 邢墨卿当年与孙伏园同在京报馆二楼的副刊编辑室办公,他是京报馆被查封及邵飘萍殡殓活动的亲历者,也是京报馆同事中唯一对此留下回忆文字的人,故其《京报生活的一断片》弥足珍贵,撷取如下: ……晚间,回到寓所不多时,伏园先生来了,他问我:“你刚回来?你知道了吗?”我说:“是的,什么事?”他说:“《京报》被封了。”这原是意中事,……单就《京报》一年来的言论以及一般青年爱读的情形看,固然不配说是“宣传赤化”,但因其倾向于国民军,是确有被封的可能的。……这一幕封门的恶剧,既大家都能料到,故在初听到这消息时,也并不怎样出惊。就接下去问伏园先生所见到的情形。他说他从东城回来,到报馆去看看有无信件,见门口站着一堆军警,大门铁栅也已半边关起,看情形不对,所以叫车夫不要停下,一直回来。 ……夜深了!时钟已将一点,虽然三个钟头之后就得动身到车站,也不得不稍睡一忽养神。刚睡下,长班在叫:“孙先生,你有电话!”于是这电话又引起了我们的疑虑,这样夜深时节,有谁会打电话来呢?伏园先生叫我先去听听是哪儿来的,……一接电话,知是报馆的李钰的声音,于是伏园先生自己接,他告诉孙先生明日如没有他的电话通知不要到报馆去,以后就挂断了。我们猜一定是巡缉队守在门外,说话不便的缘故。 ……第二天是二十六日,下午,到印刷所去,同事告诉我,报馆巡警已撤,可以自由出入了。我立刻就想到《北京乎》的稿件及铜板。……我找到了李钰,问他有没有瞧见,他缓缓地说:“不是你昨天打电话叫我留起的那叠副刊吗?在那儿。” ……夜,同事张君告诉我,次日早七时赴永定门外收尸,到地藏庵会。回寓所后,将伏园先生未走时尚未煮软的几个粽子,拿来再煮。第二天早晨急忙忙地吃了两个冷粽,就赶到报馆,他们已走。 ……地藏庵内不见馆中同事,我想到曾听他们说,尸埋二郎庙,他们或尚在那边,乃仍乘车赴二郎庙。在京师警察所义地里,遇到了他们,他们指给我,在标上写着“外右五百七十七号”的,那就是。在许多个坟起的短形泥堆中,那是最前的第二个,它的面前还有一个五百五十八号,据说是伤兵。数字上的颜色,殷红且发亮,谁也想不到,这底下是放着一个曾以笔墨为刀剑的飘萍先生的躯体罢! 把这一块泥堆拍了一个相,几个乡人就拿着器具将土拨在两面并且深深掘下去。大约有两尺多深的时候,渐渐地露出白板,一个老年的巡长说,这是特别埋得深一点的,因为飘萍先生生前,大家对他感情都很好。各个人的脸上罩着沉痛。凄咽的哭声在这广漠的空气中颤抖,……一具不及一尺高半尺宽的薄板棺材抬进芦蓬里,邵新昌先生气厥了,大家又忙着呼唤。当开棺的时候,我看了飘萍先生最后的一眼:惨白的脸色,圆睁着的右眼下是弹痕,有几条转紫的凝血,倒流在头部。 起棺后,抬到地藏庵去成殓!我受不了这种情境所给我的感觉,到那边不久,也就回来。这一晚使我不敢一个人住到伏园先生的房间中去。 上述回忆距事发仅一年时间,应比几十年后一些人的回忆更加准确、可靠。从中可知,早在奉军始进京城,不详的预感就已经笼罩在京报馆同事们心头,大家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有一定准备。当报馆被封,大家觉得“这原是意中事”,“并不怎么出惊”,京报馆仍在运转着。在邢的笔下,李钰的从容淡定和认真负责、孙伏园的及时躲避和迅速离京、邢和同事们满怀悲愤秩序井然地送别“以笔墨为刀剑”的飘萍先生等重要细节,无不生动了然,犹在眼前。从中可看出,组织者对殡殓活动作了精心策划,时间安排得很紧,整个活动过程有准备、有组织和有计划。虽然邢在行动中处于听候指令的末端,不知谁是指挥者,然其叙述却为我们搞清指令怎样发出执行,以及活动中某关键动作方面之细节提供了重要线索。 1.京报馆被封后的重要联络方式——电话 京报馆在面临社长被捕,经理暂避,报馆被封,人员不能自由出入的困境下,如何与只身在东交民巷的吴定九联系、沟通呢?这个曾让笔者感到困惑的问题,在邢墨卿的回忆中找到了答案。 4月24日晚,身居绍兴会馆寓所的孙福园接到李钰从报馆打来的电话,被告知“明日如没有他的电话通知不要到报馆去”。次日,邢也给李钰打过一个“留起的那叠副刊”的电话。另外,汤修慧在《被难后追述之事实》一文中,亦有邵被害当日三时许“得友人电话”一语。可见,京报馆虽被查封,军警严禁人员进出,但一直维系着报馆与外界联络的电话却未被警方切断。也就是说,吴定九仍能通过电话与外界、报馆及邵家一直保持联系,及时了解和掌握邵被捕后事态的进展情况,交待和安排报馆事务,而随后为邵办后事的准备、布置和实施则更离不开电话。即便报馆在26日上午已解封,吴可自由出入,但他不可能仅靠自己或手下跑腿来传递各种信息和商量事情。事实上,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旧中国,能够频繁使用当时最先进通讯工具之一的电话来处理日常事务的人,非报人莫属。所以,在京报馆被查封后和为邵飘萍殡殓期间,打电话一定是吴定九、李钰、汤修慧、邵新昌、邵逸轩等人之间最方便快捷的联络和议事方法。另外,吴与祝寿南同样可用电话联系,因其与母亲和姐姐的住所,正是邵飘萍装有电话的“侧室”。 2.记者为烈士殡殓留下历史写真 所谓“活动中某关键动作”,即指拍摄者为殡殓场面按动相机快门这一动作。如前已述,马连良到现场拍摄照片是一种缺乏根据的讹传,那么谁才是真正的拍摄者呢?按方汉奇教授的介绍,记录邵遇害后各种场景的十幅照片,有五幅是在临时掩埋处拍的,有两幅是在地藏庵的临时灵堂前拍的,有三幅是在其大殓前后的临时停放处拍的。既然照片不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拍摄的,这就不像是一人所为,而是数人为之。邢墨卿的回忆讲到他在二郎庙临时掩埋处“把这一块泥堆拍了一个相”,说明邢是现场拍摄者之一,而十幅照片中确有一幅拍的是“泥堆”,又说明他很可能就是这幅照片的作者。至于他到地藏庵后有否再继续拍几个相,其回忆中并未述及,但这种可能性仍然存在。 除邢墨卿外,其他京报馆同事有可能是拍摄者吗?答案是肯定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京报社不缺会摄影的记者。例如,那幅照片上身着白孝服的人为邵逸轩和邵新昌二者之一,邵逸轩是美术专业出身的编辑,自然也懂摄影,如果身着孝服者为邵新昌,则拍摄者很有可能就是邵逸轩。当然,同样存在着邵新昌与其他京报馆同事也是拍摄者的可能性。 除京报馆同事外,其他报社同人是否也可能是拍摄者?答案同样是肯定的。如前已引,《申报》4月27日下午1时由驻京记者发回电称:“今日邵振青遗体由永定门外土中挖出,送地蒧庵。记者等顷往襄相助成殓。”这说明当时有不少他报记者在殡殓现场,他们用随身相机拍照不就是作为记者的一种职业性习惯动作吗?当然,这些惨不忍睹的照片在当时不可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但事后,拍摄者将照片冲洗出后再交由京报馆和家属留存纪念,应该是合乎情理的一种结果。至于五十多年后年事已高的照片收藏者无法说清拍摄者是谁,本不足为怪,但可以下定论的是,只有现场记者们才是十幅殓葬照片的真正拍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