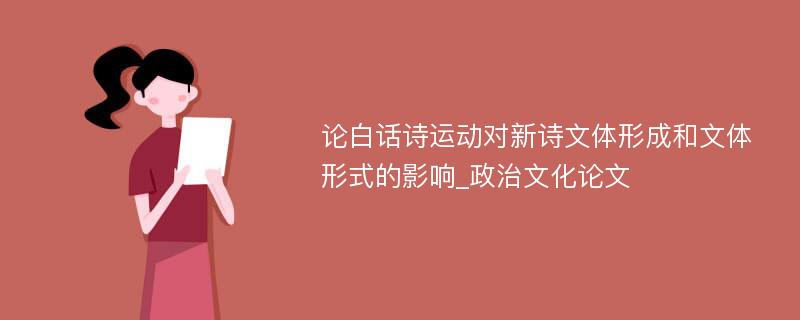
论白话诗运动对新诗的文体生成及文体形态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体论文,白话诗论文,新诗论文,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1年不是像某些旧说法所认为的那样是现代民主运动史上的主要转折点,它是中国将近二十年大动荡的顶点;这二十年中国发生的变化比以往许多世纪的任何二十年都要急剧。”① 这二十年正是由“诗界革命”向“白话诗运动”转变时期,即白话新诗的孕育时期,在如此动荡的岁月孕育出的文体革命,自然具有强烈的极端性。新诗真正问世的20世纪10年代中后期更是中国政治、文化大革命时期和社会大动荡时期,此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巨大的转折点。政治文化上的变革必然带来文体革命的变革,政治秩序的瓦解必然带来诗体秩序的瓦解,特别是在诗体秩序与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高度统一的中国,瓦解会来得更快更猛。白话诗运动本身就是政治运动的产物,又采用了“运动”的方式,造成新诗应“双运”而生,对古代汉诗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稳定了千余年的汉诗的诗体秩序毁于一旦,自由诗成为新诗的独裁诗体,现代汉诗与旧体汉诗强烈对抗。
一、白话诗运动是激进的文体大革命
新诗革命是催生新诗的特殊的文体大革命,分为“诗界革命”和“白话诗运动”两大阶段,白话新诗的真正问世,应该是在“白话诗运动”阶段。诗界革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文学激进的浪潮却不如戊戌变法时期汹涌澎湃,未免步伐缓慢,声势微弱,与现实不相协调”②。诗界革命只是重精神创新轻诗体创建的文体改良运动,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体革命,诗界革命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新诗(白话诗)。晚清诗坛的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既对抗更和解的局势决定了诗界革命的改良性质。这种文体改良方式导致了后来的汉诗革命者的极端不满,这种不满是稍后的“白话诗运动”采取激进的文体革命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诗界革命”是重内容轻形式的诗的风格的革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以语言改革和诗体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诗的体裁革命。诗界革命走的是贵族化、本土化、民族化道路,对古代的贵族诗体和民间诗体较为重视,主要使用的仍是古代汉诗的定型诗体。这种在诗体上的保守导致了白话诗运动“诗体大解放”的极端和诗由贵族文学向平民文学的巨变。诗界革命时的诗体“本土化”导致了白话诗运动时的诗体“西洋化”甚至“全盘西化”。新诗文体是新诗革命的结果,是保守的“诗界革命”和激进的“白话诗运动”的产物。前者只是汉语诗歌的一次文体改良运动,并没有动摇古代汉诗的根基,文体变革的力度太小;后者又太激进,是一次超过了汉诗承受能力的文体大革命。
“白话诗运动”是继“诗界革命”后对古代汉诗进行的第二波致命攻击,是具有极端风格的诗体大解放、大革命,特别是胡适的“诗体大解放”、“作诗如作文”进一步深化了黄遵宪的“古岂能拘牵”、“我手写我口”对旧诗体的反叛意义,打破了“无韵则非诗”的作诗教条。“诗界革命”的改良性和“白话诗运动”的极端革命性都是时势造成的,是不可避免的。民初的“新瓶装旧酒”式的“白话诗运动”虽然与晚清的“旧瓶装新酒”式的“诗界革命”异曲同工,目的更多是为了政治实用而非艺术变革,却在极端的改革浪潮中,特别是借助政治革命、文化运动等非诗力量,打造出了“白话诗(新诗)”这个“新瓶”,导致了从古代汉语诗歌到现代汉语诗歌的巨变,文言文和格律诗体等汉诗定型诗体和准定型诗体被白话文和自由诗无情替代。即使白话诗运动不成为新文化运动及政治革命的前驱,中国也会在当时出现具有改良性质的新诗革命,过分定型的古代汉诗诗体已经严重不适应呈多元状态的现代生活,特别是严重阻碍中国发展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后,汉诗的功能已经由应试求仕向自我抒情和启蒙大众宣传革命转化,自我抒情需要自由的抒写,为大众抒写要求晓畅易懂,两者都不需要雕琢呆板的诗歌形式,都需要诗体的解放。“新文学运动,是历史的,自然进化的,不是三五人在七八年内,所能忽而创造出来的,也不是留学生从外国搬来的。”③
尽管胡适自称“历史的文学进化观”是他的文学革命论的基本理论,但是实际上他更倾向于“进化”中的“突变”而非“渐变”。为了证明自己鼓吹的文学革命的合理性,他甚至把中国文学的进化都总结为“革命”(突变)的结果,把整个中国文学史及中国诗歌史视为文体革命史。他在1916年4月5日的《札记》中说:“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并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赋变而为无韵之骈文,古诗变而为律诗,三大革命也。诗之变而为词,四大革命也。词之变而为曲,为剧本,五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④ 几天后,即1916年4月30日,胡适填了一首《沁园春》词,题目就叫做《誓诗》,从题目和内容都显示出胡适的文学革命的激进。他后来回忆说:“其实是一篇文学革命宣言书:……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君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⑤
“白话诗运动”是打破了诗体的基本限制的文体改革,它产生的“新诗”首先是语言上的“新”而不是诗体上的“新”,要求诗的语言用白话取代文言。用白话直接思维远远比早期的白话运动用文言思维再译成白话自由得多,是质的飞跃。直接使用白话“写”诗的自由必定带来对用文言“做”诗,必须合体的束缚的极端反叛,白话诗自然会强调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已有的任何诗体都不合时宜,特别是在文言思维方式下确立的种种诗体已不适应白话写作的需要,甚至改良旧诗体也失去意义。如俞平伯在激进的“五四”运动过了一年多后还主张新诗应该有极端的自由,他在1920年12月14日于杭州写的《诗底自由和普遍》结论说:“我对于作诗的第一个信念是‘自由’。诗的动机只是很原始的冲动,……我平素很喜欢读民歌儿歌这类作品,相信在这里边,虽然没有完备的艺术,却有诗人底真心存在。诗人原不必有学问,更不是会弄笔头,只是他能把他所真感着的,毫无虚饰毫无做作的写给我们”⑥。因此白话诗人不但完全摒弃了汉诗已有的定型诗体,还打破了“无韵则非诗”这一作诗的基本要求,提出了“作诗如作文”的打破诗与散文的文体界限的极端口号,要求白话诗人是在完全无诗体的任何限制下、无任何游戏规则下的“自由抒写”。要打破“无韵则非诗”的作诗信条,就只能写“无韵诗”;要“作诗如作文”,“散文诗”自然是合适的文体。恰好“无韵诗”和“散文诗”两种诗体国外都有,可以直接“输入”。在译介时还夸大了两者的“文体自由”,与不受任何格律限制的“自由诗”等同。尽管当时写白话诗的重要诗人都是熟知古诗作诗法及诗体的人,在他们实际的新诗创作中,古诗仍然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新瓶”实际上受到“旧瓶”的影响,“作诗如作文”的观念也很快受到新诗诗人的怀疑和抵制,但是在白话诗运动时期,重破轻立、忽视诗体建设的倾向是相当严重的。
当时的新诗主要是要求用白话自由地描写普通人,特别是劳动者的生活形态,抒发平民的生活情感的诗歌。从这种形态的诗歌在当时的称谓上就能够看出它是故意与诗体定型的古代汉诗对抗的,它被称得最多的是“白话诗”,如《新青年》最早发表胡适的这类诗时就用了《白话诗八首》这个标题。其次是“无韵诗”和“散文诗”,特别是译介外国诗歌时,通常采用的是“无韵诗”或“散文诗”。如《新青年》发表泰戈尔的译诗时用的是“无韵诗”。1918年《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刊载了刘半农的《译诗十九首》,其中有泰戈尔的《海滨》(On the Seashore )和《同情》(Sympathy)。译者注说:“以上印度R .Jagore氏所作无韵诗七首。”⑦很多刊物发表屠格涅夫、波德莱尔的译作时多标明是“散文诗”。中国的一些诗人的作品,甚至今天看来完全与诗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作品,如俞平伯的《〈忆〉序》在《诗》第二卷第二号发表时,注明的是“散文诗”。“无韵诗”是与“有韵诗”对抗,“散文诗”是与“韵文诗”对抗,最早的新诗被称为“白话诗”,目的更是为了与文言诗对抗,当时革命的重点是在“白话”上,不是在“诗”上。如同当时的作文,是用白话还是用文言几乎是衡量作文者是进步还是保守的“政治立场”的标准。诗人写诗用白话,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表示对白话运动的支持。如在新诗草创期把诗写得最“直露”的诗人刘大白并非写不出“含蓄”的诗,他对以含蓄为本的古代汉诗极有研究,是新诗诗人中少有的谙熟古代汉诗的学者。为了把诗写得通俗易懂,他不但采用了口语俗语等民间语言,还采用了包括童谣在内的民间歌谣体。因为他是白话文的大力鼓吹者。他1919年2月9日写了《人话文与鬼话文》,发表在《文学周报》上,为白话辩护:“我的主张是小学全读人话文(我称白话为人话,文言为鬼话),初中一年级也全读人话文……中学生有懂得鬼话的必要,但是只求他们能懂为止,绝不以能做为目的。文字是吸收和发表的媒介物。做是发表,既是现代的活人,当然应该用人话发表自己底思想”⑧。梁实秋也认为“诗人也得说人话”,他在《自由评论》第十二期发表了《我也谈谈“胡适之体”的诗》。他鲜明地指出:“‘白话’的‘白’,其一意义即是‘明白’之‘白’。所以‘白话诗’亦可释为‘明白清楚的诗’。所以‘明白清楚’应为一切白话诗的共有的特点,不应为‘胡适之体’独有的特点。……胡先生的诗不足以做大家的模范,但是至少他的‘明白清楚’的主张是正确的,是今后所应依照进行的一个方向。是人就得说人话,诗人也得说人话,人话以明白清楚为第一要义。’”⑨
很多人从事“白话诗运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只是想通过“诗体大解放”来达到“文化大解放”和“政治大解放”,通过诗体革命推动文化革命,以文化革命促进政治革命,他们进行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汉诗的技术性的“诗体”变革,他们更追求汉诗在内容及功能上的变革。所以新诗革命的当事人多年以后都否认新诗革命是“新瓶装旧酒”的文体形式上的革命,他们更倾向于新诗革命的目的不是制作“新瓶”,而是在于“酒”的酿制,酒即是可以启蒙大众的新思想、新精神,因此新诗革命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诗歌甚至文学艺术革命的范畴,实质上已经成为了文化革命甚至政治革命的前驱。一九二二年三四月间,周作人应沈兼士的邀请到辅仁大学去演讲“文学革命”:“对此次文学革命运动起而反对的,是前次已经讲过的严复和林纾等人。西洋的科学哲学和文学,本是由于他们的介绍才得输入中国的,而参加文学运动的人们,也大都受过他们的影响。……他们为什么又反对起来呢?那是他们有载道的概念之故。严、林都十分聪明,他们看出了文学运动的将不限于文学方面的改变,其结果势非使儒教思想根本动摇不可,所以怕极了便出面反对。林纾有一封很长的信,致蔡元培先生,登在当时的《公言报》上,在那封信上他说明了这次文学运动将使中国人不能读中国古书,将使中国的伦常道德一齐动摇等危险,而为之担忧。”⑩ 周作人还认为文学革命及新诗革命用白话取代文言,不是像胡适认为古文是死文字白话是活文字,而是因为时代的需要,时代已经使文章及诗歌的功能发生了巨变,文体也应该随之发生巨变。他认为当时使用白话有两大理由:“因为要言志,所以用白话,——我们写文章是想将我们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的。能够将思想和感情多写出一分,文章的艺术分子即增加一分,写出得愈多便愈好。……要想将我们的思想感情,尽可能地多写出来,最好的办法是如胡适之先生所说的:‘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必如此,才可以‘不拘格套’,才可以‘独抒性灵’。……要想表达现在的思想感情,古文是不中用的。”(11) “因为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变动,所以须用白话——假如思想还和以前相同,则可仍用古文写作,文章的形式是没有改革的必要的。现在呢,由于西洋思想的输入,人们对于政治,经济,道德等的观念,和对于人生,社会的见解,都和从前不同了。应用这新的观点去观察一切,遂对一切问题又都有了新的意见要说要写。然而旧的皮囊盛不下新的东西,新的思想必须用新的文体以传达出来,因而便非用白话不可了。……现在的青年,都懂得了进化论,习过了生物学,受过了科学的训练。所以尽管写些关于花木,山水,吃酒一类的东西,题目和从前相似,而内容则前后绝不相同了。”(12)
清末民初的政治革命者都竭力倡导白话诗和平民文学,目的是与保守的贵族争夺诗歌创作的权力,把诗从少数人的象牙塔中解放出来,让每个人都可以亲近缪斯。那些并非谙熟古典诗歌传统和作诗法的革命者,特别是并未饱读诗书的青年便有了创作和运用诗歌的权力。这十分有利于他们利用诗歌为工具进行启蒙教育和革命宣传。如果诗成为少数保守的贵族享用的专利品,诗的宣教功能就不能有效地发挥。因此晚清民初为了争夺诗歌的使用权,出现了诗是贵族的文学和诗是平民的文学的剧烈之争,诗歌复古思潮严重,新诗革命派也针锋相对。不仅新诗革命初期的胡适、刘半农等改革先锋否定古代汉诗传统,如长虹在新诗已经由激进的草创期进入认真的建设期的1925年,还极端地主张:“想从事新文学工作的人,第一,必须先去发见自己的生命,先从自己中把由历史与社会所传习的东西尽量驱逐出去,以救出遗失了的生命。如是,则新文学的创作者,必须同时是一个反抗者了”(13)。1928年仲云也认为:“据我所观察现代的时代精神及中国的现状,新文艺的建设似当以下三事为准:一,文艺的进化;二,革命的精神;三,世界主义的倾向。”(14) 整个20世纪都流行的青春期写作与“革命”的时代主潮相融合,造成绝对的文体自由的“自由诗”的盛行,诗体规范及诗体建设通常被视为保守,成为青年“革命”的对象。
白话诗的问世与白话文一样,正是时代的产物。胡适最早确实是为了文学及诗歌才想进行文学革命的,他确实想进行一场纯粹的文体革命。“这是民国六年的事。其时胡适之尚在美国,他由美国向《新青年》投稿,便提出了文学革命的意见。但那时的意见还很简单,只是想将文体改变一下,不用文言而用白话,别的再没有高深的道理。当时他们的文章也还都是用文言作的。其后钱玄同刘半农参加进去,‘文学运动’‘白话文学’等旗帜口号才明显地提了出来。接着又有了胡适之的‘八不主义’。”(15) 胡适的“八不主义”也仍然是针对文学本身的,甚至还局限在文学的语言革命及文体革命之内。如“不摹仿古人”、“务去滥调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从提出“八不主义”的文章题目《文学改良刍议》和“八不主义”中的第三条“须讲求文法”看,当时的胡适并不想彻底地、极端地反叛和摒弃传统,他确实只想进行必要的“改良”,因此,尽管他在此前与友人的通信中总是采用“文学革命”而非“文学改良”,但是在第一次公开系统地发表他的主张时,他没有像陈独秀那样,用《文学革命论》这样的观点鲜明激进的题目。胡适1933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讲演中也说:“这种历史的思想路线体现在我1917年元旦发表的一篇题目相当温和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中。……此后,陈独秀先生发表了自己的、以大字标题的《文学革命论》。”(16) “须讲求文法”也体现出胡适的“改良”观念,当时新文学根本没有什么“文法”,文法只能从旧文学中获得,对文法的重视,实质上是对旧文学的合理因素,如诗歌的诗体的肯定。因此胡适当时“实验”了大量诗体,包括古代诗体和外国诗体。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就发表了陈独秀的“檄文”——《文学革命论》。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仅一个月时间。
时过境迁,胡适却认为文学革命中的形式革命是为新内容和新精神服务的,是因为有“新酒”,才需要“新瓶”。1925年9月25 日他在武昌大学以《新文学运动的意义》为题演讲时说:“什么叫做新文学?新文学是活的文学,能够表现真情实感的文学,国家、社会和民族的文学……形式的改良,是解除那些束缚新内容新精神的枷锁镣铐,枷锁镣铐不除,新内容新精神是不会有的。”(17) “近来多少人说:新文学没有好作品,提起笔胡乱地写几行长短句便谓之诗、文,价值何在?我们对于这种批评,是要负相当的责任的。新文学固然是改革形式,内容尤应特别注意,不能说形式上解放了,便一切都会跟着好。要解放形式的缘故,是拿这种解放的形式去欢迎新内容和新精神。”(18)
在新文化运动发生多年以后, 胡适一直把新文化运动称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Chinese Renaissance),表明当年的文学革命及白话诗运动不仅仅是文学界、诗歌界的革命运动。1933年7 月他在芝加哥大学的讲演中(原标题为《当代中国的文化走向》,1933年10月5日胡适改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后英文发表)就用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作为第三章的标题。他说:“其时由一群北大教授领导的新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该运动有三个突出特征,使人想起欧洲的文艺复兴。首先,它是一场自觉的、提倡用民众使用的活的语言创作的新文学取代用旧语言创作的古文学的运动。其次,它是一场自觉地反对传统文化中诸多观念、制度的运动,是一场自觉地把个人从传统力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它是一场理性对传统,自由对权威,张扬生命和人的价值对压制生命和人的价值的运动。最后,很奇怪,这场运动是由既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遗产,又力图用新的批判与探索的现代历史方法论去研究他们的文化遗产的人领导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一场人文主义的运动。在所有这些方面,这场肇始于1917年,有时亦被称为‘新文化运动’、‘新思想运动’、‘新潮’的新运动,都引起了中国青年一代的共鸣,被看成是预示着并表明一个古老民族和一个古老文明的新生的运动。”(19) 为了突出这次运动的成就,胡适甚至认为这是一次很理性的运动:“其领袖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也知道为获得所需,他们必须破坏什么。他们需要新语言、新文学、新的生活观和社会观、以及新的学术。他们需要新语言,不只是把它当作大众教育的有效工具,更把它看作是发展新中国之文学的有效媒介。他们需要新文学,它应使用一个生气勃勃的民族使用的活的语言,应能表现一个成长中的民族的真实的感情、思想、灵感和渴望。他们需要向人民灌输一种新的生活观,它应能把人民从传统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能使人民在一个新世界及其新的文明中感到自在。他们需要新学术,它们应不仅能使我们理智地理解过去的文化遗产,而且也能使我们为积极参与现代科学研究做好准备。依我的理解,这些就是中国文艺复兴的使命。”(20)
宗白华任《学灯》编辑时,刊发了大量郭沫若的白话自由诗,这些诗才真正实现了胡适等新诗革命的早期鼓吹者所追求的“诗体大解放”的理想,堪称真正的“白话自由诗”,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自由诗运动”。但是宗白华在事后仍然不认为白话诗运动是纯粹的诗体大解放运动。他为了祝贺郭沫若五十生辰,在1941年11月10日《时事新报》发表了题为《欢欣的回忆和祝贺》。他指出:“白话诗运动不只是代表一个文学技术上的改变,实是象征着一个新世界观,新生命情调,新生活意识寻找它的新的表现方式。斤斤地从文字修辞,文言白话之分上来评说新诗底意义和价值,是太过于表面的。……在文艺上摆脱两千年来传统形式的束缚,不顾讥笑责难,开始一个新的早晨,这需要气魄雄健,生力弥漫,感觉新鲜的诗人人格。而当年的郭沫若先生正是这样一个人格!他的诗——当年在《学灯》上发表的许多诗——篇篇都是创造一个有力的新形式以表现出这有力的新时代,新的生活意识。编者当年也秉着这意识,每接到他的诗,视同珍宝一样地立刻刊布于《学灯》,而获着当时一般青年的共鸣。……白话诗是新文学运动中最大胆,最冒险,最缺乏凭借,最艰难的工作,它的成就不能超过文学上其他部门原是不足怪的。”(21) 宗白华是当年《学灯》的编者,郭沫若早期的很多优秀诗作都是他编发的。他的这番话颇能说明当时大多数是青年的新诗的编者、作者和读者都具有求新求异,渴望现代新生活的心态。
事实上,鼓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大多因为“年轻气盛”,依靠的是观念的独创性和情绪的力量在进行这次运动,加上他们对传统文化遗产没有很深入的了解和很深厚的感情,并没有真正如胡适所言“理智地理解过去的文化遗产”,而是非理性地否定过去。与诗界革命的领袖相比,他们的“国学”功底和对“国学”的感情逊色很多。即使他们中的有些人对传统的文化遗产很了解,也在反叛传统的历史大潮下故意与传统作对。如胡适完全有能力写文言诗,也写了大量文言诗,却为了当反抗传统诗歌的榜样,“但开风气不为师”,在文学革命期间拒绝写文言诗。“郭沫若是熟习而且能够运用中国文言的华丽,把诗写好的。他有消化旧有词藻的力量,虽然我们仍然在他的诗上找得出旧的点线。但在初期,那故意反抗,那用生活压迫作为反抗基础而起的向上性与破坏性,使我们总不会忘记这是‘一个天真的呼喊’,即或也有‘血’,也有‘泪’,也有自称的‘我是XX主义者’,还是天真。”(22)
守常(李大钊)在1916年8月15日《晨钟》创刊号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23) 在这个“文艺复兴运动”中,“白话诗运动”及文学革命成了急先锋。胡适开始“文学革命”比“五四”运动早三年,时间是1916年,胡适的文学革命是以汉诗革命开始的,白话诗成了“中国的文艺复兴”的真正“先锋”。这种“时代的弄潮儿”的角色使白话诗及白话诗人都无法将其“革命”局限在“诗界”以内,也根本无法不让非诗的因素渗透进去。“我是一个实验主义哲学的信徒,因此,我向我的朋友提议以白话写诗作为试验。1916年7月26日, 我向我在美国的所有朋友宣布:从今以后,我决定不再用文言写诗,而开始以所谓的人民的口头语写诗的试验。刚写了四、五首诗,我即已为我的新诗集想好了一个题目,把它叫做《尝试集》。”(24) 1917年, 《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就刊登了胡适的《白话诗八首》。1918年1月,《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刊登了九首诗, 通常被认为这些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新诗的开端。其中有胡适的《鸽子》、《人力车夫》、《一念》和《景不徙》。文学革命与“五四”运动是相辅相成的,文学革命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文学革命的激进促成了“五四”运动的激进,“五四”运动又极大地提升了文学革命的革命锐气,“五四”运动在政治上的激进极大地促进了新文化运动在文化上的激进,使文学革命及白话诗运动发生了飞跃。1922年3月3日,胡适回忆说:“民国八年的学生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虽是两件事,但学生运动的影响能使白话的传播遍布全国,这是一大关系;况且‘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明白的人渐渐觉悟‘思想革新’的重要,所以他们对于新潮流,或采取欢迎的态度,或采取研究的态度,或采取容忍的态度,渐渐地把从前那种仇视的态度减少了,文学革命的运动因此得以自由发展,这也是一大关系。因此,民国八年以后,白话文的传播真有‘一日千里’之势。白话诗的作者也渐渐的多起来了。民国九年,教育部颁布了一个部令,要国民学校一二年的国文,从九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国语。”(25) “民国九年十年(1920—1921),白话公然叫做国语了。”(26)
由于受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立意高远,境界自出”等内容大于形式的中国诗歌的传统观念影响,加上白话诗运动强调的“新瓶装旧酒”不全是为了诗艺革命本身目的提出来的,带有为当时的政治及文化革命当急先锋的目的,汉诗的“旧瓶”往往是封建旧势力、政治及文化独裁者和保守的“象征”,“新瓶”被视为“自由、民主、现代”的标志,所以作为“新诗的诗体”的“新瓶”的构制工作在新诗草创期只得到了刘半农等少数人的重视,绝大多数新诗诗人重视的是写什么而非怎么写,依靠的是观念的独创性和情绪的力量,而不是依靠语言能力和作诗技法写诗。特别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及对传统的全盘否定,不仅否定了古代汉诗已有的诗体,而且并非古代汉诗独有,外国诗歌也常有的诗应该有“诗体”的诗观也被怀疑和否定,出现了“作诗如作文”、“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等新潮诗观,“新瓶装旧酒”等白话诗运动的激进口号也就失去了意义,“作诗如作文”的实质是“新诗无体”,不仅是对“旧瓶”(旧诗体、旧诗法)的否认,也是对“新瓶(新诗体)的否定。因此新诗一开始就“未成形”——没有形成相对规范和公认的诗体,又怕被主张新潮,以革命为时尚的改革者视为保守,只好对古代汉诗的已有成果保持过度的警惕,慌不择路、饥不择食地求救于外来诗歌和民间诗歌。因为新诗自孕育到诞生都太受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等非诗、非文体革命因素的巨大影响,先天决定了它充当政治革命的先锋而非纯粹意义上的文体革命的先锋的文体特性,加上20世纪是一个革命、战争、运动、改革此起彼伏的动荡时代,是很难静心进行文体建设的特殊时代,更造成思想的诗意的先锋性远远大于文体的诗艺的先锋性,导致整个20世纪新诗文体建设难。如李健吾1935年7月20日在《大公报》发表的《新诗的演变》所说:“从音律的破坏,到形式的试验,到形式的打散(不是没有形式:一种不受外在音节支配的形式,如若我可以这样解释),在这短短的年月,足见进展的迅速。我们或许感觉中间的一个阶段太短了些(无须悲观,因为始终不断有人在努力形式的试验),然而一个真正的事实是:唯其人人写诗,诗也越发难写了。”(27) 实质上没有“诗体”的自由诗成为新诗的霸权诗体,受到极端重视。郑敏在1981年还认为自由诗重在内在结构。她在《诗的内在结构》中说:“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诗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押韵、节拍整齐、有音乐感。但是事实上这种所谓的特征已经不能普遍地运用在所有的诗上了。这自然是因为自由诗的出现和愈来愈多的现代、当代诗人对自由诗的发展和运用。……诗与散文的不同不在于是否分行、押韵、节拍有规律;二者的不同在于,诗之所以成为诗是因为它有特殊的内在结构(非文字的、句法的结构)。”(28) 1929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的废名更是鼓吹自由诗,1943年他在《文学集刊》第一集上发表的诗论的题目就是《新诗应该是自由诗》。他说:“不过老牌的《尝试集》表面上是有意做白话诗而骨子里同旧诗的一派结了不解之缘,后起的新诗作家乃是有心做‘诗’了,他们根本上就没有理会旧诗,他们只是自己要做自己的诗。然而既然叫做‘做’诗,总一定不会是散文,于是他们不知不觉的同旧诗有一个诗的雷同,仿佛新诗自然要有一个新诗的格式。而新诗又实在没有什么公共的,一定的格式,像旧诗的五言七言近体古体或词的什么调什么调。新诗作家乃各奔前程,各人在家里闭门造车。实在大家都在摸索,都在那里纳闷。与西洋文学稍为接近一点的人又摸索西洋诗里头去了,结果在中国新诗坛又有了一种‘高跟鞋’。我记得闻一多在他的一首诗里将‘悲哀’二字颠倒过来用,作为‘哀悲’,大约是为了叶韵的缘故,我当时曾同了另一位诗人笑,这件事真可以‘哀悲’了。”(29) 废名的《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最后几句话是:“我们的新诗应该是自由诗,只要有诗的内容然后诗应该怎样做就怎样做,不怕旁人说我们不是诗了。”(30) 尽管已经过去了二三十年,这个观点与新诗革命时期的新诗应该有“绝端”的自由的激进观点并无多少差别。郑敏和废名在新诗史上堪称“学贯中西”的诗人,谙熟西方诗歌,他们明明知道爆发于20世纪初的西方自由诗革命(free verse revolution)根本没有打破“无韵则非诗”的世界性的作诗原则,西方诗歌更没有出现自由诗体与格律诗体的极端对抗,西方的自由诗完全应该算“准定型诗体”。即使是最激进的美国意象派诗人的“自由诗革命”也没有像中国的新诗革命那样放弃诗的韵律。“自由诗(free verse)不是简单地反对韵律,而是追求散体与韵体的和谐而生的独立韵律。如果意识不到这样的‘第三种韵律’(third rhythm),就无法解释诗失去规则韵律为何不会沦为散文。”(31) 他们也知道新诗的文体资源主要来自西方。梁实秋在1930年12月12日给徐志摩的信中说:“我一向以为新文学运动的最大的成因,便是外国文学的影响;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32) 但是他们却极端地推崇自由诗。“洋诗人”尚且如此,未出国门,不懂外语的“土诗人”当然更迷信自由诗了。
二、“五四”运动对白话诗运动及新诗生成的影响
文学“要是表现了一种风格上或技巧上的根本变革,它可能就是革命的。这种变革可能是一个真正先锋派的成就,它预示了或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实际变革”(33)。“一件艺术品,借助于美学改造,在个人的典型命运中表现了普遍的不自由和反抗力量,从而突破了被蒙蔽的(和硬化的)社会现实,打开了变革(解放)的前景,这件艺术品也可以称为革命的。”(34) 正是人与社会追求自由的革命性与文体自身存在的政治潜能相结合,才导致了文体革命。主要是前者催生了白话诗运动。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政治革命、文化革命、文学革命、诗歌革命、诗体革命中,后者分别是前者的前驱甚至替罪羊,诗体革命首当其冲,自然会出现极端的“诗体大解放”。“五四”运动是最有说明力的个案。“五四”运动带来了中国全方位的改革,新诗的真正涌现,正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因此“五四”运动时期的新诗便带有鲜明的“政治”文化革命运动的时代烙印,文学及诗的平民性、抒情性、通俗性、宣传性都得到了极端的重视,还出现了极端怀疑旧诗、极度轻视已有诗体甚至基本作诗法则的倾向。
正是因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稍后“白话诗运动”的倡导者们总结了政治上的“戊戌变法”及维新运动,和诗歌中的“诗界革命”的失败原因都是太重视虚无的精神,轻视具有操作性的对体制形式的彻底革命,才有了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彻底废除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制的政治革命。诗歌革命也如同政治革命,由渐变的改良转入突变的革命。诗歌革命者想彻底改变汉语诗歌的文体秩序,特别是诗体秩序,用体现现代人的民主自由思想的自由诗体来取代呈现大一统的封建政治秩序的定型诗体。即20世纪1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反叛、大革命时期,反叛与革命都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是不顾一切不计后果的。政治家们开始了推翻清朝政治体制的政治革命,文化界出现了质疑并否定传统的新文化运动,语言界出现了白话取代文言的主张,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以使用白话为荣的时尚,诗歌界出现了用无韵、无诗体的白话自由诗取代以定型诗体为生的文言诗的热潮。特别是“五四”运动,更具有浓郁的反传统色彩。“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从最开始的时候便强调批评的精神,……五四运动原是一种文化觉醒运动,……要救国,必须传播新的思想,所以必须要推动口语,作为传播的媒介,使新文化的意识与意义得以普及大众。要他们觉醒到国家的危机,必须对旧文化的弊病作全面的攻击,在当时,新思想者不假思索的揭传统文化的疮疤,呈露着一种战斗意识的批评精神,当时的凶猛程度,我们现在看来,是相当情绪化的,对于传统文化中一些对新文化新社会仍具有启发意义的美学内容及形式甚至生活、伦理的观念,对于它们的正面作用完全一笔抹杀者,大有人在。在当时的激流中,要停下来不分新旧只辨好坏完全客观而深思熟虑地去处理文学者实在不多,而且亦非当时的主流。”(35) 五四给我们的贡献最大者莫过于怀疑精神,反对人云亦云的批评态度,对传统的批评方法有极大的修正作用,怀疑精神所引发的必然是寻根的认为,在五四时期,由于对西洋思想方式及内容过度一厢情愿的认识,而不能对传统文化作寻根的认识到其正面价值的再肯定。(36) 在怀疑过去、否定历史甚至与传统为敌的生态中问世的新诗,必定把新旧作为判断好坏的唯一标准,当然会打倒旧诗,把对新诗有启发意义和借鉴意义的旧诗的诗体传统一笔抹杀掉。
“五四”运动对诗人的影响是巨大的,改变了很多诗人的诗歌观念和学术观念,甚至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道路。1988年,梁实秋的《关于鲁迅》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再版,其中收录了他的《五四与文艺》一文,他尖锐地指出了文学革命及新诗革命的不足:“我以为新诗如有出路,应该是于模拟外国诗之外还要向旧诗学习,至少应该学习那‘审音协律敷辞惔藻’的功夫。理由很简单,新诗旧诗使用的都是中国文字,而中国文字,如周先生所说,是先天的一字一音以整齐对称为特质。这想法也许有人以为是‘反动’或‘反革命’,不过我们不能不承认,文学传统无法抛弃,‘文学革命’云云,我们如今应该有较冷静的估价了。”(37) 1991年,台湾三民书局出版了苏雪林的回忆录《浮生九四》。“她进一步谈到,五四对她最大的影响便是‘理性主义’。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揭橥两大宗旨,一曰科学(science),一曰民主(democracy)。科学的精神是‘求真’,‘求是’,就是把传统的一切都提出来问问,都重新加以估定。我们的思想便起了革命。不过,抛弃旧的时,不能连婴儿和浴盆的水都泼了出去,应加以评审选择,这才是真正的‘理性主义’。”(38) 郑敏也在1993年2月在《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诗歌语言变革与中国诗歌新诗创作》中指出:“考虑当时遗老遗少们对文言文的依附,当时白话文运动所受到四面的包围和压力,胡、陈及郑振铎等人奋力为白话文运动打开局面的勇气和热情是值得我们今天的敬重。但是从思维方式和对语言的性质的认识,我们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又不得不对他们那种宁左勿右的心态,和它对新文学,特别是新诗的创作的负面影响作一些冷静的思考。总之他们那种矫枉必须过正的思维方式和对语言理论缺乏认识,决定了这些负面的必然出现。语言主要是武断的、继承的、不容选择的符号系统,其选择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39) 这些中肯的评价,说明“五四”运动及新诗革命对传统确实缺乏必要的科学的理性态度。“五四”运动不仅是白话诗运动无法成为纯粹的诗歌文体革命的重要原因,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诗文体的基本形态,如在内容上的高度严肃和在形体上的极端自由,特别是新诗在写什么上形成了高度的严肃性和抒情性特质,诗的启蒙功能和先锋意识分外强烈,尤其是使新诗在孕育和草创期承载了过多的政治、思想、文化改革的重任。正是因为新诗一问世就负担了过多的社会职能及教化功能,严重影响了它的文体建设。“老实说,五四以来,中国的新诗走的可以说是一条没有前途的狭路,所受的影响也脱不了西洋浪漫主义诗歌的坏习气,把原来极为广阔的领土限制在(一)抒情和(二)高度严肃性这两道界限中间。我们自以为解除出了旧诗的桎梏,谁知道我们把自己束缚得比从前更紧。中国旧诗词在形式上限制虽然很严,可是对题材的选择却很宽:赠答、应制、唱和、咏物、送别,甚至讽刺和议论都可以入诗。如果从十九世纪的浪漫派的眼光看来,这种诗当然是无聊,内容空洞和言之无物,应该在打倒之列。可是现代诗早已扬弃和推翻了十九世纪诗的传统而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现代英国诗人,后入美国籍的奥登(W.H.Auden)曾经说过:‘诗不比人性好,也不比人性坏;诗是深刻的,同时却又是浅薄的,饱经世故而又天真无邪,呆板而又俏皮,淫荡而又纯洁,时时变幻不同。’最能代表现代诗的精神。”(40) 1911年英国政治学家罗布豪斯(L.T.Hobhouse)在《解放主义》(Liberalism)一书中结论说:“19世纪可以被称为解放主义(Liberalism)的年代,尽管深入观察那个伟大运动,其结局带来了最低潮。”(41) 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是人类诗歌艺术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世界文学的“现代运动”(modern movement)的草创期。中国的白话诗运动是这次“现代运动”的一部分,它也受到了这次“现代运动”的代表、特别是世界性的自由诗革命(free verse revolution)主要代表意象派诗歌运动的影响。但是中国国情及白话诗运动的非诗化的激进态势决定了新诗诗人不但更容易选择意象派的激进派诗人的诗观,而且还会夸大意象派诗歌的诗体自由化和散文化变革。胡适的“作诗如作文”的诗歌改革观和意象派,特别是以庞德为代表的强调诗的文体纯洁性的意象派对“文”的重视有本质上的差异。新诗舍弃了意象派诗歌重视艺术、强调意象、反对诗的过度散文化和诗体的自由化等精华。因此极端的改革——白话诗运动,并没有让汉语诗歌赶上世界现代诗歌变革的潮流,汉语诗歌的唯一的“现代诗”——新诗,不仅在当时缺乏意象派诗歌具有的“现代诗品质”,而且在百年后的今天,仍然缺乏50年前的奥登所说的“现代诗的精神”。
注释:
① [美]加斯特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共和革命运动》,[美]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8页。
② 吴组缃、季镇准、陈则光:《中国近代文学鸟瞰——大系·总序》,《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轨迹》,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③ 胡适:《新文学的意义》,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胡适演讲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④⑤ 胡适:《尝试集自序》,耿云志:《胡适论争集》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9—280页、第280页。
⑥ 俞平伯:《诗底自由和普遍》,《新潮》第3卷第1号,1921年10月1日《新潮(影印本)》第二册,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75—76页。
⑦ 刘半农:《译诗十七首》,《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1918年9月15日第五卷合订本,第230—234页。
⑧ 刘大白:《人话文与鬼话文》,《文学周报》合订本第八卷,远东图书公司1929年版,第678—679页。
⑨ 梁实秋:《我也谈谈“胡适之体”的诗》, 耿云志:《胡适论争集》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页。
⑩(11)(12)(15) 周作人:《文学革命运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人文书店1932年版,第100—101页,第105—107页,第111—112页,第100页。
(13) 长虹:《新文学的希望》,《莽原》第五期,1925年5月22日。
(14) 仲云:《新文艺的建设》,《文学周报》第四卷,开明书店1928年版,第81—87页。
(16)(19)(20)(24) 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 耿云志:《胡适论争集》中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3页,第1629页,第1630页,第1632页。
(17)(18) 胡适:《新文学的意义》,杜春和、韩荣芳、 耿来金:《胡适演讲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251页、第255—256页。
(21) 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143页。
(22) 沈从文:《论郭沫若》,黄人影:《郭沫若论》,光华书局1931年版,第6—7页。
(23) 守常:《“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一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0页,原载1916年8月15日《晨钟》创刊号。
(25)(26)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耿云志:《胡适论争集》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第123页。
(27) 李健吾:《新诗的演变》,郭宏安:《李健吾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28) 郑敏:《诗的内在结构》,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下编,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第366页。
(29)(30) 废名:《新诗应该是自由诗》,《论新诗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第23页。
(31) Northrop Frye.Anatomy of Criticism.New Jers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272.
(32) 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上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页。原载1931年1月20日《诗刊》创刊号。
(33)(34) [美]赫·马尔库塞著,绿原译:《现代美学析疑》,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第2页。
(35)(36) [美]叶维廉:《中国诗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0—11页,第12页。
(37)(38) 陈漱渝:《五四文坛鳞爪》,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 第52页。
(39)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诗歌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吕进,毛翰:《中国诗歌年鉴》1993年卷,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页。
(40) 林以亮:《美国诗选序》,今日世界出版社1976年版,第1页。
(41) L.T.Hobhouse.Liberalism.London:Richard and Sons,Ltd.,1911.214.
标签:政治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胡适论文; 读书论文; 新青年论文; 学灯论文; 诗体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