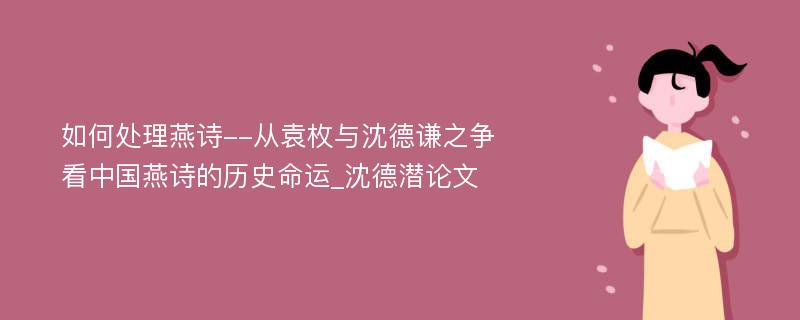
艳诗该如何对待——由袁枚、沈德潜之争谈中国艳诗的历史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艳诗论文,该如何论文,之争论文,中国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艳诗,《汉语大词典》解释为“以男女爱情为题材的诗歌”,相关的称呼还有艳歌、情诗、艳体诗、艳情诗、爱情诗等。实际上,古代“艳情”的范围远远比现代“爱情”复杂得多。中国艳诗源远流长,其绝对数量虽不算少,但一般认为中国艳诗并不发达,有时中国诗里的男女爱情,看起来远不如同性朋友间的情谊笃厚①。而更有意味的是,历代不仅对艳诗的评价大相径庭,在艳诗的理解上也存在很大分歧,有的阐释者有意识地调整、置换诗歌的重心,把男女情爱的描写引向政治或道德伦理的框架中。因此,尽管学界对中国艳诗已展开过多次讨论,亦取得了若干共识,但中国艳诗似仍未得到合理对待,一些应进入研究视野的作家作品很长时间被冷落。艳诗究竟该如何对待?我想袁枚与沈德潜因王彦泓《疑雨集》引起的论争是一个很好的窗口,由此正可透视中国艳诗的历史命运,进而探讨如何以更宽广更通达的视野来对待中国艳诗。
一、《疑雨集》:袁枚、沈德潜之争的焦点
袁枚和沈德潜之争,是由沈德潜选清诗引起的。袁枚先写了《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对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的编选原则“诗贵温柔,不可说尽,又必关系人伦日用”颇不以为然②;后语意未尽,又写了《再与沈大宗伯书》③,专门对沈德潜不选王彦泓(字次回)《疑雨集》进行质疑,信的开头说:
闻《别裁》中独不选王次回诗,以为艳体不足垂教。仆又疑焉。夫《关雎》即艳诗也,以求淑女之故,至于辗转反侧,使文公生于今,遇先生,危矣哉!《易》曰:“一阴一阳谓之道。”又曰:“有夫妇然后有父子。”阴阳夫妇,艳诗之祖也。
接下来,袁枚以史实说明写艳诗与人的品行没有直接关系,并指出沈德潜最尊崇的王士禛在创作上也深受“才藻艳绝”的王彦泓的影响:
傅鹑觚善言儿女之情,而台阁生风;其人,君子也。沈约事两朝,佞佛,有绮语之忏;其人,小人也。次回才藻艳绝,阮亭集中,时时窃之。先生最尊阮亭,不容都不考也。
进而袁枚对选诗之道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诗之道大而远”,选者应该具备史家意识,“无庸拘见而狭取之”:
选诗之道,与作史同。一代人才,其应传者皆宜列传,无庸拘见而狭取之。宋人谓蔡琰失节,范史不当置《列女》中,此陋说也。夫《列女》者,犹云女之列传云尔,非贞烈之谓。或贤或才,或关系国家,皆可列传,犹之传公卿,不必尽死难也。诗之奇、平、艳、朴,皆可采取,亦不必尽庄语也。杜少陵,圣于诗者也,岂屑为王、杨、卢、骆哉?然尊四子以为万古江河矣。黄山谷,奥于诗者也,岂屑为杨、刘哉?然尊西昆以为一朝郛郭矣。宣尼至圣,而亦取沧浪童子之诗。所以然者,非古人心虚,往往舍己从人;亦非古人爱博,故意滥收之。盖实见诗之道大而远,如地之有八音,天之有万窍,择其善鸣者而赏其鸣足矣,不必荣宫商而贱角羽,进金石而弃弦匏也。
在信的最后,袁枚认为诗人不必兼善众体,只要“就其诣之所极”,就应该兼收之,提出“艳诗宫体,自是诗家一格”:
且夫古人成名,各就其诣之所极,原不必兼众体。而论诗者,则不可不兼收之,以相题之所宜。即以唐论:庙堂典重,沈、宋所宜也;使郊、岛为之,则陋矣。山水闲适,王、孟所宜也;使温、李为之,则靡矣。边塞风云,李、杜所宜也;使王、孟为之,则薄矣。撞万石之钟,斗百韵之险,韩、孟所宜也;使韦、柳为之,则弱矣。伤往悼来,张、王、元、白所宜也;使钱、刘为之,则仄矣。题香襟,当舞所,弦工吹师,低徊容与,温、李、冬郎所宜也;使韩、孟为之,则亢矣。天地间不能一日无诸题,则古今来不可一日无诸诗。人学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要在用其所长而藏己之所短则可,护其所短而毁人之所长则不可。艳诗宫体,自是诗家一格,孔子不删郑、卫之诗,而先生独删次回之诗,不已过乎?至于卢仝、李贺险坚一流,似亦不必摈弃。两家所祖,从《大招》、《天问》来,与《易》之龙战,《诗》之天妹,同波异澜,非臆撰也。一集中不但艳体宜收,即险体亦宜收。然后诗体备而选之道全。谨以鄙意私于先生,愿与门下诸贤共详之也。
袁枚《再与沈大宗伯书》大约写在乾隆二十六年左右④,是针对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凡例》中的:“诗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可为存,所谓其言有物也。若一无关系,徒辨浮华,又或叫号撞搪以出之,非风人之旨也。尤有甚者,动作温柔乡语,如王次回《疑雨集》之类,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而发的⑤,他与沈德潜一主艳情,一反艳情,文学观念尖锐对立,势如水火,王彦泓《疑雨集》无疑是冲突的具体焦点。
面对袁枚的质疑,沈德潜并没有回应,或许他根本不屑于回应,因为这是他一贯的选诗主张,二十多年前编选《明诗别裁集》时,沈德潜就声明屏去“浮艳淫靡”之作⑥;四十多年前编选《唐诗别裁集》时,沈德潜就明确指出:“《诗》本六籍之一,王者以之观民风,考得失,非为艳情发也。……集中所载,间及夫妇男女之词,要得好色不淫之旨,而淫哇私亵,概从阙如。”⑦而袁枚则一直对沈德潜不选王彦泓诗耿耿于怀,后来撰写《随园诗话》时旧事重提:“本朝王次回《疑雨集》,香奁绝调,惜其只成此一家数耳。沈归愚尚书选国朝诗,摈而不录,何所见之狭也!尝作书难之云:‘《关雎》为《国风》之首,即言男女之情。孔子删诗,亦存《郑》、《卫》,公何独不选次回诗?’沈亦无以答也。”⑧
二、袁枚、沈德潜之争的不同回响
袁枚、沈德潜关于王彦泓《疑雨集》该选不该选的争论,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后来评论者的热门话题,斥责袁枚者有之,折中者有之,批评沈德潜者亦有之。
斥责袁枚者,当以章学诚最为激烈,从他抨击袁枚《随园诗话》的话语,不难推断他对袁、沈之争的立场:
略《易》、《书》、《礼》、《乐》、《春秋》而独《毛诗》;《毛诗》之中,又抑《雅》、《颂》而扬《国风》;《国风》之中,又轻国政民俗而专重男女慕悦;及男女慕悦之诗,又斥诗人风刺之解而主男女自述淫情;甚且言采兰赠芍,有何关系而夫子录之,以驳诗文须有关系之说。自来小人倡为邪说,不过附会古人疑似以自便其私,未闻光天化日之下,敢于进退六经,非圣无法,而恣为倾邪淫宕之说,至于如是之极者也!⑨
“甚且言采兰赠芍,有何关系而夫子录之,以驳诗文须有关系之说”虽针对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选家选近人之诗,有七病焉。……动称纲常名教,箴刺褒讥,以为非有关系者不录。不知赠勺采兰,有何关系而圣人不删”⑩而发,实也可看作对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再与沈大宗伯书》的指斥。章学诚的文学观与沈德潜虽不尽相同,但在根本上是相通的,都遵循儒家的诗教观,教化意味浓厚。因此,他对袁枚“进退六经,非圣无法”之举极为不满,挥舞封建道德的大棒向袁枚进行挞伐。另如:
声诗三百,圣教所存,千古名儒,不闻异议。今乃丧心无忌,敢侮圣言,邪说倡狂,骇人耳目。六义甚广,而彼谓《雅》、《颂》劣于《国风》;《风》诗甚多,而彼谓言情妙于男女。凡圣贤典训,无不横征曲引,以为导欲宣淫之具,其罪可胜诛乎!(11)
章学诚对袁枚如此深恶痛绝,以致于欲除之而后快。当听说刘墉欲诛杀袁枚时,章学诚认为刘墉是“知所务矣”,并赞扬刘墉“有古大臣之风烈”,而对老师朱筠为袁枚求情,则深表遗憾(12)。
章学诚之后论及袁、沈之争斥责袁枚者为数不少,至当代仍不乏章学诚的同调,如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简史》认为:“袁以王次回的《疑雨集》为香奁绝调,为书难沈,不选其诗。是则他所指的艳诗,纯粹是黄色的毒物,乃用《关雎》来为之辩护,这是一种重大的歪曲。”(13)
也有一些批评家在评论袁、沈之争时并不简单地站在哪一方,而是具体分析,平判是非。如黄培芳《香石诗话》:
《再与沈公书》则驳其明诗独不选王次回诗,至引孔子删诗,首《关雎》而不去郑、卫。论固大矣,愚窃不谓然。书词有云:“《关雎》即艳诗也。”此语大谬。孔子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小序》曰:“《关雎》,太姒之德也。”御纂《诗义析中》曰:“《关雎》,文王之本也。”此古今圣贤定论,岂寻常写艳可比,何得援此藉口?试观次回《疑雨集》,果能不淫不伤否乎?孔子删诗,贞淫并录。贞者为万世法,淫者为万世戒,终不离乎“思无邪”之旨,非存采兰赠勺之句与后人学也。若沈公之选明诗,不过备一代诗格,为学者取法,亦能如孔子之意,存次回作以为戒乎?不存以为戒,宁必存以为法乎?次回艳诗自在,好之者选之读之,自无不可;而沈公不以入选,持一家之论,亦未尝不是。至作书难之,妄引圣人,甚不伦矣。抑《别裁》一集,遗美颇多,不他之问,而是之问,何耶?书词又云:“以求淑女之故,至于辗转反侧,使文王生于今遇先生,危矣哉!”此徒取快意,复成何议论?谓足以折服沈公之心乎?论诗未尝废香奁一体,余非恶夫艳诗也,恶夫附会之言邻于非圣,启后生无忌惮之渐,故辨之。(14)
黄培芳论诗虽也持儒家诗教观,但他对袁、沈之争的辨析也有不少合理之处。首先,黄培芳对艳诗并非一味地排斥,他虽尊崇《诗经》,对袁枚引《诗经》为王彦泓艳诗辩护的“非圣”之举不满,却赞成艳诗为诗中一体,“好之者选之读之,自无不可”。在《香石诗话》中,黄培芳还举了王隼《无题》诗一百首中的若干句子,如“合欢枝上结相思,不断缠绵是兔丝”、“欲扑流萤懒下阶,愿随明月入君怀”、“侍儿亦解相思苦,偷种当归与合欢”之类,认为“皆情深韵远”(15),而这些诗句不啻《疑雨集》复出。其次,黄培芳认为沈德潜之所以不选王彦泓诗,是因为他编选《国朝诗别裁集》是“备一代诗格,为学者取法”,这对理解和把握沈德潜的选诗原则富有启发意义。既然目的是为学诗者提供范本,强调“温柔敦厚”,排斥“缘情绮靡”,就很好理解了。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对袁、沈之争的评述与黄培芳近似,他虽然认识到“袁枚的原意未尝不是为救弊而发,他想拿性灵二字来医诗学界那些讲空架子或搬弄书卷的毛病”,但对袁枚臆解经典以饰其说也颇有微词:
袁枚主张那种绘画媟亵状态的《疑雨集》实在已经和起初的艳歌大相径庭,《关雎》诗,经学家的解说当然很多,我们不暇征引;但即请看《关雎》的本文,又岂有丝毫和《疑雨集》那种艳体诗相近的地方?他拿《易经》的话来比譬更是有意取闹。(16)
在叙及袁、沈关于选不选王彦泓《疑雨集》这段公案时,赞成袁枚者在清代也不乏其人,他们多批评沈德潜的褊狭和道学气。如叶德辉《重刻〈疑雨集〉序》认为沈德潜“兢兢别裁,殆不免于村夫子之见矣”,并希望后之人“续金坛之艳缘,祛归愚之腐习,庶乎榛苓香草,不失风骚之传”(17)。到了当代,随着文学观的嬗变,儒家诗教观开始受到批判,“文以载道“的意识被重新审视,赞成袁枚、批评沈德潜逐渐成了学界的主导倾向。如邬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认为沈德潜拘守封建伦常而泯灭个人情感,“袁枚对沈氏的批评十分有力。”(18)袁济喜《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指出,袁枚对沈德潜的批驳“有力地回击了沈德潜在格调的幌子下,对于男女爱情诗的一概封杀”(19)。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直斥沈德潜为“矫饰虚伪的假道学”(20);在《中国文学史新著》中进一步对袁、沈之争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指出袁枚以一种旷放不羁、轻视名教的个人姿态,在文学理论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冲决传统诗教的激进主张,把自晚明即已开始,在清初受到阻断,以李贽“童心说”、袁宏道“性灵说”为代表,合乎人性的文学思想重又标举了出来(21)。
三、中国艳诗的历史命运
袁、沈之争及其后来的不同回响,说明不同的评论者对艳诗的理解差异很大,态度也因之大相径庭。综合历代对待艳诗的态度,大致有三种方式:
1.对艳诗的口诛笔伐。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指出:
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繇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其颂祝主人,悦媚豪右之作,可无俟言。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否则悲慨世事,感怀前贤,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倘其嗫嚅之中,偶涉眷爱,而儒服之士,即交口非之。况言之至反常俗者乎?(22)
鲁迅把中国文学中“嗫嚅之中,偶涉眷爱”之作放在“心应虫鸟,情感林泉”、“悲慨世事,感怀前贤”之上加以肯定的同时,也注意到中国主流观念对待艳诗的基本态度:“交口非之”。中国历代“儒服之士”的行列极为庞大,如俞樾《秦肤雨诗序》在梳理了诗坛“丽”与“则”的关系源流之后,指责王彦泓为“风雅之罪人”:
扬子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是知古所谓诗人词人者,虽有则与淫之别,而丽则一也。……若夫唐人温、李之诗,寄托遥深,实古风骚之遗韵,而沿其体者,徒拾浮华,不存古意。至宋初杨、刘诸公衍为西昆体,则又丽而不则矣。其弊也,以韩致光《香奁》为滥觞,极而至于国朝王次回之《疑雨集》,丽而不则,又入于淫,斯风雅之罪人矣。(23)
吊诡的是,批评艳诗的“儒服之士”,有的本身也爱写艳诗。据皮日休《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记载,白居易选拔人才时“荐凝而抑祜”,就是因为张祜好写乐府艳发之词,而徐凝的诗风朴略椎古。当令狐楚向元稹奉上张祜诗,元稹说的是:“雕虫小技,或奖激之,恐害风教”。其实当时艳诗写得最多、最好的恰恰是元稹和白居易,文学史上所谓的“元和体”,指的主要是那些“浮靡艳丽”的艳诗(24)。杜牧很同情张祜的遭遇,曾借李戡之口说:“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煽之于诗,如风之疾速。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交售,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25)。口吻与章学诚对袁枚的抨击何其相似!而杜牧自己又如何呢?“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已如自己轻狂放荡的自供状,以“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来赞美青楼女子,其“浮靡艳丽”并不比“元和体”逊色(26)。不选王彦泓艳诗的沈德潜本人又如何呢?他不也曾为苏州名妓张忆娘偶赋闲情吗?袁枚以此为佳话,书之《随园诗话》(27);有研究者注意到,除《题簪花图遗照》外,沈德潜《归愚诗钞》,表现男女风怀的作品还有不少(28)!
2.对艳诗的删除
中国古代文人编集时,不录艳诗是常态,这恐怕是我们感觉艳诗不发达的原因之一。有时是编者所为,为尊者讳,有时则是作者自己有意为之。那些坚持把艳诗入集的文人反而不被理解,成了另类。袁枚《答蕺园论诗书》开头说:“来谕谆谆教删集内缘情之作,云‘以君之才学,何必为白傅、樊川自累’。”(29)蕺园即程晋芳,他与袁枚相交甚深,他劝袁枚删去缘情之作,主观上无疑是为袁枚考虑,是爱惜袁枚的。其实,谆谆教袁枚将集中缘情之作大加删削的不只有程晋芳,还有朱珪。在给袁枚的书信中,朱珪以朱彝尊《竹垞先生集》不删《风怀二百韵》为恨事,以至于痛哭流涕(30)。袁枚当然没有听从程晋芳、朱珪的规勉,但由此不难想见,在编集时删削艳诗,在很多人看来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有些被删削的艳诗偶然会流传下来,但大多数被删削的艳诗可能就此了无踪迹了。
更为极端的是,有的甚至把删削的大斧砍向流传已久的前代作品。如朱熹的三传弟子王柏,不明白为什么一些“淫诗”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诗经》这部经典中,竟主张把它们全部逐出《诗经》,“一洗千古之芜秽(31)!
3.对艳诗的辩护
上文我们提到,在与沈德潜的论争中,袁枚搬出儒家经典为艳诗存在的合理性辩护,认为《诗经》、《周易》都有描写男女之情的作品,既然连圣人孔子和周公都不废艳诗,那么后人有什么理由排斥艳诗呢?而这恰恰触动了“儒服之士”最敏感的神经,章学诚抨击袁枚“混侧清流,妄言文学,附会经传,以圣言为导欲宣淫之具,蛊惑少年,败坏风俗人心,真名教中之蟊贼,非仅清客之谓也”(32),针对的就是袁枚诸如此类的言论。
袁枚的理解是否合理且不去管它,但把《诗经》中“风”理解为艳诗,并不是袁枚的首创。明代大戏曲家汤显祖,曾借杜丽娘之口指出《诗经》首篇《关雎》并非歌咏后妃之德,而是一首热烈的恋歌(33)。具有极高文学悟性的理学宗师朱熹,很早就对视为金科玉律的以“美刺之说”阐释《诗经》大义的做法产生了怀疑,在《诗集传序》中说:“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在此认识基础上,他把《诗经》国风中三十首诗定性为“淫诗”(34)。“淫诗”这个名称本身虽意味着否定,是对艳诗的贬称,事实上,只要在朱熹解读的基础上变化一下价值判断,就与袁枚的解读相差不远了。换言之,袁枚对《诗经》中艳诗的理解,其实质与朱熹是相通的,不过价值判断的方向相反而已。当朱熹识破“淫诗”的真相后,他对《诗经》中何以会收入“淫诗”,做了煞费苦心的解释:“圣人删录,取其善者以为法,存其恶者以为戒,无非教者,岂必灭其籍哉!”正像莫砺锋先生分析的那样,朱熹的这些话都不够理直气壮,在逻辑上也不够严密。他明白那些爱情诗本是民间的歌谣,是民间的男女自道其情、自叙其事的作品。但他无法说明为什么它们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诗经》这部经典中,为什么孔子也不将它们删去,于是只好勉强地以“为戒”二字解之(35)。
为了提高艳诗的地位,以比兴寄托来解释艳诗就成了必然。陆游因李商隐无题诗多狎邪之语而加以指摘,清人吴乔对此不以为然,不承认李商隐的无题诗是写艳情的,指出“无题诗十六篇,托男女怨慕之辞,而无一言陈本意,不亦《风》、《骚》之极致哉。”(36)为此,吴乔写了《西昆发微》,专门选评李商隐的无题诗(37)。章学诚也认为“古人思君怀友,多托男女殷情”(38),说明他其实也不排斥书写男女之情,只不过要施予道德的装饰罢了,这实即沈德潜所说的“词则托之男女,义实关乎君臣友朋”(39)。侯文灿在刊刻《疑雨集》时,也曾为之辩护:
次回先生穷年力学,屡困场屋。断瑶琴,折兰玉。其坎坷潦倒,实有屈子之哀,江淹之恨,步兵之失路无聊,与杜少陵无家垂老之忧伤憔悴。而特托之于儿女丁宁,闺门婉恋,以写其胸中之幽怨,不得概以红粉青楼、裁云镂月之句目之也。(40)
钱钟书《中国文学小史绪论》曾对中国艳诗的历史境遇作了十分精到的概括:
同一《无题》诗,伤时感世,意内言外,香草美人,骚客之寓言,子之夭桃,风人之托兴,则尊之为诗史,以为有风骚之遗意。苟缘情绮靡,结念芳华,意尽言中,羌无寄托,则虽《金荃》丽制,玉溪复生,众且以庾词侧体鄙之,法秀泥犁之诃,端为若人矣!此《疑雨集》所以不见齿于历来谭艺者,吴乔《围炉诗话》所以取韩偓诗比附于时事,而“爱西昆好”者所以纷纷刺取史实,为作“郑笺”也。究其品类之尊卑,均系于题目之大小,而所谓大小者,乃自世眼观之,初不关乎文学;由世俗之见,则国家之事为大,而男女爱悦之私,无关政本国计,老子、韩非为学派宗师,而虬髯客、毛颖则子虚乌有之伦,宜其不得相提并论矣。(41)
四、艳诗的文学史书写
当我们仔细梳理与袁、沈之争的相关资料后,一个悖论出现了:经过长期的争论,目前学界一般都肯定和赞成袁枚的观点,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就认为,袁枚公开为写男女之情的诗歌张目,“在当时颇有振聋发聩之效”(42);但具体到对王彦泓《疑雨集》的评价似乎仍站在沈德潜一边——《疑雨集》并未进入《中国文学史》的视野。其实,类似的悖论在《疑雨集》最早被刊刻时就已出现,严绳孙《疑雨集序》说:
诗发乎情,而《王风》之变,桑中洧外,列在三百,为艳歌之始。其后《读曲》、《子夜》,寂寥促节。在唐则玉溪惝怳,旨近楚骚;韩相香奁,言犹微婉。于是,金坛王先生彦泓,以闳肆之才,写宕往之致。穷情尽态,刻露深永,可谓横绝今古也。今《疑雨集》之名籍甚,江左少年传写,家藏一帙,溉其余渖,便欲名家,而本集顾未有锓板以传者。侯子蔚鬷,读而赏之。爰加校定,付之剞劂。由是,先生之诗,显然共之天下矣。嗟乎!金沙当承平之日,甲第相望。一时裙屐子弟,席华膴,擅才情,平居以声色相征逐,拂袖挂钗,留髠送客之事,习为故常。至于擘笺刻烛,才亦足以副之。故当日能诗之士,盖多其人,而风尚所归,并同一辙。虽其酣嬉荡轶,不可谓为正音,然由后以观盛衰之端,感慨系之矣。余既喜蔚鬷之能刻是诗,而因征论其世,以俟后之览者定焉。(43)
严绳孙表现出一种文学史家的眼光,在中国艳诗发展的脉络中为王彦泓《疑雨集》作了定位。“横绝今古”可不是随便就可给的评价,严绳孙无疑对《疑雨集》推崇备至!然而,批评与嗜好的矛盾如此错综交织:从描写艳情的层面看是“横绝今古”,而从诗教的视角却是“不可谓为正音”。沈德潜又何尝没感受到《疑雨集》强大的冲击力,“最足害人心术”,如果转换一下价值判断,不就是最具有打动人的力量么?认识到《疑雨集》强大感染力的文人还有很多,如黄遵宪曾向日本宫岛诚一郎推荐《疑雨集》,认为王彦泓“天赋艳才,最能写男女之事,无微不备”。(44)
既然如此,王彦泓《疑雨集》为什么长期被文学史家冷落呢?答案还得从《疑雨集》文本中去寻找。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在论述袁、沈之争时指出:
随园之言性情,是也。其失则在特重男女狎亵之情。归愚摒王次回诗,以为艳体不足垂教,随园争之,以为《关雎》即为艳诗,又曰:《易》曰:“一阴一阳谓之道。”又曰:“有夫妇然后有父子”,阴阳夫妇,艳诗之祖也。其说甚辩,然以次回《疑雨集》,与《随园诗话》所举随园、香亭兄弟之诗论之,非特与男女性情之得其正者无当,即赠勺采兰,亦不若是之绘画裸陈也。章学诚《文史通义》篇斥为“洪水猛兽”,言虽过当,持之盖有故。性情之说,本为国人旧论,若因风趣二字,遂使次回一派,以孽子而为大宗,固不可矣。(45)
朱东润先生将艳诗所表达的男女之情分为三种类型:“男女性情之得其正者”、“赠勺采兰”与“绘画裸陈”,在他看来,每种类型的价值并不等同,而《疑雨集》所写男女之情多为“绘画裸陈”的“狎亵之情”,过了情的界限,所以朱东润先生虽认为袁枚所说“甚辩”,在对《疑雨集》的评价上,还是更接近沈德潜。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的上述论断大概曾受到日本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的启发,后者对袁、沈之争的评述更为具体:
沈德潜以王次回诗为“害人心术”的“温柔乡语”而加以斥责,与此相反,随园则云“香奁诗,至本朝王次回,可称绝调”而予以激赏。王次回诗究竟如何,为便于说明,现举其《个侬》诗如下……这首诗大概是宿于妓馆的翌日所写。其此类诗句如“难藏靥晕依微笑,已露眉湾黯澹愁”……“未形猜妒思犹浅,肯露娇嗔爱始真”等,皆无非是对偎香倚玉、猜妒娇嗔的冶态柔情的细致描摹,而这也正是随园所称誉的“绝调”。对于所谓的情歌与艳诗,既不应一概加以排斥,也不可一味沉迷其中,而必须根据各种不同的实际情况,分析其情感抒发的诚挚程度以及艺术表现的形式特点,然后判断其在文学上的价值如何。有时某种作品在道德风教方面不足为训,而在文学方面却颇有价值,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乏其例的。在这方面,如果说沈德潜之见可谓“不及”,那么袁枚之见可谓“过”了。但若就王次回的艳诗看,我倒宁可赞成沈氏之见。(46)
朱东润、铃木虎雄所论实为持平之见,在大的原则上我们并没有不同意见,对于艳诗,当先看其性质如何,再论其艺术如何,艳诗可以艳冶、亲密,但不可流于轻薄与狎亵,狎亵的艳诗是不应该邀入文学经典之列的,受到文学史家的冷落,自然不足为怪。换言之,文学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遴选经典,诠释经典,轻薄、狎亵的艳诗从文学史家的视野中淡出乃为题中应有之义。问题是,如何界定轻薄与狎亵?不同时代,人们对轻薄与狎亵的理解并不相同,如朱熹眼中的“淫诗”,我们今天却公认为“爱情诗”,相去何止千里。即使同一时代,不同人的心目中,轻薄与狎亵内涵也有差异。王彦泓《疑雨集》的实际情况如何呢?
王英志《袁枚评传》曾把《疑雨集》中写男女之情的诗歌分为五类:写年轻少女对爱情的向往,如《花烛》、《催妆》等;写新婚少妇幸福、羞涩的心理活动,如《无题》、《即事》等;写对死去伴侣的思念之情,如《死别》、《空屋》等;表白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如《和于氏诸子秋词》、《感遇》等;有个别写倚香依玉之冶态者,如《个侬》。在这五类中,前四类自然可免狎亵之嫌,就是个别写倚香依玉之冶态者,王英志也认为并未涉及色情淫秽,仅是言“儿女之情”(47)。我们阅读的结果与王英志先生大略相似。为节约篇幅,我们看潘德舆对王彦泓诗的斥责:
元末之诗宗杨铁崖,乃入于妖;明末之诗宗锺伯敬、谭友夏,乃流于鬼。王彦泓《疑雨》一集,以淫靡之思,刻划入骨,使人心流气荡,觉铁崖徒炫其貌,惑人伎俩,犹有未尽致者,彦泓乃足为妖中之妖耳。句如“含毫爱学簪花格,展画惭看出浴图”,“翻成绣谱传人画,会得琴心允客挑”,“窗下有时思梦笑,灯前长不卸头眠”,“陈王著眼先罗袜,温尉关心到锦鞋”,“体自生香防姊觉,眉能为语任郎参”,“素质乍看疑是月,清欢何暇想为云”,能以佻冶不堪之事,写到通微入玄处,此即朱竹垞《静志居琴趣》所本。然在词家,亦为下乘,况以之玷污风雅哉!(48)
潘德舆所征引王彦泓的诗句,体格固然不高,但其“淫靡”之思、“佻冶不堪”之处不但不及《诗经·国风·召南·野有死麇》中的“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也不逮李商隐《北齐》诗中的“小怜玉体横陈夜”。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就不觉得王彦泓这些诗句“佻冶不堪”,认为平情论之,它们“不过写一憨慵小女子之情态”而已,潘德舆“力持诗教,坛坫气太重”,“从淫荡处着想,故见得如此”(49)。在潘德舆之前,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也曾征引“含毫爱学簪花格,展画惭看出浴图”、“翻成绣谱传人画,会得琴心允客挑”、“窗下有时思梦笑,灯前长不卸头眠”等诗句,认为“皆饶风韵,诵之感心嫮目,回肠荡气”,并赞其“深得唐人遗意”。至于朱彝尊所称引的“一层芳树一层楼,只隔欢娱不隔愁”、“当初语笑浑闲事,向后思量尽可怜”、“明明可爱人如月,漠漠难寻路隔烟”、“水国不生红豆子,赠君何物助相思”、“分明蜡烛身相似,才上欢筵泪已零”等《疑雨集》中的诗句,更是与“淫靡”、“佻冶不堪”毫无牵连(50)。
当然,王彦泓有个别诗篇咏金莲、写纳妾,难逃轻薄与纤佻之讥,但从整体上看,大都是情诗而非淫诗。退一步说,即使《疑雨集》中有个别的诗篇流于狎亵,也不能因此抹杀《疑雨集》的整体价值,我们在评价一个作家的作品价值时,应该使用望远镜而不是显微镜。
艳诗该不该进入文学史,写什么固然需要关注,其艺术上达到的高度同样值得考量。中国历代艳诗数量庞大,特别是明清时期,尚有大量艳诗没有得到清理,如明末清初,诗坛刮起了一股浓郁的香艳之风,讴歌男女情爱的诗歌十分繁盛。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三九《与吴梅村书》说:“江右艳曲,盈缃溢缥。西昆、香奁,塞破此世界矣。”(51)这些艳诗鱼龙混杂,需认真辨别,绝大多数的作品肯定只能成为文学史上的流星。我们之所以认为王彦泓《疑雨集》应该写进文学史,是因为其艺术上达到的成就。如对王彦泓艳诗甚熟的王士禛,通过与李商隐、韩偓艳诗的比较,在《倚声初集》中指出:“次回艳情诗数百篇,刻画声影,有义山、致光所未到者。”(52)李祥在为《〈疑雨集〉注》所作的序中则以文学史的宏大视野,确立《疑雨集》在艳诗发展史上的地位:
诗有六义,其三曰比,在古原与赋、兴分编,孔子合之,令人各揣其意之所在。郑、卫之诗,多托为男女慕悦之词,而郑卿即赋之以见志,未可以淫亵视也。《古诗十九首》多具此义。至《子夜》、《读曲》诸歌,则一意淫放,荡不可稽,比几于赋矣。唐之义山,以格诗写之,寓意最工,其姨子韩氏致尧和之。义山之诗,有吴江朱氏为之表章。致尧诗,近有吾友震钧在廷,著《香奁发微》。李、韩之诗,皆知其有为而言矣。明之季叶,金坛王次回所著《疑雨集》出,遂集此体之大成。(53)
总之,艳诗作为诗家一格,应该对其作出历史的分析,在文学史著作中获得适当的位置,像王彦泓这样在艳诗创作中达到很高成就的作家,应该在文学史中给予应有的关注。
王彦泓是以写艳诗出名的,《疑雨集》因此也成了艳诗的代名。其实,稍加浏览《疑雨集》,不难发现,其内容的多样性与一般文人的诗集并没有根本的差别。海纳川《冷禅室诗话》指出:
人只知王次回《疑雨集》为言情之作,以为全集不脱香奁本事窠臼,其实亦不尽然。王集中凡朋友赠答之诗,山川凭吊之作,皆屏去浮华,力求简奥,始信大家固无不能也。(54)
王彦泓是否能进入大家行列尚可商议,但《疑雨集》确实到了应该认真对待的时候了。
注释:
①黄永武:《中国情诗论》,《古典文学》第七集下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
②③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小仓山房诗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④郑幸:《袁枚年谱新编》,复旦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
⑤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凡例》,清乾隆二十五年教忠堂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58册。
⑥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⑦(39)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⑧袁枚:《随园诗话》卷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⑨章学诚:《书坊刻诗话后》,《文史通义》内篇五,民国嘉业堂章氏遗书本。
⑩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65页。
(11)章学诚:《诗话》,《文史通义》内篇五,民国嘉业堂章氏遗书本。
(12)(32)章学诚:《论文辨伪》,《文史通义》外篇一,民国嘉业堂章氏遗书本。
(13)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增订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页。
(14)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三,清嘉庆刻本。
(15)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二,清嘉庆刻本。
(16)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158页。
(17)叶德辉:《重刻〈疑雨集〉序》,《疑雨集》卷首,叶氏观古堂刻本。
(18)邬国平、王镇远:《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六《清代卷》,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38页。
(19)袁济喜:《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2页。
(20)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页。
(21)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下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总社2007年版,第454页。
(22)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0—71页。
(23)俞樾:《春在堂杂文》三编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550册,第331页。
(24)《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七,《元稹集》附,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25)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樊川文集》卷九,《四部丛刊》本。
(26)参阅康正果:《重申风月鉴》,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60—261页。
(27)袁枚:《随园诗话》卷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07—208页。
(28)参阅王炜:《〈清诗别裁集〉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193页。
(29)袁枚:《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三十《答蕺园论诗书》,《小仓山房诗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801页。
(30)袁枚:《小仓山房尺牍》卷九《答朱石君尚书》后《附来书》,《袁枚全集》第五册,南京:凤凰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页。
(31)王柏:《诗疑》,《丛书集成初编》第172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页。
(33)汤显祖:《牡丹亭》第七出《闺塾》、第九出《肃苑》,《汤显祖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34)(35)参阅莫砺锋:《从经学走向文学:朱熹“淫诗”的实质》,《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36)吴乔:《〈西昆发微〉序》,《西昆发微》卷首,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
(37)参阅吴宏一、何继文:《清代艳体诗论二题》,张宏生:《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38)章学诚《妇学》:《文史通义》内篇五,民国嘉业堂章氏遗书本。
(40)侯文灿:《〈疑雨集〉序》,《疑雨集》卷首,清康熙刻本。
(41)《国风》第三卷第八期,1933年10月16日。
(4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页。
(43)严绳孙:《〈疑雨集〉序》,《疑雨集》卷首,清康熙刻本。
(44)《黄遵宪全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39页。另参阅拙文《王次回:一个被文学史遗忘的重要诗人》,《中国韵文学刊》2006年第3期。
(45)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59—360页。
(46)[日本]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许总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1—202页,
(47)王英志:《袁枚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1页。
(48)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六,《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093—2094页。
(49)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六“潘四农斥王次回诗”条,清光绪十四年刻本。
(50)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70页。
(51)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三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52)邹祗谟、王士禛编:《倚声初集》卷十五,顺治十七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729册。
(53)李祥:《〈疑雨集〉注序》,《〈疑雨集〉注》卷首,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54)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695页。
标签:沈德潜论文; 袁枚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国风·周南·关雎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国风论文; 无题论文; 随园诗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