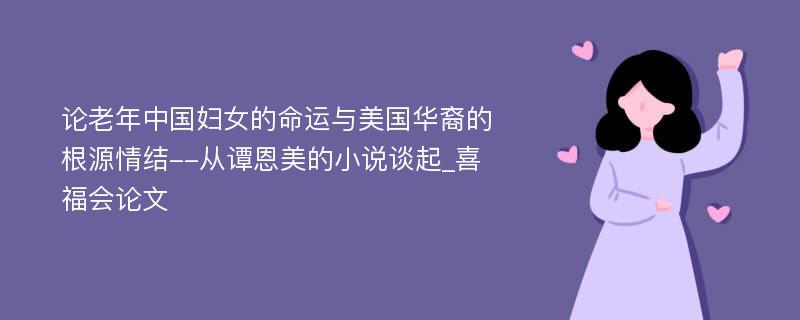
剪不断,理还乱——从艾米#183;谭的小说看旧中国妇女的命运及美籍华裔的根情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旧中国论文,美籍论文,华裔论文,情结论文,艾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艾米·谭(Amy Tan, 又名谭恩华)是一位华裔血统的美国当代女作家。迄今为止,她已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喜福会》(1989年),《灶神娘娘》(1991年)和《百种秘感》(1995年)。这三部小说发表后,在美国立即引起轰动,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并获得文学界一致好评。被称为“精心构思的、描述使我们隔绝又相连的地缘之间、文化之间及两代人之间浩瀚大海的故事”,“中国文化和美国环境的困扰”,“非常富有诗意,富有想象力和魅力。展示了两代人及两种文化之间不断的冲突和紧密的纽带”,“展示了中国、中国妇女和他们的家庭”。这三部小说都是通过母亲和女儿之口,用第一人称讲述他们各自的生活和情感波折,反映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妇女的命运及当代美国华人的生活、旧中国妇女的悲惨遭遇。
一、艾米·谭笔下的旧中国妇女
20世纪上半叶,新思想、新风尚不断地涌入中国,但在整体上,中国社会还是死水一潭,旧的传统势力和风俗习惯仍然根深蒂固,在社会上猖獗盛行。在这连年动乱中和处于宗教社会底层的妇女,无论贫富,受害最深,痛苦最多。旧中国妇女的命运和痛苦在现代中国文学中已是一个屡见不鲜的主题。但她们悲惨的遭遇和痛苦的呐喊出现在美国文学界一位美国作家的笔下,就显得别有一番特殊的意义。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封建宗族社会,伦理上受着儒家思想的统治。妇女必须恪守“三从四德”,婚姻上毫无自主权利,“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些在艾米·谭的小说中都有所反映。《灶神娘娘》中主人公蒋维丽被草草打发出嫁,心中无限凄凉。不禁发出内心的悲叹:“我既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没人征求我的意见,因为这由不得我作主”(注:艾米·谭:《灶神娘娘》第166页、178页、80页。)。婚后,蒋维丽在肉体上、精神上一直受到其虐待狂丈夫的侮辱与折磨,忍无可忍,却无权要求离婚。同样,在《喜福会》中,蒋琳铎从小被许配给一个比她小几岁的男人。全家在遭灾后被迫远走他乡时,她不得不到婆家当童养媳,倍受欺凌,过着奴仆的生活。安梅的新寡的母亲不幸被一富商设计引诱强奸,虽然她纯属受害者,但仍受到百般侮辱,被逐出家门,不得不忍气吞声,嫁与该富商为妾。由此,男尊女卑和男性主宰一切在人们心目中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为了维系这个男性宗族社会的延续,这些概念不断地灌输到下一代人特别是妇女的头脑里,以便他(她)们以后能盲目地服从、崇拜父亲和丈夫。在即将出嫁前,蒋维丽的父亲给她的唯一“忠告”是:“从今以后,你必须遵从你丈夫的意愿想法。你自己的不再重要了。”(注:艾米·谭:《灶神娘娘》第 166页、178页、80 页。)天长日久,甚至妇女自己也认为她们要比男人软弱低贱。男人是她们理所当然的主人和救星。“女人属阴,内心黑暗,欲念丛生;男人是阳,光明真理,照耀吾心。”(注:艾米·谭:《喜福会》第82页、12页、124页、331页、331页、41页、200页、22页、331页。)
千百年来,这些传统观念在中国社会和人们心目中早已是根深蒂固。人们对此习以为常,想当然地遵守服从。妇女虽然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却自觉不自觉地做了这些传统观念的盲目追随者,甚至充当了其工具或者帮凶。向下一代,特别是女儿灌输这些思想的通常是由母亲或家庭中的女性长辈担当的。母亲的职责是教育女儿“懂得规矩”。在《喜福会》中,安梅新寡的母亲正是在富商的二房太太设下的圈套中受骗失身的。而其后诅咒她最凶的却是她自己的亲生母亲,并被其母亲用来作为警告自己亲生女儿要循规蹈矩的反面教材。当蒋维丽最终再也忍受不了其丈夫的百般凌辱,离婚又不可得时,不得不离家出走。是她最好的朋友把她丈夫领到她的藏身之处,逼迫她回家。甚至蒋维丽,一个有头脑的知识女性,也经常因为她丈夫总是在家里家外寻花问柳而责怪自己,认为过错在她自己不能满足丈夫的需要。她悲愤地说道:“可能这一切都是我的错,不应该把自己的苦难归咎到别的女人身上。但是我就是这样被抚养大的——永远不能指责男人或男人统治的社会;也不能指责孔夫子,那个一手造就了这个社会的恶人”(注:艾米·谭:《喜福会》第82页、12页、124页、331页、331页、41页、200页、22页、331页。)。 作者通过蒋维丽之口发出抗议的呐喊:“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人都认为孔夫子如此大智大善。他使人压迫人,而妇女又被压在了最底层”(注:艾米·谭:《喜福会》第82页、12页、124页、331页、331页、41页、200页、22页、331页。)。
在旧中国,妇女身处社会的最底层,又受着夫权的压迫。一个丈夫,不管在社会上如何懦弱无能,地位低下,在家里可是说一无二的主人,享受着绝对的权威。艾米·谭小说中主要描写的是女性世界,对男性一般着墨很少,男性人物只起着淡淡的铺衬作用。她唯一刻画较多而且塑造非常丰满成功的男性是《灶神娘娘》中蒋维丽的丈夫文福。作为一个男人,他本性贪婪,卑鄙无耻,见利忘义,好吹嘘卖弄,实际上却是一个色厉内茬的懦夫,抗日战场上贪生怕死的逃兵;作为丈夫,自私自利,猜疑嫉妒,不问家事,在外狂嫖滥赌,在家虐待妻子;作为父亲,对儿女毫无怜爱之心,冷酷无情,出手狠毒,对儿女的健康成长不闻不问,生死无动于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为非做歹,恣意妄为,纵情肉欲,把欢乐建立在他人包括自己至亲骨肉的痛苦之上的恶人,居然一生富贵平安,儿孙满堂,寿终正寝。
在苦难的漫漫长夜中,中国妇女造就了一副既软弱又坚强的性格。她们软弱是因为在这个男性统治的社会里,她们没有也得不到法律上、道义上和经济上的支持,不得不心甘情愿地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她们之所以坚强是由于她们能用极大的耐心和毅力默默地忍受这一切苦难不公,并顽强地活了下来。她们唯一的支持只是希望,不管这种希望多么渺茫,不切实际。《喜福会》中正值青春妙龄的莹影默默地等待了十年,终于等来了新婚不久即把她抛弃的丈夫的死讯。《灶神娘娘》中的蒋维丽也同样默默地等了大约十年时间,忍受丈夫的百般欺凌,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真心爱她,尊敬她,“平等待我”并能拯救她脱离苦难的男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一个中国血统的美国男人)。然而,中国妇女决不是盲目温顺,任人宰割的羔羊,一旦时机成熟,她们会毅然决然地奋起反抗。实际上,如同艾米·谭小说中所描写地那样,她们确实在奋起反抗了。《喜福会》中安梅的母亲选择了自尽作为报复和保护她的儿女的最后手段。这种方法固然不足取,但也反映了她莫大的勇气和决心。蒋琳铎机智勇敢地偷偷吹灭了新婚之夜的红蜡烛,后来又假借祖宗灵魂附体托言,成功地为自己赢得了自由。《灶神娘娘》中蒋维丽的母亲毅然离家出走,却并没有带走丈夫给她的珠宝首饰。蒋维丽在有了机会后,坚决彻底地同丈夫断绝了关系,宁愿坐牢也不愿回到原来的家中;当她赴美前,前夫无耻地敲诈纠缠并奸污她时,敢于夺过手枪向其开火,勇敢地保护自身的自由和安全。同一小说中的另一女性人物“花生”也是最后离开了她那搞同性恋的丈夫,参加了共产党,真正地“改造社会”。确实,只有在妇女们自己觉醒反抗,砸烂镣铐,摧毁旧世界,建立新社会,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二、美国华人的根情结
艾米·谭小说另一显著特点是细腻地描写美国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国移民微妙复杂的根情结,生动地展示了两代华人对大洋彼岸母国的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情。
在她的这三部小说中,当第一代中国移民踏上美国这片异土时,他们憧憬着未来,渴望开始全新的生活,把过去完全留在大洋对岸,忘掉以前的苦难和心灵上的创伤。正如《灶神娘娘》中蒋维丽所说的那样:“当我来到这个国家时,我就对自己说过:我现在能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思考。现在我能忘记我过去的苦难,把我所有的隐痛全部留在一扇再也不会开启、我这双美国眼睛再也不会看见的门的那边。我想我的痛苦的过去会永远被封闭起来了。……在这儿没人敢把我怎样。我能把我所有的过失、所有遗憾和所有的痛苦都埋藏在心中。我能改变我自己的命运”。(注:艾米·谭:《灶神娘娘》第166页、178页、80页。)在这个新的国家里,他们能够、也确实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但是他们能够忘记过去吗?永远没有。虽然他们尽力想忘却,也自认为忘却了他们的过去,在他们心灵深处,他们非但没能与过去完全割舍,反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过去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执著情感。
近四十年来,蒋维丽的心灵一直被她前夫孽行的阴影笼罩着,而且直到知道这个恶人死之前,不敢告诉她女儿其真正的生父是谁。《喜福会》中的吴夙愿在日本侵华期间家破人亡、颠簸流离,不满周岁的孪生女儿又在战乱中失散,至此以后数十年期间一直在苦苦地徒劳地寻找她失散的女儿,心灵上的自责至死都没平息。在同一小说中,安梅自幼便同其弟分别,精妹的父亲也是从小就离开了家乡,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小姑。但六十多年后,回乡与他们见面时,仍然是情感如故,爱心不减。确实,他们是忘不掉这一切的。他们也不愿忘记这一切。相反,他们执著地保持着中国的生活方式——说的是家乡话,吃的是家乡菜,服的是中草药,信的是中国神灵,住的是中国城(china town,旧称唐人街),忘不了的是故乡情。
美国华人未能在美国这个“民族大熔炉”里完全熔化的原因之一不是他们来自不同的种族,而主要是他们来自完全不同的文化。他们是在这种文化中哺养起来的。他们也试图用这种文化哺养并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用这种文化哺养他们在美国出生的下一代。即使他们在美国住了几十年,他们仍认为自己是外国人,在《喜福会》中,当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裔姑娘罗丝与一个白人约会时,罗丝记得她母亲安梅是这样提醒她的:“‘他是美国人。’我母亲警告我说,好像我眼瞎看不见似的。‘一个外国人’”(注:艾米·谭:《喜福会》第82页、12页、124页、331页、331页、41页、200页、22页、331页。)。 美国华人难忘故土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伦理文化注重家庭的观念。在儒家思想中,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人们生活维系亲情的核心。千百年来,无数哲人和君王力图追求实现“天下一家”的理想。可见“家”在中国人心中的重量。“国”是“家”的大概念,“家”是“国”的小组成。家国难分,互为一体,使所有炎黄子孙富有一种强烈持久的归属感,爱国心。朱利叶·曾在她所著的《中国宗教》一书中指出:“(中国文化中的)家庭关系给人们的社会行为提供了一种模式。要尊重自己家族中的长辈,也要尊重他人的长辈;对自己的弟妹和儿女慈爱,对他人的弟妹和儿女也要慈爱。……这些观念已成了一代又一代儒家子弟的行为规范。这些观念不仅是形成中国家庭中强烈的凝聚力的原因,也是形成儒家社会团体,甚至海外华人社团中强烈的凝聚力的原因”。(注:朱利叶·曾:《中国宗教》第59页。)
艾米·谭的小说中反映了华裔美国人(或更准确地说美籍华人)中间这种强烈的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人们即使是仅仅沾一点血亲或姻亲,或仅仅带一点故,都认为是家庭中的一员。进而论之,不管这些华人是出生在中国,还是出生在美国,他们这种强烈的家庭观念又给了他们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喜福会》中在美国出生长大的精妹,在其母亲吴夙愿的长期熏陶下,在小说末尾与父亲踏上中国土地时,最终认识到:“一旦你生为中国人,你禁不住感觉是中国感觉,思维是中国思维”。(注:艾米·谭:《喜福会》第82页、12页、124页、331页、331页、41页、200页、22页、331页。)这种以家庭为重, 家庭完整为重的观念在艾米·谭的小说中也反映在中国母亲对她们“美国”女儿婚姻的态度上。开头,这些中国母亲千方百计地阻碍反对她们的女儿与其他种族的男青年约会结婚,后来又总是鼓励帮助她们的女儿挽救家庭的破裂。在《百种秘感》中,关——这位实际起着母亲作用的姐姐,竭尽全力挽救奥利维娅的婚姻,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
这种归属感引出了几代美籍华人心中错综复杂的根情结。第一代移民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第二代华人,不论他们是纯中国血统,还是半中国血统,尽管他们认为自己是完全的美国人,最终都认识到,他们是中国人,他们的根在中国。正如《喜福会》中精妹母亲对她经常说的那样:“它就在你的血液里,等待着流出来”。(注:艾米·谭:《喜福会》第82页、12页、124页、331页、331页、41页、200页、22页、331页。)
在艾米·谭的小说中,这种根的纽带还通过中国母亲和“美国”女儿之间的情感纽带显示出来。艾米·谭的三部小说都着重描写了母女之间的复杂关系——爱与恨,差异与相似,冲突与和解。母亲千方百计、费尽心机地用中国方式抚养她们的孩子(在小说中主要是“美国”女儿)“成长”。《百种秘感》中奥利维娅自幼丧父,母亲是一个白人,整天忙于找新欢。因此,中国母亲的角色和职责是由她在中国长大后来美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关担任起来的。正像奥利维娅本人所承认的“她(指关)在许多方面比我真正的母亲更像母亲”。(注:《百种秘感》第21页。)中国母亲的职责之一是将中国伦理文化精神倾注到下一代的心里。“美国”女儿受美国文化教育的影响,总想独立自主,按自己的意愿和方式行事,而在中国母亲的眼里,这是叛逆,不听话。母亲总想把孩子,即使在他们长大成婚之后,保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女儿则不愿意上一辈干涉她们“自己”的事务,特别是当她们已成年后。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母女两代之间的隔阂及冲突,这些既是两代人的隔阂与冲突,也是两种文化的隔阂与冲突。尽管这样,但在她们内心深处,都感到把她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血液上和情感上的纽带。这种情感纽带在艾米·谭的三部小说中有着细致生动的描写。《喜福会》中,安梅的母亲在把她赶出家门的老母病危前从遥远的天津赶回宁波尽孝。安梅看着她的母亲:“从自己的臂上割下一块肉……把它放进汤锅里。她想用古老的传统秘方最后一次治好母亲的病。这就是一个女儿如何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这就是刻骨铭心的“孝”。因为有时这是唯一的方法能使你深入骨髓,永志不忘”。(注:艾米·谭:《喜福会》第82页、12页、 124页、331页、331页、41页、200页、22页、331页。)在母女之间刻骨铭心的是割舍不断的爱心、亲情。这种深沉强烈的情感纽带不仅体现在中国母亲和中国女儿身上,也体现在中国母亲和“美国”女儿身上。在《喜福会》中,威芙妮——一个从中国人眼光来看是叛逆成性的孩子,而她自己却认为是独立自主——怒气冲冲地赶回家,向她母亲宣布她决定要和泰德,一个“外国人”结婚,因为她相信她母亲在设法阻碍这场婚姻。当她看到母亲正安详地沉睡在梦乡时,满腔怒火顿时烟消云散,一股爱心涌上心头。埋藏在心里的亲情最终“流出来了”:“我看到她香甜地睡在沙发上。……她看上去软弱无力,不堪一击。突然,我有一种无名的恐惧,因为她看上去好像死了。在我对她百般憎恨的时候悄然离去了。我曾希望她别干涉我自己的生活,她让步了,灵魂脱体而去,以逃避我对她憎恨。“妈”!我尖声喊到。“妈”!我抽泣着,接着开始哭了起来。”(注:艾米·谭:《喜福会》第82页、12页、124页、331页、331页、41页、200页、22页、331页。)
虽然儒教作为中国文化伦理道德的基础,在中国社会传统习俗中起着主导作用。中国化的佛教和本土宗教道教在社会上千百年来长期流行,在人们的思维方式、道德行为和日常生活中有很大的影响。在艾米·谭的小说中,踏上美国土地的中国移民似乎徘徊在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的十字路口。一方面,他们要想开始一种物质上、精神上都全新的生活,他们尽力照美国方式来生活和思考,他们甚至信奉了基督教。然而,另一方面,他们仍旧保持他们传统的中国生活方式,在他们的家里,在他们的心里,他们供奉的是中国神灵,他们过的是中国的宗教和世俗节日。以这种方式,他们自然忘不掉,自然维系着他们在中国的根。
由于这些宗教思想观念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美国华人中间,特别是老一代人中间,还是比较相信轮回再生这一类的说法。生命是反复循环轮回,祸福报应一切早已是前生有定。这些观念在艾米·谭的三部小说中都有所暗示。“东方是万物萌发的地方。太阳从东方升起,清风从东方吹来”(注:艾米·谭:《喜福会》第82页、12页、124页、331页、331页、41页、200页、22页、331页。)。东方——中国—— 是身居美国的中国移民的生命之源,是他们痛苦和欢乐之源,是他们的一切的根源,并且很可能是他们最后的归宿。“叶落归根”,不仅是肉体上的叶落归根,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叶落归根。在艾米·谭的三部小说结尾时,两代华人都一起回到了中国,尽管他们回国的理由不同,但目的都是一个:寻根。这决不是三部小说中偶然的巧合,在艾米·谭看来,是他们生命的一个轮回。《喜福会》中的吴精妹代表她死去的母亲回中国与她从未见过面的孪生姐姐相会,一踏上中国土地后,最终认识到“我的哪一部分是中国。这是如此明显,这就是我的家庭,就在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注:艾米·谭:《喜福会》第82页、12页、124页、331页、331页、41页、200页、22页、331页。)。在《百种秘感》中, 奥利维娅回到中国后,面对“证据”,终于相信了她姐姐关以前对她所说的话:她和丈夫西蒙的婚姻,正是一百多年前在中国太平天国时期的一对情侣之间的一段不了情的延续。更具有深刻意义的是她同她丈夫在中国逗留期间,她怀了孕,“回到”美国后,生了一个女儿。而她的丈夫在美国时,却真正患有不育症。结果是他们的婚姻得以挽救,家庭得以保全。在更深的一层意义上,这也许是暗示“保证祖宗香火不断”,是中国血液,中国根又传给了第三代,不管这第三代将会如何美国化。
艾米·谭是一位才华横溢,用英语写作的华裔美国作家。她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旧中国的社会和妇女的命运;她又用华人的眼光来审视在美国的中国移民特别是妇女的生活。她书中展现的两种文化的交织和冲突,两代华人妇女的不同遭遇和欢乐痛苦,给读者一种全新的感受。这也许正是她作品的魅力所在。加之她丰富的想象力,对中国文化及社会的透澈了解,用女性作家所特有的细腻笔调对华人妇女的经历和情感的生动描写,对英语语言驾轻就熟的掌握以及运用自如的写作(包括生动幽默的中国母亲中国式的夹生英语和“美国”女儿地道的美国英语)都给她的作品增添许多迷人色彩。这就无怪乎她的作品已译成了多种语言,在全世界拥有大量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