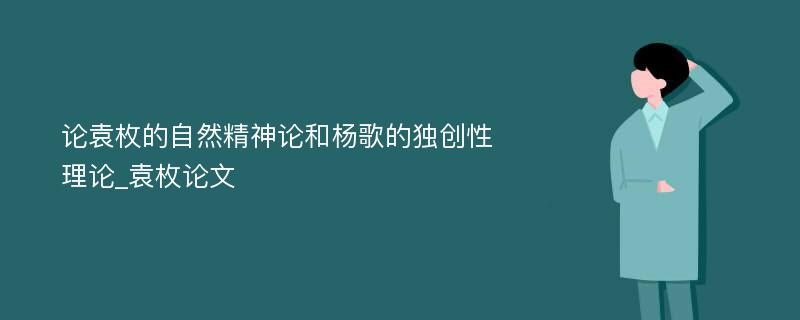
试论袁枚的“性灵说”与杨格的“独创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灵论文,试论论文,袁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学体系经常与文化的每一层面息息相关,每一层面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皆有其独特性。然而,这并不能否认不同的民族在艺术思维上的共鸣和共振。因为“有许多古代民族和近代民族,初看似乎很不相同,而精神上却有一种真正的相似点;两者所经验的、所发抒的,都是同样的感情,所祈向的、所渴望的,都是同样的理想。”〔1 〕当我们把视线投向中外诗歌美学的坐标系时,我们就会发现18世纪中国的袁枚和英国的杨格这两位美学家在不同的民族几乎同时举起了独创论美学的大旗,掀起了一股持久不衰的独创论美学的浪潮。
袁枚和杨格为什么在诗歌美学的意蕴和旨归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呢?这种奇妙的文化现象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美学的课题,值得我们搜其真,穷其源,尽其妙。
一
一个真正的美学家,他应该有哲人的玄妙神思,诗人的抒情心灵。也就是说,要有一个整合心灵的创造精神。这样,他才能在诗歌美学的莽原上纵横驰骋,革故鼎新,融成诗歌美学的佳构。在这个意义上,杨格和袁枚都是18世纪文艺价值理想的代表。
杨格论诗,高标独创,反对蹈袭摹拟,赞美生命的律动。他欣赏且推崇独创性的诗人,把独创性诗人的笔头比作能够从荒漠中唤出灿烂春天的“阿米达的魔杖”,认为一切想象的触发,文笔的变化,都是由这个魔杖控御着。
在杨格那里,“独创”这个概念具有四种功能基质:
一是发轫质。大凡杰出的诗人总是开风气之先,自铸伟词,自成一家。对于过去的经典作品,独创性诗人决不顶礼膜拜和亦步亦趋,而是另辟蹊径,敢于走前人未走的路。因而,他们“开拓了文学的疆土,为它的领域添上了一个新省区”〔2〕。
二是天才质。独创性的诗人拥有智慧,而智慧是天才的标志。在大多数场合,天才正是指用超过一般人的意念和手段去完成伟业的才性。诗歌创作尤需天才,“在幻想的仙境里,天才可以四处游荡,它具有创造性的力量,可以任意统治自己的幻影之国。自然的广阔天地也展开在它的面前,它可以自由来往,竭力有所发现,在自然界可见的范围内自由地戏弄万物,并且描绘它们。”〔3〕杨格把天才分为两类, 一类是早熟的天才,另一类是晚熟的天才;早熟的天才可喜,晚熟的天才可贺。
三是超越质。独创性的诗人总是力图在与古人的竞赛中凸现自己,“模仿是自认不如,竞赛是比个高下;模仿是卑下的,竞赛是大方的”〔4〕。前者束缚人,后者鼓舞人;前者也许能使人出名, 后者则更使人不朽。“竞赛激励我们,不要我们永远像新兵一样,在创作界的古代将领们的麾下练武,而要使戴上桂冠的老将们蒙受丧失光荣的优先地位的危险。”〔5〕只有在竞赛中猛进疾趋,才能实现超越。
四是新颖质。往往是那些致力于生气勃勃的创造的诗人,才有可能获得光荣的果实,“独创性诗人的头脑犹如肥沃而可爱的土地,享有永恒的春天。模仿者却不行,他们只能把月桂移植出来,在异乡的土地上总是落得个枯萎”〔6〕。
因此,杨格认为,藉着创造的幻想,发为灿溢的美感,以表现人生的就是好诗,具备创造基质的诗人才有独创性,才能称得上是独创性的诗人。
与杨格相枋,袁枚以“性灵”为起点构筑诗歌美学体系。袁枚论诗主性灵,薄格律。
何谓性灵?袁枚曰:“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足矣。 ”〔7〕初看起来,袁枚的“性灵说”,极富空灵飘渺之至。然而,从袁枚的《随园诗话》和有关文论中,我们可见出“性灵说”所蕴涵的丰富特性。
一是情感性。袁枚论诗把纯挚真切的情感作为第一要素。因为情感是诗文创作的驱动力:“性情者,源也;词藻者,流也。源之不清,流将焉附?”〔8〕袁枚把情感作为诗文创作的源泉, 不免陷入主观唯心论之中,但他强调情感这一诗歌创作的动力,还是可取的,“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9〕。缘情而作, 遂能摇撼读者的心旌。
二是主体性。袁枚论诗,关注抒情和审美的主体,“作诗不可以无我;无我,则剿袭敷衍之弊大,韩昌黎所以‘惟古于词必己出’也。北魏祖莹云‘文章当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不可寄人篱下’”〔10〕。袁枚标举诗人的个性,旨在强调创作主体的灵动性,因而他反对刻意讲究声律的做法,“余作诗,雅不喜迭韵、和韵及用古人韵,以为诗写性情,惟吾所适”〔11〕。也就是说,作诗须敞开心灵,直抒胸臆,扩大和提高自我的创造性和自足性,而不是抑制和削蚀。
三是变革性。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这是古今情理。袁枚反对拘泥于古人的做法,主张“当变而变,其相传者心也;当变而不变,其拘守者迹也。鹦鹉能言而不能及其所以言,夫非以迹乎?”〔12〕袁枚以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为例,说明变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唐人学汉,魏变汉楚,宋学唐变唐,其变也,非有心于变也,乃不得不变也。使不变,则不足以为唐,不足以为宋也。”〔13〕唯有变革,诗歌才有生机。优秀的诗歌艺术总是有一股盎然活力跳跃其中,蔚成酣畅饱满的自由创造精神,诗人参赞化育自然与人生,浑然同体,浩然同流,所以能昂然于美的诗歌之中。
可见,袁枚的“性灵说”,不是空明境界的晴云缱绻,清辉流照,而是如现代文论家郭绍虞先生所说的,性灵是实感与想象、情与才、韵与趣的踪合体,旨在求真、求新、求活。〔14〕
杨格和袁枚,一个高标独创,一个张扬性灵;一个强调发轫和超越,一个侧重缘情和变革;前者劲健中显流畅,后者洒脱中有灵妙。他们的诗学研究模式和理想构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致力于激发诗人不为偏见所阻遏的生机勃勃的创造性,彰显诗人无羁的情思和潇洒的个性。
二
杨格和袁枚虽然所处地域有别,天各一方,但在历史的网络上,他们均为活动于18世纪的人。
从出生年代来看,杨格生于1683年,卒于1765年;袁枚生于1716年,卒于1798年。可见,杨格比袁枚早生33年,而袁枚比杨格后死33年,两人年寿恰好相等。
从艺术才华来看,两人既是诗人,又是美学家。杨格早年在牛津大学攻读法学,并开始涉足诗坛,《末日之诗》和《普遍的激情》等诗集的出版,使杨格跻身于英国诗人之列。杨格晚年在完成了著名的长诗《哀怨》(又名《关于生命、死亡和永生的夜思》)之后,又以书信的形式发表了别具一格的诗学著作《试论独创性作品》。
袁枚是年考取进士,官溧水、沐阳、江宁等县的知县,33岁即官,筑随园于江宁城西小仓山下,怡情于园林,交游甚广,以诗文名于时,世称“随园先生”。袁枚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诗学见解大多集中于《随园诗话》之中。
不难看出,杨格和袁枚这两位美学家在阅世历程和艺术才华方面存在着相似之处。倘若透过历史的纵深,我们还可发现他们的理论命运也大致相同。
杨格的《试论独创性作品》问世后,在英国诗学领域自然激起了反响。虽然当时批评界的权威人士约翰逊认为杨格是小题大作,哗众取宠,但杨格的追随者却不这么看。比杨格稍后的诗人兼美学家柯尔律治赞赏且采纳了杨格的独创论中的有机主义美学观。不仅如此,杨格的独创论美学还超越了国界, 播撒到国外。 杨格的理论文章出版后一年内(1760年)就有了两种德文译本,并且成了18世纪末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珍品,强调激情、天才和创新的“狂飙突进”运动的理论家赫尔德等人如获至宝,把杨格看作同道和知音,视为先浪漫主义美学家。杨格的“独创论”在北美大陆也引起了反响。美国著名作家爱默生受其启发,写了《自力更生》一文,宣称“灵魂永远不会愿意作自我重复”,倡导诗人坚持独立,决不摹拟。随着时间的推移,杨格的诗歌美学越来越受到西方文艺美学界的重视。20世纪美国著名学者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专节评价了杨格独创论美学的理论贡献。〔15〕
同样,袁枚也是一个有影响的美学家。袁枚的诗话在当时就蝉脱而出。比袁枚稍后的文人赵翼是“性灵说”的积极拥护者,所著《瓯北诗话》贯穿了“性灵说”的意旨。袁枚逝世以后,虽遭一些门生故旧的深诋曲毁(例如,章学诚对《随园诗话》的艳体诗倾问进行了诋呵),但袁枚的“性灵说”,不仅不曾湮没,而且颇有市场。我们从龚自珍发出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声中,从黄遵宪关于“诗界革命”的宣言中,可以看到袁枚“性灵说”的影子。
杨格和袁枚之所以在中外诗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笔者看来,是因为他们对诗歌艺术生命形式所作的具有近代意义的思考和感悟,他们在理论探索上有三点特别引人注目:
第一,以花为喻的文艺生态学观念。花草树木与诗歌艺术在生态习性方面存在着可比性。杨格和袁枚都注意到这一点。
杨格称独创性的作品是最美丽的花朵,具有植物的属性:“它从天才的命根子上自然地生长出来,它是长成的,不是做成的;模仿之作往往是靠手艺和工夫铸成的。”〔16〕从泥土中萌发的鲜花馨香迷人,纸扎的花朵即使色彩艳丽,也只是缺乏生气的制品。显然,杨格肯定作品的有机生长属性,反对机械制作的模拟性。
袁枚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把那些清妙有真气的近体诗歌比作“今日之莺花”,并在《随园诗话》中主张:“诗有干无华,是枯木也。”袁枚还作了阐述:“牡丹芍药,花之富丽者也,剪採为之,不如野蓼闲葵矣,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心知此,而后可与论诗。”〔17〕袁枚和杨格一样都把艺术作品当作生气灌注的整体,从而揭示了诗美的有机性、鲜活性和生态性。
第二,矫枉不过正的文艺人才学思想。杨格和袁枚都承认且重视诗歌创作中的天才存在,不免打上了先验论的烙印。但是,他们并不否认天才产生的社会条件。
杨格认为“花木果实的滋生靠雨水、空气、阳光,天才果实的滋生同样靠外界条件”〔18〕。他注意到古希腊罗马文学的繁荣就是由当时的社会因素浚发的。
袁枚论诗,强调天分,也不忽视学力:“诗文之作意用笔,如美人之发肤巧笑,先天也,诗文之征文用典,如美人衣裳首饰,后天也。”〔19〕在袁枚看来,天籁与人巧,性情与学问,两者不可偏废。
第三,初露端倪的文艺创作心理学。诗人创作离不开艺术感受和心理感觉。杨格和袁枚都注重创作心理的探讨,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
杨格把诗歌创作等文艺活动视为苦闷的象征和忧愁的排遣:“我们在社会生活拥挤的通道上奔波,写作至少能使我们暂释忧虑,给我们一个可喜的片刻来从事令人神清气爽的回忆。”〔20〕诗是抒写心灵的艺术,而诗人的精神世界是个广阔的秘境,有时连诗人自己都不能意识到为生命之光所照耀的无意识:“一个人可能拥有潜在的、未被察觉的才能,直到他为高声的呼唤所惊醒,为惊人的危急所激发。”〔21〕杨格这个观点很重要,他在西方文论史上率先提出了人的潜意识问题:人在创造时,其心境分为两层,一是为意识所控制的平凡无奇的表层,二是不可理解的、深不可测的深层。这种提法比现代精神分析学派所倡导的潜意识理论要早得多。
在考察了艺术创作的外显形态和深隐层次后,杨格主张诗人“深入自己的内心,了解心灵的深厚广阔、偏见和全部力量;与内心中的陌生人建立亲密的关系;激发并爱护智慧的每一星火光和热量,把它们收集起来,让天才像太阳一样从一片混沌中升起。”〔22〕唯有如此,诗人才能呈现生命情调的实相和华奕照射的宇宙意象。
袁枚在文艺创作心理方面更坚信“情动于衷而形于言”这个至理名言,认为诗歌是诗人内心情感的表露和宣泄:“人必先有芬芳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人但知杜少陵每饭不忘君,而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儿女间,何在不一往情深耶?后人无杜之性情,学杜之风格,抑末也?”〔23〕意境隽澹,本于襟抱;韵致深美,发乎才情。袁枚擅于驰骋玄思,在创作中阐扬气韵生动的审美机趣。他所要阐述的,正是对人性之美的感受,在大化流衍之中,要将一切都点化成沉钟巨响。
杨格和袁枚侧身现世,实抒卓见。他们的美学是一种激扬创造精神的诗学,他们在诗歌美学领域力图阐扬新的文艺价值,建立新的知觉方式。这些都标明他们已从古典美学走向了近代美学。
三
的确,杨格和袁枚的美学出发点是相同的,他们都是以反拟古、重个性、求创新为旨归。而这一切又是与两位美学家所生活的时代情势相关的,离开了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就无法透析出东西方两位美学家思想模式的近似。
从宏观的世界史进程来看,18世纪是社会嬗变、新潮萌动的阶段,它既是西方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趋于壮大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
杨格生活在18世纪资本主义制度逐渐确立的英国,启蒙主义是当时的进步思潮,它的一个特点是热烈地捍卫教育、自治和自由。杨格以独创论为核心的诗歌理论不可避免地濡染了新起的启蒙主义思潮。
袁枚所处的社会历史现状,虽较杨格落后些,但在明清之际,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已开始在中国封建社会滋生,反对封建传统理法汩没性灵的思想舆论也已初现端倪。袁枚以性灵为核心的诗歌理论在当时不啻是一剂清凉散,散发出尖新奇丽之光。
美学史上,任何理论体系的建构,都同世纪的理论风云纠缠在一起,都会面临对立面的挑战。张扬新识的杨格和袁枚也不例外,他们在针锋相对的辩驳中阐发自己的理论观点。
横亘在杨格面前的是古典主义文艺思潮。英国的古典主义源自法国。由法国布瓦洛缔造的重视理性、蔑视感性、追求“三一律”的古典主义思潮,于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在英国落户,其代表人物是当时的著名诗人蒲柏。蒲柏于1711年出版《论批评》,播布古典主义的诗学原则。他还步布瓦洛的后尘,把古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视为诗的艺术中最优秀的典范。他主张诗人摹拟古典,仿效古人。在这个思想指导下,蒲柏在翻译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史诗时,固守死板的前后两行协韵的英雄双行诗译法,删除了他本人自以为是“庸俗”、“粗野”的内容。蒲柏用古典主义建构自己的诗学体系,不能说一无是处,但在当时的潮流中,蒲柏确属保守复古派之列。
杨格把蒲柏的言行讥讽为窒息诗歌灵光的迂怪胶固之举,认为蒲柏的理论表面上富丽堂皇,实际上存在着致命的“阿喀疏斯的脚踵”,其根源是古典主义的信条在作祟。正是由于缺乏创新的气魄,蒲柏“宁愿在旧世界中凯旋,而不愿寻找新世界”〔24〕。因此,在经典作品翻译上,蒲柏虽然给人们介绍了一个荷马,但他自己却是一个古典主义的信奉者和传声筒,缺乏荷马那样强旺的想象力和真正的崇高之美。
在袁枚所处的时代,也有一种与欧洲的古典主义流派类似的“格调派”。格调派的源头在明代。以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为代表的明代前后七子派,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前后七子派以格调论诗,旨在摹拟,意在法古。到了清代中叶,沈德潜集前后七子拟古主义之大成,创立“格调说”,在内容上要求诗人以“诗教”立言,“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在方法上强调拟古、蕴蓄和格律。沈德潜是当时文坛的权威人士,“格调说”由此风靡一时。
袁枚对这种束缚诗人性灵的“格调说”甚为反感。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一文中批驳了沈德潜的观点。首先,袁枚反对论诗分唐界宋:“先生许唐人之变汉魏,而独不许宋人之变唐,惑也。且先生亦知唐人自变其诗,与宋人无舆乎?”其次,袁枚反对论诗贵温柔、重含蓄、关风化:“至所云诗贵温柔,不可说尽,又必关系人伦日用。此数语有袖衣大祒气象也。”在袁枚看来,格调派囿于伦理锢蔽之习,晦昧隐曲,乖方敷理,是与诗歌的性情相悖的。
从性灵出发,袁枚还批判了当时的考据之学。乾嘉时代,考据之风极盛,以厉鹗为首的浙江诗派,探赜索隐,大兴宋人冷僻幽微之风;当时的文论家翁方纲鼓吹“肌理说”,讲究质实诗法,力倡“学人之诗”。袁枚愤然抨击了这股考据之风:“近见作诗者,全仗糟粕,琐碎零星,如剃僧发,如拆袜线,句句加注,是将诗当考据作矣。虑吾说之害之也,故续元遗山《论诗》,末二首云:‘天涯有客号詅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25〕袁枚指出:扭于惯例,抱持师说,谬袭经生,终将导致诗歌隳落。
看来,中国的“格调说”与欧洲的古典主义在精神实质上有着一致性,即:循规蹈矩,泥古不化,重视理性,蔑视感性。袁枚和杨格在当时的文坛上均属与之抗衡的“革新者”。他们以进化的历史观和美学观,探索了诗艺的底蕴,维护了他们所确认的艺术真理。
四
我国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在谈到艺术创新问题时揭橥出这样一个文艺现象,即新风气的代兴常有一个狡黠的表现:它一方面强调自己是崭新的东西,与对立的传统抗衡,另一方面它要表示自己大有来头,非同小可,又向前代找一个对自己有用的前辈作为渊源和立论之依据。 〔26〕杨格和袁枚正是有这样“狡黠的表现”,他们驰虑呈幻, 善巧迭出,既有创造,又有赓续,在建构美学理论体系时善于汲取先驱者的思想资料,以光大性情,助益精神个体之灵台。
在杨格的思想发展中,给他影响最大的是艾迪生(1672~1719)。艾迪生是介于古典派与革新派之间并赞同革新的英国诗人。他对艺术现象的评价是和蒲柏的古典主义思想相左的。艾迪生本人创作了著名的长诗《伽图》,其凝重劲健的史诗风格蜚声文坛;艾迪生写了一系列评价弥尔顿的《失乐园》的论文,阐扬弥尔顿作品中的雄深悲壮的美学风格;艾迪生从民歌中揭橥出朴素的思想和优美的诗意。
杨格推崇艾迪生这位前辈诗人,把他称为伟大的作家和独创的榜样:“在最卓越的现代作家中间,艾迪生必须有一席地位,谁不以巨大的敬意谈到他的品格呢?!”杨格自觉地从艾迪生那里汲取了勇于创新和开拓的精神。
在袁枚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对他的影响。从《随园诗话》中的众多言论来看,钟嵘的“气物感人,摇荡性情”的创作发生论观点、司空图的“思与境偕”的意境创造论观点、袁宏道的“独抒性灵,不拘一格”的诗歌抒情论观点等等,都对袁枚的“性灵说”的形成有所助益,尽管袁枚在诗话中未能一一注明。前辈诗人王士祯独标神韵、追求冲淡清远的审美观虽不合袁枚的心意,但袁枚没有彻底否定它,而是把“神韵”聊备一格,肯定它的部分合理性。
当然,杨格和袁枚对前人思想资料的汲取,不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面是综合创造,透发新声。这种呼唤激情、强调独创的美学思想蕴含着朦胧的人文主义精神,跃动着神采飞扬的理想主义风貌。
综上所述,美学追求和美感经验的相通,生活经历和理论命运的近似,文坛冲突和文学情势的类同,借鉴和创造手法的相同,是袁枚和杨格美学思想灵犀遥通、不谋而合的原因所在。当然,袁枚与杨格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说准确些,袁枚的“性灵说”与杨格的“独创论”,属于世界美学中的同质异构现象。我们把袁枚和杨格进行比较研究,“并不只是使们们求知的好奇心得到满足,而是要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人类的艺术创造力的基础上,使我们重新汲取创造的生命之泉。”〔27〕18世纪的杨格和袁枚独创论美学给予后人的启示正在于此。
注释:
〔1〕《比较文学译文选》第162~16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2〕〔3〕〔4〕〔5〕〔6〕《试论独创性作品》第5、18、32、 33、34页,爱德华·杨格著,袁可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7〕〔8〕〔9〕〔10〕〔11〕袁枚:《随园诗话》卷一、卷二、卷五、卷七、卷一。
〔12〕〔13〕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
〔14〕郭绍虞:《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
〔15〕《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第311~313页。M·H·艾布拉姆斯著,郦稚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6〕《试论独创性作品》第6页。
〔17〕《随园诗话》卷一。
〔18〕《试论独创性作品》第22页。
〔19〕袁枚:《陶怡云诗序》。
〔20〕〔21〕〔22〕〔24〕《试论独创性作品》第3、24、25、 30页。
〔23〕〔25〕《随园诗话》卷五、卷六。
〔26〕见钱钟书:《七缀集·中国诗与中国画》。
〔27〕今道友信:《美学的方法》第2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