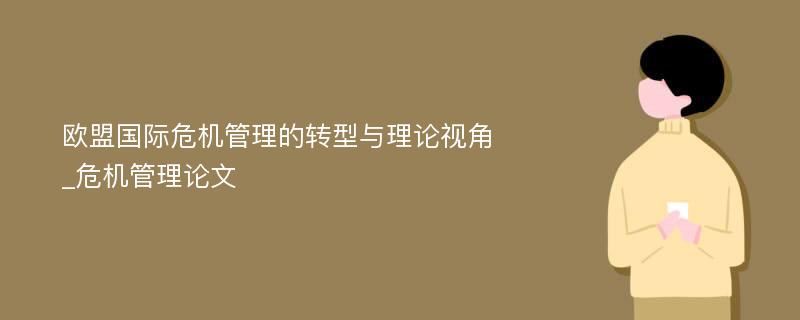
欧盟的国际危机管理转变与理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盟论文,视角论文,危机论文,理论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07-08-06]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07)09-0039-08
在近年来重大的国际危机管理中,欧洲联盟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不仅直接影响了危机的化解过程,而且为冷战后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的转型带来了理念、制度和行为规范的启示。与此同时,一体化建设中的困难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欧盟的危机管理能力,将它置于观念创新和制度改革的持续压力之下。因此,研究欧盟危机管理的“例外性”无疑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超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在当代欧洲的兴衰交替过程。本文通过回顾欧盟国际危机管理转变在各个层面所面临的动力或局限,结合相关的一体化理论,对欧盟危机管理的现实条件、核心观念和制度变迁进行经验分析,并对其作为特殊的国际行为体的发展趋势及对中国的启示做出判断。
一 国际危机管理新趋向与欧盟的转变
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危机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和政府之间在严重冲突中所发生的相互作用,这种冲突不是实际的战争,但却使人感到高度的战争威胁”。① 同时,危机的构成应至少包括“决策单位的首要目标受到威胁”、“可做出反应的时间大大受限”以及“事件本身的意外性”等要素。②
冷战结束所带来的国际政治版图变化不仅促进了各种行为体的力量消长(包括欧洲联合体的质量与数量),而且也给国际危机管理的传统观念和方式带来巨大挑战。
第一,国际危机的动因和形式发生变异,导致危机管理目标更加多元化,管理手段多样化。随着旧的两极国际体系及其高度对抗性斗争成为历史,世界大国之间的对峙与紧张态势大大下降,而国际军控领域的扩散与反扩散斗争、地区大国之间的冲突、中小国家因内部危机或战争而引发的地区动荡(包括种族屠杀和大范围的人道主义灾难)、国际恐怖主义事件对国际安全秩序的冲击等则取而代之,成为国际危机的主要表现。在这些危机的背后,无疑掩藏着大量地缘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甚至文化的深层原因。③
相形之下,一方面全球化极大地推进了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网络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些网络也因多种危机变得更加敏感和脆弱。2001年9月11日所发生的针对美国的自杀式恐怖袭击事件在相当意义上证明了这一点,同时这一事件也促进了国际危机管理向多元目标、多边合作转变。消除危机根源、预防连锁事态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管理目标,危机管理过程因“关口前移”而更早地展开;同时,主要大国对危机管理的垄断作用有所下降,利用和集合国际体系力量达到有效管理成为新的趋势。④ 无论是近年来针对有组织的恐怖活动所建立的各种跨国界、跨领域、跨技术专业的国际合作网络,还是解决朝核危机和伊朗核危机的多边合作进程,都充分表明国际危机管理方式已经发生重大转变。
第二,上述变化及其影响使得参与国际危机管理的行为体增多。危机的“决策单位”已不再局限于主权国家,而是延伸到国际组织、地区组织、军事联盟甚至非国家/政府组织。⑤ 在2002~2004年的伊拉克危机期间,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欧盟等均扮演过阶段性的角色。在解决近年来苏丹达尔富尔危机的过程中,非洲国家联盟的立场和作用直接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相关立场。⑥ 而在频繁爆发的阿以冲突中,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组织和黎巴嫩的真主党则明显地成为危机决策的另一方。危机主体之间严重的非对称性不仅使当今的危机关系更加复杂,也意味着国际危机管理的含义大大丰富了。
第三,危机所带来的决策压力时间延长。一方面,由于信息技术网络的便利和大众传媒的发达,大多数国际危机都经过一定的前期“曝光”,不再“完全地出人意料”,因而决策者做出反应的时间也较前宽裕,压力程度相对减轻。⑦ 伊朗在纳坦兹和阿拉克秘密建造两座核设施的消息,最早是由《纽约时报》在2002年8月披露的,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对此做出正式决议则是在一年多之后了;⑧ 另一方面,国际危机事件,特别是那些因持续内乱造成大量平民流离失所、生命不保的人道主义灾难,经先进的传媒手段持续报道后激起公众普遍的同情和干预冲动,又给决策者带来旷日持久的心理紧张。⑨
上述国际危机及危机管理的转型给欧盟带来的影响是多重的,并导致欧盟做出以下转变和调整:
第一,欧盟适时地改变了自己的危机观,认为后冷战时代的安全威胁是非单纯军事性质的,因此不能仅用军事手段来管理和解决危机。2003年出台的《欧洲安全战略》提出要用综合手段,特别要通过外交谈判、多边协商和推进国际规范等和平步骤解决国际和地区冲突与争端。⑩ 这些理念与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抑制后冷战单极世界格局所导致的种种弊端、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具有重要意义。(11)
欧盟还将危机管理视为输出其经济和政治制度,改善其周边安全环境,进而推进、深化一体化的机遇。2001年,前南地区马其顿共和国西北部安全部队与当地阿族武装之间发生冲突后,欧盟进行了数月的调停,使交战双方于当年8月13日达成《奥赫里德和平框架协议》。马其顿在该协议中承诺修宪、立法和结构改革,并优先发展与欧盟地区“更加紧密和趋同关系”。此后,欧盟通过增加发展援助、直接派驻维和军队(即欧盟历史上首次对外独立军事行动)和警察等帮助维持当地局势稳定,推动当局按协议实现诸领域的改革。2005年10月,欧盟又启动了帮助马其顿进一步改造内政司法系统的“配对计划(twinning project)”,拨出配套资金并派出警察顾问团,为当地机构改革、执法规范和行动标准等提供具体支持。国外的研究者认为,欧盟此举已经启动了将西巴尔干纳入欧盟的一体化进程。这种将集体安全体制的作用辐射到被管理者,增加其对欧洲观念和制度认同、向往的做法也是“干预性地区主义”的范例。(12)
第二,根据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危机“规模小、来源多样且不确定、地区性明显”等特点,欧盟采取了修复型的危机管理战略,注重发展自身对不可预测危机的快速反应和吸震(shock absorption)能力。(13) 相对于美国“更迭政权”的管理目标,这种“修复型战略”强调军事干预以塑造当地稳定而持久的和平秩序为任务,并与其他资源投入配套,最终达到对危机地区长期治理、消除动荡根源的目的。因此,其操作更精细、作用更显著、影响更深远。具体地说,在“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即欧盟所特有的合作性防务构造——ESDP)框架下,欧盟在危机地区展开的军警行动分为维稳(即分隔冲突双方或强制其休战)、替换(即取代原来由当地政权行使的军事和公检法等管理职能)、重建/改革(即督察当地法治与国家机器的改造)、监督(即确保达成的危机解决方案和协议得到贯彻执行)和保障(即为其他在事发地参与危机管理的国际组织提供安全保障)等多个步骤或类型。(14)
即使在欧盟无法主导的重要国际危机管理中,其危机管理过程也未因外交努力失败而中止。相反,欧盟及其成员国积极参与战后重建,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后危机处理(即全面的危机地区治理)实践。1999年6月,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空袭结束不久,欧盟就通过《东南欧稳定公约》,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战后重建的三大目标为“民主与人权、经济改革、发展与合作”,并成立专门的重建机构,为帮助科索沃及其周边地区恢复秩序和经济提供了80%的维和部队和70%的资金。(15) 欧洲人对次危机管理的创新不仅强化了欧盟的民事强权地位(civilian power Europe),也丰富了当代国际关系和危机管理理论。近年来,人们讨论的“次危机管理(secondary crisis management)”的概念,明确将经济和社会的繁荣与稳定作为新的管理目标,要求进行危机管理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在通过军事手段结束危机或维持和平之外,还要担负被干预国家的经济复苏、政治重构、难民安置等后续义务。(16) 这些内容主要是在欧盟的经验之上总结出来的。
第三,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危机特别是直接涉及欧洲安全的危机,进一步调动了欧盟的超国家资源潜能,使其政策独立性有了明显提升,危机管理的竞争力大大增强。以伊朗核危机为例,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欧盟及其许多成员国就实行了一套鲜明且独立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先后同伊朗恢复了外交关系。1998年以后,欧盟同伊朗建立了能源、毒品控制、难民安置、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合作机制,英、法、德三国与伊朗之间还保持着每半年一次的“全面对话”机制,协调双方在反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人权等全球性问题以及中东和平进程、伊拉克、中亚等地区性问题上的立场。与此同时,欧盟成为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欧伊双边贸易额在2002年曾超过150亿欧元。这些建设性的接触成果为后来英、法、德对伊谈判奠定了重要基础,使欧盟在战略上占据了此次危机管理的先机。(17) 欧盟的外交动员能力也得益于其资源的多样性。在联合国,除英、法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具有突出影响力之外,作为永久观察员的欧盟也积极协调、引导各成员国实现共同立场,使成员国在联合国大会的一致票率始终很高,增加了欧盟在国际危机中的共同立场。(18)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盟在推动安理会通过关于伊核问题的历次决议以及包括英、法、德和美、俄、中(“3+3”)的多边磋商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实属必然。
第四,欧盟加快了自身建设。一方面,通过增加成员国用于危机管理的预算,改善军队结构,强化各成员国之间的协同作战、快速反应与联合指挥的能力,欧洲快速反应部队已初具规模。同时,欧盟继续与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保持密切的协作关系,通过在这些组织中的欧盟成员国部队使自己的力量得到补充和延伸;(19) 另一方面,欧盟通过增设军事委员会、政策和预警署等机构增加其危机反应功能和决策集中程度,直至将有关体制设想写入《欧洲宪法条约》草案。虽然法、荷公投使欧洲政治一体化的步伐暂时放缓,但欧洲集体安全制度并未停滞不前。2007年6月23日,欧盟27国首脑会议通过了德国提出的《欧盟宪法条约》的新条约草案,同意将欧盟最高权力机构欧洲理事会由目前的成员国首脑会议转变为固定机制,设立常任主席一职,还设立统管欧盟外交和安全事务的“欧盟高级代表”一职。尽管后者与目前相同称谓的职位似乎差别不大,但因它由拟议已久的“外交部长”变化而来,并将合并目前的欧盟对外关系委员职责,还可以出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和主持成员国外长会议,其意义自然非同以往,表明欧盟进一步整合内部资源、“以一个声音说话”的制度努力仍在发展之中。(20)
二 对欧盟危机管理转变的理论解释
即使上面对欧盟相关理念、行为转变的归纳是客观和准确的,它们也只是如盲人摸象般的简单分辨和叙述,还没有说明欧盟危机管理的整体机理,未能回答“欧盟危机管理何以发生如此转变”这样的根本问题。事实上,危机管理只是整个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ESDP)以及对外行动(External Action)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欧盟内部治理和政府间主义制度安排的一个缩影。在复杂的表象之下,这一机制的运行和改良无不体现着联盟内部多元的利益构成、相互间的补充与制约关系,同时也体现着欧盟在内部和外部两个竞争图景之间的理性选择。说到底,对欧盟危机管理的深入分析不能脱离欧盟对外扩张和内部一体化的背景和原理。为此,借助于相关的一体化理论工具对欧盟危机管理加以透视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明智的。
(一)多元的利益——现实主义视角
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导致决策的主要动力来自行为者“理性决定的国家利益、权力、均势以及无政府世界中权力的运用”。而这种理性判断的前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际体系的变化可能带来各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二是国内政治形势对当局行动选择造成的影响。(21)
据此,首先可以将欧盟危机管理的观念、策略转变解释为在国际力量对比之下一种审时度势的理性选择。欧盟的对外行动能力一方面来自巩固和扩大的欧洲联合所产生的超国家权力,使得欧盟可以同时拥有集体安全的合力和各成员国的安全政策工具,通过众多的双边或多边(如联合国、北约等)舞台得到倍增和扩展;另一方面,在汇合内部利益认同的过程中,集体安全、协商一致、多边行动以及通过制度和规范约束使用武力的冲动等成员间规范已成为其国际竞争力的一部分。相对于美国“对内行民主,对外施霸权”的特性,欧盟在对内政策、行为习惯与国际活动方式之间不存在制度性分裂,也与其军事力量微弱、民事力量发达的“特殊禀赋”相一致。(22) 从实际效果看,民事力量可在危机管理全程中得到广泛应用,推延了战争的发生或减低了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对防止滥用武力或促进战后地区的全面重建起到了重要的制衡作用。反过来看,即使欧盟的观念和策略获得部分的成功,作为一种联盟的公共产品,集体行动和制度的软性推广也可以加深欧盟内部对集体利益及其全球身份的认同。
其次,可以这一视角诠释欧盟在观念、策略转变中隐含的对“均势”的追求,虽然此“均势”与梅特涅时代的“均势”已不可同日而语。上溯半个多世纪以来欧洲联合的过程,可以发现“欧洲人内部的立场分歧以及同美国的地位之争”,一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两大挑战。(23) 而冷战结束之后,这两大挑战更随着国际危机频发日益突出。一方面,欧盟扩大带来诸多新成员、新利益和新矛盾,在波兰等中东欧新成员中平衡传统大国轴心的新势力悄然出现,使联盟内部同样面临着均衡各方利益、实现新的团结与协调的压力。因此,无论是在处理国际危机的主张上,还是在具体资源和行动的调度上,欧盟必须坚持多边协商、透明公正的原则,保持各成员国均等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另一方面,冷战后欧盟对国际危机的主动干预与其重塑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望有着某种直接的关联。欧盟不再满足于做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小伙伴”,而是通过在重大危机问题上采取有别于美国的政策“来强化欧洲认同和欧洲身份”。(24) 2003年,在伊拉克的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欧盟及德、法等主要成员国与美国发生激烈的争执,从而引发了一场跨大西洋关系的严重危机。这一事件充分表明欧洲的独立身份意识得到了极大的增强,给欧美关系乃至国际政治格局所造成的冲击是结构性的。(25)
同样,现实主义视角也可以用来解释欧盟在危机管理理念和行为转变中存在的多重矛盾。在这个多层政治复合体中,传统的国家利益、决策机构的部门利益、官员的个人偏好乃至公众的参与要求等依旧顽强地存在,对联盟的集体行动构成重要的制约。从国内政治角度观察,欧盟成员国经常在不同危机情况下出现“政治意识上不同的优先考虑和对问题的不同认识”。(26) 例如,在伊拉克危机的后期,英国首相布莱尔优先考虑的是与美国的传统关系,而德国总理施罗德则更加看重德国公众的反战呼声。对美国发出的“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边,要么成为我们的对头”的要挟,西班牙首相阿斯纳尔和法国总统希拉克的认识截然相反。与此密切相关的是,高度发达的公众舆论也大大增加了危机决策者的国内政治成本,使后者的不作为与错误作为之间的灰色地带变得越来越狭窄。(27)
现实主义对行为者追逐权力的解释还有助于揭示联盟层面的利益冲突以及行动转变的艰难。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决策程序规定了成员国的独立与核心地位,而联盟的权力则主要体现于引导欧洲各国首脑及外交部长们优先讨论何种议程并提供何种决策建议。尽管后者的影响力不容低估,但欧盟要以此推动所有成员国在复杂、尖锐的危机中达成一致的管理意见显然不那么容易。此外,在欧盟本身的机构设置与职能分工上,政府间主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也造成了共同体(第一支柱)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第二支柱)之间以及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行动脱节和政策不配套等现象。属于第二支柱的欧盟理事会把对危机的评判和管理的规划视为自己的专属领域,对来自欧盟委员会的沟通意向不甚欢迎;在对危机地区的紧急援助项目上,共同体成员国则担心这种短期行为会损害其既定的援助目标与程序,使共同体沦为第二支柱的工具;即使是在欧盟理事会内部,军事部门也习惯于单向的对上负责而不愿意对民事部门开放和与之协作。(28)
现实主义的分析方法有助于证实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这一“高政治”领域内,国家权力及相关追求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而后威斯特伐利亚的超国家政治共同体还仅仅像领取了出生证的待生儿,虽然为各种内外危机所催生,却充满着脆弱与不确定性。在有限的权力结构下,欧盟危机管理只能是现实政治的妥协性安排,只能在对外目标与内部资源的动态平衡中获得自身行动的合法性。然而,现实主义的视角过于强调权力构成危机管理成败的决定因素,却无法揭示欧盟在多元利益的困境中实行危机管理转变的全部秘密。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政治妥协不完全是权力角逐中的务实考虑所致,还可能来自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习惯。尤其是当这些观念和习惯作为制度被固定下来之后,它们就可能成为约束力,弱化国家和官僚对权力的过度追求。
总之,在危机的现实面前,国际政治的影响是促使欧盟采取行动的重要前提,然而,在不同的案例和不同的客观条件下,对外竞争与联盟内部关系的平衡、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等多组现实因素频繁互动,对欧盟不同层次管理者的影响和后果是不一样的。美国因素和国内政治的作用呈明显上升的趋势,二者均在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着力点之外,更增加了欧盟的管理难度。此外,危机管理对集中权力和决策效率的自然要求又构成了对主权、支柱及部门权力的挑战,从而令欧盟经常处于选择不同价值和原则的两难境地。
(二)网络中治理——制度主义视角
制度主义理论的倡导者将欧盟视为一个非等级结构的国家联合体,设定这个体系中各成员国在合法地拥有自主权的同时,通过协商谈判“有意识地确定并努力实现一个政治目标,并确保行为者的行为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29)
在此过程中,联盟层面的官僚机构(如部长理事会、欧盟委员会以及欧洲议会等)、成员国政府相关机构和众多的专业团体、利益集团和民间组织根据共同的议题和关切组成和参与一个协商决定的网络。使各自的利益(包括联盟机构自身的利益)均有机会得到充分的表达和保护,从而进一步塑造了网络的功能及其合法性。(30) 欧盟的多层治理目标就是这样达到的。
制度主义理论对欧盟为改进危机管理以及内部整合所展现的独特性具有一定的解释力。首先,欧盟作为一个“完美的协商谈判体系”,其总体目标无疑是促进成员国兴趣和行动的“欧洲化(Europeanization)”,即“向更接近欧共体规范、政策和习惯的方向移动的进程”。(31) 尽管协商并非每每成功,但作为一种制度化行为,它增加了成员的参与感并促进其对联盟的向心力,因为联盟为协商所预定的共同目标已经打上了欧洲化标签,它可能催生某种从众效应,使任何成员难以置之度外。仍以2007年6月23日欧盟27国首脑会议为例,尽管波兰对新条约草案中的“双重多数表决机制”条款持有异议,但在最后时刻被法、英、卢等国首脑说服,对欧洲大家庭的认同使波兰终于做出妥协。(32)
其次,外部压力(如美国因素)和各成员国国内政治造成欧盟危机管理的弱化或失败也为其事后改进内部团结和制度改革提供了动力。在长期的一体化过程中,欧洲民族认同和泛欧认同始终并存和相互渗透,融会成独特的欧洲精神。在欧盟各种制度的构建和改革中,体现这种精神的“自由”与“合作”两大核心价值始终并驾齐驱,当内外危机超过临界,失败与分裂成为更现实的挑战时,人们会理智地回到合作的轨道上,以相互妥协来维护共同体的命运。(33) 伊拉克危机之后,欧盟内部关系的修复速度超出人们预料,并且直接体现于联盟在后来伊朗核危机中的突出作为。国际舆论对 2003年10月英、法、德外长共同出访德黑兰,展开对伊谈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此举“不只是解救了处在危机边缘的伊朗,也挽救了欧盟的共同外交政策”。(34)
在成员国的政治回归之外,近年来欧盟也有意改进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制度,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改进一体化的网络功能。2002年11月19日,欧盟理事会的总务及对外关系理事会(General Affairs and External Relations Council--GAERC)通过了推进民事-军事协调(Civil-Military Co-ordination--CMCO)的“行动计划”。这一计划实际上是一个制度性的部际乃至支柱间的会商活动,由政治决策部门的欧盟政治与安全委员会主导,参加者除欧盟理事会秘书长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外,均为各成员国驻布鲁塞尔大使;在此之下,还成立了由来自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秘书处的高级官员组成的危机反应协调小组(Crisis Response Coordinating Team--CRCT),以确保各军事、政治、民事行动方案在战略上的有机衔接,参加者中包括各成员国驻布鲁塞尔使团的高级官员。
此外,欧盟还利用自身和成员国的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对成员国、入盟国和候补国的外交、军事和民事部门高官、欧盟各部门官员以及参加欧盟危机管理行动的人员进行军民联合危机管理培训,两度举行了与军民协调主题有关的危机管理演习。这些举措不仅提高了管理合作网络的开放度和吸纳力,增加成员国对集体管理危机重要意义和迫切性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在潜移默化之中培育了一种跨国、跨支柱和跨部门的协调文化。(35)
由此归纳,欧盟解决危机管理中的内部利益冲突的方式是:一方面承认和保护这些现实考虑,另一方面则借助于合作网络的学习、示范功能,增加各方对集体利益的认知,软化其思维和行为偏好,而这些功效正是反应性制度主义所强调的。(36)
黑格尔说过,“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37) 欧盟危机管理的模式特点在于其内部开放度和集体参与的通道,它以共同行动的收益与必要性转化成员们的认同程度,但也因此存在决策分散、脱节和低效率等弊端。构建向效率倾斜的合作文化,达到决策的相对集中固然应该是欧盟改进其危机管理的努力方向,但这不意味着它会简单地回归到民族国家的权力模式。制度主义理论所提倡的恰恰不是传统的民族国家建设,而是民族国家经过确立共同的治理标准体系,在保留自身基本属性的同时融为新型的国家社会(a society of states)。欧盟正是以网络性建设确立自身的标准体系、加深成员国的认同等隐性方式来抵消自身的权力缺陷,以制度的力量逐步地侵蚀和软化国家主权。这个过程所积累的各种不经意甚至是不情愿中的进步,反过来又将产生示范效应,推动新的认同和新的制度网络建设。欧盟历经挫折和失败仍不断前进的真谛就在于此。
三 结语
危机管理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领导人(或集团)在利益受到高度威胁或突发性对抗的压力下的决策行为、危机决策的相互反应以及政府在决策中进行内部组织的过程等三类。最后一类研究“将政府看做是由若干组织(按层次和职能机构)形成的一种复杂关系网络,危机决策是这种组织结构下相互作用的输出”。(38) 本文选取了第三类研究视角,将欧盟危机管理活动与其所处的“复杂关系网络”之间的联系作为主题,意在从宏观上把握这一特殊国际政治行为体的个性。
上面的论证表明,危机管理是整个欧盟安全建设和对外关系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它不可能超脱于联盟的内外环境而独善其身,其目标、机制、能力和实际运行无不受到国际体系和内部动力的影响。冷战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既促进了技术扩散、人员流动、制度交汇和观念碰撞,也提高了危机发生的频率和国际管理的难度。这一历史时期的国际危机管理主要转为“由第三方通过和平的外交手段或强制性的军事手段干预使危机得到缓和与解决”。(39) 显而易见,危机管理已成为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展开激烈竞争的战略高地。在此背景下,欧盟凭借其一体化所取得的超国家体系优势,特别是其经济和制度力量参与国际危机管理竞争实属必然。随着一体化的持续进展,欧盟的安全疆界延伸到更广阔的地域,同时也深入到价值观与制度安全的层面。虽然欧盟在危机管理中不乏对强制性军事手段的应用,但如同它使用和平的外交手段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和化解危机的“外溢”效应,在恢复危机地区秩序后,用欧盟的制度推进当地改革,进而达到“良治”与和平。由此辨识欧盟的危机管理模式,可见其有别于美国管理之道的深刻和精细之处,从而准确地理解其国际竞争力的独特性和可持续性。
与此同时,必须承认超国家主义在欧盟对外关系,特别是危机管理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在欧洲政治一体化完全成型之前,民族国家仍然是危机管理的行为主体。由于成员国主权既有的竞争性、联盟的行政功能缺陷和欧洲各国社会动员体制的区别,欧盟的对外行动能力(他重力)与其客观拥有的人口、地域、经济、军备和文化资源(自重力)还远不相称。(40) 尤其当其危机管理陷于困顿和失败时,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行为属性和存在状况就变得模糊不清。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危机管理的成败也会不断刺激欧盟成员国观念和行为的转变,而联盟层面的一体化制度创新也会引导成员国产生新的共识和自我约束力,欧盟危机管理机制就是在国家和超国家两个重心之间的频繁摆动中逐次进步的。据此判断,未来欧盟危机管理的发展方向极有可能是继续强化在共同外交和安全方面的标准,在现有的法律、财政、行政框架下整合分散的权力,通过微小的、局部的示范效应,构建向效率倾斜的合作文化,达到决策的相对集中。这无疑是一个历史的博弈过程,无论这个过程充满怎样的曲折和反复,它将由欧洲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所决定,并最终为欧盟有效地应对未来的国际危机带来更大的可能和更多的机遇。
最后应该提到的是,欧盟是全球体系中正在兴起而又特殊的行为体,其管理国际危机的理念和不断改进的实践对同样处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具有诸多启示:
第一,欧盟危机管理的原则所包含的对抗性较低,也不以军事威胁为后盾,因而欧盟可以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多极化发展的基本力量。欧盟强调国际规则、国际组织在危机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坚持多边合作方式,注重外交谈判等非军事方式,其有限的军事力量投送也多服务于维持秩序和干预人道主义灾难的目的。这些特点不仅与中国一贯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存在较大相通之处或其已大部分为中国所接受,也是中欧在未来国际危机管理中加强合作的重要政治基础。
第二,欧盟危机管理更以危机后的地区治理见长,通过对危机地区的战后援助,输出其经济、法律和社会保障制度,消除未来冲突的隐患。这种“次危机管理”做法促进了管理的长效性,具有相当的普适意义。随着中国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必将增加,参与周边和世界其他地区危机处理的机会也将不断增多。因此,借鉴欧盟的经验对改进中国参与国际危机管理的观念、方式是必要和有益的,更进一步说,这对于统筹和构建未来中国外交的“软力量”也具有一定的启发。
第三,欧盟危机管理机制的合作主义内核和超国家制度设计,对中国参与建设本地区多边安全机制也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目前,东亚地区政治秩序处于结构转型时期,大国的传统关系格局正在被打破,旧的同盟关系有所弱化,局部的多边政治与安全机制(如东盟所带动的诸多对话架构)已显露雏形。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不断改善,朝核危机的最终解决,建立东亚地区和平与安全机制的时日已然可待。未雨绸缪,中国应及早研究相关经验,为此做好准备。
注释:
①Glenn H.Snyder and Paul Diesing,Conflict Among Nations:Bargaining,Decision-Making and System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Cris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p.7.
②[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30页。
③赵绪生:《论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危机与危机管理》,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l期,第24~26页。
④赵绪生:《论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危机与危机管理》,第26页。
⑤雷勇:《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危机》,载《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24页。
⑥由于达尔富尔地区局势的持续恶化,2006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曾通过决议由联合国部队接管非洲联盟在该地区的维和行动。对此,中国表示应首先尊重当事国苏丹政府的意愿。2007年6月,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决定延长非洲联盟维和部队的任期,以便有充足的时间在该地区部署联合国-非盟混合维和部队。对此,中国表示在解决达尔富尔危机中,“非盟应该发挥关键作用”。参见中国新闻网:《中国特别代表再度访非 表明对达尔富尔问题立场》,载《中国网》,2006年6月17日,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7-06/17/content_8400694.htm。
⑦赵绪生指出,“紧迫性是国际危机的根本特性”。就危机事件的国际影响而言,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从后冷战时期历次重大国际危机管理过程的角度看,其“没有持续数年的国际危机”的断言则有失客观,所称“重大决策必须在紧迫的时间压力下完成”之论点则值得商榷。参见赵绪生:《论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危机与危机管理》,第24~26页。
⑧唐志超:《伊朗核问题的由来、发展及走向》,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年第2期,第48页。
⑨西方学者曾专门就电视新闻媒体的报道量与公众对重要国际问题的认知度做了大量研究,得出前者对促成后者向当局的外交政策施加压力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结论。参见Douglas Van Belle," Domestic Imperatives and Rational Models," in David Skidmore and Valerie M.Hudson,eds.,The Limits of State Autonomy:Social Groups and Foreign Policy Formulation,London:Westview Press,1993,pp.171-172。
⑩European Council," A Secure Europe in a Better World: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Brussels,December 12,2003,p.12,pp.18-19.
(11)周敏凯:《论伊拉克战争后大西洋联盟的危机》,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23页。
(12)Isabelle Ioannides," EU Police Mission Proxima:Testing the' European' Approach to Building Peace," in Agnieszka Nowak,ed.,Civilian Crisis Management:The EU Way,Chaillot Paper,No.90,Paris:EU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2006,pp.69-86;[加拿大]阿米塔夫·阿齐亚:《地区主义和即将出现的世界秩序:主权、自治权、地区特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2期,第68页。
(13)邱美荣:《试析冷战后欧洲危机管理风格的变化》,载《欧洲研究》,2005年第1期,第19~20页、第30页。
(14)Pedro Serrano," A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in Agnieszka Nowak,ed.,Civilian Crisis Management:The EU Way,Chaillot Paper,No.90,pp.42-43.
(15)陈志敏:《欧洲联盟的军事化:从民事力量向军事力量的变形?》,载《欧洲研究》,2004年第5期,第81页。
(16)Patricia Youngson," Coercive Containment:The New Crisis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Vol.15,No.5,2001,p.37.
(17)李格琴:《欧盟介入伊朗核问题政策评估》,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419~423页;李小军:《论美国和欧盟在防扩散战略上的分歧与合作》,载《外交评论》,2005年第6期,第86页。
(18)张凡、吴倩岚:《中国和欧盟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作》,载周弘主编:《共性与差异——中欧伙伴关系评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151页。
(19)Pedro Serrano," A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in Agnieszka Nowak,ed.,Civilian Crisis Management:The EU Way,Chaillot Paper,No.90,p.40.
(20)潘革平、谢栋风、尚军:《欧盟峰会就新条约草案达成协议》,载《新华网》,2007年6月23日,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7-06/23/content_840855.htm。
(21)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81页;Andrew Moravcsik," Introduction:Integrating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in Peter B.Evans,Harold K.Jacobson,and Robert D.Putnam,eds.,Double-Edged Diplomacy: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p.1-42; Peter B.Evans," Building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olitics:Reflections and Projections," in Peter B,Evans,Harold K.Jacobson,and Robert D.Putnam,eds.,Double-Edged Diplomacy: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pp.399-405.
(22)资中筠:《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7页。
(23)[德]贝娅特·科勒-科赫、托马斯·康策尔曼、米歇勒·克诺特著,顾俊礼等译:《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7页。
(24)Robert Jervis," The Compulsive Empire," Foreign Policy,No.137,July/August 2003,pp.83-87.
(25)周敏凯:《论伊拉克战争后大西洋联盟的危机》,第21~23页;孙溯源:《认同危机与美欧关系的结构性变迁》,载《欧洲研究》,2004年第5期,第53~-63页。
(26)贝娅特·科勒-科赫、托马斯·康策尔曼、米歇勒·克诺特:《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第308页。
(27)Douglas Van Belle," Domestic Imperatives and Rational Models," in David Skidmore and Valerie M.Hudson,eds.,The Limits of State Autonomy:Social Groups and Foreign Policy Formulation,pp.159-162.
(28)Catriona Gourlay," Cinvi-Civil Coordination in EU Crisis Management," in Agnieszka Nowak,ed.,Civilian Crisis Management:The EU Way,Chaillot Paper,No.90,pp.111-112; Radek Khol," Civil-Military Coordination in EU Crisis Management," in Agnieszka Nowak,ed.,Civilian Crisis Management:The EU Way,Chaillot Paper,No.90,pp.127-128.
(29)贝娅特·科勒-科赫、托马斯·康策尔曼、米歇勒·克诺特:《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第176~179页。
(30)陈玉刚:《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199页
(31)Roy H.Ginsberg," Conceptualizing the European Union as an International Actor:Narrowing the Theoretical Capability-Expectations Gap,"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37,No.3,1999,p.443.
(32)潘革平、谢栋风、尚军:《欧盟峰会就新条约草案达成协议》,载《新华网》,2007年6月23日,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7-06/23/content_840855.htm。
(33)蔡玉辉、杨豫:《欧洲精神与欧盟制度析论》,载《欧洲研究》,2006年第1期,第90页;石佳友:《“后现代”欧洲及对中国的意义》,载《欧洲研究》,2005年第1期,第12页。
(34)戴轶尘:《伊朗核问题中的欧盟共同外交》,载《社会观察》,2007年第4期,第23页。
(35)Radek Khol," Civil-Military Coordination in EU Crisis Management," in Agnieszka Nowak,ed.,Civilian Crisis Management:The EU Way,Chaillot Paper,No.90,pp.125-133.
(36)贝娅特·科勒-科赫、托马斯·康策尔曼、米歇勒·克诺特:《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第315~316页。
(37)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c des Rechts 1820,转引自William Archibald Dunning,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ies from Rousseau to Spencer,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0,p.156。
(38)胡平:《国际冲突分析与危机管理研究》,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第159~160页。
(39)赵绪生:《论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危机与危机管理》,第27页。
(40)陈玉刚:《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第2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