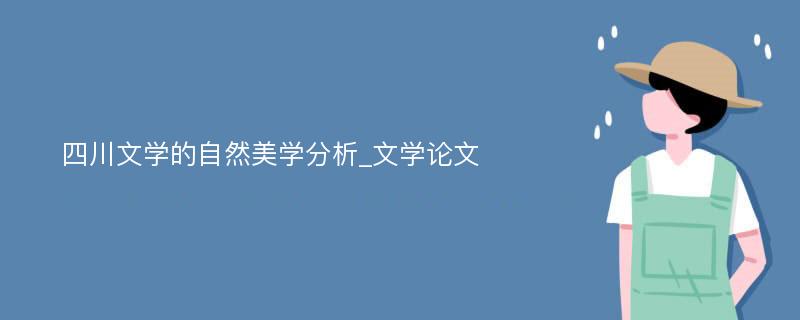
“川端文学”自然审美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然美,作为人的主体心灵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相互交融的产物,历来包含有两种主要的审美倾向:一是把主体物化,二是把自然山水人格化。这两种倾向也可以说是文学作品中自然美创造的两种基本方式。“川端文学”自然美的营造,当然也不例外,但具体情况要比此精巧繁复得多,而且极富有层次感和表现力。
众所周知,日本美学追求“物哀”。关于“物哀”,解释颇多。笔者以为,“物哀”是日本民族对自然风物与人的情感之间的同形关系、感应关系的一种审美概括。“物”就是自然风景、自然风物;“哀”则指由自然景物诱发、或因长期审美积淀而凝结在自然景物中的人的情思。川端曾言:在小说家中,自己是属于喜欢写景色和季节的。〔1 〕他同时又说:“自然,它是我的感受的借助之物”。“风景充满了幻想和象征”。〔2〕如果说“物”指称客体自然,“哀”代表主体情感, 那么“物哀”观念,在川端康成的文学实践中,明显呈示出其作为审美思维方式的意义。不过,这还不是“物哀”内涵的全部。日本民族的“物哀”追求,明显规制着其审美活动中的某种虚幻、哀伤情调,“确切一点说,是多半充满倾向于感伤、孤寂、空漠而又有所希冀的一种朦胧的情感、意趣和心绪”。〔3〕那么, “物哀”审美的这一情感内涵又是缘何而生的呢?
大和民族从自然风物的生死荣枯,引发出对生命短暂无常的哀叹,又在把这种生命哀叹投射于自然风物的过程中,感到天物的哀怜,人生的欣喜,并获得一种“物人同命”的心理平衡和“物心瞑合”的精神超脱。正如川端所言:日本人的“悲哀和哀伤本身融化了日本式的安慰和解救”。〔4 〕日本学者柳田圣山以象征日本人生命的樱花为例,对此进一步说明:一天早晨,樱花突然盛开,美丽无比,但刹那间又份份飘落,则不胜哀伤,“与其因为飘落而称无常,不如说突然盛开是无常,因无常而称作美,故而美的确是永远的。”〔5〕可以说, 正是这种积极的无常感支撑着日本人的生活和心理,它显示了大和民族那种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世事情,以宿命的精神为拼命人生的深层精神结构。“川端文学”的自然抒描,就充满了日本民族这一“物哀”式的审美追求。透析“川端文学”的自然审美,既可了解到“川端文学”独特的自然美境界的营构方式,亦可触摸到川端氏深层精神世界的某些脉络。
如果由审美客体切入进行考察,“川端文学”自然美的营构主要体现为下列几点:
一、季节感 季节感是日本文学的传统。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而南北狭长的岛国,季节在时空上的推移和变化,既细致又鲜明,从而培养了日本民族对季节变迁的敏锐感觉。
“川端文学”中,季节的推移和变换多是通过对一些具体自然物的描绘来体现的。在《古都》中,作者通过赏樱、葵节、伐竹会、大字篝火、时代节,展示古都时令的推移,自然就象一段优美的旋律,一个流动的乐章,呈现出其自身千姿百态的变化美。
川端曾指出:以“雪、月、花”几个字来表现四季时令变化的美,这是包含了山川草木、宇宙万物、大自然的一切的。这样看来,文学中追求“季节感”就象“俳句”追求“季语”一样,是对整个自然美的浓缩。一提到风花雪月,就会想到四季时令变化的美,就会想到整个大自然造化的美。这种美的联想对于日本民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无指向性的,是深远的。
但是,“季节感”在“川端文学”中的美学意义还不仅于此。叶渭渠指出:“所谓季节感,不仅是指对春夏秋冬四季的循序推移的感受性,而且是对在日本文化土壤上蕴酿而成的人与自然、人的感情与季节风物交融、内中蕴含着苦恼、妖艳、爱恋情绪的理解性”。〔6 〕“川端文学”就是在忠实再现四季自然本身美的同时,还将人的精神、感情、心绪溶铸其中,从而形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这一点充分表现在《雪国》的描写季节的变迁上。他写雪国严冬、初春、深秋的季节转换、景物变化,都是移入人的感情和精神、作为伴随人物感情的旋律来描写的。岛村与驹子的初识是在雪国的初春时节,作品在尽力捕捉雪国初春时节“新绿景象”(8处)的同时, 又把驹子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岛村对驹子纯美品质的体味溶入其中,不仅烘托了驹子的纯真存在,而且唤回了岛村“容易失去的真挚感情”。随着男女主人公情感交流的进一步加深,驹子那种认真而挚着的生活态度,也就越发让怀抱虚无思想的岛村感到吃惊和徒劳。此时,作品穿插其间的写景主要是雪国严冬“寒峭的雪夜”(17处)——驹子为了生存的苦苦挣扎,真情空付的悲凉心境以及岛村超然冷漠的内心世界,也就经过这一“季景”的强化,冷冷地向人迫来。及至岛村第三次来雪图,作品则把男女主人公最后的交往放置在雪国深秋的背景之上,以反复出现的“秋虫”(13处)“枯草”(8 处)意象暗示主人公的生离死别;以多次渲染的“月夜”(4 处)“星河”(11处)意象表征岛村“人生徒劳”“幻境恒美”的感念和精神。
“季节感”在“川端文学”中还有一个美学功能,这就是无常、哀伤氛围的创制。“人的生命与花开叶落的自然活动、天体运行一样,与宇宙现象共生共死——这种把自然和人生合为一体的思想,相当普遍地扎根于日本人的心里”。〔7〕也就是说,花开叶落的季节流动感, 经过历代审美积淀,已永远成为生命无常的固定象征,文学中表现“季节感”就必然感时伤逝。也就是说,很难分清是季节感诱发了川端的无常感,还是川端心中的无常感找到了自己的对应物。重要的是它们能升华为文学作品中一种独特氛围的艺术美,成了“川端文学”自然美境界的有机构成因素。
二、色彩感 色彩是自然审美中最易引起美感的一种形式要素。对自然风物有着细腻感受性的川端,在以纤细的笔触力显自然风物天然本色的同时,一方面用比喻、对比、拟人等手法,增强景物描写的色彩感;另一方面,又进行一些巧妙的色彩搭配和组合,不仅给人以鲜明的绘画着色之感,而且拓展了读者对于色彩想象的空间,引起极妙的美的遐想:
“蝶儿翩翩飞舞,一忽儿飞得比县界的山还高,随着黄色渐渐变白,就越飞越远了。”(《雪国》)
这是对自然物天然本色的准确捕捉。通过对比、比喻等手法来突出色彩感,这类例子在“川端文学”中更是不胜枚举:
“银杏的街树还是嫩叶的时候,那中间穿过列队的红旗,只觉得很美。”(《湖》)
可以说,绘画般鲜亮的着色,绘制出一个个质地可感的画面,极大地增强了自然审美的表现力。另外,“川端文学”即使是在那些寄托人物感情,象征人物命运的景物描写中,也是力突色彩感。不过,作者此时所营构的“色彩世界”已超出了自然物的天然本色,而是运用色彩的搭配和组合,给我们绘制了一个“超现实”的色感境界。
例如他在《雪国》中,把驹子悲哀的命运和纯美的印象进行糅合,写夜空里的“月儿皎洁得如同一把放在晶莹蓝冰上的刀”。此时的色彩绘制,已不再象绘画着色般质地可感了,而是存在于想象中,具有一定的幻美性质。它不仅是作品中人物情感命运的象征,而且是作者审美旨趣、瞑想情怀的体现。
三、动态感 动与静,作为一对对立而又统一的范畴在自然风物中普遍体现。不过,“川端文学”写景却极少静态描摹,而是在动态中展示自然之美,伴随着人物思想感情、心理活动,通过比拟、暗示、象征、移情等手法,极力显示自然景物的内在律动。
在描绘自然风物外在性状的同时,揭示其内在的生命能量、生命活力,这本身就能使静物给人以动感:
野山茶树,是棵树干上积蓄着力量的老树。”(《山音》)
通过对自然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把握,使景物描写化静为动:
“正在说话的时候,发黄的叶子不断地飘落下来。因为没有风,叶子没有飘动,直接掉下来的。”(《山音》)
以此为基础,运用比喻、拟人、感觉移入等,增强景物描写的动态感,这比动者为动更高一筹,因而在“川端文学”自然审美中,更是普遍至极。我们这里仅举几例:
“晨曦早早造访竹林,黄昏则捷足先登来到了杉树间。此时正是白昼。竹叶宛如一丛丛蜻蜓的翅膀,同阳光嬉戏作乐。”(《春天的景色》)
移情、象征等手法也给“川端文学”的自然抒描带来一定程度的动感。因为,给自然景物注入人的情感心绪,或用自然景物象征人物的命运、容貌、心理等,这自然而然就使自然景物具有了象人一样的内在律动:
“北山杉林的枝桠一直修整到树梢。在千重子看来,呈圆形残留在树梢上的叶子,就象是一朵朵雅淡的冬天的绿花。”(《古都》,象征苗子纯美、坚强的生命)
“川端文学”自然审美中对动态感的追求,是和他的文化精神追求一脉相承的。川端曾言:广袤的大自然是神圣的灵域,凡高岳、深山、瀑布、泉水、岩石,连老树都是神灵的化身。〔8 〕马林诺夫斯基则告诉我们:构成有灵观实质的乃是人类强烈的生命意识。〔9 〕由此可见,川端氏是把自然万物当作善于启示、可以交心的生命体来看待的。这种文化心理必然规制着“川端文学”景物描写上对动态感的追求。
四、朦胧感 川端曾言:“我渐渐懂得对事物不甚明了,本身就是一种幸福。”〔10〕这体现了作者企图通过艺术来把握浑涵神秘的宇宙人生而又把握不了;企图通过美来实现对现实人生的超脱而又超而不脱的复杂心境。因而,有时免不了就会产生还不如把一切都归之于朦胧模糊的心情。体现在自然审美中,就是朦胧感。就表现方法来说,可归纳为下列四点:
a、他经常化繁为简,对具体景物进行抽象含混的玄思。 如下面关于秋虫的一段,就很典型:
“有些飞蛾,看起来老贴在纱窗上,其实是已经死掉了。岛村把它们拿到手上,心想:为什么会长得这样美呢!”(《雪国》)
这分明是一段关于生命与死灭、美艳与悲哀的玄思。遣文造句,虽算明白,但寓意却是浑涵抽象的。
b、他一方面精选自然物象,进行粗线条勾勒, 另一方面却赋予其宽泛深奥的象征意义。因而深奥莫测的象征和暗示,也造成了其景物描写上的朦胧感。
如《舞姬》中以波子家挡雨板上朦朦胧胧地落下冬日的枯萎的梅枝的影子,创造出淡淡的哀愁气氛,来象征这个家庭的衰败和崩溃。
c、在此基础上,川端又经常把不同的物象和联想突然组合, 这更增强了景物描写上的朦胧感:
这些火星子迸散到银河中,然后扩展开去,岛村觉得自己仿佛又被托起飘到银河中去。黑烟冲上银河,相反地,银河倏然倾泻下来。喷射在屋顶以外的水柱,摇摇曳曳,变成了朦朦胧胧的水雾,也映着银河的亮光。”(《雪国》)
这里,迸散的火星、飘浮的黑烟、倏然的银河、摇曳的水柱、朦胧的水雾,被突然组接在一个画面中,使人无法一下子廓清它们之间的相关性,而只产生一种朦胧模糊的感受印象。
d、作者经常把自己或人物的忧郁和感伤情绪, 渗透在景物描写中,加以浓化和渲染,造成幽深朦胧的境界。这可以说是“川端文学”对景物所进行的直接朦胧化处理。《春天的景色》中的“疑是白羽虫漫天飞舞,却原来是绵绵春雨”;《雪国》中“远处的重山桑峦迷迷濛濛地罩上了一层柔和的乳白色;”如此等等,都是有意识地用暮色、梦境、春雨、叠峦等等,造成朦胧的意境,把自然物的性状、色彩朦胧化,盘托出主体迷惘悒郁的心境。
总之,这些手法的运用,常常使“川端文学”的自然抒描笼罩在一种朦胧幽玄的氛围里,造成一种蕴藉含蓄的艺术美,让读者的想象在广阔的空间自由驰骋。无疑,朦胧美,是构成“川端文学”总体幻美情调的重要因素。
五、空灵感 “川端文学”写景,极少全方位的客观展现,而是努力捕捉自然风物的突出特征。即便如此,也并不细描,而是在素描淡写的基础上,抑实扬虚、无限远延、极力幻化,主观上追求一种虚幻邈远、迷朦隐约的意境氛围,客观上造成一种空灵飘动、融思畅神的美感效应。这一审美品格在《雪国》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雪天夜色的笼罩下,家家户户低矮的屋顶显得越发低矮,仿佛整个村子都静静悄悄地沉浸在无底的深渊之中。”——利用视觉上的错觉,把景物存在的空间伸展到无限,让实存的景物带上空浮感。
“对过杉林那边,飘流着一群蜻蜓。……象被什么东西追逐着,又象急于抢在夜色降临之前不让杉林的幽黑抹去它们的身影。”——突出景物的飘流,然后进行瞑想,让人的远思遐想,代替景物的存在,完成虚化。
“对岸陡削的半山腰上开满了芭茅的花穗,摇曳起来,虽说白得刺眼,可它却又象是在秋空中翱翔的一种变幻无常的透明的东西。”——突出景物的色彩和摇曳,刺激读者对色彩进行幻想,接着用比喻直接把实物幻化。
以上,在手法上可以归结为:飘浮化、空虚化、幻觉化、玄远化。
今道友信指出:“艺术上的最高沉醉,是通过物而实现了对物的突破。”〔11〕“川端文学”的自然审美,无疑是强烈渗透着这一追求的。如果说“川端文学”自然抒描上对“季节感”、“色彩感”的追求,还多少局限于纯审美的意义,那么,对空灵感的追求,则指向了创作主体的精神深层:即对有限的突破、对无限的向往,也就是生命的救助之途——艺术超越。“生命通过艺术而自救。”(尼采语)《源氏物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四季风物中春天的樱花、秋天的红叶,都可赏心悦目。但冬夜明月照积雪之景,虽无色彩,却反而泌人心肺,令人神游物外。”〔12〕如果说“赏心悦目”还是一种纯审美的效应,那么“神游物外”则是超越精神的体验了。“川端文学”自然审美中神游物外的空灵美,就是创作主体超越体验在文学作品中的实践和表现。
如果从审美主体入手进行整理,则可以从下列几组关联体来感悟“川端文学”自然美境界的营构特点:
一、景与环境 “川端文学”中的环境构成,很少以社会生活、日常物事作为核心。即使有所涉及,也是轻描淡写、几笔带过。而主要是以大自然为背景,把人物置身于自然风景之中,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强化作品的情感意蕴。“川端文学”那种浓郁独特的抒情基调也由此奠定。
这首先体现在作品的整体构思上,不是以中心人物的观光旅行为构思的基点,就是以季节的流动为谋篇布局的主线,或者是两者的结合。
《伊豆的舞女》就是以主人公“我”的旅行为构思的基点,在自然环境中展开故事,渲染主题的。“我”在旅途上和舞女及其家人邂逅相遇,结伴而行。于是,我和舞女的物事接触、情感交流,都是在美丽的大自然怀抱中,以自然风物为媒介而生发、升级:我们在各自对风景的赞叹中体味对方的情爱心理,又在旅途的相互照拂中,感觉这种情感的加深。随着旅程的延伸,我和舞女之间那种朦胧纤细的恋情,也逐步深化和浓化。这里,自然风景不仅成为爱情的代言人,而且以其纯洁恬美的氛围,很好地衬托了人物情感的纯真美好。相比之下,旅途停宿时,一些生活场景的描述,就缺乏这种美学功能,因而作者常常是几笔带过。
在《雪国》里,作者则是把男主人公岛村的三次旅行和雪国初春、深秋、严冬的季节流动结合交叉,以寒气逼人、冰清玉洁的雪的世界为背景,作者很好地把握了女主人公那“悲美”的内心世界,并借此把这种准确的审美把握传给了读者。
其次,体现在具体环境的创制上,常把人物身处自然环境之时,作为展现人物情感心理特征的关键时刻,而很少把这一任务放在家庭关系,日常生活中来完成。
《古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品不仅以四季为框架进行谋篇布局,而且多在四时行事之时,对人物进行刻画。四时行事,是指日本民族一年四季例行的庆典活动,主要有观花、赏月、葵节、盂兰盆节等。活动内容均与大自然有关。
把大自然当做人物生活的背景和环境,其意义不只在于,可以把自然风物信手拈来,作为人物情感的触媒、心绪的象征,更主要在于,自然环境自身所具有的风貌特征,此时起着从整体上渲染和规定作品抒情基调的作用。比如有人在谈到《雪国》时指出:“白雪弥漫的山村,给作品披上一袭洁白的外衣,给读者以清冽纯净之感,这也是构思上讨巧取胜之处。”〔13〕此话就是就此而言的。
二、景与情节 “川端文学”中,情节的叙述常常伴随着对景物的描写,景物不仅起着联结人物关系、铺展故事情节的作用,甚至还能诱发人物的感情。这样,写景有时自然就成了情节推动的有机因素。情节是性格的历史,但是川端似乎要让人们相信:自然景物有时也是性格的有机组成。因为,川端小说中出现的背景及景物已不仅是人物活动的空间范围,而是人物情感和心理的对象化,也就是把景物人格化。这些人格化的自然物,不仅是作者用来观照人物命运发展的对象物,而且是人物自身个性特征的象征物。因而就具有极为重要的美学功能。
在《古都》里,作者就是独具匠心地将故事情节的展开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完美地同写古都的风物时令结合在一起,用写景来牵动情节,同时又把景物人格化,借景来塑造人物,表现感情,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
小说以四季为框架,把千重子和苗子的悲欢离合放在同一平面上,让故事情节随着四季景物的变化有秩序地深入展开:春天的苦苦思念,夏天的不期而遇,深秋的北山相约,隆冬的不告而别。小说首章“春花”,是从千重子家院中老枫树上上下两株紫花地丁开花的印象情景开始的。千重子发现这两株花之后,不无感叹:“上边和下边的紫花地丁彼此会不会相识、会不会相认呢?”作者在这里还没有道明千重子感慨的含意,只是说明千重子为这两株紫花地丁的生命所感动,引起了“无限孤寂”的感伤情绪。在“北山杉”一章再现这两株紫花地丁时,作者又借千重子的嘴说出:“我也象生长在枫树干小洞里的紫花地丁”,来象征千重子的命运,并将她对紫花地丁生命的惆怅色彩,渗透到这个人物的心间。她发出的感慨,不仅起到了故事情节铺展和人物感情流动的诱发作用,而且构成苗子登场后的微妙心理伏线。到了“祗园节”一章再一次出现同一物象时,千重子凝望着它,噙着眼泪遐思:“上下两株小小的紫花地丁大概是千重子和苗子的的象征吧?”“以前不曾见面而今晚是不是已经相认了呢?”这才点明上下两株紫花地丁的隐喻意义。这对孪生姐妹经过春夏的几次欢聚,到了深秋即将悲离,在“深秋的姐妹”一章最后一次(第四次)出现这两株紫花地丁时,它们的叶子“都已经开始枯黄了。”这简洁的一笔,浓重地渲染了千重子与苗子即将悲离的感伤情调和沉痛心绪。可以说,此时的紫花地丁已经不单纯是物象的存在,而是与人的心灵、精神以及人的命运、性格相通了。景物变化和位移的过程,就是故事情节展开的过程和人物情感心理的流程,人物性格的发展从忧到喜,又由喜而悲,完全溶进自然,和景物一体化了,从而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三、景物与人物 把自然景物的美和人物形象的美溶为一体,借助自然美来表现女性美,这在“川端文学”中是相当普遍的。川端曾说:女人比男人美,是永恒的基本的主题。所以“川端文学”除几部描写自家身世的作品外,无不以女性为主人公。而运用各种手法,表现女性的形体美和情感美,可以说是“川端文学”的一贯追求。“川端文学”展现女性之美,很少正面直接描绘,而多是结合自然风物之美——或对比、或比拟、或烘托。因而,自然景物在“川端文学”中常作为女性美的象征性、暗示性表述而出现。此外,作者不仅以自己对景物美的想象去补充人物之美,而且还充分启动读者的想象自由驰骋,来增强人物的美感度。
《雪国》中,借助自然景色,对驹子的外在美可以说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工笔画式的描绘。
写她的肤色美:“在她的脖颈上淡淡地映上一抹杉林的暗绿。”(暗示)“她没有施白粉,……娇嫩得好象新剥开的百合花或是洋葱头的球根。”(比喻)“月光照在她那艺妓特有的肌肤上,发出贝壳一般的光泽。”(衬托)
写她的身段美:“从刚才她站在杉树背后喊他之后,他感到这个女子的倩影是多么的袅娜多姿。”(暗示)
写她的容貌美:“盈盈皓月,深深地射了进来,明亮得连驹子耳朵的凹凸线条都清晰地浮现出来。”(暗示)
写她的服饰美:“她提着衣襟往前跑,每次挥动臂膀,红色的下摆时而露出,时而又藏起来,在洒满星光的雪地上,显得更加殷红了。”(对比)
用自然景物之美来象喻人物内在的心灵美,更是川端的拿手好戏。如果说《古都》中的紫花地丁是千重子的象征,那北山杉又何尝不是苗子的写照呢?
“北山的杉林层层叠叠,漫空笼翠,宛如云层一般。山上还有一行赤杉,它的树干纤细,线条清晰,整座山林象一个乐章,送来了悠长的林声……”苗子就生长、劳动在这里。她仿佛是北山杉的精英,也象北山杉一样挺拔、秀丽、生机勃勃、温良纯朴。而她对不曾见面的孪生姐姐的思念和关切之情,屡屡难拂,浓郁得一点也不亚于北山杉的“漫空笼翠”。千重子在祗园节听到的“悠扬的杉林的音乐”就是苗子对千重子的幽幽挂念。及至后来姐妹相认后,在杉树下躲雨,这一象喻意义就更明确了。作者在写了苗子扑在姐姐身上为其挡雨之后,有段写景:
“的确,北山杉树的枝桠一直修整到树梢。在千重子看来,呈园形留在树梢上的叶子,就象是一朵朵雅淡的冬天的绿花。”
无疑,作者是在喻示千重子和苗子的手足之情犹如杉树一样优雅、纤细和微妙,更以杉树的坚挺、秀丽,象征苗子那纯良、正直的心灵美。
四、景与情 毫无疑问,日本人的审美是主情的,而且是“情借景生”。不过,笔者以为还应再加上一条,这就是“情因景达”。这不仅包含有“一切景语皆情语”的含义,而且,还有着“唯景才足以情达”的含义。把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瞬息万变的大自然作为主体世界外化和对象化的自由天地,人物情感世界的复杂、微妙,借自然风物的丰富、纤细得以尽现;而通过心物合致、情景交融的意象和境界所生成的象外之象、情外之韵,来实现对感情的加深和远延——日本文学对“余情幽玄”的追求,不能不说是日本美学对世界的一种贡献。
“川端文学”很少直抒感情,而多是移情于景,以景述情。此类例子真是不胜枚举。这里,我们仅以《伊豆的舞女》中对“雨”的描绘为例,进行说明。
作品开头就写“骤雨白亮亮地罩在茂密的松林上,以迅猛之势从山脚下向我追赶过来”,仿佛连雨点也在催促着“我”去追赶舞女。雨点把我和舞女联结,表现了“我”要去会见舞女的急如火焚的心境。夜雨听鼓声,以缠绵的雨引起“我”对舞女的无限情思。例如,在雨夜中我听见鼓声,知道舞女还在宴席上,心胸就豁然开朗,鼓声一息,“我”就好象要穿过黑暗看透安静意味着什么,心烦意乱起来,生怕今夜舞女会被人玷污。作者在这里充分运用夜雨、鼓声来烘托“我”的内心感情变化,使“我”尽情地从心灵深处发出咏叹,表示了“我”对舞女的关注之深沉,爱恋之真切。作者之所以选择“雨”来作为核心物象,是因为雨是连绵不断,与缠绵的情思非常和谐;雨是透明晶亮,象征“我”和舞女纯洁的心、无瑕的友情。更因为雨与泪相连,泪雨如注,易于抒发悲哀之情。我和舞女邂逅的全过程,本来就很少语言,以语言情,更是少见,而是最大限度地把人物的感情心绪,对象化、物化,完全是情借景生,情因景达。
“川端文学”非常重视创制意象,追求余情。如果说,意境的创制还比较普遍的话,那么,通过象外之象,情外之韵,来增加作品的余情美,则更加体现了“川端文学”自身的特点。叶渭渠在《川端康成评传》中指出:川端康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寓情于景或触景生情,而是含有更高层次的意味,即他将人的思想感情、人的精神注入自然风物之中,达到变我为物、变物为我、物我一体的境界。”〔14〕此时,不管是“我”还是“物”都超越了自身存在,而成为一种象外之象,情外之韵,也就是说,成了一种既深且远的、浸润人心的余情”。
如《古都》中,对以紫花地丁和北山杉为核心的意象创制,其艺术效果,让人觉得:与其说,紫花地丁和北山杉分别是千重子和苗子性格的象征,还不如说它们是人们内心情绪在自然界引起的一种感应。它们在作品中多次出现,不仅联结故事情节、暗示人物命运,而且诱发人物的情感,甚至让人觉得自然景物仿佛是在主动呼唤人的情感一般。自然随着情感流动,情感随着自然变化,情景不仅氤氲一体,而且各失其“身”——情已不再是原情,景已不再是原景,而只是成为密集浓郁的艺术氛围的元素,淹没于无限深邃的意象之中。这些意象的外延,不仅加深了意象的内涵,而且延伸了情感表现的空间,在读者心中掀起了起起伏伏的情感的波纹,这些情感的余波荡漾开去,就象空谷回音,久久不能平息,极大地催生着余情幽玄之美。
五、景物与心理刻划 在人类意识的海洋里,心理活动是属于深层次的,很难显山露水。而且,现代心理学又揭示出人类深层心理流动的无意识性、非理性性。唯其如此,心理现实主义的直接展示方法,就显得力不从心。而借助变幻无穷、本身具有不确定性的自然风物,运用隐喻、暗示、象征、联想等手法,对人物的心理活动给予由表及里的立体展示,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川端文学”中的主要人物形象,都有复杂而细腻的心理活动,因而“以景写心”对川端来说,既顺理成章,也得心应手。在“川端文学”中,景物的述描,往往成为人物复杂心理活动的象征和暗示。用景的移动来启动意识的流动,又用意识的流动来衔接情节。在《雪国》中,岛村这个人物几乎是依靠心理描写的手段来刻划的,而心理描写又多借景物展示,因此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景物描写最后完成了对岛村形象的刻划。而且,正是通过景物所展示的心理,我们才得以窥到人物及作者的深层精神结构。
作品开首名句:“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这寥寥数语,既点出主人公岛村已经到达雪国,又写出了雪国的自然景象;接着又写出了远方“那边的白雪早已被黑暗吞噬了”的自然状态,马上给人一种冷寂、凄怆的感觉,不仅是岛村事隔一年又前往探望驹子时,那种急于见到驹子又担心驹子另有新欢的局促不安心理的暗示,也是驹子不祥未来的象征,因而对情节的发展也是个有力的铺垫。
接着写到映在车窗玻璃上的白雪、山火和叶子映像的重合叠印,暗示了自己对叶子惊人美的渴慕心理,但又无缘亲近。于是自然而然就联想到了委身于自己的驹子那美丽的容颜在镜中和早晨雪景的叠印,并启动其意识向首次来雪国和驹子幽会交欢的情节流动。岛村意识流动的此次转换,既衔接了情节,且蕴藏着下列心理活动:叶子尽管美艳无比,但却无缘接近,于是只好凭借回忆与驹子交欢时的情景来聊以自慰;通过这种回忆,自己对驹子“肌肤的渴念”更强了,而且仿佛也给自己那种感伤虚幻的情怀找到了依托,因而心理上也呈现出一种喜悦亢奋的状态。作品接下来有一段景物描写,就是岛村这种心态的写照:
“从陡削的山腰到山顶一带,遍地盛开着芭茅,白花花地一片银色,好象倾泻在山上的秋阳一般。啊!岛村不由得动了感情。”
但是,在到了目的地、受验了驹子的身心之爱后,他那种感物伤时的虚幻情怀又冒出来了——从映在化妆镜中白花花的雪景里,看见了驹子红彤彤的脸,又勾起了他对映在车窗玻璃上的景色和叶子的回忆。而这面镜子既是岛村的绘景,也是其虚构的虚幻美的象征。因而,这第二次的意识流动则暗示了下列深层心理:岛村对驹子既依恋又背离,对叶子则是既感到渴念又感到虚幻。岛村本来想把同驹子的男欢女爱当做自己虚幻情怀的一种实实在在的依托,可是一旦受验,在现实中又感到无所依附,只有转向叶子。然而叶子所象征的“美”,必定存在于虚构的幻想世界,是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小说最后还以银河的渺远空浮、叶子死时的飘飘欲坠,对这一深层意识进行暗示。
这就象生命对永恒的追求、人类对终极的探寻一样,同样是只能趋近而不能到达。有人指出:“在川端笔下,驹子和叶子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代表‘肉’、一个代表‘灵’。”〔15〕换句话说,一个代表着生命的有限,一个象征着精神的永恒。岛村这个人物形象就是作者深层精神结构中这两个方面相互冲突的产物。作品在灵与肉的冲突中对这个人物所作的心灵透视,实际上就是作者自身就这一问题进行精神探索的艺术写照。
日本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南博在其《日本人的心理》一书中说:人类生活中“只有肉体是真实的”,唯独通过肉体“才能感到自己活着”——这一心理普存于日本人的内心。〔16〕这说明了日本人生命追求的一个极端;肉欲、好色。岛村对驹子“肌肤的渴念”就包含有这个因素。但是,“日本人又特别地注重自我的心理平衡和更加纯粹的精神渴求。”〔17〕这则代表了日本人生命追求的另一个极端:彼岸和终极。肉欲的实现,只是生命对瞬间“实在”和沉醉的体验,它不仅不会替代生命本体对无限精神和永恒美的追求,而且还会使生命自身对“灵界”的向往更加强烈,更加难以遏制。两相比较,那生命的短暂“实在”,其时也就如同梦境一般无足轻重了:“尽管远离了驹子,岛村还不时惦念着她,可一旦来到她身边,也许是完全放下了心,或是与她肉体过份亲近的缘故,总是觉得对肌肤的依恋和对山峦的憧憬这种相思之情,如同一个梦境。”(《雪国》)
作品中,岛村总是形容叶子的声音美得“空灵”,是纯粹的声音。说她映在车窗玻璃上的倩影,是来自“修远的世界”,是“造化的默示”,这其实就是把叶子当作了纯粹精神和永恒美的象征了。然而,灵的境界、无限精神,必定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而,呈现在岛村的意识中,只能是既无法遏制自己对叶子的强烈渴念,又感到无边的徒劳和虚幻。
很明显,岛村的精神探求,在心理根底是以生命对无限的追求、精神对终极的探索为内驱的;而他所表现出来的感伤和虚幻很大程度上,则是源于他对灵与肉不能统一的无奈,源于他对无限和有限不能弥合的喟叹,是一种灵魂的深度痛苦。作品也曾就此点做过暗示——岛村说他很清楚驹子为何痛苦,而驹子恐怕一点也不理解他的痛苦。〔18〕可以这样说,驹子的痛苦是生活的、际遇的;而岛村的痛苦是生命的、本体的。川端曾对芥川龙之介的一句话颇有同感:我深深感到我们人类‘为生活而生活’的可悲性。〔19〕由此可以反证,岛村的虚无悲哀,就是川端所体验到的生命悲剧意识的艺术表现。人类生命中的悲剧意识,不仅引出了人对自己孤独命运的体认,还引出了对这种命运的抗议以及试图超越它的种种努力。岛村这一形象的意义,不仅在于给我们展示了这一灵魂的深度痛苦,而且还在于作者通过其心理流程,暗示人们应持有对这种痛苦的自觉。叶渭渠在《川端康成评传》中指出:“川端的虚无颓废的倾向,带有一定的自觉性。”“是含有某种反抗意味的。”〔20〕为了超越这种痛苦而进行的努力,对岛村来说,就是作品中他神游物外的美的幻想;对川端来说,就是其艺术创造本身——通过恒远的艺术美,升华一切、超越一切,这就是川端精神探求的最后归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归结“川端文学”自然美营构的总规律:物化于情,情化于物;哀中写景,景中抒哀;交互溶铸,双向建构。有人指出:“川端文学”是“从精神和技法两个方面来具现日本文学的特质”的。〔21〕凭借本文上面的大量分析,我们既可以把其“精神”概括为“物哀”,也可以把其技法概括为“物哀”。不是吗?就其“技法”表现来说,“川端文学”以物人感应为手段,以物人感应为目的。紧紧抓住物的气象和人的心态之间的相互流动,使客观与主观交相融溶而又变化无穷,渗透到具体作品中,就表现为明丽而隐没、朦胧而清晰、纤细而空灵、幻美而哀婉的丰富多样的审美品格。就其“精神”内质来说,“川端文学”以自然感悟为起点,以主客契合为中介,以超越自然为归点。这中间包含着敬爱自然的文化底蕴、生命悲哀的哲学体悟、生命救助的美学追求;投射到具体作品中,就相应地显现为:亲和自然的季节主题、悲叹人生的哀伤基调、超然物外的幻美追求。
注释:
〔1〕〔6〕〔14〕〔20〕〔21〕转引自叶渭渠:《川端康成评传》186、112、173、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2〕〔4〕〔8〕〔10〕〔19〕《川端康成散文选》247、282、156、274、153、7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
〔3〕林少华:《谷崎笔下的女性》,《暨南学报》1989年,第4期。
〔5〕柳田圣山:《禅与日本文化》(中译本)63页, 译林出版社,1991年。
〔7〕〔16〕南博:《日本人的心理》(中译本)47、121页,文汇出版社,1991年。
〔9〕参见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33页, 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4年。
〔17〕王确:《主情的审美世界》,《外国问题研究》1992年,第4期。
〔11〕今道友信:《东方的美学》(中译本)133页, 三联书店,1991年。
〔12〕紫式部:《源氏物语》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13〕〔15〕见《雪国·千鹤·古都》译序,漓江出版社,1985年。
〔18〕《雪国》,参见《川端康成小说选》305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