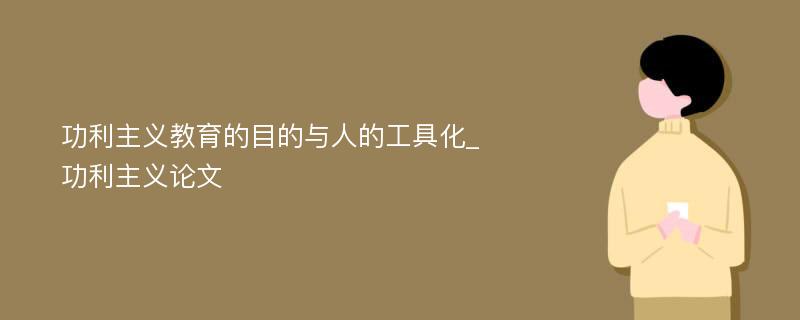
功利主义教育目的与人的工具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的论文,与人论文,功利论文,工具论文,主义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功利主义教育目的产生的深刻根源
“上帝死了!”尼采在《扎拉图士特拉如是说》中的宣告,无疑给人类世界投下一个重磅炸弹,它既标志着绝对价值的死亡,也意味着人们对永恒真理及存在的信仰成为不可能。“没什么是真的,一切都是允许的”[1]。于是,从文艺复兴以来经过启蒙运动再到近代科技理性的张扬,其间所发生的社会变革、知识制度、技术实践都预示着现代性价值的位移。在没有上帝的时代,“人通过其感觉、感情以及通过其整个存在所认识的世界现在是唯一的世界”[1]——唯一真实的世界,由此人类把目光从天上转到地下,试图为自己建立一个新的精神家园,建立一个新的普遍的价值标准。然而,“没什么是真的,一切都是允许的”的人义论在为人类带来无限创造性与可能性的同时,也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价值多元是正当的,个人可以拥有自己的真理和价值,只要不有害于他人。由此,就出现了众多迥然相异甚至截然对立的价值标准,进而引致不可避免的价值冲突:在某人看来是至高的善,对另一个人来说却可能就是恶;宣扬至善与卓越,却可能被他人认为是行价值专制。于是到处充满了怀疑与否定,却没有一个明显的、使人信服的优于其他的选择,人类终究逃脱不了上帝死后的“灾难”。
功利主义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严格说来,时代造就了功利主义,同时功利主义又推动了时代的发展。可以说,它的出现似乎解决了上述难题,因为它把正当善恶与否放置于功利的面前接受最终的裁定。这既符合人类非理性存在的一面,又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对都能认可的标准。正如麦金太尔所说“功利主义之所以能支配我们的原因是它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和道德问题上的唯一的公共标准”。如此,功利主义作为一种伦理思想在人类的生活中开始肆意渗透。尤其是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所造就的辉煌的物质成就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身体快感,使得人们愈加相信功利主义的合理性,从而引致它在社会各个领域中更加肆无忌惮,这必定给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带来深刻的影响,使得启蒙之后的世俗化的教育更是远离了大全式的终极价值,取而代之的是以功利主义为目的的教育,教育本身发生了异化。
二、功利主义教育目的内涵释义
功利主义教育目的就是以功利主义为教育的主导价值取向,在其引导下,教育过分追求功效和利益,进而教育被国家和个人当作追逐利益的工具,具言之,它有3层意涵:
第一,以功利主义为目的的教育,意味着教育实现的价值不在教育之中,而在教育之外。功利主义主张效果论,即一个行为是否正当,标准在于其带来的效果——给人带来快乐的结果,而快乐是行动的终极目的,快乐本身具有内在价值,是唯一的善。功利主义把快乐和痛苦等同于善恶,实则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经过修改的普遍标准。“意向,正和别的东西一样;其好坏悉依效果为准。依效果之足以增进或减低社会之幸福为准。一人之意向,可依两点来讨论:根据它,一是对自己幸福的影响;二是对他人幸福的影响。总此二者以观,或随便据任何一方面来看,它一方面可称为善,而在另一方面可称为恶,或在恶的情形下,可称为极恶的”[2]。所以教育目的一旦功利化,快乐(外在于教育价值本身的利益)成为教育的终极目标,教育只为其效果而存在,并且导向外在的快乐与利益,而对于教育实践中很多内在价值如知识、德性等被忽视。教育只是一味地追求有利于学生利益、适应于经济需求以最终能满足人的欲望的目的。教育自身的价值只有依附于外在于它的目的才能得以体现。教育再也不为一种大全式的终极价值而存在,而沦落为实现个人快乐、适应社会需求的手段。教育行为正当与否,最终建立在人的感官欲望的满足及其程度之上,最后落在个人的偏好之上。教育最终成为欲望与个人偏好的奴隶。
第二,功利主义的教育目的是以教育后果实现的程度为标准来评价教育,即要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不仅主张效果论,而且以行为结果的满足程度是否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作为衡量行为的标准,行为本身只是外在于它的目的的实现手段。这就意味着一个行为只要能带来好的结果,就是合乎道德的行为,而所谓好的结果就是这个行为能给人带来快乐,快乐生产得越多,这个行为就越是有价值,而不管实现此效果的手段是否正当。这就极易给集权主义者带来借口。比如法西斯主义、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如此这般,功利主义教育目的就意味着教育评价的标准并非依据教育自身的内在价值,而是以教育结果所带来的经济和物质利益的多寡来作为评价标准。这种标准只是执着于幸福、利益的数量的最大化,而忽视了甚至牺牲了少部分人或者弱势群体的利益。因为功利主义教育只是强调教育最大效果的获取而忽视了达成这一效果的过程以及教育的最终的目的的反思和审视。教育是为人的,并且是为了每一个人的教育,教育由此不能以效率来遮蔽公正,牺牲每一人受教育的权利。否则,它所带来的是教育的不正义,现今的精英主义教育、我国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等都与此脱不了干系。
第三,功利主义教育目的把一些大而空的概念来作为衡量教育的标准。麦金太尔说,“功利主义的‘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以多种面貌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福利’、‘公众利益’、‘集体利益’”,所有这些词语都暗示着一个公共的、社会所接受的行为标准,这个标准是外在于行为本身的。而功利主义的教育目的则用这些口号来消除其个人主义的嫌疑,并以这样的冠冕堂皇的口号来博得大众的认可。以这些大而空的口号来作为衡量教育的标准,意味着社会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这样做的正当理由是什么?这与功利主义主张的个人利益难道不矛盾的吗?一旦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起冲突(事实上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标榜以为了学生的利益为准的教育该做何想?大抵只能以最大幸福原则来做托词,自己的幸福就是他人的幸福,反之亦是。可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而教育打出这种口号,只是起到损害受教育者利益的作用。
三、功利主义教育目的在我国教育中造成的直接实践后果——人的工具化
在长达几十年的、畸形的“教育政治化”后,中国教育界完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唯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工具主义和经济主义盛行,“数量”、“效益”、“效率”成为事实上支配我国教育所有方面的主导价值观。功利主义教育目的的绝对胜利对我国的教育实践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其最直接、最有危害的后果是造成了人的工具化。
功利主义的教育目的观预先给教育活动提供了一个明确表述的有待追求的目的——功利,同时也提供了实现受鼓励的欲望和抑制或改变方向的欲望的手段。教育本是要引导人追求美好生活(这种美好绝不止于感官的幸福和欲望满足之后产生的快感),然而由于教育自身的媚俗和随波逐流,在现代大工业条件下,它日益成为经济的附庸,成为实利下贱的使女,成为追逐欲望的工具。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一种经济、社会需求,教育由此变成了一种适应性的教育,一种引导人片面追求利益(金钱、权力等)的教育,在其中,我们很难看到对人的整体精神培养的迫切性。这样就必然导致把其所直接指向的求教者看作一种达到社会经济利益目的的手段,人由此成为了计算和追逐欲望的工具,从而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和品行,丧失了人的尊严。人也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被割裂为日渐远离自身精神性的客观物的存在。他进入了机器大工业时代新的奴役状态,被降格为工具性职能的存在。人正如现代体制庞大机器上微不足道的齿轮和螺丝钉,只有在机器(社会)运转时,作为其上的一个零件才发挥功能和作用,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延伸和扩大自己器官的功能,以在追求利益中发挥最大的功效。
人一旦被工具化,教育也就只有在他自身以外即他所生产的产品满足社会的需求之中来衡量他的价值。人的价值隶属于机器工具,人不再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而是实现自身欲望(自身欲望最终也是为外在的经济、社会需求服务)的手段;人也不再是康德意义上的“人,一般来说,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自在的作为目的而实存着,他不单纯是这个或那个意志所随意使用的工具。在他的一切行为中,不论对于自己还是对其他有理性的东西,任何时候都必须被当作目的”[2]的人。我们的学校教育过分注重人的物质层次的发展,严重偏向于实用的知识和技术的传授和培训,忽视了人之为人的精神性发展,“像填鸭般地用那些诸如形而下之‘器’的东西,塞满学生的头脑,而对本真存在之‘道’却一再失落而不顾,这无疑阻碍了学生通向自由精神之通衢”[3]。教育自身的媚俗使得教育追求的是社会的认可,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学校教育对升学率以及造就所谓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的追求,学校课程由此也偏向那些能迅速带来实利的经济类课程,而忽视陶冶人性的艺术类课程。功利主义教育目的指导下的教育导致的人的工具化,完全割裂了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精神与肉体的统一性。
同时更为可怕的是求教者日益接受并内化了这种目的观。在这种教育引导下,学生把追求自身利益当作唯一重要的事,他们接受教育就是为了个人的谋生和为未来做准备,以获得更多更好的实际利益。在他们的生命中体验的就是追求新奇刺激和庸庸碌碌的浑噩的享乐,他们的存在以可见物和感官欲望的满足为中心。学生考虑的是他的职能如何能适应经济和社会的需求,他们认为学习知识的主要目的是将其运用到社会交换中,把金钱、权力、好工作等作为其追求的目标,不再关注自身的生活理念问题。当前,大学生逃课忙碌于不断的考级、拿琳琅满目的证书(CET-4、CET-6、计算机等级考试、公务员考试、司法考试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增加就业的砝码,修习的课程是能为他们的将来带来幸福的课程,而把德性的追求和反思、批判性的精神培养抛诸脑后。
功利主义教育目的之下的道德被降到身体感觉的基础上,人的道德性在于日常的享乐和感觉的丰富性,道德演变成在获取实存享乐的物质资料中互不侵犯的生存原则,德性成为为个体欲望的满足服务的实用性价值,成为可算度的具体价值,品性与道德已经不重要了。或者说,学生接受道德教育,不是为了增长自己的品质,不是为了追求一种真正的价值,走向绝对的善,而是因为意识到道德是其获取利益、获得幸福的有效途径,至于行为本身的道德性已经不重要了,学生自己的品格也无足轻重了,只要所采取的行为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和利益就是正当的。学生习得了道德内容或所谓的“道德理解力”(当然更有甚者是连这点也达不到的),却丢失了道德责任感,失去从善的意识,即使是行善也要算计着这个行动是否对自己有利,正如怀特教授在《再论教育目的》中所说,具备道德理解力的人如果他很精明,则他可能“通过了解真正具有道德感的人们的动机以及他们对道德的看法,他可以借此来操纵他们,为自己谋取利益”[4]。
另外,学生只是一味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利益,就忽视了自己批判性精神的培养,日益成为尼采所谓的“最后的人”(last man)。功利主义教育目的之下,“饲养型”学校要么成为百货公司,要么成为劳动力工厂,向社会兜售各类商品(知识、片面适合社会经济需求的人才),学生被放在教育的生产流程线中进行加工制作,其自主精神和创造力被剥夺,久而久之,他们的惰性和依赖性暴露无遗,他们成为没有批判能力的劳动力大军中的一员,不再对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层面的东西予以关注,只是习惯性地接受学校教育单向传递的工业社会特定的价值观,他们只被要求学会某专业领域的知识、技能,并且大多数学生只是被当成普通的劳动力来培训,社会、学校也不需要其对之进行反省,只是强调服从和追随,并且用考试这一有效的现代教育技术来控制学生的自主性和反思思维的发展。而反省则意味着可能孕育不满情绪,破坏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也是“教育体系中一些当权者为何特别重视学生服从老师的绝对权威以及学校组织中那些权威机构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对注人算术和外语等科目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特别偏爱的原因”[3]。
四、走向人的教育
功利主义教育目的使得教育背离了本来的真实使命,使学生朝着人格分裂的方向发展。教育如果只关注学生实用生存的知识、技能,那么无论物质生活多么多彩纷呈、吸引人的注意力,仍然无法掩盖丰盛物质背后精神的空虚和迷茫,而精神性恰恰是人之为人的那种东西。人作为一个有限的存在,易被自身和外在的欲望所束缚,但是人更重要的就是他是理性的存在,终有一天会接触到无限的存在——精神生活,即使人们并未全部意识到,但总有从“洞穴”中看到阳光并努力走出“洞穴”的人。人们就会发问,我们究竟为什么活着?我们究竟为什么接受教育?我们究竟要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教育究竟为了什么?
人是一种整体性存在。人之为人,不仅在于其是一种客观存在(其自然结构),更甚者是一种精神存在。正如康德所谓的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除了要受其欲望或外在冲动的规约外,更有意义的是他的理性存在,可以摆脱自身的感官欲望的束缚,实现一种超越性,精神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包括“‘理性’这个概念,另外,除了‘观念思维’外,它还包括对原始现象或本质内容的特定‘直观’;同时它还包括诸如善良、爱、悔恨、敬畏、心灵的惊奇、极乐、绝望和自由抉择等意志和情感活动”[5]。所以精神包括了人之为人的所有方面。
人之为人就在于其具有的精神性是超越自身、超越世界、不受动物式欲求和环境的束缚,具有自主性,能够进行自我创造。而教育根本上作为一种使人向善、引导人过一种良善生活(good life)的活动,在现代大工业时代的神圣使命就是回归本真的教育,“引出”人之精神,引导人追求卓越的精神品质,使其超越自身和世界,实现个人真正的成长(精神成长),战胜功利主义教育目的引导的异化的教育。在此使命下,教育不是仅仅要关心学生的物质层次的提高(散文式生活),更为根本的是要关注学生的精神世界(诗的生活)之成长,关心学生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教育应该给予怎样的引导?毕竟,“教育非它,乃是心灵转向”,柏拉图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