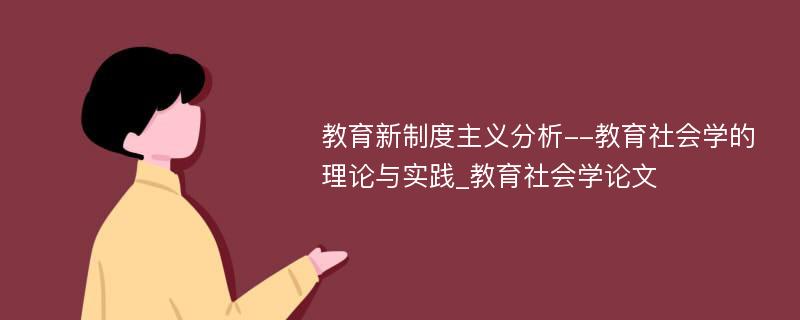
教育的新制度主义分析———种教育社会学理论和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主义论文,制度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03)06-0028-07
本文不是一篇关于新制度主义理论和研究的文献综述。作为近年来对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带来巨大冲击的理论思潮,新制度主义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术领域所呈现的面目是不同的。这不仅是指在这些不同的学术领域中,新制度主义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各不相同,而且就新制度主义理论中最基础的概念“制度”本身在这三个不同的学术领域里的内涵和外延也是不同的(注:W.R.Scott,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Inc.2001.p1-19.),此外新制度主义作为一个新的理论方向与既有的行动理论以及社会构建理论之间的关系也是互有渗透的(注:Paul J.DiMaggio & Walter W.Powell,Introduction Chapter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Analysis,Paul J.Dimaggio & Walter W.Powell(ed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p15-27.),因而要在一篇文章中厘清这些错综复杂的学术逻辑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本文也不是一篇关于教育社会学学科领域中新制度主义理论和研究的文献综述。只要翻开国际上新近出版的几本教育社会学专著就不难看出,新制度主义分析无论是作为理论还是实践,在当前的西方教育社会学领域都是边缘的(注:例如1995年出版、1998年再版的Sociology of Education:emerging perspectives(C.A.Torres&T.R.Mitchell eds.Albany:S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98),又如Sociology of Education Today(J.Demaire ed.Basingstoke:Palgrave,2001)。事实上,关于新制度主义理论在西方教育社会学学科中的边缘位置,连该理论的创始人J.W.Meyer也不曾讳言,在与笔者的通信中他曾对此做过明确的判断和分析.)。这部分是因为学术市场的问题(对此后文将加以说明),部分则是因为有些社会学家对其术语和分析视角一向持有疑义。这也是笔者在一次会议上所亲身经历的,当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J.W.Meyer做大会主题发言时,有与会学者认为他不过是把一套旧的社会学概念换上新的说法。本文的目的在于厘清以下三个问题:
(1)作为社会学分支的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是教育的制度分析;
(2)但旧的教育制度分析无论是20世纪前半叶的旧教育社会学还是60、70年代突然兴起并发展至鼎盛的新教育社会学都有其局限性。前者将制度分析的关注点放在了教育制度外在功能的分析上,从而忽略了对教育制度的内生特征的分析;而60、70年代兴盛的新教育社会学虽然加强了对教育制度的内生特征的分析(如不平等性),却是通过引入一个横向社会分析体系(即社会阶层)来实施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具有了社会体边界的局限性。因为,不是每个社会体都是阶层化结构的,如中国在很长时期里就是一个身份化结构的社会。这种边界局限性不仅使这种旧的教育制度分析的研究成果很难普遍化,更重要的是它无法解释跨越不同社会体之间的制度选择和制度传播的现象,这种理论上的不足在越来越全球化的整体人类文化背景下就更暴露出其严重的缺陷。
(3)与教育的旧制度分析建构在一个横向的社会体系上不同,新制度主义为教育分析带来了一个纵向延伸的分析视角,即规范—组织—制度(尤其是深层次的文化认知构建)。从对教育活动中规范体系的分析到对其组织形式—学校—的研究,再到教育制度构建的深层次剖析,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揭示一种内生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不同社会体之间发生的教育制度的迁移和传播,以及在各种制度环境交互作用下出现的制度创新。一言以蔽之,新制度主义的教育分析可以突破旧制度主义分析的边界局限性。
一、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是“制度分析”
“制度”和“制度分析”概念的提出源自现代社会学的先驱迪尔凯姆(Durkheim)。(注:Paul J.DiMaggio & Walter W.Powell,Introduction Chapter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Paul J.DiMaggio & Walter W.Powell(ed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p1.)自然科学发现物质的最基本构成是分子和原子,并通过经验性手段得到验证,由此又导致了技术进步,并大大提升人类基本的生存状态,迪尔凯姆由此得到启发,产生了要依此模式构建一门“社会科学”的强烈愿望,以解决当时因社会急剧变迁而产生的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而发现社会的最基本构成和如何用经验性的方式来验证其存在成为他思考的两个基本点(注:迪尔凯姆(Durkheim)思考的最终结果便成为社会学学科得以建立的奠基之作《社会学研究方法》(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为此,他提出了“社会性事实”(social facts)的概念,从而突破了传统哲学中关于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的两分法,将社会学从其哲学母体中分离了出来。迪尔凯姆指出,人不仅是认识的主体也可以是认识的客体,人的价值观和情感不仅属于精神的范畴,也可以视为一种客观的实在;因此社会不是个体的集合,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实体(societal body),它有基本的结构,此结构先于个体的存在并对个体的行为产生约束,社会体因此具有秩序。迪尔凯姆认为社会体结构的基本构成便是“规范”,即为共同价值观所支持并用以指导个体行为的准则,而“规范”在某个领域的集结和体系化便是“制度”。至此,迪尔凯姆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找到了社会的基本构成,它不是过去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宗教等社会领域的划分,正如自然科学不认为物质世界的基本构成是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一样。迪尔凯姆将“制度”定义为社会的基本构成,社会学因此而被定义为“制度的科学”。为了经验性地验证“制度”的存在,他进而提出了“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注:迪尔凯姆所倡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曾被建构为社会科学的一种主流研究范式,但在20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以现象学哲学论为基础的定性研究范式开始了对“实证主义”范式的批判、纠正和补充.),并身体力行。值得指出的是,不久以后,很多文化人类学者将迪尔凯姆的“制度”概念以及“制度分析”的视角,运用于对部落社会的实地研究并得到验证,尤其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这无疑进一步加强了制度主义的学术生命力。
由于迪尔凯姆将规范/制度视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并认为支撑整个社会规范体系的是共同价值观(common value),考察共同价值观的构建和维系便成为他学术兴趣(研究社会秩序)的一部分。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迪尔凯姆对道德教育特别关注,因为在他看来正是社会道德教育体系承担着社会共同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体系的构建和延续的功能。循此推论,他进一步得出人类整个教育制度就是一个宏大的个体社会化体系,不仅社会共同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体系,而且还包括共同的符号、情感乃至经验,都需要并且事实上也是通过教育体系向社会新生代个体传承和延续的。(注:迪尔凯姆的主要教育社会学著作有《教育与社会》(1922)和《道德教育》(1925).)虽然迪尔凯姆一生都没能获得社会学讲座教授的头衔,对其职业生涯不能不说是巨大的挫折,但作为教育学讲座教授,他的教育理论不再从个体的角度来考察教育的目的、内容、过程和方法,早已远远超出传统教育学的知识框架。而究其本质来说,迪尔凯姆的教育社会化理论就是一种“制度分析”的结果,并因此开创了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先河。虽然教育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经历了旧教育社会学和新教育社会学的历史变革,也产生过“规范学科”和“事实学科”之争(注:吴康宁.简论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5),61-64.),但是“制度分析”的视角是使其始终能区别于教育学体系而获得学科独立性的根本原因。下面我们就具体分析“制度分析”是如何在教育社会学研究中被不断拓展和深化的。
二、教育的旧制度主义分析及其局限性
众所周知,教育社会学研究主要包括功能论、冲突论和解释论三种范式。一般认为功能论是与冲突论相对立的一种和谐理论,而解释论则是针对前二者的研究仅停留在宏观机制层面的不足,为了加强对过程的分析(未必一定是微观层面)而作出的理论突破。这三种理论,要么是基本的理论前提和观点对立,要么是分析视角和研究层面各自相殊,虽然彼此有批判和补充的逻辑继承,但似乎很难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这个体系是松散的。但笔者认为,从功能论到冲突论再到解释论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发展,实际上是对迪尔凯姆所倡导的教育“制度主义分析”的不断拓展和深化,因而是成体系的,是一以贯之的。
首先,虽然功能论和冲突论在基本理论前提上存在着对立,如功能论认为共同价值观是普遍社会行为规范和制度的基础,而冲突论则质疑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因此表面上来看冲突论对功能论的颠覆是根本性的。但值得深思的是,冲突论者在对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进行了一番定量和定性的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却是“教育再生产理论”,即肯定了教育对既有社会结构和利益体系的维系和传递功能。这难道不是与功能论的观点如出一辙吗?虽然功能论和冲突论在对该功能实现方式的认识上存在着差异,如功能论认为教育对社会的维系和整合功能是以一种“和谐”的方式“合理”地发生的(即为了社会体的整体利益),而冲突论却认为该功能是以“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注:"Symbolic violence"一词为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Bourdieu)所提出,指一种出现在符号体系中的霸权和控制,在他的分析中主要是社会阶级性的.)和“霸权”(hegemony)等“不合理”的方式进行的,是以牺牲部分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的,但它们对教育的社会维系功能却是一致认可的。从这个意义来说,冲突论实质上是一种“隐性的功能论”。
其次,虽然解释论与前两种理论在分析的层面和视角上存在着不小的差异,比如解释论的分析一般都具体到了社会个体的层面,因而研究视角也相应地从对教育活动体系、知识体系以及社会价值观体系的整体考察转为对具体教育行动(act)和情境(context)的符号意义的剖析。所以毫不奇怪,对同一个社会现象的考察,三种理论所用的术语却各自不同,如在功能论中人们谈论共同价值观,在冲突论中人们则讨论意识形态(即为某个社会群体所共享的价值观体系),而在解释论中人们却挖掘个体对行动意义的诠释,其分析逻辑的不断深入和细化一目了然。但是无论是那个层次或角度的考察,无论其所用的术语如何不同,其理论体系都是一脉相承的,即对教育的“制度分析”。如果说功能论是对教育制度外在功能的一种审视,冲突论在对该功能予以认可的同时着重对其实现的内部机制予以剖析,那么解释论则是在“制度”的最基础(即“规范”)层面探讨教育制度的基本构成。因此,教育社会学从功能论发展至冲突论而后又产生出解释论,实际上是教育制度分析的不断拓展和深入。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教育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不仅不是松散的,而且是有着内在发展理路的。
英国社会学家威利斯(P.Willis)的专著《学习成为领导者:劳动阶层的孩子是怎么成为劳动者的》(注:Willis,Paul E.Learning to Labor: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Farnborough,Eng:Saxon House,1977.)生动地展示了这三种理论范式的一致性。同样是探讨为什么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孩子更可能成为工人这样一个“社会再生产”的问题,威利斯没有从对学校制度的考察入手(如考察双轨制),也没有从对课程体系的剖析着眼(像艾普尔(M.Apple)那样考察霸权(hegemony)与课程体系之间的关系),相反他是从对一群(12名)来自工人家庭背景男孩的日常学校生活进行参与性观察和访谈开始的。他向他们了解他们如何诠释自己日常学校生活中的那些情境和角色,又如何诠释自己每个行动的符号意义以及对不同学校情境所产生的影响。这似乎应该是一个以解释理论为框架的微观层面的经验性研究。但是威利斯在对这些“规范”层面的数据进行系统化和结构化的整理之后,将其定义为“反学校文化”模式,并开始考察该亚文化和工人阶级的底层文化(shopping-floor culture)之间的源生关系,最终形成了对整个教育制度特征和功能的分析,即英国教育制度的不平等性及其对既有社会结构和利益体系的维护。在这个著名的研究中,研究者威利斯不仅自如地往返于微观和宏观的分析层面之间,也游刃有余地穿梭在解释论、冲突论和功能论的理论范式之间。在笔者看来,他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贯穿整个研究始终的是“制度分析”这一条主线。无论是个体行为规范层面数据的收集和解释,还是后来上升为对社会群体意识形态的考察,继而发展为对整个制度性质和功能的分析,威利斯是自下而上地完成了制度分析的整个过程。与绝大多数只在一个角度和层面对教育进行制度分析的学者相比,威利斯的研究展示了一个完整制度分析的可能性和范例;他的研究也证明了教育社会学中这三种不同的理论范式不仅不是割裂和松散的,相反是成体系和一致的。笔者把它这个体系称为教育的“旧制度主义分析”,以区别于“新制度主义分析”。
虽然旧的教育制度的分析在分析的层面上不断得到深化和细化,但仍有其局限性。在迪尔凯姆功能论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旧教育社会学只关注教育制度外在的社会功能而忽略了对教育制度内部特征的分析。后来出现并迅速发展鼎盛的新教育社会学对教育制度内生特征的分析常常是通过引入一个横向社会分析体系—社会阶层—来进行的,如凯迪(keddie)在教育活动的规范层面对课堂知识的考察,布迪厄(Bourdieu)在学校组织层面对法国大学文化机制的分析,艾普尔(M.Apple)在宏观制度层面对课程体系的考察等,无一不是以社会阶层体系作为分析的维度和指标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社会体边界的局限性。这是因为,并不是每个社会体都是阶层化结构的。社会分层只是社会不平等的一种,它是财富、声望和权力以某种方式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进行相对封闭性的层级划分时才产生的。而中国在很长时期里只是一个身份化结构的社会,人们之间虽然存在农村/城市、公职/非公职、干部/非干部以及隶属不同单位的身份差别,但是对这些身份团体而言,有声望的不一定有权力,有权力的不一定有财富(通过权力寻租而获得的财富是非法收入,因而具有不稳定性)、有财富的又不一定有声望,所以社会中虽然存在财富、声望和权力的不平等分配,但不是以相关和相对封闭的方式进行的。(注:Walder,Andrew George.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形式与西方普遍存在的社会分层结构是不同的,因而教育制度在其中所发生的影响和作用也必然会不同。西方主流教育社会学的成果因为深刻地揭示了其教育制度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倾向性以及对该社会分层体系的维系功能,因而非常有影响,不仅公众普遍关注,而且公共机构在进行教育决策时也不得不面对。但是,用一个建立在社会分层体系基础上而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来分析一个具有身份结构特征的社会,其合理性和有效性就很值得怀疑了。这就是为什么1980年代后我们开始引入西方主流教育社会学体系时,常常会遇上概念与本土社会现象、理论和本土社会问题难以匹配的原因所在。更重要的是,西方目前主流的教育制度分析框架,着重对制度内部特征的分析,而忽略了对跨越不同社会体之间的制度选择和制度传播等现象的考察。这种理论不足在越来越全球化的整体人类文化背景下不能不说是个重大的缺陷。尤其是对于教育制度一直处于激烈变革的中国来说,就更是如此。因此,笔者认为应以新制度主义分析的理论视角来加速我国教育社会学体系的本土化进程。
三、教育的新制度主义分析
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兴起了一股制度主义复兴的理论思潮,使得迪尔凯姆主义一时重新变得炙手可热。这次制度主义的卷土重来比起世纪初迪尔凯姆大力倡导“社会学主义”(Sociologism)时影响还要深广得多。那时,迪尔凯姆把社会学定义为“制度的科学”,而将经济学定义为“市场的科学”(注:(美)科斯、诺斯 威廉姆森.制度、契约与组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9.),以此划定社会学的学科边界。可是这次制度主义重临之时,“市场”本身也被定义为一种“制度”。新制度经济学流派提出的交易成本的概念和对此所实施的计算,对一向侧重价格分析的经典经济学体系作了重要的修订和补充,市场、科层制(hierarchy)以及其它众多的混合形式被界定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制度构成,并因此而展开对其效益的考察。比较制度分析于是成为经济研究领域中的新贵,制度的传播和迁移现象也开始为学者所关注。同样的学术兴趣也逐渐出现在政治科学和其它的研究领域中。学术界把这次制度主义的复兴称为“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的莅临。
在教育社会学领域,虽然新制度主义分析的影响和地位目前还只是边缘性的,但它所展现出来的理论视角和学术潜质已经展示出旧制度主义分析所没有的优势,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与旧制度主义相比,新制度主义对“制度”概念的界定更准确、更深入。在旧制度分析中,“制度”被定义为围绕某种社会功能的实现而产生的社会行为规范在某个领域内的集结和体系化。社会学传统的所谓五大社会制度家庭制度、教育制度、宗教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划分便是由此而来。因此,在旧制度主义中“制度”的最基本的构成是“规范”,而“规范”的产生是为了满足某种社会功能实现的需求,这其中的以果证因的逻辑瑕疵显而易见。与旧制度主义相比,“制度”在新制度主义中被界定为“由社会符号、社会活动和物质资源所组成的多层次稳定的社会结构,它包含以下的三大要素:法令规章体系(regulative)、规范体系(normative)和文化认知体系(cultural-cognitive)”。(注:W.R.Scott,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Inc.2001.p49-58.)显然,与把“规范”作为制度的最基本构成相比,新制度主义拓展了制度的涵义,不仅向上拓展了其法令的层面,而且向下拓展了其认知的层面。一方面它把旧制度主义中模棱两可的“规范的集结和体系化”明确地界定为“法令规章体系”,另一方面也界定了制度产生的根本机制是社会的文化认知,即“普遍的符号体系”(collective symbolic system)和“共同意义”(common meaning)的构建。关于新制度主义中“制度”的这三个层面的多维特征参见下表:
当然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者和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者在理解和使用“制度”这一概念时侧重点并不同。比如,经济学家更侧重于“制度”中的法令规章性因素,诺斯(North,1990)就认为制度“完全等同于竞技比赛中的规则,是由正式的成文法规和支持性、补充性的不成文行为准则所构成…如果违反就应受到相应的惩罚。因此制度运作的关键在于查明违法行为的成本和惩罚的严厉性”。而社会学家则更侧重“制度”中的文化—认知因素,甚至认为“行为被重复以及被自我和他人赋予相似意义的过程”就是制度化。值得注意的是,与迪尔凯姆认为制度的基础是“共同价值观”(common value)不同,新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的基础是“共同意义”(common meaning);前者属于道德范畴,而后者属于认知范畴,这是新、旧制度制度主义对“制度”概念理解的根本差别之所在。一言以蔽之,新制度主义中的“制度”概念被界定得更明确、更清晰,而且避免了旧制度主义中以果证因的逻辑瑕疵,因而更严谨,此外它对“制度”产生的深层机制的揭示也使得该定义更深刻。
表1 新制度主义中“制度”构成的三大因素系统
RegulativeNormativeCultural-Cognitive
法令规章 行为规范 文化—认知
命令的基础
法令条文 共同期望 共同的认知框架
服从的基础
权宜之计 社会义务 建立在共同理念上的
不加思索性
发生机制外在强制力内在规范性模仿
逻辑
工具性
得体性
正统性
指标
法律、法规证书与认证流行的概念和行为
和奖惩制度
合法性基础
法律认可 符合道德要为社会文化所理解、
求接受和支持
(来源:W.R.Scott,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2001.p52.)
其二,也是二者差异中最重要的一方面,即由于新、旧制度主义对“制度”概念的界定和理解不同,例如旧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基础属于道德范畴,其本质是社会行为的协调和约束机制,因此除了迪尔凯姆的早期功能论认为它产生于人类共同价值观的积淀外,后来的制度分析主义者都把不同群体的“利益角逐”视为社会行为协调和约束机制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也就不奇怪,为什么教育的旧制度主义分析往往是通过引入一个外在社会指标—社会分层体系—来展开了。因为在西方社会,没有比社会分层体系能提供更好的对“利益角逐”进行分析的框架的了。而在教育的新制度主义分析中,由于认定制度的本质不是道德而是认知范畴,所以无需通过引入外在的指标体系来进行制度分析,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独立性被强调了出来。与旧制度主义学者关注社会结构体系对教育制度的影响相反,新制度主义分析更强调教育制度对社会体系的反作用。新制度主义分析者认为教育制度对整个社会体系扮演着合法化的角色,即教育制度通过对社会知识体系和价值观进行分类和定义,从而界定社会中各个成员的权利义务以及相应的地位和权力,例如现代教育制度是各种专门化人才的提供者和界定者,因而也是“社会精英”的界定者,大量医生、律师、MBA等专门职业的资格授予或认证工作都是由教育制度来承担的;又比如公民教育快速而大量地塑造并传播着民族国家成员的资格,而大众教育为个体提供了一整套关于社会共同文化的理解准则,比如语言和历史,从而为他们构建了一个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现实,等等。总之,现代教育制度对社会体系的影响决不是零散的、片面的,相反是整体的、结构性的。由于它是现代社会机构中人员和各种制度性因素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提供者,所以形成组织结构高度同质性(isomorphism)和社会高度制度化的特征。显然,与旧制度主义分析中把教育制度视为社会结构的被动反应体系相比,如鲍利斯(Bowles)和金緹斯(Gintis)的“对应理论”(correspondence theory),新制度主义分析展现了教育制度的独立性和主动性。
其三,与第二点相关,由于新制度主义分析对教育制度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予以肯定,由此教育制度的形成、维系和变迁也就为新制度主义分析框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一点与旧制度主义很不相同。在教育的旧制度主义分析中,无论是社会体系结构还是教育制度本身都被假设为不变的,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对教育制度内部特征的分析才得以被充分展开。但是在新制度主义分析的框架中,制度是变异的、是动态发展的。这不仅指在特定时间背景下,不同空间范围内的制度各有不同;也指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制度在时间维度上发生变迁、更替的过程;还指制度在跨时间和空间的背景下所发生的传播、迁移现象。新制度主义对制度的动态变迁提供了一个二元的解释框架。首先,它认为任何制度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总是在旧的制度瓦解的时候被建构的。而一个制度的危机往往来源于两方面:一个是结构层面,一个是行动层面。所谓结构层面是指就制度本身而言,如果制度的法令、规范和认知三个层面发生了不一致的状况,那么制度内部便会产生变更的张力,而外在环境的变化,如政治、经济和技术体系的变化,也会通过改变制度中的或者法令、或者规范或者认知中任何一个或几个层面而引发制度内部的冲突,导致旧制度的危机。与结构层面相应的是行动层面。新制度主义并不认为制度的行动层面是以个体为载体的行为体系,而是组织的群体以及组织群体之间的网络。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危机和变迁都会体现在并最终落实到组织特征的变化和重构上。
其四,新制度主义分析在分析的层次上纳入了组织分析这一新的层面。虽然在旧制度主义分析中,不乏对对学校的考察,但是在那里,被考察的不是作为一个组织群落的学校,而是经过典型化了的学校组织个体。因此,旧制度主义将学校定义为一种为承担特定功能而存在的目标理性系统,并相应采取了正规结构(formal structure)/非正规结构(informal structure)的划分,符合其所要承担社会功能的那部分便被定义为正规结构,而不符合的其社会功能的那部分则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被定义为非正规结构,例如学生的违规行为(deviance)、价值体系与群体集合(peer group)就被界定为“学校亚文化”甚至“反学校文化”。新制度主义对这种以功能为依据而进行的结构二分法却不认同,相反它把所谓“非理性”的结构纳入到正规结构中一并考察,认为学校组织的部门或操作程序所表现出来一定的分散性不是由其功能所决定的,而是由组织间的求同性、组织间的相互影响、以及组织内和环境中的文化特征所导致的。因此,在新制度主义者看来被制度化的不是组织的个体,而是组织的形式、组织结构的组成因素和组织的规则等组织的诸多构成因素。于是,组织在旧制度主义中被视为有机的整体(organic wholes);而在新制度分析中则被视为标准因素的松散排列组合(loosely coupled arrays of standardized elements)。如此看来,旧制度主义分析考察的是典型化了的学校个体,而新制度主义考察的是学校作为社会组织的群落。本专题的两个制度分析的案例研究——郭歆和赵琳等对我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的得失分析,便是在这个层面上进行的。笔者以为,组织层面的发现是新制度主义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突破。
简而言之,与教育的旧制度主义分析框架相比,新制度主义不仅拓展了“制度”概念本身,将其由过去单纯的“规范”构成而扩展、深化为由“规范”、“法令”和“文化认知”三个要素构成的体系;此外,新制度主义还将旧制度主义的规范—制度的分析体系拓展为规范—组织—制度。组织分析层面的纳入一方面丰富了教育制度分析的层次和维度,另一方面也完成了制度分析的独立性。这两点是新制度主义分析在概念上和理论体系上对旧制度主义的突破。正因为有以上的突破,新制度主义的教育分析才具有了与旧制度主义分析完全不同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不再把利益群体的角逐作为分析的核心和重点,也不再将教育制度视为社会体系结构的被动反应;相反通过对教育制度不同层面的分析,以及它对社会体系结构特征影响的考察,新制度主义强调了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变动性。这无疑是其理论的优势和特点。
一种理论是否真正具有优势,不仅在于其概念界定的准确性和清晰性,也不仅在于其概念和概念之间所建立命题的严谨性,因为这些只能说明其理论建构的技巧和能力。事实上,更能说明理论优势的是它的解释力、与现实的结合性及其对现实的指导性。笔者以为,教育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可以突破旧制度分析的边界局限性,对教育制度正处于激烈变革的中国具有相当强的适应性和解释力。为了验证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关联,笔者在所讲授的《教育社会学》课程中,把研究生分成五个小组,采用Grounded Theory的定性研究方法论,对我国自1970年代末以来发生的教育“市场化”的制度变迁的不同方面予以考察。在这里选取其中的两个分报告与本文一起作为一个小的专题,与读者分享。报告中的不少精彩之处,都是学生在大量烦琐的数据收集、分析和讨论过程中产生的,至于其中理论分析力度的不足则与笔者的指导不足有关。笔者希望,本专题的研究有助于推动中国教育社会学的本土化,并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教育制度变迁带来积极的作用。
标签:教育社会学论文; 新制度主义理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价值观论文; 文化价值观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功能分析论文; 冲突规范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