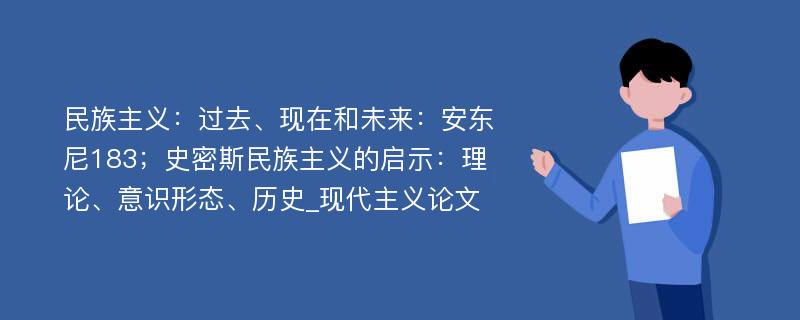
民族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安东尼#183;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一书的启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安东尼论文,史密斯论文,意识形态论文,启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634(2008)01-0043-(06)
当代西方著名的民族和民族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史密斯曾经说道:“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运动,至少从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以来,就一直是世界政治中的一支强大力量”,时至今日,民族和民族主义成为“全球化世界中无处不在的力量”。[1](序P5,P192) 然而,根据柏林的考证和判断,“奇怪的是,没有任何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曾预料到它会在未来扮演远为重要的角色”。换言之,“没有任何一位有重大影响力的思想家预见到民族主义的未来——毕竟没人明确地谈论过”。这种状况令人不可思议,因为“于其他方面如此敏锐的社会思想家,于民族主义却如此迟钝、言不及义”。概而言之,“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至少值得更广泛深刻地探讨”。[2] 按照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所主张的“长时段”来观察民族主义的历史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同时,我们今天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研究,也恰恰是布罗代尔所津津乐道的“问题”史学的一个方面:民族和民族主义作为历史航线上的问题,到底是如何发生、发展而其结局又会如何呢?而安东尼·史密斯的著作《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3] 为我们的考察提供了极佳的路线图和十分有益的启迪。
一
众所周知,民族主义所涵盖的内容的广泛性和多侧面性决定了对其进行全面而准确的界定十分困难,也决定了目前学术界对其所进行的诠释的多元性,以致学者们对民族主义的定义众说纷纭。英国著名的民族主义研究者埃里·凯杜里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学说,它“认为人类自然地分成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由于某些可以证实的特性而能被人认识,政府的唯一合法形式是民族自治政府”。[4](P1) 或者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认为人类自然地分成不同的称之为“民族”的人类群体,这些不同的民族是而且必须是政治组织的严格单位。英国民族主义经典作家厄内斯特·盖尔纳则认为,“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它作为一种情绪或者运动,可以用这个原则作最恰当的界定”,[5](P1) 而“共同的文化背景”是其深厚的基础。[6]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当代现实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和奠基人汉斯·摩根索认为,民族主义的内涵有传统和当代之分,它们的共同点都在于把国家作为政治效忠和政治行动的基准。不同在于前者将国家作为奋斗的终点;后者则将国家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起点,“它是一种世俗化的宗教,它对人的本性和命运的解释以及它拯救全人类的救世主式的誓言都是普遍适用的”。[7](P411)
史密斯综合其他人的看法,根据民族主义促进民族利益的主要目标是民族自治、统一和认同,给出了一个指导性的定义:“一种为某一群体争取和维护自治、统一和认同的意识形态运动,该群体的部分成员认为有必要组成一个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民族’。”[3](P10) 而从“民族主义”的词义来说,他认为有八种用法:民族特点或民族特性;用以专指民族的术语、成语或特征;忠于某一民族并维护其利益的一种感情;热望本民族独立和统一的一种态度;使这样的热望体现于组织形式中的一种政治纲领;以工业国有化为基础的一种社会主义形式;一种鼓吹某些民族为上帝的选民的学说;历史上民族形成的整个过程。[8](P89)
一般认为,民族主义是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产生的。当然,不同的学者所给出民族主义产生的时间稍有差异。例如,凯杜里认为,民族主义在19世纪产生于欧洲;安德森和吉登斯都认为是18世纪末;霍布斯鲍姆认为是19世纪末;而盖尔纳和史密斯则认为是19世纪初。不管争论如何,法国大革命及随后的拿破仑战争被公认为现代民族主义产生的一个转折点,“拿破仑战争开始了国家外交政策和战争的时代;也就是说,国家众多的公民对国家权力和国家政策的认同取代了对王朝利益的认同”。[7]((P145)
至于民族主义为何产生或民族主义的起源问题,学者们更是见仁见智②。凯杜里从思想史与政治史两个方面探讨民族主义现象,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学说:这一学说讲述了一系列有关人类、社会和政治的相互联系的思想观点。促成其发展和完善的因素,一是法国大革命;此外,则是在思想领域中发生的另一场革命,用作者的原话:“如果说民族主义学说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逐渐流行开来的话,那么,这不仅是哲学家们的辩论所带来的结果,而且是那些赋予这些哲学问题直接和明显的意义的事件所带来的结果。”[4](P2) 盖尔纳通过检验我们已经或正在经历的三种社会形态,即前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结果是工业社会符合这一民族主义原则,或“那些条件碰巧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条件相同”。[5](P164) 由此推出民族主义产生和流行的条件,即同质性、识字和没有个性特征。安德森则详细地探讨了民族主义起源的文化根源和具体的根源。
史密斯主张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民族主义的起源,认为其成功有赖于特殊的文化和历史环境,所以,“我们不是从现代化和全球主义的力量中,而是在族裔共同体与族裔类型的历史与文化中找寻民族主义的力量与轫性。”[1](序P4) 在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史密斯本人早年是‘现代主义’民族理论大师盖尔纳的博士生,在其治学过程中受到其师的很大影响,比如他并不完全否认现代民族的市民或公民性以及政治性,同时也对‘原始主义’民族理论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但是在阐述民族的本质特性及其历史性方面,史密斯很有一些‘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治学精神,他坚持自己的研究结论而与其师终身倡导的‘现代主义’民族理论分道扬镳乃至分庭抗礼。”[9]
最后,在当代西方对民族主义研究中主要存在四种范式,即原生主义、永存主义、现代主义和族群—象征主义(当然,可能还存在后现代主义等其他研究方法)。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现代主义”和“族群—象征主义”。④ 史密斯是“族群—象征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他代表人物还有约翰·哈金森、阿德里安·哈斯廷斯和约翰·阿姆斯特朗等。概括起来,史密斯认为持“族群—象征主义”的学者中间具有一些共同的关照,即扬弃现代主义的完全精英导向的分析特点;通过长时段对社会和文化模式进行分析;在族群的框架中分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关注集体激情与依念问题;重视研究族群和民族认同的公众的、道德的和情感的维度,因此能够抓住集体文化认同的持续性和转变性。总之,与其他范式形成对照的是,“历史族群—象征主义特别强调主观因素在族群延续、民族形成和民族主义影响中的作用”,换言之,“给予主观的因素如记忆、价值、情感、神话和象征等以更多的重视,并且由此寻求进入并理解族群和民族主义的‘内在世界’”。[3](P59)
二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在确定现代世界的面貌方面,没有哪个政治学说能比民族主义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10](P1) 民族主义自从近代产生以来,就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包括世界格局、国际秩序和世界冲突等。[11] 有学者提出,“对国际关系理论来说,民族主义是一个如此边缘性问题”。[12](P233)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边缘的问题却对近现代的国际关系史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对人类的生死存亡起作用。仅以一战为例:这场源于民族主义的世界大战就导致超过1500万人丧失生命,而同样与民族主义有紧密关系的二战则造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杀戮,以致最终动用最为先进的乃至可以将整个人类消灭的核武器。正因如此,伯林甚至希望“这种意识形态也许根本就不应该诞生”。[2] 即便如此,民族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民族主义依然还在延续着塑造现代世界乃至现代人类心灵的历史。
按照目前流行的现代主义学派提倡的“民族主义历史观”,民族主义从18世纪的最后25年开始发生,接着从1810年到19世纪20年代,间歇性扩散并开始在欧洲的其他地方落脚。随后由1848年欧洲革命掀起的民族主义第一次浪潮促成德、意的统一,并由此导致19世纪最后30年,民族主义的第二次浪潮在东北欧的迅速发展。与此同时,民族主义在亚洲或非洲开始散布;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主义的冲击几乎遍布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当代民族主义的复兴则是在20世纪最后10年发生的事情了。[3](P92~93) 霍布斯鲍姆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两百多年的民族主义历史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革命的年代”的民族主义(1789~1848)、“自由主义世纪”的民族主义(1830~1870)、民族主义转型时期(1870~1918)、民族主义最高峰(1918~1950)和20世纪晚期的民族主义。总之,根据现代主义的民族主义历史观,“在第一个孕育的阶段产生了一个浪漫的高潮,这一高潮引导出1871年之后大国的进攻性民族主义,接着产生出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和民族主义的消散”。到今天,“民族主义已经变得落伍了。它已经失去其原先的造就国家和组织经济的功能,并且已经成为一种‘失去的梦境的替代品’”。[3](P93,P97)
史密斯对以上现代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虽然承认,“现代主义坚持把现代世界的民族类型与过去的集体文化认同区分开来是正确的”。但是却指出,“我们却应该注意不要在这些‘前现代群体’和‘现代民族’之间划出太大的断裂,也不要像霍布斯鲍姆那样预先否定前现代群体和现代民族之间的任何延续性”,更不要简单地宣告民族主义的终结。通过详细考查族群、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演化过程,史密斯总结道,“这样的过程从1848年革命通过种族的民族主义时代,到1945年之后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乃至直到最近的族群民族主义到处开花”。而且,这样的过程和运动呈现出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亦即这些运动的意识形态新颖;族群基础对现代民族十分重要;以及强调族群和民族的内在世界等。[3](113,P122~123) 毫无疑问,史密斯这样的分析对深入理解民族主义是有帮助的,尽管似有过于强调民族主义的族群基础的倾向。
三
关于“民族主义的未来”这样一个大问题,西方学者们根据自己的研究,给出了各自独特的见解。其中,按照霍布斯鲍姆的说法,民族主义在经历17世纪的童年期、18世纪的青年期、19和20世纪的壮年期后,现在正进入其老年:“虽然民族主义是一种不可能避得掉的历史力量,但它的确不复具有全盛时期那种呼风唤雨的神效”,“未来的世界历史绝不可能是‘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历史,不管这里的民族主义指的是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甚至语言上的。”[13](P202,P223) 而且,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是,“民族或民族主义的确已过了其鼎盛时期。黑格尔说,智慧女神的猫头鹰在黄昏时飞出。如今它正环飞于民族与民族主义周围,这显然是个吉兆”。[13](P224) 真实情况如何呢?史密斯认为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事实上,我们所面临的至少是三种不同的主张和相应的争论。第一种与‘民族—国家’及其是否会即将消亡还是会长期存在有关,第二种聚焦于‘民族认同’的转化和可能产生的碎片化,而第三种则集中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是否会衰弱和被取代的可能。”[3](P128) 这些问题则正是史密斯在《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一书中加以详细讨论的。
首先,针对民族一国家主要功能的消失或缩减以及全球化的影响,史密斯经过分析认为,“无论如何,民族的国家所获取的新功能却大部分地补偿了这种侵蚀,这些新功能的获得是为了民族的特性及公民的福利”。[3](P128,P130) 以欧洲联盟为例,时空压缩以及对更大的政治单位和文化空间的需求并未创造出欧洲共同的神话和象征,与之相反,“与这种即使是虚构的但却生动而真实的民族国家家庭比较,欧洲的‘文化家庭’看上去是如此空洞苍白和瘦骨嶙峋”。[1](P165~166) 况且,“欧洲的统一方针意味着通过民族的国家及其制度来实现,这再一次地赋予了国家更多的合法性和权威”。[3](P132) 由此怎能推断民族——国家的终结呢?
其次,关于“民族认同”转化和碎片化的问题。移民、难民和寻求避难者们极大地冲击着传统的民族认同,不少学者对此忧心忡忡,甚至发问:“我们是谁?”[14] 但实际上,“有关民族的文化统一及其单一的、即使是遥远的族群起源从来就没有确定性”,这意味着,“‘民族认同’始终是被每一代人重新解释和重新塑造的”。其结果,“现代民族可能有多面性,并且异族通婚比例的提高,也可能促进产生我们在不久的过去中所从未见到过的文化上更为混合的人民”,“但是许多所涉及的国家依然保持它们长时间的主导族群,并且,在大城市之外,主导的族群依然维持他们本土的、尽管也在变化的文化、记忆、象征和起源的神话”。[3](P133,P135)
最后,关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是否会解体的问题。尽管霍布斯鲍姆承认,民族主义曾经是“一种带动历史变革的力量”,但因时易势已成明日黄花,至多只能成为未来历史的配角。而史密斯则认为:“种族民族主义取代了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成为全世界社会运动和政治理想的基础和语言。”换言之,在可预见的将来,“民族主义仍具有强大威力”,这是因为“民族主义远不止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与其他现代信仰体系不同,权威不仅仅存在于民族的普遍意识中,而且存在于此民族或彼民族的特有形象和特性之中。民族主义使这种形象和特性变成了绝对性的东西。因此,民族主义的成功有赖于特殊的文化和历史环境”。总之,“那种认为民族主义不久将被替代、民族即将被超越的预测是愚蠢的”。[1](序P1~6,P192)
除了上述争论之外,“后民族”社会理论也对民族主义的未来提出了质疑。这一“后民族的”社会的设想,是“建立在不断地包容和侵蚀民族文化和认同世界主义全球文化正在兴起的论点基础之上”的。[3](P138) 而且,这种论点具有两种形式,一是强调大众消费主义以稀释民族文化的差异;二是以全球文化观点超越民族的文化。史密斯对此分析道:对于前者,“与接受西方的技术和传媒,包括接受英语同时出现的却是,许多民族的国家中的精英们则在接受全球消费主义时,寻求培育他们自己的文化习惯、信仰和风格,并且为民族文化的自治而奋斗,从而反抗文化帝国主义”;就后者而言,“无疑,我们正在经历大众传播在形式、范围和深度上的巨大变化”,“但是,这一切是否达到了产生新的全球文化的程度?”现实告诉我们,“不论科学的还是折中的全球文化形式都不能得到大众的回应、都没有耐久性”。[3](P138,P140,P142)
在批判的基础上,史密斯提出自己的观点,“全球化远远没有导致废弃民族主义,甚至可能在事实上还加强了它。”[3](P142) 具体论证如下:首先,全球化以三种形式导致“民族主义的国际化”,其结果,“实际上促进了民族主义的传播并且鼓励民族成为更有参与性和更为独特的群体”;其次,文化和族群的象征资源的不平衡分布刺激了民族之间持续的比拟、竞争与效法,“由于全世界族群的数量巨大,这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21世纪初民族主义的持续存在和不断扩散的现象”;最后,民族的神圣基础带来“民族认同持久的把持力和民族的持久力”。史密斯认为民族的四个方面的基本范畴即共同体、领土、历史和命运,它们过去被视为、而且现在还继续被视为是“神圣的”,由此构造的“神圣基础”虽然也不是静止不变的,但是,“只要民族的神圣基础持续着,并且世俗的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还没有破坏对群体的历史和命运的主要信仰,那么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公共文化和政治宗教的民族主义就必然会持续兴盛,民族的认同也将继续为当代世界秩序提供基础构块”。[3](P144,P147,P150~151)
四
史密斯的《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一书从多种学科角度“对与民族与民族主义相关的概念如民族、族群、民族认同、族群认同、民族的国家等进行了颇为系统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概括性地阐释以作者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族群—象征主义民族主义理论观点”。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史密斯及其‘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认为,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决定了民族和民族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历史作用”。而且,“正是由于强调民族的族群基础,‘族群—象征主义’理论还反对‘现代主义’理论对民族的政治性和国家性的过分重视,虽然并不反对民族具有这方面的特征”。[9]
然而,诚如哈斯所言,“民族主义是只大象,研究者是个瞎子,每个研究者只能摸到‘民族主义’大象的一部分”,[15] 任何理论只是在某一特定领域、特定时空和特定假定下具有解释力。对此,我们应该铭记。事实上,民族主义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事物,一种理论不能穷尽其所有方面,尽管学者们可能有这种愿望。所以,“族群—象征主义”理论受到不同学者的批判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有学者为此进行了细致的考查,总结出六条对“族群—象征主义”的批评:1.概念的混乱;2.低估了现代民族与早期族群共同体的区别;3.在前现代无法谈及民族和民族主义;4.低估了族群认同的易变性和适应性;5.现代民族认同和过去的文化物质之间的关系值得怀疑;6.对族群意识形成的过程分析具有误导性。[10](P183~189) 不管这些批评是否都正确,我们在阅读史密斯的《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时还是应该不时地想想这些批评,以便能更好地把握作者的理论。
在当代中国大陆,由于建国之后官方不再使用“民族主义”而改用“爱国主义”一词,[16](P70) 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对民族主义的研究被有意无意忽视。自然地,我国在很长时期内对民族主义的认识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例如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对民族主义的解释是:“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他们观察、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原则、纲领和政策。”该词条列举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有:“把民族分为‘优等’和‘劣等’,认为只有所谓‘优等’民族才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极力抹杀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以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种族矛盾,不惜牺牲本民族工人和其他民族人民的利益”;“奉行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的政策”。这种认识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当代情况相去甚远。所幸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许多学者对民族思想和民族主义问题进行了孜孜不倦的研究,但是,与当代西方的相关学术研究相比,国内的民族主义问题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史密斯的《民族主义》一书的启迪不仅仅在于帮助我们了解当代西方学术界关于民族主义学术研究的深度,而且还在于能帮助我们比较全面地认识民族主义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其中特别是对民族主义的阶级性问题、现代性问题以及民族主义的未来前景问题等会因此而有更为深入和全面的认识。
注释:
① 两种理论的详细区分,参见叶江《当代西方的两种民族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② 有关民族主义起源的一些深入分析,可参见叶江、沈惠平:《西方民族主义兴起的思想背景探析》,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收稿日期:2007-05-14
标签:现代主义论文; 民族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民族论文; 政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象征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