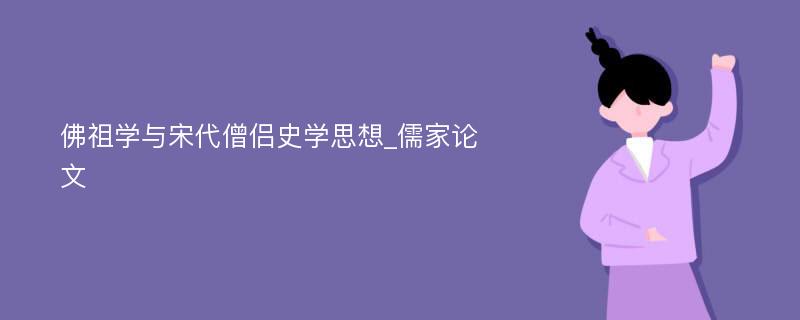
《佛祖统纪》与中国宋代僧人的史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僧人论文,宋代论文,佛祖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3)05-0167-05
宋代是中国佛教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各类僧史著作的编写相当引人注目,其中尤以 南宋僧人志磐的《佛祖统纪》一书最为著名。《佛祖统纪》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大 最完整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佛教通史巨著。它以宏大而有机统一起来的著作体例、广博 深厚的内容、进步的史学思想,把宋代僧人对自身历史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该书采择史料面广,资料翔实,编选精当,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很高的史料和思想价值 。从《佛祖统纪》可以看出,宋代的佛教史学,不仅丰富了佛教自身,扩大了它的社会 影响,而且也为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成分,它的出现有着历史与宗教的双 重意义,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
一、唐宋时期的史学变革对佛教史学的影响
佛教进入中国后便有了佛教史学。“鉴于史学至少有着反映一种宗教形态来龙去脉的 功能,所以佛教史学也是全面认识中国佛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1]早在东汉年 间,中国就已出现了佛教史学。《牟子理惑论》、《四十二章经》等早期佛教典籍的出 现,标志着中国佛教史学的形成。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经典的大量翻译和僧 史著作的出现,佛教史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宋代时,佛教史学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 。佛教原本并不重视历史,印度的神话和历史往往混淆在一起,有时不易区别是历史人 物或是神话人物。但在中国,情况则完全不同。原本并不重视史学的佛教,在进入中国 后则出现了大量的史学著作。这一文化现象,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从史学的角度来看 ,佛教史学作为佛教思想和佛教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与宗教的双重功能。它的出现, 对中国佛教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释志磐,号大石,南宋天台宗僧人,曾住四明(今浙江省鄞县)福泉寺及东湖月坡山, 不详其身世及生平事迹,只知其学识颇丰,幼年从儒者袁机受学,后出家学禅[2](P225 9)。志磐生活的宋代,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作为传统学术思想文 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史学,由于受晚唐北宋中期以来儒学复兴思潮的强烈影响,也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重义理”、“重编年体”、“重正统之辨”的趋势,导致了 儒家史学在修撰过程中对佛教历史进行不实的记载。陈寅恪指出,“宋代史家之著述, 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独由于意执之偏蔽,亦其知见之狭陋有以致之”[3](P240)。同时,史学领域内的这一变化,又引起了史学评判标准的变化。从西汉到宋初,中国古代 史学基本上遵循着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修史原则,注重对史料的编 辑,注重总结前代的兴衰成败,以便为统治阶级提供借鉴。但自北宋中叶以后,新儒学 的兴起对史学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以往史学评判标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儒家们 认为历史不应该是史料和史事的单纯记载,而应该是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表现褒善贬 恶的“春秋”精神,并最终把“儒家思想作为评判是非得失的最高标准”[4](P88)。苏 洵说,“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 之常法,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5](《史论》),明确指出儒家经典应成为史学的指 导原则。在这一史风的影响下,“崇尚《春秋》而贬低司马迁、推崇编年而贬斥纪传的 史学观,与唐初已大为不同”[4](P89)。《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 史书的修撰,反映了这一时期新史学风气的变化。欧阳修说:“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者欤!自古未之有也。”[6] (P173)又说:“予于《五代书》,窃有善善恶恶之志。”[7](P570)林駧也说:“公( 指司马光)之所论者,凛凛乎君臣父子之经,三纲五常之理,仁义忠信之道,岂非有关 于风教乎?”[8](《通鉴》)明确指出史学领域内应该“振三纲”、“讲人伦”、“重人 道”。同时,这一风气的变化又影响了史书的编纂体例,即史书在撰写形式上深受孔子 《春秋》编年体例的影响。这样,中国古代史学在宋以后逐渐纳入了儒学范畴之内,演 变成为地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工具。史学领域内的变革,反映了这一时期强烈的时代特 征。
唐宋时期史学领域内的变革,对宋代佛教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史学领域内的“正统论”及其向“义理化”、“伦理化”的转进对宋代佛教史 学发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这一史论的影响下,历代正史中有关僧人的传记和佛教在 中国传播的记载,到北宋中期以后的《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唐 史记》、《唐鉴》等史书中一概删除。同时,这一史论又引发了新史家们以儒家的“正 统”来抗衡佛家的“法统”。欧阳修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 天下之不一也。”[9](《正统论》上)因此,在史书修撰中,大发《春秋》精神,宣扬 三纲五常之道,从重建国家权威和思想秩序的角度出发,对佛教“无父无君”有悖于传 统伦理的做法给予了猛烈的批判。这一史风,在宋代新修成的几部史书中都有所反映。 陈荣照指出,“利用和通过史书来宣扬伦常道德,显然比后来理学家高唱‘三纲五常’ 更能发挥其教育作用,这对于影响一代士风,无疑起了促进的作用”[10];陈寅恪也说 ,“然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 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故苏子瞻之史论, 北宋之政论也;胡致堂之史论,南宋之政论也;王船山之史论,明末之政论也”[3](P2 48)。两位学者的论述,是极为精辟的。面对儒家史书中“佛老之事悉删之”的局面, 佛教史学在宋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次,效法《春秋》而兴起的编年体例成为宋代史书撰写的基本通例,这大大地影响 了宋代佛教史的撰写。宗鉴的《释门正统》、祖琇的《隆兴编年通论》、本觉的《释氏通鉴》、觉岸的《释氏稽古略》和志磐的《佛祖统纪》,无一不受编年体体例 的影响[11]。尤其是通史性著作“宗史”的兴起,更是宋代僧人对儒家史学批判性地认 识与取舍的结果。所谓宗史,即“以本宗传承为中心,以编年体的形式叙述的,其中包 括朝代、甲子、年号、佛教事实等;此外还有关于佛教的著名学者、祖师、学说等的记 载”[12](P6),是一种不以人为主而只记述一般事实的著作。宗史的出现,反映了宋代 佛教宗派林立、各宗重视自身历史的事实。开始写宗史的是禅宗,早在唐代就有了著作 ,如神会的《南宗定是非论》就辩论到禅宗的世系问题。以后发展到知矩的《宝林传》 ,包括了印、中两方的世系。单讲中国世系的,有敦煌发现的《楞伽师资记》和《历代 法宝记》。此外,讲派别的有宗密的《禅们师资承袭图》等。到了宋代,宗史更发展到 规模巨大、模仿一般通史体裁的著作,如契嵩的《传法正宗记》,把禅宗的传承一直推 到印度祖师释迦牟尼,而且是按照禅宗自己的传承来写的;释元颖的《天台宗元录》, 是按天台宗的世系来叙述中国佛教的。一直到南宋释志磐的《佛祖统纪》,这方面的著 述络绎不绝。“宗史”的出现,是中国佛教史的一大特色。它的产生,反映了宋代佛教 史学的变迁,标志着宋代僧人对儒家史学的认识与反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再次,史学领域的变革体现在佛教史学既然是宋代僧人对儒家史学认识与取舍的产物 ,它自然而然就成为连接儒、道两家的纽带,大大丰富了佛教史学的内涵。两宋时期, 是宋学发展及其向理学演变的时期,儒释道三家在冲突和斗争的同时,广泛吸收各家学 说,出现了“援佛入儒”、“援儒入佛”的趋势[13]。学术思想领域内的变化如此,史 学领域内的变化亦是如此。这种对各家学说兼收并蓄的态度,大大地促进了史学的进一 步发展,从而使宋代的学术呈现出繁荣的局面[14](P47)。在这种空前活跃的学术大背 景下,宋代僧人既研读佛教经典,也研读儒学经典,力求将二者贯通。儒释相通之说, 不仅促进了僧人思想的解放,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水平。这些都大大促 进了佛教史学内容和体裁的转型,导致了佛教史学繁盛局面的出现。方豪认为,“唐时 佛教号称极盛,而史学著作尚不逮宋”[15];邓广铭也说,“宋代史学的发展所达到的 水平,在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也是最高的”[16]。这个成就,自然也包括佛教史学。
最后,史学领域内的变革还体现在新史学方法对佛教史编撰的影响上。宋代佛教史, 不仅承袭了前代编年体和纪传体,并进而将新型的会要体、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运用到 史学研究中。同时,还对注重“博征与考信”[17]的金石学也给予了关注。漆侠指出, 宋代史学之所以能够远绍史迁、傲视明清诸代者,就在于宋人辨析文献材料的能力非常 突出,尤其是金石学的发展,大大拓宽了宋人的眼界和思路[14]。宋代佛教史学的发展 ,不仅表现在史书种类的增多,而且也表现在史书质量、新史学方法的应用及其所创立 的体裁方面。
总之,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必然影响到史学的发展、面貌、特点。唐宋时期,史学领 域内的变革及宋代僧人对儒家史学的认识与反思,为宋代新型佛教通史的撰写,提供了 良好的学术氛围。
二、《佛祖统纪》的编撰目的与主要内容
对于历史研究的目的,梁启超指出:“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什么是历史的 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 动之资鉴。”[18](P148)因此,综观《佛祖统纪》的编撰,笔者认为,其主要目的有三 :一是与宋代佛教内部盛行的圆融调和论有关。晚唐北宋时期,天台宗和禅宗为争夺正 统,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同时,天台宗内部也有“山家”与“山外”两个学派的对立。 但自北宋中期以后,随着以“判教”为特色的中土佛教圆融精神的发展,佛教内部出现 了各宗调和的倾向。《佛祖统纪》的出现,就是当时佛教内部各种理论学说调和融合在史学上的反映[19](P223)。二是与宋代僧人对儒家史学的认识和批判有关。儒家新史学 对佛教事实的歪曲和不实记载,对佛教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强烈的挑战。释志磐撰写该 书,一方面是为了澄清一般世俗对佛教的失实误解,倡导佛儒调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 构建佛教史学的“正统”,以“正统史学”的形式展现佛教在中国存在的历史性与合理 性。在《法运通塞志》中,他提出了撰写该书的原委,“儒宗道流之信不具者,时有排 毁,然终莫能为之泯没,以此道本常也。夫世称三教,谓皆足以教世,而皆有通塞,亦 时使之然耳,列三教之迹,究一理之归,系以编年,用观通塞之相”[20](P1363)。三 是与宋代僧人对佛教历史自身的认识和反省有关。在释志磐以前,有关天台宗的史书已 经出现,如释元颖的《天台宗元录》、吴克己的《释门正统》、景迁的《宗源录》等; 到南宋晚期,天台一宗的史传已初具规模。但是,释志磐痛感以上诸书弊陋甚多,“志 磐手抱遗编,久从师学,每念佛祖传授之迹,不有纪述,后将何闻?”[20]对于宗鉴的 《释门正统》,他认为“虽粗立体法,而义乖文秽”;对于景迁的《宗源录》,他认为 “但列文传,而辞陋事疏,至于遗逸而不收者,则举皆此失于是”[20]。为了弥补这些 缺点,遂发愿撰写一部以天台为正统、兼及其他诸宗的佛教通史。于是,他以《宗源录 》和《释门正统》二书为基础,仿照史书纪传体和编年体体例,“参对文义,且删且补 ,而复大藏经典、教门疏记、儒宗史记、诸家传录之辞及琇师《隆兴统纪》、修师《 释氏通纪》,用助援引”[20],历时十二年增编而成。
《佛祖统纪》作为纪传体佛教通史,其体例包括本纪、世家、列传、表、志五部分, 共54卷。所包括的时代之长和记载内容之广,在宋以前的佛教史书中是绝无仅有的。它 上起周昭王二十六年,下迄南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年),时间跨度约两千二百多年;所 记载的地理范围,远远地延伸到了今日中国的版图之外:西至五天竺、中亚,北至大漠 ,东至高丽、日本,南至中南半岛,从这个意义上说,《佛祖统纪》是我国古代较完整 的具有世界史性质的佛教通史。它在广阔的时空间架上,使以天台宗为主的佛教历史, 如政治、经济、交通、民族、军事,和构成佛教社会的各阶层,如佛教人物,与佛教有 关的皇帝、贵族、官吏、将士、学者,以及各种佛教故事和传说,都得到了较为全面的 反映。
《佛祖统纪》中的“本纪”8卷,“以诸佛诸祖为本纪”,效法了《史记》的编撰体例 ,介绍了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源流及其传承更迭。在《释迦牟尼佛本纪》中,释志磐 以“正统”史学的笔法,记述了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一生传教的历史。在《西土二十四 祖纪》中,记载了从大迦叶至师子尊者24位历代嫡传大师的传教活动。在《东土九祖纪 》和《兴道下八祖纪》中,记载了从北齐慧文禅师至唐代荆溪法师堪然,以及远祖龙树 尊者创立、继承和发扬天台宗的事实,对他们“中兴天台一家教观之道”[20](《通例 ·释本纪》)的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世家”是一种记载诸侯、勋贵和对社会起过比较突出作用的人物及大事,兼用编年 和人物传记的写作方法。《佛祖统纪》中的“世家”2卷,“以诸祖旁出为世家”[25]( P1239),模仿了《史记》中“世家”的写作方法。《诸祖旁出世家》收有南岳、天台、 至宝十三世家,“起自南岳旁出照禅师,下至慈云诸师”,共205人。在释志磐眼中, 他们“皆传教明宗,分镫照世,与正统诸祖相为辉映”[20](《通例·释世家》),为佛 法的弘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列传,即人物传记,有专传、合传、寄传和杂传等类型。《佛祖统纪》中的“列传”1 2卷,以“广智以下”诸师为列传,“名言懿行皆入此宗”[20](《序》)。《诸师列传 》专记天台宗“山家”大师,包括四明慈云法师和广智、神照、南屏三家,释志磐称赞 他们“盛守家法,御外侮,人能弘道”[20](《通例·释列传》)。《诸师杂传》则专记 天台宗“山外”大师,释志磐认为他们“背宗破祖,失其宗绪”[20](《通例·释列传 》),故“以杂传处之”,尤其将“背宗破祖,别树门庭”的净觉、神智、草蓭列载其 中。《未详承嗣传》记载了派系不明的佛教人物,释志磐认为他们“有功教门,事远失 记”[20](《通例·释列传》),“旧虽有传而无所师附,见它传而无所考”[20](P795) ,故作《未详承嗣传》。
表是中国正史书中一种常见的编纂体例。它以时间为顺序,用谱谍的形式条理大事, 起提纲挈领的作用。它把本身就有密切联系但原先散见于各篇的史事集中而又简明的表 现出来,使史事之间的关联和趋向更加豁朗,从而弥补了纪、传、志的不足。《佛祖统 纪》中的表2卷,就是对传统史学“表”的承袭与发展,同时也是佛教目录学、年代学 的重要体现。《历代传教表》记载了天台宗从北齐至南宋传承更迭的历史。《佛祖世系 表》以表格的形式叙述了“释迦列祖”至“今时诸师”的传承关系,深刻地反映了宋代 佛教各宗派纵向发展的历史。一经表列,其历史脉络赫然在目。
如果说纪、表是对社会历史纵向发展的记录,志则是对社会历史横断面的剖析,能否 尽量多地涉及这个横断面中的重要方面,是能否全面地反映佛教历史的关键所在。《佛 祖统纪》中的志30卷,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涉及的范围极广。据陈垣考证,《佛祖统 纪》的“志”模仿了《魏书》的体例[21](P796)。但据笔者看来,该书的“志”更多地 吸取了《资治通鉴》的写法。《山家教典志》犹如纪传体史书中的《艺文志》,专载天 台宗著述目录,从而达到“斯固法门之盛烈”[20](《通例·释志》)。《净土立教志》 记叙了净土宗创立、发展的历史及僧俗的活动情况。《诸宗立教志》记叙了禅宗、华严 宗、法相宗、密宗、律宗诸宗兴衰更迭的历史,它们“虽共明此道,而各专一门”[20] (《通例·释志》)。《三世出兴志》记叙了佛教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循环演变的历史 。《世界名体志》绘有华藏世界、万亿须弥、九山八海、大千世界、韧利天宫、诸天和 震旦、西域、五印度及地狱等图,并附以文字说明。实际上它是佛教地理学知识的一个 汇总,“南洲五竺,东华震旦,若名若体,有说有图,虽自广以至狭,实举别而会总。 既明三世,须辨方界,此学者所宜知也”[20](《世界名体志》一)。在《佛祖统纪》中 ,《法运通塞志》几乎占了整个志的一半。该志“法司马公”[20](《序》)编年体的长 处,记载了历代佛教史迹及佛教与儒道之间的冲突、斗争及相互渗透的关系。它起“周 昭王至我朝”,“儒释道之立法,禅教律的开宗,统而会之,莫不毕录”[20](《序》) 。对于该志编著的目的和意义,释志磐说:“考古及今,具列行事,用见法运通塞之相 。至若儒宗道流,世间之教,虽随时而抑扬,而其事迹,莫不昭然可训可戒。”[20]( 《通例·释志》)《名文光教志》,犹如地方志之艺文志,专载有关天台宗的志记、碑 文、序言、论述、书牒等,凡“大儒、高释,有能以文字铺张大道,为法门之标表者, 是不可不略录也”[20](《通例·释志》)。《历代会要志》专辑历代兴废佛教的事例。 会要做为一种新型的史书编纂体例,出现于唐代,成熟于宋代。它分门别类,专记典章 制度,起纲领性的作用。释志磐在编撰《佛祖统纪》时,就运用了这一新型的史书编纂 体例。
三、《佛祖统纪》中反映出的宋代僧人的史学思想
《佛祖统纪》作为宋代佛教史学的代表,蕴涵着丰富的史学思想,反映了宋代僧人对 历史的深刻理解和整体认识,以及表述这种理解和认识的杰出才能。其史学思想包括: 注重章法和义例的创新,讲求信史原则,重视“通识”和新史学方法的运用等。在中国 佛教史上,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第一,灵活地运用纪传体、编年体及其他体例相结合的方法,以“综合体”的形式展 现佛教历史。
纪传体是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创立的。它是一种综合性的史书体裁,由 本纪、世家、列传、表、志五部分组成,能够记载广泛的历史现象和复杂的历史过程。 它的优点在于记述范围广泛,便于通观一个时期历史的发展形势,这是编年体史书所不 及的。它的缺点是纪事分散重复,“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 大纲要领,观者茫然”[22](《二体》),难以清晰地表达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和各事件 、各人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编年体出现于《春秋》,而以《资治通鉴》最为成功。它以 时间顺序排列各种大事,能够比较明显地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有 利于对历史作纵横两方面的考察,理解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联系。“中国外夷,同年共事 ,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22](《二体 》)它的缺点是头绪较多,不易掌握,以时为断,前后隔越,不易集中地反映同一事件 的前后联系,人物传记更无法容纳[23](P209)。对这两种体裁,白寿彝指出:“历史现 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24](P495) 《佛祖统纪》弥补了史书编纂体例上的弱点,灵活地运用和发挥了纪传体与编年体体例 的长处,巧妙地把二者结合了起来。“纪、传、世家,法太史公”,“志,法司马公” [20](《序》)。《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全仿正史之例,大旨以教门为正脉”[25](P12 39)。同时,该书还对宋代新出现的几种史书体裁,如会要体、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 也给予了重视,从而使《佛祖统纪》呈现出“综合体”的体例。
在《佛祖统纪》中,或在篇首,或在文中,或在卷后,都有“述曰”,它与《史记》 中“太史公曰”和《资治通鉴》中“臣光曰”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史书不可分割的重 要组成部分。“述曰”在《佛祖统纪》中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对事实材料和 流行说法进行的考辨,有的是对前文的解释,有的是对佛教历史的补充说明,但更多更 重要的则是作者的议论,因事设文,机动灵活,异彩纷呈。在“述曰”的议论中,释志 磐不仅用自己的语言,而且大量征引他人的见解,因而保存了大批珍贵的原始资料。它 既可以用来说明材料、解释材料和补充材料,也可以用来评论事实,发表作者的见解。 在印度佛教典籍中,并无编年撰史的传统,《佛祖统纪》效法儒家史学的体例,其意义 非常深远,影响了后来佛教史的编撰。
《佛祖统纪》中的这五种体裁,加上“述曰”,组成了记叙和总结佛教历史的有机统 一起来的完整体系。它们各自为用,又交织配合,相辅相成,从而包容了更多的佛教内 容,扩大了佛学的研究范围。从整体上看,这种体例是当时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结 构层次在史学著作体裁上的投影,它能最大限度地包括那个时代著作者们企图包括的社 会内容。释志磐灵活地运用“综合体”体例的长处,其奥秘就在于此。
第二,以“信史”的要求客观地描述佛教史实。
漆侠对何为信史曾有过精辟地论述:“一个史家对历史可以持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 但对历史的实际(即事实、资料)则应有真诚的、丝毫不能缺少的尊重,绝不能够以个人 的是非爱憎取舍材料;只有持有这种态度,才能撰写成信史。”[14](P93)冯友兰从哲 学的高度亦概括说:“向来说好的历史书是‘信史’。‘信史’这个‘史’就是指写的 历史,本来历史无所谓信不信,写的历史则有信不信之分,信不信就看其所写的是不是 与本来历史相符合。”[26](P2)《佛祖统纪》的史学思想和价值,在于它不仅继承与发 展了纪传体和编年体相结合的史书写作方法,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以“信史”的要求客观 地叙述了中国佛教史发展的历史轨迹。《佛祖统纪》继承了儒家史书中“秉笔直书”的 优良传统,以“求实与取信”的笔法,客观真实地记述了宋代佛教诸宗派的历史。在《 佛祖统纪》中,释志磐没有以个人的好恶来掩埋历史,也没有以某种道义的原则来歪曲 历史,更没有因为他是天台宗的僧徒而忌讳历史。以“信史”的要求客观真实地记录历 史,就成为《佛祖统纪》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在《法运通塞志》中,释志磐提出了自己的修史原则:
史者,所以记当时失德之迹也,以故恶如弑君必书,丑如烝母必书,岂以其丑恶而不 之记邪?是知修史者不没其当时善恶之事,斯可为信史也。昔范晔著《汉书·西域传》 ,始论佛法;陈寿志《三国》,则忽而不录;唐太宗修《晋书》,于沙门高行时有所取 ;魏收于《北史》,著《佛老志》;李延寿于《南史》,作《顾欢传》,凡帝王公卿毁 赞佛老者,莫不悉载。其于二教之偏正优劣,当年今日未尝不明识所归。欧阳氏之修《 唐书》、《五代史》也,于佛老之事则删之。夫《唐书》,唐家之正史,非欧阳之私书 也。借使不足法,论之可也。岂当以己所不好而删之邪?是知无通识者,不足以当修史 之任也。夫佛法之取舍,大较系乎人之好恶,韩、欧、司马始不好佛,遇事立言必有诋 诃。……吁,佛法之取舍,果在于人之好恶,可不审乎哉[20]?
释志磐的这段论述,讴歌了敢于秉笔直书的范晔、袁宏、魏收等,对他们在史书中客 观公正地记载佛教史事的态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对以个人好恶来掩埋佛教历史 、歪曲佛教历史的欧阳修、司马光等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乏通学,守隘见有若是 ,谓之信史,未信也”。并明确表明了自己的修史态度,“修史者不没其当时善恶之事 ,斯为信史也”,“岂当以己所不好而删之邪?”因此,他以“无通识者不足以当修史 之任”来要求自己,肩负起了修撰《佛祖统纪》的重任。从古代学术思想史来看,佛教 与儒家是处于竞争的局面,但释志磐以“信史”的精神,对儒家、道家有相当的肯定。 他说:“后代人主,尊称先圣,通祀天下,为万世师儒之法者,自汉家始,岂不盛哉! ”[20](《法运通塞志》六)从《佛祖统纪》的思想价值和史学成就可以看出,历史上一 切成名的史学巨著,其“良史之直笔”,足可以为“万代之准”的[27](《史传》)。《 佛祖统纪》中所反映的“信史”精神,是宋代僧人对儒家史学认识与取舍的结果,是我 国古代史学思想中的宝贵财富。
第三,注重史学中“通识”思想的运用。
“通识”是指史学研究从纵向和横向入手,将表面上分裂孤立的材料加以归纳贯串, 发现其内在联系,作出合理的分析,讲清历史问题的真相,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是史家 取得突破性成就的关键[28]。《佛祖统纪》中“通识”思想的运用是极其明显的。这一 特色表现在,《佛祖统纪》不仅从纵向上记述了天台宗及其他佛教宗派发展的历史,而 且从横向上也记载了与佛教相关的儒道二教的历史,纠正了此前佛教内部因宗派之争而 对僧史的不实记载,澄清了一般世俗对佛教史事的误解。《佛祖统纪》中的“通识”涉 及佛教史、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人物传、史论、史著等许多方面,显示出宋代佛 教史学多途发展的盎然生机,客观上具有破除当时浓厚的复古倒退思想(指宋儒的反佛) 的积极意义,而且以艰苦的史学实践,成功地回答了时代对“僧史”的需要。同时,“ 通识”思想的运用还体现在该书对唐宋时期学术领域内盛行的“三教合一”思想给予的 关注。《佛祖统纪》卷54所载的“三教出兴”、“三教厄运”、“三教訞伪”、“三 教谈论”等,就是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三教合一”思潮的学术总结,弥补了正史记载 的不足。
第四,重视史学表达形式的创新。
《佛祖统纪》中的《法运通塞志》,在中国古代史学传统中是个创例。《佛祖统纪》 虽仿正史的纪传体,但在“史学表达形式上,亦有所创新,是充分展现佛教史观的一部 史作”[29]。“志”原本是纪传体独有的体例,《佛祖统纪》由整体架构来看,是纪传 体,但纪传体的“志”并不强调编年,而《法运通塞志》虽名为“志”却编年记事,志 中有编年,这是《佛祖统纪》所独有的。这种表达形式,是佛教史学对传统史学的贡献 。它不仅突破了传统史学的局限,扩充了“正史”的体例,而且也囊括了更多的史学内 容,丰富了传统史学的内涵。释志磐撰述此志的目的,在于说明“一代化事”,强调佛 教与世俗的关系。“夫世称三教,谓皆足以教世,而皆有通塞,亦时使之然耳,列三教 之迹,究一理之归,系以编年,用观通塞之相。”[20](《法运通塞志》一)佛教在中国 有所谓“三武之祸”,在经历了多次严酷考验之后仍能流传于世,释志磐认为这就能证 明佛教有其颠扑不破的常理。至于佛教与儒、道二教的关系,他认为应维持和平关系; 儒、释、道三教,“皆足以教世”,而三教又各有易为接受,或遭到排斥的时代,故说 三教“皆有通塞”。因此,《法运通塞志》从佛教史学反省的角度出发,不仅记述了佛 教史的兴衰,而且对于儒家与道流之兴废,也多有记载,“大儒、高释,有能以文字铺 张大道,为法门之标表者,是不可不略录也”[20](《通例·释志》)。对于这种创新, 方豪评价说:“求之欧西天主、基督史家中,亦无如此识力者,志磐真大史学家也。” [15]
综上所述,《佛祖统纪》中所反映的宋代僧人的史学思想,是中古时期佛教史学与儒 家史学相互渗透与影响的产物。《佛祖统纪》在宋代佛教史学中开启了一代风气。它的 史学思想典型地反映了宋代学术思想的变迁。它所开创的史书新格局也成为后来佛教史 的“定式”之一,对元明清佛教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后人认真加以总结。但是 ,另一方面,《佛祖统纪》中宣扬的“善恶无常”、“因果报应”的史学思想,削弱了 史学通古今之辨的能力。尤其是它对早期佛教的不实考证和因门派之争对其他宗教派别 阙如的记载,造成史学失实、史学范围难以扩大的局面,这些理应加以批判。
收稿日期:2003-06-19
标签:儒家论文; 佛教论文; 文化论文; 释迦牟尼论文; 资治通鉴论文; 春秋论文; 读书论文; 天台宗论文; 编年体论文; 宋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