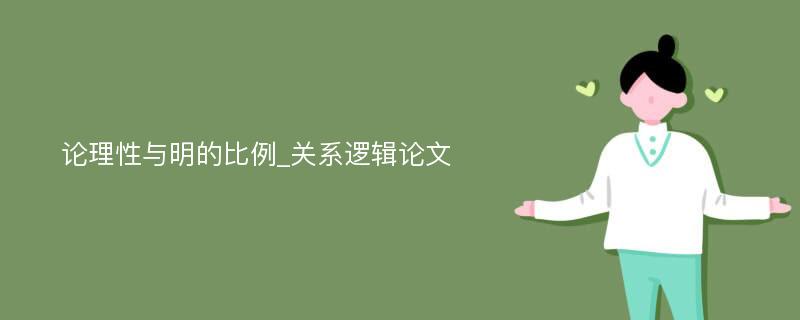
论因明比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 B81
比量是因明立具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因明家的著述中讨论得最为充分的思想,很有必要加以深入研究,以期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推进逻辑学的进一步发展。
在因明典籍中,比量有宽狭二义。狭比量仅指推理;宽比量则除了推理之外,还包括论证。本文主要从狭义方面对因明比量进行探讨,以图抛砖引玉。
一、比量的基础
推理是逻辑的主要内容。比量即推理。量的一般意义是人们行动要达目的所必须预先具有的正确认识。比量也不能凭空虚构、主观猜测,而人们在运用比量这种思维形式时,应当具备关于推理对象及其演变原理、规则的正确知识,这是因明正确进行比量的必要条件。
首先,因三相是因明比量的根本性原则。因三相是陈那在批判继承古因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核心理论,在新因明体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而也成为因明比量的基本依据。陈那《理门论》中说,不仅三支论式的建构必须以因三相为前提,而且比量也是在因三相的基础上形成的:“又比量中唯见此理:若所比处,此相定遍;于余同类,念此定有;于彼无处,念此遍无。是故由此生决定解。”比量属于一种间接知识,是根据已知推出未知的思维形式,推理的方法要凭借一定的理由即“因”来作媒介,这就是因三相。例如,新因明依据“因法所作性皆具宗法无常性”与“同品瓶等具有所作性和无常性”为前提,推出“声是无常”这个结论。可以说,比量是从三相的因所产生的知识。窥基《大疏》卷八中云:“由借因三相因,比度知有火,无常等,故是名比量。”
其次,真现量是因明比量成立的基本前提和条件。因明立具唯有现量与比量。现量是由感官与对象接触所产生的感性认识。陈那等认为,“离分别”与“不迷乱”是构成真现量的必要条件。“离分别”即不加入思维活动、不能用语言表述出来的纯感觉,各感官感受到的各种个别属性(种类)尚未在人脑中联系起来,更没有形成确定的概念(名言)。“不迷乱”即感觉不发生错乱(正智)。怎样做到不迷乱呢?这要从内外各种原因所发生的错觉去加以区别,有些错觉由于内在原因,如见了一条绳子却误以为蛇等;有些由于外在原因,如见了旋转的火焰以为是火轮等;有些兼由内外原因,如乘船见河岸的移动等,真现量一定要离开这些错觉。陈那《理门论》中云:“谓若有智于色等境,远离一切种类名言假立无异诸门分别,由不共缘,现现别转,故名现量。”天主《入论》中亦道:“此中现量,谓无分别。若有正智于色等义,离名种等所有分别,现现别转,故名现量。”离分别与不迷乱对形成真现量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加入了名言、种类等思维的分别活动,即使感觉不错乱,仍不能视作真现量;反之,如果感觉发生了迷乱,即使离开了名言、种类等所有分别,也不是真现量,因而将迷乱的“邪智”和有分别现量一概看作似现量。《入论》中说:“有分别智于义异转名似现量。”这是很有见地的。陈那等认为,真现量是构成真比量的基本前提,而似现量是造成似比量的主要原因。陈那《集量论》卷二中云:“若现量之境义,能施设名言,即由彼声,应成比量。”《入论》中道:“用彼为因,于似所比,诸有智生,不能正解,名似比量。”《大疏》卷八中亦说:“由彼邪因,妄起邪智,不能正解彼火有无等,是真之流,而非真故,名似比量。”例如,由于迷乱的“邪智”和有分别现量,使得人们将雾、尘等误认为烟,从而“邪证”山中有火,成为了似比量。
再次,宗因不相离性是因明比量的重要根基。正理派认为,比量的基础是直接能够经验到的具体事物(包括实际上属于思维领域的概念)。如有人未见水牛而闻其有似家牛,后于森林中看见一动物有似家牛而知这就是所谓的水牛。正理派还认为,属性总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的,如“所作性”与“无常性”即是共存于“瓶子”的两大属性,如果把这两大属性从瓶子这个具体事物中抽出来,二者便失去了联系,就谈不上“不相离性”了。所以因宗不相离性不能成为推理的基础。陈那等却认为,因宗不相离性是因明比量成立的根基。《集量论》卷三中云:“知有所作处即与无常宗不相离,能生此比量者,念因力故”、“又彼宗法即是因性,说因宗所随,宗无因不有。”正是由于因法所作性与宗法无常性之间具有不可分离的联系,才使因明比量得以顺利地进行。陈那等以“诸所作者见彼无常”这样的普遍性命题作为比量的前提,是使因明由或然性推理向必然性推理迈进的一个突出贡献。
可以看出,陈那等提出,人们在运用比量这种思维形式时,不仅要求比量的前提应当真实无误,而且必须遵循有关的思维规律和推理的基本原则,才能形成真比量。这一思想与恩格斯有关思维规律的观点是一致的。恩格斯说:“如果我们有正确的前提,并且把思维规律正确地运用于这些前提,那么结果必定与现实相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1页。)
二、比量的形成
与西方亚氏逻辑、中国墨辩相比,印度因明在探讨推理的形成方面有其独到之处,也是因明优越于其他世界逻辑源头的地方。但是,这在因明研究中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陈那认为,人类的正确知识只有现量和比量两种,其根本依据在于所量之境不外自相(个别)与共相(一般)而已。《集量论》卷一中云:“缘自相之有境心即现量,现量以自相为所现境故。缘共相之有境心即比量,比量以共相为所现境故。除自相共相外,更无余相为所量故。”因此,“圣教量与譬喻量等皆假名量,非真实量。”何谓自相?“诸法实义,各附己体为自相。”就是说,事物本身或其特定意义各依附着它的本身而不通到其他方面的叫自相。如风声,无关其他声音,就是事物本身;无常只指风声而不指其他,这叫特定的意义,都属于自相。但是这种自相,只属自内证智之所证智,绝非思虑说话之所能表诠,如果思虑说话能得到事物之自相,那么如火以烧物为它的自相,我们说火时就应烧口,思火想火时就应烧脑,而事实上并不如此,因而所思所说的并非火的自相,应是贯通诸火(厨火、灯火及野火等)的共相。何谓共相?《集量论》卷一中云:“假立分别,通在诸法为共相。”《大疏》卷八中亦道:“以分别心假立一法,贯通诸法,如缕贯华,此名共相。”如“声”这概念,通于人声、钟声、鸟声、风声、雨声等;“无常”这概念,通于瓶、盆、草、木、鸟、兽等,都属于共相。认识自相的叫现量,因为是对现在事物显现(非索隐钩深)现成(非逞私营己)获知的;认识共相的叫比量,因为是有待三相比度才决定知道的。《理门论》中云:“由此能了自、共相故,非离此二,别有所量,为了知彼,更立余量。故依二相,唯立二量。”
接着,陈那等阐述了因明比量的形成过程。由前所述,比量是从因三相及宗因不相离性等为基础进行建构的。例如,过去在厨房等处见火有烟,而在湖河海洋等处则不会看到,明确了烟与火有因果必然联系,后来看到隔岸烟起,审此观察智,忆念到前知,合为比度,决定隔岸有火;又如,我们曾经知道“所作物”与“无常”有必然的联系,后来听到含有所作性的动物等声、风铃等声、击鼓吹贝等声,忆念前知而进行推论,决定声是无常。在这里,审观察智是远因,因为它们不亲生智的缘故;忆因之念才是近因,由回忆才知道宗因不相离性,从而正面了解“有烟”应“有火”、“所作物”应“无常”,反面也明确了无火就无烟,常住就非所作物。可见,决定智实为合审观察智和忆因念远近二因而生的。《理门论》中云:“谓于所比,审观察智,从现量生或比量生,及忆此因与所立宗不相离念,由是前举所说力,念因同品定有等故,是近及远比度因故,俱名比量。”我们可以将比量的形成过程试解如下:
(1)审观察智——远因(前提)
(2)忆因念——近因 (前提)
(3)决定智——果 (结论)
可见,比量是从因立名,因从果名,关键在于因。《入论》中云:“言比量者,谓借众相而观于义。相有三种,如前已说。由彼为因,于所比义有正智生;了知有火,或无常等,是名比量。”而“若似因智为先,所起诸似义智,名似比量。”
三、比量的形式
正理派的推理局限于个别事物内涵方面的推理模式,它把比量分为三类:(1)有前比量,自因推果,如从看到黑云就推论有雨; 或者由以前的经验而推知,如由过去知烟与火之相连,现在隔岸有烟,比知有火。(2)有余比量,由果推因,如从洋溢的河流而推知上流有雨; 或者通过淘汰而推知,如声音或为一种实体或为一种属性或为一种动作,既然知道声音不是实体也不是动作,推出声音必是属性。(3 )平等比量,由二事的相类似而推断,如根据所见物体的变换位置是因其有了移动,从而观察太阳在一天行程中位置不同而推断它也有了移动;或者通过感觉可见之事某部分的抽象相类似而推断不可感觉之事,如知斧头工具须有工匠,推断心为工具必有作者,即“自我”或“灵魂”。正理派所说的这三类比量,正如《正理经》上所说,只是“将一可能说明事件自与既知者的类似而推定之”,并没有总结出普遍性命题来进行推理,在形式上是不严格的。
弥勒在《瑜伽师地论》卷十五里对比量的形式作了重要的补充和拓展。他把比量分为五类:(1)相比量,就是随所有相状相属, 或由现在或先所见而推断境界。如以面皱发白等相状,推断为老年;山见烟故,推断有火等。(2)体比量, 就是以现在所见事物之自体性推断另一未见事物之自体性,或者由现见事物一部分自体性而推度其余部分的自体性。如以现在推知过去;以眼前事物的本性推度远处事物的本性;以梨一分成熟推断其余部分亦熟等。(3)业比量, 就是以事物的动作情状进行推断。如见远物摇动,鸟惊飞起等而推知有人;若见环境草木滋润,茎叶青翠等而推断有水等。(4)法比量, 就是以相邻相属之法推断其余相邻相属之法。如它属于生物推度其会老,因它会老推知其有死;因它属于有色彩可见可触之物,推断其有处所与有质体等。(5 )因果比量,就是以事物的因果关系来循环推理。如见有丰盛饮食推知饱满,而见有饱满推知丰盛饮食;若见有人饮食不平衡推度他会生病,而现见他有病推断其饮食不平衡等。可见,弥勒所说的五类比量基本上停留在“从特殊到特殊”的类比方式,局限于个别事物内涵方面的比度或因果关系的推断,并没有上升到普遍性命题进行推理,也没有能够在外延上进行类推,在形式上是不严密的。
陈那以来的新因明,强调比量须借助因三相进行推断。因的第一相为“因法普遍具有宗法性”,即因法(中项)必须在外延上被宗法(大项)所包含;因的第二相为“同品必定具有因法性”,即与有法(小项)同类的同品必定在外延上被因法所包含;因的第三相为“异品遍无因法性”,即与有法异类的异品必须在外延上排斥因法。(注:参见拙著:《 因三相管见》,《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6期。)比量凭借因三相由已知推及未知,使推理具有了严格的形式。法称在《正理一滴》卷一中云:“推理的对象如同它的同类。例如我看见的一条牛是特殊的一条牛,它具有某些与其他的牛不同的特征,而我推论的一条牛是一般的牛,它具有一些其他的牛所共有的属性。……推理是一般的知识。”
在新因明大师的典籍中,他们对比量的有关论述具备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三种基本推理形式。例如,从瓶、盆、碗、缶等这些具体的所作物具有的“无常性”为前提,而概括出“诸所作者见彼无常”这个普遍性命题作结论,无疑相当于形式逻辑的归纳推理;从“诸所作者见彼无常”为前提,推出“声是无常”这个结论,显然相当于形式逻辑的演绎推理;从所作物瓶盆等同品具有无常性为前提,类推出“声是无常”作结论,这是形式逻辑的类比推理在因明中的具体体现。此外,新因明还以语言材料为筹码讨论了与现代逻辑相类似的诸多推理形式,创造了完密的形式体系。如法称把因法与宗法的关系分为同一性、因果性和非现量三类,还把因分为自性、所作、不可得三类,其分析之精辟详尽并不逊色于现代逻辑的蕴涵理论;新因明对诸如合取、析取、蕴涵及其否定的深入理解,用抽象程度极高的语言表述了现代逻辑中德摩根定律、类推理、空类与实类的转换、逻辑积、实质蕴涵等等思想;陈那、法称等用全分与一分、表诠与遮诠等概念为基础,表述了现代逻辑中命题、词项或真值函项的逻辑推演问题;陈那等还以“合”、“离”、“遣”、“周摄”等概念为工具,详细地分析了关系命题和关系推理及其规则,其精密细致的程度毫不亚于现代逻辑,等等。这些成就以其时代来说是相当突出和惊人的,表明新因明大师在推理的外延化、抽象化方面是走得相当远的。
四、为自比量与为他比量
新因明还将比量分为为自比量与为他比量。《集量论》卷二中云:“谓比量有为自比量与为他比量”、“三相之因观所比义,是谓为自比量。”卷三中道:“如自以因知有相法,欲他亦知,说三相言,是谓为他比量。”就是说,为自比量是不形之于语言文字以借助因三相而思考所比之义的内心推度,其功能在于自悟;为他比量是用语言文字表述出因三相所比之义的论证形式,其功能在于开悟他人。诚如《集量论》卷二中道:为自比量“由具足三相之因,观见所欲比度之义”,是纯粹的内心思维过程,因而为自所显示的比量是必然的,对比量者来说,在其内心所思考的对象及其推度过程是依据因三相而进行的,由前提推出结论应当是顺理成章、意料之中的。为他比量是因明进行论辩的工具和手段,因明大师们就是通过设立为他比量来破斥敌者论宗、弘扬自宗教义以开悟敌者和证义者的。
为自比量与为他比量是有联系的。一方面,为自比量是为他比量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为自比量就无以形成为他比量。《理门论》中云:“如是应知悟他比量,亦不离此得成能立。”《集量论》卷三中亦道:“为他比量者,显自所观义。自由三相因,生有因智,如是为令他生有因智故,说三相因,是名为他比量,是因立果名故。”就是说,在为自比量基础上,为使他人亦能明了立者所推知的意旨,而说出具足三相因的道理。《正理一滴》中说得尤为简明:“宣说三相正因(开示他人),是名为他比量。”《大疏》卷八中则讲得具体而形象:为自比量“亲能自悟,隐悟他名及能立称,次彼二立明,显亦他悟,疏能立,犹二灯、二炬互相影显故。”这是由于所有为开悟他人的论式必须首先在立者的思维中进行过适当的推断,如果连自己都思虑不通的比量怎能用来说服别人、证成自宗呢?从行文的秩序上看,陈那《集量论》和法称《释量论》、《正理一滴》等都是先论述为自比量,而后才依其逻辑顺序分析为他比量的。对此,第一世达赖僧成在《释量论释》中云:“分辩是义非义,须要依靠比量智故。为建立比量智,故先释自义比量也。”另一方面,为他比量是为自比量的结果和目的,设立为自比量的目的在于将自宗示之于人,用语言文字表述出来开悟他人,从而获得弘扬自宗教义、破斥敌者论宗的效果;没有为他比量,为自比量就不可能达此成效,也达不到因明“悟他”的目的。《大疏》卷八中云;“故知能立必借于此量(为自比量),显即悟他,明此二量,亲疏合说,通自、他悟及以能立,此即兼明立量意讫”、“故指如前,由彼为因,释前借义,由即因由,借待之义,于所比义,此即释前而观于义。前谈照镜之能,曰之为观,后约筹虑之用,号之曰比,言于所彰结比故也。”
然而,为自比量与为他比量毕竟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思维形式。首先,从两者的内涵及实质来看,为自比量是比量者“借众相而观于义”的内心推度,实质上是一种推理形式,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为他比量则是立者“欲他亦知,说三相言”而建立论式以开悟他人的外在论辩,通常表现为五支论式或三支论式等,笔者在另文中已讨论过,它实质上是一种论证形式。因此,一“观”一“说”,一为推理一为论证,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其次,从两者的思维进程及目的来看,为自比量是先有前提后有结论的,其目的在于从已知推出新知,当人们进行推理的时候,并未曾预料到将会推出什么结果。譬如,在归纳推理过程中,从个别性前提出发,既可以得到一般性的结论,如观察到山、厨房等处有烟,见其遍有“有火”之性,从而总结出“诸有烟处必有火”的一般性命题;同时也可能得不到一般性结论,如“并非天鹅都是白色的”。在演绎推理过程中,如从“诸有烟处见彼有火”的一般性命题出发,可以推出“此山有火”,也可以推出“隔岸有火”或“厨房有火”等等,结论并不是预先确定的。类比推理亦然,由前提出发,既可以得到相应的结论,也可能得不到相应的结论,而且结论也不是预先给定的。《入论》卷一中云:“因喻已成,宗非先许,用已许法,成未许宗。如缕贯华,因义通彼,共相智起,印决先宗,分别解生,故名比量。”《大疏》卷一中亦道:“用已极成,证非先许,共相智决,故名比量。”但是,作为为他比量的五支论式或三支论式,总是先示论题,次出论据,而后进行论证的,其目的在于证实立者已经确定的论题或者破斥敌者预先确立的论题,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大疏》卷一中说:“悟他自悟,论各别显。”再次,从两者的外在特征来看,由于为自比量是比量者内心的独立思考,他早已把思考的对象了然于胸,因而在推理过程中用不着进行正反两方面的推度,也不必将例证非举出来不可。一般来说,每一种推理都是单纯的,在同一推理过程中不可能同时进行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推理,尤其是不同类型的推理,而在“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推理中,举出其他的例证反成为“蛇足”了。相反,为他比量主要是用语言做媒介,提出自己的论宗建立论式来加以反复论证的,而在论辩过程中,只有兼举正证和反证,并同举相应的喻依,才能更具有说服力,更有效地开悟他人,否则是难以奏效的。《入论》中云:“由此论显真而无妄,义亦兼彰具而无阙,简此诚言,生他正解,宗由言显,故名能立。”而“宗因喻三,随应阙减。……伪立妄陈,邪宗谬显,兴言自陷,故名似立。”《大疏》卷一中亦道:“因喻具正,宗义圆成,显以悟他,故名能立。”而“三支互阙,多言有过,虚功自陷,故名似立。”可见,为自比量与为他比量的区别是相当明显的。
五、余论
综而论之,因明对有关推理的论述以及对推理与论证之间关系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精辟独到的,在逻辑发展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而且在今天看来仍有其重大的借鉴价值。不过,以陈那为代表的因明所达到的成就毕竟是有局限的。首先,许多基本术语,如“比量”、“所比”、“宗”、“宗法”、“法”、“品”、“相”等都不是一义的,往往在不同场合以同一词语不加解释地表达各不相同的概念,这就造成了理解、注疏上的分歧和混乱。术语的出现也缺乏顺序性,一些在后面几卷才加以界说议论的概念,常常在前面甚至一开始就出现了,从而导致若干部分的重复、繁琐与凌乱。其次,不少提法缺乏前后一贯性,如陈那《集量论》卷一中云:“量唯二种,谓现、比二量。”但在后面的卷三、卷四及《理门论》中却容忍了“圣教量”、“譬喻量”等的存在,后来的注疏者虽然对此曲为之解,但说得越多,逻辑上的不一致性也越明显。再次,由于因明的主要任务在于探索一个足以“悟他”的论证的途径,因而在比量的形式化、抽象化方面不可能走得很远,形式化的因明体系始终未能建立起来。而且,因明对比量的讨论也是不系统的,有关比量的论述通常散见于各典籍及各卷之中,没有形成一个易为人们领会、顺理成章的体系。最后,在因明体系中引入了许多无法阐明的命题和方法,由此增添了内容的驳杂性。并且,诸多因明论著拘泥于格律,其文字古奥艰深,大多局限于对教义经典的比量诠释,集中于各派之教理的辩难,远离丰富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造成了因明比量论的相对贫乏和单调,影响了它的进一步发展。当然,我们不能用今人的眼光去苛求古人,这些缺陷在当时来说也许并不足奇,有些纰漏则是因明侧重于论辩所造成的。然而,我们今天对因明进行研究,区分其中的精华和糟粕,恰如其分地显示因明的成就与不足,才能摧破歪曲,澄清误解与错谬,给因明一个正确的评价;同时,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对推动逻辑学的普及和发展,提高人们的理论思维水平,是有着较大的现实意义的。
收稿日期:1998—0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