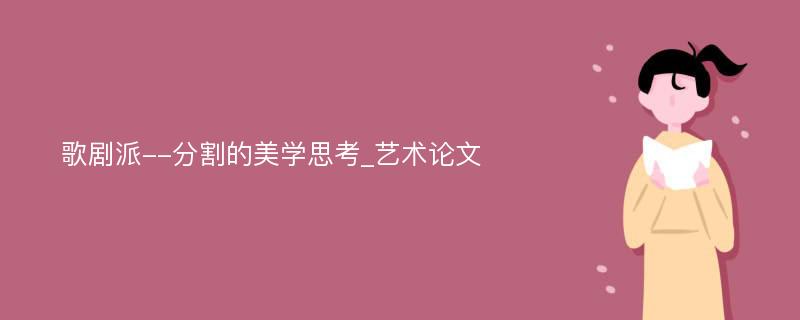
戏曲流派——分割性的审美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派论文,戏曲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我国戏曲的流派问题耐人寻味。有人称流派的繁盛为戏曲兴旺的象征,有人对当今戏曲界缺乏响当当的流派而扼腕叹息,也有人对当年曾使多少观众为之醉心的流派如今却“流派不流”而焦虑万分。遗憾的是,如同戏曲的众多流派只是停留在浅层次的某些特征的呈现上一样,戏曲流派的讨论大多也只是泛泛地分析某一流派形成的历程及其艺术上的表象特征,并未对我国戏曲流派问题进行宏观的理论构建。
“流派”,这是一个含义比较狭窄同时也比较模糊的概念。它的本义应是地理学或水利学对水系的一种称谓。因此,它应是指上有源头、下有归宿的河流的流程,引伸到戏曲艺术上来,应是指一种艺术风格衍变的流程。作为综合艺术的戏曲,这种风格的衍变在编、导、演、音、舞、美诸方面均有明显而充分的表现。任何一种“只取一点,不及其余”的艺术实践或理论概括,难免给人偏狭的感觉。不少人谈及戏曲流派,不但把戏曲母体撇到了一边,而且把戏曲其他诸多因素(如剧本、导演、舞美等)也都撇到了一边,剩下的仅仅是演员的表演。到了戏曲流派发展的鼎盛时期,更有人把构成中国戏曲表演特征的“唱、念、做、打”进行肢解,独取其“唱”作为形成流派的唯一标准。目前京剧界、越剧界流行的一些流派,除个别流派以外,实际上只是唱腔艺术的特征区分。
非常有趣也值得人思索的是,别的艺术门类,大凡形成某种特征者均称之为“风格”。如果谁把贝多芬、萧邦说成是某一作曲流派的代表人物,那是要贻笑大方的,甚至会给人贬低大家的感觉。即使中国戏曲,直至今天,谁也不会把关汉卿、王实甫这样的戏曲大家说成是关派、王派的宗师。但是,关、王的剧作风格却是谁也不能否认的。读他们的作品,不能不强烈地感觉到一种不但体现在剧作中同时也潜藏在作家人格中的“风骨”精神和文化品格。这种“风格”,在我国漫长的文化发展长河中,也是能找到承继的先师的,但他们之间的继承关系,决不仅仅是某些技巧或笔法的因袭,而首先是一种精神品格的传递。
细细琢磨,“风格”和“流派”这两个词在词义上确实有一些微妙而本质的差异。它们之间的相同处是都想表述艺术的某种特征,不同处是后者表述的是艺术局部的表象特征,前者表述的不但是表象,而是透过表象揭示了艺术本身深藏的意蕴和创造者倾注于作品中看似无形却又无处不显的文化品格。衡量一部艺术作品、一种艺术风格的品位高下,权威的座标系应该在这里去寻找。
二
严格地说,现代中国戏曲的所谓“流派”,其实只是某些剧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演员的唱或演的风格呈现。
有人说,流派的出现是剧种成熟的标志,此话不无道理,但不全面。我认为,大凡一个剧种处于上升发展同时又不太成熟的时期,才会呈现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流派纷呈的局面。在这里,“上升发展”和“不太成熟”是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中国戏曲几百个剧种中,形成流派之多莫过于京剧和越剧。京剧自形成之初始,迄今已近200年,其代表人物泱泱难数,但它的创始人程长庚和其后曾名播朝野的谭鑫培均未被人承认为“程”派或“谭”派。谭派的最终被人认可始自谭富英,这才有人追溯到谭派的祖宗——谭富英的祖父谭鑫培。那是因为,在程长庚、谭鑫培时代,京剧虽然处于上升时期,但尚未发展到产生全国性影响的阶段。清末以后,京剧昂首阔步地从宫廷走向民间,走向大众,走向全国,这才呈现出了中国戏曲表演史上史无前例的发展势头,才逐步出现了梅、程、尚、荀、马、谭、杨、奚等四大名旦和四大须生,以及在他们之前或之后的高庆奎、余叔岩、杨小楼、言菊朋、金少山、郝寿臣、周信芳、裘盛戎、张君秋等诸家。上述各流派,除个别流派以外(如杨小楼、周信芳),为人称道的主要是唱,也许正因为此,杨(小楼)派艺术为人熟知的程度就大不如其他各派了。所有这些名家,时人均以其姓冠名其派。唯独周信芳却以其艺名麒麟童称之为麒派,这多少也体现了海派艺术不甘墨守成规的倔傲。麒派并不是以“唱”为唯一标志而成派的。麒派的特点首先是表演,然后才是唱。这与其他京剧流派似乎都不同。但是,平心而论,即使在京剧流派蜂拥而起的年代里,就京剧表演艺术本身而言,恰恰是不太成熟的时期,起码与昆剧相比,它明显地呈现出形态的不稳定性和可塑性,这才给诸多名家提供了发展创造的余地。所以,成熟至于衰化的昆剧,与梅兰芳先生同时代的代表人物俞振飞以及传字辈表演艺术家,就其表演造诣而言,称之为“派”决非谀词,然时人却并不冠之“俞”派或“周”(传瑛)派。原因何在?很简单,昆剧太成熟了。
京剧的流派还有一点值得玩味的地方是,它仅止于张(君秋)派,此后再也没有出现公认的流派了。原因倒也不是以后再也没有出现杰出的表演大家,而是京剧也同昆剧一样,变得十分的成熟乃至于退化了发展的功能。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越剧中。所不同的是,当京剧的流派诸家已名震遐迩之时,越剧的“的笃班”还在浙江农村的草台上用极简陋的行头、极简单的板腔唱着一些乡民们所喜闻乐见的才子佳人戏。也许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小剧种却蕴藏着顽强的生命潜能。人们用惊奇的甚至是调侃的目光看着她们登上了十里洋场的上海舞台。当时上海滩上的市民,尤其是那些有地位的达官贵人,总是习惯地把京剧称作大戏,把越剧称作小戏。在这次历史性的大转移中,当时的代表人物,如姚水娟、施银花、王杏花、赵瑞花、筱丹桂、屠杏花、马璋花等,在越剧发展史上无疑留下了英名,但时人并未冠之以派。其原因非他,恰恰是因为当时的越剧正处于相当于京剧的陈德霖、王瑶卿时代。陈德霖、王瑶卿孕育了梅、程、尚、荀四大名旦,姚水娟、施银花这一代越剧前辈也为后来蔚蔚大观的众多越剧流派的出现充任了铺路石子。越剧真正进入大发展时期是40年代,在那种处于明显上升且又不甚成熟的混合形态下,诞生了袁(雪芬)派、尹(桂芳)派、徐(玉兰)派、范(瑞娟)派、傅(全香)派、王(文娟)派、陆(锦花)派、张(桂凤)派、戚(雅仙)派、毕(春芳)派等等流派。与京剧的流派发展史十分相似的是,越剧的流派也止于50年代的金(采风)派和吕(瑞英)派。那是因为,到了50年代中期,越剧已发展成仅次于京剧的全国第二大剧种,剧种的风格基本定型,于是,成熟的同时透显出了发展功能退化的趋势。
三
50年代以来,京剧界和越剧界均未出现独树一帜的新的流派。最近十几年来,在京剧界更是出现了“无旦不张(君秋)”、“无生不杨(宝森)”、“无净不裘(盛戎)”的令人忧虑的现象。无独有偶,越剧界的年轻小生也竞相学尹(桂芳),一时间尹派鹊起,也大有“无生不尹”的架势。面对这么多的张派青衣、杨派老生、裘派花脸、尹派小生,人们闭眼听听,个个都有点像,睁眼看看,很少有人学到家。
毋庸置疑,张君秋、杨宝森、裘盛戎、尹桂芳的唱腔艺术的成就的确已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但是我们对流派的价值取向仅止于“唱”这一点,则不但是对“张派”、“杨派”、“裘派”、“尹派”艺术的误会,更是对戏曲艺术的误会。这里既有演员误学的问题,也有观众误看、舆论界误导的问题。这种分割性审美思维定势,正是反映了长期以来我国戏曲理论对戏曲艺术总体规律性把握的漠视或忽视。
中国戏曲源于歌舞,我国古代戏剧理论史上首先出现的便是以“曲”的作法和唱法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人称“曲学体系”。这种理论体系根深蒂固、影响深远,虽然在它之后中国戏剧理论史上也出现了以李渔为代表的把戏曲作为综合艺术进行研究的新的理论体系,但是“曲学体系”仍然显示出了它的强大的生命力。戏曲以表演为中心,表演以唱为核心,传统的审美定势对戏曲这门综合艺术进行了人为的分割。到了本世纪初期,这种人为的分割随着科学传媒手段的发展竟达到了空前偏执的程度。当时,戏曲进入了唱片时代,随着那一张张留着演员美妙动听的声腔的唱片进入千家万户,原来就习惯于“听”戏的戏迷们离开剧场也得到了同样的陶醉。于是,声腔艺术的影响越来越得到张扬,相应之下,表演体系中的“念、做、打”就明显受抑。
表演艺术的乖张造成了剧本艺术、导演艺术的萎缩,于是,关汉卿的后人只存了个“打本的”名份,李渔的传人只成个“说戏的”人。而声腔艺术的空前发展又导致了表演体系的畸型分割,由此造成的影响波及至今,这从当今京剧界麒派老生、荀派花旦、文武老生、架子花脸后继乏人的现象中似可见一斑。去年纪念梅兰芳、周信芳两位大师诞辰100周年,有人称这次纪念活动是“扬梅抑周”,其实这决不是人为的“抑”,恰恰是由于麒派艺术以“做”见长而遭致历史的不公正的奚落的结果。
其实,中国戏曲流派艺术的状况是极其复杂的,决不能一概而论。有的以“唱”见长,同时在“做”的方面也具特色,如马连良、程砚秋,有的以“做”见长,在“唱”的方面也具功力,如周信芳、荀慧生,有的已融“唱、念、做、打”于一体,形成了实际已超越“流派”概念的表演风格,如梅兰芳;当然,也还有相当多的确实难以唱见长、别无甚特色的流派。遗憾的是,多少年来,戏曲理论界在审视和归纳流派现象时,总是有意或无意地把“唱”作为流派标志的最主要甚至唯一的因素。理论的误导导致艺术实践的偏航。即如人们常说的“梅兰芳体系”,与梅先生的艺术实践相比,我们也明显地感觉理论研究上的滞后和苍白。
也许在这个问题上越剧表现得更为突出。平心而论,从表演角度来讲,越剧的“做、念、打”并未形成明显的剧种风格,演员个人也未见在这些方面有明显特色乃至可称作流派者,倒是它们唱腔却极尽戏曲女声声腔清丽婉转的韵致,徐疾适中,音域适度,既雅且俗,很容易被广大群众所接受。这是越剧能够成功地向全国发展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它的沉重的包袱,这几年江、浙、沪举行的一些越剧流派演出会,实际上只是流派演唱会。很多学流派的年轻演员,或摹演乃师的成名作,或把前人代表作的著名唱腔移植到新戏中,于是人物形象不见了,音乐形象不见了,剩下的仅仅是某派唱腔。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流派”含义的偏狭,并且在相当程度上误导了越剧艺术的发展。一些原本可以闪光溢彩的年轻演员成了录音机的奴隶和流派代表人物的替身,这抑或是当今越剧界最大的悲剧。
作为唱腔,京剧和越剧在经历了100多年和几十年的发展后,到了本世纪50年代,可能已达到极致,谁还想在这条狭小的通道上自成其派,几乎已不可能了。但是人们偏偏还要把我们的演员往这条路上引,于是,可悲的事情发生了:时间又过去了半个世纪,留给我们的则是新流派的一片空白。
四
在我国京剧流派中,还有两个人们熟知的大的派系,曰:京派和海派。老北京把到剧场欣赏京剧称作“听戏”,上海人称作“看戏”。“听”和“看”,虽说一字之差,却反映了欣赏习惯的不同,也反映了欣赏者所处文化背景的不同。作为这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对应物,必然产生了风格迥异、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的流派。
在古老的中华民族的版图上,上海是一片奇异的土地。它面对浩瀚的太平洋,背负广袤的神州大陆,当新世纪的海风迎面吹来,当黄浦江畔矗起了一座座巍峨的银行、洋行、钱庄之时,它背后的大陆却仍然沉睡在农村自然经济的摇篮之中。东西方文化的碰撞首先在这里溅起了刺目的火花。反映在戏曲领域中,先是出现了影响颇大的麒派和盖(叫天)派,接着又出现了煞是好看的连台本戏。所有这些戏剧,决非只带一副耳朵去“听”就行的。传统意义上的流派在这里遭到了强劲的冲击。上海人也真有意思,50年代捧出了一个擅演包公戏的李如春和一个擅演红娘戏的赵燕侠,80年代又捧出了宋长荣、胡芝风,而他们均非以唱为专长。即使是曾拜于梅门之下的弟子,只要在上海呆久了,也会给人“变味”的感觉。
很长一段时间里,京派和海派是作为我国京剧界的两座对峙的大山而矗立在我们面前的。遗憾的是,桀骜不驯的海派表现出来的这种张力,最终还是没有能突破传统审美定势的控制力,因此,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的京剧乃至于整个戏曲仍然在传统框架中蠕动。人们在仍然陶醉于对传统流派的欣赏之余,还不时地期盼这种狭窄含义上的新流派的出现。然而,历史已不断昭示我们:这也许是一种永远不会实现的空盼了。
关于中国戏曲的流派问题,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明显的缺憾。对历史的缺憾人们总是抱着宽容的态度予以认同。这是一种无奈的认同,也是一种阶段性的认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必将成为历史链环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样,随着时代的进步,历史也必将证明,任何一种把历史链环中的一环视作永恒的凝固的想法,无疑是思维上的一种形而上。谁能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看戏曲,这不是时代前进的标志呢?
历史已不会重复过去那种分割性的审美思维。未来的观众将更注重对戏曲艺术浑然一体综合性的欣赏。那种仍然一味地醉心于某些唱腔或技巧代代因袭的欣赏习惯,并企图以此为戏曲艺术的最高评判准则,在当前只能成为世纪末的无可奈何的悲叹。时代正在呼唤和催生新流派的诞生,而这种流派比之传统意义上的流派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和更宏广的外延。它将诞生在明天。我相信,当明天新世纪的曙光照临我们戏曲舞台上时,它必将呼之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