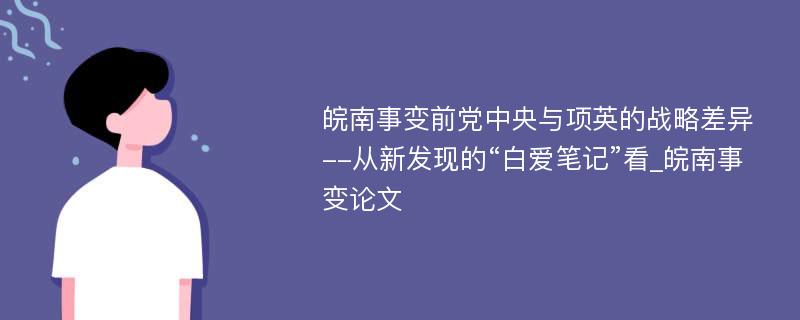
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与项英的战略分歧——从新发现的白艾笔记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皖南事变论文,中共中央论文,分歧论文,战略论文,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5)04-0105-09 笔者在整理新四军史料时,发现一篇没有披露的白艾①笔记,标题为《皖南事变前,周恩来和项英、叶挺、陈毅、袁国平的对话》(以下简称“对话”),记录了周恩来与项英、叶挺、陈毅、袁国平关于新四军发展战略的谈话,对于探讨中共中央与项英在战略方针上的分歧以及皖南事变的发生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笔记内容与记录时间 《皖南事变前,周恩来和项英、叶挺、陈毅、袁国平的对话》全文如下: 周恩来同志到云岭村。叶挺说:“这里就是云岭村,这里只住军法处和副官处。”指着村上的鸣凤石说:“老乡叫簸箕石。”袁国平说:“像个大簸箕,口向村里。云岭村富商地主多,迷信说全靠大簸箕的风水好,向里扒。”周:“你们新四军军部的风水可不好,三面是国民党的军队,住在国民党的大簸箕里。”陈毅:“弹丸之地。”项英:“就这人家还不想给哩。”陈:“你这是江南特殊论,捆住自己的手脚,听从国民党的摆布。不欠阎王债,不怕鬼打门。胸无城府,以诚待人。一团、三团都给你调回去了,给个六团还扣下一个营②,你这是执行中央方针?”项:“六团主要骨干都给了。”陈:“好吧,叶飞去了,再加陶勇、王必成,我也能把这盘棋走活。”陈再跟他吵架。项:“从油山③吵起,见面就吵,每次来军部,别处不睡,偏睡我这里,跟我吵。”陈:“这个人,老保守,在油山,环境紧张,他把全部金子、银洋捆在自己腰里。我说,你分散分散吧,小心坏蛋看上你,谋财害命。他说,这是党的财富!现在他又把上千干部,延安来的、前方来的,捆在自己腰里,进了他的教导大队,就难出去啦!”项:“老实说,六团干部给你,我还不放心,你老兄要他们钻到苏州、上海去打游击,弄不好倾家荡产啊!”陈:“周副主席、叶军长做证人,我立下军令状,要是我杀进苏州、上海去,打好了,你军部就挪窝,到苏南茅山来。”周:“这个问题上,我要同陈司令坐在一条板凳了。军部到苏南去,比住在国民党的簸箕里自由。可以执行中央的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袁:“华北和华中不同,华中到处有国民党正规军,一发展就要摩擦。”陈:“苏南冷欣、苏北韩德勤两个反共顽固,我们和他们摩擦不少。”项:“他就爱捅蒋介石的马蜂窝。同志哥,不要捅垮了统一战线啰!”陈;“我在苏南捅了八个月的马蜂窝,统战牢固的很。我穿的军装,布比你身上的好看。我送来的税款收到?有不少是蒋介石七大姑八大姨送的。项英同志,你准备什么时候大发展?”项:“等日寇打通浙干(赣——笔者注)线,国民党战区撤退。”叶挺:“白等了一年,错过了多少向敌后发展机会!”陈:“等待,这叫守株待兔,可别鬼子未等来,却等来了一豺狼。”陈:“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敢独立自主,就是陈独秀。”周:“列宁在两个策略中指出;无产者必须掌握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我们要掌握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就必须大发展。内战时期,我们党被困在山头上,没有成为全国范围的大党,没有能和全国各革命阶级广泛合作,没有直接领导他们。现在抗日形势让我下山了。毛由井冈山下来扩建江西苏区,五次反围剿提出打到浙东、安徽、江苏一带,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大发展成全国范围的大党,这是一个战略任务。关系今后革命成败,不能再搞占山为王了,要放手发展。项英同志,你的做法很奇怪,一方面处处向国民党让步,把蒋的演讲编进新四军的政治教材,把党领导的新四军称为统一战线的军队;另一方面,对群众,对朋友,却缩手缩脚,不敢发动争取。周子昆,你是叶军长的老部下,只让他和国民党打交道,参谋处都不和他住一起,叫他指挥谁?④可党中央尊重他,决定参加中央军委新四军分委会。希夷,敌人最怕我们党的团结。抗日战争,蒋介石对红军的政策是借刀杀人。我们的方针是向日本收复失地,独立发展。” 中央的五四指示,1940年5月4日,毛泽东起草指示,指出确定苏南的陈传达,皖南的项传达全体干部。“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的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各地区虽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发展,均应该发展。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限制。在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要饷,独立自主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党领导抗日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一年内扩大十万人枪。”⑤陈给项的信:“建议军部率皖南全部主力东进苏南,我们全部挺进苏北,和南下八路军打成一片。第二步,军部到苏北建立巩固的华中根据地,不是背靠国民党,而是背靠八路军,然后再南下浙江、江西、福建,则有恃无恐,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此段文字不是对话——笔者注) 项:“什么西起南京,南到杭州?那是蒋的老窝,去一、二个支队犹可,军部去,大闹天宫,鸡也飞了,蛋也打了。”叶:“你迟迟不向北发展,老让我军替国民党守大门,讨嘉奖。你原来一心想向南发展,到黄山、天目山、武夷山,打自己的天下,搞自己的山头,建第二个延安。”叶:“子昆,你和北伐时的周营判若两人啊!那时很勇敢,听说你被王明路线吓怕了,差点杀头,给枪毙?以后宁可在政治上犯自由主义,不敢在组织上顶党委书记。” 突围至星潭只有敌两个营,一个营被我打垮,营长身死,结果未按叶挺的指挥,延误战机。全军覆没。真实的历史事件如何贯串虚构的人物故事?(此段是白艾的感慨而发——笔者注) 白艾于2003年逝世。2013年,白艾夫人呼冉将其9个笔记本交给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内容非常丰富,包括解放战争中在华东野战军的战地日记、采访徐向前元帅的笔记等等,弥足珍贵。此“对话”是用铅笔记在一红色塑料硬皮笔记本上,有个别字系补写的;题目则是钢笔的笔迹,显示是后加上的,却没有记下明确的时间。白艾13岁参加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做抗日宣传工作。彭雪枫部活跃在豫东,开辟豫皖边区抗日根据地。白艾不可能身在新四军军部的云岭,不在对话现场,故不是当时的日记。 为了考证“对话”的记录情况,2015年4月30日,笔者赴北京军区干休所拜访呼冉,请她谈谈白艾笔记本中“对话”一文及其他笔记内容的记录背景。呼冉回忆:1968年秋白艾“解放”出来后,北京军区政治部李宣化将军调白艾来政治部创作室工作,与魏巍在一起。后来粟裕叫他过去,帮助写东西,住在粟裕家里一段时间,该笔记本上有关内容是粟裕的回忆记录。另外,呼冉说白艾没有围绕皖南事变创作过文学作品,当时的政治环境也不适合公开谈论。粟裕夫人楚青同志1987年7月回忆:1976年夏,粟裕重病初愈,决心把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战役、战斗写出来,“他讲述,我们记录整理”,协助整理过资料的前后有24人,其中有白艾⑥。检视红色笔记本有关内容,可确定为摘录的资料有:陈毅同志谈八一起义情况1952年6月14日(78.6.9);七一九一三后陈总讲话有关南昌起义部分(4月);陈总谈三年游击战争;朱总谈南昌暴动若干问题;朱总讲话:八一起义向南进军失败以后(57年11月在政治学院,4月11日);《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会师》战史部(77.4.30);《南昌起义》(77.7)。白艾听录音、做记录、讨论文稿的笔记有:粟裕同志谈抗日先遣队(78.10);粟裕同志讲三年游击(78.6.29);楚青同志谈八一井冈山一文的意图(4月12日);4月11日听录音;《千流归大海》二稿情况,几个待解决的问题,须要请示粟总;粟总的录音稿和朱总的谈话记录等。其中,《千流归大海》是讲朱德、陈毅、粟裕南昌起义后的战斗经历,后题目改为《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分别在1978年12月1日⑦和1979年5月公开发表⑧。这可证实白艾在1978年记录并整理了粟裕回忆资料。查阅1988年初版的《粟裕战争回忆录》目录:第一章从枫木树脚谈起;第二章南昌起义前后片段;第三章激流归大海;第四章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第五章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第六章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第七章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与笔记本内容相互印证,说明白艾协助其他同志参加了南昌起义、激流归大海、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等章节的编写工作。至于后来不再整理回忆录的原因,楚青回忆:“文革”结束后,粟裕认为写回忆录的事不用太急,故讲述和整理工作慢慢进行。1981年2月1日,粟裕突发脑溢血之后,帮助整理材料的几位同志陆续回到其他工作岗位⑨。故该红皮笔记本上内容只是白艾在1978年为撰写回忆录所做的工作笔记。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七章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谈到了粟裕对皖南事变之前项英错误的认识:“一九三九年二月下旬,周恩来同志亲自到皖南来对项英同志做工作”,“他(项英)常常屈服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压力而不断动摇”;“项英同志不仅不敢理直气壮地予对方(指顾祝同顽军)以反击,反而责难我们破坏统一战线”;“以陈毅同志为代表的广大指战员就是这样坚决地抵制项英同志的错误主张”⑩。这是党的高级将领较早公开出版的回忆录,披露了很多以前不便公开的观点,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粟裕批评项英错误无疑是基于亲身经历而发。 红皮笔记本内“对话”之后是一则笔记,题目是陈总谈项英(节自九一三后揭批林彪的老同志座谈会),也无记录时间,内容是:“项英的机会主义表现在统战只联合不斗争,害怕到敌后作战,恐日病,他在军事上机会主义是反对到敌后打游击,强调正规化,反对游击战争;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反映到军事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搞精兵主义,反对数量,以一万人对付顾祝同30万人。反党反中央,可耻失败最后身败名裂。”摘录的用意显然与“对话”相同,重点是批评项英的错误主张,与粟裕战争回忆录的观点吻合。结合“对话”中包括1940年5月4日毛泽东的电报、陈毅致项英的信、皖南事变星潭突围等,显示白艾是在为撰写新四军早期粟裕的战争经历做资料准备。解放战争期间,白艾是华东野战军随军记者,长期跟随司令部奋战在前线,与陈毅、粟裕等同志都有接触。这也是粟裕邀请白艾整理资料的渊源所在。“对话”内容具体详细,符合当时的情况,只有在场的人才能知悉。 粟裕确实是“对话”的现场人物。“周恩来同志来到云岭村”点出了“对话”的地点。1938年8月2日上午10时,新四军军部移驻安徽皖南泾县云岭村(11)。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总结抗战经验,强调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突出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委托中央军委副主席、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到新四军军部传达全会精神,确定新四军发展战略。1939年2月16日,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偕同新四军军长叶挺,离开重庆。2月23日下午15:30分,周恩来一行人抵达新四军兵站驻地章家渡(12),项英等率众迎接至云岭。2月26日,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等人从前线赶到云岭(3月28日离开)。3月3日,周恩来召集新四军军部和支队负责人在军部召开会议(13),持续了四、五天(14)。3月14日,周恩来离开云岭村。5月初,到重庆;7月,回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8月底,赴苏联治疗摔伤的右臂。1940年3月底,回到延安。5月31日,到重庆继续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至皖南事变发生(15)。故皖南事变之前,周恩来唯一一次来云岭即在1939年2月23日—3月14日。在这期间,粟裕参加了军部会议,由于他的地位次于周、叶、项、陈、袁等,不适合主导讨论意见,又目睹了此次争论,在回忆皖南事变前后新四军发展战略时,回忆了此次对话,由白艾记录下来,作为撰写回忆录的史料。 粟裕等在场同志都已经作古,生前也无人公开此次会议讨论的内容。20世纪80年代,关于皖南事变的新四军史料才逐渐披露,部分新四军老同志也陆续回忆了自己看到、听到的云岭新四军军部的故事。安徽省军区政治部曾组织老同志回忆新四军在安徽战斗的经历,其中一篇文章记载:“一天晚上,新四军首长会议刚刚结束,周恩来又开始和项英谈话。项英强调‘江南特殊’,说什么江南不比延安,不宜自由行动。如要发展,就必然和蒋介石发生摩擦,国共合作必然破裂。所以,江南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听从三战区的命令。‘这就是关键’,周副主席忽地站起来,铿锵有力地说道:‘迅速发展抗日力量,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任务,关系着今后革命的成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在党中央统一指挥下放手地发展。’接着,周副主席批评了项英,指出:‘一方面,处处向国民党让步,甚至把蒋介石的演说、宣言编进新四军的政治教材,把党绝对领导的新四军称为统一战线的队伍,还要听从三战区的命令;另一方面,对群众,对朋友,却缩手缩脚,不敢发动,不敢争取!你们甚至连叶挺军长也不想要啊!’周恩来一边说着,一边微皱双眉,在办公室里来回踱着,语气变得更加严厉了,他说:‘也许,我的话说重了,国民党和日寇都怕叶挺指挥新四军作战,你们可就是不给他指挥权,连参谋处也不让和他住在一起,叫他指挥谁啊?可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很尊重叶军长,中央已经决定,叶挺同志参加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今后军分会会议,一定要通知叶挺同志参加。”(16)文章没有说明回忆者的姓名,记忆不是很具体详细,是属于概括性的表露周、项谈话之意,与“对话”吻合,可以作为一个佐证,证明“对话”不是编造的。“对话”发生在周恩来主持军部会议期间,应在3月3—8日的某天晚上。时至今日,粟裕的回忆、白艾记录的“对话”可以作为一篇有价值的史料来评析。 二、中共中央华中大发展与项英株守皖南的战略分歧 周恩来借云岭地形说新四军军部风水不好,住在国民党的大簸箕里,说的很形象,也意有所指。新四军军部朝北面对长江沿岸的繁昌、铜陵、贵池一带,是日伪军占领区,南面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驻地,东西两侧有国民党军队布防,只能在横宽约百公里,纵深约五六十公里的狭长区域活动,处在四面受围的险境。故陈毅批评项英窝在弹丸之地,过分相信国民党,胸无城府,把新四军主力“捆在自己的腰里”。“对话”并不复杂,揭示了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周、叶、陈希望新四军能东进、北上,大发展;而项英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株守皖南,这是关于新四军发展战略的一次大争论。 这涉及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项英是否执行党中央东进、北上的计划,有无“三山计划”(黄山、天目山、武夷山)?笔者结合“对话”内容,征引相关史料,做进一步的探讨。 新四军要生存发展,战略方向是核心。周恩来主持会议与军部、支队负责人多次讨论,确定了新四军“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有阵地”的方针(17)。这符合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1938年5月4日,毛泽东致电项英:“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探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18)要求新四军主动、积极地到苏北、苏南创建根据地,深入敌人后方,大胆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独立自主地抗战。正如周恩来所说,在抗日中发展壮大,多抢占地盘、人、枪,在华中和八路军连成一片。共产党军队不能龟缩在局部,要吸取井冈山的教训,不占山为王,以免被困在山头上,而是通过发展来掌握抗战的领导权,做全国性的大党,这是关系到战后夺取全国政权的大战略。1939年,党中央逐步实施发展华中的战略,指示“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区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希望东南局及新四军领导同志顾全全国局势及华中之重要,抽调大员及大批干部到江北。”计划从延安、华北、新四军抽调县营以上干部到江北,由项英或陈毅主持指挥部,建立新队伍(19)。 项英则有南进的想法。1938年6月15日,项英致电毛泽东:“军部及三支队位置于南陵至泾县间山地整训队伍,以大力争取这一带群众,准备以太平(不含)与泾县、青阳、南陵之间山地为根据地,后方已移至这一区域内。如敌前进,即可依据这一地区在敌侧翼活动,并在某种情况下,即可派一部队伍到天目山脉与仙霞山脉发展游击战争。”(20)1938年6月23日,项英复信陈毅:“我们计划在皖南要建立一个根据地,这在战略上非常重要。将来在战争形势变化时,我们即可依靠这一支点向皖南各县发展,以及利用机会争取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故部队不宜全部出动。目前除你及二支队主力出动,其余暂留此地帮助建立根据地,以备将来成为发展的基本力量。”(21)项英打算以皖南为中心根据地,仅以偏师活动于苏南,等待时机向南方赣、闽发展,这是他把一支队第一团、三支队第六团从苏南调回的主要原因。 1963年编写的《新四军抗日战争史初稿》及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岳星明最早提出项英有“南进计划”(22)。有学者不赞同:“这个计划的先决条件依据是什么?这个说法出自何处,根据又是什么?却没有人能讲清楚。”(23)著名军史专家王辅一引述原新四军军部通信科科长胡立教同志之言,说他不知道项英有什么“三山主义”的计划或说法。“史学界遍查史料,至今也未查出三山计划”。“有人说成是搞三山计划,有意保存实力,不向敌后发展。这是站不住脚的”(24)。 周恩来主持军部会议,与会各人的分歧和争论,会议应该有记录,可惜新四军军部档案在皖南事变中销毁,不可能发现项英南进系统主张!“对话”揭示了项英有三个想法:第一,新四军向东作战,必将与国民党军队发生摩擦,会破坏统一战线。第二,新四军到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敌伪核心区域作战要冒被消灭的危险,是大闹天宫,会鸡飞蛋打。第三,待日军打通浙赣线后,国民党第三战区撤走,新四军军部就可以在皖南之南大力发展。基本点出了项英株守皖南的核心思想。虽然,项英在军部会议上同意了新四军的主要发展方向是长江以北,只应巩固已取得的阵地。但是不是真心接受呢?叶挺批评项英有“黄山、天目山、武夷山”的想法,则是直接的现场证言,有很大的历史价值。“建第二个延安”更含义深刻,直指其有“政治野心”,欲与延安分庭抗礼,目无中央。 生死之交的亲密战友陈毅最了解项英,曾多次批评项英的“三山计划”。1941年5月17日,陈毅在盐城新四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项英对形势估计不对,坚持南进政策,坚持黄山计划、天目山计划、浙西计划。”(25)1944年夏,陈毅在延安汇报华中工作时谈到项英“毫无根据地提出天目山的计划、浙江计划、黄山计划”;“提出所谓具有中国伟大战略前途的坚持江南计划,企图与华北、华中鼎足而三。”(26)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科长汪海粟说:“项英是有南进的打算的……陈毅最了解他,说他是‘守株待兔’。中央也讲过他‘株守皖南’。项英为了守皖南之株,待日寇打通浙赣线之兔,曾经把老一团从江南调回,也曾要求把四、五支队南调,陈毅向他要干部,他一个也不舍得给。项英坚持他的主张,原因是多方面的,至少有三条:一、他害怕到平原和水网地区流动作战,到江南或苏北,不及山区驾轻就熟,不及皖南安逸。二、中央五四指示,要求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的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项英对中央这个专给新四军的指示,简直不敢设想,不能接受。中央指示皖南由项英传达,他置之不理,交给袁国平传达,一交了之。三、项自视甚高,在皖南的大小会议上,很少提到中央,从来不提毛泽东。他是想,一旦日寇打通浙赣线,黄山、天目山沦为敌后,仙霞岭、四明山也变成沦陷区,皖南部队就可以南下打开一个大局面,那时候你老毛就无话可说了。”(27) 王辅一认为项英执行了中央“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说项英三年来对中央一贯阳奉阴违,反对向北和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设抗日根据地的讲法不符合实际情况(28)。有学者认为项英基本上执行了党中央关于向北发展的方针,与中央的指示有差别(29)。向南发展并不是项英自作主张,项英没有抵制发展华中的战略(30)。1940年5月之前,党中央发展华中不意味着放弃皖南,“新四军能否向南发展,向皖浙赣大活动,抑或过江向北,要看今后形势来决定。”皖、浙、赣、闽交界处,只是一个退路(31)。视皖南为防御的一个根据地。“对话”展现了项英的真实想法:“去一二个支队犹可”,军部去南京、杭州等地就是大闹天宫,内心并不赞同党中央东进、北上计划。归根结底,项英在对抗战形势的分析和判断方面出现了重大错误。项英即使没有系统的“三山计划”,也有自以为高明的“南进”想法。白艾笔记再次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注解。 王辅一强调不能把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的损失归咎项英一人,有一定道理。他认为党中央、毛主席对形势过于乐观,对时局的危险性估计不足;对北移的态度变化大,要求走的决心下得太迟;对苏北、皖南部队的行动协调不够等等方面“失误是明显的”(3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也有情绪激动、看法不周、思想反复的时候,认为蒋介石大举剿共不可能,有乐观的估计,有在皖南再拖一两月,不立即北移的主张(33)。他们强调的这些“失误”都是1940年下半年随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在判断上的“反复”。我们还应看到1940年5月之前,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已经非常明确。1939年11月,中原局书记刘少奇自延安抵达皖东,经过调查研究,进一步明确苏北是最有利、最能发展的地区,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34)。1940年1月29日,毛泽东致电项英:“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35)4月21日,陈毅、粟裕致电中央:“应先放弃皖南,集中力量发展苏南。”(36)5月,党中央派黄克诚率八路军一部南下皖北执行开辟苏北的任务。同时,发出“五四指示”要求项英率部北上。陈毅在接到“五四指示”后精神振奋,迅速向干部传达贯彻,并请示中央:“要求中央批准将苏北叶、张两部仍拟以一部南调应急,同时请中央即电项英东移,宜饬大行李及重要资材东进,不要再迟缓,要根本放弃挺进皖东南的下策。”(37)5月26日,中央指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38)。陈毅、粟裕派了三个团接应军部,将电台呼号、通信联络都准备好了,项英再次拒绝北移(39)。陈毅派江南指挥部民运科长曾如清急赴皖南,面请项英率军部东进到茅山根据地,陈则率领江南指挥部主力部队渡江北上,与南下的八路军会合,待苏北打开局面后,军部再迁到苏北去,建立联成一片的华中抗日根据地。这个建议遭到了项英的漠视。1940年6月,蒋介石部署,由顾祝同、冷欣、韩德勤、李品仙所部从南、北、西三个方面围攻新四军的阵势已成,由于项英的坚持,我皖南、苏南部队已无法集中(40)。国民党军队做好布防之后,不管是选择什么路线,新四军军部转移都会遭受损失,故在1940年5月之前,是新四军军部东进苏南有利时机,项英却错过了。 皖南事变前夕,形势已经很紧张,毛泽东在斗争策略上出现判断反复,也是正常现象,谁都不能对未发生的事洞若神明,评价历史人物不能揪住细节来否定整体思想。党中央和毛泽东1939年发展华中的战略已经很清晰。如毛泽东在1940年12月26日所说:“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41)项英是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军部的作战安排,什么时间转移,他有处理事务的主动权。项英只是部分执行东进指示,也是显而易见的。项英对“五四指示”的批评非常不满,1940年5月9日向中央报告:“为了保证中央方针与党及革命的利益,我郑重请求中央,立即派一政治局委员到新四军及东南局负领导之责。……应公开宣布撤我之职,是属必要。”12日,又报告中央:“我之领导已有路线错误和不执行中央方针……我当然不能继续领导,而且无法领导,为党的利益,应公开宣布撤职。”“中央责成我传达,不能负此责,既不愿杂以我的意见或辩论,影响中央指示精神,又不能静默不言,非我口是心非,为党的利益,故请袁传达。”(42)23日,党中央致电东南局和军分会:“你处错误不是总路线,而是抗日战争与统一战线中某些个别策略问题错误。”希望他“继续担负东南局及军分会书记之责”,“对政治上及策略上的不同意见,望告中央,对中央指示仍由项英同志传达”;“现当时局严重转变关头,全党同志应当团结一致。中央号召东南局及新四军全体同志在项英同志领导下,亲密团结起来,为执行中央路线,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而奋斗。”(43)党中央顾全大局,维护新四军内部的团结,并没有向全党宣布项英的错误。叶飞曾坦承当时绝大多数新四军指战员并不了解项英与中央的分歧,他是与刘少奇谈话后,才明白的。刘少奇告诉他:“现在中央还在争取教育项英,所以对他的错误,目前在党内还不公布。争取项英同志到江北,执行中央的路线。”(44)党中央对处分项英显得犹豫和谨慎,没有及时调项英回延安,错过了调整新四军领导班子,落实军部尽快转移的战略部署最后有利时机,是很大的失误。 皖南事变发生后,党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批评项英犯了“机会主义路线”,与张国焘并提(45);党内部分同志批评项英“执行了王明的逃跑主义路线”,拔到了“路线”高度,确是过激之辞。王辅一评价项英:“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犹豫动摇,处置失当,对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受严重损失负有责任”(46),淡化了他在事变之前的严重错误。项英为中国革命作出很多贡献,不能因为皖南事变一笔抹杀其功绩。他为人正直,但也保守、固执,不积极执行北上计划,是有思想根源的,其南方山区游击战争的经验已经不适应抗战形势,缺乏远大的战略眼光,没有深刻认识到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只考虑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看到的是江南局部,而不是中国共产党抗日大发展。如果他能接受老友陈毅的主张,坚决执行党中央决定,命令军部主力在1939年东进苏南,留一部在皖南,那么发生“皖南事变”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或者说损失不会那么惨重。战略错误是根本错误,会贻误时机,导致战术选择处处被动,增加了许多行动的困难和凶险,项英要为此承担责任。 ①白艾(1926.9-2003.9),原名蒋志侠,安徽和县人。1938年参加抗日队伍,历任新四军六支队司令部机要科译电员、文化教员,《建军报》杂志记者、前线分社记者,华东野战军《拂晓报》记者,七兵团新华分社记者,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新华总分社记者,《解放军报》记者,北京军区政治部作家,正师级。 ②1938年12月,项英将一支队第一团从苏南调回皖南;三支队第六团调苏南,拨归一支队。1939年1月,二支队第三团划归军部。项英安排中央派来的上千个干部、知识青年编入教导大队,并没有分入各支队。 ③油山是位于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西北部的一座山,是项英、陈毅领导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 ④军部作战科参谋颜伏、叶超回忆,周恩来来云岭之前,参谋处是在项英住处罗里村大夫第(即项英的办公室)。参见甘发俊:《云岭漫笔》,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135页。 ⑤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给东南局的指示,题目是《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通称“第二个五四指示”。《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第711—716页。 ⑥粟裕:《粟裕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650—652页。 ⑦粟裕:《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解放军报》,1978年12月1日。 ⑧粟裕:《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⑨粟裕:《粟裕战争回忆录》,第650页。 ⑩粟裕:《粟裕战争回忆录》,第206—207页。 (11)沈阳军区《赖传珠日记》整理编辑领导小组:《赖传珠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0页。 (12)《赖传珠日记》,第152页。 (13)《赖传珠日记》,第152页。 (14)王少明:《访问邱南章同志记录》,《周恩来云岭视察纪实》,郑洪泉主编:《周恩来与新四军研究文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版,第89—91页。邱南章回忆周恩来在军部主持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叶挺、项英、袁国平、李一氓、邓子恢、周子昆、陈毅、粟裕、赖传珠、王必成、宋裕和、邱南章等。 (15)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229页。 (16)安徽省军区政治部主编:《周副主席在皖南》,载《新四军在安徽》,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24页。 (17)《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26页。 (18)《毛泽东关于新四军进行敌后游击战争致项英电》(1938年5月4日)(通称第一个五四指示),《新四军·文献(1)》,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页。 (19)《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1939年4月21日),《新四军·文献(1)》,第126、127页。 (20)《项英关于第一、二、三支队部署与任务致毛泽东等电》(1938年6月15日),《新四军·文献(1)》,第220页。 (21)《项英关于第一、二支队进入敌后的行动原则致陈毅信》(1938年6月23日),《新四军·文献(1)》,第234—235页。 (22)新四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抗日战争史初稿》,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军史汇编资料之二)1980年。岳星明:《有关皖南事变反动阴谋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83页。 (23)王荣科:《浅谈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前的南进计划》,童志强主编:《皖南事变研究与争鸣》,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页。 (24)王辅一:《项英传》,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514、301页。 (25)黎汝清:《我要说的话》,童志强主编:《皖南事变研究与争鸣》,第370页。 (26)陈毅:《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新四军在皖南》,合肥:安徽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396页。 (27)汪海粟:《力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和谐统一》,童志强主编:《皖南事变研究与争鸣》,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3—374页。 (28)王辅一:《项英传》,第475页。 (29)房列曙:《关于项英“南进”、“南调”、“向北发展”问题的重新评价》,《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2期。 (30)王建国:《项英在皖南时期主要“错误”辨析》,《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2期。 (31)《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1940年1月19日),《新四军·文献(1)》,第141页。 (32)王辅一:《项英传》,第461—468页。 (33)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 (34)《刘少奇关于目前华中发展地区及工作部署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12月19日),《新四军·文献(1)》,第137页。 (35)《毛泽东、王稼祥关于皖南部队须力争江北致项英、叶挺电》(1940年1月29日),《新四军·文献(1)》,第145页。 (36)《陈毅、粟裕、罗忠毅、邓振询建议皖南部队东移苏南致中共中央电》(1940年4月21日),《新四军·文献(1)》,第157页。 (37)《陈毅关于贯彻五四指示发展苏南的布置致中共中央电》(1940年5月19日),《新四军·文献(1)》,第312页。 (38)《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陈毅发展苏南布置致项英电》(1940年5月26日),《新四军·文献(1)》,第313页。 (39)粟裕:《粟裕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页。 (40)粟裕:《粟裕回忆录》,第166页。 (4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关于克服动摇犹豫,坚决执行北移方针给项英等的指示》(1940年12月26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20页。 (42)中央档案馆编:《一九四○年五月九日的报告》、《一九四○年五月十二日的报告》,《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66—68页。 (4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性质及东南军分会仍由项英领导的指示》(1940年5月23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65—66页。 (44)叶飞:《叶飞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页。 (4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1941年1月15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66—268页。 (46)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审室:《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17),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标签:皖南事变论文; 项英论文; 粟裕论文; 新四军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白艾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历史论文; 陈毅论文; 叶挺论文; 苏北论文; 根据地论文; 国民党论文; 淮海战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