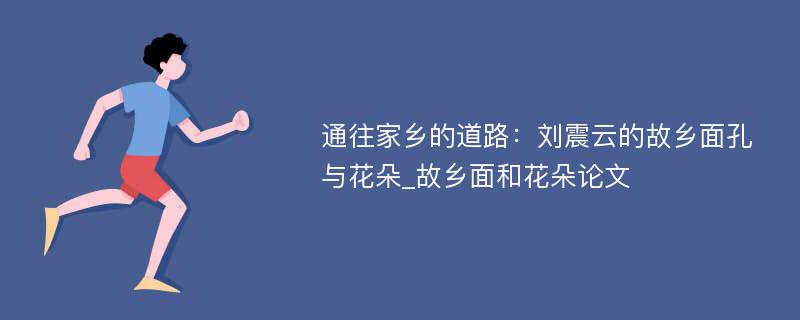
通往故乡的路——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故乡论文,花朵论文,刘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很多条路通往故乡,《故乡面和花朵》也有多种读法,你可以从正门进去,穿堂入户,从第1页一直读到第2183页,对此我没什么意见。 而我的办法是,先读第四卷,第四卷不是“正文”吗?那就不妨放下“卷一 前言卷”、“卷二 前言卷”、“卷三 结局”,先看看“正文”。当然这“正文”又是“对大家回忆录的共同序言”,也就是说,可以把卷一、卷二和卷三视为相对于卷四的“正文”。所以,如果你有足够强的“正文”期待,事情的结果就是你读完了整部长篇。
《故乡面和花朵》的前三卷和第四卷互为正文或前言,这就像地狱和天堂是人间的正文或前言,人间也是地狱和天堂的正文或前言,在刘震云这里,一种二元论模式被编织起来,同时遭到拆解。
所以,前三卷和第四卷之间,是我们可以恰当地提出和探讨问题的关键地带,作者怎样把这两部分榫合起来?他完成这一工作时,面临和克服了怎样的艺术困难从而达到对世界的本质性的“综览”?
再比如,这部小说的叙述者是谁?表面上看,卷一至卷三的叙述者均为小刘儿,到卷四变成了白石头。 翻到第四卷, 劈面第一句就是“1969年,我学会了骑自行车。”再往下翻翻,发现这个“我”名叫白石头,于是我们就放心了,以为往下都是这个“我”了,孰不知正好就错了,往下说话的除了“我”还有“我们”,还有一个无人称的声音指着“你”或“他”说话,你要是认真看了你是不是有点糊涂呢?
汉语中有“你”、“我”、“他”、“你们”、“我们”、“他们”等人称代词,当然其它语言也有。离了这些词人类就说不成话,因为它们界定了语言交流的空间、情境。日常口语中,任何说话都预设了“我”与“你”,但在小说中,情况可能极为复杂,《故乡面和花朵》中,人称代词惊人地活跃,它们站在语流的潮头,看似在前,忽焉在后,舒卷自如,矫夭多姿:“我”说着说着忽然一换位就成了“我们”,“我们”一不留神又成了“你”,指着“你”一篇话数道完缓一口气峰回路转成了心平气和的“他”。
“你”在小说叙述语言中的运用直接建立起说话的现场,这就像说书人滔滔不绝夹叙夹议,忽然指着一位现场听众的鼻子问“你说是不是?”这时听众或读者就被强制地带入文本,构成虚拟的对话情境,当然他并不指望你真的回答是或不是,如果你是读小说,你也无从回答,这是一个姿态,它的表面效果是在寻求共识,但实际上它已经预先肯定你对叙述的认同,它的真正目的不过是要强调这一点,由此说者和听者构成具有共同立场的“我们”。
的确,《故乡面和花朵》中到处都是“我们”,说到眉飞色舞,“我”就不知不觉地膨胀成了“我们”,由“我”到“我们”,这可能是这部小说根本的言语姿态。这个“我”可能是小刘儿,也可能是白石头,无论是谁,按照第一人称叙述的基本规范,他本来是不应该溢出“我”的,他应该是自足的主体,世界在他的主观中呈现。但是,刘震云并不相信存在自足的主体,不相信有纯粹的主观视境,“我”所发出的声音在很多时候和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我们”的声音,当“我”说话时,他的背后站着无数人,他的面前坐着无数人,他的声音是声浪的顶点,所以能被清晰地听到。
第一人称的、主观视角的叙述的可信性早已遭到质疑和颠覆,而《故乡面和花朵》进一步颠覆了它的可能性。刘震云的隐秘意图是将“我”的单纯语境还原成嘈杂的、众声喧哗的公共场所,“我”是对“我们”的模仿,或者说,我们选定了“我”扮演“我们”,“我”所说的话贯注着集体的欲望、梦想和激情,具有公共场所那种不负责任的庞杂、冲突、悖谬。
“我”是被命名的、具有主观的表面效果。“我们”则是无名的,在刘震云的构想中,它包括书中的所有人物,包括作者和读者,进而包括所有操持汉语的人。相对于“我”,它更具权威的客观性立场,这个立场中包含着“我”,但有时声浪涌动,“我”被抛入浪谷,竟会沦落为“你”或“他”,也就是说,“手把红旗旗不湿”是不容易的,你驾驶着汽车时你是“我”,可当汽车超速,你被甩到大街上时,你就成了“他”,你被汽车“他者化”了。在《故乡面和花朵》中,说话的“我”经常遭此命运。
——这也正是我们在语言中生存的真相,我们以为我们是“我”,其实“我”往往是“我们”,而当“我”舌灿莲花时,我们以为是“我”说话,孰不知已是话说“我”,这时的“我”就是“他”或“你”了。
那么,在《故乡面和花朵》中,这个“我”究竟是谁?在卷四的开头,小刘儿和白石头郑重举行了交接仪式:“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过去的叔叔大爷们,我们就在这里分手吧,感谢你们在过去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对我的照看,临分手之前,请受小刘儿一拜。请原谅现在操作文字的已不是我而是白石头了。”
这一番做作与其说澄清了疑问,不如说是把水搅浑,我们——这些“过去的叔叔大爷们”,本已接受了前三卷中小刘儿“花马掉嘴”、巧言令色的叙述,当然小刘儿不是诚恳的叙述者,我们对他的可信性始终抱有警觉,但我们对小刘儿本身在每个具体情境中作为行动、思想和言说着的人物的存在并无怀疑,“我说故我在”,小刘儿的存在是那个世界存在的前提和证明,而现在这个小刘儿躬身一拜就不存在了,不仅如此,他还怀着临去拆台的恶意透露,他仅仅是文字的“操作”者,而且白石头也是。这样,他就在一个微小的缝隙里对前三卷和第四卷各自的情境提出了根本质疑。
小刘儿意欲何为?最终的问题是,刘震云意欲何为?前三卷是显而易见的反面乌托邦,一个反讽性的叙述者在读者面前自行碎裂是可理解的,但其连带后果是为第四卷留下了一个不“真实”的叙述者,而第四卷本来是要刻意求“真”的,是要在前三卷的狂想之后建立一个稳定的、合乎经验的日常世界。
现在,由于小刘儿恶毒的背叛行为,一切都成了疑问,究竟哪个世界更“真实”?
在第四卷里,白石头偶而仍然提到他的童年朋友小刘儿,语调冷漠,仿佛小刘儿只是无关紧要的外姓旁人。但有时小刘儿却像阴魂一样飘荡过来,与白石头鬼鬼祟祟地嘀嘀咕咕,他们似乎共同保守着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就是:白石头是“假”石头,而小刘儿是“真”石头,或者说白石头是“真”小刘儿,而小刘儿是“假”小刘儿。这听上去像绕口令,其实只要想一想《红楼梦》里有个贾(假)宝玉——也是石头——还有个甄(真)宝玉事情就明白了,他们互为对方的影子,当白石头出现时,他是小刘儿的影子,反之,当小刘儿出现时,他是白石头的影子,他们相互取消了对方的真实性,而他们各自所讲述的世界也在真实的价值等级上被拉平,反面乌托邦的幻想世界不比日常生活的经验世界更不真实,而经验世界也并不比幻想世界更真实。
这个秘密尽管云遮雾绕,细心的读者还是能看出蛛丝马迹草蛇灰线。我们至少还记得第二卷第八章的最后一段话:但是,从此,小刘儿和姥娘,在这个故乡就不存在了,小刘儿再在故乡天边的缝隙中出现,就已经是又一个魂灵了。
什么“魂灵”呢?在接下来的第九章《一块石头、一副剃头挑子和一只猴子的对话》中,我们得知,原来小刘儿变成了一块“石头”,这块“生活在往昔”里苦苦“等俺的姥娘”的石头不正是第四卷中白石头的本相吗?况且该石头沉甸甸硬梆梆正好可以拍死人,而据《故乡面和花朵》第1页《部分写作资料来源》记载:“1991 年我开始写作本书的时候他(指白石头)还是我的好朋友,1997年我结束本书写作的时候——秋高气爽的十月,他在故乡神秘死亡——被王楼乡粮站一块从天而降的石头当场拍死。”——白石头死于“石头”,这意味着他已经完成了他作为叙述者的角色,于是小刘儿这块“石头”就从前三卷那巨大的幻想世界中掉了下来,大幕拉开,新戏开场,第四卷——《对大家回忆录的序言》结束,第一卷就开始了。
尽管《故乡面和花朵》是规模宏大千门万户的迷宫,但它有一块最初的基石,就是“石头”。早在第一卷中,礼义廉耻恢复委员会刘老孬秘书长在发给小刘儿的传真中就已经透露了秘密:
热泪撒别之时,我再告诉你一句知心话。当然这句话也不是我的发明了,而是我在一部叫《石头记》的书中看到的。这是书的结束语。我觉得这句话结束得很有道理。
这一群鸡巴人,不是好弄的。
——我们知道有一本书叫《红楼梦》,《红楼梦》有个本名叫《石头记》,但我们想直了肠子也想不出来《石头记》里哪有这么一句粗话,莫不是孬舅他老人家另有孤本秘籍?现在我们明白了,原来孬舅是在点拨我们呢,他借此透露了《故乡面和花朵》对《红楼梦》这部汉语小说最伟大的典籍处心积虑的指涉。
这块基石提供了一个具有全景性视野的立足点,由此我们可能比小说的叙述者、甚至比作者本人更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总体构成——
本书作者白石头说,我要在这张扬的《故乡面和花朵》飞舞和飘动了三卷之后——你是三个大气球吗?现在要坠一个现实的对故乡一个固定年份的规定性考察为铅砣。或者哪怕它是一个空桶呢,现在要在这空桶里装满水。去坠住那在天空里任意飘荡的三个气球或是干脆就是风筝,不使它们像成年之后的人一样过于张扬和飞向天外或魂飞天外,自作主张或装腔作势。
——这是卷四开头的一段话,细心的读者当能看得出来,白石头此时直接僭占了全书讲述者的地位,以一种溢出他本人身分的声音说话,这再次提醒我们,白石头作为讲述者的每一句话实际上也是小刘儿的声音的回响。而刘震云曾经引用这段话阐述《故乡面和花朵》第四卷与前三卷的结构关系,这就使得这段话获得了最终的权威性,它是经过作者和讲述者双重认可的标准答案。
但是,在《故乡面和花朵》的讲述者与读者之间,维持着一种恒定的关系格局,读者永远在智力和道德上高于讲述者,这是精心扮演的,极富诱骗性的姿态,讲述者就像读者面前的“弄臣”,当我们感到明显优越于对方时,我们就能够容忍和欣赏他那肆无忌惮的言辞和行为,而与此同时,我们的智力——或者不如说是“理性”——和道德感却在不知不觉中被搁置。事情之吊诡正在于此,我们感到我们是有理性、有道德的,所以我们能够容忍他们的胡闹,但这种胡闹却从根本上嘲笑了我们的“理性”和“道德”。
所以,对《故乡面和花朵》的作者和讲述者共同给出的这份标准答案,我们不能认真对待,安知这不是又一个小小的玩笑,实际上你要是据此以为卷四终于曲终奏雅要“现实”、“写实”了,我们终于要摸到一块沉甸甸的“生活”了,显然你就又上当了。卷四写的是一个“固定年份”也就是1969年,但1969年并非以现在进行时直接呈现,而是三十年后,在白石头的回忆中被讲述,而白石头这位讲述者又身分诡异,他实际上是飘在空中的小刘儿在大地上印下的影子,经过这一道又一道的拆解,我们眼前这结结实实的“现实”显然失去了“铅砣”一般的重量。
《故乡面和花朵》出版后刘震云在答记者问时除了引述上面那段话之外还说:“我到了三十多岁以后,才知道一些肯定性的词语譬如‘再现’、‘反映’‘现实’……等对于文学的空洞无力。”“在近三千年的汉语写作史上,‘现实’这一话语指令一直处于精神的主导地位而‘精神想象’一直处于受到严格压抑的状态。”可见在刘震云那里“现实”不是一种摆在阳光下等着人们去反映、去再现的事物,“现实”是幽深的海底,被想象和梦想的汪洋所覆盖,我们对“现实”的任何言说都是在测量和证实海水的深度,当谈论“现实”时我们不过是在穿越我们的想象和梦想,所以我们需要一块沉重的石头,让它从海面下落。
由此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故乡面和花朵》的前三卷是梦想而最后一卷是“现实”,按照通常的逻辑也就是刘震云所说的“现实”这一话语指令的主导地位,本应是梦想生于现实,卷四应该是第一卷而一至三卷变为二至四卷,但刘震云把整个结构翻转了过来,在他看来“现实”也许是梦想中比较重比较粗糙比较不真实的成分,是梦想的沉淀或剩余。
所以,尽管刘震云自己把《故乡面和花朵》的结构形容为三个气球和一个铅砣,但我还是认为它更像一个圆圈,演示着梦想和现实生生不息的循环。——在卷四的最后,经过大规模的流血械斗,老庄村“成了一个有‘会’的村庄。从此每年到这一天,我们熟悉的村庄里,就开始行走着成千上万的陌生人。”
“成千上万的陌生人”——那些“同性关系者”回到了故乡。
在《故乡面和花朵》开头的《部分写作资料来源》中,有一个词被反复强调,那就是“关系”——“可作名词,也可作动词,分正当关系和不正当关系。”
于是翻开《辞海》,找到“关”条,有趣的是,“关”字下面竟无“关系”,搜索两遍,还是没有。便合上书发一会儿呆,琢磨为什么没有“关系”。
琢磨的结果是这样的:编《辞海》的老先生们认为这个词太简单太日常,不证自明,你要是不知道“关系”是什么你还翻什么《辞海》呀!——我当然知道“关系”,实际上我天天在处理“关系”。但“关系”于我仍是不解之谜,就像我们不证自明地生活着,而生活永远有待于阐释和解说。
据说一只蝴蝶在阿姆斯特丹振翼翩飞,可以导致太平洋上的一场风暴,同理,你偶感风寒打个喷嚏也许最后就化为纽约市的倾盆大雨,其间起作用的正是事物与事物无比复杂的关系。在如此漫无边际的关系中,因与果的意义也就成了问题——因之因果之果又在哪里呢?任何关于因果的情节和论述也许都不过是一次快刀斩乱麻的专断言说,而“关系”由此成为一座庞大的迷宫,其中埋伏着吞噬意义的怪兽。
当然谈到“关系”完全不必把风筝或气球放得那么远那么高,在你的身边关系就围绕着你包裹着你,这在汉语中叫作社会关系。社会是一种虚拟,但后边加上“关系”,“社会”就获得了血肉,变得具体、日常,我们的“现实”就是由这些关系所构成,你被你的关系所说明所界定,当然你也力图在这些关系中说明和界定自己。
关系“可作名词,也可作动词”,但它的本质是动词:甲关系到乙,在每一次的陈述中谁是甲谁是乙,谁是主语谁是宾语,这是生存的根本问题。因为甲就是主角乙就是配角,甲就是原因乙就是结果,甲就是主动乙就是被动,你在各种情境下如何被“关系”这个动词表述关系到你在这个世界中的相对位置。
关于“关系”,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第四章《意识自身确定性的真理性》中讲述了一个题为《主人和奴隶》的故事:
黑格尔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主人和奴隶,前者“是独立的意识,它的本质是自为存在”,“后者为依赖的意识,它的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
主人通过独立存在间接地使自身与奴隶相关联,因为正是在这种关系里,奴隶才成为奴隶。这就是他在斗争中所未能挣脱的锁链,并且因而证明了他自己不是独立的,只有在物的形式下它才有独立性。
……
那另一种意识(奴隶)扬弃了他自己的自为存在或独立性,而他本身所作的正是主人对他所要作的事,同样又出现了另外的一面:奴隶的行动也正是主人自己的行动,因为奴隶所作的事,真正讲来,就是主人所作的事。
这个故事可以作为《故乡面和花朵》的“关系”主题的重要参照。在《故乡面和花朵》中,四种关系模式的斗争和更替构成了前三卷的基本框架:异性关系、同性关系、生灵及灵生关系,还有自我关系或合体关系。谁都知道这是“玩笑”——小说的《题记》写道:“为什么我眼中常含泪水,是因为这玩笑开得过分”。但这是一场庞大的玩笑,刘震云对“历史”作了一次狂欢式的戏仿。在这里历史之所以被置入引号,因为被戏仿的与其说是实然的历史,不如说是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一种线性的、在变革中不断进步的历史观。
据《部分写作资料来源》中说,该小说最重要的来源除了“关系”一词还有“他”、“她”、“它”三个词。所以你还可以把这四种关系模式翻译成他她关系、他他(她她)关系、它他关系或他它关系、他+她关系。在《故乡面和花朵》的伪历史中,这些代词的组合变化被一本正经地宣称为“历史”的内在规律的表征,每次变化都是一个重大进步,都调动和消费了浩瀚的激情、欲望和言辞。
刘震云对世界作了元素化的还原:男—女,人—物,对此最直接的解释是从人类生活中最基本、恒常的关系出发可以达到“一本万殊”的效果。但同样明显的是,当他把诸如“男女”这样通常不能进入历史的宏大叙事的“关系”作为这个历史乌托邦的基本动力时,其中含有对乌托邦梦想的尖刻反讽——也许的确是“一本万殊”,当我们自以为已经走得很远时,我们实质上总是准确无误地落在原地。
有位朋友对我说过:刘震云写的同性恋根本不像那么回事儿。——说得或许不错,但对于“异性关系时代”、“同性关系时代”等等小说家言你不可不认真也不可太认真,不可不认真是因为它确实构成了对于宏大的人类活动和梦想、对宏大的“历史”极具本质力量的模仿,但正因为是“模仿”,能指与所指之间有一个相互指涉的游移的空间,无论对能指还是所指你都不能敲钉转角地坐实了去看,“玩笑”而已,虽然“眼里常含泪水”。
——实际上,“他”、“她”、“它”不仅是上帝眼中世界的基本元素,而且是在任何一个“说话”现场用以指称第三者,指称你我之外的广大世界的最基本的词,如果我们言说世界,我们正是在言说“他”、“她”、“它”这三个代词,《故乡面和花朵》中它们之间的排列组合刁钻地表明,世界可以被不同的话语系统所言说、所界定,“历史”的本质也正是这些话语系统之间的斗争。
“关系”一词有一层暧昧的深意,这就是男女关系,或者更宽泛一点是性关系。《部分写作资料来源》指出:关系“分正当关系和不正当关系”,这种分法在现代汉语中通常也正是用在男女关系或性关系上,当然还有“拉关系”、“搞关系”等等,都隐含着负面的伦理判断。可见谈到“关系”,总是预设着价值立场,在词语的运用中隐含着秩序的强制力量。
但是,就像《部分写作资料来源》所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军队中已不再歧视同性关系。在冷冰冰的原则面前,对关系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当然,“发生了改变”,从此赦你无罪,旧的原则旧的秩序改变了部分失效了,美国那些同性关系者的梦想和斗争终于取得了重大胜利,但这胜利的实质是什么呢?实质是他们确立了自己对于“关系”的言说的权力,当“他”或“她”拥有这种权力时,“关系”就由“不正当”变为“正当”。世界并无改变,改变的只是对世界的言说。
显然,谈到“关系”、谈到关系正当不正当那得看话由谁说话怎么说,人类生活和“关系”中一个恒常的“现实”就是争夺话语权力的斗争,你在这场斗争中的强弱胜负取决于你在关系中的角色但也决定了你在关系中的角色。你要知道某一种关系是怎么回事你当然要去查资料翻书本,但在查资料翻书本的时候你也别忘了这些资料这些书本说的是有权力“说话”的人的话,比如《故乡面和花朵》,很不幸但是很自然的,这部书据刘震云说是小刘儿或白石头写的,小刘儿是什么人?两面三刀看风使舵喝彩下暗绊儿推倒了油瓶儿不扶作梦都想当贵族当上等人,这种人当然是奴隶是弱者放到任何一种关系一台戏里也只配演个匪兵甲群众乙,你看着他在那儿忙乎个不停喋喋不休谁也没他话多,但其实他是在心里在梦想中念叨主角的台词儿呢,真让他当了主角你以为他能妙语惊人别开生面?他顶多不过是把他学会的背熟的再演一遍也不管台下的观众烦不烦。所幸小刘儿在艺人圈里混得久会码字儿会写书,于是他就写了《故乡面和花朵》,他不写我们还不知道,他这一写他可就自我暴露了,原来不管戏码儿怎么变不管话怎么说,你看着是天翻地覆血流成河,其实舞台上只有两种人只有一种关系:
说话者和学话者。
《故乡面和花朵》正是在这一点上敞开了人性的奇观:广阔、丰饶、欢乐、恐怖。
附录一:《故乡面和花朵》的语言
现代汉语的历史十分短暂,从白话文运动至今也不过八十多年,对一种语言或一种语言的文学来说,一切还刚刚开始。本世纪上半叶的大师们力图使现代汉语成为一种审美语言,他们做的是草创性的工作,我们至今还在承受恩泽。
但是,对现代汉语的形成和演化起主要作用的从来不是文学或文学家。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主宰着我们的想象、思考和表达的是意识形态,或者用刘震云的话说是权力关系。当然意识形态或“关系”在任何语种中的作用都至关重要,但在每一个语种的正常状态中语言的运用是有不同的界面不同的区隔,比如男女谈情,应是柔情万种甜言蜜语,但在现代汉语中有的时候你就算是柔情万种也没有甜言蜜语可说,你说的是“让我们互帮互学共同进步”,这种话你在两情缱绻的私室里说,而其实应该是在众目睽睽的广场上说的。现代汉语的根本特点就是公共的、意识形态的语言全面地侵占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一统江山一极世界以于作为私人你无话可说,精神和梦想全面失语。
当然现在情况有所不同,我们写家书不再是“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好好歇歇吧”然后就“此致那个敬礼”,二十年来许多中国作家苦心孤诣于开辟或建设现代汉语的私人领域,让你找到话表达你的精神你的梦想不至于连说梦话都像作报告或念检讨。
但是,由“我们”的话到“我”的话,显然不仅是主语转换问题,更不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如果说刘震云对“我们”对“我”的覆盖有深刻洞察,那么他也尖锐地意识到,纯粹的“我”是虚幻的梦想。这里有一个触目的矛盾:只有通过“我”的语言个人才能被识别,才获得意义,但“我”又有一种深刻的冲动,它要扩张成为“我们”,——也就是说,“我”在自我确立的同时也是自我取消的。这是人在语言中、在现代汉语中充满疯狂和谬误的处境,远不是“我”——“我们”、私人—公共这些二元对立方案所能解决。
——所以,当刘震云在1991年开始写作《故乡面和花朵》时,他心里一定有一个宏大的场面,他在与现代汉语这种中国人所操持和被操持的语言对话,他对“我”和“我们”所能说的话展开了一次规模惊人的戏仿,在戏仿中,“我”和“我们”都暴露出极限和枯竭,同时遭到祛魅。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故乡面和花朵》的语言策略,理解刘震云或小刘儿或白石头为什么这么写这么说——
一、说话:
《故乡面和花朵》在滔滔不绝地“说话”,它的语言基本上是口语,这是菲勒斯中心主义无限膨胀的闹剧。相对于书写,说话有强大的交际功能,任何说话的地方都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关系”现场,都发生着“关系”之中必有的对抗、闪避、欺骗、威胁,发生着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斗争,所以口语是语言的拳击台是“关系”的谈判桌,无论何时何地当你说话时你就会获得明确的角色感,宛如面对世界面对人声鼎沸的广场。而且说话还有一种来自于语音的权威感,当一个声音从众人的声音浮现出来时,这简直是对上帝的一次模仿,你很难不认为自己是在宣叙真理。所以,通过说话,语言中“我”—“我们”之间复杂的腾挪转换尽展无遗。
二、延异:
《故乡面和花朵》的语言无限延异——语流如一棵树不断地似乎是没完没了地分杈,从北京去天津如果你坐上火车汽车用不了两个小时就到了,可在《故乡面和花朵》的语言中他可能路上下车买东西偶遇美女于是不上车了就地展开强大的追求攻势一波三折千回百转等他抵达天津可能孩子都快上小学了。
这种延异这种不断离题不仅表现了精神活动的真相,更重要的是,在每一个具体的说话现场这种语言都是精心设计的圈套老谋深算的诡计,就是要把你绕晕,把你绕晕了我就合了适了,你看着我离题万里天外云游以为我回不来了,其实我心里有数我时刻没有忘记我的主题我的目的,等你迷糊了疲惫了这个主题这个目的就像一把尖刀顶在你的喉咙上了。
——所以《故乡面和花朵》暴露的是语言中精微的权力策略,这是一种艰苦卓绝又若无其事的互相淹没互相麻痹的努力。
三、广场:
《故乡面和花朵》中有许多公众场合,如广场、会场、集市等等,其实至少在前三卷中几乎没有私人场所,因为到处都架着摄像机,夫妻吵架也是一个被千家万户共享的大众娱乐事件。——美国影片《楚门的世界》后来对一个类似的情境作了浪漫+悬疑的敷演。——所以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分析的,《故乡面和花朵》中讲述者的声音有一种奇异的喧哗,广场上人声鼎沸,讲述者的声音在声浪中盘旋跳荡,表达着、引领着集体精神的翻腾,我想这种感觉类似于收听电台的足球比赛直播,那个激动的解说员总能把你带入癫狂的现场——但愿这将是二十世纪的蛊惑家们的最后职业。
附录二:摄像机与舞台
《故乡面和花朵》中有多重、复杂的模仿、扮演。举其大者,比如一至三卷的所有人都在扮演“历史”这台大戏。 第四卷是白石头对1969年的回忆, 这在当代文学中独传一脉叫作“童年视角”或“童年记忆”,但白石头的回忆恐怕并非“童年视角”或“童年记忆”,而是对此类文学作品颇为滑稽的模仿,当他一本正经地把自己童年的那点烂事儿当作发展中的“历史”叙述时,“童年视角”或“童年记忆”中那迷惘的、但同样一本正经的自我成长被放大被夸张被嘲笑:同时遭到模仿的还有“历史”的叙事逻辑,但这种模仿是以小拟大,人们通常用来分析和论证宏大之事的一套话语被用在一个乡村少年身上,这就像小孩儿穿了大人的衣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
奴隶在说主人的话。
奴隶说主人的话固然可笑,但主人的话经过奴隶模仿也显得滑稽,一副袍带由庙堂流落民间,乡野匹夫穿上它招摇过市,在这个狂欢节般的场面中主人和奴隶煮在一个锅里咕嘟咕嘟冒泡煞是热闹。
整部《故乡面和花朵》,前三卷和第四卷其实也在互相模仿,就像小刘儿扮白石头,白石头扮小刘儿,前三卷是极度夸张狂放地模仿第四卷的个人史,而第四卷的个人史则是前三卷的“宏大叙事”的一段遥远日常的回响。
模仿、游戏、真真假假虚实难测,《故乡面》是一个戏剧的迷宫,许多时候,人物还以为他在台下看戏看到得意处一拍大腿喝一声好,谁知道千百双眼睛也在看着他呢。他自己就在舞台上就是演员聚光灯明晃晃正照着他他以为正看着别人作梦殊不知他自己也是梦中人呢。
所以,注意摄像机!《故乡面》里到处埋伏着摄像器材灯光设备,这使得许多场面最终变成了舞台。
标签:故乡面和花朵论文; 刘震云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故乡论文; 花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声音模仿论文; 文化论文; 辞海论文; 红楼梦论文; 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