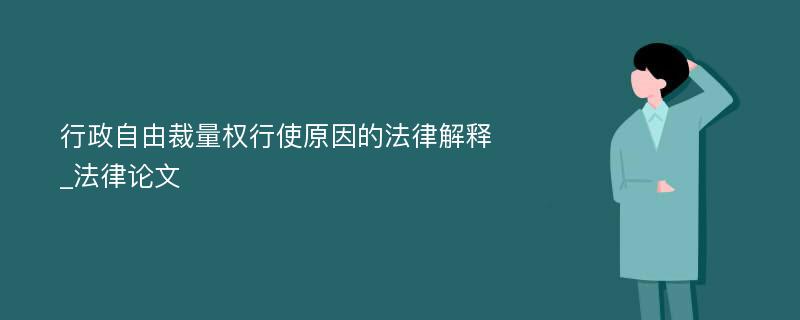
行政裁量权行使之理由说明——以法律论证为分析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理由论文,行政论文,裁量权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69X(2006)04-0045-07
一、行政裁量权、论证理论与理由说明
行政裁量权问题始终是行政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田中二郎更是直言不讳的指出,行政法的精髓在于裁量①。对行政裁量权的规范不仅在理论层面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还对我国向现代化国家转型有着积极的意义,更是我国贯彻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国家实践进程中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说其“有积极的意义”是因为现代国家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以及“福利国家”②的追求越来越依赖于行政机关的裁量权,只有通过行政机关裁量权的行使才能达到相关的立法目的③;说其“不可或缺”是因为再好的规则也必须转变为具体的行为,而将抽象的规则转化为现实就需要相关人员的解释、选择和判断。因此,现代国家的行政管理依赖于行政裁量,而对行政裁量权规范的过程就是依法行政和实现法治国家的过程。
在对待行政裁量权的态度上,行政法法学界基本分为两大流派:一派为功能主义,一派为规范主义④。双方对此有着迥异的价值取向,相应地,双方也开出了完全不同的治理方案。两派学者就行政裁量问题及其相关问题唇枪舌战,进行着无休止的论争,而实践中,行政裁量权已经在人们的论争过程中大张旗鼓的登上了行政管理的舞台。经验告诉我们:行政裁量既不是魔鬼也不是天使。因此,当前行政法研究的主要任务已经不再是要不要行政裁量权的问题,而是承认现实⑤,以及如何界定(confine)建构(construct)与控制(check)行政裁量的问题了。而在某种程度上而言⑥,无论是功能主义学派还是规范主义学派,虽然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其本质上都是一种权力模式,即都将行政裁量权视为一种权力,一种垄断对事实认定、法律解释以及适用的权力。具体而言,在规范主义者看来,行政裁量权必须臣服于更高、更神圣的立法意志,并通过司法权来保障其不发生偏差。为了达到这目的,他们提出了两条道路:一条是立法的,一条是司法的。但问题是,通过立法规范裁量权必然会有相当的缝隙,而司法权同样存在裁量的可能与必要性。这样,在某种程度上,规范主义者的解决方案就是将裁量权从行政机关转移到司法机关,用司法裁量权来约束行政裁量权⑦。但就如Willis所指出的⑧:行政决定的作出涉及到专业技术、工作量、可利用资源以及速度等因素的综合考量,而这些因素往往不是法院运用一些法律原则就能解决的。因此,我们并不能指望法官就比行政官员具备更高的洞察力。而就功能主义者而言,行政裁量权就是行政机关运用专业知识解决行政管理问题的权力,行政裁量权就如同医生就专门问题运用的权力一样。但是其强调的技术专业性与行政管理的现实情形⑨有着巨大的差别,同时,“管制俘虏”和“专家父权主义”的盛行使得其也失去了解释力。
总之,两者本质上都将裁量权视为一种权力,一种绝对的、自上而下的、独断式的对规则进行解释的权力。如果说这种规则认识理论在常态的非裁量权领域还尚能具备一定正当性的话,则非常态的疑难案件(规则模糊不清)中的裁量权行使就不能通过这种强权式的直线论证⑩。因为在规则模糊的情形下,规则的权威性就有所降低,而相应的理由说明的必要性就有所增加(11)。换而言之,这两种理论假设都建立在一种绝对真理观的基础之上。而事实上,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除了“符合真理观”外,还存在着“共识真理观”。而无论是规范主义所依赖的“传送带理论”还是功能主义强调的“专业技术理论”都不能有力的支撑疑难案件中(一定程度上的规则失效)行政权力的正当性,“毕竟,现代行政权基本上是自由裁量的情况下,仅有合法性显然是不够的”(12)。在事实认定存在障碍,法律规则不能直接适用的案件中,行政机关必须就其行政决定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作出论证,而不能如同在“一般案件”中仅依靠行政行为的“效力理论”的强制力取得正当性[13]。因为,这种效力由于受到“是否存在法律规则”这不确定性的影响而不必然具有正当性。这时,如何使行政机关裁量权的行使既具有合法性又具有正当性就成为规范裁量权的关键。比较可行的方案就是如同法官在作出判决后必须对其判决作出法律论证一样(14),行政机关在疑难案件中同样要就其裁量权力的运用进行论证。只有这样,行政机关才能弥补其在规则模糊情形下行政决定正当性的不足,行政决定才具备可接受性。而且,除了欠缺正当性,这种权力模式存在着相当的弊端(15),例如,阻碍技术革新,成本效率低下等。
行政决定的权威性必须建立在“正当性”而非“强权”的基础之上。因此,疑难案件中的裁量权正当性来源就不能仅仅依赖于法律,也不能依赖于行政机关自身,而应该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通过各种形式的法律论证来增加其行为的正当性。基于裁量权领域的特殊性,哈贝马斯的协商理论较之通常的逻辑论证有着更多的优势,也就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裁量权的过程中应该同众多交谈者一起进行平等而诚实的论辩、协商和交谈。从行政主体的角度来看,这一过程就表现为主体间的法律论证过程;而从相对方来看,就是行政参与。最终通过行政机关与相对方以及其他相关人之间的协商、交流,最终达成为大家所接受的方案。
法律论证问题的研究目前主要局限在司法领域,该理论的提出主要是为解决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判决的合法性和可接受问题。而该研究的兴起与传统分权学说的破产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在传统分权理论看来,立法者的任务就是制定清晰明确的法律规范,而法官的任务就是将这些法律规则适用于具体的案件而已。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羁绊,立法机关已经无法扮演这种近乎上帝的角色。结果就是法官和行政机关在权力的分配中得以重新定位。这样,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判决的同时,就面临着该判决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问题。他们不得不阐明其解释和决定。当然,法官在不同的案件中,这种论证的标准是不同的。在简易案件中,法官只需提及相关事实和法律规则即可,而无须进行更深入的论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基本达成共识,而法官裁判权行使的正当性也无庸质疑。但是,在疑难案件中,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无论是事实的认定、法律规则的解释以及将规则适用于具体事实,法官都必须将其决定,通过一定的论证方式一一作出论证。当然,司法/行政两者间还存在着区别,例如,论证的标准不同。司法的本质(保障权利的最后一道堤防)决定了司法论证的标准较之行政机关的论证更为高。再例如,司法活动主要是纠纷解决(16),而行政机关的行为则更为复杂多元,因此,行政机关的论证要求随着其行为方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这种差异并不影响两者在裁量权行使过程中必须进行的法律论证。与法官对其判决的论证相类似,行政机关也必须对其作出的行政决定进行不同程度的论证,在简易案件中,行政行为的正当性与可接受性可以得到行政行为效力理论的支撑论,因此,论证程度要求较低,而且主要是逻辑层面的形式论证;而在疑难案件中,论证的程度要求较高。而且,行政机关不仅要使用逻辑论证理论,可能更依赖于协商对话论证理论。通过这种依赖于主体间性的论证理论来弥补正当性和可接受性的不足。
将协商对话论证理论引入行政裁量权领域,这对裁量权行使的正当化以及对其的法律规制有着积极的意义。而行政机关的理由说明制度可以视为论证理由的重要表现形式。传统上,我们将理由说明视为正当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其作用也限于程序方面。但是,理由说明的功能远远不止于此。如果我们从法律论证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理由说明制度,则该制度的价值和内涵将更为广泛。例如行政裁量权行使的正当性,如何通过行政裁量达至行政正义(Administrative Justice)(17)等问题。而根据JERRY MASHAW的经典定义,行政正义就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相关程序的质量,以及由此带来的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这样可接受性成为判断行政裁量权行使是否合理、合法的重要指标。而可接受性本身并不能仅仅依靠行政强制力就可以获得,也不是将事实、法律条款罗列于相关法律文书中就可以得到,相反,其必须在法律的基本框架之下,双方(多方)进行必要的妥协,能够充分考虑和体谅各自立场,通过理由说明这种沟通机制能够与行政相对人乃至普通公众进行信息的交流与沟通,从而在法律框架内与公众达成共识,最终增强行政裁量权行使的可接受程度。总之,理由说明制度应该存在着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是表面的、权宜的和实用的,也就是理由说明对行政行为在正当程序方面以及由此带来的实体方面质量提高所起的作用,这也是我们推行理由说明制度的初衷;而除此之外,其还有着本质的、根本性的作用。也就是当在行政机关采取积极干预定位过程中,弥补了行政裁量权的合法性的不足,增进了民主正当性,提高了行政权威。而由于传统角度的偏狭,其仅仅着眼于程序性问题,这导致了许多相关问题得不到有效解释。
二、理由说明制度的反思
就普通法而言,其并不要求法官与行政机关必须就其作出的决定进行理由说明(18)。但是,随着制定法的要求、欧洲人权法案的实施以及正当法律程序观念的滥觞,普通法国家也逐渐抛弃了传统的做法,而趋向于将理由说明作为行政机关的一项法定义务。1932年,多诺莫尔(Donoughmore)委员会在关于部长权力的报告中写到:“任何受到行政决定影响的一方都必须被告知该行政决定作出的理由……”。其还认为说明理由的义务是法治原则下司法行为的重要原则,同时要求说明理由的权利被认为是自然公正原则的第三条原则(19)。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1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行政许可法》第38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显然,理由说明作为行政机关权力行使的一项伴随义务,其已经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一般认为,理由说明义务主要有以下作用:首先,行政机关进行理由说明的过程有助于其更加理性的思考,从而保证行政决定的质量。其次,行政机关的理由有助于相对方进行分析,进而提高行政决定的可接受性。再次,有助于司法审查的进行。我国法律也是基于上述作用的考量而对理由说明义务制度也作出了如上规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法律对理由说明义务作出了上述规定,但是,由于这种规定仅仅是从传统的正当程序的角度出发,因此,其在范围上都仅仅局限于侵害性行为,在程度上也是模糊不清,在性质上也是左右徘徊,在种类上仅仅局限于事后(20)。而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法律并没有提供相关的标准来评估这种制度(21),以至于理由说明制度最终流于形式。
本文所理解的理由说明义务视角不同于传统的在正当程序框架下的理由说明(书面理由),而是将其视为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以及公众就其裁量行为所作的一种主体间平等对话的一种寻求正当性、民主性的尝试。既然我们将理由说明视为平等主体间的一种协商对话,则其内容就不仅仅限于程序性问题,其还涉及到实体问题、行政参与、裁量权行使的正当性与可接受性、法律论证等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是正当法律程序视角下理由说明制度所不能包涵的。目前研究理由说明制度主要面临以下问题:
首先,理由说明义务的适用范围。传统行政法理论认为,理由说明义务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侵害行政,这也是正当程序的核心主旨。这在传统的政府/个人二元关系以及“消极的政府角色定位”背景下,对于个人权力保护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侵害行政与受益行政的分类方式在一定程度并不能有效解决行政国家出现后,行政法律关系从二元转变为多元之后个人与行政机关的矛盾。况且,在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之下,行政机关的受益行政的作出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受益人的权利(22)。因此,将理由说明仅仅定位于侵害行政有着相当的缺陷。
而从论证理论的角度而言,由于事实认定、法律规则解释的模糊性导致了行政裁量权的正当性的减弱,这样,理由说明义务可以视为行政机关弥补其正当性的机制,照此推论,理由说明义务适用于所有行政裁量权有关的领域,而不论其是否为侵害行政。因此,从论证理论的角度出发,行政机关的理由说明义务适用的范围要远远大于从正当程序视角下的理由说明机制。只是在论证理论的框架下,理由说明的范围与理由说明的强度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些行政手段的采取需要深度的理由说明,而有些行政手段的采取则需要表面的、程序性的理由说明。总之,理由说明义务的适用范围在行政裁量权盛行的现代行政领域必须相应作出扩展,不能局限于侵害行政领域,更应该扩张到积极行政领域。换而言之,理由说明制度适用的标准将不再是“是否侵犯行政相对人权利”而是“是否涉及到裁量权”。
其次,理由说明的方式。理由说明究竟仅仅是行政机关按照既定的程序进行一个法定程序还是行政机关与当事人就相关事项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的动态的论证过程?从法律论证的角度来说,理由说明应该是双向的,平等的、动态的。所谓“双向的”就是行政机关作出的理由说明不仅仅是正当程序要求下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宣布命令式的说明,相反,其应该是相互协商的,行政机关必须及时回应当事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并适时调整其行政决策,而相对人也应该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出发,对行政机关所处位置进行考虑。总之,两者间是基于相互信任而建立起的一种互惠的双向关系。所谓“平等的”,也就是行政机关与当事人行政机关在理由说明的过程中地位相同,而由于行政机关在事实上拥有优势,因此,如何保证弱势群体在协商论证的过程中真正具有交谈协商的地位,而不至沦为权力的玩物(23),这就是理由说明配套制度必须要解决的,而国外也有专门研究此问题的脆弱理论。所谓“动态的”就是行政机关的理由说明是在法律框下的存在着相当自主性的行为,而不是法律严格规定下的法律程序。行政机关必须根据当事人的信息及时作出调整和反映。总之,行政机关的理由说明机制主要是在法律的框架下对其裁量权作出合理的解释,在当事人有疑惑或者不同意见和建议时能够及时听取相对人及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并作出回应,而不应该仅仅是履行一项既定的法律程序。正如有学者提出的:“我们反对愚弄法律程序的形式主义,主张程序的实际作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程序的作用要素来体现。”也就是,行政机关不仅是进行理由说明,还要听取对方的意见和建议,并进行实质性的考虑(24)。
再次,理由说明所运用的方式。理由说明究竟应该采取何种论证方式,是逻辑的、修辞的还是协商对话?对此,传统行政法相关理论并没有给出详细介绍。一般而言,形式逻辑论证(三段论)是法律人最为熟悉的论证方式。但是,在裁量权领域,大小前提都不确定,传统的“符合真理观”往往无法发挥其作用,很容易出现辛豪森的“困境”(25)(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此,我们必须探索新的理论工具。而现代哲学真理观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变,为我们研究裁量权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换而言之,最传统的理由说明方式——逻辑论证在裁量权领域仅仅成是充分条件。因此,在裁量权领域,由于传统的程序正义观往往无法解释理由说明究竟应该采用何种论证方式,而这往往直接影响到行政裁量权行使的合法性与可接受性。而哈贝马斯的协商理论无疑是现代法律论证理论中的重要一脉(26)。就裁量权领域而言,行政主体作为交谈一方可以就裁量权问题与其他交谈者进行协商、说明和论证,通过用真理共识论来取代传统的真理符合论。可以说,这种真理观的转变是我们研究裁量权的重要突破点。也就是说,传统理论对模糊法律规则的阐释,对事实的认定要么赋予行政机关,要么赋予司法机关,而协商理论则认为对模糊规则进行解读的任务不仅在于行政机关、法院而且还在于相对人。通过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协商达成一致,行政裁量权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双方所拥有,而非仅仅行政机关所拥有。这样,行政裁量权就由传统的权力模式转为对话模式。
第四,理由说明的程度(司法审查的强度)。说明理由究竟应该达到何种程度?是将事实、法律罗列于法律文书?还是需要对其行为进行论证?法院对理由说明究竟是程序性的还是实质性的?一般认为,理由说明应该是个程序性的问题。因为各国的司法审查经验表明理由说明是个程序问题。也就是行政机关是否进行了理由说明,如果没有说明,则行政机关违反相关程序,从而导致一定的法律后果;如果行政机关说明了,则无论该理由是否成立,无论该理由说明的好坏,都是符合法律的规定。这种认识主要是基于司法/行政的分工不同所形成的。但是,法院对行政机关理由说明义务的程序性审查标准往往导致行政机关的“走过场”的弊病,也使得理由说明往往无法真正有效的规范行政裁量权。就美国的APA的规定而言,行政机关的理由说明应该达到充足(ADEQUATE)。而法院判断行政机关是否有充足理由的判断标准就是行政机关是否认真听取了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并且作出了回应。这样行政机关的理由说明义务就成为行政机关回应各方建议和意见的义务,而理由说明的程度也就成为了行政机关回应各方的论证程度。而且,美国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这项要求也经历和一个逐渐演变和发展的过程(27)。在70年代,联邦法院要求行政机关对所有参与非正式规则制定程序者的提议必须作出回应。在80年代,其要求不仅是参与者提出的提议,而是对所有的提议都必须作出回应。因此,行政机关的义务就不仅仅是与参与者进行协商交流,对各种提议都进行理由说明,而且还应该作出“概要式行政决定”(SYNOPTIC DECISION),也就是行政机关必须就其政策取向的说明;考虑所有可替代性方案的可行性;收集所有相关证据;并且作出最符合上述情形的决定。这样,行政机关就其行政决定作出理由说明的标准就从“只要说明理由,行政机关就可以采取任何其感兴趣的决定”转变为“其必须采取最具说服力和最理性的决定”。总之,就美国联邦法院的态度而言,行政机关的理由说明义务的程度逐渐由程序性的、温和的自律标准转变为实体性的、严格的他律标准。随着司法外部政治环境的变迁,各国法院对理由说明的审查逐渐从程序性审查标准转为实体性审查标准。这种转变可能会给行政机关理由带来实质性的转变,也就是行政机关从一般性的表面性的理由说明义务转变为对其裁量权行为进行充分的实质性论证,并且就为何采取该种决定,而不采取其他替代性决定作出说明(28)。
第五,理由说明的分类。一般认为说明理由仅仅是行政机关对其所做出的行政决定(大多是行政行为)作出解释和阐述,也就是个案的理由说明。也有学者认为:理由说明可以分为“事前的理由说明”和“事后(时)的理由说明”。弗兰克斯委员会报告等一系列研究都就事后说明理由作出了详尽而有力的说明。但是对事前的理由说明还未引起学者与实践的重视,即使有相关要求和论述,也都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所谓“事前的理由说明”也就是行政机关就作出该决定的标准和因素作出相关说明。该种理由说明主要针对的是行政机关制定的内部的各种标准、守则、执法细则,相对于事后(时)的理由进行说明,其针对的对象是抽象的,是不特定的公众。一般而言,行政机关作出一个具体行政决定必须依据相应的法律,以及相关的政策、标准、方针,在一些具体案件中,甚至还要求具备如何解决相关问题的知识和意见。因为,行政决定的作出必须受具体环境的影响,而远远不止法律的规定。换而言之,行政机关执法的执法依据的运用必须与法律规范的层级相反,因此,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决定时并不是直接运用法律的规定,而是运用其下位的规则——这些规则在德国法中称为“行政规则”。也就是行政机关所颁布的拘束其内部人员的规则或规范行政体系内部事项的命令,其通常不直接对外发生效力,与人民的权利义务也没有直接的关系(29)。也正是此原因,行政机关往往不公开此类规则。而法律也常常将此权力赋予行政机关,由其独自进行运作,并不要求其作出理由说明。但是,从协商理论的角度而言,行政机关也应该对公众就这些事前规则进行理由说明。只有这样,才能使公众对这些裁量标准等内部行政规则有所了解。因此,就行政机关的内部性行政规则而言,其不仅应该公开,而且应该进行理由说明。
最后,理由说明的作用。传统认为理由说明有以下作用:首先,有利于提高行政决定的质量;其次,有利于相对人的理解;最后,有理于今后的司法审查。但是,如果从法律论证的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发现,行政机关的理由说明机制除了上述作用外,还有着更为重要的教育作用、正当化作用和妥协作用。所谓教育作用,就是行政机关通过理由说明来阐述其目标、计划以及拟采取的方式等,从而使得人们能够认同、理解其所作所为,并进而采取合作的态度和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也树立了行政机关的执法权威(30)。因此,通过该制度可以从根本上消除行政机关与个人之间的对峙状态(31),为行政机关的良好行政奠定基础。
三、理由说明制度的未来
韦德曾经认为,就所作出的行为说明理由从未成为自然正义的一项原则,即使法院也没有此类规则,更何况是行政机关了(32)。显然,在普通法的传统中,理由说明义务缺乏明文规定。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制定法规定了行政机关作出理由说明的义务。这种规定可能来源于Bridge勋爵所观察到的事实:即制定法要求说明理由就如同普通法要求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实现过程也要能被看到。但是,普通法至少在表面上尚未要求决定的作出必须附带说明理由。那么,为何普通法对此视而不见呢?是不是普通法就能容忍专断、恣意和没有理由的决定呢?还是法治的精神还没有深入人心呢?其实,就如澳大利亚大法官在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V.Bond一案中所言:就其本质而言,理性行为(act judicially)的义务(包括程序公正和自然正义等)已经排除了行政机关专断、恣意和没有理由的行为,而且该义务要求行政机关必须考虑相关的因素和不考虑不相关的因素。这样就排除了行政机关基于偏见、怀疑和先见等作出行为的可能性。因此,虽然普通法中没有理由说明制度的相关规定,但是,其对理性行为的规定完全可以替代理由说明制度的功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政府奉行“自由放任”的消极定位下,行政机关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完全可以从明确的法律规定中得到支持(行政裁量权也并不是盛行,是真正的依法律行政),而无需理由说明制度。而理由说明制度的表面性功能也完全可以由普通法的其他制度予以代位行使。俱往矣,今日之理由说明制度已非复吴下阿蒙。短短几十年后的今天,理由说明制度已经在程序正义之激荡人心的感召下,大行其道,这无疑是法治发展的进步。
但是,就发生学意义上而言,理由说明制度的盛行与其说是法治程序观念发展的产物,还不如说是政府在不断膨胀的权力行使过程中,为其行为正当性不足而所作的一种弥补措施,或者通过赋予自身一定的程序义务来换取权力的扩张的一种尝试。因此,在理由说明制度的功能上,我们固然可以强调其表面性的功用,但是,我们却不能忘记除了这些权宜性的功能作用之外,理由说明制度还有着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价值。就如Carl Friedrich所言,在西方的政治传统中,政治权威或者其他权威其实就意味着理由说明。如果我们承认权威不同于赤裸裸的强权,则我们就必须承认对所为行为作出一个好的理由说明是权威存在的核心(33)。同样,在行政裁量权领域,如果行政裁量权要存在并发展,则对裁量权的行使进行充分的、实质性的理由说明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毕竟,现代行政权基本上是自由裁量的情况下,仅有合法性显然是不够的”。
可以预测,理由说明制度在裁量权不断扩展的行政领域,必然有着更为巨大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也是裁量权存在的基础条件。
注释:
①转引自杨建顺.行政裁量权的运作及其监督[J].法学研究,2004,(1).对行政裁量权重要性的介绍可以见GEORGE C.DISCRETION AN ESSAY ON DISCRETION 1986 DUKE L.J.747
②就福利国家问题,学术界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
③行政裁量权扩张的重要原因是框架立法(framwork legislation)的兴起,这种框架立法与传统的法律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行政机关在执行此类法律规则时拥有更大的权力。
④关于功能主义和规范主义的划分和各自的观点可以参考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卡罗尔·哈洛和理查德·罗林斯.法律与行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⑤Cole Blease Graham and Steven W.Hays CITIZEN ACCESS AND THE CONTROL OF ADMINISTRATION DISCRETION Douglas H.Shumavon and H.K.Hibbeln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AND PUBLIC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aeger Publishers,1986.PP233.
⑥关于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本质上的权力性见徐文星.从权力理论到对话理论——行政裁量权方法的转变[DB/OL]http://www.lawthinker.com
⑦Martin Shapiro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The Next Stage 92 Yale L.J.1488 1982-1983F.
⑧Lorne Sossin ADMINISTRATIVE LAW TODAY:Culture,Ideas,Institutions,Processes,Values:Essays in Honour of John Willis:II.THE UNIQUENESS OF ADMINISTRATIVE LAW:LEGAL VALUES AND CIVIL SERVANTS' VALUES:FROM NEUTRALITY TO COMPASSION:THE PLACE OF CIVIL SERVICE VALUES AND LEGAL NORMS IN THE EXERCISE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55 Univ.of Toronto L.J.427.
⑨管制俘虏、公共利益保护机制的失效等问题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行政官僚占主导地位的管理模式,也对该种管理模式的政治基础——多元主义模式进行了反思。
⑩舒国滢.法律论证中的若干问题[EB/OL].http//www.law-thinker.com/show.asp? id=2999
(11)Frederick Schauer GIVING REASONS 47 Stan.L Rev.633 April,1995.
(12)章剑生.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判解[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51.
(13)按照叶必丰教授的研究,行政行为的效力主要包括先定力、公定力、确定力、执行力与存续力。而行政行为的效力则来源于法律以及行政法的性质。具体到行政机关的执法领域而言,当行政法规范有明文规定时,行政机关可以以公共利益为理由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这一过程虽然需要行政相对人的参与与配合,但是,行政行为还是具有支配相对人的意志。行政行为的先定力就是这种效力的鲜明表现。但是,这种先定力的前提是“行政法规范的明文规定”,如果不具备此前提,则行政机关径直作出行政行为并执行之的行为就值得反思。
(14)对法官是否必须对其判决作出理由说明学术界有过争论。而实践中,法官一直以来也并未就其判决作出理由说明。但是一般认为,欧洲人权公约第六条关于公正、公开听证的规定是要求法官承担理由说明义务的直接法律根据。关于法官是否应当进行理由说明的详细介绍见H L Ho The Judicial Duty to Give Reasons 20 Legal Stud.42,2000.
(15)关于权力/控制模式的缺陷详见Timothy A.Wilkins and Terrell E.Hunt APPROACHES TOWARD THE REGULATED COMMUNITY AS A MODEL FOR THE CONGRESS-AGENCY RELATIONSHIP 63 GEO.WASH.L.REV.479 1994-1995.
(16)ATIYAH认为司法主要有两大功能,一项是纠纷解决,另一项则是行为激励(HORTATORY FUNCTATION)。详细介绍见P.S.Atiyah From Principle to Pragmatism:Changes in the Function of the Judicial Process and the Law 65 Iowa L.Rev.1249 1979-1980.
(17)行政正义(administrative justice)这个概念是由Jerry Mashaw在其著作《官僚的正义》中首次提出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在该书中作者对行政正义的概念和意义进行了研究分析。参见杰里·L·马萧.官僚的正义——以社会保障中对残疾人权利主张的处理为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8)对此,丹宁勋爵在R.V.Gaming Board for Great Britain,ex p.Benaim and Khaida等判决中有过论述。
(19)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inister's Power,Cmd 4060(1932)at 76-80.
(20)组织学的研究表明:行政机关具有适应性。因此,在法律课于其理由说明的义务之后,行政机关出现了对外的(适用于外部)与对内(适用于内部)的两种理由,这就在相当程度上虚置了理由说明制度。因此,不仅要进行事后的说明,对于事前的内部一般性行政规则也要说明理由。
(21)Lorne Sossin An Intimate Approach to Fairness,Impartiality and Reasonableness in Administrative Law27 Queen's L.J.809.
(22)权利概念的变迁表明了政府角色定位。
(23)在80年代晚期,批判种族主义法学的研究表明,就许多边缘性组织而言,正式的法律权利机制对其权利的维护起着重要的作用,而那些赋予行政机关的宽泛裁量权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益处,而恰恰成为了剥夺这些团体的借口。因此,其认为未经组织的行政裁量权较之有缺陷的程序会导致更多的不公正。详细介绍见K.Crenshaw,"Race,Reform and Retrenchment:Transformation and Legitimation in Antidiscrimination Law"(1988)101 Harv.L.Rev.1331; R.Delgado,"The Ethereal Scholar:Does Critical Legal Studies Have What Minorities Want?"(1987)22Harv.C.R.-C.L.L.Rev.301;M.Matsuda,"Looking to the Bottom:Critical Legal Studies and Preparations"(1987)22 Harv.C.R.-C.L.L.Rev.323; and P.Williams" Alchemical Notes:Reconstructing Ideals from Deconstructed Rights"(1987)22Harv.C.R.-C.L.L.Rev.401; and R.Williams,Jr.,"Taking Rights Aggressively:The Perils and Promises of Critical Legal Theory for People of Color"(1987)5 Law & Inequality:A Journal of Theory and Practice 103.
(24)应松年,杨小君.法定行政程序实证研究——从司法审查角度的分析[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5.31.
(25)转引自舒国滢.法律论证中的若干问题[EB/OL].http//www.law-thinker.com/show.asp? id=2999
(26)关于法律论证的相关问题讨论见伊芙琳·T·菲特丽丝.法律论证原理——司法裁决之证立理论概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7)Martin Shapiro THE GIVING REASONS REQUIREMENT 1992 U.Chi.Legal F.179.
(28)这种情况:在杨小君教授的文章中也得到了反映,其认为,随着程序制度和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就不能再满足于这些起码的形式要求了,而是要进一步提出程序步骤的作用问题,每一个步骤是否起到了它应当起到的作用。这就是程序制度和理论在朝着实质意义的方向发展。参见应松年,杨小君.法定行政程序实证研究——从司法审查角度的分析[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5.31.
(29)例如台湾行政程序法159条第1项规定,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或长官对属官,依其权限或职权为规范机关内部秩序及运作,所为的非直接对外发生法规范效力之一般、抽象之规定。
(30)章剑生教授教授认为,理由说明制度意义除了限制行政恣意之外,还有提高可接受性和树立行政权威的作用,而这两个作用显然在某种程度上与教育和正当化作用有着相通之处。
(31)行政机关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对峙还是合作?对此,有着不同看法。但是,笔者认为导致这种情形的根本原因可能在于我们将理论假设与实际情况相混淆了。
(32)WADE Administrative law 5th edn(oxford 1982)pp 486
(33)Carl J.Friedrich,"Authority,Reason,and Discretion," in Carl J.Friedrich,ed,Authority 28(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
标签:法律论文; 行政事实行为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正当程序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规范分析论文; 案件分析论文; 法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