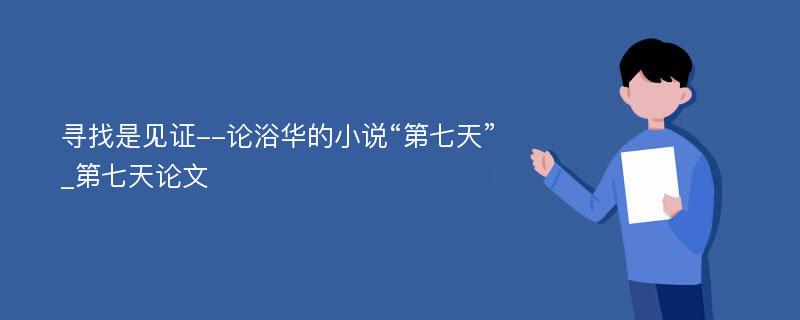
寻找,是为了见证——论余华的长篇小说《第七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篇小说论文,见证论文,是为了论文,第七天论文,余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余华的《活着》是一个被动性的、等待的故事,那么他的《第七天》则是一个主动性的、寻找的故事。当福贵在等待中被迫承受着一个又一个巨大的人生劫难,他依然相信,活着是一件重要的事;而杨飞却无法通过这样的命运来证明“眼泪的宽广”,他只能让自己的亡灵去寻觅人间应有的关爱与尊严。“我游荡在生与死的边境线上。雪是亮的,雨是暗淡的,我似乎同时行走在早晨和晚上。”①在这种迷惘式的叙述引导下,我们跟随主人公杨飞的步履,一次次穿越生与死的鸿沟,穿越过去与现在的栅栏,审视死的悲凉,体悟生的伤痛。
在《第七天》里,余华一直在演绎这样的场景:生者寻找死者,死者寻找生者;儿子寻找父亲,女孩寻找恋人;现实寻找记忆,事实寻找真相……可以说,“寻找”是各种故事相互交织的纽带,也是小说叙事的内驱力。通过“寻找”,余华想展示怎样的生活?借助“寻找”,余华想表达怎样的思考?无论人们对这部小说持有怎样的异议,我以为,在那种漫长而无望的“寻找”中,有许多内涵依然值得我们认真地发掘与思考。
一切都是从“寻找”开始。在《第七天》里,当杨飞赶到殡仪馆里候烧时,发现没有墓地的人将无法火化,他的亡灵只好踏上了茫然无措的漫游之途。这是他死后第一天的遭遇,也是他“由人变成鬼”之后所面临的全新问题。角色的转变,首先需要的是“自我的确认”。因此第一天的叙述,主要是围绕着杨飞的最后人生轨迹,努力还原他为何成为一个亡灵的真相。于是杨飞不断地向记忆发出邀请,从市政府广场抗议强拆的人群,到郑小敏无助地坐在废墟上等待父母,从谭家菜饭店里看到有关李青自杀的报道,到饭店突然遭遇火灾爆炸,他艰难地复苏了自己从生到死的过程,也激活了他寻找失踪养父的艰难历程,同时还打开了阴间与阳界自由往返的心灵通道。
这个通道的建立非常重要。它有些类似于卡夫卡的《变形记》。在《变形记》的开头,当格利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大甲虫时,他首先要解决的,也是角色变化后的自我确认。他认真地观察房间内的各种布局,桌上的物品,身体两侧不断蠕动的细脚。当这一切确认无疑之后,他才开始了一只大甲虫的生活。——当然,从叙事上说,这也解决了读者心中的疑虑。《第七天》里的“第一天”也是如此。从死亡开始,杨飞通过艰难的回忆,既确认了自己是一个带着残破躯体的游魂,也实现了自己在阴间与阳界之间自由穿梭的可能。从叙事功能上说,它也解决了读者内心的现实障碍,让人们明确地意识到,这部小说将是通过一个亡灵来叙述他的故事。
正因如此,我们常常读到,“我走出自己趋向繁复的记忆,如同走出层峦叠翠的森林,疲惫的思维躺下休息了,身体仍然向前行走,走在无边无际的混沌和无声无息的空虚里。”②“我继续游荡在早晨和晚上之间。没有骨灰盒,没有墓地,无法前往安息之地。没有雪花,没有雨水,只看见流动的空气像风那样离去又回来。”③这类极具时空张力且又不乏诗意的叙述,成为杨飞的亡灵每天必须面对的一种活动处境。作为一个游魂,杨飞存在的唯一方式就是“行走”。通过“行走”,他要寻找自己的人生记忆,寻找失踪一年的养父;通过“行走”,他遇见更多的亡灵,看到他们同样也在寻找阳界的亲人,以及阳界的记忆;通过“行走”,他还发现了许多阳界的重要事件,其背后都有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真相。
正是通过阴间与阳界之间的频繁穿梭和行走,杨飞几乎是不自觉地踏上了漫漫的寻找之途。表面上看,他是要寻找身患绝症且失踪一年之久的养父杨金彪,以期重返当年相濡以沫的温暖生活,而实质上,寻找养父只是整个小说的一条叙事主线。在这条主线的统摄下,我们可以发现,《第七天》主要由三个层面的故事所构成:一是杨飞的个人成长史和命运史,包括他与养父杨金彪、亲生父母的关系,他与李青的婚姻生活等;二是“死无葬身之地”的阴间世界,那里简单,纯朴,和谐,平等,自由,充满了至善至美的人性理想,是一种乌托邦的建构,与诡异的阳间世界形成了绝妙的反衬;三是杨飞在阴间寻找养父亡灵过程中,碰到的一个个亡灵所倾诉的生前故事,主要是死亡过程的真相还原。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层面的故事都是通过“寻找”来呈现的。先看第一个层面的故事,即有关杨飞的成长史和婚姻史的叙述。它主要集中在第二天和第三天的叙事之中,是杨飞的亡灵通过对自己记忆的寻找,逐步还原出自己在人世间艰辛而温暖的成长史,以及温馨而又苦涩的婚姻史。作为亡灵的杨飞,终于打开了自己曾经活着的记忆,所以,这些记忆性的叙事都是写实性的,是对现实的努力还原。由是,我们看到,尽管他与李青的婚姻经历近乎于《天仙配》的翻版,是由真诚和坦荡建构起来的一段奇缘,但依然充满了甜蜜而深厚的情感。他们生前由合而分,死后又由分而合,彼此之间所展示出来的,却没有任何抱怨和嫉恨,只有关爱、眷恋、理解与体恤。这段姻缘几乎摆脱了所有世俗的羁绊,呈现出圣洁而高迈的伦理情操。但人毕竟是生活在世俗社会中,与一个恶俗的时代作战,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和智慧,还需要清晰而坚定的内心律令,尤其是对于李青这样渴望“成功”的女性,所以这段婚姻的失败,注定是不可避免的。
从婚姻开始,杨飞继续沿着记忆的铁轨向远方寻找,由此也缓缓地打开了他那曲折艰辛的成长史。这便是第三天的叙事核心。它同样是一个温暖而又悲情的故事。从火车厕所里诞生之后,杨飞便成了一个孤儿。所幸的是,年轻的扳道工杨金彪发现了他,并用全部的精力将他抚养成人。当然,还有邻居郝强生和李月珍一家无私的相助。在这一天的叙述中,余华依然动用了他那异常强悍的写实能力,将杨飞的成长过程书写得感人至深。无论是杨金彪因为遗弃杨飞而产生的一生的自责,还是李月珍母亲般长期无私的呵护;无论是杨飞与亲生父母相认,还是后来为养父卖房治病,在这一过程中,贫穷和苦难并没有击倒他们,相反却使他与养父之间相依为命的生活显得极为温暖。在那里,我们看到,杨金彪既是一位像大山一样沉默的父亲,又是一位像大海一样宽广的父亲,他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用全部的生命,哺育杨飞的成长,并且无怨无悔。“我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认为自己一生里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收养了一个名叫杨飞的儿子。”④这种超越血缘的父子之情,看似平凡,却是撼魂动魄。
通过婚姻与成长的复述,杨飞终于打开了自己的全部记忆,完成了他对自身历史的寻找和再现,“我的记忆轻松抵达了山顶,记忆的视野豁然开阔了。”⑤从第四天开始,小说转入阴间的世界,开始叙述第二个层面的故事。这依然是一个有关寻找的故事。在鼠妹刘梅的带领下,杨飞终于抵达了“死无葬身之地”。在那里,亡灵们都熟知各自生前的遭遇,他们相互调侃,彼此友善,向每一个后来者打听自己死前的境况,同时又以向导般的姿态,为后来者提供一切帮助。这意味着,杨飞寻找养父的亡灵将成为可能,但又充满了无数的不确定性,因为所有时间太久的亡灵都已变成了没有面容和表情的骨骼,只能通过声音才能辨认。
这种寻找的不确定性,带来了另一个叙事空间的拓展,那就是第三个层面的故事,即很多亡灵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复述。这些复述摆脱了杨飞自我叙述的写实特征,很多时候转为全知视角,呈现出荒诞性的戏谑意味,直接呼应那些人世间曾经出现的新闻事件。如鼠妹刘梅对自己生前情感的叙述,尤其是当她发现男友伍超送给自己的礼物是一只苹果高仿手机之后,选择以跳楼方式逼迫伍超现身时,叙述视角其实转换为局外人,叙述的重点也转向广场上的看客。于是我们看到,卖墨镜的,卖快活油的,甚至卖窃听器的,都热情地穿梭在众多的看客之间,而刘梅的生死,成了他们谋利的契机。这不能不让人想起鲁迅对中国看客心态的分析。这里,刘梅想通过极端的方式,寻找自己的男友伍超,却发现自己以生命的代价,最后找到的只是人间的冷漠。同样,张刚和姓李男人之间的恩怨,也是在寻找中陷入怪圈。姓李男人因为男扮女装去卖淫而被踢坏了睾丸,从此不断寻找张刚,要他还自己一双睾丸。在漫长的寻找与等待中,他绝望地杀死了张刚,自己也成了阴间的亡灵。
寻找是艰难的。“我寻找父亲的行走周而复始,就像钟表上的指针那样走了一圈又一圈,一直走不出钟表。”⑥这种寻找过程的延展,为更多的亡灵呈现自己的生前故事提供了大量机遇。所以,在第五天和第六天里,杨飞在寻找养父亡灵的过程中,几乎变成了一个倾听者,一个诸多真相的记录者。在那里,遭遇商场火灾的38个亡灵,终于道出了自己死无墓地的原因,那是他们的家人被封口费锁住真相的结果;郑小敏的父母也终于道出了被强拆埋葬而死的事实;背负杀妻冤案而死的亡灵终于道出了刑讯逼供的情景。在那里,李月珍带着27个被视为医疗垃圾的婴儿,讲述了官员偷梁换柱的经过,以至丈夫和女儿抱着别人的骨灰登上了赴美的飞机;同时,李月珍也道出了杨飞养父亡灵的去向。在那里,肖庄遇见了鼠妹刘梅,进一步补充了刘梅死后伍超的生活——为了给刘梅买块墓地,身无分文的伍超,通过黑市卖掉了自己的一只肾脏……所有这些,在阳界的生活里都曾是一些重大的社会新闻,但都是被修饰、遮蔽或歪曲的新闻,现在,通过一个个亡灵的复述,真相逐渐得以还原。杨飞作为一个后来的倾听者,他在无意之间,终于找到了太多的事件真相——尽管这些真相是如此的荒诞不经。
由于李月珍的亡灵提供了准确信息,杨飞终于知道了养父的去向,同时也知道了养父的失踪之谜——他用尽自己最后一丝力气,为当年抛弃杨飞而进行了一次艰难的心理赎罪,并因此客死异地。所以,到了第七天,在完成了刘梅神圣的净身之后,杨飞和一群亡灵簇拥着刘梅来到了殡仪馆,将她送上了安息之地,而杨飞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养父。即使死后没有葬身之地,养父仍然坚持守候在殡仪馆充当“管理员”,为了等待终有一天会到来的儿子;当他看到儿子这么快地来到阴间,杨飞“看见他空洞的眼睛里流出两颗泪珠”。这对相濡以沫的父子,又在相依为命中开始了生命的另一种轮回。
从寻找养父开始,到父子相见而终,《第七天》以创世神话的思维,从阳界到阴界,完成了一次旷世般的寻找之旅。通过杨飞的寻找,小说又打开了更多亡灵的生前记忆,呈现了无数亡灵的死亡真相。这些真相,因为一个个生命的消失,早已被阳界的各种现实秩序所埋藏,只有在阴间才能得以还原。而这,正是《第七天》别具一格的审美意图。
活着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但死去也同样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即使是在殡仪馆的候烧室里,仍然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区别。通往安息的路是如此的曲折,同样布满了人间不平等的沟沟壑壑。在长达七天的游走中,杨飞所见到的,只有李青和刘梅踏上了安息之路,更多的亡灵只能在“死无葬身之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游荡。所幸的是,“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⑦——这当然只是余华虚设的乌托邦愿景,为了给那些无辜的亡灵提供一个美好的栖息之地。
事实上,当余华不断地动用极具诗意的笔触,精心地营构着所谓的“死无葬身之地”时,他的叙述依然无时无刻不在直面我们当下的现实。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第七天》中,所有关于阴间世界的理想性建构,只是一种声东击西的表达手段,一个创作主体用来观察社会、审视现实的视点。余华的真实意图,就是要对当下缭乱而无序的现实生活,进行一次多层面、立体化的现场直击。他试图借用这种“以死观生”的叙事策略,打开当下现实中各种吊诡的生存现状,展示一个作家内心的焦灼与疼痛,传达创作主体对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深层思考。
这种思考是忧伤的,也是激愤的。无序的现实已经对余华的内心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压力,一种挥之不去的隐痛,使他不得不产生书写的冲动。因为在近30年的写作历程中,余华一直对当下的现实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有意无意地与之拉开距离。他曾不止一次地强调,自己与现实之间有着极为紧张的、不信任的关系。无论是在早期暴力化的先锋实验中,还是在后来执着于温情化的故事书写中,余华总是刻意地游离当下的社会现实,将背景处理得更模糊或更遥远一些。即使是《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也都与当时的现实保持着特定的距离。
到了《兄弟》的下部,余华终于忍不住了。于是,他让李光头一路高歌猛进地挺入当下的生活。作为一个混世魔王,李光头就像一台欲望的发动机,永远保持着亢奋的激情,不断地炮制各种闹剧性的社会群体事件,将刘镇拖入一场又一场狂欢化的欲望派对之中,并使自己赢得了世俗的各种荣耀。无疑,李光头就是混乱的现实制造出来的一个欲望怪胎。他的命运之中,凸现了余华对这个失序世界的焦虑、无奈和嘲讽。
与《兄弟》颇不相同,《第七天》在逼近缭乱的现实时,没有了狂欢的氛围,也没有了过度嘲讽的格调。但它所凸现出来的,依然是余华对当下现实的愤懑、焦虑、感伤,甚至是无奈。只不过,他将主人公由世俗欲望的操纵者,换成了世俗欲望的受害者。也就是说,它以受难者和受辱者的形象,展示了这个时代的混乱、荒诞和吊诡。在那里,强拆事件、黑市卖肾事件、袭警事件、毒食品事件、弃婴事件、瞒报灾难死亡事件、刑讯逼供事件……所有这些事件,最终都是以屈死者的生命为代价,被现实巧妙而轻松地掩盖在一篇篇新闻报道之中。他们找不到向世间传达真相的窗口,只能在阴间相互倾诉。没有人知道它们的真实原因,也没有人能够追索其中的真正问题。
有很多人认为,《第七天》中吸纳了大多的新闻事件,以至于像“新闻串烧”和“微博汇编”,显得有些“轻和薄”(郜元宝语);还有人甚至断定,余华完全丧失了基本的艺术想象力。我以为这类看法有失偏颇,至少没有理解余华的真实用意。在一个全媒体的时代,我们都生活在信息编码中,我们对于现实状况的判断,很多时候都来源于各种信息的聚合,尤其是新闻报道。特别是近些年来,各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社会事件层出不穷。它们纷纷跃上各种媒介的醒目位置,但在转瞬之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新闻的速朽与人们的遗忘,构成了速度层面上的循环比赛。面对现实,我们由新闻的快速更替而养成了快速遗忘的适应性心理,并进而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麻木和见怪不怪。
然而,这是中国当下的现实,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实。它们记录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阵痛,承载了很多平民百姓真切的命运,我们不能因为新闻的速朽而遗忘。它们需要一个有效的文本来承载、记录与反思。当余华直面这些社会的现实时,他没有选择虚构,而是直接择取了这些真实的新闻事件,并对之进行稍加改写。余华这样处理,不是艺术想象的贫乏或偷懒,而是为了最大程度上的存真,为中国存真,为记忆存真。所以余华精心选择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新闻事件作为底色,多角度、多方位地呈现了这个时代的荒诞景象。如果只有一两个事件,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这只是一种偶然,而当这么多真实而又吊诡的事件集纳在一起,那就足以说明当下现实的混乱与荒谬了,也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了。诚如有人所言:“让新闻成为‘世态’、让世相成为‘存在’、让戾气化为‘情感’、让‘正能量’沉淀为‘价值观’。余华用作家的胃口艰难地吞咽并顽强地消化着‘新闻’,以绝不遗忘和咀嚼反刍的姿态,让痛深入骨髓,让爱融入心灵。”⑧用绝对真实的新闻事件作为凸现现实的手段,并进而展示这些新闻事件背后的荒诞与沉重、悲凉与疼痛、愤怒与绝望,是《第七天》的内在底色。试想,如果文明无力保护弱者,如果现实无力展示真相,如果尊严无法获得维护,作为一个一直生活其中的作家,只要稍有良知,我以为,都会做出应有的承诺和回应。
当然,回应的策略和方式会因人而异。譬如,阎连科的《风雅颂》就选择了狂欢式的反讽性叙事;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动用了多角度的聚焦式呈现,甚至也不乏亡灵的对抗和戏谑性的反讽;而苏童的《蛇为什么会飞》则选择了某种寓言化的表达策略,让欲望之蛇横行于生活的角角落落。在《第七天》里,余华选择了亡灵的视角,并在叙事上做了两个前提上的限定:首先是杨飞为了寻找养父的亡灵。这意味着,他虽然是一个倾听者,但他无暇去听每个亡灵完整的一生,也不可能像《活着》那样,可以让福贵进行漫长的叙述。其次是每个亡灵与他相遇时,杨飞的主要目的是要帮助他们恢复死亡前的状态或死亡事件,而不是要打探他们各自的一生。所以,在双重限制之下,余华只能对那些亡灵事件进行简约化的处理。当然,他也尽可能对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件进行了反复的补充式叙述,像伍超与鼠妹刘梅的爱情。
无论现实是怎样的荒诞和残酷,但爱、牺牲、体恤……这些人类引以为荣的人性之光泽,终究不会泯灭。它是照亮幽暗现实的烛火,也是反抗沉重现实的法宝。《第七天》不断地呈现各种来自底层的人性之光,包括宽广无私的爱,无怨无悔的牺牲,深切的体恤,它们沉淀在杨金彪、李月珍、伍超、刘梅、杨飞、李青等等人物心里,不时地散发出迷人的光泽。这些来自阳界底层生活的人性,构成了《第七天》追问荒诞现实的一个视点,也折射了余华对于理想人伦的渴望,以及对“诗性正义”的强烈捍卫。余华曾多次强调,30多年来的飞速发展,给中国社会创造了无数的物质奇迹,却也留下了无数匪夷所思的精神奇观。在这些精神奇观里,余华看到的是世道人心的破败和凋敝,是美好人伦的不断倾斜和坍塌,是无数生命的悲剧与喜剧同台共舞。但他也同样发现,在无数卑微的生命之中,依然闪耀着人性的光泽,依然弥漫着人间特有的温情。
我们有理由认为,在《第七天》里,“寻找”只是故事的外在形式,只是叙事的内驱力。“寻找”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和再现。它意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亡魂都见证了一种荒诞的现实,每一个亡魂也道出了世间的一个真相。寻找,是为了见证。既见证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混乱和浮躁,也见证了善良人性的光泽。
从结构上看,《第七天》是紧凑而简洁的。它从寻找出发,让杨飞的亡灵不断穿越于阴阳两界,一边复活自己的记忆,打量阴间的世界,一边倾听各种亡灵的遭遇,不断还原种种被现实遮蔽的真相。经过七天的奔波,杨飞终于打开了生与死的双重世界,并揭示了大量令人震惊、揪心、感伤、愤懑的现实景象。在这一结构中,余华精心营构了一种内在的叙事逻辑:杨飞必须要找到相依为命的养父。生前,他已卖掉了房子,关掉了小卖店,又四处打探商场火灾的死难者,甚至找到了他从未去过的养父家乡……在所有他能寻找的地方,他都不曾放弃。在濒临绝望之际,杨飞终于在饭店的爆炸事故中身亡,由此开始了在阴间对养父的继续寻找。这种“上穷碧落下黄泉”式的寻找,使整个叙事弥漫着浓厚的温情,也昭示了人性中超越血缘的爱与牺牲。
尽管亡灵视角的选择并不是余华的独创,像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都是以亡灵的视角展示了沉重而吊诡的历史,但对于习惯常态视角的余华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挑战,多少也体现了他试图突破自我的积极姿态。这一特殊的人物视角,不仅有效地控制了整个故事的发展,也使叙事的空间变得自由而广袤。事实上,《第七天》里每一个新闻事件的背后,都有一个完整而悲怆的故事,但都因杨飞要寻找养父而变成了片段,只有刘梅与伍超的爱情,在几个亡灵的补充诉说中变得相对完整。这种叙事的剪裁,既符合故事的情节逻辑,又体现了余华的简约风格。
从叙事的审美格调上看,《第七天》依然承续了余华某些一以贯之的写作特质,如悲剧与喜剧相交融的叙事方法,对底层平民生存及命运的深切体恤之情,对荒诞现实强烈嘲讽的姿态,以及异常简约的叙事风格。这些特点,在余华以往的小说中都体现得非常明显。像《在细雨中呼喊》里,既有孙广才天才般的无赖行径,又有孙光林的孤独、恐惧和绝望;《活着》中的福贵,曾经是一个败光了所有家产的纨绔子弟,最终却以巨大的韧力承受了无数的人生劫难;《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同样也是苦中作乐,悲中求欢,甚至用“嘴巴炒菜”对抗饥饿;《兄弟》更是悲喜交集,浓郁的亲情与世俗的欲望,在两兄弟之间形成了各种奇妙的交织……所有这些长篇,其实都显示了余华是一个擅长悲喜交织式叙事的作家。他崇尚极致美学,喜欢在大喜大悲之中展示人物的命运,传达自己的审美追求,同时又讲究简约轻盈的原则,以叙事的“减法”(张清华语)取胜。
在《第七天》里,最引人注目的,无疑也是这种悲喜相融的叙事策略。它立足于底层平民的深厚伦理,又直指现实秩序的荒诞无序;它深入到一个个生活现场,又超然于各种现实之外;它紧扣着杨飞的视角,以不同的方式向记忆与现实、阴间与阳界发出各种邀请。这种分裂式的叙事策略,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很少有人运用,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的作家更少。余华对此却操控自如,且又显得异常简约。所以,程永新由衷地说道:“奇异幻想和残酷现实浑然天成,一扫充斥文坛的庸俗叙事,与大量伪写实作品相比,《第七天》犹如存活率稀少的优质婴儿。幻想和现实结合后的基因,汩汩流淌在此书的血液里。”⑨的确,在这部小说中,各种奇异的幻想随处可见,从杨金彪准确分辨婴儿杨飞饥饿之声与口渴之声的区别,到“死无葬身之地”里种种匪夷所思的祥和与平等,这些超验性的叙事,与坚硬的现实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既尖锐又温暖、既真实又怪诞、既质朴又戏谑的审美特质。
这种审美特质,强化了《第七天》在叙事形式和精神内涵上的张力关系,也使余华在逼视现实时,更有效地凸现了自身的人道立场和价值观念,从而建构了一座通往“诗性正义”的审美桥梁。玛莎·努斯鲍姆曾说:“小说阅读并不能提供给我们关于社会正义的全部故事,但是它能够成为一座同时通向正义图景和实践这幅图景的桥梁。”⑩就《第七天》而言,寻找,是为了见证,但见证并非是余华的最终目的,而是他质询、追问和反思的目标。余华试图通过对荒诞现实的举证和质证,努力唤醒我们渐行渐远的人性之美。如果绕开二元对立的思维,我们会发现,《第七天》里各种张力关系的建立,都明确地折射了创作主体对无序现实进行无情解构的价值立场,即以亲情、友爱、平等、体恤、牺牲来对视混乱而丑陋的现实,以乌托邦式的“死无葬身之地”来洞穿现实世界的幽暗与冷漠。所以,《第七天》的整个叙述基调,始终是温暖而绵长的,凸现了作家内心深处宽厚的人道情怀。尤其是在他动用写实的笔触时,总是能够迅速抵达人性中最柔软的部位。譬如,当他叙述9岁的郑小敏坐在寒风冷冽的废墟中做作业时,他会让小女孩情不自禁地说道:“爸爸妈妈回来会找不到我的”;当他叙述养父的亡魂时,“他的声音有着源远流长的疲惫”,明确地呼应养父重病在身的现世镜像;在叙述杨金彪的五位农民兄弟的悲伤时,“这五个老人眼圈红了,可能是他们的手指手掌太粗糙,他们五个都用手背擦眼泪”;在小说的结尾,当所有的亡魂都为刘梅净身、缝衣,咏歌时,一切都变得如此的圣洁,如此的华光四闪。
在喜剧性手法的表达上,《第七天》主要体现在余华对吊诡、荒诞的现实事件处理中。它的语调体现为反讽性、戏谑性和嘲解性,从而使强拆、毒食品、袭警、卖肾、瞒报灾情……这些我们经常面对的现实,呈现出某些漫画式的审美效果,凸现了理性萎缩、欲望增殖之后,当下社会里所涌现出来的各种反伦理、反逻辑的生存景象。当基本的理性缺失之后,当基本的公正无法维持的时候,当弱者永远也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时候,我们已很难用逻辑来建构现实,而用荒诞来表现荒诞,也许是一种更有效的策略。我以为,这或许是余华的真实用意。《第七天》里的喜剧性表达,常常直指现实本身的失范和失序,如刘梅跳楼时,广场上围观的人群里却穿梭着各种小贩;一场扫黄打非行动,结果却让一个嫌犯失去了一对睾丸;张刚的父母为儿子申请烈士,最后成了专业的上访户;谭家菜饭店在阴间的开张,成了食品最安全的饭馆;夫妻双双下班回家休息,却在浑然不知的强拆中葬身废墟……这些叙事不断溢出经验的范畴,也溢出了我们对社会进步理念的理解范畴。它是众多平民百姓的生存之痛,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伤痛。
嘲解不只是因为焦虑和愤懑,还有感伤和无奈、警示与反省。本雅明曾经说过:“所谓写小说,就意味着在表征人类存在时,把其中不可通约的一面推向极致。处身于生活的繁复之中,且试图对这种丰富性进行表征,小说所揭示的却是生活的深刻的困惑。”(11)毫无疑问,《第七天》所直面的,正是这种异常“繁复”的生活。余华将那些荒诞的现实不断地呈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将现实中“不可通约的一面”推向了极致,并由此表达了创作主体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与思考,以及对“诗性正义”的彰显与召唤。
①②③④⑤⑥⑦余华:《第七天》,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63、108、111、92、112、143、225页。
⑧刘广雄:《〈第七天〉为何遭遇“恶评如潮”?》,《文艺报》2013年7月17日。
⑨程永新:《与一本书相遇是缘分——谈余华的〈第七天〉》,《文汇报》2013年7月7日。
⑩[美]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公共生活》,丁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11)[德]瓦尔特·本雅明:《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李茂增、苏仲乐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