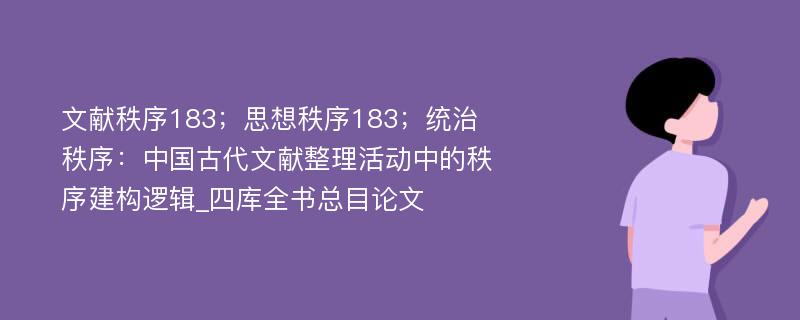
文献秩序#183;思想秩序#183;统治秩序——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中的秩序建构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秩序论文,文献论文,中国古代论文,逻辑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2-0147-10
人类对自己生产的文献加以整理,是为了求得文献秩序。中国古代的文献整理活动,不仅产生了文献秩序,而且还“参与”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秩序和统治秩序的建构。这就产生了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中的文献秩序、思想秩序、统治秩序之间是什么关系的问题。本文意在讨论这一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称“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是广义上的统称,即包括对文献加以分类(分类学)、编目(目录学)、编纂与汇编(类书学、百科全书学等)、版本鉴定(版本学和校勘学)、训诂与注解(训诂学、考据学、注释学和诠释学)等多种形式的文献整理活动。限于篇幅,本文以中国古代的文献分类、目录和类书编纂活动为主要讨论对象。
一、文献秩序:秩序建构的表象
求得文献秩序固然是文献整理活动的直接目的。那么,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的目的是否仅仅是求得文献秩序呢?从文献分类和编目的技术性任务看,文献整理的目的似乎就是求得文献秩序。一些学者也是如此言说的,如著名目录学家姚名达在评论《七略》时认为,“书籍既多,部别不分则寻求不易;学科既多,门类不明则研究为难。故汇集各书之叙录,以学术之歧异而分别部类,既可准其论次而安排书籍,以便寻检,又可综合研究而辨章学术”[1](P49-50)。有的学者在总结宋代帝王热衷于编纂类书的原因时也认为,历史发展到宋代,各类书籍已经汗牛充栋,帝王要在生活和听政之余将它们全部阅读,实在是既无此可能,亦无此必要,因而,有选择地编修百科全书式的类书,以供随时查找阅读,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北宋前期的四部著名类书,亦即被人们称为“宋代四大类书”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编修而成的。[2]唐玄宗时,之所以纂修《初学记》这一类书,《大唐新语》载唐玄宗谓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3](P137)也就是说,《初学记》是唐玄宗为了使其儿子学习时的“省便”而“集要事并要文”所成的。这里的“集要事并要文”就是文献秩序的形成过程。唐人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中谈到《艺文类聚》的编纂目的时说:“《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爰诏撰其事且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号曰《艺文类聚》。”[4](P27)
从以上学者们的论述看,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的目的在于求得“集要事并要文”以便寻检的文献秩序。然而,求得文献秩序只是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表面性的、外在的目的,而其中蕴含着更为本质性的、内在的目的。在此以中国古代文献分类目录编制中的“经→史→子→集”次序结构和类书编纂中的“天→地→人→事→物”次序结构予以说明。
1.分类目录中的“经→史→子→集”次序结构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文献分类法大体经历了从“六分法”到“七分法”再到“四分法”的过程。汉代刘歆所编《七略》首创文献分类的“六分法”,即把所有文献分别归入六个大类,这六个大类依次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其中列于首位的六艺略,就是专门用来类分儒家经典著作的,当时把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等九类儒家经典全部归入此类。①此后,南齐王俭纂修《七志》,南梁阮孝绪纂修《七录》,创建文献分类的“七分法”;魏郑默作《中经》,西晋荀勖编制《中经新簿》,东晋李充受命编制《晋元帝四部书目》,一直到唐太宗时期由魏征领衔编修《隋书·经籍志》,终于形成了文献分类的“四分法”体制。所谓“四分法”(全称为“四部分类法”),就是把文献分门别类为经部、史部、子部、集部这四大部类,且其次序固定不变。四分法的集大成者就是清代乾隆朝所修《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纵观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法的演变过程,可以明显地发现一个不变的事实,那就是:无论是“六分法”、“七分法”还是“四分法”,都把“经部”——儒家经典列于首位。那么,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活动为什么始终坚持以经为首的分类次序呢?这就需要我们弄清中国古人对“经”的理解。
《白虎通义·五经》在解释“五经”时指出,“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明代王阳明对“经”也作了“常道”解释,他说:“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5](P254)《汉书·艺文志》则把“经”解释为“圣人之心”、“不易之道”,即“六经者,圣人之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人天之理,可得而知,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正因为经是“永永不易之道”,所以在文献分类中必然把记载经义的书籍(经典)列于首位,以示经的至高无上地位。所谓经典(这里指儒家经典),就是中国封建专制统治阶级“法定”的儒家书籍,随着儒家思想的演变和统治阶级需要的变化,经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故有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三经之名。[6](P654)
经典的地位如此重要,是因为经典乃载道、论道、传道的基本载体,通过经典来体道、悟道,才能实现“内圣外王”的崇高志向。在这种志向的导引下,自然形成两种社会风气:以经取人和“文出于经”。以经取人,自汉武帝实行“四科取士”以来,“明经”成为选官用人的必考科目,虽然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未采用“明经”科目而是以“品第”取人,但随即被隋唐科举制所取代,自此至1905年废科举,“明经”一直是选官用人的必备条件。“文出于经”,其典型表现就是“引经据典”。对古代中国人来说,引经据典是人们考辩论理、作文赋诗必要的表现手法,甚至还是一些人明理善断、聪颖好学的表征。南宋李耆卿在《文章精义》中认为,六经“皆圣贤明道经世之书,虽非为作文设,而千万世文章从是出焉”。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篇》中说:“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议论,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中对此概括地说:“战国之文,皆源出于六艺。何谓也?曰: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这些认识,其实都在提出一个无形的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答案就是:经学知识最有价值。②这说明,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活动的宗旨不在于文献秩序,而在于“明道”,即通过文献分类活动,把统治阶级认可的“经义”(王道)凸显出来,使其法定化。对此,《四库全书总目》凡例十九则说得非常明确:“圣朝编录遗文,以阐圣学、明王道为主。”
那么,为什么必须遵循“经→史→子→集”这种次第关系呢?对此,乾隆皇帝有一段精彩比喻:“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流也、支也、派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故吾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7](P17)乾隆皇帝的这段话,明确了“经→史→子→集”这种次第结构的内在逻辑。这种“经→史→子→集”次第结构,其实就是中国古人对“什么知识最有价值”问题的明确回答。这说明,“斯宾塞问题”在中国古人那里早有定论,只不过中国古人认为“首重者经”而非科学知识。
2.类书中的“天→地→人→事→物”次序结构
类书是通过“辑录”或“撮述”的编纂方法,将多种相关文献中的内容分门别类地加以组织而成的一种文献类型。“分门别类”就需要设类目,且按照一定次序形成类目体系。中国古代类书编纂传统源远流长③,形成与西方百科全书体例不大相同的类目设置体例,所以有人认为中国的类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百科全书。自唐初纂修《艺文类聚》以来,中国古代类书的类目体例基本定型为“天→地→人→事→物”次第格局。④这种次第格局的形成,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对“天—地—人”(所谓“三才”)三者关系赋予特定的秩序意义紧密相关。
汉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立元神》中说:“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从“天、地、人”关系中推出万事万物之本,就形成了“天→地→人→事→物”序列,而这正是《艺文类聚》辑录资料的编排顺序。陈鼓应认为,“三才说”源于《老子》二十五章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先秦道家天地人一体观的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8](P179)。
那么,《艺文类聚》为什么把“物”这个大类排列在最后呢?葛兆光认为,《艺文类聚》中的“物”对应于“自然世界中的各种具体知识”,而这些知识在古代中国传统中往往被认为是“多识草木虫鱼鸟兽之名”的枝梢末节或“奇技淫巧”类东西,所以《艺文类聚》把“物”放在最后,以示其“不雅”地位。[9](P457)其实,在中国古人心目中把物理原理及其应用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的观念极为普遍。《礼记·王制》就说:“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在中国古代文献分类目录中,记载物理的书籍归入“方技”类,而“方技”类在整个类目体系中一般被列于最后,如刘歆的《七略》、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都把“方技”略列于末尾。在古汉语中,“技”、“伎”、“妓”三词同源。可见,在中国古人那里,研究物理的科学技术,往往被认为是“奇技淫巧”,始终处于被鄙视之列。所以,在《艺文类聚》中,“物”这个大类共有40卷,在卷数比例上占了《艺文类聚》全书的五分之二,但却只能占据末尾之列。
在中国现存类书中,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类书。该类书共分六大部类,分别是历象汇编、方舆汇编、明伦汇编、博物汇编、理学汇编和经济汇编,可以看作是按照“天→地→人→物→知→事”序列安排。这种类目设置及其次第安排,看似与传统的“天→地→人→事→物”体例有区别,但仔细分析就可发现,两种体例安排之间并无实质性的区别。首先,“天地人”三类及其次第安排完全相同;其次,虽然多了一个“知”(理学汇编)类,但这只是对传统的“物”类的扩充而已,即传统的“物”类主要指代“自然科学”知识,而“知”类主要指代“人文科学”知识,这可从博物汇编和理学汇编所包含的子目中得到判断,博物汇编的子目包括“艺术典”、“神异典”、“禽虫典”、“草木典”,理学汇编的子目包括“经籍典”、“学行典”、“文学典”、“字学典”;再次,虽然把“物”类置于“事”(经济汇编)类⑤之前,但“物”类和“事”类在总体上处于末尾的地位没有改变。《古今图书集成》的这种“天→地→人→物→知→事”序列安排,其依据在“凡例”中作了明确交代:“法象莫大乎天地,故汇编首历象而继方舆。乾坤定而成位其间者人也,故明伦次之。三才既立,庶类繁生,故次博物。……次理学经济,而是书备焉。”
由此可知,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从表面上看是在追求文献秩序,但在这表象背后还有一种更为深层的秩序追求。也就是说,文献整理活动所产生的文献秩序必须体现出更为深层的一种秩序。这种更为深层的秩序就是思想秩序。
二、思想秩序:文献秩序的深层指向
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的首要任务,并不是给每一文献以知识分科体系中的某一固定位置,而是赋予每一文献以特定的价值意义(此即为“赋义”)。所以,中国古代的文献分类,实际上并不是学科分类或知识分类,而是价值意义分类。类书编纂活动中的立类及其次第安排,也不是按照知识分科体系立类,而是按照类目名称所蕴含的意义之别来分门别类并安排其次第。这就说明,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并不是一种客观分类过程,而是一种主观赋义过程。那么,这种主观赋义过程是不是一种纯粹“随意”的过程呢?也不是,而是始终遵循一种标准,即依据儒家坚守不渝的伦理教化标准来为每一文献赋予伦理价值意义。对此,傅荣贤指出,中国古代文献分类,在类目次序的安排上普遍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即意义和功能大的类名(或文献)排在意义和功能小的类名(或文献)之前,意义和功能相同或相近的类名(或文献)靠得较近,这种安排体现了一种规律性:文献按照其内涵的意义和功能递减序列排序。[10](P110)当然,傅荣贤所说的“意义和功能”,指的是伦理教化意义和功能。人们都知道,儒家强调伦理教化,其目的就是为了整饬人们的思想秩序,使人们的思想观念都趋附于儒家所宣扬的尊经重道的秩序,这就是所谓的“道统”。那么,中国古代的文献整理活动是如何给每一文献赋予伦理价值意义,从而服务于思想秩序建构的呢?本文从以下三方面予以论述。
1.通过判断文献所表达的立场来分别处理文献
在中国古代的文献整理活动中,并不是把所有的文献都予以翔实整理,而是根据文献作者所表达的政治或伦理立场来分别予以处理。在这方面,《四库全书总目》表现得尤为突出。
针对《四库全书总目》的收录原则,乾隆皇帝作出了一道严厉的规定:“今所采录,惟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狭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对这一原则,乾隆帝数次降诏明确指出,“令总裁等悉心校勘,分别应刊应抄及存目三项,以广流传”,“谬于是非大义在所必删”,“词意抵触本朝者当在销毁之例”,“有俚浅讹谬者止存书名”,“悖于义理者自当从改”。由此可以看出,《四库全书总目》对所收录的文献进行了“录”、“存”、“删”、“改”、“毁”等有区别的处理。所以,每篇提要的后面,都附有总纂官提出的“应刊刻”、“应钞录”、“酌存目”、“毋庸存目”等意见。总体而言,《四库全书总目》所处理的文献主要分为著录、存目、销毁三类。
《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并刊刻的文献自然属于那些被编撰者认为符合当朝政教人伦价值取向的“应刊”文献,共著录了3461部。而那些被认为是“言非立训”或者是有所“违碍”的文献则只为其“存目”,共存目6793部,比著录文献数量还多。如李贽的《藏书》和《续藏书》就被《四库全书总目》编撰者批评为“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故将此两书打入存目类。而那些被认为是“离经畔道,颠倒是非”或“怀诈狭私、荧惑视听”的文献,则坚决予以销毁。据统计,在《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过程中,用于禁书和毁书的时间达十九年之长,共禁毁书三千一百多种、十五万一千多部,销毁书板八万块以上。对此,顾颉刚说:“以故网罗虽富,而珍闻秘笈之横遭屏斥者乃难悉数。惟其寓禁于征,故锢蔽摧残靡所不至,其沦为灰烬者又不知几千万卷也。”[11](原序,P1)王重民曾指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思想内容集中在宣传封建思想和消灭民族思想的两个主要方面”[12]。也就是说,有悖于宣传“封建思想”和“狭隘民族思想”的书籍,必然遭禁、遭毁。
2.通过类目次序安排界定文献意义的大小
通过类目次序安排来显示文献意义的大小,是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中“意义分类”的常用手段。如在《七略》中,六艺之学和诸子之学被认为是“大道”之所存,故排列于前;而数术、方技之学则被认为是形而下之“艺学”,故排列于后。杜定友曾说:“夫古之学术有道器之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诸子之学,所谓道者也,为无形之学;术数方技,所谓器者也。虚理实事,义不同科。”[13](P44)如术数略在子目顺序的安排上,从天文到历谱,从五行、卜筮到形法,其次序是从天上到地下,先天文而后地理,构成了前后有序的知识价值序列。在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思想体系的演变过程中,始终贯穿着经学为上、技艺为下的传统,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为什么自然科学知识不受重视的思想根源。
在类书的部类设置及其次序的安排上,明显地反映出以儒家的伦理秩序观念来划定文献(资料)价值大小的意图。如《艺文类聚》共设四十六部,前二十一部依次为:天部、岁时、地部、州部、郡部、山部、水部、符命部、帝王部、后妃部、储宫部、人部、礼部、乐部、职官部、封爵部、治政部、刑法部、杂文部、武部、军器部(剩下二十五部均属“物”部类)。这二十一部严格按“天→地→人→事”序列编排,其中从符命部到军器部(共十四部)属于“人”部类,其次序安排逻辑是:附命乃证明帝王是上帝的安排,故置于帝王之前;帝王、后妃、储宫是人间主子,故置于人部之前;礼、乐是维系人伦秩序的基本规范,故紧接于人部之后;职官、封爵、治政、刑法是“治人”的基本手段,而杂文、武是支撑帝王统治的理论依据和实力基础,故置于“殿后”位置。再如《古今图书集成》的“明伦汇编”下有若干子目,依次为:皇极典、宫闱典、官常典、家范典、交谊典……对这种次序安排逻辑,《古今图书集成》凡例曰:“伦莫大于君父,化必始于宫闱,故首皇极而次宫闱。百职惟贞,臣道之常也,故次曰官常。修身齐家,父子兄弟足法,故次曰家范。师教友规,推之宾客,里党皆有交谊,统之曰交谊。”雍正皇帝在为《古今图书集成》所作的序中说明了全书六大部类次序逻辑:“始之以历象,观天文也;次之以方舆,察地理也;次之以明伦,立人极也;又次之以博物、理学、经济,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治国、平天下之道咸具于是矣。”这说明,某一文献(资料)的意义的大小,取决于该文献(资料)所属的类目在整个类目体系中的位置,而某一类目的位置又是由统治阶级对该类目思想意义的主观界定所决定的(这里针对官修类书而言)。
3.通过作“序”的方法来表达编纂者的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的一些书目著作有为类目作“序”的体例安排。置于部类者,谓之“总序”;置于小类者,谓之“小序”。如《四库全书总目》的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余嘉锡说:“小序之体,所以辨章学术之得失也。”[14](P56)这种“序”文为编撰者发挥主观“赋义”(即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之能事提供了有效空间。如《隋书·经籍志》总序云:“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前一段话,表达一般意义上的经籍的功用,后一段话则表达了编纂者的一个重要价值判断,即把儒家经典、方技数术、诸子之言的功用归结为“为治之具”。又如《汉志·艺文略》总序云:“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此学者之大患也。”在这段话中,班固委婉地批评了两汉时期今文经学者们“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的乱发义理、牵强附会、主观臆断之“学者之大患”。这是通过作“序”来表达作者价值取向的极好例证。
在《四库全书总目》的子部总序中,总纂官纪昀通过说明子部各类的排序逻辑,表达了《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者的价值取向。该序言指出,“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唐、虞无皋陶,则寇贼奸宄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家。民,国之本也。穀,民之天也,故次以农家。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故次以医家。重民事者先授时……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百家方技,或有益,或无益……故次以术数。游艺亦学问之余事……故次以艺术。……博闻有取,利用攸资,故次以谱录。群言岐出,不名一类,总为荟粹,皆可采摭菁英,故次以杂家。隶事分类,亦难言也,归附于子部,今从其例,故次以类书。裨官所述,其事末矣……故次以小说家。……二氏,外学也,故次以释家、道家终焉”。这里,纪昀共用了十二个“次以”说明了子部各家文献的意义递减次序,足见其用心良苦。在上引子部“序”言中,从“儒家尚矣”到最后“释家、道家终焉”,实际上就是对各家文献之伦理教化价值的递减次序的界定,同时也是编纂者所代表的统治阶级价值取向的逻辑阐明。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中国古代的文献整理活动始终贯穿着一根“红线”,这一红线就是儒家伦理教化观念。文献整理活动中的立类及其次序安排,皆以其伦理教化价值的大小或轻重来选择和布局。儒家士人一以贯之地坚持伦理教化的意义,实际上就是为了实现其“三纲五常”之思想秩序。如果说,文献秩序只是一种“物”的秩序,那么,思想秩序则是一种“心”的秩序。然而,儒家士人“经世致用”的治学态度和“内圣外王”的人生追求,致使他们所极力宣扬的思想秩序观念,很容易被统治者所“收容”,最终为统治秩序服务。
三、统治秩序:秩序建构的最终目标
任何统治行为都需要被统治者思想的统一性或同质性,因为被统治者思想的统一性或同质性是统治合法性的根本来源。所以,任何统治者都需要建构一种思想秩序,以保证其统治秩序的长治久安。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对于建立儒家思想秩序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大都非常重视文献整理活动,为此不惜花费巨大人力物力。这也是中国古代官修史书、官修类书、官修目录传统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那么,古代官修史书、官修类书、官修目录等文献整理活动是如何体现为统治秩序服务的使命的呢?或者说,通过文献整理活动来建构统治秩序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呢?以下从三个方面予以论述。
1.总结经验——学习机制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不难发现,几乎每个朝代都在建立之初总结前朝覆灭的经验教训,以助巩固本朝政权。总结历史经验,无法通过“亲身经历”的途径去体会,而只能通过相关言传或文献阅读来思考和体悟。这种阅读和思考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当然,这种学习不仅仅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同时还要满足学习者增长知识、拓宽视野、陶冶情操的需要。这时,为了提高学习的效率和质量,专门编纂相关书籍供皇帝和其他人阅读是极其必要的。古代史书和类书的编纂活动就是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
唐开国之初,帝王及其周围的臣僚们非常重视总结前朝(隋朝)短命而亡的教训。据《旧唐书》记载,当时的秘书丞令狐德棻就向高祖李渊建议修史:“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李渊回应说:“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这说明李渊肯定了史书鉴往知来的社会作用。于是,仅唐代就修有《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共八部正史。武德五年(622年),欧阳询、令狐德棻、陈叔达等受诏撰《艺文类聚》,成书100卷,武德七年(624年)奏上。《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白氏六帖》合称“唐代四大类书”。
宋代开朝皇帝赵匡胤虽是武人出身,却十分喜欢读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周世宗曾经不解地问他:“卿方为朕作将帅,辟封疆,当务坚甲利兵,何用书为?”他的回答是:“……所以聚书,欲广闻见,增智虑也。”[15](P171)当然,作为皇帝,他们读书的目的决不仅仅局限于“增智虑”,而是要从中吸取历代统治者成败得失的经验和教训。赵匡胤之弟赵光义(宋太宗)继位后,对近臣说:“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代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15](P528)又说:“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15](P571)可见,两位兄弟皇帝的读书目的主要在于学习“为治之道”。宋太宗为此下诏李昉、扈蒙、徐铉、张洎等儒臣编纂宋代四大类书中的前三种:史类类书一千卷,书名《太平总类》;文章类类书一千卷,书名《文苑英华》;小说类类书一千卷,书名《太平广记》。在这三部类书中,宋太宗最喜欢《太平总类》,他“日览三卷”,用一年的时间读完全书,故改书名为《太平御览》。
到了明代,朱棣篡夺帝位,被方孝孺等士大夫们视为“大逆不道”。在这关键时刻,朱棣想到继承太祖编修一部大型类书的未竟之业。于是就在即位当年(1403年)七月,下令编纂《永乐大典》(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类书)。这样,一方面可以把士人集中起来,消弭朝野间的抗拒力量,达到笼络士人的目的;另一方面还可以炫耀文治,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对此有学者评论说:“明成祖朱棣在1402年篡夺了他的侄儿对明王朝的统治权,恐怕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不服,为了笼络他们,便在1403年(永乐元年)开始了《永乐大典》的纂修工作。由于他想广泛地进行笼络知识分子并夸耀文治,所以他对于这一纂修的内容,企图越丰富越好,卷帙的数目越能超越前人越好。”[16]在中国历史上,“每逢改朝换代或政治动荡之后,官方例有编撰类书之举……类书往往成为历代统治者粉饰太平的工具,有其明显的政治目的”[17](P469)。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中国历代当权者热衷于史书、类书的编纂,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学习“为治之道”。反过来说,学习“为治之道”的需要,导致了编纂史书、类书事业的兴盛。
2.宣扬“文治”——文化机制
北宋史学家宋敏求在《唐大诏令集》中引唐高祖言曰:“自古为政,莫不以学为先,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具备,故能为利博深。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唐太宗李世民在给大臣萧德言的信中说:“自隋季版荡,庠序无闻,儒道坠泥途,《诗》《书》填坑穽。眷言坟典,每用伤怀。顷年已来,天下无事,方欲建礼作乐,偃武修文。卿年齿已衰,教将何恃!所冀才德犹茂,卧振高风,使济南伏生,重在于兹日;关西孔子,故显于当今。令问令望,何其美也!”[18](P4952-4953)这说明,唐高祖、唐太宗开始重视“敦本息末”、“偃武修文”、“行先王之典训”之“文治”的重要意义。
熟谙“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道理的历代君臣们,在武力征讨天下取得胜利后,必然认识到文治的重要性,故欧阳修等人认为,“武为救世砭剂,文其膏粱欤!乱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是病损而进砭剂,其伤多矣!然则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盗,圣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创业,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举天下一之于仁义,莫若儒”[19](P5637)。明成祖朱棣为修《永乐大典》,命人“四出购求遗书”,并吩咐“书籍不可较价,惟其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朱棣编纂《永乐大典》,在全国搜购图书且不计价格,俨然一位爱文、崇文、欲大兴文治之君主,与以武力夺取皇位的朱棣相比判若两人。
另外,历代朝廷大兴编纂类书活动彰显文治,在客观上产生了笼络或收编知识分子,进而削弱其反思和反抗的意志的作用。宋人王明清在《挥麈后录》卷一中说:“太平兴国中诸降王死,其旧臣或宣怨言,太宗尽收用之,置之馆阁,使修群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之类。广其卷帙,厚其廪禄赡给,以役其心,多卒老于文字之间。”宋末元初学者刘埙在《隐居通议》一书中指出,“宋初编《文苑英华》之类,尤不足采。……其降臣聚朝多怀旧者,虑其或有异志,故皆位之馆阁,厚其爵禄,使编幕群书,如《太平御览》、《广记》、《英华》诸书,迟其岁月,困其心志,于是诸国之臣,俱老死文字间,世以为深得老英雄法,推为长策”。现代学者张涤华亦赞同刘埙的观点,他写道:“宋初削平诸僭,降臣聚朝,虑其才无所施,或怀怨望,于是丰其廪饩,使撰不急之书,困老英雄,允推长策。然则当时类书之盛,非特缘于学术风气,抑且有政治作用推移其间矣。……历代君主牢笼人才之法,大率如是,又不仅有宋为然矣。”20](P69)明代学者李晔在《紫桃轩又缀》卷二中说:“《永乐大典》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卷,一万一千九十五本……号召四方文墨之士,累十余年而就,亦所以耗磨逊国诸儒不平之气。”中国历史上修类书最多的皇帝是康熙。先修200卷的大类书《渊鉴类函》,修这部书设了4个总裁官,46个分纂官,15个校勘官,67个校录官,4个收掌官,共130多人。此书未修完,又接着修《佩文韵府》、《佩文韵府拾遗》、《骈字类编》、《子史精华》、《分类字锦》等。在此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参加到修书队伍中来,如王士禛、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何焯、王兰生等一大批具有显赫身份的知识分子都参与过编纂类书。让大批知识分子参与到繁重的类书编纂活动中来,“迟其岁月,困其心志,于是诸国之臣,俱老死文字间”,这种文治方法确实比文字狱方法“高明”多了。
用历史的眼光看,文治当然要比“武治”文明得多。但是,如果文治成为“文化专政”的代名词,那么,文治的历史进步意义就会一落千丈,反而成为历史进步的阻碍力量。所以,中国古代所谓“文治”背景下的文献整理活动,始终未能摆脱为统治阶级构建文化秩序服务的命运。
3.排除异己——排斥机制
纵观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的历史,不难看出,几乎所有的文献分类、文献目录和类书编纂活动在方法论上都始终贯穿着一种选择机制——选择符合统治集团伦理教化标准的类目名称、类目次序、收录原则、评价原则等。而那种真正贯彻“述而不作”原则的分类、目录、类书少之又少。有选择必然会同时产生“不被选择”的被排除者,所以,选择和排除是共生共存的“孪生体”。那么,在文献整理活动中,选择和排除的对象是什么呢?毋庸置疑,选择的对象是“同己”,排除的对象是“异己”。而判断是“同己”还是“异己”的标准就是统治集团的伦理教化旨趣,或者说是统治集团的统治秩序需要。
在类目体例安排上,给“经”以首要地位,选择“经”为纲,而其他为目。在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活动中,“以经为首”的原则成为自汉代《七略》至清代《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延绵两千多年不易的“永制”。
在类目次序安排上,以有利于维护统治秩序的伦理纲常为标准来选择性地安排其次第。这一点在上文中已有论述,这里再引述一段葛兆光的话作为补叙。葛兆光在谈到《艺文类聚》类目安排以及内容的取舍时说:“‘圣、贤、忠、孝、德、让、智’的排列次第暗示了基本道德的构成和伦理等秩的先后,对各种行为的褒贬与评骘,则表达了社会集体意识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力。那种社会秩序优先于个人自由、社会价值高于个人成就、他人评价优先于自我感觉的观念,不仅在古代中国由来已久,而且在这部类书的分类里也表现得相当清楚。”[9](P457)
在收录原则和评价原则上,以统治集团的善恶标准来决定去取并给予价值评价。宋真宗针对编纂《册府元龟》下诏曰:“今所修君臣事迹尤宜区别善恶,有前代褒贬不当者,宜析理论之,以资世教。”[15](P1452)后又强调“朕与此书,非独听政之暇,资于阅览,亦乃区别善恶,垂之后世。俾君臣父子,有所鉴诫”。上文所引《四库全书总目》凡例第十七则所云“今所采录,惟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狭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典型地说明了“纳同己,斥异己”的选择标准。更为明显的是,在编纂《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时还专门制定有《四库馆办违碍书籍条款》。该条款第八款规定,“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记载事迹,有用敌国之词,语句乖戾者,俱应酌量改正”。对此,鲁迅讽刺说:“‘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敌夷’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面,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21](P146)鲁迅的这段话虽非学术评断语,却也揭示了清朝统治者敏感于“种族思想”的心态。可见,那些宣传民族思想的“违碍书籍”是不可能不加“改正”而入选《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之收录范围的。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古代的文献整理活动并不是一种自主性活动,而是一种如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Foucault)所说的“话语事件”(discursive events)。这种话语事件必须在一定的规限之下展开,“排斥”(exclusion)就是话语规限方式之一。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们不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谈论任何东西,亦即在特定的场域(field)中,人们能谈论什么,不能谈论什么,这些都是被给定了的。话语(discurse)是一种展现秩序的符号系统,因而,作为话语事件的古代文献整理活动必须用“纳同己,斥异己”的排斥机制来保证话语秩序(即权力秩序)。
清人章学诚把中国古代编纂文献分类目录的要旨概括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古代无数学人为这种考辨事业倾注了无穷的心血,由此形成了贯穿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始终的一种独特“学统”——求得文献秩序所必须遵循的学术准则。然而,这种“学统”并不是自主和自足的,因为它还要遵循伦理教化的“道统”准则,即以儒家伦理纲常为准绳来整理文献。所以,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所产生的文献秩序实际上是一种伦理价值秩序——思想秩序。那么,这种思想秩序是自治和自足的吗?也不是,因为这种思想秩序还要接受“治统”的规限,即以维护统治集团的权力秩序为目标来整理文献。在这一连环序列中,“学统”受限于“道统”,而“道统”又被“治统”所规限。关于“道统”和“治统”,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二中有言:“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显然,在古代中国,无论“学统”和“道统”多么重要,都不允许从根本上颠覆“治统”的威权地位。当然,一些仁人志士以自己的“学统”和“道统”意志不屈不挠地反抗“治统”的威权地位,谱写出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悲壮曲目,但每一次抗争都必然遭到统治者的严酷镇压,其中既有公开的血腥镇压,也有隐蔽的“文治”性销蚀或消磨。中国古代统治集团利用文献整理活动来建构统治秩序,其隐蔽性和“文明性”可谓巧妙之极。“当你在你的公民头脑中建立起这种观念锁链时,你就能够自豪地指导他们,成为他们的主人。愚蠢的暴君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而真正的政治家则用奴隶自己的思想锁链更有力地约束他们。正是在这种稳健的理智基点上,他紧紧地把握着锁链的终端。这种联系是更牢固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做成的,而且我们相信它是我们自愿的结果。绝望和时间能够销蚀钢铁的镣铐,但却无力破坏思想的习惯性结合,而只能使之变得更紧密。最坚固的帝国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就建立在大脑的软纤维组织上。”[22](P113)《隋书·经籍志》在解释“经籍”时认为,“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黻黼,皆为治之具也”。如果说,经籍的功用在于“所以治国”、“为治之具”,那么,始终坚持“以经为首”原则的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自然也摆脱不掉“为治之具”的宿命。总而言之,通过“以经为首”的思想秩序来构建文献秩序,再通过这种文献秩序和思想秩序来为建构统治秩序服务,这就是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中蕴含的秩序建构逻辑。
注释:
①《七略·六艺略》名为“六艺”,但却列出了九类,即多出了论语、孝经、小学三类。之所以如此,清人王鸣盛(1722-1797)在《蛾术篇》卷一中解释道:“《论语》、《孝经》皆记夫子之言,宜附于经,而其文简易,可启童蒙,故虽别为两门,其实与文字同为小学。小学者,经之始基,故附经也。”王国维在《观堂集林·汉魏博士考》中也作了大体相同的解释,认为刘向、刘歆父子于五经之后,“附以《论语》、《孝经》、小学三目,六艺与此三者,皆汉时学校诵习之书”。
②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H.Spencer)在《教育论》一书中提出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他自己给出的答案是:科学知识最有价值。后来学者们把这一问题称为“斯宾塞问题”。参见斯宾塞:《教育论》,胡毅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第8、43页。
③据张涤华先生统计,自魏至清,历代史志书目和官私书目的类书达1035种。参见张涤华:《类书流别》,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页。
④我国古代类书大部分以“天→地→人→事→物”为类目次第,但个别类书除外,如我国最大类书《永乐大典》的编纂体例为“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
⑤“经济汇编”中的“经济”一词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economic)有较大区别,它包含“经国”和“济世”两方面的含义,所以经济汇编的子目包括:“选举典”、“铨衡典”、“食货典”、“礼仪典”、“乐律典”、“戎政典”、“祥刑典”、“考工典”。
标签:四库全书总目论文; 儒家论文; 艺文类聚论文; 文献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古今图书集成论文; 读书论文; 汉朝论文; 文化论文; 宋朝论文; 七略论文; 初学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