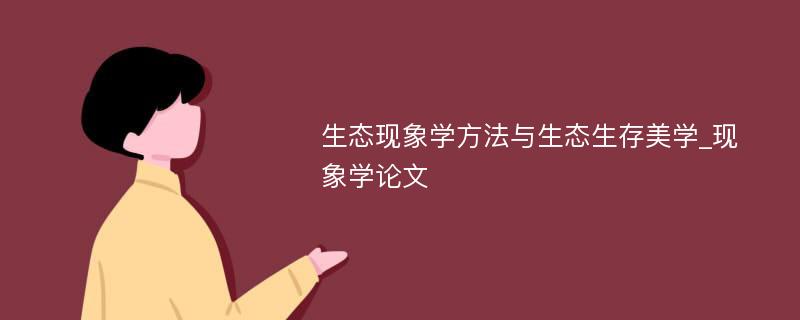
生态现象学方法与生态存在论审美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现象学论文,审美观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生态美学的基本范畴是生态存在论审美观,其所遵循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生态现象学方法。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1](P42) 这种方法就是通过对物质和精神实体的“悬搁”,“走向事情本身”,对事物进行“本质的直观”。将现象学方法运用于生态哲学与生态美学领域即成为生态现象学,生态现象学的最早实践者就是海德格尔,他早在1927年就在著名的《存在与时间》一书中运用现象学的方法,论证人的“此在与世界”的在世模式。但生态现象学的正式提出则是晚近的事情,2003年3月,德国哲学家U·梅勒在乌尔兹堡举行的德国现象学年会上作了“生态现象学”的报告。他说:“什么是生态现象学?生态现象学是这样一种尝试:它试图用现象学来丰富那迄今为止主要是用分析的方法而达到的生态哲学”。[2]对于生态现象学的具体内涵,我们尝试作这样几点概括:
第一,摒弃工具理性的主客二分、人与自然对立的思维模式,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与对自然过分掠夺的物欲加以“悬搁”。诚如梅勒所说:“比起一种为人类的自我完善和世界完善的计划的自然基础负责的人类中心论来说,生态现象学更不让自己建立在将自然和精神二分的存在论的二元论基础之上”;[2]第二,回到事情本身,首先是回到人的精神的自然基础,探寻人的精神与存在的自然本性。梅勒指出:“对于生态现象学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进一步规定这个精神的自然基础。”[2]第三,扭转人与自然的纯粹工具的、计算性的处理方式,走向平等对话的相互间性的交往方式。梅勒指出,在生态现象学道路上,“人们试图回忆起和具体描述出另外一种对于自然的经验方式,以及尝试指出,对自然的纯粹工具——计算性的处理方式是对我们经验可能性的一种扭曲,也是对我们的体验世界的一种贫化。”[2]第四,生态现象学只有在适度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正如梅勒所言,“只有当自然拥有一种不可穷竭其规定性的内在方面,一种谜一般的自我调节性的时候,只有当自然的他者性和陌生化拥有一种深不可测性的时候,那种对非人自然的尊重和敬畏的感情才会树立起来,自然才可能出于它自身的缘故而成为我们所关心照料的对象”。[2]第五,对自然内在价值的适度承认必然导致对自然的祛魅与对机械论世界观的批判与抛弃。梅勒指出:“对自然内在价值的承认首先是对那种通过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而发生的自然祛魅的一种批评。”[2]第六,生态现象学的提出与发展还可以导致将其与深层生态学的“生态自我”思想相联系。梅勒指出,“根据内斯,属人的他者与非人的他者是我们较大的社会自我与生态自我,因此,我自己的自我实现紧密不可分地、相互依赖地与所有他者的自我实现联系在一起:没有一个人得救,直到我们都得救”。[2]
由上述可见,我们只有凭借这种“生态现象学方法”才能超越物欲进入与自然万物平等对话、共生共存的审美境界。中国古代道家的“心斋”、“坐忘”,所谓“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还有禅宗的“悬搁”物欲、善待自然的“禅定”方法,所谓“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明镜本洁净,何处惹尘埃”等,也是一种古典形态的生态现象学,完全可以将其与当代生态学的建设结合在一起运用,使这种来自西方的理论方法更加本土化、民族化。
二
存在论与现象学是紧密相连的,生态现象学方法必然导向生态存在论审美观。而“生态论的存在观”是当代生态审美观的最基本的哲学支撑与文化立场,由美国建设性后现代理论家大卫·雷·格里芬提出,他从批判的角度提出“生态论的存在观”这一极为重要的哲学理念。这一哲学理念是对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当代存在论哲学观的继承与发展,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涵,标志着当代哲学与美学由认识论到存在论、由人类中心到生态整体以及由对于自然的完全“祛魅”到部分“返魅”的过渡。从认识论到存在论的过渡是海德格尔的首创,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提供了理论的根据。 众所周知,认识论是一种人与世界“主客二分”的在世关系,在这种在世关系中人与自然从根本上来说是对立的,不可能达到统一协调。而当代存在论哲学则是一种“此在与世界”的在世关系,只有这种在世关系才提供了人与自然统一协调的可能与前提,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这种“主体和客体同此在和世界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1](P70)这种“此在与世界”的“在世”关系之所以能够提供人与自然统一的前提,就是因为“此在”即人的此时此刻与周围事物构成的关系性的生存状态,此在就在这种关系性的状态中生存与展开。这里只有“关系”与“因缘”,而没有“分裂”与“对立”。“此在”存在的“实际性这个概念本身就含有这样的意思:某个‘在世界之内的’存在者在世界之中,或说这个存在者在世;就是说:它能够领会到自己在它的‘天命’中已经同那些在它自己的世界之内向它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缚在一起了”。[1](P65~66)海德格尔又进一步将这种“此在”在世之中与同它照面并“缚在一起”的存在者解释为是一种“上手的东西”,犹如人们在生活中面对无数的东西,但只有真正使用并关注的东西才是“上手的东西”,其他则为“在手的东西”,亦即此物尽管在手边但没有使用与关注,因而没有与其建立真正的关系。他将这种“上手的东西”说成是一种“因缘”,并说“上手的东西的存在性质就是因缘。在因缘中就包含着:因某种东西而缘,某种东西的结缘”。[1](P98)这就是说人与自然在人的实际生存中结缘,自然是人的实际生存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然包含在“此在”之中,而不是在“此在”之外。这就是当代存在论提出的人与自然两者统一协调的哲学根据,标志着由“主客二分”到“此在与世界”以及由认识论到当代存在论的过渡。正如当代生态批评家哈罗德·弗洛姆所说,“因此,必须在根本上将‘环境问题’视为一种关于当代人类自我定义的核心的哲学与本体论问题,而不是有些人眼中的一种围绕在人类生活周围的细微末节的问题”。[3](P38)
“生态论的存在观”还包含着由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整体过渡的重要内容。“人类中心主义”自工业革命以来成为思想哲学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一时间“人为自然立法”、“人是宇宙的中心”、“人是最高贵的”等思想成为压倒一切的理论观念,这是人对自然无限索取以及生态问题逐步严峻的重要原因之一。“生态论的存在观”是对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扬弃,同时也是对当代“生态整体观”的倡导。当代生态批评家威廉·鲁克尔特指出,“在生态学中,人类的悲剧性缺陷是人类中心主义(与之相对的是生态中心主义)视野,以及人类要想征服、教化、驯服、破坏、利用自然万物的冲动”。他将人类的这种“冲动”称作“生态梦魇”。[4](P113)冲破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梦魇”而走向“生态整体观”的最有力的根据就是“生态圈”思想的提出。这种思想告诉我们,地球上的物种构成一个完整系统,物种与物种之间以及物种与大地、空气都须臾难分,构成一种能量循环的平衡的有机整体,对这种整体的破坏就意味着危及到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的发生。从著名的莱切尔·卡逊到汤因比、再到巴里·康芒纳都对这种“生态圈”思想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康芒纳在《封闭的循环》一书中指出,“任何希望在地球上生存的生物都必须适应这个生物圈,否则就得毁灭。环境危机就是一个标志:在生命和它的周围事物之间精心雕琢起来的完美的适应开始发生损伤了。由于一种生物和另一种生物之间的联系,以及所有生物和其周围事物之间的联系开始中断,因此维持着整体的相互之间的作用和影响也开始动摇了,而且,在某些地方已经停止了”。[5](P7)由此可知,一种生物与另一种生物之间的联系以及所有生物和其周围事物之间的联系就是生态整体性的基本内涵,这种生态整体的破坏就是生态危机形成的原因,必将危及人类的生存。
按照格里芬的理解,生态论的存在观还必然地包含着对自然的部分“返魅”的重要内涵,这就反映了当代哲学与美学由自然的完全“祛魅”到对自然的部分“返魅”的过渡。所谓“魅”乃是远古时期由于科技的不发达所形成的自然自身的神秘感以及人类对它的敬畏感与恐惧感。工业革命以来,科技的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人类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能力,于是人类以为对于自然可以无所不知,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借助于工具理性的人类对自然的“祛魅”。正是这种“祛魅”成为人类肆无忌惮地掠夺自然从而造成严重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诚如格里芬所说,“因而,‘自然的祛魅’导致一种更加贪得无厌的人类的出现:在他们看来,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占有,因而他们越来越噬求得到超过其需要的东西,并往往为此而诉诸武力”。他接着指出,“由于现代范式对当今世界的日益牢固的统治,世界被推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这种情况只有当我们发展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伦理学之后才有可能得到改变。而这就要求实现‘世界的返魅’(the reenchantment of the world),后现代范式有助于这一理想的实现”。[6](P221)当然,这种“世界的返魅”绝不是恢复到人类的蒙昧时期,也不是对工业革命的全盘否定,而是在工业革命取得巨大成绩之后的当代对于自然的部分“返魅”,亦即部分地恢复自然的神圣性、神秘性与潜在的审美性。只有在上述“生态论存在观”的理论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建立起当代的人与自然以及人文主义与生态主义相统一的生态人文主义,并成为当代生态美学观的哲学基础与文化立场。正因此,我们将当代生态美学观称作当代生态存在论美学观。
上面说到的“生态存在论”的“此在与世界”的在世关系解决了生态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性问题,但生态性又如何与审美性相统一呢?为什么说生态存在论哲学观同时也是一种美学观呢?在存在论哲学中,美的内涵与传统的认识论美学中作为“感性认识完善”的美学内涵已大不一样——它的美的内涵已经与真、存在没有根本的区别,而是紧密相联。所谓美就是存在的敞开与真理的无蔽。海德格尔指出“美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7](P276)对此还进一步举例解释道:“在神庙的矗立中发生着真理。这并不是说,在这里某种东西被正确地表现和描绘出来了,而是说,存在者整体被带入无蔽并保持于无蔽之中。”[7](P276)在这里,海氏所说的是不同于通常的“比例、对称与和谐”的一种别样的“美”。这种美不是认识的美,不是对事物正确表现和描绘的美,而是一种“生态存在”之美,是真理的敞开、存在的显现。海氏以古希腊神殿为例说明这种别具特点的“生态存在”之美。他说,这个神殿素朴地置身于巨岩满布之中,包含着神的形象,神殿无声地承受着席卷而来的风暴,岩石的光芒是太阳的恩赐,神殿的坚固与泰然宁静则显示出海潮的凶猛,与神殿密不可分的树木、草地、兀鹰、公牛、蛇和蟋蟀也显示出自然的本色,这就是“大地”,人赖以乐居之所,也是万物涌现返身隐匿之所,从而大地成为人与万物的“庇护者”。正是在“大地”之上,神殿嵌合包括人在内的一切,构成一个统一体,并由此演绎出一幕幕人类的活剧,从而真理敞开,存在显现。“诞生和死亡,灾祸和福祉,胜利和耻辱,忍耐和堕落——从人类存有那里获得了人类命运的形态。这些敞开的关联所作用的范围,正是这个历史性民族的世界。出自这个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这个民族才回归它自身,从而实现它的使命。”[7](P262)由此,神殿由其所屹立的大地构成的天、地、人、万物与千年历史的独特的“世界”在其敞开中所显示的是希腊人千年的悲欢离合、整个民族起伏跌宕的历史及其不同寻常的命运。这就是一种真理显现、存在敞开之美,就是“生态存在”之美。但如果将神殿搬离其千年屹立的岩石,离开这长久呼吸与共的“世界”,被安放在博物馆和展览厅里,这种“生态存在”之美将不复存在。在此,生态性、人文性与审美性就在这种“此在与世界”的在世结构中得以统一。可见,“此在与世界”的在世结构成为生态存在论美学的关键与奥秘所在。其实,马克思在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论述的“美的规律”就是人与自然以及人文观、生态观与审美观的统一。因为,“美的规律”涉及到了三个层面内在统一的问题。首先是“内在的尺度”,主要讲的是人的需要,属于人文观的范围;其次是“物的尺度”,主要讲的是物种的需要,是生态观的范围,而两者的统一则是“美的规律”,属于审美观的范围。这实际上是人文观、生态观与审美观的统一,包含着浓郁的生态美学意蕴。
三
生态现象学之所以与生态存在论审美观紧密相连,是因为现象学方法与美学是相通的。胡塞尔指出,“现象学的直观与‘纯粹’艺术中的美学直观是相近的”。又说,艺术家“对待世界的态度与现象学家对待世界的态度是相似的”。[8](P1203)这就是说,现象学通过“悬搁”的“意向性”途径回到“现象”本身的方法,与审美的摆脱客体与主体的艺术直观是相近的。在这里,点明了现象学的“现象”与审美的“经验”的相通性。而生态存在论美学观的产生则与现象学的第二阶段紧密相关。所谓现象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就是1927年左右产生的“相互主体性”阶段。胡塞尔在《笛卡尔的深思》与海德格尔在《存在于时间》中提出“相互主体性”论断。胡塞尔指出,“一门完整的先验现象学显然还包含着由先验唯我论通向先验交互主体性的进一步途径”。[8](编者引论,P17)而海德格尔则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人与世界的“此在与世界”的关联性关系。先后克服唯我论,走向人与自然万物的平等对话。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下生态现象学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态审美观才有产生的可能。
生态现象学以及生态审美观最重要的美学范畴即为“家园意识”。海德格尔早在1927年就在《存在于时间》中提出,“我居住于世界,我把世界作为如此这般熟悉之所在而依寓之、逗留之”。[1](P63~64)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则将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比喻为家庭内部的母子、夫妻之间的关系。他说,人对自然的审美关系“就是一种隐藏着的力量、盖亚、母亲,也是召唤丈夫的妻子”。又说,“人类只因为自己是自然的产品、自然的儿子,才是这个自然的关联物”。[9](P7)这其实是通过现象学方法对长期占据压倒地位的科学主义与自然人化说“悬搁”的结果。海德格尔将失去家园的“无家可归”看作是科学主义盛行的情况下人之“在世”的基本方式。他说,“无家可归指在世的基本的方式,只是这种方式日常被掩盖着”。[1](P318)他的审美的“家园意识”的提出就是对这种工具理性过度膨胀情况下的“无家可归”意识与情形的否弃。而杜夫海纳则对自然自身的审美表现力给予了肯定,并对资本主义工业化之中的“人化自然论”给予了批判。他说,“不管自然人化与否,只要它是具有表现力的又是自然的时候,它就成为审美对象”。又说,在科技主义盛行的情况下人对自然是一种技术的态度,“这技术的态度恰恰不是艺术性的技术态度而是工业的态度。工业对自然使用暴力,把思想上所想要的形式与功能强加给自然,而不是按照物质的启示和根据动作的自发性行事”。[9](P58,注1)
在这里,“家园意识”还意味着对一切传统哲学与美学观念的“悬搁”与否弃。首先当然是对传统的实体性美学的“悬搁”与否弃。因为,“家园”表明人与自然是一种“在家”的“关系”,不存在实体性物质性的自然之美,也不存在实体精神性的自然之美,自然之美是一种关系中的美。诚如杜夫海纳所说,自然之美是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之美。他说,“自然之所以能从审美的角度去看,那是因为它能从文化的角度去看”。[9](P43)这种文化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一种“在家”的关系。“家园意识”是对人与自然“疏离性”的一种“悬搁”与否弃,也是走向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众所周知,工业革命时期人类中心主义盛行,人对自然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改造”、甚至“阉割”的态度,人与自然是疏离的,甚至是对立的。海德格尔将这种情况比喻为人类在工具理性“促逼”下的“订造”,给予了严厉的批判与否定。他说,“这片大地上的人类受到了现代技术之本质连同这种技术本身无条件的统治地位的促逼,去把世界整体当作一个单调的、由一个终极的世界公式来保障的、因而可计算的储存物(Restnd)来加以订造”。[10](P221)海德格尔生态审美观中“家园意识”的提出就是对这种工具理性的促逼与订造理论的“悬搁”与否弃,并提出著名的人与自然亲密无间的“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深刻地阐述了其中所包含的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内涵。他说,“命运使四方进入其中从而取得自身,命运保存四方,使四方开始进入亲密性之中”。[10](P221)“家园意识”也是对“比例、和谐、对称”等物质的无机之美的适度悬搁与否弃。众所周知,古代希腊强调一种物质自身的比例、和谐与对称等无机之美;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则将这种物质的无机之美称作是一种“浅层次的美”,而更加赞成一种与“生命价值”有关的“深层含义”的美。著名加拿大环境美学家卡尔松(Allen Cartson)转述了霍斯普斯(John Hospers)将美分为“浅层含义”与“深层含义”的观点。他说,“霍斯普斯描述它作为‘审美’的‘浅层含义’与‘深层含义’的区分。当我们审美地喜爱对象时,浅层含义是相关的,主要因为对象的自然表象,不仅包括它表面的诸自然特征,而且包括与线条、形状和色彩相关的形式特征。另一方面,深层含义,不仅关涉到对象的自然表象,而且关系到对象表现或传达给观众的某些特征和价值。普拉尔称其为对象的‘表现的美’,以及霍斯普斯谈到对象表现‘生命价值’”。[11](P206~207)卡尔松举出了塑料树的例子加以说明,他说塑料的树可能是完美的复制品,非常类似于真正的树,但它最终在审美上不被接受,“主要因为它们不表现生命价值”。[11](P213)由此说明“生命力”被引入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领域,恰是生态现象学介入的结果。这种作为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中的“生命力”因素的另一个例证是,20世纪70年代大气化学家拉夫洛克(James E.Lovelock)提出著名的“盖亚定则”,以希腊神话中的地母盖亚比喻地球母亲,提出地球通过植物与阳光的光合作用产生营养,哺育万物,地球是有生命的,是有着新陈代谢功能的,保持地球的生命健康是人类和万物得以繁茂的前提。这种“盖亚定则”也被称作“地球生理学”,成为当代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重要理论支撑。
总之,现象学方法是20世纪以来用以“解构”工业化以来主客二分思维模式蔓延与工具理性膨胀的主要途径,带来了哲学与美学领域的革命。从本质上来说,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庸俗唯物主义的批判是相通的,其“生活世界”的理论难以摆脱唯心主义的弊端,但其革命性的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而生态现象学则带来了对“人类中心主义”与“艺术中心主义”的解构和生态存在论审美观的建立,一系列新的美学观念应运而生,是美学领域的一场革命。我们将以此迎来新的生态文明时代,并将使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在新的时代发挥有助于人们确立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自然环境的作用。
收稿日期:2010-12-10
标签:现象学论文; 存在论论文; 审美观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美学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人与自然论文; 哲学家论文;
